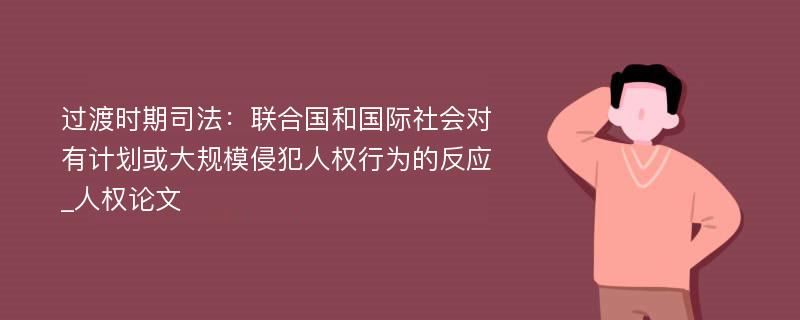
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人权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司法论文,性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0.01.061
2004年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名为《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联合国在促进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司法和法治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为了理解国际社会在加强人权、使个人免于恐惧和贫穷、解决财产争端、鼓励经济发展、促进负责治理以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努力,‘司法’、‘法治’和‘过渡司法’这样的概念非常重要”[1]5。相对于“司法”和“法治”,“过渡司法”是其中较为新颖和陌生的概念,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过渡司法”译自英文transitional justice,它是近年来学界和日常政治中的一个流行话语。截至2009年2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过渡司法数据工程”收录的相关文献已达2300多份[2]。2001年,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过渡司法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简称ICTJ)成立,专门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与实践。2007年3月,《国际过渡司法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正式创刊,成为该领域的第一本国际性学术杂志。本文将首先探讨过渡司法的产生背景及其中文译法,然后重点介绍过渡司法的具体机制,最后对过渡司法的实践和理论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总结。
一、过渡司法的产生背景及其中文译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幅全球性的政治景观:二十年间有几十个国家从非民主体制过渡为民主体制,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时,随着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的出现以及美国卡特政府“人权外交”的推行,“人权”逐渐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词汇之一。在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政府必须向人民兑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承诺,即与过去的所谓威权政府不同,否则其正当性就无从谈起。然而,过去的所谓威权政府的势力仍然掌控着重要的权力资源,随时可能重新颠覆新生的民主。孱弱的民主政府于是陷入了一种困境:究竟是应该听取民众的呼声,揭露真相并且惩治罪犯,还是应该屈从于前政府的要求,对过去的罪行给予豁免?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的“虐待者的难题”[3]264-285。不同国家针对这一难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马克·阿姆斯图茨(Mark Amstutz)看来,这些方式在“抵赖”(denial)与“问责”(accountability)之间呈现出光谱式排列:遗忘—赦免—宽恕—真相—赔偿—清洗—审判[4]17-18。
1995年,美国和平研究所学者内尔·克里兹(Neil Kritz)主编的三卷本著作《过渡司法:新兴民主如何面对旧体制》出版,该书第一次用“过渡司法”来指涉民主政府处理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种种方式[5]。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之后,战争和国内武装冲突越来越受关注,这一概念又被用来指战争、冲突结束后,或者国家转型后,如何在重建和平、追求和解的过程中追究过去的各种暴行。由于政治状况的变化,当前国际上对过渡司法的关注更多的是以这种“冲突对和平”的范式进行的。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
Transitional justice有多种译法,联合国的文件一般将其翻译为“过渡司法”、“过渡时期司法”,我国台湾地区通常译为“转型正义”,日本则译为“移行期正义”,另外还有“转型期正义”、“变迁中的正义”等。这些译法上的差异大致源于两个方面:第一,语言本身的客观原因,由此而来的差异可称为消极差异。英文的justice在中文里同时有正义、司法、审判、法院、法官等多种含义,而且这些意思很难分开,但是它们在中文里却有很大不同。而transitional既可以形容事物本身正在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如transitional society(转型社会),也可以形容产生或存在于某种转变时期内的尚未固定的事物,如新闻中经常出现的transitional government(过渡政府)。这给中文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上述各种译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transitional justice的意思,但也都难以完整体现其在英文中的含义。
第二,译者主观的原因,由此而来的差异可称为积极差异。对于联合国而言,它一方面要在国际间倡导正义、人权等普遍价值,以求在各种文明与意识形态中间达成“重叠共识”;但在开展具体的日常工作时,它又必须尽量避免使用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采取更为具体和中性的话语,在不得不使用诸如justice一类话语的时候,它就必须用共同的语言将其具体化,促使各国在一个抽象程度相对较低的层面上达成“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①。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联合国将transitional justice界定为“进程和机制”,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国译员会将其翻译成“过渡司法”。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受其历史经历和政治生态的影响,这一概念被寄托了太多的抱负和希望,进而被译为宏大的“转型正义”,这本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转型正义是一个可以激发无限憧憬的词汇,而深谙选举政治的台湾民进党人想必对勒庞的话烂熟于胸:“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6]150为准备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突然对“转型正义”大肆炒作,从“没收国民党党产”到“去中国化”,大凡可以打击竞选对手的话题,都被包装成神圣而摩登的转型正义。由于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是出于对受迫害者的真正同情和负责,结果反而使大家产生嫌恶排斥情绪,以至最初系统地引介相关理论的吴乃德都感慨“所有好东西在台湾都变了样”[7]。
可见,transitional justice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暗示性。抽象地说,它的诸多译法无所谓对错,正如苏力所言,“一个制度或一个人并不因为有什么名号而高贵起来或堕落下去,其高贵或堕落全在于它或他或她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的对人或人们的实际作用”[8]。
二、过渡司法的机制
根据安南在前述报告中用“共同语言”所作的界定,过渡司法“包含与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努力的所有相关进程和机制”[1]5。这一定义认为,这种进程和机制既可以是司法性质的,也可以是非司法性质的,其中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该报告还强调,在进行过渡时期司法活动时,“战略必须是全面的,包括兼顾起诉个人、赔偿、寻求真相、改革机构、审查和革职的问题,或这些行动的任何适当组合”[1]9。
(一)刑事诉讼
以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战争或暴政元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4世纪就已出现过对战犯的审判,审判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更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以当代的人权视角来看,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无疑是过渡司法的典范。通过法院实现正义,这是以人权活动者和法律专家为代表的守法主义者不懈的追求②。史蒂芬·兰德斯曼(Stephan Landsman)认为,以刑事诉讼来回应暴行至少存在六个优点:第一,通过诉讼将加害者绳之以法,有助于在民众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而促进法治的建立,而法治正是确保民主与和平的关键;第二,诉讼具有教育功能,民众可以在审判过程中了解暴行的性质与程度,既有助于培育民众对暴行的道德反感,又能留下准确的历史记录;第三,诉讼是认定受害者、制定补偿方案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第四,诉讼使报应成为可能,可以缓解私人的复仇欲望;第五,诉讼具有威慑作用,有助于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悲剧;第六,诉讼是治愈社会创伤的基础,人们经常念叨不能惩罚的就是不能宽恕的③,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诉讼就是恢复社会和谐的第一步[9]83-84。
然而,在政治现实主义者看来,进行刑事诉讼却是民主、和平、和解等目标的障碍。亨廷顿曾针对民主过渡总结了六种反对诉讼的理由:(1)民主必须建立在和解的基础上;(2)民主化的进程需要各社会团体达成谅解,而不是宣泄私愤;(3)在许多情况下,反对派与政府军都严重地侵犯过人权,大赦会为民主提供一个比惩罚更为坚实的基础;(4)威权政府官吏的罪行在当时具有正当性,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5)社会中的许多人或团体都参与了威权政权的罪行,没有一个人只是其受害者,大家都应对此负责;(6)大赦是夯实民主的必要步骤,即便有充分的法律或道德理由去惩治那些人,这种理由也会在稳定民主这一道道律令面前瓦解,民主巩固应该优先于对个人的惩罚[3]267-268。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各种武装冲突中,惩罚与赦免也是影响停火谈判的重要议题,类似的理由仍然屡见不鲜,只不过在这里将民主换成了和平。
不仅如此,以刑事诉讼来处置暴行甚至也不能让极端的守法主义者满意,其表现正如荷兰法官洛林在东京审判中的矛盾心态。洛林一生都对审判的全部目的和公正性保持赞许的态度,但却在很多方面对判决持保留意见[10]432。众所周知,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对其溯及既往、有选择性和高度政治化等的质疑在此类审判中不绝于耳[11]25-51。究其原因,是由于系统性的侵犯人权毕竟不同于普通犯罪,其令人发指的性质和罄竹难书的规模使法律在它面前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米莉亚·沃克曼(Miriam Aukerman)所言,将大规模暴行理解为犯罪当然是最好的类比方式,但也只能是一种类比[12]96。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以及其他此类审判暴露出的道德与法律的两难成为二战后法理学复兴的重要契机:拉德布鲁赫、哈特和富勒等人在“告密者案件”中的你来我往,就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试图对这一困境的化解。
今天,在过渡司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法律与道德不再是最棘手的问题,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尊重人权和人性的原则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通过诉诸国际法即可在逻辑上消解两者之间的紧张。但另一方面,来自现实政治的阻力却不可能像二战后那样可以通过盟军的武力予以清除。1991年,尼诺与美国国际法学者迪亚娜·奥伦特利切(Diane Ortenlicher)之间的一场论战,就充分展示了国际法下追惩暴行的义务与国内政治情境之间的张力④。
(二)真相委员会
真相委员会是过渡司法中最具特色的机制,它一般是指由某国官方设立的非司法性质的临时性事实调查机构,负责调查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侵犯人权或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⑤。这是因为在有些国家中,长期的集体暴力和政治宣传势必在冲突各方之间形成一种敌对意识,各自都把自己想象为受害者,进而形成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和历史认知,严重阻碍社会关系的重建。以官方委员会的方式来澄清真相,有助于建立一种为各方都认可的、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记录,进而消弭双方的隔阂,终结“观念中的战争”。自1974年乌于达成立失踪人士调查委员会以来,世界上已出现过近四十个真相委员会。
历史上,国际人道法曾规定家属有了解其亲属命运的权利,冲突各方有搜寻失踪人员的义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拉美国家的军人政府普遍采用强制失踪的手段镇压异见人士,这一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以阿根廷为例,在近八年的军人专政中,有不下一万人“被失踪”;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后,立即成立了旨在调查失踪者下落的“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最终确认了8960名失踪者的下落,但并未提及加害者。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本是针对该国暴行的性质和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处理机制,但此后被其他国家有意识地当做诉讼的替代机制。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几乎完全移植了阿根廷的模式,用总统埃尔文的话说就是获得“所有的真相以及尽可能多的正义”[13]313。
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后,全面考察了各国在处理暴行方面的经验,最终决定在“纽伦堡模式”和“全民遗忘”之外另开第三条道路——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TRC)。南非的TRC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真相换赦免,或者说赦免换真相。为了全面掌握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种种罪行,同时又不伤害和解的进程,TRC一改无条件大赦的模式,实行一种有条件的赦免:凡是在法定期间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罪行的个人,只有在披露事实的全部真相并经审定后,才能获得赦免令。第二,受害者本位。TRC与刑事诉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旨在查明加害者的罪行,更是要为受害者提供一个公共平台,让受害者通过诉说真相的方式释放内心的悲痛,恢复其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TRC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受害者及其家属制定赔偿计划,但该计划最终未能彻底落实。第三,通过真相实现和解。不同于其他单纯以澄清真相为目标的真相委员会,TRC从一开始就被寄托了和解这一目标,进而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典范。此外,由大主教图图担任TRC的主席,也反映出TRC对宽恕、和解等心理因素的重视,因为图图始终大力倡导黑人的仁爱精神(Ubuntu),对TRC的运作起到了重要影响[14]。
TRC让世人进一步认识了真相委员会的功能,比起个案审判,它不仅可以更完整地展现历史的全景图,而且更关注受害者的感受,更注重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未来的繁荣。不过,它也绝非尽善尽美。在南非,有些白人就认为TRC是一种政治迫害;而守法主义者指责TRC是以和解为名对暴徒给予明目张胆的赦免;受害者代言人则认为过分强调宽恕给受害者造成了不应有的压力[15]93-96。此外,尽管TRC为南非和解之路开了一个好头,但和解绝非朝夕之事,也绝非TRC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种族歧视的阴影至今未能消除,各种族之间仍有诸多嫌隙⑥。一般认为真相委员会绝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机制,也并不是次优选择,它与起诉、赔偿等机制相互补充,各自都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16]104。
(三)赔偿
在国际法上,赔偿的历史和战争一样悠久。但过渡司法中的赔偿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赔偿,其对象是受害人及其亲属或继承人。1952年,联邦德国政府给予纳粹灭绝政策和集中营生还者的赔偿是其最初尝试。国外学者往往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赔偿这一概念。根据《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赔偿包括五种形式: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满足、保证不再发生,每种形式下又有若干具体内容,几乎涵盖了过渡司法的所有机制⑦。虽然赔偿的准确定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主导精神应是一切从受害者角度出发,向为数众多的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弥补,以满足他们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并避免悲剧的重演。狭义的赔偿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实质性赔偿,如复权(rehabilitation)、恢复职务、返还原物、经济补偿等;二是象征性赔偿,如官方道歉、设立哀悼日、建造纪念碑等。
赔偿在处理暴行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过渡司法的诸多机制中,能给受害者带去直接利益的只有赔偿,赔偿是承认受害者遭遇、恢复尊严、改善境遇、实现和解的重要环节。其次,赔偿还有重要的政治蕴含。璐蒂·泰铎(Ruti Teitel)认为,在过渡司法的情境中,赔偿的正当理由主要不是传统的矫正正义,而是政治价值,其道德上的象征意义远甚于对物质损失的弥补。赔偿一方面表明政府承担了过去遗留的义务,因而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者;另一方面又表明政府对暴行的彻底否定,确证了与过去不一样的价值观,如此可以实现决裂与继承这两个看似不可兼得的目的[17]146-147。
对赔偿在道德上的争论相对较少,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过渡司法有别于民事侵权制度中“加害者—受害者”的对称结构,所以责任的认定与救济的实施是两回事,有可能提供救济的几乎都不是对暴行负有责任的政府。由此而来的争论是,让无辜者为他人的罪行买单,让后代为前人的罪恶负责,这在道义上正当吗?除此之外,诸如赔偿的对象、赔偿的损害种类、损害的量化、赔偿金额的分配等等,都是难以认定的问题。
(四)机构改革和人事审查
改造公共机构,进行人事审查,是过渡司法的另一重要机制。这里的机构改革主要是指对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的改革。允许这些机关垄断暴力的原初意图是让其捍卫人权,然而,在那些饱经创伤的国家,这些公共机构要么因欠缺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不能切实履行其职责,要么直接变成侵犯人权的工具,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造。机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但由于机构的行为只能通过其成员实施,其最终责任也只能落实到个人;而以机构名义实施的暴行通常也源于其成员的恶意,因此,任何有效和长久的机构改革进程,其核心部分都是人事改革。人事改革的方式主要是审查(vetting),它是指对机构成员的操守(integrity)进行评估,以决定其是否适合担任公职。所谓操守,主要是指职员对国际人权标准的遵守情况、职业行为以及个人的财务状况[18]5。
机构改造与人事审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中就曾提到,“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不过,这一措施在实践中却经常被滥用,招致非议最多的就是一些东欧国家在剧变后实施的清洗法(lustration law)。东欧各国清洗的范围和程度各不相同。以较为温和的波兰为例,它最初试图效法西班牙,欲以“粗线条”的方式来处理历史问题,但议会仍在1997年通过了清洗法,规定任何参与竞选或谋求官职的人员,都必须发表声明以澄清自己是否有过与秘密警察(secret police)合作的历史。其声明有专门的清洗法院进行核实,一旦发现造假,十年之内禁止担任公职,并有可能以伪证罪受到指控。2007年,波兰议会又对清洗法进行了增补,根据修正后的法案,大约30万人必须向当局书面汇报是否曾为旧政府的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在波兰保守派政府领导人卡钦斯基兄弟看来,迄今为止,过去的共产党员、腐败的经济界人士以及曾经的合作者共同组成的“灰色网络”,还在掌控着波兰这个国家,从而导致了波兰社会的混乱。波兰学者奥夏滕斯基(Wiktor Osiatynski)评论说:“在今天的波兰,清洗已不仅是复仇手段,还变成了政治工具,与共产党的历史和解完全是两码事。”[19]而清洗法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理由主要有:(1)违背无罪推定的原则;(2)被审查者的上诉权非常有限,侵犯了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3)溯及既往;(4)引入了集体犯罪,许多人被革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是某组织的成员或者在档案中出现过他们的名字;(5)缺乏充分的调查取证,过分依赖秘密警察档案来决定人们的命运;(6)侵犯了个人的工作权、不受歧视待遇等基本人权[20]110-111。
为了避免以保障人权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联合国特别强调审查工作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尤其是要向被审查者提供申辩和救济渠道,例如被审查人有权获知被审查的事由,有提出抗辩的权利,有权向法院或其他机构就不利本人的裁判提出上诉等等。安南认为,这些正当程序的内容“使正式的审查进程有别于某些国家的大批清洗做法,后者不是根据个人记录,而是根据所属党派、政治观点,或与前国家机构的联系而大规模革除人员和剥夺任职资格”[1]17。
三、对过渡司法的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分析和总结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界对过渡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相关文献层出不穷,以至有学者在1998年就迫不及待地宣称:“一门全新的学科——过渡司法比较研究已经诞生”[21]283。对这一所谓“新的学科”,笔者有以下几点分析和总结:
第一,按照俞飞博士的术语,过渡司法涉及三种情境:民主转型、和平转型以及历史转型⑧。笔者认为,这三种情境尽管形态各异,但之所以都被统摄到过渡司法的概念之下,乃是因为它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对象:系统性或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因此,就其核心意义而言,过渡司法就是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⑨。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指明其丰富多彩的外延及其回应方式,而这也正是其引发争议的关键。不过,它首先明确了过渡司法的对象和范围,即它既不是毫无原则的政治清算,也并非与老牌民主国家绝缘。其次,它意味着过渡司法具有常态性和普遍性。璐蒂·泰铎认为,由于战争和暴力冲突时常发生,对暴行的处理已成为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它不断通过国际法的形式予以扩张和规范化,过渡司法逐渐成为定态(steady-state)[22]89-92。最后,尽管不存在统一的回应模式,但是回应(response)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基本的道德态度:人们有责任(responsibility)去对暴行作出积极的反应,而不是无动于衷⑩。
第二,过渡司法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事实上,过渡司法是在把握有关国家千差万别的实践基础上归纳出的一个概念,其理论精髓不在于提出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特殊的正义/司法理念,而是要提供一种方法论,以调和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进而在问责、真相、民主、和解等价值之间达至平衡。纵观全球过渡司法的实践,守法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并存与拉锯是其最大特色。虽然刑事诉讼备受法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推崇,但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并没有发生有效的惩治事件。在那些1990年前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只有在希腊有一大批威权政府的官员受到了实质性的审判和处罚”[3]268。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刑事手段追究暴行元凶的尝试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1998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前往英国就医,西班牙法院就对其发出传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普遍管辖”的概念由此受到极大关注。2005年,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当初的赦免法违宪,联邦法院开始重新受理过去的侵犯人权案件。更重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终结,二战后的国际法庭模式重新获得生机,并呈现出多种形式,包括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两个特设法庭,在塞拉利昂、柬埔寨、波黑、东帝汶、科索沃、黎巴嫩等地设立的各种混合刑事司法机构,以及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
尽管如此,正如安南所说,“在冲突后国家中,绝大多数严重侵犯人权和犯有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的行为人最终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永远不会受到审判”[1]15。他同时还强调:“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过渡司法不仅是法院和法庭的问题。为应付冲突后环境的挑战,必须采取一种能在诸多目标之间实现均衡的方法,其中包括追究责任、真相与赔偿、保全和平以及建立民主和法治。”[1]9即便是坚定的守法主义者,如今也承认“对严重侵犯人权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办法。遭受过这种侵犯的每个社会的独特历史经验必然影响其公民对司法的理解”(11)。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过渡司法有着极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不管对transitional justice进行何种翻译和诠释,这一概念强调的都不是一种绝对的、“在那里”的正义理念,也不是一种新颖的或一以贯之的司法模式。所以,我们要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在各国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领悟和反思历史上存在过、今后仍有可能发生的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本质;要在全面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去协调和追求人类共同的各种道德标准。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基于国际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和人权观,进一步研究过渡司法的理论、实践及其机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0-01-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05-25
注释:
①关于“重叠共识”与“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的区别与联系,可参见[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胡爱平、高建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6页。
②守法主义(legalism)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作为道德行为的标准。守法主义认为,由于正义的核心就是对既定规则的尊重,因此正义乃是“善之巅峰、德之缩影”,正义行为的典范无疑就是只服从于法律的司法程序,其极端者倾向于将所有的政治都融入到司法之中。参见[美]朱迪丝·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彭亚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及以下。
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像纳粹屠犹之类的暴行乃是康德所谓的“根本恶”,人类对其知之甚少,迄今为止为我们所知的所有刑罚,都不足以与此等惨绝人寰的罪行成比例,因此它们是不能惩罚的,由于它们不能被惩罚,同样也是不能被宽恕的。参见H.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241。汉娜·阿伦特显然对刑罚持应报论。阿根廷法学家卡洛斯·尼诺(Carlos Nino)提出了一种修正过的预防论,并从政治、伦理、法律三个层面论证了惩罚“根本恶”的正当理由。参见C.Nino,Radical Evil on Tria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④有关过渡司法的各种争议基本都可在这场论战中找到源头,参见D.Ortenlicher,"Settling Accounts:The Duty to Prosecut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a Prior Regime," Yale Law Journal,Vol.100,No.8 (1991),pp.2537-2615; C.Nino,"The Duty to Punish Past Abuses of Human Rights Put into Context:The Case of Argentina," Yale Law Journal,Vol.100,No.8 (1991),pp.2619-2640; D.Ortenlicher,"A Reply to Professor Nino," Yale Law Journal,Vol.100,No.8(1991),pp.2641-2643。
⑤除了官方的真相委员会以外,还有许多民间性质的真相委员会,但如果不加特别说明,真相委员会通常都是指为调查过去的暴行而成立的官方性质的机构,参见P.B.Hayner,Unspeakable Truth:Confronting State Terror and Atrocity,New York:Routledge,2001,p.23。
⑥关于当前南非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可参见夏吉生《“真相委员会”与新南非种族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96-103页。
⑦参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联合国文件A/RES/60/147,2006年。
⑧参见俞飞《转型正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13页。
⑨过渡司法国际中心就持此种看法,参见http://www.ictj.org/en/tj/。“系统性或大规模人权侵犯”是有待进一步认识的现象,目前尚无精确定义,通常是指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涉嫌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行为,一般习语称之为“暴行”(atrocities)。本文以上所说的暴行,就是这类犯罪行为。
⑩亨廷顿认为,针对暴行的每一种做法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最满意的情形也许是“不法办、不惩治、不宽恕、不遗忘”。参见[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5页。关于
response与responsibility,参见[日]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12页。
(11)参见《迪亚娜·奥伦特利切教授就帮助各国加强与法不治罪的所有方面作斗争的国家能力的最佳做法进行的独立研究报告以及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文件E/CN.4/2004/88,2004年,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