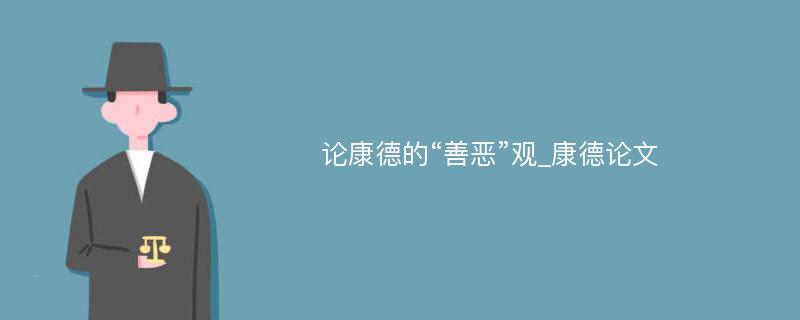
论康德的“善恶”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善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7-0052-04
康德在完成《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出版后,在1784年至1797年间发表了不少有关社会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历史哲学论文。国内有学者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构成他的批判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三大批判之外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的思想并非别立门户,而是从他的自然目的论(第三批判)思想中引申出来的。这里,二者虽然在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晚年康德的历史观是他对理性与自由这一近代哲学精神进行反思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的历史观是研究康德哲学不容忽视的部分。康德从自然目的论和先验的人类纯粹理性出发,论证了人类社会在大自然的预设下,依靠自然赋予的人类理性自觉,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的斗争,最终达到了人人自由、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美好境地。其中,他把善对恶的斗争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本文就对康德的“善恶”观作出简要评析。
一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讨论了“善”与“恶”,他把善和恶看作是形成实践理性的实践对象的一些概念。康德指出:“实践理性的惟一客体就是那些善和恶的客体。因为我们通过前者来理解欲求能力的必然对象,通过后者来理解厌恶能力的必然对象。”① 善和恶只关乎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而跟它里面所包括的经验材料没有关系,因为“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是指导作为自由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的表象”②。这跟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范畴不一样。范畴是不能脱离经验材料单独形成知识的,而善和恶的概念不需要经验材料,它只涉及人的动机,至于这个动机所造成的后果,则不构成善和恶的材料。那么,善和恶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认为只能来自先验理性、道德律令,先有道德律令才有善恶概念,而不能倒过来。康德说:“善和恶的概念必须不先于道德的法则(哪怕这法则表面看来似乎必须由善恶概念提供基础),而只(正如这里也发生的那样)在这法则之后并通过它来得到规定。”③
康德把善恶与福祸绝对分开,认为善、恶不是福、祸,也不属于事物的对象或性质。它首先属于行为本身,是指行为作为客体(客观对象)是否体现了道德律令。康德以古希腊斯多亚派的人为例子,来证实行为的善恶与经验的福祸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写道:“一个斯多亚派的人在剧烈的痛风发作时喊道:‘疼病,你尽管更厉害地折磨我吧,我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你是某种恶的东西的!’我们当然可以嘲笑他。但他毕竟是对的。他所感到的是一种祸,这是他的喊叫所透露了的;但因此就在他身上看出一种恶,这是他根本没有理由承认的;因为疼痛丝毫也不减少他的人格的价值,而只是减少他的健康善的价值。”④
康德认为,善和恶的评价不涉及后果,只看动机。在动机中预先已经考虑了效果,就是说,在订立动机的时候,必须把效果考虑在内,使之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一个动机能不能被后来的人普遍接受,它当然要涉及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别人不会接受,要成为普遍法则就不可能了。要有动机才能谈得上善和恶。如果是一个自然灾害,那就没有善和恶的问题。比如洪水淹死了人,没有人说这个自然灾害非常恶,没有人说这洪水有罪。善的动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所以,康德说,善和恶不涉及经验材料,它立足于自由意志的原因,也就是动机⑤。
康德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坚持道德不是根源于感性的人的幸福、快乐和利益,它是超越了这种经验感性之上的先验的绝对命令,即道德律令。人不得不服从于它而行动。“善”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恶”则是有意选择了违反道德律令的行为原理。康德认为,人是恶的,只能解释为:他意识到道德律令,但采取了背离它的原则。人性本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恶是人的反社会的个体倾向。正是康德这种对“恶”的解释,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论点,即使得历史的进步之成为必要而且可能的是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恶”。
康德说:“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由恶而开始,因为它是人的创作。”⑥ 所谓从善开始,就是指大自然使人类作为族类日益由坏变好,即一开始似乎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使这个人类作为种族将不断向前进步。所谓从恶开始,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理性的觉醒下,开始了自由意志的选择,为个人的私利而奋斗。大自然赋予人以理性,而理性却具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它可以仅靠想象力的帮助便创造出种种愿望来。由于人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是着眼于自己本身,于是有忧虑、有恐惧、有苦恼,所以说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而演出一幕幕的愚蠢、幼稚、虚空的世界历史的剧目。卢梭也曾指出:“一切出手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⑦ 不过,康德在这里虽然继承了卢梭的思想,却又超越了卢梭,因为他指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幕由善而恶的堕落过程”,而且同时更是“一场由坏到好的进步”。康德指出:“当理性开始它的作用的时候,并且——尽管它是那么地软弱——与动物性及其全部的顽强性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于是就必定会产生的无知状态,因而也就是为无辜状态所完全陌生的灾难以及使其令人困惑的是,随着理性的开化而来的罪行。因此,脱离这种状态(指自然状态,亦即无知而又无辜的状态——引者)的第一步,就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而在物理方面,则这一堕落的后果便是一大堆此前所以不知道的生活灾难,故而也就是一场惩罚……对个人来说,由于他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是着眼于自己本身,这样的一场变化(指由自由状态进入公民状态——引者)就是损失;对大自然来说,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是针对着全物种,这样的一场变化就是收获。”⑧ 康德的历史观以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开始,以所谓“永久和平”告终,这也是所谓以“恶”始,以“善”终。
二
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首先,康德社会历史观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起来,而“善恶”的对立统一是使二者结合起来的联系环节。康德认为,历史具有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就其应然而论,历史就是朝着一个目的在前进的,所以它不是盲目的;就其实然而论,历史就是按照规律而开展的,所以它不是偶然的。这二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康德的答案就是他所精心规划的自然目的论。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的“命题八”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所谓“大自然的计划”亦即“上帝的立法”。大自然秉赋的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并且要让这种理性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大自然赋予人的理性,其目的是为了自南地自我实现。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是大自然所展示所安排的基本目标。康德在历史哲学中,既考察作为道德本体的人的自由,又考察作为自然现象的人的必然。人既是动物,又不仅是动物,他既服从自然原则,同时又是自由的。人不单是自由的主体,因为同时他还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但他也不只是经验的客体,因为同时他还是自由意志的人。人类自由意志所表现的行为就成为历史。所以历史(作为自然现象)合规律性与历史(作为自由意志的表现)的合目的性两者是一致的。二者的一致性统一于历史的理性,即人的理性的运用。上帝一旦创造了人,就把理性、自我给了人,所以人就不可能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人由于自由就可以作恶,而每个人的恶却恰好成就了全体善,这就成其为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人类历史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个体与类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大自然对人的理性的运用是通过个体的生死衰亡和人类的不断延续来得以实现的,个体历史的艰辛痛苦与人类历史的不断收获的相互交织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
其次,“恶”推动历史的发展,是康德社会历史进步观的基本论点。康德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预告有三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第一种是“道德的恐惧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第二种是“幸福主义”或“千年福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朝着改善而进”;第三种是“阿布德拉主义”主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的世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⑨。康德对上述三种主张都有所保留和批判,在总体上他还是倾向于幸福主义。他坚信人类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人类决不是在演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悲剧,更不是朝着更坏的方向倒退。然而,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什么呢?康德指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⑩ 他将这种对抗性归结为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两种倾向的对峙。这里,他把人性中利己性的一面称为“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恶”,把人性中利他的一面称社会性,也就是“善”。康德认为正是人性的这种“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康德指出:“人类要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在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彻始终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秉赋显然就存在于人性之中。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的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会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第一步。”(11) 这就是说,正是由于恶与善的对峙,使人的聪明才智和各种能力在与他人竞争、对抗和冲突中不断发展起来。康德还举例说,“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正是由于每一株都力求攫取别的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就迫使得彼此双方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直的姿态那样;反之,那些在自由的状态之中彼此隔离而任意在滋蔓着自己枝叶的树木,便会生长得残缺、佝偻而又弯曲”(12)。康德认为,没有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所以,康德满怀感激之情写道:“让我们感谢大自然能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13)
再次,善对恶的斗争是康德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指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14) 在他看来,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所以,人类的对抗性(善与恶的斗争)必然会合乎规律地发展成合法秩序,人类要解决的大问题是要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自由不是任性,而是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律前提下的自由,无法律的自由和盲目的偶然性并无二致。他说:“惟有在社会里,并且惟有在一个具有最高度的自由,因为它的成员之间也就具有彻底的对抗性,但同时这种自由的界限却又具有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从而这一自由可以和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里:——惟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大自然的最高目标,亦即她那全部秉赋的发展,才能在人类的身上得以实现。大自然还要求人类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大自然所规定的一切目的那样;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因为惟有通过这一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大自然才能够成就她对于我们人类的其他目标。”(15) 康德所说的建立“正义的公民宪法”,就是建立共和宪法,亦即建立共和政府。为什么要建立共和政府呢?他认为人性有非社会性,因而就需要有一个主人来统治,但是主人也是一个人,他并不比别人更天使。这就是共和政体取代任何专制政体的理由,因为只有共和国才能成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的保证,她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充分发展的保证。
三
康德的历史观与其形式主义的道德理论是有很大区别的。康德认为,道德与历史,一个属于本体,一个只是现象,道德的理念高于历史的理念,历史从属于道德。康德许多历史观点如同他伦理学中的上帝、灵魂等一样,终究不是客观规律,而只是主观理念,即不能由经验证实的。因此康德未能从哲学上把他的这些历史观点贯穿起来,成为强有力的杠杆。因为这样就必须冲破整个“批判哲学”体系,摧毁和舍弃那个不可认识的本体世界和形式主义的道德律令,这当然是康德所不能做到的。然而,康德从1784年到1797年间发表了有关社会政治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其所述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观点,对于打通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已经蕴涵了潜在萌芽。毫无疑问,康德不能正确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发展的联系,他把历史的发展单纯归结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过程。不过,他关于善与恶的思想对他之后的哲学家、理论家有很大影响,也是我们当今值得关注的问题。
康德的“善恶”观念在其历史观中的重大意义就是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自然的隐秘计划”),形成一种“总体现性”(16)。黑格尔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必须以恶的发展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康德,他接着康德,对人类总体的伟大历史感构成了他的辩证法的灵魂,建立了一种总体历史观(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却缺乏这种总体历史观,他之所以失败,在于他想以个体感性的普遍性来代替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总体理性的普遍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的“善恶”观念是称许的。但马克思在历史观和道德观上,反对对善、恶观念与道德作抽象的理解,对历史因果与自然因果、人的个体与族类的发展的关系作出了科学阐述。就人的个体与族类的关系,马克思说,在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到达之前,作为族类的人(整体)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有时处在尖锐的对抗之中,并经常要牺牲后者而向前迈进。他指出:李嘉图要求“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伤感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级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17)
当今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分配体制、管理体制,要调整产业结构,要缩小城乡差别,所有这些都要涉及到个体的利益,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能要牺牲某些个体甚至某个阶层的利益,这种个体利益的牺牲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而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能更好地满足个体的需要。从这一方面来看,今天我们解读康德的善恶的思想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④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78、85-86、82-83页。
⑤ 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⑥⑧⑨⑩(11)(12)(13)(14)(15)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70-71、158-159、6-7、7、9-10、8、8-9、9页。
⑦ 卢梭:《爱弥尔》,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6)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4-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