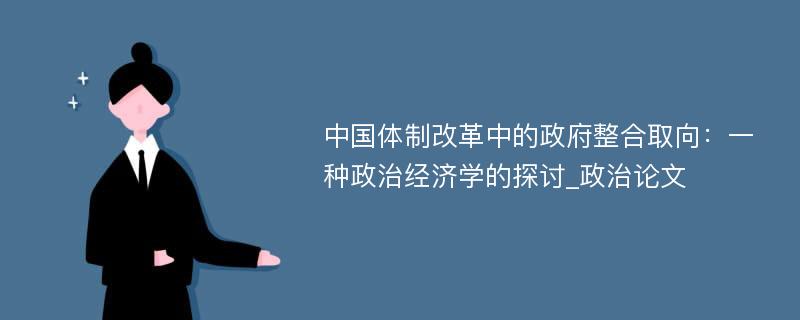
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一项政治——经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经济-政治相关性来分析政府作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种体制改革的模式。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府整合面临严重挑战。政府整合困难既根源于经济变量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的锐减,又反过来影响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其重要表现是地方主义的扩张,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须着手重建政府的整合。它有赖于中央政府一定的行政集权,同时又要以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为前提。重建政府整合在理论上基于区分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基本功能,这一政府功能的二元范畴规范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政府整合由内及外优化政府功能,有利于政治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政府整合正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变迁的副产品,缺少主动和合理的变革,以至于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经济体制不断突破,经济结构革故鼎新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则缺乏规范的目标导向,未能做出适应性变化,从而引起政治功能的紊乱,而尤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整合的困难。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相关性视之比较实质的一个步骤是“下放权力”,即中央政府为了搞活地方经济把许多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建国以来,围绕着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曾有过几次起伏。中央政府曾在1957年和1969年较大幅度地下放了一些事权。但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程度。是前两次望尘莫及的,其关键的步骤是把传统的统收统支的“吃大锅饭”的财政体制转为一些地方实行财政包干的“分灶吃饭”的体制,使地方权力的强化具有了财政和经济基础。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功能萎缩而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甚至是“功能膨胀”①。中央和地方权力消长的这一趋向最集中也是最根本地反映在对社会资源控制的比例上。在整个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百分比不断下降,1981年为54%,1985年为45.3%,而1989年又下降为36.4%,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百分比则大幅度上升,由1981年的46%上升到1989年的63.6%②。同时,政府的许多经济管制权也从中央向地方下移,特别是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拥有地方自主投资权和“直接融资自主权”等许多重要经济权力,而且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的比例也不断减少,在1993年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降至16%以下,中央控制的商品种类也由原来的722种下降至30种,国家统配的生产资源已减少至19种。这客观上都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管制权。相形之下,中央政府所控资源和实力则过于弱小,举世罕见。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在最近一个世纪政府的规模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规模一直在稳步增长。据哈罗德·德姆塞茨的研究,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的财政比重的实际的和比较理想的幅度是占GNP总额的30-45%③,而其中中央政府在整个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一般达60%左右或更高。而近年来中国的情况则反其道而行之,政府收入与GNP之比由1978年的34%降至1992年的15%,其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比例一度不足30%,形成极不正常的“倒三七开”。
这一经济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它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而首先是中央政府调控力的下降和地方力量的相对增强,使地方主义迅速不断地滋长。地方主义历来都是中国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80年代以来,地方主义由于经济驱动并走向了难以驾驭的程度,这是前所未有的,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④早在1988年就有人尖锐指出全国已有20多个“独立王国”,2000多个“诸侯”,而这种状况并未受到有效的抑制。⑤地方主义就经济方面而言,表现为对地区资源、商品等进行区域性的垄断和封锁,人为设立贸易壁垒和经济栅栏。在商品销售上,盲目排外保内,各地相互禁运;在资源分配上,强调就地加工,自产自用,“肥水不流外人田”;在生产布局上,强调地区内配套,限制外协,重走“大而全”、“小而全”的老路;在资金流动上,只许进不许出等。就政治方面而言,则表现为分散主义和行政失控,各地政府纷纷趋向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的办法。在行政上,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的中观调控不能正常衔接,使中央政府功能的履行发生严重障碍;在司法体制上,各地地方保护主义也大行其道,不仅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也妨碍了市场的发展。
地方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和伴随物,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流失和功能障碍。中央政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和危险的地步。就近来的情况来看,这一状况比较明显的表现如中央关于转换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条例和减轻农民负担等重要政策在地方上不能落实,不少地方都截留中央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和中央给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至于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法规,自行其是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总之,一方面,地方政府功能膨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功能萎缩,两种运动交互作用,造成中央政府宏观失控而地方政府中观干预加强的背反现象,使企业实际上仍然不能获得自主权,最后隐入“宏观失控、微观管死”的畸形状态。这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问题,即政府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政府整合的缺失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有害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与统一市场甚至世界市场的形成分不开的,而统一市场的形成又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与西方整个现代化过程共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时,曾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制度、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来实现经济腾飞的新兴国家,政府的权力整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变得更为集中和统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权力趋于扩张的过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⑦,在美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二元联邦主义”的衰落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⑧。至于稍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不仅政府权力集中统一,而且政府强大的经济功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没有一个现代的具有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是与政府的整合危机和功能障碍相伴相随的。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在政府系统的软弱涣散的状态下达到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可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但必然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必须努力促成统一市场的形成,它同样也是与全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性共生的。而目前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化,不是朝着统一性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分散性演变。从经济发展观之,这种演变造成地方经济保护主义和市场的分割,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政治发展观之,这种变化也不是现代化的一个取向。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权力分散,但这种权力分散是在整合基础上的分散,C·E·布莱克透过历史的分析指出现代化的政治是在公共事务领域决策强化并“采取了国家行政机构日益集中化的方式。”⑨如果权力下放的结果是促进社会的分层和多元化,同时又保持高度的整合,这种趋向才符合现代化,也是与民主发展一致的;但如果权力下放造成的是地方的各自为政,这就与现代化和民主化不仅无缘,甚至是背道而驰,也有害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可见,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观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要改革这种状况,还要从纠正“权力下放”开始。实际上,仅从经济方面考虑,“下放权力”也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方。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到两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另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中国的改革应着眼于经济转型中的政府结构和功能的重塑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中央要有权威,要由中央把各地统一起来:“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⑩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目标,不是也不能是把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代替中央政府去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力,而是把整个政府系统应当由企业承担的职能统统转给企业,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实现其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集权,实现较高程度的政府整合。
二
现阶段中国加强政府整合离不开一定程度的中央政府的行政集权。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条件下,实行中央政府的行政集权,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市场经济下加强政府权力的整合,从理论上讲有别于过去的政府集权模式,从实际上讲,也要注意防止回复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行政集权,是建立在政治——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并与政治集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中轴的政治集权的副产品。邓小平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在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11)由于过去党政不分,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是融为一体的,所谓行政集权,不过是政治集权的必然结果。因此,过去政治体制是政治经济一体化、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三位一体。
在当前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行政集权应当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和民主为前提,这是它与传统的行政集权的本质区别所在。易言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整合,其前提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即政治经济的二元化、政治民主化和行政集权化。
第一,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结果和要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通过政治权力行政指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政治和经济是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有赖于政府的活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政府的经济功能由过去的包揽一切转变为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这就意味着政治与经济必须相对分离,因此,行政集权的后果不是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把经济管死,而 主要是加强政府系统内部的整合,增强行政效能,使行政活动更加有序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但另一方面,市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应积极地、主动地、有意识地促成与经济的分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现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但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需要注意防止的就是政治权力以不规范的方式介入经济活动,形成畸形的政治——经济一元化,阻碍甚至窒息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形成。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而形成这一问题的结构性因素,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截留中央转交给企业的权力,以不正当的手段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利。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有赖于政治民主和行政集权,削减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功能,使政府官员以失范的方式介入经济活动失去结构性基础,使政府行为从失范走向规范,使市场运作从无序走向有序。
第二,政治民主从理论上讲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后国家的“硬政治、软经济”已经证明政治独裁与市场经济发展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可以共存的。然而,即使抛开民主的价值不谈,这种模式由于其特定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难再套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是并行不悖的。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可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所谓政治民主,就是国家主权在民,而其一般的形式是人民通过其代议机构即立法机构行使权力,制定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并监督和制约行政和司法机关。而行政集权则仅仅是政府科层组织体系内部的集权,这与把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权力集中于某个领袖身上或某一政治组织之中的政治集权(或政治独裁)是断然不同的。
在当今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建立一套民主的、开放的决策机制。决策权力不应过分集中,而应当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只有在政策是按照民主的程序制定出来,因此也就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前提下,行政的集权才不致于偏离正确的方向,才不致于导致对社会和公众的危害。其二,是要建立法治的政制,这必须通过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约来实现,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也是实现政策过程民主化的一个条件。
第三,要在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中央行政集权的体制,以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提高政府系统的效能,做到令行禁止。中国政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集权化和行政上的分权化,这与政治现代化是大相径庭的。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决策机制上权力过分集中,而政策执行则困难重重,议而能决,决而不行。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应当加以纠正,即决策权应适当分散,而行政权则应相对集中。因为决策过程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而应遵循决策的科学规律,按照政策制定的法定程序一步步进行,宁慢勿错。过去中国实行“议而能决,决而能行”的模式,这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中轴的集权体制的产物,现在已很难行得通。目前加强中央的行政集权,与决策的民主化是并行不悖的,即要按照政治民主和行政集权的要求,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议可不决,决则必行。
总之,政治分权化,行政集权化;政治民主化,行政高效化——这是经济转型后政府整合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应成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政府系统的整合,加强行政集权,其目的正在于促进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为市场机制的形成开辟道路,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它们所共同构成了今后中国政府整合的基本内容。
三
政府整合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政府整合的困难。一般而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整合困难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它是传统存在的政治整合危机在政府系统中的必然表现。派伊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困境时,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其核心即整合危机,而整合危机则是由认同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所致。(12)这些危机是一直缠绕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痼疾。而在中国,自1949年以后,上述诸种危机并不存在,相反,政治整合的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很高的。因此,目前中国所存在的政府整合困难并非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削弱政府权力统一性的结果。虽然其生成原因和发展线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但任其发展下去,结果必将也是整合危机,同时也必将伴随着其他各种危机。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始终求之不得的政府整合,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视而正在逐渐丧失。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和纠正,我们传统的政治优势将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况。这不仅对于经济发展不利,而且最终必然威胁到政治权威的生存。这一不良趋势之所以会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甚至产生误导,这乃是中国近年来缺少一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合理的政治规范使然。
在以后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着眼于维护和加强政府系统的整合,其基本的政治规范是什么呢?这首先要理清政府的功能范畴问题。任何一个组织,都具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的目的、性质、原则和内容却有所不同。政府系统作为一个高级的政治组织,也必然具有两种基本的功能:一种是就政府系统与其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等的关系而言所具备的功能,或称为政府体制的“外功能”,它所涉及的是政府与社会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种是政府维系自身正常运转的功能,或称为政府体制“内功能”,它所针对的是政府系统自身。这两种功能有着各自的运动规律,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就政府体制外功能而论,政府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它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军事、外交等重大事项,具有管理社会事务的功能。政府应当管什么,不管什么,采取何种方式何种手段来管,以及管到什么程度,因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社会系统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政府必须尊重这些规律。就政治层面而言,政府应当保持社会政治生活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发挥社会政治力量的活力,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政治民主。就经济层面而言,政府不能直接具体地控制经济运行,而应当充分尊重市场运行的机制,使生产经营者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这就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过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
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的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体制的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如果是以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来执行体制内功能,就必然导致政府功能的紊乱,破坏政府系统的整合。
我国在设定政治体制的模式的时候,恰恰就是不能很好地区分政府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以设定体制内功能的方式来确立体制外功能,政府权力过于庞大,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结果是窒息了社会活力,抑制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但矫枉过正,在转变政府体制外功能、向社会放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政府系统内放权,结果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失衡和混乱。
因此,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从思路上廓清政府体制内外的这两种正常功能,并且首先从体制内入手。中国以往的改革,采用的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绕过困难进行改革的战略,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就会愈来愈大。(13)现阶段的改革已经到了从体制外纵深到体制内,必须自上而下深入进行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而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艰巨也更主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由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经济体制转型,由体制内变革促进体制外鼎新。因此,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应首先强化体制内功能。从政府整合问题入手,正是抓住了整个改革的关节点。
注释:
①胡伟:《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功能》,载《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五期。
②《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87-8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⑤参见《新闻报》,1988年7月9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255-256页。
⑦S·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
⑧D·C·Saffcll,The Politics of Amcrcian National Gorernment,Boston:Littlc,Brown&Comnany,1983,P66.
⑨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8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12)L·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Company,1966,P63-67.
(13)吴敬琏:《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载《文汇报》,1993年7月23日。
标签:政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