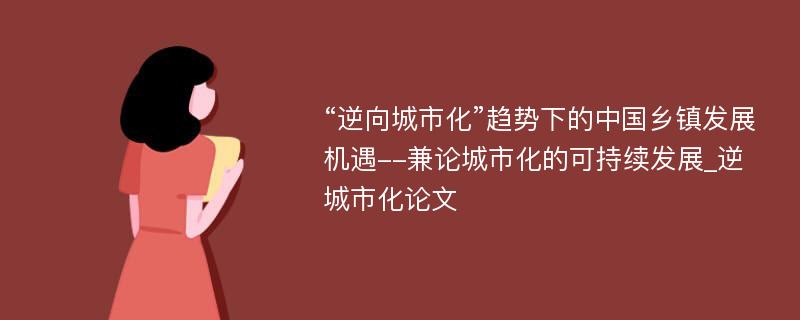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的发展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镇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发展机遇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3-0053-05
一、引言
中国城乡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20多年来中国城市迅猛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专家们归纳为城市“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1]。这样的城市化面临难以持续发展的危机。而城市的迅猛发展又带来了城乡发展很不平衡的问题①,乡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由此,中央提出“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就城市发展解决城市问题,就农村发展解决农村问题,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见效不大。② 有没有一条既能够保证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村镇跨越发展之路呢?本文认为,基于优化城市功能的目的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引导或激励一些城市产业向村镇转移,能够两全其美。“引导或激励一些城市产业向村镇转移”,就是“逆城市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逆城市化”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所谓“引导或激励”,就是政府创造不同的区位地租利润和产业发展空间助推“逆城市化”。助推“逆城市化”,既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特色突出,又有利于村镇发展。而“一些城市产业向村镇转移”无疑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了城市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2] 这就是说,城市规模的边际效益总会接近极限。城市功能不同、特色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边际效益的极限也不同。越接近极限,成本与收益的反差越大。由于城市化是不断地聚集资源和壮大产业的过程,城市空间的容纳力终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可能异化为城市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即创造“递增与分化”对流的条件。这里的“分化”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分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被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文化旅游、观光农业等。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同时进行,同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以往国家政策性安排下的行为,如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以及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化和人口分流现象。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效益“递增”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规模越大,“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过程,因而“逆城市化”也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三、“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由单一地发展城市向城乡一体共同发展转变的必然趋势。而城乡一体,疏通了“逆城市化”的渠道,为村镇利用“逆城市化”力量发展自己创造了新机遇。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20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3]。“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被提出,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主要针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以革命性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和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即是运用这一理论的代表之作。[4]
从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中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大师们凭借自己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为城市化克服城市病和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止。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于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因“大城市化”累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促进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尽管城市化遭遇过严重的城市病,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表明“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巨大力量。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又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
四、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其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按常住人口计算,2005年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5]。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6],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凸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因此成都的“逆城市化”流动也表现得特别活跃。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确立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支柱的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后,成都市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已经实现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同时也标志着成都“农家乐”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出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远郊也出现了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四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四大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的强劲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规律,不失时机地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的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做法,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的经验值得借鉴。[7]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大城市化”向“城镇化”的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和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二十七位[8]。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五、经验与启示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和城市病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经验、新启示。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从成都的经验来看,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分流在发挥重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那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的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电信、光纤向乡镇的延伸,为更多的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乡镇转移创造了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可以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或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或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原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促使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从而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注释:
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之首。
②对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专家们就提出来了,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这几年中央在解决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总体上失衡的问题上所下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仍然是“发展很不平衡”。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理性、利己、利益最大化驱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制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