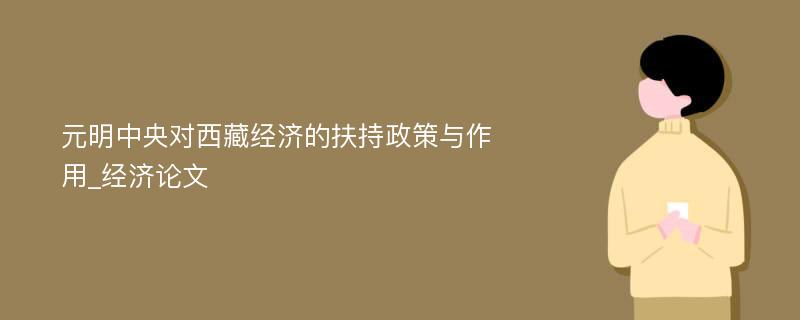
元明中央对西藏经济的扶持政策及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扶持政策论文,作用论文,中央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明时期,西藏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和繁荣,是西藏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一段。由于处于分割动乱中的西藏地区归属中央王朝,在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支持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这一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首先以10世纪阿里地区古格拉德王为寺院赏赐庄园为标志,寺院主也开始变为占有一定庄园和牲畜的封建领主,领主与寺主合为一体。[①]无论是寺院集团还是世俗社会,其庄园经济都在不断发展。元代对萨迦派和帕竹家族的扶持,是促进西藏领主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当帕竹家族结束了萨迦政权统治后,元王朝即加封其领袖绛曲坚赞为大司徒,颁给印信。他及其后任在中央王朝支持下,通驿道、复修庄园,新建13座宗城,减轻僧众负担,扩大藏汉经济交流。到元末明初,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溪卡)遍布于前后藏各地。[②]
有明一代,特别是15到17世纪中叶,是西藏寺院领主经济巩固并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在明中央王朝扶持下,黄教寺院经济迅猛发展。到16世纪中叶,黄教寺院经济已形成具有全藏规模和主导地位的经济集团。明朝末年,黄教寺院经济进一步扩展至今青、甘、川、蒙、滇等地,强大的寺院领主经济集团与世俗贵族溪卡及“马头”“大户”等,成为17世纪西藏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最大特色。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时期西藏地主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就不难发现,除了上述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和西藏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外,在完成这一历史转变和飞跃的过程中,元明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经济的多方扶持政策和藏汉经济文化的积极交流则起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些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元明中央积极拓展西藏与内地的交通
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从西藏早期历史看,吐蕃时期之所以能兴盛一时,其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唐蕃古道的开通,加强了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两宋时期,吐蕃衰亡,唐蕃古道断绝,陷入分裂动乱之中。元初当西藏各派归附后,忽必烈即着手令达门开拓西藏与内地的交通,从青海、前后藏直至萨迦,设置27个大驿站。由点到线,沟通了元朝在藏区所设的三大辖区。[③]为了保护驿道的畅通,元中央政权把支应各站的用具及乌拉差役分别落实到万户府,实行站户负责制。1276年后,针对站户逃亡事件,又令大臣桑哥对藏地驿站管理进行改革,将驿站移交蒙古军队,由军队分兵专管。从此,卫地藏民不必亲赴藏北驻站,不但确保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往来[④],而且缓解了藏民负担,必然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元朝中央多次以赈济之法从经济上直接资助站户,约两年一次,最多时一年给银11000余两,外加牲口800头。[⑤]
明代是西藏与内地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朝中央为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复修青藏、川藏驿站,多次派内地民工入藏,与藏族人民通力合作,整治旧线上的险阻路段,架设桥梁,开辟新线与商道。“自是通路毕通……无虞寇盗矣。”[⑥]特别是茶道(即商道)开通后,促进了茶马贸易及商旅往来,成为联结藏族与内地人民的纽带。
明代青藏驿道分别是在元及唐旧址上复修的。其中路大体从西藏经墨竹、那曲卡、当拉岭、通天河、查灵海、日月山到西宁,是官方驿道的主道。[⑦]东路由玉树入藏,是在唐及唐以前入藏的古道基础上复修的,全线长约4000里。[⑧]川藏道是由明初驿站和茶道整修而成的,主要是将川内驿道续修至昌都后与青藏东道相接而成,全线长约4700里。宣德时因青藏道盗匪劫掠,贡使及官员改由古茶路从川藏道往返。[⑨]年经此道的贡使多达数千,嘉靖十五年(1536)一次即高达4170人。因此,川藏道不论是从驿使还是茶马贸易量上均与青藏道一同成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通热线。此外,松藩道在明洪武及宣德年间多次进行大规模整修,还新增了邮亭。其南路从成都经灌县、咸(汶川)、茂(茂汶)、叠溪、松蕃,出黄生关与青藏大道相通。东路西通文县与今甘肃藏区相连。[⑩]
明代使用率最高,对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是茶道。藏民将此商道亲切地称为“嘉(即茶)兰姆”。除由陕西经甘青入青藏道运送在陕西泾阳加工之湖南砖茶外,在四川境内主要是川藏道与松蕃道。川藏商道指从雅州经打箭炉通乌思藏的茶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初制,长河西等番(即藏)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是(定)价……于碉门茶课司给之。”明初,政府专门整修了碉门到岚安的道路,并开拓了岩州至碉门的通道。民间茶商为图便捷,或取道碉门或取道黎州。嘉靖以后,因明朝大力扶持黎雅一带的茶叶生产,其地道路又相对平易,更促使了民间茶商的汉藏贸易,往来商族多改行黎州。从雅州到打箭炉,茶叶以人力背负搬运为主。从打箭炉入藏,改由牦牛、骡马等畜力驮运。翻折多山,从两路口经理塘、巴塘过宁静山到芒康,再经察瓦岗到昌都西北瓦合寨与昌都至拉萨驿路会合。松藩茶道主要是用于向西藏转运转销南路的边茶,在小东路和汶川金川形成两条专用茶道。(11)
二、在支持庄园经济的同时,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以间接资助藏区
元中央政权对新兴的僧俗领主庄园占有制度不但从政治上支持,也从经济上予以扶助。13世纪末,元帝师10余次奉朝廷旨意向乌思藏宣慰使、万户长及僧俗民众发布文法,屡次申明对各僧俗领主封地上的百姓、土地、水草、牲畜及工具等一律严加保护,不许侵犯。同时,告诫所有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向各领主属下百姓骚扰,及滥索供应、乱派赋役。大元首任帝师八思巴1267年所下法旨即规定:“无论何人俱不得(向寺院僧俗)征派兵役、赋税、劳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税,不得索要饮食及乌拉差役”等。1319年元帝师奉皇帝旨令曰:“对寺庙、庄园及其地、水、草场、札巴等,遵照皇帝圣旨,不得增收前所未征的差、食物、乌拉,不得强令饲养牛马”。1321年又下旨:“不得群攫牛羊,不得催磨青稞,遵照皇帝圣旨,不得追究旧差”。(12)
明初为了怀柔藏民,未向西藏地方征收任何差赋。在整修驿站时,虽曾有少量乌拉差役,也是用于西藏驿站的供应,而管理维修西藏驿站的驻藏蒙古军队,均由中央调拨经费开支。使西藏成为更优惠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区。直到1383年(洪武16年),才因为保证战马供给,从川边藏区征收有限的马匹。当时向松州卫发出的敕谕称:“西番(藏)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目的并非为征赋,而是“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13)九年之后,又命太监“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当时含乌思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14)即给征马以茶叶补偿。
以马为赋又补偿以茶的经济政策在藏区推行以后,必然刺激庄园畜牧业的发展。但一些边吏其后曾乘机敲诈,向藏区勒索额外马匹以肥私。为保护藏地利益,使中央对藏区的特殊政策能落到实处,1393年,明太祖命曹国公李景隆亲至藏区推行“金牌信符”制,(15)它是朝廷发给纳马藏族部落的一种铜质凭证,“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16)金牌一式两面,“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17)并规定“三岁一遣官合符。”(18)
到正统末年(15世纪中后期),由于西北边地战争频仍、加上私茶冲击,以金牌信符为标志的差发马制度中断执行,中央政府干脆听由藏番随意“以马入贡而已”。到嘉靖时,改差发马手续为勘合制。崇祯年间,差发马制才完全被破坏。在差发马实施期间,中央补偿每匹马的茶叶数量不一。以万历时为例,每匹马不分等级平场给茶百斤左右,(19)当时市场上茶马的比价,约为每马200斤左右,(20)则中央政府偿付藏区数量有限的差发马的茶价,将近二分之一。也就是说藏民每三年由四户征交的一匹马,实际上平均每年每户实交为每匹马的百分之四五左右。(20)
与此同时,元明中央政府还以赈济灾民方式,间接资助藏区。以元代为例,每遇雪灾饥荒,元中央政府就及时减免有限的西藏赋税,并予以赈济。藏文《萨迦世系史》中记载,元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就曾“向大皇帝请求”之后,“免除了乌思藏民众数年赋税,使雪域众生获享安乐。”(21)对于十三万户承担的藏北驿站的赋税,元朝多次予以专项赈济。据初步统计,从1288年至1314年的6次赈济中,共用去白银11.3万余两,大元宝钞15.3万余锭,牛羊马匹一千几百头。(22)
三、以厚赏朝贡下的补偿贸易为手段,向西藏封建领主经济“输血”
终明一代,乌思藏与明中央朝廷间的朝贡与回赐始终不绝,不论就其规模还是贡使及赐物数量,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绝无仅有的纪录。明王朝针对西藏教派林立而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政策的同时,在经济上对朝贡臣服明王朝的各派除封敕外,特别给以丰厚的经济赏赐,形成一种以“贡赐”为形式的特殊的补偿性贸易。《明会典·朝贡》记载:“洪武初……乌思藏有阐教王、阐化王……大宝法王凡七王,俱赐银印,令比岁或向岁朝贡。”“至成化元年,始定三岁一贡之例。”朝贡虽本是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的体现,但由于明廷的回赐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而且来往频繁,成为中央对地方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换和经济资助,所以我们从经济交流的角度,称其为“贡赐贸易”或“朝贡式互市”。
在这种贡赐往来下的补偿贸易中,尽管途中苦不堪言,藏族贡使却不远万里,乐此不疲,原因就在于明王朝对藏使赏赐“宁厚勿薄”(23),“务令远人得站实惠”(24)的资助政策。据《明会典》记载:“乌斯藏……喇嘛番僧人等,从四川起送来(京)者,到京每人彩缎一表里,苎丝衣一套,俱本色。……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十斤。”进贡“中等马,每匹苎丝一匹,钞三百锭。”(25)数信于马价。成化年间,每钞一锭,折银4钱,300锭折银7.5两。每匹苎丝折银2.25两。上等马加赏绢一匹。则上等贡马的赏价,高于其实价(每匹折银约五六两)两倍至两倍半。(26)
政治上的臣属朝贡在经济上得中央的大力资助,也使西藏获得了生活必需品:食、茶、丝绸等,同时促进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正德年间(1506—1521),乌思藏及天全六番招讨司贡使从中央“得赐番茶六万斤。”(27)贡使不但由明中央负担途中一切费用,且其挟带私货也可以不花分文。如大悟法王私自收购私茶、彩缎、绢布等大量货物,“乞命沿途军卫有司供应转递”,明廷居然也“许之”。(28)于是,许多假朝贡之名进行商贸活动的喇嘛藏商便应运而生。“其意盖假朝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29)甚至“边民见其得利,故将(特意让)子孙学其语言,投作番僧通事混同进贡。”(30)因而藏族贡使的批数及人数迅速扩增。“宣德、正统间、番僧入页不过三四十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1499年为2800人,1537年(嘉靖十五年),乌思藏及长河西等处的贡使多达4170余人。
明初虽定例贡三年一次,但为了优待西藏,破例扩大,遂有一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者。藏族贡使潮水般涌入内地,以至明廷感到难以负担,不得不多次控制入贡入数及赏赐,但仍无济于事。如1470年曾限定乌思藏亦三年一贡,人数不得超过150人。但到1569年(隆庆三年),鉴于前述年仍达数千人的事实,不得不将限额扩增至千人,同时对违例入贡者仍予以接待。当万历中一度停止大乘法王等朝贡时,经不起他们苦苦申辩,仍恢复其朝贡的要求。(31)
元明中央除以朝贡赏赐资助西藏封建领主外,还对各帝师、法王及寺庙以臣额赏赐及布施。除政治意义外,它也是元明中央对西藏封建领主制经济的一种财政资助的“输血”手段。元世祖忽必烈给帝师入思巴的赏赐首开其端。当时除赐于土地庄园外,尚有珍珠、宝石、黄金饰物十余件,黄金一大锭,白银57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1312年(皇庆元年),元中央派专使一次赏赐西藏僧界黄金500两,白银25000两,币帛近4万匹。1321年(至治元年),仅为帝师西藏受戒一次赐黄金1350两,白银4500两,币帛万匹,钞50万贯。(32)到了明代,也是贯彻同一政策。仅明初三个月内就两次赏赐尚师哈立麻黄金200两,白银2000两,钞22000贯,彩币表里百余及其它物品多件。(33)1585年(万历十三年),明廷尽管因节慎库空虚,但为了恩赏大乘法王等人,委四川藩司转拨赐予9300两,后因藏僧不愿由四川藩司拨付,遂改由工部直接赐予。(34)
四、为推进汉藏经济交流,繁荣发展以茶马为中心的官、私互市贸易
茶马互市,是推进汉藏经济政治往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它肇始于唐,盛于宋明。元代,虽由于蒙古族本身长期游牧业而不需得到军马。但由于藏族迫切需要食茶及汉地用品,故元代也承宋制,曾设局专卖,“榷成都茶”。1269年又在四川设西蜀监摧茶场使司,管理与藏区的茶叶贸易。1276年(至元十三年)又恢复了南宋时的茶引制,次年又特“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35)
明代中央则十分重视马玫,改进完善茶法,使内地与西藏的茶马互市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在官营互市兴盛的同时,民间商户的茶马及其它经济贸易也由小到大,并最终取官营而代之。明代与藏区的茶马互市,实际存在官营、私营及贡使的贡马易茶三种方式。从明初开始,官方茶马互市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其中重要的首先是茶马司的设置。《因榷》记载,1372年(洪武五年),先后置秦州(今天水)、洮川(今临潭)茶马司,次年十月“置河州(今临夏)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1397年。为与藏区互市方便,又迁秦川于西宁为茶马司。其次是制订茶法。明初,为保证官营茶马交易正常进行,严禁私茶进入藏区及西藏。洪武末年,一度实行开中法,允许商人于藏区等边地纳米中茶。到1415年(永乐十三年),入藏使者上奏:“西番无他产,惟以马易茶。近年禁约(私营),生理实艰,乞仍许开中。”(36)明成祖应允,但对民间购茶课税,即“纳钱请引”,每引百斤,初收税200文,后增至千文或纳银二钱。
官办的茶马互市自洪武至永乐时暂停,宣德十年复开至正统末年为民营取代。时间虽不长,规模却很大。以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春为例,“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37)宣德年间,还大大提高藏地输马的价格,使藏区增加实惠。如洪武中,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永乐中先将西宁茶马司所市藏区之马每匹分别加茶20斤,河州则上马加20斤,中马加10斤。到宣德时从河州等地所输之马价则比洪武时更增加至倍余以上。明初,茶马司散设于秦、洮、河、雅(州)等地,为方便藏民就近交易,洪武末将秦州司改移至西宁。由于在川藏所市之马输往西北路途遥远,永乐后将“番马悉由陕西道”。1502年(弘治十五年),扬一清总理马政后又制订招商运茶例,开放输茶市场。规定凡招商输茶于荼马司者,每千斤给运费50金。从此,明朝汉藏区茶运事务正式由官办改为商民私营。商人运茶的制度推行以后;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汉藏贸易如虎添翼,迅速发展,明朝与藏区及西藏茶马贸易中的官办互市受到严重冲击,逐步为私茶贸易所取代。
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私茶”贸易,最初只是官方茶马互市的补充形式。“私茶”,是明朝对官方贸易外违例进行的藏汉民间贸易的总称。它由暗到明,由小到大,终于成为明代中期内地与西藏及藏区贸易的基本形式。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边镇官吏利用职权趁官方茶马互市之便私自同藏区进行的贸易。首先是各茶马司官员以职权之便或受商人之贿后同贩,为牟取暴利,或以伪劣茶叶调换司衙所存良马良茶,或以良茶换取劣马以充良马,然后将大量差额余茶私贩藏区以牟利。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就曾伙同布政司官,以大东50辆至河州与藏区私相贸易。1445年(正统十年),陕西布政司上奏:“每年运茶入番,其洮州等三卫军官往往夹带私茶,以致茶价亏损。”(38)特别到了晚明时,有司官员不但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私易兴贩,甚至纵容其子孙冒中进行,及将茶叶辗转运贩,然后通过商人再以高价向国家转售。这种做法虽然坑害了国家,败坏了茶法马政,但却有利于藏区经济发展,促使了私茶贸易的日益兴盛。
其二,是相邻地区军民与藏区的贸易往来,目的是解决双方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因为汉藏交界地区历史上长期自然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决定的,非政府政策可以管制得住的。一般是汉区军民利用邻近之便,以私储良茶易取藏地良马,先高价出售于商贾获得大量茶叶,再反手与藏地农牧民交换各种土特产品,藏民与此同时则获得日常必需的食茶丝布等。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经青、康藏区转入西藏。如1448年(正统十三年),陕西洮州、河州茶马司上奏说:“(官茶)未有完者,盖近年邻近府卫军民兴贩私茶者多。”(39)到嘉靖时,川陕边军民或“潜入蕃族贸易”,或“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40)
其三,是内地商人同藏区及西藏的贸易。其途径,一是通过邻近藏区的官吏进行间接贸易,二是潜入藏区进行直接贸易。这种贸易其实由来已久,且自成一体。其茶叶是来自纳粮草中茶与为官府运茶所得的酬茶,当然还有私自收购者。明朝招商纳粮草中茶数量巨大,如弘治七、八、十四3年的中茶数量竟多达千万斤以上,这么多茶叶均由商人运输。“运至茶司,官商对分。……每上引(5000斤)仍给附茶一百篦(每篦十斤、共1000斤);中引(4000斤)八十篦;下引(3000斤)六十篦,名曰酬劳。”(41)商人从中不但获得酬金,还得到大量良茶。商人以良茶从藏区及西藏所得马匹量多质优,因而很快凌驾于官方茶马互市之上。明廷为了得到这部分良马,永乐时曾令陕、甘茶马司实行招商纳马以茶偿之。景秦及正德时又曾以盐引茶引来招商上纳,场促使民间商贸迅速加入这一贸易中来。因此,尽管明廷曾多方禁止与藏区的“私茶”贸易,但因这一贸易符合民心民情、适应西藏需要、合乎经济规律,所以民间汉藏贸易与官营并行,且日益兴盛,在晚明成为西藏及藏区与内地经贸交流的主要渠道。
此外,入朝藏僧的贡马易茶,也是西藏地方同内地贸易交流的一个特殊渠道。前文述及,入贡僧人返藏时不但得到朝廷大量赐茶,而且在政府保护和允许范围内,以其他货物私易民间茶叶等物品,以及交换彩帛及铜、铁器诸物。如1440年(正统五年)、藏使“葛藏等复私易茶、彩(帛)数万以往。”景泰时,番僧、国师、喇嘛“进贡毕日,许带食茶回还。因此,货卖私茶至万数千斤及铜、锡、磁、铁等器用。”成化时,大悟法王札巴坚参一次即私购货茶达二万余斤。(4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元明时期,通过赏赐、贡市、赈济、布施、茶马互市、民间贸易等官私途径,不但体现出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的扶助,从而促使西藏领主庄园制经济兴起、繁荣与发展,而且加速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经济交流,加强并扩大了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据藏汉文史籍所载,自元初开始,西藏地方进入内地的土特产品有:虎、豹、猞俐、野猫、水獭、牦牛等皮革、蕃呢、毛布、氆氇、藏绒、足力麻、羊毛、毛缨、牦牛、犀角、藏香、牛黄、虫草、红花、麝香、良马、青稞、银珠、赭石、佛画像、铜佛、铜塔、藏经及西藏加工制作的金、银及珊瑚制品、象牙雕刻、珍珠镶嵌、甲胄、左髻、典罗帽、藏刀剑等物。而内地的彩币、锦帛、苎绸、绸缎、僧帽、法衣、鞍马、巴茶、陕茶、湘茶、果、米、汉文佛经、炉具、帐房、锣锅、伞盖、幡幢、骡、黄牛、乘驼、姜、盐、土布、纸张、书籍、印刷术、瓷器、绮衣、绢衣、蒙族衣饰用具等,也通过上述方式传入西藏。以元初为例,萨迦班智达在致乌思藏各地信中提及向元朝进献的方物有象牙等14种。(43)而元世祖赏赐八思巴的物品则有坎肩、金爵等17种。到了明代,明成祖赏给大宝法王的物品有牙仗、交椅等20种,且多数为生活日用品。(44)西藏向明廷的贡品也在20种以上。
茶马互市及贡赐所带来的补偿贸易的发展,使西藏及藏区在一些交通线的交汇点上,形成了一批新兴城镇。特别是在藏汉毗邻地区,如西藏的昌都,安多的结古、拉卜楞,川康的打箭炉、甘孜、松藩等地。以打箭炉为例,元明时期,该地以西藏为依托,汉藏间的贡道及互市经过此地,遂由荒岭峡谷成为交通枢纽及经贸重要站口。(45)汉族及藏族商人经营茶叶及其它物资贸易的行栈“锅庄”,就创始于元代。元代仅陕西商人在甘孜一地已达300人以上,明清以后甚至在打箭炉城内形成一条陕西街。(46)
元、明时西藏与祖国内地经济交流的加强和深入,使西藏经济繁荣发展还表现在纸币的流通和使用。1959年,在西藏原萨迦政权中心地萨迦寺发现了因多次流通而磨损的元代纸币,就是元中央货币在西藏流通使用的珍贵证据。这些纸币一是元前期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的“至元通行宝钞”,票面二贯,值银一两;二是元后期至正年间(1341—1367)印制的“中统元宝交钞”,票面一贯,当银五钱。这两种纸币均是元代不受时间和区域限制广为流通的国家货币。
元明时期在中央扶助下的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往来充分说明:其一,在祖国大家庭中藏汉民族是相互依存的,经济上是互补的,谁也离不开谁。其二,西藏地方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特殊政策的资助下,经济文化才能不断繁荣和发展。其三,通过贸易往来,不但可以促进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可进一步密切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注释:
①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②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38页、42页;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③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页。
④《汉藏史集》第180—181页;《元史》卷101,站赤条。
⑤《元史》卷15,世祖本纪12;卷17,世祖本纪14;卷25,仁宗本纪1。
⑥《明史》卷331,西域传。
⑦⑧参阅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二期。
⑨《续文献通考》卷29;《明宪宗实录》卷78。
⑩《明宣宗实录》卷10,《松藩县志》卷8,《明宪宗实录》卷179,《明孝宗实录》卷122。
(11)《明世宗实录》卷9,《明武宗实录》卷13,《明代宗实录》卷210附28。
(12)陆莲蒂、孟庆芬译《元朝十一篇藏文帝师法旨》,载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历史室、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藏文史料译文集》,1985年版。
(13)《明太宗实录》卷151。
(14)《明太祖实录》卷220。
(15)《明太祖实录》卷251;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9。
(16)《明经世文编》卷115。
(17)《续文献通考》卷22。
(18)《明会典》卷37。
(19)《明宣宗实录》卷2。
(20)参见赵毅《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21)《萨迦世系史》(德格版),第152页。
(22)《元史》卷15,世祖本纪12;卷17,世祖本纪卷14;卷19,成宗本纪2;卷25,仁宗本纪1。
(23)《明成祖实录》卷47。
(24)《明神宗实录》卷81。
(25)《明会典》卷112。
(26)《明会典》卷31、卷113;《明宪宗实录》卷33。
(27)《明武宗实录》卷162。
(28)《明宪宗实录》卷150。
(29)《明英宗实录》卷177。
(30)《明代宗实录》卷232。
(31)《明史宗实录》卷457。
(32)《萨迦世系史》,第97—98页;《元史》卷24,仁宗1;卷27,英宗1。
(33)《明太宗实录》卷62、卷64。
(34)《明神宗实录》卷169。
(35)《元史》卷9,世祖本纪。
(36)《明史》卷331,西域传。
(37)《明太祖实录》卷256。
(38)《明实录藏族史料》,《英宗实录》。
(39)同③⑧
(40)《明史·食货志》卷80。
(41)王圻《续文献通考》。
(42)《明英宗实录。卷66,《明代宗实录》卷232,《明宪宗实录》卷150。
(43)《萨迦世系史》第78—81页;《明会典》卷108。礼部;《明史》列传219。西域三;《西番馆译语》来文二。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44)《明太宗实录》卷63。
(45)《圣武纪》卷5,《西藏后记》。
(46)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区州概况》,四川民族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