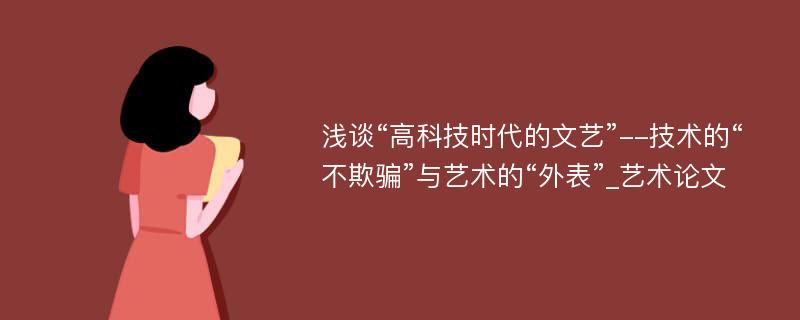
“高科技时代中的文艺学”笔谈——技术的“去蔽”与艺术的“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笔谈论文,高科技论文,艺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堇命以来,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甚一日。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文化同样无法避免科学技术那咄咄逼人的攻势。如果说,近代理性文化中的那种强烈的人文精神正在因理性的技术化而萎缩,那么,技术霸权下艺术怎样“出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文学艺术曾被当作“救世”的重要手段。在现代主义时期,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地位得到确立之后,艺术以一种抵抗的态度对待技术。现代主义时期的思想大师们,大都对技术的霸权地位发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抗议之声。海德格尔虽然承认技术与艺术都可以“去蔽”,但作为一种“装置”的技术却阻碍着人的思维;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使人的生存走向自由,反而更深地危及人类的精神。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比海德格尔激进得多。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用满足物欲和普及技术理性的方式造成了工业社会中的“单面人”现象,他认为,技术的发展等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也等于人被奴役的程度加深。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极力推崇以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来对抗技术理性的现代主义艺术。
后现代文化形成以后,思想大师们似乎不像现代主义时期那样对技术存有戒心了。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承认,技术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利奥塔对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追求的那种整一性观念表示反感,主张“叙事知识”应当在科技知识霸权体制中寻找新的合法性通道。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后现代技术造成了人们对客观外部世界和主观心理世界的新观念,只是我们主体的感觉方式还停留在现代主义时期,没有作出应变。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甚至认为,后现代技术与人文精神正在相互靠近,“祛魅”的科学已开始“返魅”。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使得“第一生产力”作用下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龟缩在象牙塔中去寻找不食人间烟火的纯艺术是非常可笑的。在DNA学说教给我们以一种新的生命观念、Internet把我们纳入一种新的人际交往方式的时代里,我们还可能按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感悟方式去表现人的生命经验吗?
冷兵器时代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的故事在远程打击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时代决不会重演,因为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文对自然的胜利,人文的胜利又是以技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被称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已脱离了由自然物或被驯化的自然物构成的时代,构成现代人生活世界的物品技术含量日益增强,因而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支配性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科学技术也必然地影响到人类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也就是艺术不可能逃离技术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李政道先生经常找一些画家谈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艺术可以表现某种理论物理学的观念。好几位国画大师曾为说明诸如宇称不守恒之类的原理而泼墨作画。其实这种做法中包含着两个明显错误的观念:首先,科学与艺术之所以共同存在于人类文明之中,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或表现对象,艺术不能替代什么,但什么也不能替代艺术。如果说科学与艺术表现的是同一内容,那么,以科学之精确清晰,艺术何必存在?其次,艺术家决非编撰看图说话之类识字课本的普教工作者。真正的艺术家,是要用一种独创的形式去领悟那只能用艺术去领悟的东西,我们不能将艺术当作抽象真理的通俗说明。
在科学技术大潮席卷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用直线因果的逻辑图式来说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危险的。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技术至上主义。但是反过来说,对技术大潮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乃至于不承认现代高新技术将改变经典艺术的既定范式,就表现出抱残守缺的僵化。我们应当研究的是技术以何种方式、在怎样的条件下对艺术发生哪些层面上的影响。
从技术影响艺术的过程来看,艺术并不是直接从科学理论或技术方法中领受启示来打造创作的方法。对特定艺术形态起作用的是特定的人类生存状况所形成的人与世界的特定关系。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是以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者的身份决定着人的生存状况。因此,技术必须首先成为生产方式,继而形成人类生活的物品或手段,最终演化出人与世界的特定关系,由此才可能对人的艺术观念发生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必须经过产业化才能影响文化生活。书斋化或实验室化的科学技术无法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也就无法改变艺术。科学技术产业化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变成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物品和新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形式。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和马克斯韦尔方程,前者几乎与人类现实生活无关,而后者通过电磁学的产业化而变成了一种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所以,科学技术首先必须产业化,然后才能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对艺术产生影响。
站在艺术一极来看,对艺术发生影响的也并非所有能够产业化的科技。艺术有属于自身的感悟方式和理解对象。作为人对自身生命形态的理解和作为人类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的艺术,最关注的是怎样感悟我们的生命和怎样实现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只有那些能形成特定的有关生命形态或人类交流模式的科技,才能通过其产业化影响到艺术。比如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技术使我们用基因组合的概念来认识人的生命表征,而电子信息技术则为我们营造了互联网这样的代码化交流的空间,这两种技术所形成的感悟方式、表述方式及价值原则,我们可以在后现代艺术中鲜明地感受到。从传播技术的角度看,书写、印刷、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这几种传播技术,在形成一定的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范式。而一些与人的生命感悟或人际交流相距较远的技术,往往与文学艺术关系也较淡漠,比如深海探测技术。
即便是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感悟和交流方式且能够产业化的技术,也并非将其全部功能和内涵施之艺术之上,技术进入人的生活可能在三个层面上发生,即,技术物品的层面,技术方式的层面和技术化观念的层面。技术物品即由技术生产出来的生活物品,技术方式即由技术提供的某种生活程序或行为方式,比如由SOHO工作模式带来的弹性工作时间。这二者对艺术肯定会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表面的,真正介入到艺术内核之中对之施加影响的,是借技术物品和技术方式得以“出场”的、潜藏在技术背后的那种理解宇宙运动之规律的观念,技术依赖这观念而得以形成,这是一种技术化的宇宙观,以对宇宙运动或生存现象的基本界定为其内涵。比如19世纪科技中,经典物理学透露出的一种基本的技术化观念就是:力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运动”构成了宇宙现象的内涵。现代高新技术则通过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各种物品或手段表现出一种以“代码”和“结构”解释生命状态和人类社会的观念。从艺术特性根本上来自于艺术主体对宇宙人生的理解这一意义上来说,技术化观念对艺术的影响是本质性的。比如,19世纪文学大量描写社会生活中的冲突矛盾,不能说没有受到“运动”概念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充斥的虚拟幻像,也让我们看到了高新技术中的“代码”概念。所以说,研究技术对艺术的影响问题,应当首先研究包含在技术物品和技术方式中的那种技术化观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对人类生活发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影响,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把人类的交流方式带出了被大众传播媒介控制的时代。互联网提供的交流平台是一个民主化的“聚会”场所,它完全取消了大众传媒的那种话语霸权。在以印刷品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中,话语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言说者(比如作家)把他声称的真理像发布皇家广告一样向大众宣告,于是形成了一种霸权化的宣言式话语,这就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孤芳自赏的风格。互联网时代的交流摧毁了话语霸权,这就是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指出的那种“通讯交流”模式。通讯交流为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提供了言说的权利,它将使文学艺术的创作变为一场“话语聚会”。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的所谓网络文学还不是真正的网络文学,这些以网络文学为名的文学只是把传统写作模式创造的文本贴到网上发布而已。真正的网络文学只能在网络交流中产生,它必须体现网络时代人际关系的特征。
生物工程技术赖以产生的基因学说在理解人类生命性状方面带来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进化论把生命体的性状理解为生命体与环境间冲突、适应、演化的结果,于是在人文精神领域中也出现了一种以事物相互运动过程为中心的理解方式。日本语言学家西槙光正就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派是进化论普及的产物。DNA学说的建立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对生命体表征的理解方式。该学说视生命现象为代码组合的结果。一切生物体的外表特征都可以用特定的代码(碱基对)组构方式来解释,甚至可以将不同的生物体某段代码相互转移拼制出一种貌似自然却纯系人工制作的生物体来。生物工程技术把基因学说中的这种技术观念普及到人类精神生活之中,使人类文化的那些传统概念,比如艺术的真实、人的历史性等等,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代码拼合的艺术生物工程,它只有各种代码组合成的虚拟幻像,没有由社会历史内涵构成的整一性观念。
有些论者惊叹于技术占据了当代社会“国教”的地位,以至于艺术已接近终结。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论题换成技术时代艺术“出场”方式的变化,结论就可能不那么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