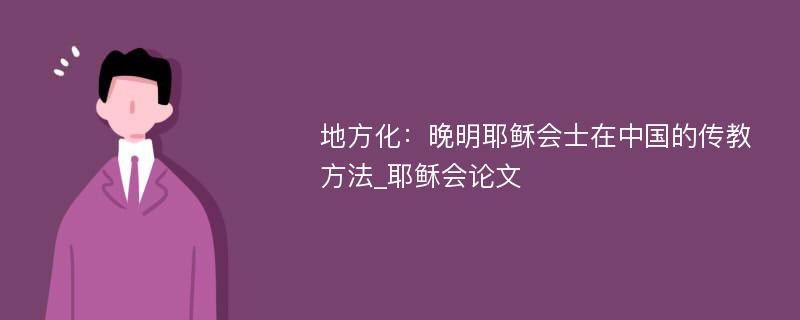
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稣论文,本土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复兴的中心是人文主义,这一文化现象强调人类世俗的现实以及人的能力。16世纪的人文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它与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令人敬畏的宗教神灵启示和激情紧密结合。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主要人物有圣方济沙忽略(1506—1610)、范礼安(1538—1606)、利玛窦(1552—1610)和艾儒略(1582—1649),他们本质上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能够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宗教神灵启示的精华和非凡的科学知识以及能力综合于一身,甚至按现代的标准看,他们也有着非凡的的开放思想。在他们身上时而和谐时而冲突的综合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复杂性中温和的特征,以及那些意识到来自上帝的最高使命的人的强大人格特征。
天主教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新的宗教会众的出现,这是改革的任何阶段都有的一个典型特征。16世纪诞生了Teatins(1524), Capuchins(1528),Bamabits(1533),Oratorians(1560), 但最重要的是耶稣会士的出现(1540)。
圣依纳爵劳耀拉(1491—1556)是耶稣会的创立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中世纪的宗教激情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世界和未来的宽广视野是共存的。新诞生的传教团的第一个理想是传教的理想。对教皇格外服从的第四誓约,与其说是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和耶稣会士的服从精神,不如说表达了会士对耶稣会整体有效性的肯定,也表达了会士极其希望被派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传播教旨。
在耶稣会的《宪法》中,依格纳爵根据埃及掠夺物在艺术品中的反映这一事实,认为对非基督徒典籍的使用是正确的。这是理解耶稣会通向本土化方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依格纳爵看来,古典文学的学习至少有三个目的。首先,有必要学习原初文本中的圣经,因为它曾在严格的人文主义者的规范下实践过;其次是关于宗徒的目的,即培养出在文艺复兴的知识界中竞争的能力,使能够通过人类科学的文化媒介传播信仰;依格纳爵还认识到古典文学有伦理道德和对人的培养进行薰陶的价值。
耶稣会的学习课程很丰富,包括诗、修辞学、逻辑、自然科学、伦理、形而上学、数学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会士才真正开始神学的学习。因此,神学并非学习的起点,而是终点。在当时,很多新教徒片面地强调上帝恩宠的力量这些论题,甚至于宣告人无任何善的能力。而耶稣会士则重新肯定了造物的价值。造物由上帝创造,并带有他的形象特征。他们思考自然启示和实证启示、自然和恩宠、创造和赎罪的差别,这些观念对后来阐释中国的典籍极具价值。耶稣会士不仅大量吸收文艺复兴的思想,其自身也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推动者和传播者。正因为如此,耶稣会在那些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区域扎根下来。同时,人文学者也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对耶稣和现代灵修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基督论倾向:回到精神化的教会,在人的维度上重新发现耶稣,耶稣的人性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认神学的中心。
由于它的新式制度和教育,耶稣会很快吸引了欧洲各国青年中的精英到它的学校学习。学生想进入耶稣会,就得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过程。耶稣会士掌握了古代和近代的学问,在经院哲学的技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他们很快成了欧洲最有才能的人。耶稣会也能根据不同情况向其成员分派各种各样的重要工作。由于他们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优越,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常常在政治界和知识界拥有很高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政治、智性和宗教方面对天主教改革的贡献显著。
罗马学院于1551年由依格纳爵创立,它成为耶稣会最重要的培训中心。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最好的教师的出现,如克里斯托夫·克莱甫斯( 1537—1612)、格里恩柏格·谢纳、 贝拉尔诺(注:从教辩论课的罗·贝拉明那里,利玛窦学到了对教义的清晰的解释,后来他将这些用于在中国的实践。)(伽利略也是那儿的一个客人),罗马学院成了世界上最领先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学生们在学习结束后被派往世界各地,他们与各自的教授通信,寄回工作所在国的消息,如月食或日蚀、地理、动物、习俗和文化。在这些学生中有范礼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1591—1666)、卫匡国(1614—1661),以及其他一些将推动中国传教业的人。(注:《拉奎因,一个文化灌输的例子》第32陈述了若没有传教士在耶稣会学院接受的这种背景,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
一、本土化:一个历史的神学的本质的适应
本土化是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传教政策的关键。他在其著作《DellaEntrta》中谈及以善事为目的的传教团时使用了此术语。他认为传教团必须做到“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去修正和适应”(emandataed accomaodate al modo deela christianity )(注:选自《强大的》第481~482页。《中国对利琶窦思想的接受》,N·施坦达特, 载《光明的生活道路》,1985年,第53页。)。
本土化早在耶稣使徒时代就实行了。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使德行传》15,1—31),保罗对待犹太人的方法,以及他在雅典的布道, 这些都是本土化的例证(注:佛斯:《远东的传教本土化和祖传仪式》,载《神学研究》1943年第4期,第527页。色比斯:《东方和西方的桥梁》,第3~5页。)。许多教父和早期护教者追随这一方法,并进一步发展了它。早期的护教者从希腊哲学家那里借用了智力辩论这一方式来维护和解释基督教教义。中世纪的神学家则是他们的追随者。
传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文献是和里高利教皇给阿柏特·梅利突斯的训导,梅利突斯是康特拜瑞的奥古斯丁的传教同事。据佛斯所言,这就是传教本土化的《大宪章》。
“告知奥古斯丁,他不应破坏诸神的庙宇,更确切地说,不要破坏这些庙宇中的神像。在用圣水洗净它们之后,让他们把神坛和圣德的圣物放在那里……看到他们敬仰的地方没有遭到破坏,人们将会更容易从心中去除错误,赞美和敬仰真的上帝,因为他们来到熟悉而亲切的地方……他们祭献和吃掉的动物,不再是对魔鬼的奉品,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将把上帝当作万物的创造者而感激上帝。”(注:冯·比德:《英国非犹太裔传教士的历史》,翻译同前,第528~529页。)
1658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给东方传教团寄了一份重要的《宪法》,根据这文件要求,传教士必需拥有丰富的语言知识,以便能够使用当地人的日常语与本地方言完成传教职责。传教士不能依靠外力和各种承诺,应从信仰上驯服非基督徒,要依靠对上帝言语的传教和优秀著作的例证;每一次教义问答活动的具体处理以及他们交谈的动机都应该写成报告;洗礼时的训导务必充实,以便不让新入教者对基督的法规与非基督徒的法术,真正的信仰与偶像崇拜相混淆;在训导过程中,传教士应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最好不要,或尽可能少地采用肉体惩罚方式。1659年,信仰宣传处也发布了一个文件,支持基督教的本土化与本地化。
17世纪末和18世纪期间,中国的本土化在形式上有所堕落,这一点我们在所谓的圣像崇拜者(注:圣像崇拜者在中国的经典中发现了《圣经》和基督教的所有真理和图像。P ·儒勒:《孔丘或孔子:耶稣会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悉尼/伦敦/波士顿,1986年版,第150~182页。)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本土化决非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传教的需要,它其实有自己深远的教义基础。本土化不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不仅仅只是方便和妥协,而是基督精神本质所要求的。经由梵蒂冈二次大会和教皇保罗四世,本土化的神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已有了极大进步,本土化这一概念获得了新的涵义和术语。
二、圣方济沙忽略的经历
中国近代传教团的历史开始于一位优秀人士——圣方济沙忽略。他在日本创建的传教团(1549年8月15 日)对后来中国的传教团产生极大影响。经过三年的福音传教,日本前景可观,但沙忽略却希望日本能转变得更快。沙忽略以一种后来对远东的传教团影响至深的方式系统地进行实践。他强调传教士的文化修养之必要,以便能够灵活地同儒家人士和佛教徒打交道。他也提倡科学知识的修养,把这作为吸引别人对传教内容感兴趣的方式。
认识到一定的本土化对于实现目标的必要,沙忽略乃是第一人。但由于缺乏经验,沙忽略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使他困难重重。沙忽略的一些经验后来对中国很有用,他也指出,儒家思想和佛教不仅影响了文化和个人品格,且对社会群体影响巨大,而这两者都是自中国传入日本。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沙忽略认为应该首先改变中国,然后才是使日本皈依。他怀有一个流俗的想法,认为通过使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皈依,便会自然改变整个国家。因此沙忽略想方设法接近当时的皇帝,却最终仅仅只是意识到,真正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儒教官吏阶层的手中。
从他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少量信息中,沙忽略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皇帝的权力远较日本有效。他因此决定以政府代表身份赴中国见皇帝。但由于一些政治人物出于嫉妒的干涉,沙忽略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能获得他所希望的合作。他遭到出卖,只身离开了中国。《神父之路》一书再次表明这一计划与他的宗教事业是多么地不相干。尽管如此,沙忽略仍打算经由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到达中国,他所等待的船夫却一直没有出现。沙忽略病逝于1552年12月3日,终年46 岁,死前身边仅有一名从澳门来的基督徒相伴。
三、中国本土化之父:范礼安
范礼安是在远东地区的第二位伟大的基督教传教士。1570年他作为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旅游家到了日本。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乃是实践了沙忽略所追求的本土化方法和在中国开始传教的设想。由于属于不同教派的60多个传教士努力试图在中国建立根基,却总不能成功,范礼安对这种失败的尝试认真地做了反思。与沙忽略一样,范礼安在日本的经验也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组织活动。玛利窦曾亲口称范礼安为“耶稣会传教团之父(Padre di questa mission )”(注:利玛窦致总会长阿奎维瓦的信(北京,1608年8月22日),《接受的历史》第299页。转引自N ·斯坦达特《中国对利玛窦思想的接受》第56页。)。近代学者N ·斯坦达尔特则断言“没有范礼安,也就没有利玛窦”(注:利玛窦致总会长阿奎维瓦的信(北京,1608年8月22日),《接受的历史》第299页。转引自N ·斯坦达特《中国对利玛窦思想的接受》第56页。)。
首先,范礼安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他清楚地看到在福音传教中使用翻译人员的不便,而且他还认为仅仅只是学会口语并不够,还应学会书面表达和写作。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丰富,愈发肯定必需了解中国的经典。他要求罗明坚,尤其是利玛窦去研习中国经典,把它们译成拉丁文,更深地加以理解,以便能够在护教和教理著作中加以引用。他要罗明坚学习汉语经典并写出第一本汉语教理书,即1584年出版的《天主实录》,它由一本在日本出版过的书的要点编写而成。后来范礼安要利玛窦重写这本教理书,要求尽量多地参考中国经典。范礼安指出,一旦在中国建立了基础,传教士应穿着佛教和尚的法衣来强调他们传教的宗教特性。范礼安提倡基督教的本土化。与在日本(以及印度)传教士的普遍倾向相反,范礼安对于依靠本土人的能力来提高传教士事业的质量有着极大的信心。他清楚教会必需当地化,而国外传教士根本无法仅凭自身来承担这个宗教事务。他还试图在北京设一公使馆,但最终采纳利玛窦的建议放弃了这个沙忽略设想过的旧计划。罗明坚在1587年被派往罗马与教皇一道组织公使馆。利玛窦为实现这目标,花了十多个年头在北京同皇帝交往。最后,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传教并不需要一个官方使馆,皇帝的统治并非直接由他本人予以贯彻,而是经由一个庞大的太监和文职官员的官僚系统来完成的。此外,中国人并不熟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他们喜欢听人进言甚于协商讨论。一旦明白了中国人惯于以沉默的忍受来表明他的认同,而不是诉诸法律行动之中,利玛窦便放弃了让基督教获得官方认可的打算。
四、罗明坚与利玛窦
罗明坚最大的荣誉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被承认的基督教传教团的创建者。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普格利亚。1579年,罗明坚到澳门贯彻由范礼安开创的新传教方针。他学了几年中文,并成功地与广东省的一些中国官员建立了联系和交流。1583年9月,由利玛窦相伴, 他在广州西边的肇庆定居。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耶稣会的开始。1584年他写了第一本汉语教理书《天主实录》。
罗明坚在一句著名的话中表达了适应的精神:“为把中国基督化,我们已变得像中国人(Siano fatti ut Christo Sinas Lucrifaciamus)”。
利玛窦更是受到高度赞扬,有称之为“历史上最杰出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注:J·尼德汉姆:《中国的科学文明》, 剑桥版, 1956 ~1976,第一卷第140页。尼德汉姆尽管对耶稣会不无微词, 但他的这一评价却非常之高。),有称之为“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使者”,还有称之为“一个不朽的人”(注:W ·弗兰克勒:《利玛窦》,录于《明代词典》1137~1144页;D·E·穆戈勒《奇异的土地:耶稣会本土化和汉学根源》,斯图加特版,1985年,第54页。)。中国学者郭其昌(音译)声称利玛窦应被视为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异邦人”。另一个中国学者沈德福(音译)写道:“我以前住在京都时,利玛窦是我的邻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曾发誓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改信他的教义……。当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时,利玛窦也并不固执。他总是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于危难。人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与善良,也常常感激他,回报他。”(注:色比斯:《东方与西方的桥梁》,第62~63页。)
有关利玛窦活动的记述将可成为直到艾儒略到达中国为止的整个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年表基础。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玛色拉塔,早于沙忽略逝世两个月。1571年8月15日他成为耶稣会会员,1571年5月18日离开意大利到葡萄牙,1578年秋天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完成学业后,1580年7月26 日他被任命为教士。1582年他被派往澳门学习汉语。利玛窦在1583年9 月10日与罗明坚想尽一切办法,身着佛教和尚的衣服,住在肇庆。自此,他的历史重要性开始直线上升,他想方设法进入明代社会圈。利玛窦长于语言,有极好的记忆力。他是一位迷人的交谈者,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尤其擅长数学与天文学。他的这种包容性使他能够吸收大量的中国文化并形成本土化的策略,“对中国和欧洲文化的汇合而言,这是一个大胆的传教策略,同时也是一条深刻的原则。”(注:色比斯:《东方与西方的桥梁》,第44页。)
1584年底,利玛窦首次印刷出版他自己绘制的著名的世界地图,这引起许多参观者的好奇(注:世界地图(与地山海全图)非常流行,再版16次。见色比斯《东方与西方的桥梁》第30页。)。从1589年起,利玛窦在广东省北部的韵州落脚,并与当地的文吏建立起了亲密关系,同时继续他的汉语学习,还首次创造出罗马拼音系统,完成《四书》的拉丁文翻译。这两个成果使他获得了“西方汉学之父”的称号。
1595年,在赴京途中,利玛窦曾试图在南京落脚,结果没能成功。他转而在江西南昌住下, 在那里他写了第一本汉语著作《交友论》。 1596年,他重写了罗明坚的教理书,即《天主实录》,但此书直到1663年才正式出版。利玛窦获得了护送南京“仪式团公使”赴京的机会,在1598年9月7日到了北京。时值高丽战争,他无法在北京安身。经长时间辗转,1599年的5月,利玛窦终于在南京安顿下来。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决定去北京长期定居。在到达北京之前,他在天津成了一名囚犯,被囚禁在令人极其恐怖的太监马堂达半年之久。在中国的京都,利玛窦充分地显示了他的人格、才能和知识。1610年5月11日,由于压力和过度操劳,利玛窦逝世,年仅57岁。
利玛窦葬礼之隆重和他被允许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荣光,表明了利玛窦为中国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程度已经极其之高。
德国历史学家W·莱茵哈德认为, 利玛窦的方法是不同于欧洲在全世界扩张的残酷种族中心主义的有限几种慎重的做法之一(注:《东方与西方的桥梁》,第17页。)。Y·拉奎因在文章中写道:“今天, 利玛窦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典范,因为他试图在非基督教的语境中详细阐述仪式,给予仪式以基督教的内涵,至少使之具有基督教的倾向。”(注:拉奎图:《一个文化输入的例子》第34页。拉奎图认为既然文化输入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利玛窦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于他的文化输入精神,而不是他的实践方法和结果。)
学者们把利玛窦的本土化方法综述为不同的类型。J ·贝特利把它分为六个方面:外在的、语言的、审美的、社会行为的、智性的和宗教的(注:贝特利:《本土化方法》,贝特利把本土化的六类型说归功于J·索伦,这位传教团的学者在1927年写了一篇关于本土化的文章,D·伊利阿为此写了一篇热情的长评论《适应的方法》,第174~182页。)。据J·色比斯(注:色比斯:《利玛窦的中国与中国》, 载《研究》,1982年,第361~374页。)的说法,本土化则可分为四个方面(注:见《东方与本文的桥梁》,第46~54页。色比斯例举了文化输入的各个方面,却遗漏了伦理学。):
(一)生活方式本土化:包括语言、衣着、食物、饮食方式、礼节、旅游(最典型的是文吏坐轿子而行)等等。
(二)转译思想观念本土化:为解释基督教教义某些方面的意义,引用儒家经典和其他中国文化内容,如流行的成语,故事与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三)道德规范本土化:使用西方道德范畴里中国人所熟悉的概念成分,如友情的价值等等。利玛窦相信基于普遍的伦理基础——自然道德的交往的可能性。他认为使徒的个人诚实与传教内容的可信度是一致的。色比斯有一个奇怪的看法,他认为利玛窦最大的错误想法是把他自身和他同伴的高度品行作为基督教宗教真理的证明。而实际上,利玛窦的继承者并不能达到这种高度。
(四)仪式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基督徒参加儒家的仪式。利玛窦去世之后,这成了中国仪式中有名的难题。
据G·L·哈瑞斯看来,本土化范例包括八个阶段,这实际上总结了利玛窦的整个传教方法:
1.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包括学习中国口语和书面语);2.结交精英人士并建立关系网;3.承担确定的社会角色;4.以基督教的名义提议把学习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一种必需;5.在基督教教义中区分出:可改变的和不可改变的;6.运用西方文化,如科学、艺术、哲学等;7.采用中国社会的交流渠道和方法;8.建立本地化教会的基础。
P·D· 伊利阿和L·古塞慈等学者也总结了同样的基督教传道方式的轮廓(注:D ·伊利阿:《伟大传教士的方法》第二部分《作为基督使者的伟大传教士的方法》,第217~264页。L ·古塞慈:《什么是利玛窦传教方法的特殊之处》,录于《东亚传教回顾》,第20期,1983年版,第104~116页。)。
五、直接和间接传教
除了本土化,传教方式中最新的和最有决定性的方面是所谓的“间接传教”。这一方法是基于对非基督徒一方和神父或牧师及基督徒一方的引导之差异而形成。就像中国经典一样,与非基督徒的讨论风格是争论性和对话性的。这样,对话双方都有机会表示反对及得到相应的回答。利玛窦和文吏们讨论科学、伦理学和哲学。当然他喜欢讨论宗教真理,诸如神的存在、灵魂不朽、善恶在天堂和地狱的报应等。在这些话题中他寻求中国经典中相关内容的支持。讨论会上利玛窦对教义的阐释通常包括八个步骤:神是创造者、人在寻找神、灵魂不灭、人和宇宙其他物体的本体性差异(人和宇宙并非由同一物质所成)、驳斥轮回观和其他的佛教教理、天堂和地狱、基督教的神迹和人之本质(为儒家哲学极好地思考过)之间的联系,最后关于欧洲的宗教、传教士的独身、以及上帝降生的原因。这一框架与利玛窦《天主实义》中提到的很相似。讨论中利玛窦并未谈到基督教信仰特有的神秘,也仅使完全的教理训导给予那些真正热切的皈依基督信仰的人。事实上,洗礼前的宗教训导时间很长,完整且庄严。
在间接传教问题上,耶稣会成员龙华民(1556—1655)和王丰肃(1566—1640)并不同意利玛窦,他们提倡并追求公开讲道的方式。在他们看来,交谈涉及的对象实在太少,利玛窦的传道方式难以影响普通百姓、从乡村来的人,以及妇女与儿童。利玛窦则认为,从整体上影响社会比在一些社会边远地区建立小小的社团要有价值。
六、道理和教理
对应于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的两种方式,中国耶稣会教士的文献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第一,道理,它是和儒家学者的对话及和佛教徒、道家人士的争论中,对基督教的基本哲学概念地初步阐发。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艾儒略的《万物真源》便属于此种类型;第二种是教理,这是为神父和信徒所做的有关基督真理的充分阐释。这两种类型的根本区别是理解耶稣会会士传道方法的关键,利玛窦曾亲自对这一区别及其内涵做过清楚的阐述。许多来自托钵僧们对耶稣会会士的批评便是因为缺乏对这一根本区别的理解。J ·詹尼斯用两个术语来指称这种区别:护教著作(道理)和基督徒手册(教理)。
中国耶稣会传教方法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包括采用科学、技术、艺术和其他的西方文化知识。下面罗列出早期耶稣会会士在中国所传播的西方科学与文化:数学、天文学与日历、地理学、制图法、医药、物理学、建筑学、文学和语言学、哲学与伦理学、美术、音乐。有些学者指责利玛窦使用了他们的知识作为诱饵,来吸引中国人进入教会。中国历史学家冯天瑜(音译)则认为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来中国传播他们的宗教,但实际上却留下了科学遗产。约瑟夫·谢哈也指出:“难道是利玛窦脱离了他的传教使命,以传播科学来代替福音书的传教?或者说他的行动是一个没能实现其目标的策略?中国人吃掉了诱饵(科学),却没有落入陷阱(宗教)?”(注:J·谢哈:《使者利玛窦》,第 37~38页。J ·堂也对近代中国的学者钱穆和侯外庐对利玛窦把西方学问引入中国的批评作了回答。J ·堂:《利玛窦的贡献——对两位中国学者观点的反响》,见《鼎》,1982年12期第112~121页。)正如已经指出的,表现西方文化知识意味着提高了利玛窦和他同伴们的声望,并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价值,由此也就显示了传教团宗教教义的价值。其中包括:试错的方法、向上层阶层的传教、在礼仪中推广使用本地神职人员和汉语、培养和支持教友团体,在这一切中,利玛窦向具体的事件和敌人学习,从中国朋友处吸取建议,继续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利玛窦对使中国福音化的困难并没有很清楚地把握:在中国工作的多年时间里,他用来与中国人进行交谈的方式和方法的确在变化。利玛窦既诚心又灵活,以致他和他的同伴不仅试图理解和适应中国,而且也为中国所改变(注:D ·穆戈勒:《利玛窦:本土化步骤和当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趣与关注》,录自《笔记》,1978年第36期,第37页。在同一篇文章里,穆戈勒指出了利玛窦方法上的框架:生活方式的适应、精英阶层的友谊、基督教的本土化、运用科学、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本土化。穆戈勒指出,既然分歧在中国就是一个表示虚假的信号,压制性的教皇规定以及与其他传教团间的分歧,是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成功甚微的原因。)。
(本文系作者1998年4月22 日在浙江大学比较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原文16000字,编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