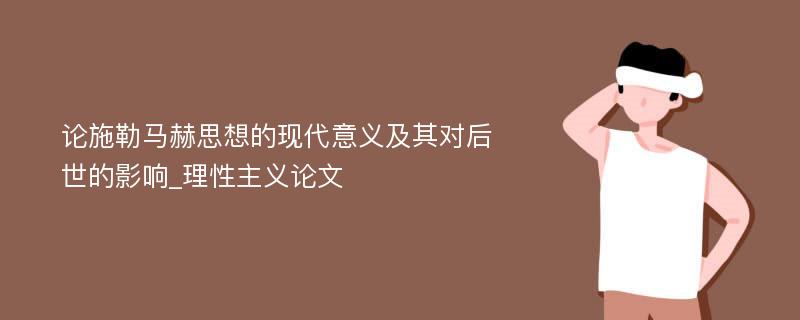
试论施莱尔马赫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赫论文,后世论文,试论论文,莱尔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家的现代意义,总是和他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推进和解决他所生活的那个年时代的文化精神所面临的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说,康德那一代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文化精神问题,是如何推进德国的启蒙运动,进一步确立科学理性精神,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的话,那么,在施莱尔马赫所生活的“后康德时代”,哲学家所面临的文化精神问题,更多的是对康德所确立的“范式”的反思。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心灵世界的领悟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施莱尔马赫从神学、哲学、伦理学、释义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等方面,推进和建构了德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世界。可以说,在上述各个领域,均确立了其不朽的丰碑。
一、神学“现代性”的开拓者
“现代性”主要是标示西方现代“知识状态”的概念,它包含了西方现代的精神结构、话语方式、价值倾向、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等。神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能够为现代人提供精神信仰的那种神学形态和信仰体系。施莱尔马赫时代的德国,为人们提供信仰的,主要是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且两者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虔敬派强调上帝神性的崇高与伟大,人性的有限性和原罪,因而要通过信仰基督教而得救;理性派强调人的理性的万能,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因而强调通过社会的理性化来推动人类进步和世俗生活水平的提高。虔敬派说理性派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必定带来道德的堕落,生活的腐化,失去内在的灵性;理性派则指责虔敬派拒斥科学,愚昧无知,心灵病态。在虔敬主义神学襁褓中长大的施莱尔马赫,优于一般虔敬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深入研究和领会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尤其是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从而能以科学精神为武器,对传统路德派的正统神学教条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而他优于一般理性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对神性的虔敬,使他能对理性的盲目乐观主义和自大狂始终保持着警惕。因此,施莱尔马赫一直确信,在彻底由自然律统治的世界中,仍有人类必须崇敬的最后神秘之处;可以说,施莱尔马赫正是把康德的科学理性信念同虔敬派的神学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才超越了虔敬派和理性派神学,开创了“现代性”神学的典范。正如汉斯.昆所言:“在施莱尔马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现代人的神学家。”(注:汉斯.昆《基督教的大思想家》,1995年香港中文版,页170。)
这种“现代性”神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在宗教观上,不把宗教看成外在于人的仪式,而是从人的内在精神需要、从人的直接自我意识、直观、情感和灵性出发,把宗教真正发展成人的“心灵的宗教”;在信仰上,把情感和理智结合起来,既不把上帝看作外在于世界和人的万能的主宰,也不把上帝当作形上学的“实体”和种种知识论、道德论的僵死的“概念”。上帝是无限发展了的和完善的人性本身,是人的生命活生生的高级潜能,因而成为人本主义的人性理想。在教会观上,既反对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合一而导致的专制与腐败,也反对取消教会的一切偏激行为。他把教会看作是所有虔敬的人自愿组成的自由团体,是在一起宣讲和倾听圣言、交流宗教体验、领悟上帝成人的生命之光的场所。因此“教会史的新时期在他这儿达到了神学上的成熟”。(注:汉斯.昆《基督教的大思想家》,页170,版本同前。)在研究方法上,他也自觉采用了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历史批评法,对圣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解神话”活动,不仅使圣经更易于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而且,他的圣经解释学也发展成为现代神学、哲学和文学的普遍方法论;在文化效果上,他的神学思想使他的时代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怀疑、批判和不信之后,又重新确立了宗教信仰,使人既能是“现代的”,又能是“宗教的”,从而也使他自己真正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和知音。因此,施莱尔马赫名符其实地成为“现代性”发轫之际的现代典范神学家,他的著作成为宗教哲学、信仰学、教义学和释义学的现代经典文本。
二、现代人文精神的推进者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文里,都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不想陷入概念史的详细考证之中,而只想从西方的原义,引出我们的基本用法。从词根来看,西文的“人文主义”(Humanism)直译过来,就是“人(Human)学主义”,“唯人论”,或者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西方的“人文主义”,实质上,并不是指一个统一的哲学学说、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指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经过启蒙运动(包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种种“人文主义”哲学)、浪漫主义所形成的一种尊重人的价值、地位、注重人的修养,以人为出发点的思想倾向和信仰维度。因此,在这一传统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思想家,他们对人文主义这一文化精神资源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同的。那么,施莱尔马赫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或者说,他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人文精神的养成呢?第一,他把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声势浩大的理性化、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中,施莱尔马赫之前的宗教神学,虽然也在不断地改革,以适应人文主义的价值演变,但是,路德派神学家主要还是生活于前哥白尼的心态中,基本上立足于中世纪的、天使与魔鬼对立的世界,对其它的信仰形式不能宽容;加尔文宗的宗教伦理,虽然对财富让了路,为世俗化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但是他那严格而阴郁的教规,也容忍不了自由的、批判的理性精神存在,只有在施莱尔马赫这里,人文主义和宗教信仰才真正结合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对上帝的信仰,不是来自神学的论据或基督教教条,而是来自人的自由意识,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来自他所说的“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的生活,又不受时间严格规律的约束。”(注:转引自[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53。)因为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信仰中,耶稣基督,不是外在于人、外在于世界的神,它既有真实的人性,又有真实的神性;它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高级的潜能,是一个无限扩展了的完善的人性理想。因此,在基督中,上帝意识是塑造整个人格的原则。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念,既是虔敬信仰的,又是理性批判的;既是超越的,又是在世俗此岸实现这种超越;既对上帝有绝对的依赖感,又是人性自由意识的最充分表露。这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念,是西方精神界的一次灿烂的日出,把施莱尔马赫推上了“十九世纪西方的教父”的宝座。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唤醒了人们长期被世俗的物质功利所拖累的灵性,而且为人的精神重新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支柱,为塑造西方人的人格精神和教养找到了主要的原则。
第二,施莱尔马赫为在学校教育中,弘扬人文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施莱尔马赫当时受洪堡之邀,一同策划、组织普鲁士的教育科学体制。他们按照瑞士教育改革家皮斯塔洛茨(Johan Pestalozze Pestalozzi,1746—1827)的方针(即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主张教育要以具体经验为基础)改革基础教育,创建了人文中学(Gymnasium),以学习希腊、拉丁文、德语和数学为基础,培养学生的个性。他们还创建了柏林科学院和柏林大学。在施莱尔马赫的论文《德国式大学的基本构想——论即将建立的一所新大学》中,(注:关于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可参阅拙著《施莱尔马赫》第一章,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他完全按照人文主义理想来设想伯林大学的院系设置,使该校成为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高等教育楷模。施莱尔马赫后来还在洪堡的推荐下,担任过普鲁士教育部的一个处长,亲自主管教育改革。不仅如此,施莱尔马赫在教育实践中,以其丰富的知识、深厚的教养、全面的才华所作的每一堂深受学生欢迎的讲课,也堪称人文教育的典范。另外,施莱尔马赫不仅在其《教育学》专著中,阐述了其丰富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而且,在其《基督教家庭讲道集》中,对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也有一系列独见,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光辉:“荣耀你孩子的独特与奇想,以使他们能健康发展,使你的孩子能在此世中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因此,在德国人文主义教育史上,无论是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都留下了施莱尔马赫的痕迹。第三,施莱尔马赫从哲学上,将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同浪漫主义的个体性原则结合起来。既防止了它们各自的偏颇,也为僵化的理性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主体性(Subjektivtaet)原则的确立,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从知识论、价值论和生存论上,都确立了以“自我”(Ich,Ichbeit)的在场性为基础和中心的原则,成为人文主义的哲学表达和最高阶段。然而,在认识论的“主体性”中,实际上,是以极其抽象的人类普遍的“自我意识”为主体;在价值论的“道德主体性”中,实际上是以人类实践理性的“自律”为主体;这些学说,虽然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有助于确立人的主体性,但实质上,活生生的个人被抽象为理性的概念,被各式各样的人的集合体(诸如国家、市民社会、教会等)和体现人的价值的理念(诸如“自我”、“理性”“法权”等)所架空,失去了其内在的生命活力。
德国浪漫主义的追求,正是要以“流动着的生命”反对“僵化的存在”,以充满感性魅力的个人取代干枯的理性“主体”,以富有天才创造力和丰富的艺术修养的诗性人格取代老成持重、精于算计的理性道德人格。因此,在德国刚刚兴起的这种浪漫主义所实现的一次重大的价值转变在于,使创造性的生活高于模仿性的认知,使感情的价值优于理性的价值,对自然与审美的崇拜取代对理智和逻辑的崇拜。总之,是要向理性主义高高在上而又抽象干枯的“主体”注入鲜活的浪漫内容。施莱尔马赫从一开始,就深刻领悟了浪漫主义的这一价值转向,把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个体性”哲学,这在其伦理学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与康德主体性道德学强调主体的立法意志不同,施莱尔马赫使个体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和爱情成为其学说的核心。“人”不再被要求成为没有欲望冲动的纯粹“善良意志”的主体,人的“自然性”即“本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人”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这样,许多真正属于人的生活的主题,如家庭、两性关系、爱情、幸福、信仰、财富,甚至连经济、政治和教会生活等等,也都进入其伦理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就大大扩展了康德责任伦理学的界限,为人们在各个方面所应具有的“德性”、“品质”和“能力”这些人文主义的“教养”,提供了一份可供选择(而不是康德命令式的“你必须……)的价值范型。
当然,无论是“主体性”哲学,还是“个体性”哲学,它们都是人文主义的重要理论表现形式。但“主体性”哲学突出强调和尊重的,是人的理性能力和社会的理性化,从而使人和社会都成为“单面的”。个体性哲学意在把个人的生命作为哲学的根本,反对理性主义对人的抽象化和单面化,使人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即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理智的;既注重科学的认识,又需要宗教的信仰。在这种“个体性”的哲学中,施莱尔马赫说:“要想使伦理学本身,作为对人的完整规定(die ganze Bestimmung desMenschen),成为最高的科学。”(注:《施莱尔马赫选集》,卷一,汉堡,Felix Meiner出版社,1981年德文版。第23页。)。
在德国,他们把人文主义与Bildung(个人修养)等同起来,(注:参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51页,版本同⑤。)而这种个人修养又同理性主义的“自我主体性”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缺点在于,个人可能总是封闭在“自我”的狭小范围内,只顾自己,而不关心集体和社会。而施莱尔马赫的“个体性”原则,即使人成为个体的,又使人成为集体和社会的;集本要以个体性为基础,个体要以集体为皈依。他说:“绝对集体性的东西,要再次成为个体性的东西;个体应该再次进入集体。”(注:《施莱尔马赫选集》,卷二,第91页,版本同7。)在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的欧洲,能以这种辩证的态度对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既防止了理性主义狭隘的理智的偏颇,又避免了浪漫主义个体激情的放纵,奠定了一种新的人格教养的基础,从而把人文精神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级。
三、现代“方法论”释义学的创建者
整个西方释义学(Hermeneutik),从古至今,大致说来,经历了三大阶级:一是古代的“局部”解释学;二是现代“方法论”释义学;三是当代“本体论”释义学。我们认为,无论后人如何评价释义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转变的意义,施莱尔马赫创立的普遍“方法论”的释义学都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
这种创造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在“认识论”上追随康德的结果,并达到了他那时代的最高水平。康德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在提出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之前,首先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我们知识客观性的普遍条件;而被狄尔泰称为“释义学的康德”的施莱尔马赫,则是通过追问有效解释的普遍可能的条件,而实现了普遍方法论释义学的独创。
普遍方法论释义学的现代意义,在于施莱尔马赫以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认识论为榜样,把认识的对象扩展到人类精神文化上来,并相应于科学方法论,制定出人文学的系统的普遍方法论。在他那里,作为理解对象的文化产品一原文一就如同科学认识论中的“客体”,其意义既有独立于解释和理解的客观性,又假定了它们不随时间而变异的绝对性。这种意义,是由作者的书写所确定,存在于本文自身的语言结构之中,包括语言的公共意义和作者意欲表达的心理意义和象征意义两种,他们都独立于读者的理解而存在。他所阐发的“语法的解释”、“心理的解释”(包括“技术的解释”)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方法论,都是为了达到对原文的客观理解,把握原文的客观含义。他的语法解释,第一次把“语言问题”引入哲学,并最早作出了对20世纪影响深远的“语言”和“话语”的区别;他的心理解释,第一次把心理学引入释义学,竭力创造性地重建原文作者当初的思想创造过程;这些都促使他就把研究的重心转到对理解过程本身(而不是被理解的单个的特殊文本)的分析,探索客观理解形式的条件、过程及其可能性的限度。因此,他的释义学一方面具有了现代认识论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现代认识论的范围,为后人开辟独立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后世神学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于1799年5月出版的《论宗教》和1800年元旦出版的《独白》,堪称新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第一道曙光,照亮了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发展的道路。以后的1805年,施莱尔马赫又出版了《庆祝圣诞节谈话》,1810年撰写了《导论——简论神学的研究》,1821/22年出版了《基督教信仰——按照新教教会的原则相关的描述》。这些著作的出版和他那富于感染力和凝聚力的神学讲道,都使得他在这个革命与复辟、启蒙与浪漫、科学与宗教相互激荡的时代,重新把新教神学,确立为人们的内在信仰;把遭受湮灭威胁的宗教,重新置入无比丰富的现代理智生活的核心之中。因此,无论他在神学界的朋友、还是神学界的敌手,都不得不承认,施莱尔马赫是他那时代最有创造性、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大师。施莱尔马赫对19世纪神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对德国浪漫派宗教转向的影响上。德国浪漫派对世俗社会和世俗生活一直感到一种强烈的压抑,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追求的“理性化”也深表失望。总之,他们在现代文化面前,感到的只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恐惧和失去真正生命之内在诗意的苦痛。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生活,在外受制于对物质的盲目追求;在内,精神被束缚在理性的清规戒律之中,自由和无限,仍然只是梦中的理想。他们渴慕无限,追求自然,向往诗意和灵性的生活,但哪里有“无限”,哪里有充满诗意和灵性的“兰花”呢?在浪漫派渴求无限的征途中,一开始,他们找到的并不是“宗教”,而是艺术、审美和诗。只有在施莱尔马赫加盟浪漫派之后,并在他的内在意识论和直觉体验验论的宗教中,浪漫派才看到了通往无限的惊喜,以及宗教意识与审美、艺术、诗性思维的内在关联。
诺瓦利斯在阅读了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后不久,就写出了《基督性与欧洲》,内心的宗教之火一下就被点燃了。
谢林虽然在其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找到了哲学与诗的结合点和通往无限的道路,然而,宗教还是在他的视野之外。但在他于1802/03年讲授《艺术哲学》时,就把他原来作为“理性”解释的“绝对”(Absolute),直接等同于上帝和神性了。认为“一切艺术源自绝对”,就是说“一切艺术的直接原因是神”(die unmittelbareUrsache aller Kunse ist cott)(注:《谢林全集》,第五卷,德文版,第386页。)在1804年,他就以其《哲学与宗教》一书,同他刚刚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一刀两断,向宗教神学转变,以至他的后大半生都是陷在宗教神学之中。
弗.施莱格尔虽然起初对施莱尔马赫缺乏历史感的宗教观不太满意,但他的宗教意识的确被施莱尔马赫这位真诚的朋友强烈的唤醒了。其后半生,也是主要沉浸于哲学与神学的著述之中,并经历了从新教的重要代表和领袖到改宗天主教的重大转变。在他的《论新教的性格》一书中,人们完全看到施莱尔马赫宗教哲学的印痕:“只有那种同时赋予一切以灵魂、在其中天下众生未经约定便成一体的、称为他们纽带的东西,才是新教的本质。这就是宗教改革家们所借之以宣讲其主张的自由,就是独立思考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信仰的勇气;就是抛弃那即使最坚实、刚刚还为他们自己所神圣地珍惜的谬误组成的桎梏时的果敢。”(注:思斯特.贝勒:《弗.施莱格尔》,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第7—8页。)
可以说,浪漫派成员无不受到了施莱尔马赫宗教思想的影响。正如俄图·布劳恩所说:施莱尔马赫“新思想的影响面起初并不宽,但深深地植根于同志们的精神之中:施莱格尔的、诺瓦利斯的、谢林和卡洛五林娜的,大家都因他的思想而同宗教有了联系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受到了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注:Otto Braun:《施莱尔马赫的生平和著作》,载《施莱尔马赫选集》,卷一,LIX—LX。)。
其次,施莱尔马赫对19世纪宗教神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他那自由而宽容的宗教信仰方式,在大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而影响到神学思想的发展。在神学思想上,他很早就成了任何一种僵化体系的最尖锐的反对者,而不论这种体系是正统路德派的,还是自由改革派的;也不论这种体系是福音派的,还是理性派的。在神学实践中,施莱尔马赫是19世纪民众宗教的发起人。这种民众宗教,实质上就是以自己内心真实存在的“心灵的宗教”自愿组成的民间的自由宗教,它的最大敌人是国家教会。施莱尔马赫坚决拒绝国家教会,反对政府对主教发号施令。他的改革目标是使世俗的民众教徒自愿地组织起来,教区应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来管理,独立于国家。他的晚年一直在同复辟派的、正统派的、黑格尔派的、甚至国本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以使教会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国家。他甚至完全不顾自己的名利得失,违背国王的意志,激烈批评国王自上而下的礼拜仪式改革,反对国王自己弄出来的礼拜规则。这一切,不仅显示出施莱尔马赫是一位献身于自由的人性和基督教与上帝紧密联系的现代典范神学家,而且“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之先驱”,“他的宗教观为自由主义神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自由神学之父里奇耳(Albrecht Ritschl,1822—1889)所继承”。(注: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再次,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哲学开创了宗教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清除了现代文化所强加于宗教的种种偏见和误解,廓清了宗教与形而上学、知识论、道德学、神话学、甚至审美的区别,使宗教自在的本性在描述性的语言中显现出来。这种宗教现象学方法的影响,超出了19世纪,启发了20世纪宗教现象学的兴起。“在众多的追随者中间,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73)被公认为施莱尔马赫观点在当代最有影响的传承者。”(注:张志刚《理性的仿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五、对后世哲学与美学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不仅仅是作为神学家,对其身后的宗教哲学与神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举世公认的重要哲学家和美学家,对其身后的哲学与美学的深远影响,也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
在19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中,受施莱尔马赫影响最大的,是威廉狄尔泰。他作为施莱尔马赫的传记作者,对他的哲学思想相当熟悉并十分感兴趣。面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种挑战,狄尔泰受施莱尔马赫把科学分成物理学和伦学理思想的影响,极力强调“精神科学”(Geoisteswis-senschaft,相当于施氏的“伦理学”,指的是“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并且,狄尔泰还在施莱尔马赫释义学的影响下,把释义学的“理解”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他赞同施氏的看法,把人类文化的世界,看作是自由的、创造的世界,对宇宙的直观和感受,即起源于人类的意识和心灵。这同物理的世界是绝对对立的。但狄尔泰不同于施莱尔马赫,仅重视文化精神世界的民族差异性,他更把这个世界看作是历史的世界。狄尔泰赞同施氏释义学的客观主义方法论,并尤其重视运用施氏心理学的“体验”方法,进入原文作者的精神世界。不同的是,施氏始终重视重建原作者表达于文本中的客观含义,而狄氏重建的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精神”。狄尔泰还把施氏的“体验”概念,广泛运用于美学之中,创立了“体验美学”。总之,没有施莱尔马赫,就没有狄尔泰;而没有狄尔泰,就没有人文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独立性。
施莱尔马赫释义学的客观主义方法论在现代的传承者,主要有意大利的著名哲学家贝蒂(E.Betti)和美国文论家黑施(E.D.Hirsch)。贝蒂在释义学上的两个关键问题上,完全采取了施莱尔马赫同样的做法,这就是,第一,仔细研究解释过程的细节,弄清理解的条件、过程和可能的限度;第二,提出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来确保解释的客观性。不同的是,他为了确保解释不带主观性,连在施氏和狄氏那里都很重视的心理方法,他都要剔除干净。
黑施在其代表作《解释的有效性》的“前言”中,就公开声明,他的思想受到了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注:E Hirsch:《解释的有效性》,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6。)他像施氏一样,认为释义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保卫作者”,准确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含义,避免误解。通过黑施对伽达默尔的批判,施莱尔马赫的释义学思想,不仅在当代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且更广泛地在文艺理论界传播。
在当代哲学中,德国哲学泰斗伽达默尔虽然是施莱尔马赫释义学的激烈批判者,但由于他对施氏在释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所以,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也是通过他的批判和肯定而得以在哲学、史学、语言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等文化领域中广泛传播,作为人们思想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参与当代的学术对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施莱尔马赫仍是一位“活着的现代人”,在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标签:理性主义论文; 主体性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康德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认识论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