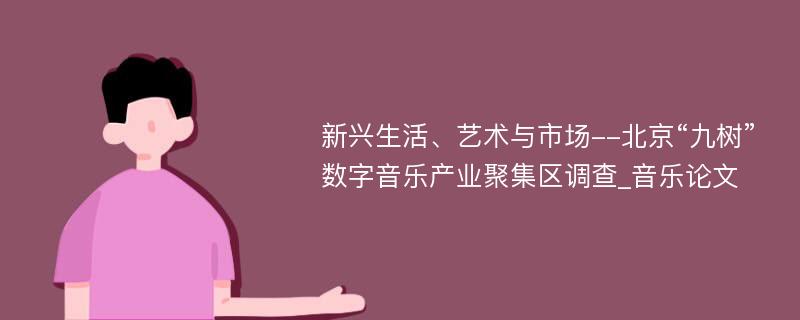
浮现中的生活、艺术与市场——北京“九棵树”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调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棵树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数字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最初获得的信息很简单:北京通州九棵树这个区域聚居着3000音乐人,有500个音乐工作室、50余个录音棚。但这里已经是对全国数字音乐产品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和吸引力的产业集聚区。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调研,并试着进行初步的经济学分析。
这里有两个市场:音乐表演市场和原创数字音乐作品制作市场。两个市场相互连接,形成环环相扣的市场链。北音的存在对这个群落的发展起着引领的作用。“原创数字音乐作品制作”是一个较为含混的说法,指通俗音乐作品原创,同时是数字技术编码的介入。在这一点上它和电影有点儿像,而且它本身就是在为影视作品提供音乐及音响服务的,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行业中,“编曲”是核心环节。
一、浮现着的生活
通州九棵树有一座民办的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在当地被简称为“北音”),办学已有10年左右的历史。据说每年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约有40%继续从事音乐专业工作,其中多数人选择在九棵树聚居(租房或购房)。这些20多岁年轻人的音乐人生就从这里起步。每年毕业1000人,那么10年间就会在这个区域留下约3000位音乐人。我们上面那个数字背后的推算公式可能就这么简单。
年轻的音乐人们是自我就业,属于“北漂”一类。很多音乐人一开始也不是全职作音乐,还要兼作别样(例如开黑车、开饭馆或者卖保险);也有很多人都是“入行不入业”,即从事音乐创作和制作、音乐产品开发但不是经营一个企业(不进行工商注册);还有一些合伙人只是像朋友那样共同创业。在“创业”期间,家庭(父辈)的经济支持也许是不可缺少的。所幸这些音乐人的家庭条件通常还可以,所以最终支持子女从事这种风险比较高的职业(“波西米亚”)。要搞音乐,毕竟在这里抱团打拼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一般说他们的住房状况、生活状况或叫进入社会的“初始状态”也许会比海淀唐家岭的“蚁族”要好许多。
最普通的音乐人只是一些歌手或乐手。他们会在市内一些宾馆、酒吧、各类娱乐场所进行非正式的音乐表演,如在宾馆大堂弹奏钢琴,或在后海的音乐咖啡馆里为客人助兴演唱。据说一场演出大约是1小时(计时单位),有300-500元的收入(根据演出效果、上座率确定,也会涉及技巧、风格、个性等)。他们每周可能有3个晚上去“上班”,有时一个晚上会有一两次“转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歌手或乐手的组合可能是商家建议的,而他们自己形成组合也是可能的。一位做了录音棚的音乐人的妻子是著名女生三重唱组合“黑鸭子”的歌手之一。如果工作合同比较饱满,那么一周下来,他们在通州租房的月租金就到手了,后几周的收入就是更可自由支配的收益了,既可用于生活成本开支,也可作为再生产的投入(如乐器、设备甚至录音棚建设的投入)。要感谢通州的房价,感谢大量小产权房对通州房价的拉低作用,还有通州与北京市中心的交通便利。而且这些在表演时不乏疯狂的音乐人回到家里并不扰民,多数十分沉静甚至内向。于是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背着乐器的年轻人在九棵树地区行走。
与瞄准西洋音乐教育的中央音乐学院及瞄准中国传统音乐提高的中国音乐学院不同,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寻求差异化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定位是通俗音乐及数字音乐制作。学院里使用电脑软件进行音乐处理合成是一门基本课程。所以如果一个歌手或乐手除了乐器还有一台可以编辑音乐作品的电脑,那么现在这些毕业生的居所就可以被称为音乐工作室。而如果除了电脑还有更多的录音设备和一小间专门的录音室,可以因此接受委托制作一些大众音乐产品并逐步获得声誉,那么这里就可以被称为录音棚。当然,即便这些录音棚就蛰伏在居民区里,音乐人的理想是让家与工作室分开。工作室或录音棚就像是“单位”。小区的居民听不到喧闹,因为这些录音棚经过极为专业的隔音处理,外面的声音传不进去,里面的声音也毫不外泄。毕竟这是一件靠耳朵进行的工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音乐人那个重要的感官功能被充分调动(歌手们的耳朵都很好,能准确地分辨声音,然后唱出来、弹出来)。而使用软件、操作设备的技巧大多都是通过“百度”搜索得到训练。
歌手乐手的表演活动也需要有一些记录。也许他们在“谋职”时也需要经过“面试”,要提供“简历”。所以许多歌手乐手会对自己的表演进行有伴奏的、较正式的录音,制作成一个光碟。而如果录制不是自己动手作的,那么别人的录音棚就有了“生意”。更何况,还会有很多具有出版发行权的唱片公司会找上门来委托他们制作一些音乐产品。据说当前音乐录制的价格在走低,从以前万元录制一首压到了每首只有五六千元。另外每年有上万部电视剧被创作完成,尽管不是所有的电视剧最后都在电视台播映过,但其音乐制作是不可缺少的。据说一部20-30集构成的电视剧在音乐制作上要花费10万元。这里有一些主题歌,有几段主题音乐及不同情境下的变奏。大约需要有总长一个小时的音乐素材在剪辑中使用。而一个录音棚大约要花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这样的活儿能接上几单,一年的收入就有点儿可观了。当然这里有设备的成本,也需要支付请乐手歌手乐队来录音的费用。而通常情况下,每月能有5-6个小活儿,工作也就够紧张了。这样我们大致可以想象这个市场的规模和音乐人们的收入水平。音乐人们觉得周围他们的同行很多,需要的人手打个电话就“招之即来”,不必约到几天之后,因此干起活儿来很方便。我们向一些音乐人询问当地有3000音乐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他们感到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从进入通州的八里桥过来一直到城区东南部张家湾一带,说有1万音乐人集聚他们也愿相信。据说这两年过来的人很多,有从市里(将录音棚)迁过来的;也有从南方比如广州过来的;还有台湾来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九棵树地区是最大的数字音乐制作基地。
二、浮现着的艺术
通俗音乐当然是大众文化的范畴。但它们是当代活着的艺术,是当代人生活最直接也最新鲜的表达与流露。2013年初,大雾笼罩北京,当晚就有一首旧歌被翻唱,表达人们生活在雾霾中的感受。我觉得这首歌很可能就是在九棵树制作完成。当代的艺术和古代的艺术不同,无论和传统的民间音乐比还是和西方19世纪的古典音乐比。这种不同有三个方面。一是在通俗音乐中,生活和艺术分离得不是很开,因此不成熟成了它们的特征。二是在网络时代,新的、以互动游戏为范型的、即时创作的艺术种类正在草创和形成当中。三是技术、机械(器材、设备)对创作过程的参与很彻底,没有这些物的因素,作曲家几乎没法展开想象。但是它们仍是原创的艺术,仍然追求着完美和希望。
每个稍具影响的录音棚里都会在显著位置陈列他们的作品(哪怕他们只是在这个作品生产的某些环节参与过),例如有20张左右的光盘连同它们的封面被展示着。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广告!重要的是你是否知道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包括它们的演唱者是谁,出品人是谁,曾在哪些电视台播出,等等!我们看着那些作品的封套,就会识别出熟悉的电视剧或流行歌曲,脑海里就有了旋律(比如“老鼠爱大米”)。
每位棚主也会很自豪地对你介绍自己的设备。有些是从西方国家买的二手货,经港台等地转口进来,这样关税会低一些。但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音响器材质量相当好,光凭分量就可以知道,为此他们愿意投两倍以上于今天新产品的价格。这样的设备如果再被设置在一个做过悬浮处理的工作间里,那感觉可就好极了。这就意味着作品的品质是上乘的。平时人们只知道在家里听音乐的发烧友会炫耀设备,原来制作音乐的设备更是可以“发烧”的。一位棚主告诉我们,为了录制吉他曲,他所使用的麦克风及从录音室到制作间的传输线都是专用的。另一位棚主身兼多种职业,除了制作音乐也参与演出,甚至还开着一家餐厅。他说:“生活不太如意的时候也会悲观、灰心”,但一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拨弄着那些可以推上推下的机键,心情就会好起来:“我毕竟已经置办了这么好的一套设备啊!”谁能说这样的事业心及感受与学院派的音乐家有本质上的区别呢?!这是很多年轻音乐人多年的梦想,只是并非所有的音乐人都能梦想成真。
曾有棚主略带悲哀地说:“人们知道一首歌的词作者是谁,曲作者是谁,歌手是谁,乐队是谁,但有谁知道作品的编曲是谁呢?!”编曲,这个称呼在数字音乐制作行当中意味着太多太多。一首歌如果没有经过编曲,那么它就可能什么也不是。传统的民歌是在长期的传唱中慢慢成熟起来的。即使没有伴奏,仍然可以唱得非常感人。古典音乐作品在作曲家手里不仅有了旋律、乐章、和声、配器……而且已经有了全部演出总谱。这里没有什么工作要留给编曲去做。但通俗音乐很不同。很可能会有一个歌手走进门来,说“我要录几首歌”。于是他就百无禁忌地唱起来。但这可能与一张专辑相隔十万八千里。这时编曲要对他的歌唱做全部音乐分析、改编和配器,然后给他做伴奏,完成整个音乐形象的织体,再分别录制各个乐器的不同音部,最后“缩混”合成。最终,丑小鸭出落成白天鹅。据说甚至有一个歌手走进门来说“我有一个动机”。连旋律都没有,仅仅是一个动机,这样的“作品”也能生成吗?!这取决于编曲!事实上,数字音乐制作之所以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产业原因也在这里。从歌手的表演冲动到一个曲子的流行,这属于编曲的工作空间就是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一般说,棚主首先是一个作曲家,而他通常也会雇用一位优秀的录音师。
三、浮现着的市场
我们开始时说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市场链,这话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因为这个市场还基本处于半地下状态。这里所有上述音乐委托创作、编曲、录制活动都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而只是自然人之间偶然的交易,哪怕它要经过好几个交易环节(公司或剧组委托创作或制作一个产品要把钱付给录音棚;录音棚又找到恰当的乐人或歌手来录制,还可能要向其他工作室或机构租用设备,这些环节都需要从前一款项中向后者支付报酬)。就像我们到乡间的小餐馆吃饭,然后向饭店索要发票,那会是很可笑的事。混迹于居民区或农民房里的工作室或者录音棚都不挂招牌,也根本没有经过工商注册。圈内的人口耳相传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合作者;朋友们也可能通过电话联络。相信这些个人间的交易也大致会有信用的存在,因为没听说有太多的官司。当然这里也不会有税收的事情发生。国家只注意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对于这些自然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大就是不在乎这些!
但今天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世界各地兴起。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群,一般说它包括两类规模不等的公司。文化产业是广义的媒体,通常它是依靠强势复制技术和巨大商业网络,通过知识产权交易购买作品或内容,然后开发成廉价的复制性产品展开营销。但这个产业的竞争使文化企业也希望尽可能控制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文化原创资源,尽可能早地将原创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商业组织。但原创作品的市场化前景是有风险的,只有更加内行的商家敢于做最初的商业投资,而普通的商家只希望拿到市场前景比较明朗的产品薄利多销。于是文化企业分成了两类,并构成进一步的上下游关系。处于上游的往往是一些小微企业,它们尽可能靠前地接触原创,然后取得开发授权。然后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下游大规模的复制企业、有品牌的大公司,让它们去经营和开拓市场。两类商业组织中小企业的数量非常多,而大企业的数量比较少。通州九棵树地区这些工作室或录音棚就具有与原创环节最接近的小公司、小企业的特征。它们的位置甚至介乎于影视产品制作、音像制品出版机构和纯粹的艺术家之间;而它们的下家还要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播出或发行机构。在通州,这些小机构通常只有1-3人。
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纵向非一体化”。大的文化传媒期望作全媒体经营,这叫“横向一体化”。一个传媒集团,既经营广播电视,也发行报刊书籍。但原创产品的高风险要靠许许多多的小公司靠专业知识去规避,去分担。而数码技术的应用是这种分散化经营得以实现的条件。当然还有“纵向一体化”。所谓“纵向一体化”指的是一个产品的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一个商业组织内部完成。但我们会在每部电影结尾的字幕上看到一大串机构的名称。原来今天一个作品的原创很少再是由一个单独的创作主体从头到尾完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一个独立的、专业的商业公司完成的。这就是所谓“纵向非一体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由少数大的传媒公司和大批小的原创公司匹配而成的产业结构格局必然形成;而且人们还经常会感受到“媒体过剩、内容稀缺”的窘迫。
因此在发达国家,要发展创意产业就要支持原创,要关注、支持、发展这类小微企业。正所谓源远才会流长。政府的许多优惠政策都是针对艺术家和这些小企业的。但是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文化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放,还没有出台这类优惠政策的紧迫感。反之它更愿意给那些靠行政垄断地位已经获利甚丰的大型播出或出版机构以更大的资助。这样的文化产业政策是灾难性的。为了不被世界更远地抛在后面,这样的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那么为什么不愿意让这些小的艺术生产机构、小的商业组织浮出水面进行工商登记,让数字音乐制作的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从而尽快做大做强呢?有人以为是这些艺术家很难管理,说他们本能地倾向避税。而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他们并不太计较纳税,并且他们知道在发达国家税收优惠通常是针对小型原创企业的;同时他们还知道自己如果进行工商登记成为企业,就应该拥有独立的出版发行权。这样做更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和我们从一些管理部门听到的说法有出入。我们还听到,棚主们多对前不久通过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的法律表示难以理解,认为这是对原作者创作的不尊重,认为这会伤害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这一点也令我们有几分惊讶。我们听到较多的是国外的企业对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满,对于这些甚至还没有进入市场的音乐人的不满我们估计不足。看来,不愿意市场化的不是艺术家、音乐人或编曲们。当然,目前这种半地下状态的活动并没有被严厉禁止,因此生活和创作可以继续,只是说起来不太有尊严,从事文化创作的音乐人如同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
发展、培育并有效管理艺术品市场是国家的责任,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项工作变得更加迫切。文化市场开放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届时政府还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这个市场的规模迅速变大,管理迅速变得有效。或许对于这些小型文化企业的成长来说,集聚区的搭建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们应该使音乐人们在九棵树周边地区的集聚现象变成九棵树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集聚区不仅是一个街区的建设,后续工作也不仅是物业管理。重要的是这里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它表明政府在以具体的措施支持这些产业。如果草根性的音乐工作室或者隐藏在居民区中的棚主身份很难辨识,因此政策的受惠人(beneficiary)无法确定,那么进入集聚区像是一种资格认定。行业行政管理者可以知道这些业主在干什么。集聚区通常也是创意产品的孵化器。一些年轻的音乐人头脑里产生了旋律或者动机(motif),但他暂时没有设备实现它,于是他们可以向集聚区有关机构申请使用这里的设备。同时可能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资金,那么集聚区可以经过对他们最初创意的审查,帮他们垫付资金。甚至有些创作最后失败了,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集聚区先将其成本负担起来。这些政策性经济扶植是政府的举措,看上去政府可能有损失,但同时政府也可以因此拥有未来一定份额的知识产权。一个有政府机构参与的版权结构,或许在需要维权时使事情变得简单。当然政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投入或者资助,集聚区里可以有金融机构开展贷款服务;也可以引入一些创投机构、一些唱片公司在此寻找机会。这时集聚区对当事人的资格认定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担保作用。政策、金融、设备与技术的支持,这些才是集聚区真正的功能。
音乐人在集聚区的集聚更有利于他们之间开展的合作,他们休息时的小聚也许就会碰创出新的音乐火花。尤其重要的是,当代音乐的创作的确由于音响及数字制作技术的发展变成“集体进行的”。这里强调的是更加细腻的专业分工,而且是在明晰的知识产权框架下进行的分工。对此法兰克福思想家是有忧虑的,但从影视这种艺术门类产生之日起,以前潜伏在交响乐作品创作中的原作—解释、创作—再创作不断循环的构造被在市场条件下发展起来。推敲起来,早期的神话或史诗都是特定文明共同体的“集体”创作,只是我们难以辨明其作者,更没有什么知识产权含义。似乎是这样:没有知识产权制度,艺术的创作最终变成了个人行为;有了知识产权制度,创作重新成为集体行动。
这时,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作用也再次显现。北音是这里许多音乐人的母校。这里有他们许多的老师、同学或校友。由于共同的音乐人生涯和在九棵树集聚的便利,他们会频繁地再聚首。毕业生离开了学校,但学校对他们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学校就是潮流。在不断增加的交往当中,音乐及其风格的传承才表现出来。难能可贵的是,北音的教育管理者们对当代音乐产业的发展趋势有敏锐的认识,他们的办学理念就是要精确瞄准两个市场:通俗音乐表演市场和数字音乐制作市场。通俗音乐的流行表现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旺盛文化需求;而数字音乐制作技术同时可以应用于古典音乐与传统的民间音乐。北音现有包括流行演唱、爵士乐、音乐传媒、音乐教育、新媒体艺术设计等在内的8个二级学院及流行音乐、电子音乐、影视传媒、音乐录制4个研究所,20个专业学科、45个培养方向,1000余名教职工,9000名在校生(含蓟县分校)。同时它不仅有4000平方米的演播大厅、350间标准琴房,还有8个音频工作站、6个视频工作站、16个MIDI工作室及双排键工作室;拥有独立、完善的影视节目制作中心、动画制作中心和网络管理中心。学校注重与当地社会发展的互动,自2010年起开始举办“北京·九棵树数字音乐节”。它的社会影响力正逐步显示出来。
音乐节不仅是表演和创作的展示。利用学院西校区建成的数字音乐及多媒体设备、产品交易大厅,音乐节包含了乐器及音响设备展销;接续通俗音乐作品大赛,学院开展原创作品知识产权拍卖。学校还正在筹办中国现代音乐博物馆,打造北京数字音乐在线交互网络平台等。学校既希望做长产业链,也希望做全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络。学校计划建设音乐厅与音乐剧剧场,希望将位于市内的音乐消费市场引向通州,引向九棵树。因此,北音也给正在打造国际新城和创意通州的当地政府一个机遇:九棵树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可以依托北音加以实现。这样通州的本地音乐艺术市场可以就地浮现出来。
应该说,创意城市的理念比一般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的概念更胜一筹。它不仅彰显了文化经济化的产业前景,而且烘托出整个社会创造力的激发,文化、教育、市场、公共部门及社会第三社会部门共同参与,营造出极易点燃创意的城市氛围,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这里创业的美好前景。九棵树音乐人的集聚对于通州来说已经是第二例,它北部的宋庄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家集聚的重镇。未来的创意通州将如同礼花绽放,而现在积极打造九棵树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只是它又一个“引爆”装置。
标签:音乐论文; 录音棚论文; 艺术论文; 数字音乐论文; 九棵树论文; 音乐人论文; 歌手论文; 剧情片论文; 日本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