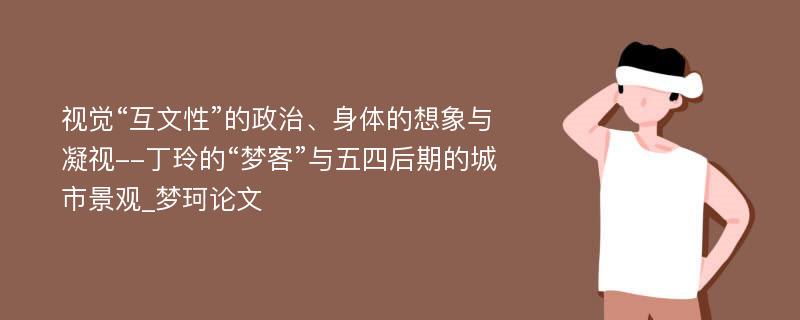
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视觉论文,身体论文,政治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视觉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将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事物予以“视觉化”(visualizing)。(注:参见Nicholas Mirzoeff: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一书绪论部分“何谓视觉文化”的论述,特别是第一部分“视觉化”,London, Routledge, 1999。)而“技术化观视”(the technologiced visuality)则成为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相对于“肉眼观视”而言,所谓“技术化观视”指的是通过现代媒体如摄影、幻灯、电影等科技和机械运作而产生的视觉影像,有别于平日单靠肉眼所看到的景象。现代媒体能将细微的事物放大好几十倍,眩目而怪异。这种革命性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过去肉眼前所未见的视像,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带给人们一种巨大的震撼性视觉体验。由新的视觉技术——摄影术以及衍生出来的电影技术——带来的“震惊”效果,成为了本雅明讨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核心”概念:传统绘画允许你从容思考,电影却不断修正你的知觉,由此造成的“震惊”体验使得观看对象失去了经典的“灵光”,却发挥出“蒙太奇”的效果,它把各不相同的事物重新联系与组合起来,重建了观众与置身其中的世界之间新的“想象”关系和“批判”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指出:“艺术作品可借机械复制:这项事实改变了大众对于艺术的看法。一般大众看毕加索的绘画,会有很保守落伍的反应,可是看卓别林的电影又变得十分激进。这种先进态度的特点是:欣赏演出的愉悦感与相对应的生活经验以直接而亲密的方式和行家的态度建立了关联。这种关联具有社会性的重要意义。”(注: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载《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似乎并没有和电影及摄影有所牵连,他们仍是被卷入了“技术化观视”的“认识论问题”中:“在二十世纪,正是摄像和电影这样的新媒体所带来的视觉性力量,才改变了作家们对文学本身的思考。无论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这种新的文学模式是无可争议地被彻底媒介化了,在其中也包含着对技术化视觉的反应。就像其他论述的传统模式,当然也包括像绘画和雕塑这类的视觉艺术,文学必须进行自我设计,以应对作为普遍交流技术的视觉所显现的优越性。”(注:参见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张艳虹译,载《视觉文化读本》第258—278页,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那么,当“新的文学模式是无可争议地被彻底媒介化了”时,中国现代文学在面临“技术化观视”挑战时究竟做出了怎样具体的回应?现代作家是如何积极介入到电影、摄影和画报等新兴的图像传媒领域?又是如何用文学创作来化解、容纳和提升来自图像领域的刺激和震惊,从而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激发出文字前所未有的视觉潜能?本文不可能全面讨论这个问题,但希望借助于对丁玲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处女作《梦珂》的解读,在一种文字与视觉更为复杂的关系中,深化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写作“视觉化”倾向的理解。
二
选择丁玲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由于她在成为作家之前与电影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这在20年代的新文学作家中是比较少见的。1926年,著名戏剧家洪深受明星公司张石川委托,去北京参加影片《空谷兰》的献映仪式,并应邀到北京艺专演讲,此间结识了丁玲。聆听洪深充溢激情的演讲,增强了丁玲从影的信念。于是,她给洪深写了封信,倾吐自己的心愿。洪深回信中给予她热情的鼓励,而且两人在北海公园会晤,作进一步交谈。洪深回上海之后,丁玲与胡也频筹资造访上海。经洪深推荐,丁玲去明星公司报到。但是纯真、充满幻想的她,刚涉足影坛,便觉察这一领域与自己的想象反差太大,只好满怀歉意告别了对她寄予厚望的洪深,没有签约就离开片场。此后南国电影剧社的田汉,又邀她去舞台演出,因不擅于演剧生涯的浪漫,丁玲的明星之梦终于幻为泡影。(注:参见张伟:《洪深和丁玲早年的一段交往》,载《沪渎旧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直到晚年,丁玲仍对这段从影的经历耿耿于怀,据她的秘书王增如回忆,丁玲读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因其中描绘了她当年的“明星梦”,丁玲特别写了一段这样的评语:“我去演电影不是为了生活,是为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参见王增如:《丁玲的一次特殊“表演”》,载《世纪》2005年1期。)这段并不愉快的经历在《梦珂》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所饱领的,便是男女演员或导演间的粗鄙的俏皮话,或是当那大腿上被扭后发出的细小的叫声,以及种种互相传递的眼光。谁也都是那样自如地嬉笑,快乐地谈着、玩着,只有她惊诧、怀疑,像自己也变成妓女似地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自己的眼光去观览。”(注:丁玲:《梦珂》,载《小说月报》第18卷12号(1927年12月),丁玲的这篇小说在以后收入不同版本的小说集和选集中有程度不一的修改和删节,本文根据的是《小说月报》的初版本,以下引用该文不再注明。)
另一方面,丁玲的从影经验不仅使她在小说中直接描写了当时上海电影界的情形(既描述了电影公司招募演员,拍摄电影的场景,也渲染了作为普通观众在卡尔登看电影时体验的心理),而且也使得《梦珂》中留下了电影技法影响的痕迹,小说中有多处带有“特写”画面性质的描写,特别小说的开头几个场面的组接,具有强烈的镜头感,甚至可以当作分镜头剧本来读: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镜头一)
“看,鼻子!”其中一个这样急促地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镜头二)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左腿直哼的样儿发笑。(镜头三)
“笑什么,看呀,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镜头四)
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这时他从第八教室出来,满脸绯红,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皮靴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叹息:“咳,慢点呀!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气冲冲的,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镜头五)
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打网球的几个人也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镜头六)
“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大家一哄的挤了进去。(镜头七)
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地咭咕着,抱怨着,咒骂着……(镜头八)
靠帐幔边,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有一个还没穿外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实的眼光,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镜头九)
“喂,什么事?”扭开门的女生问,但谁也没回答,都像被什么骇得噤住了的一样,只无声地做出那苦闷的表情。(镜头十)
挨墙的第二个画架边,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等到当当地慢慢地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就开始移动她那直产得像雕像的身躯,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紧紧的瞅着,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镜头十一)
“喂,谁呀?”
“三级的,梦珂。”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镜头十二)
女主人公梦珂就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读者的视野中。小说娴熟地运用电影技法,可以证明丁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无可争议地被彻底媒介化了”。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一名想做电影明星的女性,丁玲和男性作家“触电”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男性作家一般以编剧、导演和评论家的身份介入到电影之中——这种经验极其强烈地放大了女性身体被观看的感受。对于一位后五四的时代女性来说,这是一种“震惊”体验:如果五四之后,新女性获得了以“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名义来展示自己身体的权利,但在商业化的环境中,这种对身体的展示恰恰迎合了男性的欲望,沦为“消费”的对象,那么女性争取“身体”自主权的合法性又从哪里来?有趣的是丁玲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是把这种震惊体验转化为一种与“视觉”密切相关的叙述形式:在被观看的“女体”上铭刻着男/女,公/私,城/乡,阶级/性别……诸多紧张的历史关系。
三
小说的主人公梦珂以美术学校的学生的身份登场,显然出自作者的有意安排。因为丁玲在《梦珂》中将两种视觉形式——“绘画”与“电影”——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回旋曲的叙述结构,不断形成主题(即“被观看的‘女体’”)的回响和变奏。这种“视觉形式”(绘画)与“视觉形式”(电影),“视觉形式”(绘画和电影)与“文字形式”(小说)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就是我所要特别强调的丁玲小说中的“视觉互文”结构。
这种“视觉互文”相当充分地显示出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巨大视觉潜力。需要说明的是,“绘画”(特指“西洋现代绘画”)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技术化观视”的方式。因为“西洋现代绘画”最根本的特征是由“现代透视法”决定的,而“透视法”正如柄谷行人指出的,植根于所谓“风景之发现”:“即使在西欧,现代透视法确立之前,其绘画中也是没有‘纵深度’的。这个纵深度乃是经过数世纪的努力过程,与其说是通过消失点作图法之艺术上的努力,不如说是数学上的努力,才得以确立起来的。实际上,纵深度不是存在于知觉上的,而主要是存在于‘作图上’的。……习惯了这种透视法的空间,我们便会忘记这是‘作图上’的存在,而倾向于认为此前的绘画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客观的’现实似的”。(注: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风景之发现”和“关于结构力”两部分中对“现代透视法”的论述,引文见第135页,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也就是说,“透视法”好像出于“肉眼”的观看,却并非出自“自然”,而是现代性认识装置构造的产物,它与电影、摄影一样重新塑造了人们感知和观看世界的方式。
具体地看,以“身体想象”为主题的“视觉互文”结构在《梦珂》中大体可以区分了两个层面:
第一,从“女模特”受“男教师”的侮辱开始,小说首先让人们看到的是展露的女性身体受到男性的侵害,奠定了整部作品以“被观看的女体”为焦点的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女模特”的出现是现代艺术教育制度的产物,而在中国,围绕着“女模特”发生了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剧烈冲突,熟悉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人,一定记得1917年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引发了美术史上著名的“模特儿”风波。“女模特”最终获得社会和政府的许可与认同,标志着现代视觉体制在中国的进一步确立。(注:1914年,刘海粟开始在教学中使用模特,初为男人体。1917年上海美专因展出人体习作,引一场“模特儿”风波。教学中使用女人体比较晚,据刘海粟回忆,上海美专于1920年雇用白俄女子为人体模特。参见刘海粟:《漫话人体艺术》,载《中国现代画报》1985年3、4期。而李超在《上海油画史》中则更具体地描绘这场“模特儿”风波:“暑期(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院选出学生习作五十件,于静安寺张园安垲弟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会上其中展出人体素描习作。翌日《时报》发表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的文章,题为《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引起社会舆论。由此酿成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轰动一时的‘模特儿事件’。该事件前后斗争持续进行达十年之久。”李超:《上海油画史》第277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但侮辱女模特事件正是发生在这个体制中,最后的结果是模特儿被撤换,打抱不平的梦珂退学,男教师照样教书,学校“直过了两个月,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一个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
小说这一序幕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丁玲不是在“现代”与“传统”观念冲突的空间中展示“看”与“被看”的屈辱性关系,而是把“被观看的女体”遭受的屈辱放置在现代视觉体制的背景下,甚至直陈现代社会透过“艺术”、“娱乐”和“消费”等诸多体制,把“看”与“被看”的关系制度化和正当化了。
果然,在小说的主体部分,梦珂周围出现的男子都是“新青年”:表哥“从法国回来还不到半年,好久以前便常常在杂志看到他的名字,大半是翻译一点小说”;詹明“一个专门学校的图画教员”;张寿琛“留美戏剧专家,话剧和电影的导演”……这些男人在他们和梦珂之间复制了那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小说中充满了在男性欲望目光注视下的“女性身体”:眼睛、睫毛、耳垂、额头、手指、小腿:
又是在一个下棋的晚上。她是正坐在澹明的对面。晓淞是斜靠拢她的椅背边坐着……晓淞便又可以看到她那眼睫毛的一排阴影直拖到鼻梁上,于是也偏过脸去,想细看那灯影下的黑眼珠,并把椅子又移拢去。
梦珂却一心一意在盘算自己的棋,也没留心到对面还有一双眼睛在审视她纤长的手指,几个修得齐齐的透着嫩红的指甲衬在一双雪白的手上。皮肤也像是透明的一样,莹净的里面,隐隐分辨出许多一丝一丝的紫色脉纹,和细细的几缕青筋。
在这时,表哥无声的走上凉台。
“着凉!梦妹!”手是轻轻的附着她的臂膀。
看见了星光下的两颗亮晶晶的东西在那双自己所爱恋的黑眼睛里闪耀,忍不住便紧紧的握住那另外的两只手。
梦珂反更张大起一双大眼望着表哥笑了起来
表哥坐在一个矮凳上看梦珂穿衣。在短短的黑绸衬裙下露出一双圆圆的小腿,从薄丝袜里透出那细白的肉,眼光于是便深深的落在这腿上,好像还另外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描写常常以“特写”镜头的形式凸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带有挑衅性的笔调,它似乎暗示着丁玲对自己小说的读者身份有某种自觉。大多数读者自然是站在男性立场上,希望可以在小说中再次观赏“女体”,而丁玲在写作中不无夸张地把“女性身体”的细节突兀地展示出来,与其说是迎合读者,不如说是嘲讽和挑衅。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叙述视角在序幕和主体部分之间也有调整,在“女模特”事件中,处于“女模特”和“男教师”之间的梦珂相当清醒地意识到后者对前者的欲望和侮辱,所以她才会挺身而出。与此相关,小说的叙述视角基本上统一在梦珂的视角中;但是当“被观看的女体”变为梦珂以后,梦珂对男性欲望的眼光失去了敏感,她不能体会出“新青年”与“男教师”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叙述视角脱离了梦珂的视角,而以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来处理梦珂和她周围男性的关系,把天真的梦珂一时无法感受的男性欲望暴露出来。等到梦珂最终觉悟自己仍然处于“看”与“被看”的屈辱性关系中,小说的叙述视角又与梦珂的视角逐渐合一,她自觉地在导演和镜头面前展露身体,“……无声的举起一双手去勒上两鬓及额上的短发,显出那圆圆的额头并两个小小的玲珑的耳垂给人审视的时候,她伤心——不,完全是受逼迫得想哭一样”,在这一刻,梦珂清醒地意识到作为“被观看的女体”所承受的欲望和侮辱。于是,一个回旋曲的结构得以完成,“女模特”和“女明星”遥相呼应,只是“被观看的女体”未变,遭受屈辱的命运未变!
然而,丁玲没有简单地把梦珂塑造成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也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地展示一个新女性的“堕落”过程,她在“被观看的女体”上寄寓了更大的野心,这就涉及小说的第二个层面,也是一个相当容易忽视的层面。
如果我们承认小说开头的“模特儿事件”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与梦珂成为“女明星”的结尾遥相呼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绘画”和“电影”两种视觉形式也应该在小说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影作为一种与男性观看的欲望密切相关的视觉形式,已经广为人知。近年来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绘画”也隐含着男性的观点,这不单指诸如女性人体或人像之类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作品包含着男性的欲望,即使那些似乎与性别无关的静物画、风景画,由于通过“透视法”预设了一个“男性”的视野,也与性别观看的欲望有关。(注:关于“绘画”与性别观看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可以参看英国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在《视线与差异》一书中的论述,陈香君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
之所以强调“绘画”与性别观看的关系,是因为它在事实和隐喻的层面上指涉了梦珂从“女学生”到" Modern Girl" (时代女性抑或摩登女郎),再到“女明星”的变化,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她在姑母家中的一段经历,而这段经历和“绘画”(事实的和隐喻的)关系密切。所谓“事实”层面指的是梦珂一直在学习绘画,即使因为“模特儿事件”离开美术学校(她看到了男教师对女模特的侮辱,却未必意识到这种侮辱内在于“美术教育”这种现代视觉体制中),她在姑母家中也没有放弃,反而在表哥和詹明的怂恿下,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看法国的裸女和风景画册,画窗前的景色,画自己的手脚和其他静物,到野外写生……),而在“隐喻”的层面则暗示梦珂不仅在学习“绘画”,同时也在学习“绘画”背后的男性“观看”的眼光。自然,后一种“学习”对应的是她在姑母家中慢慢地从一个朴素的“女学生”转变为一个浮华的" Modern Girl" (时代女性抑或摩登女郎)。在这个过程中,梦珂的变化不仅是物质上的,小说对此有非常精细的描写,譬如梦珂离开美术学校来到姑母家中,住进城里富贵人家的第一个“夜晚”:
她更是不能安睡的辗转在她的那张又香又软的新床上,指尖一摸触到那天鹅绒的枕缘,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致的装饰,漂亮的面孔,以及快乐的笑容……好像这都是能使她把前两天的一场气忿消失得尽净,而只醉一般的来领略这所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以及这一所谓的朋友情谊。但,实实在在这新的环境却只扰乱了她,拘束了她,当她回忆到自己的那些勉强装出来的样子,做得真像是非常自然的夹在那男女中笑谈着一切,不觉羞惭得把眼皮也润湿了。过后才又拿起许多“不得已”的理由,算是来宽恕了自己被逼迫做出来的那些丑态。但暗地里却不敢真的便把那一点愧心放下。如此的翻来覆去的,好半夜都不能睡着。真的,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虚饰的生活,除非再跳转到童时。“难道这里的人都是不坦白,不真诚……”最后只好归怨到自己。为什么自己不忠实的来亲切这里所有的人。
“他们待我都是真好的……”在这样默念中,才稍稍含了点快意睡觉去。
细腻之处可以和后来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媲美,但由于直接引入了乡村和经济的因素,在视野的开阔上与张爱玲相比犹有过之;同时她的变化也是精神上的,“新青年”式的高雅文学和艺术,是否隐含着“欲望”的陷阱?当梦珂留连陶醉于浪漫的文艺,她有没有意识到其中危险?将一切归于表哥的“伪君子”形象实在过于简单,多年以后《青春之歌》用另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疑问:余永泽的“真诚”为什么也不能疏解林道静的“精神危机”?尽管“梦珂”和“林道静”不是同路人。实际产生的效果是,梦珂越疏离她的旧同学匀珍,她就越靠近本来有些厌恶的表姐和杨小姐,“虽说后来匀珍曾向她又修好过,但她一半为负气却没覆信,一个冬天尽陪着这几个漂亮青年听戏,看电影,吃糖,下棋,看小说过去了”。和表姐她们一样,梦珂慢慢懂得了“男性”眼光的含义,知道怎样来应付这种眼光,并尝试着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别人,最终学会如何利用这种眼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男性的眼光“塑造”了她,她成为了“女明星”,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现实中:“她居然很能够安闲的,高贵的,走过来握那少年导演的手,又用那神采飞扬的眼光去照顾一下全室的人。”
从第一个层面“被观看的女体”到第二个层面“被观看者”也逐渐受到这种眼光的影响,直至逐渐认同这一眼光,贯穿着两个层面的是一种共同的“凝视”逻辑。
所谓“凝视”(Gaze),作为一种观看的方式既可以体现在“电影”上,按照劳拉·莫拉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的分析,指的是藉由“编写视觉领域的过程”(凝视的第一层意义),电影引导观者眼睛观看(第二层意义)的视线(第三层意义)的移动,并为之生产意义和快感;(注:参见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 Movies and Methods, Vo.2.ed.Bill Nichols.Berkeley: U of Cal.Press.1985.P.746—757。中译文见劳拉·穆拉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载《电影与新方法》,张红军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它也同样表现在“绘画”上,即绘画的编写过程带领了观者视线的移动范围。“凝视”与一般“观看”(Look)的区别在于,除了明显的性别观看的因素外,它还包含了一种目光的游走和移动的路线与轨迹。这就使得“男性凝视”不是简单地指男人观看的视线和眼光,而是意味着编写、组织观看对象的过程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与幻想而设计的。所谓“凝视的逻辑”,也即控制着这个过程的思维方法和内在机制。它并非男性的专利,女性同样可能落入这种“逻辑”的控制。
“凝视”的逻辑落实在社会层面,就是通过电影、摄影、绘画等视觉机制生产出某种普遍性的观看方式。由于现代社会的充分媒介化,这种人为构造的“观看”方式被自然化了,使得人们不知不觉间认同了这种眼光,进而内化为自我观看的模式。《梦珂》的意义不仅在于将“观看”的两个层面并置,暴露了“凝视”逻辑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把梦珂受控制的“眼光”扩展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视野”,经由这种“视野”批判性地建构了一幅后五四时代的都市景观,在这幅图景中,何者被安放在显眼位置,何者被排斥在视线之外,全由“凝视”的逻辑来决定,它构造出一种“观看”的政治。
四
把“观看”的政治和都市的图景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加以出色表现的文学家是波德莱尔。他在1863年《费加罗报》上发表了《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在其中题为“女人与姑娘”的部分,波德莱尔为游手好闲者/艺术家策划了一次穿越巴黎的行程,女人在这里似乎只不过是天生令人瞩目的尤物。一旦开始这一部分的阅读,你势必意识到文章正借着都市空间——现代性的空间——的虚构地图在构建“女性”的概念。游手好闲者/艺术家的旅程是从戏院大厅开始的,那儿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们衣着雪白,呆在她们的包厢里。接着他留意到一些属于上流社会的家庭在公园里悠闲的溜达,妻子们满足的斜靠在丈夫的手臂上,而瘦削的小女孩们也模仿着他们的长辈,玩着打社交电话的游戏。他继续走,来到一个低级的舞场,一些苗条纤弱的舞者出现在耀目的聚光灯下,尤令那些肥胖的中产阶级男子艳羡。在咖啡厅门口,我们碰见了一位体面的人物,他的情妇就在里面,文中称之为“肥胖的滑稽女人”,她其实完全可能成为一名贵妇,可就因为阶层有别,也就无此希望了。然后我们进入瓦伦提诺(Valention' s)、普拉多(the Prado)或卡西诺(Casino)的大门,在地狱般幽暗的灯光背景中,我们目睹了变幻莫测的放荡美女——高级娼妓——的形像,“滋生在文明的腹地的奴隶的完美形象”。最后,他描绘了不同的女人,上至富有贵族气质的年轻且享有盛名的妓女,下至低级妓院中的可怜奴隶。(注:参见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女人与姑娘》,载《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508页,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波洛克在《视线与差异》一书中也结合印象派绘画的历史讨论了波德莱尔的这篇文章,她指出:“波德莱尔的文章将巴黎的图像构画为女人的城市。它建构出一种可与印象派艺术实践相互连结的性化旅程。”(第111页))
丁玲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是,《梦珂》不是单纯按照空间的移动来建构都市图景的,而是以梦珂身份的变化(女学生,Modern Girl,女明星)为线索,依照她的眼光,或容纳或排斥各种女性人物,表达出对她们背后都市面貌的态度。丁玲与波德莱尔相似的是,她或他都通过描写女性的位置来展示都市的图景。
作为“女学生”的梦珂已经和家乡疏远,与乡村相比,城市或许给她更多的归宿感([梦珂说:]“我想回去,爹一人在家一定寂寞得不像样……还有袁大她们都要念我的。”匀珍心里却想:“你也常常忘记你爹的。哼,袁大,人家都快有小孩,谁还会同你玩……”);当梦珂由“女学生”变成" Modern Girl" ,她的眼光逐渐被“凝视”的逻辑所捕获,愈益认同表哥和表姐常常出入的都市娱乐和消费空间(“她邀表姊同去买衣料,但表姊硬自作主替她买了一件貂皮大氅,两件衣料,和些帽子、皮鞋、丝袜零星东西,一共便去了两百四五十元,表姊还在挑剔那些东西的坏处,后来又只得把自己的许多好的手套、香水……送给她。梦珂还有点难过,当想到父亲时。既至一看钱所剩已不多,便请姑母辈吃了一餐大菜”);而渐渐远离她的同学和老乡匀珍居住的普通市民空间(“民厚里已非早先的可留恋!一进门便听了许多似责备的讥讽话。她只好努力的去解释,小心的去体会,但匀珍总不肯转过她的脸色来,单单为那一件大衣,总足够忍受了四五次的犀锐的眼锋和尖利的笑声,因此反使她觉到曾经轻视过和还不曾施用过的许多装饰都是好的。为什么一个人不应当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点自己的美,总不该说是不对吧!一个女人想表示点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侪属,难道就必得拿‘乱头粗服’去做商标吗?……她忍不住回报了匀珍几句才回来”);更不用说她对女革命者——中国的“苏菲亚”——的天然拒斥,是与她对革命活动所依赖的肮脏黑暗的城市空间的厌恶密切相关(“在一个黑弄里踅人,走进一间披满烟尘的后门,从房里传出来一阵又粗、又大、又哑的歌声,厨房里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厮在低着头吃饭,爬满桌上灶上的是许多偷油婆。雅南已走进客堂门,梦珂在自来水管边窗前,望清了房里,那儿正有两对男女在,歌声便是从那睡在躺椅上的男人所唱出,他的半身又已被一个穿短裤的女子压着,所以那粗声中还带点喘。书桌前面的那一对,是搂抱住在吸纸烟”);即使梦珂识破了“新青年”的虚伪,认识到“被看”的命运,她可以逃离姑母的公馆,却再也无法摆脱已经固定了的社会位置以及与这一位置同构的城市空间:
她本是为了不愿再见那些虚伪的人儿才离开那所住屋,但她便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吗?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她简直疯狂般的毫不曾想到将来,在自己生涯中造下如许不幸的事。但这都能怪她吗?哦,要她去替人民服务,办学校,兴工厂,她哪有这样大的才力。再去进学校念书,她还不够厌倦那些教师,同学们中的周旋吗?还不够痛心那敷衍的所谓的朋友的关系?未必真能整个牺牲自己去做那病院看护,那整天的同病人伤者去温存,她哪来这种能耐呵!难道为了自己所喜欢的小孩们去做一个保姆,但敢不敢去尝试那下人的待遇,同一些油脸的厨子,狡笑的听差,偷东西的仆妇们在一起……当然,她是应该回去的,不过,她一看到那仅仅剩下的二三十元便发恨,“呵!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还能忍耐到回去吗!……”结果,她决定了!她是有幻想的。她不知道这是更把自己弄到“还不堪收拾”的地方去了。
小说中这一大段关于梦珂走投无路的告白,不是出于矫情的抒发,而来自真实的感受,她别无选择地成为“女明星”,用另一种方式参与和分享了城市的娱乐和消费空间。
从这儿引申出来的问题与五四女性解放的议程有关,正如我在前文中强调,丁玲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而是在都市的消费文化、社会的凝视逻辑和女性的阶级分化等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把抽象的“解放”口号加以“语境化”了,透过“视觉互文”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一方面女性解放的口号因为无法回应分化了的社会处境而愈显“空洞”;另一方面刚刚建立起来现代体制已经耗尽“解放”的潜力,反而在商业化的环境中把对女性的侮辱“制度化”了。面对这种情景,妇女如何寻找新的“解放”的可能,是后五四时代丁玲持续追问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