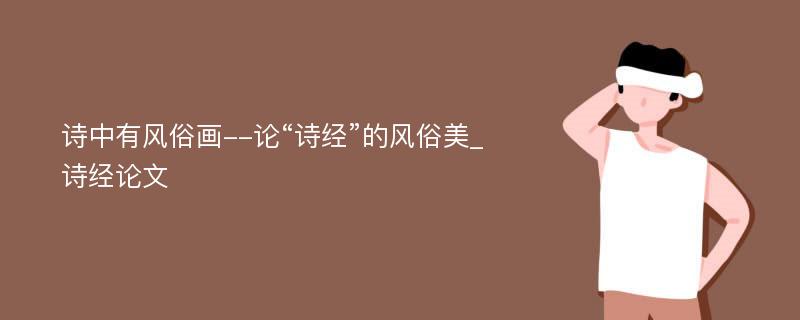
诗中自有风俗画——谈《诗经》的风俗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俗画论文,诗经论文,风俗论文,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经》里保留了离现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种种风俗。这些民风民俗的图画,对于古今的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具有令人心醉的美感。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就是美”。遥远古代的生活也应该是美学。朱光潜先生说:“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自从人类开始断发文身,披树叶遮羞,筑巢掘洞,敬神祭祖,乃至进行乐歌舞踊之类文艺活动之日起,人类就已开始有了审美的观念和美学思想。应该说,《诗经》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是异常珍贵的。对《诗经》中民歌的风俗美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活动。过去“文学史”上,以至一些研究《诗经》的论文中,极少涉猎于此,大有买椟遗珠之憾。
《诗经》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社会由西周奴隶制极盛时期逐渐转变为封建制的时期。当时的生产有农业、畜牧、以及渔猎等,以农业为主。为了祈祷农作物丰收,统治者在一定的季节里要进行祈年祭神的大典。《诗经》里的《甫田》、《大田》就是王者祈年祭神的歌。原始社会,音乐、舞蹈都与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精神密切相关的。从《诗经》里这些祈年祭神的诗歌中可以看出,美的实用目的非常突出,就是表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无限崇拜,对于祖先的虔诚祭祀、对于丰收的烈热庆祝。这种美的实用目的早于美感的享受目的。《吕氏春秋》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述了当时歌舞的场面、内容,也记载了先民们有歌有舞的民俗。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种祭祀庆典中的歌舞代表着我们民族风俗美一种最早的追求。
在举行祭祀“社”神(土神)大典上,伴有歌唱、舞蹈,《大田》描写了这个盛大的场面:(译文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下同)
“以我齐明, 黍稷装满碗和盆,
与我牺羊,配上羊羔毛色纯。
以社以方。祭祀土神四方神。
我田既臧,我的庄稼长得好,
农夫之庆。召集农夫同欢庆。
琴瑟击鼓,击鼓奏瑟又弹琴,
以御田祖,迎神赛会祭农神,
以祈甘雨,祈求上天降甘霖,
以介我稷黍。 使我庄稼得丰收,
…… ……
这是西周时的蜡祭。在举行蜡祭这一天,举国腾欢,歌舞宴饮。奴隶主们认为,奴隶们一年的劳作成果已经入仓,农闲时,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以期来年他们更卖力气。而对于农奴们来说,则是一次盛大的节日,是对丰收的庆祝。他们“琴瑟击鼓”纵情狂欢,尽情歌唱。我们似乎看到他们欢欣的笑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歌声。这一节日中他们唱的什么歌,跳的什么舞,文献记载阙如,我们不得而知。宋代苏轼在其《东坡志林》一书中说:“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己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表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他是说,蜡祭有“尸”(主祭),迎猫则为猫之“尸”,迎虎则为虎之“尸”,近于倡优所为。此说不知是他根据宋代情况的一种推测,还是另有史籍可征?如果是后者,那末这种舞蹈就是巫人扮虎和猫的拟兽舞蹈;可知当时也有在蜡祭中扮演其他神祗的舞蹈,这就是所谓“蜡戏”。“蜡祭”起源很早,之后通称“蜡”,盛行于整个封建社会。今天的“蜡八”节(农历蜡月初八)就是“蜡祭”之遗风。《诗经》里描绘祭祀风俗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音乐和舞蹈分别借声音与形体的动的节奏,旋律和表现形成的艺术美这是动形态美”。“人们欣赏舞蹈,是因为舞蹈通过有形的节奏能表现出形体美,人们能从这种形体美以及由它的各种相关动作、面部表情、手势及道具等效果所构成整个图景,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要求,得到美的享受。因此,就美的感染力的性质来说,舞蹈和音乐是很相近的。”
当时宗庙的祭祀,年轻的女子也可以主祭。《召南·采苹》篇里记载:“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那时认为少女可以作为主祭,因为她“有齐”,即“美而恭敬”就可。这种风俗表示了当时对女性尊重的社会风尚。
《诗经》里反映婚姻和爱情的诗歌是大量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民俗。
有不少诗歌反映了当时“会男女”的风习。如《郑风·溱洧》的第一段:
溱与洧,
溱水流,洧水淌,
方涣涣兮; 三月冰融水流畅。
士与女,
男男女女来游春,
方秉蔺(兰)兮。
手拿兰草驱不祥。
女曰:“观乎?”妹说:“咱们去看看?”
士曰:“既且(徂)。”哥说:“我已去一趟。”
“且往观乎?
“陪我再去又何妨!”
洧之外,洧水外,河岸旁,
洵于且乐。 确实好玩又宽敞。
维士与女,
男男女女喜洋洋,
伊其相谑,
相互调笑心花放,
赠之以勺药。 送支芍药表情长。
这首诗,写的是郑国溱水、洧水之滨,于“上巳节”(魏晋时定为三月三日)男女会合的情景。在清波荡漾的水边,青年男女熙熙攘攘,山歌互答,尽情欢笑嬉戏,并互赠定情物,表达爱恋之情。《韩诗》解释:“《溱洧》,说(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俱往观也。”《汉书·地理志》引此诗,颜注曰:“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这种风俗,《论语》巳有记载。汉末的蔡邕在《月令章句》中说:“《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而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溪,盖出于此也。”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也记载:“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
可见,最初的“上巳节”是人们祈求消灾去病的,即所谓“祓禊”,后来,人们就以男女春游取而代之。由祈求消灾去病而演变为男女爱情的追求,这是美的转移,美的回归。
据《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诗经》中的《周南·关睢》、《周南·汉广》、《周南·汝坟》、《召南·江有汜》、《邶风·匏有苦叶》、《鄘风·桑中》、《卫风·淇奥》、《郑风·褰裳》、《秦风·蒹葭》等篇都有所反映。
《郑风·野有蔓草》,更是浪漫,一对青年男女,不期而遇,异性吸引,一见钟情,并且在“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的环境中尽情表爱,如愿以偿。
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的青年男女,在“合法”的节日里,大胆而带有“野性”的恋爱,结合的习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在性爱中都是大胆主动的,与后来封建社会里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女性有别。远古人总是把“性爱”与“祈天”联系在一起。正如龙辉宏同志在《“云雨”与巫山神话考释》文中指出,“云雨”是中国最古老的隐语,除了猥亵、淫媚之外,尚有更深层的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先民求雨祈年活动;而先民求雨祈年的仪式“均是通过男欢女爱的性行为来诱发天帝兴云布雨的”。当然,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男欢女爱的性行为”是不能“诱发”“天帝兴云布雨的”。但远古时代人们对此坚信不移。所以才会出现“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风俗。
《诗经》里描写的“性爱文学”,作为中国最早的“性爱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了“中国式”的审美特征。它是隐讳的,它是朦胧的,它是与自然美融为一体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诗经》这些篇中青年男女选择配偶的审美标准也值得注意。他(她)们希望男女的人体美是高大硕壮。形容男的如“伯兮遏兮,邦之杰兮”(《卫风·伯兮》);“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郑风·泽陂》);形容女的如“硕人其颀”、“硕人敖敖”(《卫风·硕人》);“硕大无朋”(《唐风·椒聊》)。这种对健美的选择与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劳动考虑的审美有关。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男性的“阳刚之美”特别欣赏,甚至希望女性也带有一定的“男性美”。当然《诗经》中也有“阴柔之美”“秀丽”的女性形象,但“雄伟”的“阳刚之美”占了上风。
定情时互以花草(包括花果、佩玉)为赠,是当时一种纯朴而带有诗意的礼俗。《静女》篇中写道:(译文用余冠英先生的,笔者注。)
静女其娈,
幽静的姑娘长得俏,
贻我彤管。
送我一把红管草。
彤管有炜,
我爱你红草颜色鲜,
说怿女美。
我爱你红草颜色好。
自牧归荑,
牧场嫩草为我采,
洵美且异。
我爱草儿美得怪。
匪女之为美, 不是你草儿美得怪,
美人之贻。
打从美人手里来。
《溱洧》篇:“士与女,方秉蔺(兰)兮”,“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木瓜》篇:“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
这里的“红管草”,一束兰花,一束“芍药”,一颗“木瓜”、“木桃”“木李”,并不是十分珍贵的花草、花果,但在热恋中的少男少女心里,它们是爱情的传递,深挚恋情的象征。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的:“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泪表达出来的那么深的思想。”这就是美学上的“移情作用”。
从这些风俗看,当时男女双方定情,并不要求丰厚的财礼,而以花草为赠。这种爱情的信物是表现我国古代人民的节俭为美的美学观的。男女定情时,女的赠以花草,男以多以佩玉赠之。如《女曰鸡鸣》:“杂佩以赠之”;《丘中有麻》:“贻我佩玖”。这里佩玉与花草一样,也是一种传情的信物。从美学上讲,它不具备或少有使用价值,而更多地带上装饰、欣赏的价值,孔子说过:“男女无媒不交,无币(见面礼)不相见”。这里的“币”(见面礼)就是指赠“花草”“佩玉”之属。
《诗经》里有一些迎亲、送亲及在婚礼上唱的赞歌。当时婚礼唱赞歌是一种礼俗。据《仪礼·士昏礼》载,男女之婚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齐风·著》:“俟我于著乎而”,“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这里记叙了迎亲的礼俗。迎亲者——新郎骑着高头大马(红白色的马),新娘的母亲嫁女时要亲自为女儿结上佩巾,谓之“结缡”。“九十其仪”,可见其礼仪特别繁琐。《礼记·昏义》载:“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延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而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受绶,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即《齐风·著》写的“俟我于著乎而”(屏风前),)妇至,婿揖而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古老的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仪之美,实际上是古代劳动人民心灵美的具体的体现。
赞美新娘的诗,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柔嫩的桃枝和艳丽的桃花赞美新娘的美丽,以“有蕡其实”(桃子结实肥又大)、“其叶蓁蓁”(叶子浓密有光华)作为希望她婚后早生贵子的“隐”语。高尔基说:“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此外,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
社会美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生活形象。新嫁娘之美,人们对她的赞美都是劳动人民对自己劳动创造力的一种积极的肯定。这种风俗,甚至赞诗中特有的“赞语”,如“宜其室家”,“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一直影响到今天婚礼赞歌,可见这种风俗美强大的生命力。
《唐风·绸缪》,这是“一首行婚礼时晚会的歌曲。所以仍是参加婚礼的亲友对于新郎新娘的赞歌”“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这“当是婚礼的晚上亲友们闹房的唱词。当时可能由一个人领着唱,然后大家应和着唱”这是中国“闹新房”最早的记载。这种风俗值得研究。它表现我国古代人民具有的喜剧美的传统性格。这首诗,以雅表俗,“寓庄于谐”。《史记》的《滑稽列传》中讲优旃“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谐辞隐言”这种“谐”与“庄”的统一,就是构成喜剧美的基础。“闹新房”中的语言要求以雅表俗。如此诗中,以“绸缪来薪”,用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柴禾,象征新婚夫妻拥抱、交媾,以“三星在天”,点明新婚之夜。以“薪”、“刍”、“楚”,象征新娘新郎爱情之火,如“烈火遇干柴”。以含蓄的隐语,造成一种诙谐喧闹的气氛。袁梅先生在《诗经中反映的先秦婚俗》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这样说:“直到近代婚俗,犹有将一束木炭置于新房内者,亦有将一束竹筷和一把木勺悬于梁上者,这大概就是‘束薪’的遗俗。”此言极是。
《诗经》中有些诗反映了当时多子多福的风俗。古人认为多生子女是一种幸福和欣慰。“三多九如”中的“三多”,就指寿、富、多男子。《庄子·天地篇》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多生子女思想,是宗法社会的产物,现在看来,是不足取的。但不能以今天的节育,优生的观点去要求《诗经》时代的民俗。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只有多生子女,繁衍后代,人丁兴旺,生产才能发展。如《螽斯》就是祝贺多生子女的诗。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有好客之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诗经》里有许多招待朋友,燕饮所唱的歌,就反映这种风俗。如《小雅·伐木》篇中写道:“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此诗,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起兴。以鸟鸣求友喻人求友。主人为了宴请诸父与诸舅,不惜用“肥羜(zhū肥嫩的羊)与甜酒,倾其所有,热情款待,洒扫庭除,杯盘罗列。第三章写用美酒佳肴宴乐兄弟。《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鹿鸣》都是写求友与宴饮的。
《礼记·学记》载:“《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把学习《小雅》三篇诗,即《鹿鸣》、《田牡》、《皇皇者华》,作为官之始。《大戴礼·投壶》中所记可歌的八篇诗,也有《鹿鸣》。唐代宴乡贡,《鹿鸣》为席上歌曲之一。可见此诗影响之大。
宴请亲朋好友,以丰美的酒菜招待。这不仅是酒菜的问题。而是一种感情的倾注、传递,是一种美的心灵的体现。古语有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唐诗有所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直到今天,还有所谓“感情深,一口闷”(“闷”者,干杯也。)之类,都是这种古风俗的遗传。
古代西方也有备酒款待客人之风俗,但与中国古代的宴饮文化就有很大区别。中国自《诗经》以来的宴饮文化,往往是重感情的转化、传递,又同时是重礼仪的。“情”与“礼”融而为一,西方往往偏重于外交礼节。
《诗经》的风俗美内容丰富,在美学研究中这是一块急待开采、发掘的宝地。本文属“抛砖”之想,庶几引方家之“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