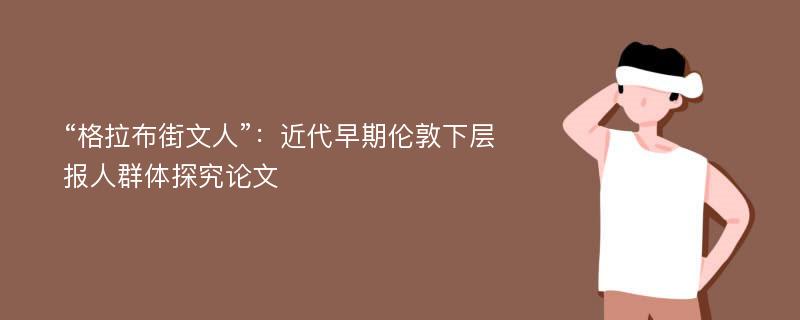
“格拉布街文人”:近代早期伦敦下层报人群体探究
张英明,陆伟芳
摘 要: “格拉布街文人”是17、18世纪英国伦敦的一个下层文人群体,包括受雇记者、报刊的撰稿人以及文学苦力,亦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出版印刷商以及某些成名之前的作家等。社会转型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被看成雇佣文人的象征,生活困顿、煮字疗饥、声誉极低,为世人所嘲讽。但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社会地位以及精神状态等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为英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于社会的批判,亦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社会转型。
关键词: 格拉布街文人;近代英国;亚文化群体;社会转型
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下的复杂社会政治环境孕育出一批以写小册子为生的自由职业文人群体。17世纪30年代,由于“出版法庭法令”[注] 1586年,女王颁布“出版法庭法令”,亦即“星法院法令”,严厉压制出版自由。法令的颁布及长期应用,使得印刷违禁报刊书籍的文人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和学徒制度的限制,英国伦敦西区墨菲尔德的格拉布街及其周边地区,因易于躲避追查的环境,便成为一些学徒工和印刷商躲避政府检查的庇护所。随后,众多贫困作家及新闻记者等自由职业文人不断向这里聚集,他们受雇于一些印刷出版商,在格拉布街的阁楼上从事编写、校对、翻译以及诗歌创作等工作。久而久之,这些贫困作家、新闻记者及印刷商等便被称为“格拉布街文人”(Grubstreet Literati)。18世纪初,受文学商业化浪潮的推动,众多文人作家来到伦敦寻求成功的机会,导致伦敦文学市场劳动力严重过剩,格拉布街的状况扩展到了整个伦敦的贫困区。“格拉布街文人”的适用范围亦有所扩展,既包括受雇的记者、为报纸写作的人以及文学苦力,也包括一些出身较低的出版商、印刷人以及成名之前的某些作家,例如18 世纪英国文学巨匠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及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他们被视为文学商业化浪潮中的典型雇佣文人,逐渐成为伦敦下层文人的代名词。
很多农村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师资力量和配置资源相对比较薄弱,使得学生的总体音乐基础水平都低于城市小学或者规模相对较大学校的学生。为此,在有限的条件下,必须改进合唱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是创新教学方式,让学生积极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诸如,可以采取两两搭档或者分组比赛的形式,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提升音乐合唱教学的课堂效果;二是改革教学模式。摒弃传统合唱教学模式,借鉴国外和大城市小学音乐合唱教学的成功经验,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进行传承、改革与创新,将音乐合唱教学效果提高到新层次、新境界。
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使得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少数能引起轰动的政论文人、文学大家,而大部分边缘化的格拉布街文人往往为社会所忽略。然而,正是由于这个被大众忽略的群体的努力,英国新闻出版行业才从初创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他们的作为对英国社会转型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社会地位、精神状态等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不断斗争以及对于社会不满的宣泄,也反映了转型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
一、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
17、18世纪,文学商业化浪潮中的格拉布街文人没有固定的个人收入,他们为生计写作,按照写作的行数获得报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低等的文学活动,生活困顿、煮字疗饥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整个17世纪,“伦敦既是一个财富中心,又是一个拥挤、不卫生和危险的地方”。[注]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 陈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格拉布街的环境亦极差。据记载,该街道以疟疾和黑死病的存在而著称,[注] Pat Rogers, Hacks and Dunces :Pope ,Swift and Grub Street , London: Methuen, 1972,pp.23-24.是臭名昭著的不健康之地,极易传播疫病。其治安状况更是恶劣,暴力事件多发,有人曾见到一天晚上有一个制鞋匠被两个暴徒打倒并抢走三先令六便士。[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London: Ashgate, 2004, p.3.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曾描述格拉布街说:“其极不规则的建筑群,……就像一个丛林,在这里,盗贼就像是非洲或者阿拉伯沙漠里的野兽一样可以极为安全地躲藏。”[注] Henry Fielding,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p.3.卖淫亦泛滥。自一个叫哈比杰的小姐将卖淫场所引入格拉布街,随后出现了牛夫人、半便士夫人、哈里森夫人等“狡猾的鸨母”,以及乌洛斯夫人等“普通妓女”。[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1.总之,格拉布街经济落后、盗贼横行、卖淫泛滥、疾病传播严重,整个街道上充斥着狭窄的小巷、贼窝、妓院。这种状况在整个伦敦边缘贫困区[注] 当时的英国贫困区是环克拉肯韦尔区(Clerkenwell)与圣· 约翰门(St John’s Gat)一带。 普遍存在。
其次,格拉布街文人多从事新闻出版行业,在行业声誉不佳的情况下,其声誉自然受行业所累。内容缺乏准确性,是新闻出版行业声誉不佳的主要原因。18世纪,英国政府对消息严格控制,在缺乏消息的情况下,格拉布街文人费尽心思获得的都是些二手甚至多手资料,内容多来自咖啡馆或酒吧的流言蜚语,所以,在报刊上出现偏差甚至编造故事的状况十分普遍。艾迪逊曾讽刺道:“大不列颠的新闻记者比士兵更为英勇,当我们的军队按兵不动时,新闻记者发起了多处进攻,当我们的长官满足于伟大的会战时,新闻记者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尤金亲王杀死上千人的地方,博耶(一名格拉布街文人)杀死了一万人。”[注] 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第126—127页。 由此可见报刊内容的失实程度。报刊之间相互抄袭的状况亦较为常见,很多报刊在晚上刊登早报上的事件,在第二天早上又刊登前天晚上的事件,使新闻和旧闻相互交错,混乱不堪。交通通信条件的落后也造成时效性较差,比如法国的事件要在一周之后才能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报刊内容亦多粗俗,有些报刊为增加发行量,甚至会出现妓院指南等低俗内容。[注] Pat Rogers, Grub Street :Studies in A Subculture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91.总之,这些状况使得新闻出版行业的声誉受损,一度被描述为“剪刀加胶水的行业”,这自然也给格拉布街文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能够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旅游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融合是乡村振兴的绿色之路,两者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发展新业态的新手段。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为规范出版市场,英国政府又建立了出版法庭,制定了针对文人的《煽动诽谤法》。这一法令对于文人的惩罚十分常见,一般有三种:戴枷示众、监禁以及罚款。笛福曾经历过以上三种惩罚。其中,最为大众化的当属监禁。煽动诽谤罪,加上债务的原因,使得入狱成为18世纪格拉布街文人的职业危险。在查尔斯·罗克罗夫特(Charles Rowcroft)的《舰队监狱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Fleet prison )中,列举了一些有着入狱经历的格拉布街文人,如W. H. 安斯沃思(W. H. Ainsworth)、G. W. M. 雷诺兹(G. W. M. Reynolds)、西奥多·胡克(Theodor Hook)、G. P. R. 詹姆斯(G. P. R. James)、皮尔斯·伊根(Pierce Egan)、道格拉斯·杰罗德(Douglas Jerrold)等均名列其中。狱中的生活十分艰苦,著名诗人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Ligota)在1768年入狱,因不堪狱中生活,1771年死于狱中。格拉布街文人为了生存,在狱中依然需要写作,如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会付钱给同监狱中的其他人来保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能够继续写作。[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45.但并不是所有的格拉布街文人都有这样的运气。曾是《文艺论坛》(Athenaeum )编辑的托马斯·基布尔·赫维(Thomas Keble Hervey)多次入狱,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没有单独的房间,连写作必需品都缺乏,甚至没有床,更不用说写作的桌子了。[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45.格拉布街女文人伊丽莎白·哈迪(Elizabeth Hardy),因债务被监禁,两年后死于狱中。一位护士曾对哈迪的狱中生活描述道:“哈迪最后两年完全处于生死边缘……她会在破晓起床,亦经常写作到深夜,尽管在狱中,她完全像作家一样生活。”[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p.157-158.
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密钥协商协议……………………………………………………张佳妮,何德彪,李莉 24-6-23
格拉布街文人亦喜欢组织俱乐部。蒲柏、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盖伊、艾迪逊等组成了“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Scriblerus Club)。约翰逊成名后成为伦敦文学俱乐部的领袖,像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注] 夏洛特·伦诺克斯是18世纪著名的女性小说家,深受约翰逊赏识,著有小说《女吉诃德》,在许多的报刊上发表过重要文章,在当时文名较高。但是其一生不停地与贫困做抗争,始终未能摆脱贫困的缠绕。她很多时候受到约翰逊的帮助,是格拉布街文人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详见李维屏、宋建福:《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外国语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5页。 等格拉布街文人均是该文学俱乐部的常客。其中,哥尔德斯密斯更是还热衷于参加诸如“星期三俱乐部”“先令惠斯特俱乐部” 等下层文人俱乐部,并经常表演以娱乐大众。[注] 具体可参见华盛顿·欧文:《哥尔德斯密斯传》,王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书中描写了很多日常娱乐活动,哥尔德斯密斯等文人经常在酒馆、咖啡屋中组织俱乐部聚会。
格拉布街文人困顿到如此地步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有限。这些文人多供职于新闻出版行业,在广告收入甚微的情况下,报刊的销量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在今天发行量普遍巨大的报刊,在18世纪每天最多只能卖出几千份。[注] 18世纪,由于出版技术有限,版面设计及印刷方法亦沿用手工模式,严重阻碍了印刷数量和销量。1766年,《公共广告人》(Public Advertiser )日平均发行量为2228份;1789年,《记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 )每天的发行量为4000份。具体可参见Bob Clarke ,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p. 97-100。《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在1795年的发行量仅为350份每天,即使到1803年,日均发行量也只有4500份。可参见W. Hindle, The Morning Post ,1772-1937 , 1937。 这样的发行量维持收支平衡尚且不易,能够盈利的则是少之又少,由此可知,格拉布街文人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实际上,处于新闻出版行业主压榨下的文人的报酬少得可怜。比如,约翰逊一首《伦敦》(London )的诗酬不足10个基尼;[注] 科塞:《理念人》,郭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波伊斯将英国文学家乔叟的作品引入现代英语中,其报酬却只有每百行三个便士。[注] Edward Hart, Portrait of a Grub :Samuel Boys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7 No.3( Summer 1967), p.419.与之同时,这些文人的支出却较大,家庭的重担常使他们疲于应付。[注] 很多文人都有较为庞大的家庭,如笛福有七个孩子,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有八个孩子需要抚养,科利·西伯(Colley Cibber)先后有过10个孩子,在贫困的环境中有六个先于他去世。具体可参见R. H. Barker, Mr Cibber of Drury Lan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257-258。关于科利·西伯的具体状况,亦可参见James Vinson , Daniel L. Kirkpatrick , Dramastists :Great Writ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79, pp. 117-120。比如,丹尼尔·笛福身处监狱时曾写信给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ry),他担心地说:“没能给孩子提供学费是我欠孩子们一笔债,这一不可推诿的责任常常使我感到沮丧。”[注] 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另外,娱乐活动亦是格拉布街文人的一大支出,很多文人沉浸于剧院、酒吧和咖啡馆中,有些甚至染上了酗酒、赌博、吸毒等恶习(后文详述)。[注] 18世纪英国消费主义大兴,娱乐活动盛行,很多格拉布街文人沉浸在剧院、酒吧和咖啡馆中,一些文人更是染上了酗酒、赌博甚至吸毒等恶习,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詹姆斯·汉内(James Hannay)、理查德·萨维奇均有嗜酒恶习,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和托马斯·德·昆西是众人皆知的瘾君子。关于格拉布街文人的娱乐活动以及不良嗜好,在后文的精神生活中有详细介绍。 收入有限而花费巨大,使得经济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格拉布街文人,对很多人而言,生活的困顿伴随他们终生。
二、格拉布街文人的社会地位
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工业革命时期,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格拉布街文人”一直是一个侮辱性的称号,社会地位极低。约翰逊曾评价说:“他们是贫困且默默无闻的一族,这是由于普通的理解力无法理解他们的用处。他们生前未获承认,死后亦无人同情,长期遭受侮辱却没有辩护者,遭受别人的指责却没有人向他们道歉。”[注] Edward Hart, Portrait of a Grub :Samuel Boys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 p.416.斯内德·沃德(Ned Ward)也对自身的状况描述道:“我们与妓女十分相似……如果问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臭名昭著的、下贱的写小册子的工作,答案就是,暗淡的命运导致的不幸境遇逼着我们干这一行来养家糊口。”[注] Howard W. Troyer, Ned Ward of Grub Street :A Study of Sub -Literary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Routledge, 1968, p.3.从他们的描述中可见格拉布街文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境地,他们因生计所迫而从事低等的文学工作,还要时刻承受着大众的指责和谩骂。
垃圾产沼气用于发动机发电是很好的节能减排的方法。但发动机发电后产生的烟气温度高达400℃,大量烟气热量排放大气,造成浪费。发动机本身的缸套水温也高达106~108℃,需通过发动机带的风扇冷却后循环利用,造成大量的低温热浪费。多数大型垃圾填埋场一般会配置多台沼气发电机组,如杭州某填埋场,目前已发电的机组就达到8台,根据未来的沼气产量,沼气机组最终可达到16台。如此多的沼气机组,其余热量也是相当大的。如果加以利用,就可以提高机组的效率,获得更多收益。笔者以某生活垃圾填埋场为例,建立了沼气产气模型,提出了利用余热进行发电的方案。
导致格拉布街文人处于如此境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人自身的行为多为人所诟病。如前已述,处于党派斗争的政治环境下,格拉布街文人多接受党派津贴而相互攻击。例如,笛福在其写作生涯中数次转换政治立场,以致被人称为“唯利是图的精神妓女”。[注] K. Willias, Read All About It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ewspaper ,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60.英国学者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曾评价说:“笛福是一位极端的实用主义者,既是一位温和的辉格党人,也是一位温和的托利党人,所以同时为两个党派写作或者偶尔改变拥护对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注] M.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 London: Sage, 2004, p.61.而约翰逊早年为谋求生计,不得不充当雇佣文人,亦曾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固定立场、只要付钱就可以帮任何人写作的毫无诚信和名誉的文学流氓。[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5.像笛福和约翰逊这样的著名人物尚且如此立场不坚定,其他文人就可想而知。而且,很多格拉布街文人的确还有一些不端行为。比如,波伊斯经常一稿多投,将自己的诗寄给任何可能付给他稿酬的人。萨维奇经常以蒲柏或斯威夫特的名义胡乱编造文章,他曾说:“我有时是盖伊先生,有时又是伯纳特或者艾迪逊。我删减历史和游记,翻译根本不存在的法语书,而且擅长为旧书寻觅新的书名……”[注] https://www.uc.pupessoal/mportela/arslonga/MPENSAJOS/writing_for money.htm. 格拉布街文人的这些不良甚至违法行为,使得他们备受质疑、鄙视,是其社会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
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格拉布街文人生活极为窘迫,英国史学家马考莱(Thomas Macaulay)曾描绘他们的境况说:“住在八级台阶的阁楼上…… 7月,与大伙睡大通铺,12月,在温室的灰烬中安睡,其后死在医院,埋葬在教区的地窖。”[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5.文人汤姆·布朗(Tom Brown)曾声称,自己是 “被锁在了阁楼里”。[注] Paul Daws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new humanitie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15-16.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在没钱住宿的时候,便在一些地下旅店、恶臭的地窖,甚至是一些人渣聚集的地方睡觉:夏天他会睡在露天的地方,冬天则和一些盗贼、乞丐挤在一起。[注]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London: Routledge, 1948, p.348.由此可见,格拉布街文人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他们生活在贫困混乱的地区,很多时候不得不与乞丐、盗贼为伍。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政府和社会的无情打压。在文学商业化浪潮刚刚出现的18世纪,作为第一代受雇文人的格拉布街文人,其为金钱而写作的生活方式不被当时的社会认可,他们被看成是“被黑客和煽动者占据,为了政治家报酬的贪婪冒险者,更有甚者致力于邪恶的目的,煽动大众对抗已经建立的统治阶层”。[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256.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拉布街文人完全被边缘化,受到主流社会的压制。
“魔方就像生活,看起来混乱不堪,却有其规律和秩序。”萧健说,“如果你不急走的话,我给你表演一下。”他将魔方打乱,让静秋帮他计时。他的手飞快地转动着魔方,他令人不可置信的灵巧与熟稔让楚墨眩晕。少顷他将魔方猛地拍上桌子,魔方已经被神奇地复原。他问静秋:“多久?”静秋说:“一分钟四十八秒。”他看着楚墨,说:“今天发挥得不好,我的记录是一分钟二十九秒。”
尽管格拉布街文人追求上层生活方式,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放浪形骸的姿态,崇尚精神的自由,看似一种风流洒脱,但实际上这是他们郁郁不得志而又充满无奈的真实表现。
从图3~图5可以看出:(1)ωc越大,谐振带宽越宽,ωc越小,带宽越窄,对基波频率的控制效果越好,一般情况下ωc的取值介于5 rad/s~15 rad/s;(2)KR越大,控制器的峰值增益越大,而谐振带宽几乎没有影响;(3)Kp越大,系统比例增益越大[11]。
18世纪,在英国社会的论战中,打击对手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对手强力压制到被社会所隔离的下层。由于格拉布街文人的言论对政府构成威胁,他们受到了政府的无情打压。政府精英阶层将格拉布街文人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加以侮辱,在他们眼中文人群体和犯罪群体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文学犯罪群体。在社会中,视格拉布街文人以犯罪的方式对抗政府政治秩序是普遍的事情。在党派政治环境之下,文人为维持生计,要么接受执政党津贴,要么写作高风险的反政府文章,以赚取高回报。于是,众多文人都因党派站队问题而成为不停轮换的政府的所谓“罪犯”。尤其是处于《煽动诽谤法》监控之下,很多时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最出名的当是安妮女王时期的“马休斯事件”(Matthews Affair)。印刷商约翰·马休斯(John Matthews)只是因为出版的刊物有对女王不利的言论,被认为是坚持女王不具有合法继承权的主犯,他被宣判犯有煽动诽谤罪而处以绞刑。[注] James Sutherland, Background for Queen Anne , London: R. West, 1939, pp.182-200.在煽动诽谤罪的控告威胁直接与工作任务的执行相关联的情况下,最危险的莫过于以写作政治小册子为生的文人,像乔治·里德帕斯、查尔斯·莱斯利、约翰·塔钦甚至笛福,都曾有因支持某一党而被另一党判定为犯有煽动诽谤罪的经历。入狱对很多格拉布街文人来说亦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反复地被抓、被放,久而久之,已经适应了这一切而将其看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妓女一样,时常被骚扰而不会抱怨。[注] Pat Rogers, Grub Street :Studies in A Subculture , p.286.
与此同时,格拉布街文人仿佛成了这一时期讽刺文学家的“福利”,在后者口中,格拉布街文人很难逃脱“犯罪阶层”的定论。讽刺文学家总是极尽所能地将格拉布街文人与下层生活相联系,将他们描述成居住在伦敦下层世界的人。比如,笛福曾被说成是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江湖骗子、靠诽谤过日子的文人,约翰逊被称为生活在肮脏地方的酒鬼。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曾讽刺女作家、演员兼出版商伊丽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不知羞耻的涂鸦者用满是诽谤的回忆录和小说揭开男女两性的缺点和不幸,不是损毁人们的社会声誉就是扰乱私人的幸福。”[注] Dale Spender, Mothers of the Novel :100 Good Women Writers Before Jane Austen , New York: Pandora, 1986, p.79.对著名人物尚且如此,其他格拉布街文人更是被讽刺得一文不值。蒲柏的《群愚史诗》(The Dunciad )是讽刺格拉布街文人的名作,诗中以“群愚”来影射格拉布街的庸俗批评家、蹩脚诗人和不法书商,甚至将格拉布街比喻为粪堆,将格拉布街文人视为生活在粪堆里的无知愚人,将他们创作的诗歌、戏剧作品看作滋生的蛆虫和昆虫。[注] 具体可参见Alexander Pope, The Dunciad , Hong Kong: Pearson Longman, 2009。
总之,处于转型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打压,游走于城市的边缘,为了生计而写作,在社会中完全没有位置。他们的工作经常被用“粗俗”“下流”等词汇形容,伴随着文学商业化的节奏,就像注释和符号一样衬托着作为“正文”的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将这些文人的写作热情等同于犯罪、卖淫以及疾病的传播,并为他们塑造了一个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地方,这便是格拉布街。可以说,是格拉布街文人赋予了格拉布街以特殊的含义,而格拉布街亦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
三、格拉布街文人的精神世界
格拉布街文人之所以生活困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精神层次的追求花费较大。17、18世纪的英国,享乐主义盛行,娱乐活动大兴。记者爱德华·托汉姆曾说:“我们有高雅的剧院和很好的演员、社交集会、音乐会、公园和散步场所、俱乐部以及无数的娱乐方式。”[注] Edward Topham, Letters from Edinburgh :Written in the Years 1744 and 1755 , Edinburgh: West Port Books, 2003, p.90.阿萨·勃里格斯亦认为,此时的英国“是一个以时髦为荣、追求享乐的口味日益复杂以及人们用很大的努力来成功地满足这些欲望的时代”。[注]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17页。 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拉布街文人亦多追求享乐,对各种娱乐活动趋之若鹜。就如同波伊斯一样,“疯狂地涂鸦到傍晚来获得一杯杜松子酒,典当财产以便能够观看爵士乐表演”。[注] Bob Clarke, 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 , p.6.
观看戏剧是伦敦市民的常态活动,格拉布街文人与戏剧的联系亦较为紧密。比如,约翰逊便是一名忠实的戏剧迷,在利奇菲尔德的剧院中有他的专座。不仅如此,他还热衷于结识演员,经常和演员谈论演出情况。在他学生戴维·加里克(David Garik)的帮助下,他的悲剧《艾琳》(Irene )得以上演,他自己也参与了演出。[注] 关于约翰逊对戏剧的热爱,具体可参见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王增澄、史美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诗人约翰·盖伊(John Gay)同样不仅喜欢观看,而且创作了著名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 ’s Opera )等,作为一名戏剧家而声名远扬。
咖啡馆社交是格拉布街文人的日常活动。著名的威尔咖啡馆是格拉布街文人常聚的地方: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在这里拥有专座;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也是这里的常客;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自称每天早上六点便在咖啡馆了;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dison)更是每天都要待在咖啡馆里六七个小时,观察生活,参与谈话,了解读者兴趣,撰写文章。[注] 科塞:《理念人》,第24页。
并且,生活境遇固然堪忧,当时的政治环境亦不容乐观。18世纪前后,处于英国政党政治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很难置身事外。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接受党派津贴并为之效力。像笛福、约翰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等著名文人均接受过党派津贴。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遭到反对党的报复,如为辉格党写作的乔治·里德帕斯(George Ridpath)在托利党人眼中则是一个“煽动性人物,文字诽谤的制造者,臭名昭著”,他因撰文反对签订《乌特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而被关入监狱,后被迫逃往荷兰。[注] https://www.uc.pupessoal/mportela/arslonga/MPENSAJOS/writing_for money.htm. 反过来,为托利党服务的文人亦是如此,查尔斯·莱斯利(Charles Leslie)就因写作反对辉格党的小册子而被迫逃离英国。除政治迫害外,这些文人还经常遭到暴力恐吓,比如约翰·塔钦(John Tutchin)曾创办《空中邮报》(Flying -Post ),批评时政,攻击安妮女王,1707年他遭到政敌的殴打,不久因伤重不治而亡。[注] H. C. G. Matthew, Brian Harriso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 vol.5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708-711.就连笛福亦曾收到匿名信,威胁说要暗杀他并推倒他的房子。
除了观看戏剧、咖啡馆社交和组织俱乐部之外,格拉布街文人还有很多低级趣味的娱乐方式,比如饮酒、赌博等。菲尔丁认为,当时英国涌现出巨大的奢侈之风,极大地促使下层民众沉溺于昂贵的娱乐、酗酒和赌博这些恶习中。[注] Malvin R. Zirker,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and Related Writing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77-97.格拉布街文人自然不能免俗。众多格拉布街文人都饮酒无度,他们多聚集在简陋的杜松子酒吧中豪饮烈酒。1702年,笛福写道:“一个诚实的酒伴是值得赞许的。”[注] M. Dorothy George, 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th Century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50.约翰逊是尽人皆知的酒鬼,他经常与人在廉价酒吧中彻夜痛饮,最疯狂的一次就连戴维·加里克都觉得他们“嬉闹了一夜,将要名垂青史”。[注] 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传》,蔡田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8页。 哥尔德斯密斯常年沉迷于赌博、醉酒,其同乡格洛弗经常泡在“环球酒馆”和“魔鬼酒馆”之中。[注] 华盛顿·欧文:《哥尔德斯密斯传》,第131页。 詹姆斯·汉内嗜酒成性,最后因酒精中毒死在了大街上。理查德·萨维奇死于饮酒导致的肝衰竭。更有文人甚至染上了鸦片瘾。科勒律治因风湿痛等多种疾病的镇痛需要,长期服食鸦片,竟至上瘾。托马斯·德·昆西亦是瘾君子,由于受害颇深,便写作了《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来表达自身的痛苦。
格拉布街文人还深受英国追求风尚传统的影响,处处标榜贵族生活,模仿上流社会以获得身份认同。如约翰逊成名前喜欢参加宴会,每次通常花费八个便士,其中七个便士用于肉和面包消费,另外一个便士则用于小费,以便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注] 相关内容可参见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p.349。他的朋友萨维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极端贫困的时候依然嫌弃吃饭时没有鸡肉,甚至买了一件镶着金线的披风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注] Richard Holmes, Johnson and Savage :Biographical Mystery ,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3, p.139.
1.1 试验材料 黑斑病菌的分离和纯化:从甘薯窖中采集黑斑病发病薯块,采用组织分离法分离甘薯黑斑病菌。首先清洗薯块表面,然后用自来水流水冲洗约20 min,将带病薯块取出擦干置于超净工作台中,取黑斑病病健交接部位置于75%乙醇中进行表面消毒,再用0.1 %的升汞消毒后,用灭菌水清洗干净后置于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DA)平板中培养,经分离纯化以及柯赫氏法则验证确定后保留菌株。该菌株分离并保存于4 ℃冰箱中。
The trajectory parameter equation in the XOY system is in the following
在18世纪,写作成为格拉布街文人赖以摆脱悲惨命运的寄托。随着文学商业化的日益加深,在当时“对于一个意欲成名的时尚人士来说,最佳路径乃是提笔创作”。[注] Paul Keen, The Crisis of Literature in the 1790s :Print Culture and Public Spher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9.受名利驱使,众人一拥而上,都想趁乱分一杯跻身英国诗人、文学家行列的美梦之羹。对于这种局面,科勒律治感觉大众“像贸易一样追求文学”。[注] 关于当时写作风气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见S. T.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 New York: Routledge, 1906, Chapter XI。俄国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说:“他们就像赌徒一样,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命运会改变,即使100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够成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注] William Jerdan,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Jerdan :With His Lite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 London: Arthur Hall, Virtue, & Co., 25, Paternoster Row, 1852, ii, pp.8-37.但是,成名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历经艰辛之后许多人便沦为“黑客文人”,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出卖自己的思想来迎合能够给予他们报酬的大众,生活困顿,不断举债,甚至入狱。如此状况下的文人有着极大的生存危机感。波伊斯在极端困顿的情况下曾经向《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 ’s Magazine )的凯夫写信求助:“每时每刻都有人威胁我要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因为我已经没钱支付房租了,自从上周二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讨债人随时会脱下我的大衣拿去抵债,如果这样,我只能赤条条地进监狱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注]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p.348.约翰逊也经常三餐不继。1737年,他在给凯夫的信中署名“没有吃早点的人”(Yours Impransus)。他曾经故意躲开卖粥的街道,因为“那美味的香气对于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来说诱惑力极大”。[注]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pp.348-349.可见,格拉布街文人在很多时候基本的生存需求尚且不能满足,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不得不委屈自己向别人求助。同时,危机感不仅存在于生存需求方面,《煽动诽谤法》的威胁更是对格拉布街文人的精神构成了极大伤害。伴随着写作而来的是煽动诽谤罪的枷刑、罚款和入狱等惩罚,这使得以写作为生的格拉布文人极度缺乏安全感,每一天都是带着罪恶感醒来。笛福感觉枷刑示众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比死还坏”。[注] 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第95页。 罚款,使得本就收入有限的格拉布街文人在生存危机中越陷越深。《周刊》(The Weekly Journal )的创办者纳撒尼尔·米斯特(Nathaniel Mist)因屡次被罚,最终没有能力支付,导致其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中度过。[注] 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第144页。 监狱生活更是使格拉布街文人承受着极大的精神折磨,有检察院官员就认为,“被监禁于怀特克罗斯街道监狱的作家不堕落几乎是不可能的”。[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43.罗伯特·吉利斯(Robert Gillies)感觉监狱中“纷乱的环境使得作家无法进行思考”。[注] R. P. Gillies, Memoirs of a Literary Veteran ,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1, ii, pp.20-319.托马斯·阿什在给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的信中亦说:“监狱中的混乱就像风暴一样摧毁一切思想和智慧。”[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44.
然而,生存的危机感只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痛苦的表象,其精神的郁结更是难以排解。生活的困顿以及社会的不公,使成功无望的格拉布街文人对自己和社会极为失望。
然而,较之恶劣的生活环境,经济的拮据是他们面临的更大困境。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格拉布街文人很多时候会陷入极端的贫困。比如,塞缪尔·波伊斯(Samuel Boyce)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裹着一张毯子坐在床上,他在毯子上挖两个洞以便能够写作。他由于没有体面的衣服,只得将白纸绕在脖子和手上出门与书商们洽谈“生意”。[注]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p.349.穷困潦倒的萨维奇,没有容身之所,不得不“在街上游走的时候进行构思,进入杂货店祈求笔墨,将自己的构思写在捡到的纸上”。[注]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18th Century ,1660-1744 , p.348.最终,萨维奇死于狱中,甚至连安葬的钱都是门卫捐助的。而即便是业已成名的人物,亦不能摆脱囊中羞涩的状况。比如,1759年时约翰逊已小有名气,其母亲去世却无以为葬,他用秉烛七个日夜写出的《拉塞拉斯》(Rasselas )的稿酬才应付了葬礼的开销。[注] 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1800年,已名满英伦的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返回英国,要借住在朋友家中,其经济来源多靠写诗和演讲,经常接受官方和慈善机构的补贴。久病以及鸦片的吸食影响了他的写作,甚至他子女的学费都靠朋友资助。[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3.
格拉布街文人很多时候不认可自己,亦不认同自己的工作。比如,亨利·萨拉(Henry Sara)作为一个常年混迹于格拉布街的文人,感觉自己所处的这一群体不像是在工作,大多数人就像是怠惰的小狗在巴黎和伦敦的街头上游荡,……每周用于文学创作的平均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注]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 p.94.约翰逊更是直接指出,新闻作家是没有美德的,常常为了自身利益而编写谎言。他认为格拉布街文人“不需要天分和知识,但是对真理的侮辱和漠视是绝对必要的”。[注] Samuel Johnson, Idler, Payne ’s Universal Chronicle , 11 November 1758.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亦描绘文人的遭遇说:“所有模式的生活中,相信自己的文学努力的人,支撑他们的只能是痛苦……他们厌倦于必须接受的日常劳动,不可避免地被受其声誉影响的销路问题所玷污。”[注] Edith Heraud, Memoirs of John A .Heraud ,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9, p.19.
格拉布街文人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生群体,群体认同意识更是淡薄。他们热衷于给自己的同行戴“沉闷的卖身文人”“傲慢可耻的诽谤者”的帽子,相互之间为了利益(甚至只是逞一时之快)而攻击、讽刺的情况比比皆是。约翰·德莱顿曾塑造“弗莱克诺”这一角色对其文坛敌人沙德威尔 (Thomas Shadwell)进行讽刺和攻击。[注] 约翰·德莱顿与沙德威相互攻击的具体情况,可详见Joseph Spence,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and Men , Carbondale and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4, p.64。蒲柏的《群愚史诗》除了攻击刘易斯·蒂博德(Lewis Theobald)、丹尼斯( John Dennis)、吉尔敦 (Charles Gildon)等对手外,也对一些低级的小册子文人和出版印刷商等格拉布街文人进行无情的讽刺。如前所述,党派政治的大环境更是使得格拉布街文人往往为了津贴而互相攻伐,从初期的奈德海姆与伯肯海德,到后来的笛福、约翰·塔钦、尼古拉斯·阿莫斯特(Nicholas Amhurst)、查尔斯·莱斯利、乔治·里德帕斯、威廉·阿纳尔(William Arnal)等,格拉布街文人之间的唇枪舌战从未间断。
格拉布街文人对于政府和社会也存在极度的不满。托马斯·布朗曾针对当时的社会评论说:“日光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聪明人创办公司,而傻瓜只知道写作和阅读。卖书商较为优越,务实的人可以成为政治家,有钱的人才表现出仁慈,骗子泛滥,酒鬼很少受到谴责,结婚的人并不相爱,情妇在教堂中祈祷并发誓要和淫秽虚伪的行为做斗争。”[注] James Vinson, Novelists and Prose Writers :Great Writ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79, p.173.这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中道德沦丧状况的不满。在对于社会的嬉笑怒骂中,明嘲暗讽是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萨维奇曾写道:“我是一个理想的城镇作者,我憎恨人类。”[注] https://www.uc.pupessoal/mportela/arslonga/MPENSAJOS/writing_for money.htm. 约翰逊在《伦敦》一诗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心境,描述了拜金主义社会中穷人的不幸境地。他在《人类希望的幻灭》(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中更是叙述道:“知识分子的生活有很多可怕之处:谩骂、傲慢、嫉妒、欲望、贫困和坐牢。”[注] 具体可参见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
如果说萨维奇和约翰逊只是单纯表达不满的话,那么,有些格拉布街文人对社会状况的揭露则带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女文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小说《庄园古宅》(The Old Manor House )以及《德斯蒙德》(Desmond )等,对英国的社会生活、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进行了批判与揭露,赢得了“颠覆社会”的名声,被视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注] Dale Spender, Mothers of the Novel :100 Good Women Writers Before Jane Austen , p.224.对社会状态揭露最深刻的当属托比亚斯·斯摩莱特,长期不人道的社会积怨使他在创作之中更多地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心态。其小说的主人公多是自私缺德、毛病较多的流氓或恶棍,在他行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扯掉社会遮羞布的心态,希望以此激发人们改变现实的愿望。此外,还有盖伊的《乞丐的歌剧》、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 ’s Travels )等都是讽刺英国社会的名作。
四、 格拉布街文人与英国社会转型
格拉布街文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英国17、18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这一群体。
16世纪,宗教改革中复杂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一个以写小册子为生的文人群体。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这些小册子的反封建、反宗教倾向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政府陆续出台了控制措施。1538年,英国正式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规定:不经特许的出版物不允许出版。[注] F. S. Siebert ,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overnment Controls ,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2, p.30.在皇家特许制度的压制下,为躲避检查,众多文人便选择了环境混乱的格拉布街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庇护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便获得了“格拉布街文人”的“恶名”。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印刷品被大量用于社会和政治斗争,“在1640年英国只有22种小册子,而到1642年则有1996种”。[注]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161页。 革命派与保王派的唇枪舌战引发的舆论攻势,亦使得格拉布街出现了众多报刊,吸引了更多印刷商和文人来到此地。1695年,有关出版检查的制度最终废除,格拉布街的新闻出版行业迎来了春天,从事这一行业的格拉布街文人群体进一步壮大。在政党政治繁荣的18世纪,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轮流执政的复杂政治环境,造成了新闻出版行业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政府会给予一定津贴,由此经济困难的新闻出版行业得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业又是反对党派和激进人士批判政府的重要阵地,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压制。这种状况使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工作的格拉布街文人处于一种备受打压而又不至于消亡的尴尬状态。
格拉布街文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社会转型时期的大环境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处境。17、18世纪,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大量向伦敦集中,其中便包括文学商业浪潮催生的众多文人。但是,由于市场相对狭小,购买力不足,造成伦敦的文学劳动力严重过剩,众多文人沦落于格拉布街。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写作。他们为报刊提供消息、写作文章,报刊则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报酬。在市场经济大行的今天,这种交易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作为文学商业化浪潮初期的第一代受雇文人,他们的这种生存方式与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不符,很难得到认同,因此受到排挤,成为一个亚文化边缘群体。他们承受着社会的多重打压,政府通过法令对他们进行限制,讽刺文学家对他们加以讽刺和贬低。市场的狭小又使得新闻出版产业难以盈利,导致他们时常陷入经济困境。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格拉布街文人的缺点被放大化,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受雇于党派互相攻伐、编写粗俗读物、热衷于各种花边新闻的“黑客文人”。
尽管如此,格拉布街文人的诸多缺点并不能掩盖他们的价值。他们对于17、18世纪新闻出版行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2.5 ACR影响因素分析 Pearson分析结果(表2)表明:ACR与GLU、FINS、FFA、IL-1、TNF-α、IL-6正相关(P<0.05)。以ACR为因变量,GLU、FINS、FFA、IL-1、TNF-α、IL-6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6与ACR独立正相关[OR=1.18,95%CI 1.03~1.35,P=0.014]。
18世纪前后,由于党派政治的大环境影响,很多报刊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格拉布街文人与政府之间你来我往、斗争不断,对于政府的批判更是从未停止。格拉布街的新闻出版行业从萌芽时期的小册子开始就具有反封建、反宗教的特性,并因此受到政府的压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大张力。在斗争的过程中,英国新闻出版行业不断发展,社会民主化脚步亦不断前进,格拉布街文人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比如,米斯特创办的激进政治刊物《周刊》除刊登一系列奇闻异事,还有一些敢于批评政府的激烈言辞,不仅扩大了报刊的读者群体,而且对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浸透着格拉布街文人心血的政府反对刊物《匠人》(The Craftsman ),将针对政府的批判提到一种新的高度,使得以新闻出版行业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成为各方讨论斗争的新场地,在引导民众关注政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注] 关于《周刊》和《匠人》对于政府批判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第141—151页。亦可参见Jeremy Black, The English Press ,1621-1861 , Stroud: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pp. 25-47。威尔克斯创办的《北不列颠人报》(The North Briton ),品评时政、揭露政府,在限制国王权力、捍卫议会代议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最终经过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等格拉布街文人的斗争,总逮捕令得以废除。[注] 约翰·威尔克斯是18世纪一位敢于直言的英国新闻工作者和受欢迎的伦敦政治家。其创办的《北不列颠人报》批评政府行为,掀起了捍卫议会权力、争取言论自由的“威尔克斯事件”。具体可参见Dennos Griffiths, Fleet Street :Five Hundred Years of the Press , British Library, 2006, pp. 42-44.在“朱比厄斯来信”事件中,格拉布街的报刊揭露政府腐败,带领民众争取言论自由,使得陪审团掌握了不接受政府训令而独立做出判决的权力。[注] 1768到1772年,英国著名报刊《公共广告人》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书信形式的政治评论文章,批评王室行动和议会决定,谴责政府破坏宪法。这些文章署名 “朱比厄斯”,被称为“朱比厄斯来信”。参见Dennos Griffiths, Fleet Street :Five Hundred Years of the Press , pp. 44-46。报刊业主威廉·伍德福尔(William Woodford)和凯夫、詹姆斯·佩里(James Perry)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权利。
总之,在17、 18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政治环境之中,格拉布街文人创办报纸、发行杂志,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的新闻出版行业得以不断发展。
而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品论时事,构建了一个以格拉布街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为英国民众打开了了解本国政治的窗口,建立了公众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成为英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南国社的戏剧演出力图达到自然真实的艺术效果,同时注重营造感伤浪漫的氛围,引起了青年人及上海舆论界的轰动。“南国社在戏剧上的投石虽然小,但青年间的反响却相当大。他们除了以陶醉的要求来接近我们的戏剧的以外也很有能站在一定的立场来批评我们的。”[26]115
在政府和社会的压制下,格拉布街文人恶劣的生存环境、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对于政府压制的抗争和对社会不满的宣泄,又都是社会转型中英国社会矛盾和张力的表现。这些矛盾和张力,不仅是英国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更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的社会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格拉布街文人”一词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取而代之的是“第四等级”[注] “第四等级”一词出现于18世纪。据称,最早提出第四等级观念的是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74年,在英国国会的会议中,伯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这一词语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代指报刊新闻出版业以及从事新闻出版的记者群体,是当时报刊新闻出版业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政府行为的“监察者”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的表现。 的权威。
“Grubstreet Literati” —A Perspective of a Subculture Group in Early Modern London
ZHANG Yingming,LU Weifang
Abstract: “Grubstreet literati” was a low-level literati group in London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group included employed journalists, newspaper and magazine writers, literary coolies, some publishers of humble origins, and some not-yet-famous writers. The literati of Grub Stree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ere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the employed literati. They lived on their writing with hard life, and they had low reputation and were also ridiculed by the world. The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status and mental state of Grubstreet literati are distinctively marked with the vestiges of their age, and the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press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both the constant struggles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iterati’s social critics also promoted the British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Grubstreet literati, modern Britain, subculture group, social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K5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9)03-0116-(10)
DOI: 10.13852/J.CNKI.JSHNU.2019.03.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英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洪庆明)
标签:格拉布街文人论文; 近代英国论文; 亚文化群体论文; 社会转型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