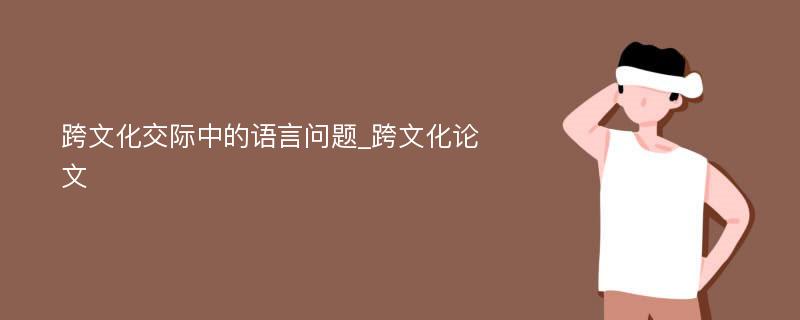
跨文化传播的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6
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必备要件是文化旅行的载体,在构建、传达话语体系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维持、复制和巩固跨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在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语言会造成人们新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因此,对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描述、理解和反思一直是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
跨文化传播中语言问题的呈现又顺应着西方语言观念的走向,即从视语言、思维和世界为同一的语言观走向将语言表征视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语言观;从对语言进行内部的静态考察以揭示其内部的深层规律,走向现实中使用话语的动态研究;从语言是反映客观世界和内心思想的透明的媒介,走向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的相互勾联。以此来研究语言与跨文化理解、语言与文化身份的建构、语言与意识形态以及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与此同时,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语言问题便突显出来。
一、语言与跨文化理解
在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就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互相理解吗?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之所以能够相对容易地进行沟通,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表征了大致相同的概念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可以定义为是“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那么,说不同语言的人在跨文化交流中情况如何呢?当他人的文化思想用不同于我们且具有不同的心理范畴的语言表达时,我们是否还能再现他者的思想?词汇量、词汇分类和语法结构迥异的语言之间是否能相互翻译?悲观者存在,乐观者也有之。
悲观者认为,语言是人与外在世界的一个中间世界,它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世界图”。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人从自身中创造了语言,但同时也成为了语言的囚徒,语言制约着人的思维路径。就是communication这个英文单词就很难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有学者将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术语挑选出来,请熟谙外语的传播学研究者用4个标准对其在相应的语言中的可译性进行评估:A表示在该语言中有与之完全相同的词汇,B表示在该语言中有与之大致相同的词汇,C表示在该语言中可以翻译,但翻译后的词汇有与英文不同的内涵,D表示在该语言中完全无法翻译。communication在以下语言中的可译度分别为:锡兰语(B)、汉语(B)、孟加拉语(C)、印尼语(B)、菲律宾语(C)、印地语(A)、日语(C)。① 由此可见,跨文化的理解是多么的困难。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语言的结构影响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语言的不同导致了世界的不同。
戴维·潘(David Pan)等人又进一步提出,跨文化叙事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跨文化叙事拥有“象征”和“审美”的性质,前者是由任意的符号所构成,后者由审美机制所构成。跨文化叙事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符号系统具有文化的特性,它构成了认知的结构,所以不同的符号系统就会导致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另一方面,跨文化叙事作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叙事的确不可能,但一种叙事却具有通过翻译,以不同的功能在多种文化之间扩散的能力。换句话说,叙事的知识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有可能丢失,但它却能保留情感意义,尽管与原叙事所承载的情感意义有所不同。一个单一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是单一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永远只能在单一的文化语境下行使其功能,获取其意义,因此跨文化叙事就成为不可能。②
乐观者则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发出尖锐的质疑之声,认为它存在着一个逻辑悖论:如果该假设是对的,那么讲不同语言的人则无法相互理解;而如果跨语言的理解不可能,讲英语的沃尔夫又怎么能够弄懂这些印第安人的语言?他又怎么能够通过英语让人们理解印第安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个理论假设?③ 由此可见,差异只是语言形式上的,讲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翻译在各领域里进行沟通和理解,说明人类的思维认知存在着共性,否则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将会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
顺此思路,西班牙学者塞尔(Joathan P.A.Sell)认为,跨文化叙事是可能的,并提出了一个隐喻模式作为解决跨文化叙事的有效工具。他将隐喻(metaphor)看成是跨文化叙事的基础。语篇和认知是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纽带就是隐喻。审美起源于惊异(wonder),而隐喻是惊异的修辞同源语(rhetorical homologue)。希腊语中的metaphor一词,翻译成拉丁文是translatio,译成英语就成为transport。因此,任何人际交流都是隐喻的,因为传受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也就是说,交流需要移情(empathy)能力。如果跨文化叙事的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者经验格式塔与第二种文化的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经验格式塔相耦合的话,跨文化叙事就有可能实现。第一种文化的情感机制或许不能通过翻译而进入到第二种文化中,但是它的符号系统却可以表征情景使第二种文化的接受者通过移情来体会情感。所以,跨文化叙事不仅能够理解他者,而且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使理解发生变化。④ 针对戴维·潘的说法,一个单一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是单一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永远只能在单一的文化语境下行使其功能,获取其意义,这样跨文化叙事就成为不可能,他把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修正:单一文化叙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成多文化叙事,因为它能旅行到另外一种语境,变成一种新的叙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然而,对语言与跨文化理解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语言形式固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人类认知共性的公分母到底有多大呢?在美国电影《通天塔》所表现的文化冲突中,人们直接使用各自的母语进行对白,加之交流的失败所带来的种种悲剧,无不暗示着某种挥之不去的心灵隔阂和跨文化交流的无奈。
二、语言与文化身份的建构
跨文化叙事必须承认的是:一个社群的界限是流动的,是能够按照个人和群体的需要、语境的需要,根据“他者”是否在场而被建构、重构、解构、想象或否认的。英国开放大学的比文(Tita Beaven)通过分析三位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人有关新生活的叙事,探讨了这些跨文化叙事对构成定居者新的社会文化身份所形成的三个重要要素:物理环境、通过定居者适应性的表象来探询他者,以及跨文化经历者所暗含的对自我的重新定义。通过故事的叙述,人们得以了解身份是如何朝异国文化以不同的速度和结果而流变的,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新身份。跨文化叙事所表征的种族景观(ethnoscape)对接受国文化和母国文化都有影响,而中介景观(mediascape)则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意想和意义生产机制,这些能使他们接触有关跨文化交往的事件,并使他们能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想象生活。⑤
洪堡特曾写道:“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而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⑥ 文化可理解成为“共享的意义和共享的概念图”,而语言则是对意义和概念图的表征,很显然,每一群体或民族的成员所说的语言都与他们的文化身份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身份,或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身份=一个民族国家。这种简单的等式也许在孤立和同质化的社会中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在现代高度流动的和异质的社会中却不可能。例如,新加坡有很多人也说汉语,但是他们认同的是新加坡文化。英语在很多国家使用,但绝不意味着这些国家都拥有同一种文化。此外,一个人还可能会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并出于展现不同的文化身份而进行语码的转化(switching of codes)。这反映了他/她的文化身份是多样的和流动的,并形成于与他人的协商之中。
语言只是界定文化身份的标准之一,其他如种族、宗教、阶级、性别、政治观点、经济地位等也从不同角度界定着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是显示文化身份最敏感的指标,因为它与人们的思维密不可分,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所以,为了维护文化的纯洁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维护语言的纯洁性。例如,法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的使用,其目的是想塑造一种超国家的文化身份——说法语者身份(francophone identity or francophonie)。并且,法国还设立了一个国家机构——法语学会(Academie Francaise)来监察作为国际化语言的法语,避免受到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的污染和侵蚀,其实质是要维护法兰西文化的纯正性。
现代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起源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刷文字来维系这个乌托邦。所以,一个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一个语言的乌托邦。当殖民地取得独立时,或一个多民族共和国(如苏联)分裂成多个国家时,民族语言就会被重新使用或重新组合,“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限相一致”。⑦
但问题接踵而至。当殖民地纷纷独立,多民族国家分裂成为多个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民族文化呈现出强劲反弹之时,作为文化身份最敏感标志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然而,由于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大量迁移、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密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但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甚至文化战争也愈演愈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所以,必须要有一种通用的语言作为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因为“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⑧ 但是在世界上众多的语言中,哪一种语言被选定为国际间的“普通话”呢?在历史上,西方的拉丁语、法语,东方的汉语,非洲的斯瓦希里语都曾在不同的区域里担当了这一角色,而在当今世界,毫无疑问是英语更多地担当了这一角色。
对于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因为语言与文化身份和民族国家之间具有象征性的联系,所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某种语言,就意味着推广该语言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这被称之为语言主义(linguicism)。菲利普森在其《语言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意识形态、结构和实践被用来使以语言为基础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和资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不平等分配合法化、有效化和再生化”。⑨ 因此,人们担心的恐怕不是英语的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而是裹挟在英语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但是,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亨廷顿认为: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或深入地考察,“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拥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⑩ 有的学者更进一步将英语教育与世界公民身份的培养联系起来。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大学的曼纽尔·吉尔赫米(Manuela Guilherme)提出,应采用批评性的教育方式来看待作为全球性语言的英语教育。(11) 将英语看作是一门普通语言,而不是一门交际语言(lingua franca),能够为我们提供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机会。这样,就不会丧失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基,也不会将英语转换成一种中立的、无所牵连的或没有隶属的媒介。作为一种威力强大的媒介,全球性的英语(EGL)为各国的教育体制并通过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来培养富有批判性和积极的世界公民。这个目的通过扩大他们的视野以及使他们意识到作为个人或作为各个不同群体(或远或近)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而达到。EGL具有的跨文化纬度是获得跨文化自由的重要因素,是成为世界公民的基础。培育跨文化自由不仅包括自由行动的能力,或包括理解各种语言的知识能力,还包括对未知恐惧(情感层面)的控制、对批判性世界观(认知层面)的倡导以及强化自我发展意识(经验层面)。
由此看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能不能重返“通天塔”的问题,而且还是要不要重返“通天塔”的问题。
三、语言与意识形态
现今有关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之间的研究大多从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那里吸取了灵感。萨丕尔和沃尔夫通过对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与英语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们是透过语言所构造的心理范畴来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语言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不同;而对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就产生了该文化特定的思维模式,语言塑造着思维。沃尔夫写道:“我们分析自然是依照母语规定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从客观世界中提取出来的范畴和类型在客观世界里之所以看不到,正是因为它们就在观察者眼皮下面。相反,客观世界如同万花筒,呈现给我们五彩纷纭的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头脑加以组织。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分解开来,组织安排成概念,赋予其意义,这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协议’,同意这样进行组织。这个协议对于所有说这种语言的人都有效,并且以这种语言的模式编纂成典。当然,这个协议是隐含而非公开的,但它的‘条款’却具有绝对的强制性。我们必须遵守协议规定的组织方法和分类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开口说话。”(12)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深刻,受到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学者的高度重视。它包含几层意思:首先,语言中隐含着认知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它是不为人所觉察的心理范畴、背景知识、认知图式等,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们很容易对那些通过具有社会属性的语言的运用而获得强化的感性知识习以为常,并将其与客观现实等同起来,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之为“现实的社会性建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再者,语言中隐含的预设信息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通过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及其编码的意义体系是如何导致意识形态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和“习惯化”(habitualization)的。人们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语言的中介来理解周遭的世界的,但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却不是个人的、任意的或偶然的。
“在一个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会有一种词汇体系或措辞发展成适合该社会需求的体系——这些需求是占支配地位的特权群体的利益要求。这些重要群体控制着把他们喜欢的意义体系合法化的手段:学校、图书馆、大众传播媒体等。这样,语言就变成了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成为维持主要社会秩序的工具。”(13) 因此,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便昭然若揭了。当人们对浸润着意识形态的语言不加质疑和审查地频繁使用时,那些带有意识形态的语句,如“恐怖主义”(terrorism)、“人权”(human rights)、“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便作为一般语言意义而悄然进入人们的潜意识了,费尔克劳称其为意识形态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正是意识形态在语言中的“合法化”和“自然化”,促使当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去关注那些人们熟视无睹、更具迷惑性的各种不平等的话语,如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偏见、歧视等。正如梵·迪克所说:“这些形式的种族主义不同于旧式的白人优越感的奴役、种族隔离、处绞刑和系统的歧视,以及在公共话语和日常谈话中的赤裸裸的贬损。新种族主义希望是民主的、可敬的并首先否认它是种族主义的。传统意义的真正的种族主义仅仅存在于极端右翼分子中。”(14)
盖特纳和多维迪称这种新型的种族主义为“下意识的种族主义”,(15) 其特征是如白人对非裔美国人不得不承受的遭遇保持同情,又觉得黑人令人厌恶或者对黑人不屑一顾。这种矛盾之情使媒介表现出微妙的种族主义,而受众却几乎觉察不出来。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研究就是群体间的语言偏见。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使用更抽象的语言描述内部成员的正面行为或者外部群体成员的负面行为;而在描述内部成员的负面行为或者外部群体成员的正面行为时,则倾向于使用更具体和更客观的语言。
下面举例说明语言从具体到抽象的三个等级:(1)约翰打了她;(2)约翰恨她;(3)约翰是好斗的。在群体间语境中,使用不同抽象度的语言可视为是对行为进行条件归因或者意向归因的标志。对某一行为使用具体语言进行描述,暗示着该行为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环境)下发生,而使用抽象语言描述则意味着某种行为的发生与那个人以及所属的群体的内在特征相关,且不容易发生变化。
戈勒姆运用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来研究白人大学生受众对电视犯罪新闻报道的反应时发现,当嫌疑人是黑人的时候,更大比例的描述是形容词的,大部分是抽象的描述词。研究结论证明,通过观看犯罪报道,这些白人学生心目中关于黑人的刻板形象已被激活,并反过来影响了他们谈论嫌疑人的方式。(16)
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显示,语言可以以一种更为迷惑性、不易被觉察的方式来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意识形态。该理论对思考跨文化媒介内容的效果、媒介如何隐性地涵化某种世界观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文化同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彼此的仇恨;(17) 充斥在博客日志引导的对“他者”的谈论,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进行“文化的排他”,和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加深着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种族的不平等系统,并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18)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依存。人们探讨交往中亲密关系的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和代际传承关系,努力为超越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障碍寻找着出路。如何应对这种矛盾,把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合性和文化差异真正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语言与权力
跨文化叙事的可能性始终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中,所谓多元化的叙事语境建立在语言流向不均衡或不平等的基础上,语言传播的流向、流量不仅是国家权力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成为全球化格局中国家权力流向、流量形成的社会基础。
毋庸置疑,美英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媒体等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使得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强势语言,英语被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际之间的转换,其流量和流向还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以英语为例,中国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书籍要远远超过美英从中文中翻译过去的书籍,英语在中国无论作为译出语还是译入语,都受到尊重。这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中,部分学者主张英汉翻译以异化(foreignisation)为主,即在英汉翻译中,译者不太考虑读者的感受,他们由于害怕不“忠实”原文,很少改动英语的结构;汉英翻译则尽量归化(domestication),即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倾向于重新组织中文的习惯表达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清楚地表明,中文和英文在中国译者和批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世界上的语言也被一些学者分为三个层次:中心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半边缘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和捷克语);边缘语言(中文、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Heilbron,1999)。(19) 另一些学者认为,应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权力,比如,英汉语之间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称的中心—边缘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是日语和汉语虽然都是边缘语言,它们之间的翻译同样也是不对称的。所以,区分强势和弱势语言,不仅要考虑语言在全世界和某个区域的地位,还要注意到互译语言之间相对实力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语言间的互译现象。(20)
由于语言符号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语境和参与者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因此其意义不再具有确定性。语言不是反映客观和主观世界透明的媒介,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为权力提供服务的,如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用来指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21) 这样,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三者间就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语言和意识形态一起帮助建构、维护和解构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语言既受权力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着权力关系。正如福柯所说,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于是,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就变成一种符号资本而成为各个群体争相控制的对象。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奠基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可以说是关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杰作。萨义德以福柯的话语观念为基础,采用西方/东方二分法的方式,将东方主义视作是西方思考、言说和表征东方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东西方力量关系的模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东方只是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与现实中的“东方”本身无关。“东方”在语言的魔镜中不断地被刻板化和妖魔化。(22)
在当今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中,处于文化强势的一方通过操纵语言来歪曲和妖魔化“他者”的现象非常普遍,但经常会遭到对方激烈的抗议。例如,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暴乱和奥运火炬在一些西方国家传递时所遭受的冲击的歪曲报道引发了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从而导致了“做人不能太CNN”这样的对抗性话语。这种外显的由于权力关系导致的话语失衡往往令人一目了然,不再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点。但是跨文化传播话语中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权力的习惯化则尤其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它们以不为人所觉察的方式掩盖了既存的权力关系,使被支配者自动地接受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结构。话语的非政治化是指在交际中,处于权力支配地位的一方为了减轻和消除对被支配一方施加影响时带来的副作用,避免对抗情绪而采取的隐藏权力支配方、间接暗示、以请求的方式发出命令、各种礼貌方式等语言策略。被支配的一方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对方的话语陷阱,从而接受对方的影响。例如,现在全世界人们津津乐道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经常以名词的形式出现,似乎指示着某种客观实在。然而,有多少人去拷问过“全球化”(globalize)的施动者是谁呢?
语言既是权力关系的反映,反之又维护了既存的权力关系。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认为,英国社会中的下层阶级所使用的语言相对于中产阶级的“精致符码”(elaborated code)来说是“限制符码”(restricted code)。他列举了两种语言符码的种种特征,认为“限制符码”使下层阶级难以进行抽象思维,阻碍了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善的要求;而“精致符码”有利于逻辑和抽象思维,满足学校、社会和政治的要求。这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颇为相似,即语言结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伯恩斯坦的理论遭人诟病多多,他自己也最终放弃。但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不同的语言形式不仅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建构了这个结构。一种语言对其他语言的特权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语言行为。一些所谓的“优越”语言在维持和传播主导文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优越”语言的推行过程中,被支配者会被不知不觉地纳入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深刻分析了英语和其他欧洲经典的语言文学是如何维护帝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平等权力的,“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批评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拉斯金(John Ruskin)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劣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23)
然而,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语言也可能为它自己所属的文化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英语的垄断地位潜在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美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悖论:美国的语言多样性和英语垄断语言主义(monolingualism)。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融合准则,拒绝承认多元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是一种国家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外语危机”。美国人对英语的霸权地位抑制了他们掌握多门语言的动力和机会表现出极大的沮丧之情。(24) 也许,通天塔之后所形成的各种不同语言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噩耗,而真正可怕的是某一种语言凌驾于其他的语言之上。
注释:
①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② David Pan,J.G.Herder,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ultural Narratives,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 (2),2004,pp.10~20.
③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④ P.A.Joathan,A,Sell,Metaphorical Basis for Transcultural Narrative: A Response to David Pan,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7 (1),2007,pp.2~15.
⑤ Tita Beaven,A Life in the Sun:Accounts of New Lives Abroad as Intercultural Narratives,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7 (3),2007,pp.188~202.
⑥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35~136页。
⑦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⑧ 同上,第49页。
⑨ 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76.
⑩ [美]塞缪尔·亨廷顿,2002年,第50页。
(11) Manuela Guilherme,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and Education for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7 (1),2007,pp.72~90.
(12) 转引自[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109~110页。
(13) 辛彬:《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4) 转引自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途径》,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7年,第190页。
(15) Bradley W. Gorham, News
Media '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6,March,2006,pp.289~308.
(16) 同上,pp.289~308。
(17) Seth J.Schwartz et al.,Nativity and Years in the Receiving Culture as Markers of Acculturation in Ethnic Enclaves,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37,2006,pp.345~353.
(18) Lena Karlsson,The Diary Weblog and the Travelling Tales of Diasporic Tourist,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Vol.27,Aug.,2006,pp.299~312.
(19) J.Heilbron,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 System,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4),1999,pp.429~444.
(20) He Xianbin,Power Relations and Transl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Vol.7 (3),2007,pp.240~252.
(21) 辛彬:《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2) 转引自[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2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4页。
(24) Chistof Demont-Heinrich,Globalization,Language,and the Tongue-Tied Americ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1 (2),April,2007,pp.98~117.
标签:跨文化论文; 跨文化传播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全球化论文; 他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