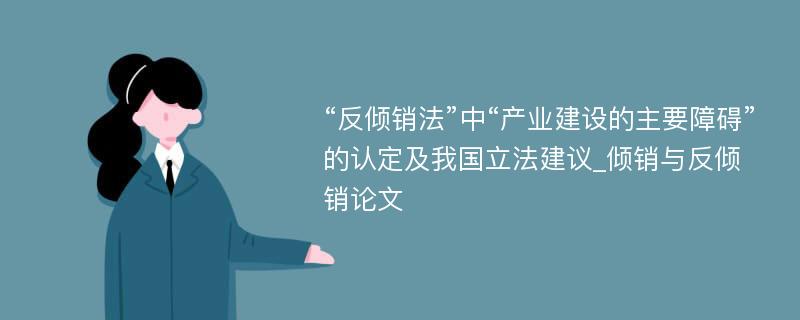
反倾销法关于“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的认定及我国立法之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议论文,我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倾销法作为维护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公平竞争的法律,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反倾销附加关税的征收,遏止外国产品以低于公平价值或正常价值的价格涌入国境的增长势头,从而达到保护本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产业的目的。此种保护不仅针对业已建立的产业,而且针对尚未建立但已采取实际步骤即将建立的产业。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的反倾销立法无不将阻碍国内新兴产业之建立作为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相同或相似产品生产产业的损害之一。
一、反倾销法中“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其运用
把阻碍相同或相似产品产业之建立作为损害的情形之一(另外两种是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之威胁),这在反倾销立法上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美国在其早年的反倾销立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尤其是国会在立法辩论中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国会认为,面对德国当时的强势出口,不但美国既存产业会遭到大量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且尚未建立的产业特别是化学工业亦可能在其初期发展阶段,就遭到德国强大的化学工业的摧残。由此,当时的反倾销法将阻碍产业的建立作为构成损害的要件之一,这一做法不但后来被延续下来,而且被引用到关贸总协定及其《反倾销守则》之中。
《关贸总协定》第6条在论述倾销及其损害时指出,“如果倾销……对某一国内产业的新建产生重大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遣责。”美国反倾销法指出,如果国内同类产业的建立受到了倾销进口产品的重大阻碍,受损害的厂商可以向美国反倾销机构提起诉讼。欧共体反倾销法指出,当某一进口产品重大阻碍某一产业的建立时,反倾销机构可以作出损害的裁定。台湾反倾销法指出,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倾销进口产品延续了其即将新建的同类产业的建立,他则可以提起反倾销诉讼。我国新颁布的对外贸易法及正在起草中的反倾销条例草案指出,如果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种阻碍。从上述一系列法律规定可以看到,即使倾销进口产品未对进口国的有关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威胁,但若阻碍了进口国生产该类产品的一个新产业的建立,进口国也可以对其征收反倾销税。
虽然反倾销法中阻碍产业建立的规定已有较长的历史,但这一规则很少被实际援用。在美国,直到1974年才有人在反倾销案件的审理中首次提出希望适用“建立阻碍产业”规则,但这一提议当时并没有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采纳〔1〕。迄今为止,就美国而言,仅在1982年和1985年的两个反倾销案件审理中,国际贸易委员会适用了“建立阻碍产业”之规则,并作出了肯定性裁决〔2〕。
二、认定“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的构成要件
1.受阻产业须为尚未建立之产业
一个产业倘若已经建立起来,则倾销进口产品对该产业的冲击就只能是实际的损害或潜在的损害,因而谈不上阻碍该产业的建立。只有尚未建立的产业,才会受到阻碍。这也正是“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要件在反倾销法中与重大损害及重大损害之威胁这两个损害要件并存的原因。这一点似乎毋须多说,但在实践中如何判定某一类厂商究竟是属于已建立之产业还是属于未建立之产业却殊非易事。例如,在某一反倾销案诉讼中,原告为一家已经注册设立之厂商,该厂商在生产某产品约达2年之后,因无法盈利而难以为继,最后清盘结业。反倾销主管机构认为,在其营运的2年中,原告无法稳定其生产以达到维持合理的损益平衡点之规模,从而使该产业不能变成持续建立的产业,因此,反倾销主管机关得出结论:一个已经实际上存在的厂商,纵使其实际上已经开始生产,仍不一定能被视为一个已经建立之产业〔3〕。可见,在实践中区分一个产业是否属于未建立产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必须区分,因为倘若属于已建立之产业,则只能适用“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之威胁”标准来进行损害测试;只有对未建立之产业,才适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标准来进行损害测试。两种测试在标准方法上各不相同。
2.受阻产业须是投资人已采取实际步骤正在建立或将要建立之产业
由于受科技水平、工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制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不可能集所有产业之大成,而只能建立其各方面条件允许、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建立的产业。也就是说,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总有一些产业是尚未建立的或无法建立的。反倾销法并不笼统地保护所有该国未建立的产业,它所保护的只是也只能是那些国内投资人已经有明晰可行的投资意愿、设想或计划,并已采取实际行动正在建立之中的或准备建立的产业。实际上,倘若国内投资人还没有产生建立某一新兴产业之意图,或者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建立某一产业(比如气候寒冷干燥的内陆国要建立鳄鱼养殖和鳄鱼皮革制造的产业),则也就不会有人会以产业建立受阻为由寻求反倾销法的保护了。
由此可见,从反倾销法中引进“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损害测试机制的内在要求和反倾销调查机器一般以产业界投诉来启动这一机制来看,应受到阻碍而受反倾销法保护的只能是投资人不仅已经有明确的投资意愿计划,而且已采取了可行的步骤去建立或准备建立的产业。为防止在产业建立中投资人凭借反倾销法的规定,去保护一个后来并没有被建立的产业,反倾销机构一般以投诉人就其将来产业之开始生产,是否已作成“实质性承诺”这一标准去衡量。这种“实质性承诺”标准是使那些有意念或期望去设立某产业,而未采取实际步骤以建立产业的申请人,无法获得反倾销措施的救济〔4〕。
3.尚未建立之新产业的实际建立过程须受到了阻碍
“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概念,其主要的核心词为“阻碍”,它意味着投资人已经有明确可行的计划,并采取实际步骤建立新产业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一般说来,声称新的产业不能建立必须具有充分的证据,不能将“阻碍产业建立”理解为是倾销的产品阻碍了建立一个新产业的设想或计划,而应该是一个新产业的实际建立过程受阻。例如工厂已经建立,设备已经测量,然而由于大量倾销产品的涌人或价格下跌,使进口国的新产业无法开工投产。因此,进口国就可以以倾销进口产品阻碍产业为由征收反倾销税。
4.此种对产业的阻碍须是重大的阻碍
要获得反倾销法的救济,投诉人须证明其意欲投资,且已采取实质步骤准备或正在建立的产业所受到进口倾销产品的阻碍是重大的阻碍,而不是一般的轻微的阻碍。
应该指出的是,欧、美等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法以及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法在谈到损害的三种形态(即实际损害、损害之威胁、阻碍产业建立)时均用了同一个修饰词,即mate-rial(ly)。
对该词作出恰如其分的中文翻译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大部分专门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倾向于将material译成“严重”,因为字典里就是如此译的;而大部分法律研究者则喜欢将material(ly)译成“实质性的(地)”。
其实上述两种译法均会遇到麻烦,因为英文中尚有“Serious”和“substantial”两词,而且原关贸总协定的第19条中就有“seriousinjury”的表述,若将“material(ly)”译成“严重损害”,则“Serious injury”又当何译呢?因此译成“严重”显然是不妥的。
那么,将“material(ly)”译成“实质性的(地)”是否妥当呢?也不妥,因为“实质性的”一词的英文的正确表述应为“substantial”,换言之,“substantial injury”才能译成“实质性损害”。那么为什么许多法学研究者将“materialinjury”译成“实质性损害”呢?这恐怕与原关贸总协定专家小组的解释有关,因为专家小组认为“material injury”应与“substantial in-jury”同义。然而在事实上,专家小组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而受到了不少非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委员会就明确指责,认为这种解释对“损害”的成立或认定附加了颇为苛刻的条件〔5〕。由此看来,“实质性”的译法也有争议,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对于“material”的中文译法,早有现成的译法可供借鉴,只是这种译法始于会计业,会计原理中有一条原则叫重大性原则,其英文为“principle of materiality”。其中“materiality”是“material”(重大)的名词形态,故将“material”译成重大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对反倾销法所界定的三种损害形态中均涉及的“重大”(material)一词的含义,法学家们的解释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反倾销法中所谓的“重大损害”比原关贸总协定19条所指的“严重损害”的损害程度要轻〔6〕,同时总也比法国法律中所规定的重要损害(important injury)要轻〔7〕。如果作进一步的比较,就可以发现material在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中的标准比美国法院在使用这一词的时候的标准要松一些、低一些。
既然对“重大”一词的含义无法作出正面的界定,那么就只有从反面来加以理解。美国学者因而提出了三个“不是”来界定损害的重大性,即“不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微不足道的;不是细微的”的损害才能算是重大损害〔8〕。
美国学者的关于“重大”的上述界定,不仅适用于实际损害,也适用于阻碍产业建立的损害,此种界定也许不一定尽善尽美,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比上述界定更加合理的解释。
三、判例确立的规则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1985年在审理加拿大鱼类产品倾销案中,就“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规则之适用提出了以下三项标准:
1.可以适用“产业建立阻碍”的情形,并不限于尚未开始生产的产业,还包括虽有新的设备,而且开始生产,但其经营尚未稳定的产业。
2.由于每一种建立新产业的努力都有其特殊性,因而在决定某一产业的建立是否被阻碍时,应逐案个别决定。
3.如果某一产业尚未开始生产,则其必须有充分资料显示该产业已经作成开始生产的实质承诺。
上述解释表明,如果建立产业的困难,只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进入本来就竞争激烈或极不易进人的市场所面临的状况,这不应视为“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但若其实际的营运,比合理的预期更为不利,则属于“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
四、发达国家较少援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要件来认定损害的原因
目前反倾销法领域法制较为完备,法律较为严密的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然而发达国家很少在反倾销实践中运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标准来判断损害的有无,从而决定应否征收反倾销税。如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只有2个反倾销案件的审理中,国际贸易委员会适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的规则,并作出了肯定性裁决。而欧共体、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反倾销法时,也很少援用过“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标准。
那么,发达国家较少援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要件来认定损害存在的原因何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发达国家之所以称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它们科学技术先进,绝大部分产业已经建立,门类比较齐全,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但发达国家却尚未建立起某一产业的情况,尤其是当产业涉及到科技水平的时候,即使有上述情形发生,那也是极个别的。
正因为发达国家大部分产业是已经建立的产业,因而也就谈不上阻碍其发展了。因而在反倾销实践中也就很少援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标准了。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但发达国家反而没有建立的产业往往是在某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特殊的资源禀赋或民族文化所致,所以可以预测在援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这一标准的案件大多是具有民族历史传统的手工艺或类似产业。比如景泰兰制造业,本来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但自从日本“借鉴”了该技术后,日本可能建立类似的产业,为了保护这样的产业的正当建立,就有可能采用“产业建立之重大阻碍”来对中国的便宜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当然上述情形仅仅是虚拟的,但很能说明问题。
五、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一点建议
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立法中,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是参照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的原则;第二是符合我国国情原则。也就是说,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时要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要同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条约相衔接,这样才能推动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妥善处理我国与各国间贸易关系,达到贸易利益的平衡。
目前我国已完成的《反倾销条例》草案较好地贯彻了上述两条原则,因为它是在多次开会征集国内各部门意见并在多次出国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但也并非完美无缺,主要体现就是前一个原则参照国际惯例的原则照顾得多了一些,但对国情的照顾较少一些。
具体而言: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故有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但我国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中的产业,因此对已经建立产业的保护固属重要,但对未建立产业的保护更为必要。因此,新颁布反倾销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一定要体现这一国情。所以建议在条例或其施行细则中增加“阻碍产业之重大阻碍”这种损害评估的具体标准(本文第二部分的四个要件),使之更具操作性。
注释:
〔1〕Inv.No.AA 1921~140.ITC Pub,676(May,1924).
〔2〕Inv.No.75~TA~5,USITC Pub,1234(March,1982).Inv.No.731-TA-199(Final),USITC Pub,1711(July, 1985).
〔3〕N.David palmeter:Injury Determinations i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Cases-A Commentaryon U.S Practice,21 Jounal World Trade Law No.130(1987).
〔4〕Jeannett Sheet Glass Corp.V.United States,607.F.Supp.121,131-32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1985).
〔5〕J.F.Beseler:EEC Protection Against Dumping andSubsidies from Third Country,6 Common Market Law.Pev.336(1968).
〔6〕范健蓍:《反倾销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 109页。
〔7〕J.F.Beseler and A.W.Willians:Anti-Dumpingand Anti-Subsidy Law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60,1986).
〔8〕盛建明:《反倾销国际惯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