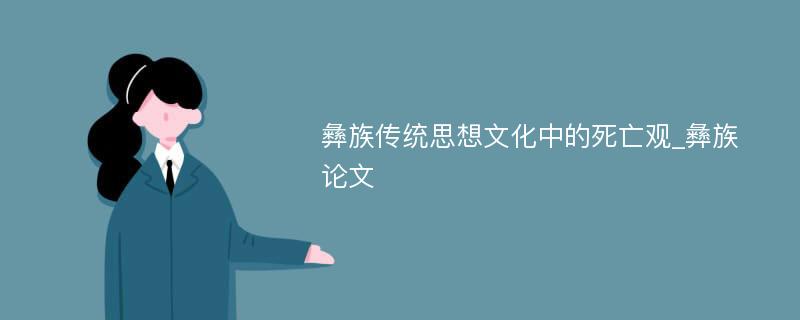
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彝族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3-0035-04
死亡问题是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总有一死,如何看待死,如何面对死,这是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多方位、多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系中,生命的价值只是一个方面。在紧要关头,要人们做出生与死的决择。所以,死亡问题是人生因而也是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人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民族,关于生死的思想文化也各不相同。彝族的死亡观念具有特殊的个性,这表现在他的宗教、哲学和民俗文化中。
一、神话:不死的烦恼
生命是人的存在的首要问题,也是人的价值的首要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死亡是人生和人生价值的否定。可是问题是否总是这样呢?对此能否说不?即肯定死的地位及其价值。从价值阶梯论的立场出发,不少崇高、浪漫的诗篇肯定过死亡的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都是从人的多种价值追求与存在来肯定人的死亡的相对价值。这种肯定,是大多数民族所共有的,因而也存在于彝族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中。但在彝族的神话宗教思想观念中,还有肯定生命与死亡的统一性,就人的生命肯定人的死亡的价值的思想。
彝族有一个《爱慕死亡作祭》的神话故事。相传古人长生不老,到了老年便感到烦恼。一日,人们从远山抬回一只死虎设灵作祭,羡慕死亡的可贵。后来人们又抬回死猴、死鸟一而再,再而三设灵作祭,格兹天神派遣使者三勘人们作祭。使者回来报告:“世间人心烦恼”,在用鸟兽尸体“作祭”。格兹听了大怒,以为人类太不识趣,竟会恶生好死。传旨让人死,于是从此人就有死。[1](P276-277)
彝族毕教作祭经中也记载着类似的神话,叫《舍妁祭猴灵》。舍妁以死猴当人灵作祭,格兹派使者三勘祭场。格兹听了报告说:“舍妁向往死,舍妁恋作祭……舍妁行不端,戏尝死亡境。”于是播下死亡种,舍妁支后裔从此遭死种有死。毕教经中把这个故事界定为讲“安乐死”的“死亡之道”。这一神话蕴含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含义。它认为老而有死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追求,已达到了生而有老、老而有死的客观必然与主观自觉认识的统一。把老而不死看作是人的痛苦与烦恼之源,把人老而有死与“安乐死”的“死亡之道”联结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思想。人老而不死,病而不死,并过分地延长这一过程,或无限地延长这一过程,不仅不能给个体和群体带来什么意义,相反还会给个体和群体带来一种痛苦。
彝族还有一个关于《人类和石头的战争》的生死神话。相传远古天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当时人和石头都有自由的生命,且长生不死。结果人和石头无限繁衍和活动,发生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弄得两败俱伤。大地荒凉起来,人和石头的战争依然不停息,且越打越烈。格兹天神出来调解。人有智慧,讲出一番道理,石头无智慧讲不出道理。于是,格兹让石头不再有生命,不能再繁殖,而让人有生命,能繁殖但有死,从此人就不能长生不老了。[3]
这个神话故事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人类如无限繁衍又不死,就会出现生存空间的危机,人与自然的生存空间也会出现问题,因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必须与个体的生命的有限性为前提。个人不应追求不死。彝族“尔比”有这样的话:“鸟类若不死,林中容不下。人类若不死,世上纳不下。”[4]这里包含有很深的生态意识。巴霍芬说过:“如果生应是不断的创造,那末,只有当陈旧的东西死亡为此提供场所,生才能把新的东西带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能生气勃勃。从而生成与消亡是相互关联着的。”[5]
二、斋祭场歌舞:否定死亡的痛苦
《礼记·坛弓》有这样的话:“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认为已死因而按死亡去处理,是不仁,已经死亡但还按生者去对待,是不智,因而都不可为。这个用感情和理智处理都两难的问题,《论语·八佾》中提出了一个办法:“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说:“丧致乎哀而止。”主张在丧事中坚持哀戚的原则。生离死别总关情,丧事中“致乎哀”是人之常情,也是世界性处理丧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哀戚就意味着生死离别的痛苦,意味着对于死亡的难于接受。哀戚之情一旦把他看做一种原则,并用丧礼的形式确定下来,哀戚本身就会被强化,变成对死亡的一种抗拒、抗争。不可抗拒的自然会给抗拒一种更强烈的反弹,加深对死亡的痛苦,从而带来人们对死亡的惧怕。
彝族在丧事处理中,从作祭到做斋,有哀戚也有欢笑,斋祭场也是歌舞场,能节哀而致乎乐。彝族的这种传统,历史相当悠久,据《汉唐地理书钞·永昌郡传》记载:“建宁郡葬彝,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火正上,则杀牛羊共相贺作乐;若遇风气旁邪,亦乃悲哭。”《续云南通志·南蛮志·罗罗条》说:“丧以火……祭祀则捣牲畜心肝竹抄,绕尸旁歌舞,孝子受贺,孝妇衣彩。”魏大鸣、古振今叙述彝族丧葬说:“富者丧礼名曰‘做白’,是日亲眷必至,以赛马,说人命,大哭为吊,惟赛马必赌银,大哭必不下泪,否则非顶天立地之好汉。”[6]
丧葬“相贺作乐”或“亦乃悲哭”,虽“大哭为吊”,但“大哭必不下泪,否则非顶天立地好汉。”有悲哭,但以欢乐为主。还有“亲眷必至”,家族亲戚共聚一堂,杀牛宰羊,歌舞、赛马、赌银,孝子受贺,孝妇衣彩,的确不乏喜庆气氛。
此外,斋祭场还有刀舞迎宾、对歌赛歌、赛诗、耍狮、耍龙跳把式,逗趣嬉戏“闹丧”、醉舞“闹酒”等等活动和程序。吊祭者或围火谈笑,开怀畅饮,或跳脚达旦。毕教经文说:“祭场同集会,烟火一夜暖。”[1](P281)“活人拿冬青,死人笑吟吟。”[7]谚语说:“爷爷死了,孙子过年。”马学良先生说:宾主入祭献场,“炮声乐声喧嚷全场,如同赶山会般热闹。”[1](P282)
关于丧葬斋祭场歌舞欢宴,《俚颇古歌·跳丧》有这样一段唱词:“亡魂要走了,舅家和村里人来跳丧,让亡魂欢欢喜喜到阴间……他们一夜跳到天亮,劳累辛苦,他们为亡者操劳,为主家辛苦,让他们跳的欢乐,让他们把恶鬼驱散,让亡者顺利到阴间。”[8]认为歌舞欢乐是要让亡者欢欢喜喜,让生者欢乐。
彝族丧葬斋祭场的歌舞及欢乐的礼仪和习俗说明,彝族传统思想文化并非把死亡看作完全的不幸。死亡和处理死亡是有值得庆贺的某种理由的。死给生者的并不完全是痛苦,其中应有愉快与欢乐。陶学良先生说:彝族的这一丧葬仪式“是彝家视死如归的人生观的体现,故把丧事当喜事办。”[9]这是深得彝族丧祭场礼仪的文化底蕴的。
三、活送灵:笑谈死亡事
处理死亡的问题叫办后事,通常都是人死后才办理的,否则就会被视为咒人死,希望人早死。而彝族却有一种超前处理死亡问题的礼仪。这是一种特别的礼仪,也是一种习惯的和传统的行为,叫活送灵,又叫活超度。即为健在老人做斋超度送灵,使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与祖先汇合,过平安幸福的生活。
活送灵的礼仪,据肖建华先生的解释,主要居于如下两方面的认识:“其一是彝民认为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老人过于长寿反而会给子孙带来不利,亦即人丁不兴旺,因之提前履行超度仪式。其二是为活人超度说明子孙富裕、有势力。”[4](P202)已经为其做过活送灵的老人,照常在家生活,只是禁忌性生活及忌讳某些食物。最后死亡时只需做简单的丧葬事务就可以了。
彝族有一个长寿之冠约特斯理的故事。传说约特斯理为氏族首领,体魄健壮。活到120岁时,儿子对他说:“你现在超出了人生之龄,古话说七十不语,你已多活了五十,我们先给你超度送灵后,背您到岩洞住。”约特斯理感到年迈闲坐无聊,高兴答应这样做,儿子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活送灵仪式,约特斯理十分快慰,赞扬儿子道:“好儿女为父如此才值得。”仪式完毕后,儿子用精制的背兜把父亲和“父灵”一并送到灵山岩洞。待一切安置妥贴,含泪转身返家时,父亲对儿子说:“把背兜带回去,万一你能有我的年岁,可免一些孙儿们的破费。”儿子为父亲替儿孙们着想所感动,又强行把父亲背回家中,约特斯理老人在众多儿孙们的无微不至的赡养下,又活了120年。[10]这个故事说明,在彝族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中,包含着老人不可让其活进灵山岩洞,只能好好赡养,但是可以为他们超度活送灵。活送灵不折寿,还会长寿,活送灵是好儿子为父亲该做的事,也是老人和孩子都高兴的事。
活超度送灵和斋祭歌舞一样,体现坦然面对生死的思想文化观念。这种把死亡与痛苦分开的文化意识,实际上是对生死因而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深深的了悟。实际上,只有了悟生死的人,才能悠然幸福地生活。只有不忌讳死的事,不怕生命的终结死亡,才能活得更快乐、更有价值。
四、神学与哲学:升天会祖和有生必有死
死亡的问题是宗教和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各族关于死亡思想文化的深层问题或最高问题,是哲学和宗教的死亡观。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其核心和思想基础也是宗教与哲学的死亡观。
彝族的宗教称为“毕教”或“毕摩教”。毕是彝族宗教礼仪法事和道场的统称,毕摩指彝族宗教神职人员大法师或首席祭师,亦是彝族宗教神职人员“毕摩”、“毕兹”(二法师)、“毕惹”(众小法师)的统称。毕教讲“人生三次幼”、“人生三次孤”。幼、孤指无知、力薄。三次指幼年、成年、老死三个时期。认为人生三个不同的时期,需要有相应的教育和关怀帮助。毕教经说:“人生在世上,一生学三次。小时所知事,都是父母教,青年所知事,全靠伙伴教,老来还得学,恒荣呗来教。”[11](P110)老即老死,恒荣呗即造诣高深的毕摩,所以经书上又说:“死后归阴间,毕摩来指路。”[11](P100)毕教的教义及其斋祭法事,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教导死者升天会祖。
毕教认为,人生到死,并不是最终消失。人有躯体和灵魂,人死是灵魂离开了躯体。人的先祖死后灵魂升天成仙,在天上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后世的人死后由儿孙请毕摩替他们作祭作斋,就可以顺利到达祖先住地,与祖先一道过平安幸福的生活。如果不为死者作祭作斋,死者就不能升天会祖,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不仅会让死者痛苦,而且会缠着生者,叫生者痛苦。所以,彝族很重视为死者作祭作斋。彝族谚语说:“父欠儿子债,为儿子娶媳妇,儿子欠父债,为父亲作斋超度。”又说:“汉人有钱买地盖房,彝人有钱作斋超度。”人生的两大债,也就是解决人生的两件大事:一是生,二是死。
毕教解决死的事,一是作祭,由毕摩教导死者由生路走向死路。通过教路安灵,教死者不要恋生,不要留恋尘世,阴间和阳间完全一样,或更好。还要为他们清除世间所受的或所有的邪恶灾害,消除创伤,让死者的灵魂安宁,并指明死者如何走向死路,愉快升天会祖。二是作斋,教导并帮助死者由死路走向天堂成仙,与祖为伍。
毕教关于死和处理死亡的思想,是彝族对待死亡及处理死者的基本思想。这一观念,把死亡与灵魂不灭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人的追求划分为生的追求与死的追求。生的追求很现实,经验上给人的不满和痛苦都很多,死的追求只是信仰中的幻想,但给人幸福平安的安慰。这样毕教的最后和大多数宗教一样,使人在痛苦面前自然会产生“不望今生望来生”或“不望生时望死后”的思想,宗教上关于死的安慰,本来是人惧死的表现及其结果。但这种宗教认识可导致人们不怕死,可以坦然接受死亡。当然,这是消极的,它只是惧死者的鸦片。
生死问题在彝族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中,从本体论到辩证法都肯定人有生死。毕教的经文说:“人人都有生和死,世上没有不死的人”。[12]彝族《尔比》说:“人虽不想老,时光留不住,人老后要死,乃自然规律”。[4](P397)这就是说,人的死是一个客观、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生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个辩证的过程。彝族的这一哲学思想也是教人们按自然规律对待死亡,不去追求不死亡。与其宗教思想比,这是一个智慧的指导。
五、价值选择:遇战斗视死如归与怕羞不怕死
知生之宝贵,又知人终有一死,不怕死,能坦然面对死,才能活得更好。陈荣基在给“充满了生的智慧”的《生死之歌》一书写序说:“真的,能好好面对死的人,更能了解生的意义,更能把握当下的生。”[13]只有视死如归,才敢于冒险,勇于奉献和牺牲,无所畏惧地去进取,为理想和信念而斗争。
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与价值观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不怕死,但知生命的宝贵;另一方面,认为生命宝贵,但更注重生命的社会价值,不怕死、不怕苦。彝族《尔比》说:“老人不怕死,见石头滚来也避让;勇士不怕死,作战还要障碍物。”[4](P396)又说:“作战之日莫想活,想活不勇敢,劳动之日莫想死,想死没力气。”[4](P174)认为要根据社会活动的情况来作生死价值判断,这是充满了辩证法的积极的思想。作战不怕死的观念,是彝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特征之一,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民间故事中也有传说。
《新唐书》上说:“爨蛮……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14]《宋史》上说:“叙州三路蛮……俗椎髻、披毡、佩刀……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15]《云南志略》说:罗罗“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16]彝族支系花腰彝二月祭龙,相传是为了纪念阿罗,阿罗是为民除害而牺牲的。阿罗死时唱道:“为花腰彝的幸福,愉快地去死。”
彝族有句谚语“彝人怕羞不怕死”。这是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生死观与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史书缺少这方面的案例记载和评判,但这确乎是彝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物。以往的民族调查中,有的已涉及这方面的描述,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怕羞,是知耻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态度。怕羞知耻是人类的首要特征。他不仅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为人类提供了调控人的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怕羞耻作为人们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它看作是一个比人的生物自然生命更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积极价值,如果形而上学地看,其局限性或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彝族传统文化中,有辩证的理解,也有形而上学的理解,这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不怕死的价值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只有在需要坦然对待自然死亡和为更高的利益而牺牲时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无条件讲不怕死,看轻人的生命,就否认了人权,否认了刑罚的威慑和调控。又如在苦与死上讲不怕死,就有可能否认不怕苦。在羞与死上过分怕羞不怕死,就会因小羞小耻而轻生。总之,就会影响人们努力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的发挥。最后,如果怕苦不怕死,怕穷不怕死,那不怕死也就是到了它的反面,成了消极有害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