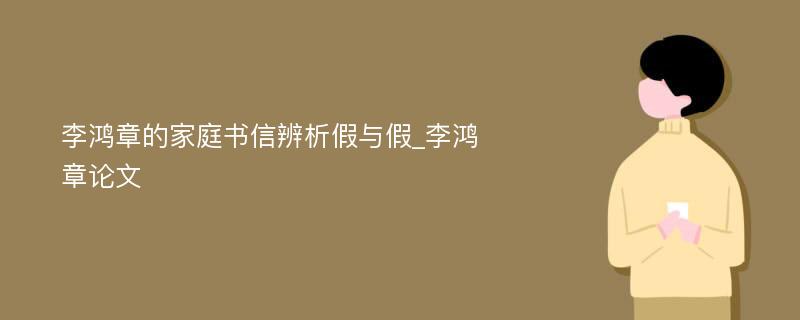
李鸿章家书辨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书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四名人家书》系广益书局于1936年排印出版,近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将该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其中有李鸿章家书90通。旧时坊间曾将其印制成单行本,名为《李鸿章尺牍》。
笔者初读这90通李鸿章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发现错误甚多,后经仔细考辨,可以认定全是赝品,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出版的一些研究李鸿章的著述,多有引用此种“家书”的情况。为免以讹传讹,笔者深感有进行辨伪的必要。
一、关于给父母和姑母的家书
《家书》的致信对象可分为给父母姑母等亲长、给兄弟和给子侄等三类。第一类计29通,其中给母亲的有26通,另外3通是分别给父、 父母和姑母的。
(一)《禀父》、《禀父母》、《禀姑母》三函
这3通函件都很短,但至少有以下作伪的痕迹。
1.父死前未曾有“接篆”之事
《家书》第1函《禀父母》写道:“接诵手谕, 命儿为官清正……敢不遵命。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彼等有愿以巨金为儿寿。儿弗论财物,却而璧之。”此段文字曾被人引为李早年为官清廉的例证,实际上它与李鸿章无关。李1847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2月他告别做京官的父亲, 随侍郎吕贤基回皖办团练,先入署皖抚周廷爵幕,堵击捻军,又先后随吕贤基、皖抚李清瑞及其继任江忠源、福济等在合肥、巢县、含山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在此期间,李鸿章一直是在籍翰林院编修的身份。1855 年2月,因率团练攻占含山,李得赏知府衔。同年7月6日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死于合肥军次,当时李仍无实际官职。及至1857年10月福济命他丁忧服阕后回京供职,李鸿章因而“茫无指归”,当时他也只是有记名道员等虚衔,因此很不得意。后来他记述当时情景:“余亦展转兵间,无所就,久乃谋引去。”〔1〕可见, 李鸿章在父亲去世之前并未有“接篆”之荣,因而也不会有“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的事情。此函之伪当可断定。
2.《经史百家杂钞》选编于李父死后
《家书》第9 函《禀父》写道:“曾夫子近编《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今由儿校正。一俟工竣,当付版制印。”此信之伪,亦很明显。关于曾国藩所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无论是光绪二年(1876年)传忠书局的刻本,还是近年岳麓书社的排印本,均未明示该书何时选编。但据黎庶昌所记,它的选录是在曾国藩“出都以后,治官临军”的一段时期〔2〕。旧时印本确曾有“李鸿章校”字样。 而李鸿章入曾国藩营为1859年1月2日〔3〕,其时距他父亲去世已三年多。这样, 李若“校正”曾编《杂钞》,也肯定在其父死后若干年。此函竟说“今由儿校正”,实属荒谬。
3.王念孙已死多年不能招收弟子
第4函《禀姑母》字数不多,但杜撰得更加荒谬。 如它写道:“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 ”信中所说的王怀祖, 即王念孙,他的生卒年代为1744—1832年。而曾国藩1838年中进士后在北京做官,至1852年因充江乡试正考官驰驿出都, 旋丁母忧, 结束京官生涯。 李鸿章“受业曾门”是1845年〔4〕。这些都是王念孙死去多年以后的事。 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尊崇,曾说过:“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5〕。他作京官时岂能不知王已死去多年,而李鸿章也是湛学之士, 且又师事曾氏,他也不会闹出要表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问业弟子”的大笑话。
(二)《禀母》函虚构应顺天乡试三事
《家书》中《禀母》和《禀母亲》类的函件中谈及去北京应举的有四通。实际上,李鸿章1843年去北京后是与父母同住,无需给母亲写信。由此即可断定其伪,另外还可从以下几事中看出作伪的痕迹。
1.“一入都门已到家”,无需另住
第21函《禀母》写道:“拜别赴京……已于本月十二日安抵圣都。当夜寓安徽会馆,翌晨即移居狮子胡同九号马文虎家。”此信常被论者所征引。据记载,李鸿章于1843年在庐州府学得优贡〔6〕。 李文安时在京任刑部郎中,闻讯后写信催他入都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顺天乡试。李文安1838年中进士后就任京官,1840年冬写有“三载长安居”的诗句。1845年仲春又写有题为《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的诗〔7〕。 他在京寓的书室取名为“省心阁”〔8〕。李鸿章的母亲当时也住在京寓。 李文安1848年春所写怀念大儿子瀚章(又名章锐)的《怀锐儿》诗中有“祖昔爱尔顺,早代父晨昏。尔母去长安,弟妹往返频”等诗句〔9〕, 表明李鸿章的父母是同住北京的。李鸿章在所撰《诰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中也说:“初,先侍御公与吾母留京邸”〔10〕。另外,李鸿章在1843年所写《入都诗》中写有“桑乾河上白云横,惟祝双亲旅舍平”、“一入都门已到家”和“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等诗句〔11〕。因为父母均旅寓京师,自感到京后又会增加父母负担,所以有“祝双亲”、“已到家”和“累高堂”之句。因此,李鸿章入都是“到家”,不会他住,也无需给母亲写信。所谓夜寓会馆、翌晨移居以及马文虎其人,都是虚构的。
2.初次抵京是凉秋而不是盛夏
第22函《禀母》写道:“六月十五日抵京后所发家书不知收到否?前日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慕曾涤笙〔12〕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此信也常为论者所征引。事实是,阴历六月十五日时值盛夏,而李鸿章的《入都诗》中有“帆影波浪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的诗句〔13〕,表明他到京时是霜华满地的凉秋。另外,前已言及,李鸿章受业曾门是1845年, 而他中举是1844年〔14〕,即是说他是在中举后才拜曾国藩为师的。此信却说1843年入都后组织文社,因诗文受知于曾因而“师事之”,这显然是杜撰的。
3.旧时举人不分甲第
第24函和25函《禀母》写道:“跪诵八月十九日在省所发手谕……北闱秋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放榜之日,男列二甲第十三名,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这里首先暴露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旧时科举制度规定进士有“三甲”之分,而举人仅列名次,不分“甲”第。1844年,李鸿章中顺天恩科乡试第84名举人〔15〕,此函记为“二甲第十三名”,不仅名次不对,而且不合制度。有的论者只着眼于“二甲”,便误以为此函可以说明李鸿章中进士“二甲第十三名”。这不仅审意有误,而且与史实不符。据记载,李鸿章1847年丁未科会试是二甲第三十六名〔16〕。可见此函所记李鸿章中乡试名次以及曾门之“盛”全部是编造的。
(三)《禀母》函谈及参加会试情况有误
《禀母》函件中谈及参加会试情况的有4通,其中破绽如下:
1.没有再次入都的痕迹
1844年李鸿章在北京中举后,1845年参加乙巳恩科会试未中。不久,祖父去世,他随父母回乡奔丧。李文安在他的诗序中有“丙午人日,奉讳里居”〔17〕的记载。为准备参加丁未科会试,李鸿章于1846年秋再去北京。他所写的《山东旅舍题壁丙午》中有“黄河东抱乱山流,迢递征途又暮秋”的诗句〔18〕,表明他是1846年深秋再次入都的。但第28、29、31、32等4通《禀母》函谈及准备和参加会试情况, 其行文语气都是立足于李鸿章中举后一直留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直至及第,而没有流露任何初次参加会试未中后曾经回乡和1846年秋再次入都的痕迹。因而可以推知这些信件是杜撰的。
2.“文儿”等是虚构的
第29函《禀母》写道:“……季弟自二月十六日寄男一信后,信息杳然。男知其不得意,屡次作书相慰,不得一报……益妹能时时归宁否?遥想英甥、文儿,此刻牵衣相问,泥人竹马,渐知顽笑矣。”此信破绽也明显。季弟是指最小的兄弟,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弟昭庆,1835年生,1846年秋,他才十一岁,还不可能成为失意士子。另外,李鸿章有两妹,但都不名“益”。长妹1828年生。二妹最年幼,比六弟昭庆小,当为1836年后出生,其时还不足十岁。假定“益妹”即长妹,其时只十八岁,即使已嫁,所生的孩子也很难说已到“牵衣相问”、会骑“竹马”的年龄。据记载,李鸿章长妹后嫁同县张绍棠为妻,她的儿女中没有名“英”者〔19〕。而李鸿章也没有一个名“文”的儿子。事实是,他与夫人周氏婚后一直无子。 1861 年9 月周夫人死时才以六弟昭庆之子经方(1855年生)承嗣。后来,继室赵夫人生子经述等则是在1864年以后。显然,这里的“文儿”、“英甥”都是虚构的。
3.会试“挂榜”何来“二院编修”
第31函《禀母》报告已参加“春闱”应试。第32函《禀母》则报喜道:“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现已入院视事。”有的论者因李鸿章曾任翰林院编修对此信征引不疑。实际上,清代科举会试在发榜时只公布一、二、三甲名次,再经过朝考,然后引见分发官职,成绩优异者分入翰林院,统称庶吉士,三年散馆后才分授修撰、编修和检讨等职。因此,绝不会有新科进士在发榜当时已经名列“编修”的事情。据记载,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为二甲第三十六名,位列李位三和黄彭年之间〔20〕;同年6月15日引见,改为翰林院庶吉士〔21〕;1850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22〕。显然,《家书》炮制者缺乏科举制常识,把李做“编修”的时间提前了三年。
(四)《禀母》函7通谈及与太平军作战漏洞百出
1.史实错乱,“署”“授”混淆
第37函《禀母》写道:“前贼犯上海,上海官绅立会防局……至是贼犯吴淞口,又盘踞浦东高桥镇……旋华尔阵亡,白齐文索饷不遂,投贼军,于是以戈登代领常胜军。二月,曾夫子遣男赴上海……皇恩浩荡,授男江苏巡抚……遂于十二日拜表谢恩,受职视事。而别授薛焕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宜。”早在抗战前夕,“上海通社”社员撰写《近代名人在上海·李鸿章》时,此信被全文征引〔23〕。家信不厌其说地历述两年间的军政要事有悖常情,而且叙事时序颠倒,因果错乱。事实上,白齐文索饷是1863年1月,索饷不成被免职, 洋枪队统领由奥伦暂代,3月25日由戈登正式充任〔24〕。8月初,白齐文投奔太平军。此函把白齐文投奔太平军说成是戈登接任的原因,显然是颠倒因果。再者,李鸿章抵达上海是1862年4月8日,而上述事件以及华尔于1862年9 月在慈溪战死,都是李抵沪一年多后发生的。此函将上述各事作为李到上海的背景或前提,显然不合乎事实。另外,1862年4月15日, 清廷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改充通商大臣,5月13日李接受抚篆〔25〕。 同年12月3日(十月十二日),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26〕。因此, 李“署”苏抚与薛改任是同时,而李“授”苏抚是在薛改任的7个半月之后。 清代官职的“署”与“授”有明显区别,李在接到“署”、“授”的谕旨后曾分别“具折恭谢”。此信以“署”为“授”,又含混地说“十二日拜表谢恩”,显然是编造。
2.颠倒事实,虚构“玉侄”
第39函《禀母》写道:“前日一役……法提督卜罗德亦阵亡。卒赖天佑圣朝,将士饮血,士卒用命,而贼众尽数覆没。现拟用士卒之余勇,进援苏常,使贼腹背受敌,早日翦灭。 ”史实是, 李鸿章会同洋兵于1862年5月17日攻占奉贤南桥镇后, 并未确定“进援苏常”的作战路线。清廷当时的战略意图很重视镇江,李鸿章赴上海前半个月,曾国藩曾计划派李鸿章率部“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27〕。3 月28日上海官绅雇洋轮七号抵安庆后,李才最后决定进驻上海。李部到上海后,“屡奉移驻镇江之旨”〔28〕。甚至在南桥之战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在《权衡沪镇缓急片》中,仍不得不提出“容臣将沪事办妥即移师出江”的许诺与请求〔29〕。显然,此函“进援苏常”之说是将后事推前了。
第41函《禀母》写道:“前日圣旨下,命薛焕调京使用,着男暂署办理通商事务……三弟在署,读书写字,一如往昔办理琐事,实获儿心。季弟与文儿、玉侄耕读之道,不知可慰先人于地下否?”此信内容也出于编造。清廷命薛焕调京是1862年5月5日(四月九日),此信称“前日”,当为5月7日所写。而其时,李鹤章还未到上海。据记载,李鸿章率淮军赴沪时,李鹤章所统亲兵一营和各营马匹,“洋船不能尽载”,由李鹤章统带,“绕道皖北,押赴下游”,“由海门渡上海”〔30〕。6月3日,即谕令薛焕调京后一个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三舍弟已带马及勇,至仙女庙,望前可抵沪。”〔31〕“望前”即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才可抵沪,岂能在5月初“在署读书”。再者, 根据第67函《致瀚章兄》行文,“玉侄”意指李瀚章之子。但据记载,在1862年前,李瀚章只有长子李经畲一个儿子,此时年方四岁,谈不上“耕读”,而且不名“玉”。事实是,1862年李瀚章从湖南去广东做官,幼儿李经畲随父母同往,并未与祖母在一起。因此,“玉侄”如同前文考辨的“文儿”一样,也是虚构的。
3.不合常情,内容错乱
第44、45、50等3通《禀母》函不及一件家事,全为军政要闻, 不仅有悖常情,而且内容多有错乱。如第44函以“接大哥书”开头,一口气用600字记述1863年云南回民事件,从总督潘铎“被戕”, 说到马荣“为官军擒斩”和“以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其时,李瀚章在广东任按察使,与云南无任何关系。李鸿章官位比李瀚章高,政情当更为熟悉,无需由他告知此事。同时李鸿章更不会用这么长的篇幅向老母禀述与李家毫无关系的军国要事。第45函《禀母》叙述淮军攻占苏州和杀降事,述及郜永宽等“开齐门请降,男入城抚视”。“学启……力请于男,尽杀郜云官等八伪王数百人”。此函记“杀降”事在李“入城”之后,与史实不符。据记载,郜等于12月15日“夜开齐门迎降”,程学启“令郑国魁以二营入城”。16日,“学启入城抚视”。17日“加午”,郜等“出城,请鸿章受谒”,遂发生“杀降”事。18日,李鸿章“整部入城”〔32〕。可见,李是在“杀降”后第二天才入城的。另外,第49函《禀母》叙述清军攻陷天京经过,把洪秀全死的日期四月二十七日误记为“五月二十七日”。第50函《禀母》叙述清军俘杀幼天王,提到“诏赏江南巡抚沈保桢”,把“江西巡抚”误为“江南巡抚”,把“沈葆桢”误为“沈保桢”。李鸿章与沈葆桢是丁未会试同年,政见又较契合,他不会发生这些讹错。
(五)《禀母》类的后11通函件谈及对捻军作战和调任直督前后各事,至少由以下问题可以断定为伪作。
1.称谓不敬,立场不合
第52函《禀母亲》以“僧格林沁既歼”开头,叙述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阵亡的经过,并述及“曾涤笙夫子赴山东督师,以男暂署两江总督”。这里用“歼”不用“殁”称述僧格林沁之死,当是20世纪史书的口吻。僧格林沁是嘉庆帝额驸的嗣子,晋封亲王,声望显赫。他死后,清廷“震悼”,皇帝“亲奠”,“配享太庙”,谥忠亲王〔33〕。李鸿章作为清朝命臣,绝不会作如此不敬的称述。
第56函《禀母亲》谈述1867年2月对捻军的湖北尹隆河之战。 述及鲍超率霆军和刘铭传率铭军“分路进剿”,“期以庚午日晨时进行夹击,而铭传冀独得首功,先一刻进攻,竟大败”,“及霆军践期来……救铭传于重围之中”。实际上,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嫡系亲信,而鲍超及其霆军是由湘军划归李指挥的。据记载,“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34〕。显然,此函史乘式的叙述并不合乎李鸿章袒刘的立场。
2.时间讹错,地名有误
第57函《禀母》谈述官文被曾国荃参劾后革职,“并命谭廷襄署湖广总督。本月六日,命男为湖广总署,仍在营督办剿匪事宜,并调瀚章兄为江苏巡抚,命署理湖广总督。”这种叙述在时间上有讹错。如湖广总督官文被参后,1866年12月28日离任赴京,由户部左侍郎谭廷襄署理湖广总督;1867年1 月谭还京, 由湘抚李瀚章调任江苏巡抚, 留署。1867年2月15日,官文被革职,李鸿章授任湖广总督, 但因军务不能赴任,仍由李瀚章留署。这些人事变动前后经过一个多月,此函竟说成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李鸿章任湖广总督的授命时间是同治六年正月十一日(1867年2月15日),此函称为“本月六日”,显然不合乎事实。 第77函《禀母亲》谈述捻军张宗禹部“由陕渡河”等事,把“山西吉州”记作“山西吉安”。吉州在山西,吉安在江西。李鸿章不会发生这种错乱。
另外,第55函《禀母亲》写道:“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事宜。男已拜表谢恩。一俟曾夫子到署,当立即交代北上。”实际上,在1866年12月7日曾国藩奉命回任两江之前两个月, 即10月1日,曾国藩“请旨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 会办对捻战事〔35〕。旋李鸿章奉命移驻徐州〔36〕。因此,曾、李交接“钦差大臣关防”和“两江总督关防”是在徐州进行的〔37〕。此信意为在南京两江督“署”交接,是一种想当然的编造。
3.交接直督时间上的差错
第80、81、82三函《禀母亲》是谈述调赴直隶前后的事,其中许多细节显露出作伪的痕迹。如第83函记述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后写道:“因命曾夫子调任两江总督,以男为直隶总督,瀚章兄为湖广总督。男已于本月二十二日拜表谢恩,到署受印。曾夫子即于翌日起程,赴两江总督署接绾视事。”事实是,曾、李、李的几项任命都是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1870年8月29日)。 李鸿章在由陕去津途中的直隶获鹿行次获悉授命,于八月初六日(9月1日)拜表谢恩〔38〕,9月20日抵天津。9月30日,曾国藩向李鸿章交卸关防印信。10月17日,曾离津入都觐见,在北京召对三次,12月12日抵南京,12月14日在督署接受关防印信〔39〕。可见,此信所谓“本月十二日拜表谢恩,到署受印”云云,全是想当然编造出来的。
4.母在“署”,无需“迎”
第87函《禀母亲》不足200字,但有好几处明显的谬误。 它说:“前日调瀚章兄为湖广总督,以丁宝祯为四川总督。想瀚章兄现在已交代完竣,向武汉进发矣。”李鸿章和丁宝桢交谊深厚,他不会误写为“丁宝祯”。“武汉”一词不是当时人的语汇。当时,武昌为湖广总督所在地,系湖北省治和武昌府治。汉阳既是县名,又是府名。汉口仅为江夏县(1912年改武昌县)的一个镇,开埠不久。武汉作为一个复合性地名是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才逐步使用的。当时李鸿章绝不会用“武汉”一词代替和代表“武昌”。此信末尾写道:“瀚章兄到武昌后,如派人迎母亲大人到署,请以途中情形,令瀚章兄写信与男。”实际上,李鸿章在对捻作战结束后,于1869年2月20日抵武昌就任湖广总督时, 已将母亲“迎养”在督署〔40〕。1870年间,他虽有“差黔”和调直之命,但前后署理和授任湖广总督的都是他长兄李翰章。1876年1月, 李瀚章虽一度调任川督,但只九个月,便又调回湖广总督任,直至1882年病故为止。前后十多年间,李母一直住在湖广督署。史称李瀚章“督湖广最久,前后四次,皆与弟鸿章更迭受代,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人以为荣”〔41〕。李鸿章在1882年也说:“臣母李氏,迎养在臣兄瀚章湖广督署,先后已阅十年。”〔42〕可见,1876年李瀚章一度任川督时,李母仍住在湖广总督督署,他回任时无需再行“迎养”。
二、关于致兄弟的函件
《家书》中有51通是致兄弟的函件,其中《寄弟》2通, 《致弟》和《致三弟》各4通,《寄三弟》和《寄四弟》各3通,《致鹤章弟》13通,《致昭庆弟》12通,《致瀚章兄》9通,《致瀚章鹤章》1通。这些信函谬误百出,甚至连兄弟人数和称谓也发生错乱。
(一)关于时况不明的函件
致兄弟的函件中有18通时况不清楚,但仍可从下列谬误中断定为伪作。
1.兄弟人数和称谓错乱
李鸿章兄弟六人,兄瀚章,本人行二,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均为一母所生。但《家书》第59函《致鹤章》、第69函《致瀚章兄》均称“吾兄弟四人”。第68函《致四弟》称:“我弟兄四人,惟吾弟年幼,尚在攻读……老母年近古稀,精神日退。”“老母年近古稀”时仍是“弟兄四人”,可见《家书》炮制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李氏弟兄共有六人,各函也没有出现过蕴章和凤章的名字。这大概是因为,李氏兄弟前三人和六弟昭庆事功比较显赫, 《清史稿》中有传〔43〕,而蕴章、凤章二人身位不显,所以《家书》炮制者不知有此二人。
《家书》中的兄弟称谓也很混乱。它多次出现三弟、四弟和季弟的称谓。按兄弟六人排行,“四弟”应为蕴章,但《家书》中有时意指昭庆,有时意指不清。而“季弟”,无论根据排行还是根据《家书》认可的“弟兄四人”,都应指昭庆。但第61函《致季弟》说:“昨日高升来,知吾弟患湿温症”,紧接着的62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来书,吾弟患湿温渐愈,寒热渐退,喜甚”。从这两函联系起来看,“季弟”竟又表指为三弟“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充分暴露了作伪者的混乱。
2.虚构“徐明经”其人
致兄弟函件中有一些谈读经的内容,所谈之道是从一些书本上转抄的。如第2函《致三弟》说:“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读。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里的“徐明经”不见诸记载,而其读经“经验”却似曾相识。在《家书》中一再被称为“曾夫子”的曾国藩,曾在京师向理学大师唐请教治学门经,他记录唐的教诲有:“治经宜专一经”〔44〕和“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45〕等。此信所谓“读经之法”当系抄录“曾夫子”的著述,“徐明经”就是“曾夫子”的化身。有的论者不察,竟把这位虚构的贡生出身的徐夫子征信为李鸿章早年的“导师”之一。
3.周菊初接济祖父事不可信
第59函《致鹤章》和第60函《致瀚章兄》讲到所谓祖父轶事。前者说:“前吾祖父穷且困,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吾弟年少,此事或未之详也。”后者也述及“祖父晚年颇受周姻伯之厚惠”事。这个祖父受周接济的故事娓娓动听,有的论者不疑,竟信为新史料。实际上,周菊初其人不见诸记载,而李鸿章祖上向有“家贫绩学”、“力田习武”的家风〔46〕。祖父李殿华年轻时就“肄武游庠”,两应乡试,虽然不第,但“男耕女织,督课勿懈”。李家虽不富裕, 却是能役使“佃户雇工”的“耕读之家”〔47〕。“穷且困”以及受人“周济”和规劝,而后注意“勤俭”和“亟命儿孙就学”等等,不符合事实。再有,李鸿章比三弟鹤章仅大两岁,也不可能大言“吾弟年少”等。
4.谈书法和养生之法与李鸿章无关
在18通时况不明的函件中,大多为谈论读经、书法和读书养生之法等内容,表面上说得有板有眼,实际上露出了编造的马脚。如第15函《致瀚章兄》大谈书法,述及“二王”、“赵法”、“初唐四家”、“南派”、“北派”,末尾写道:“嘱四弟从赵法入门……望将此意转告二弟。大哥于公退之余,可随时指导诸弟侄。为盼。”事实上,李瀚章从1849年以拔贡到湖南做知县,此后直到1882年丁忧,长期离开家乡。 1849年前,他在家乡还没有子侄,且因年轻无官职,无所谓“公余”;1849年后他在外做官,有了“公余”,却一直不在家乡,不可能“随时指导诸弟侄”。此函之伪,由此可以断定。实际上此类函件,均出于杜撰。其中所谈各种书法、读书、养生等事,与李鸿章无关。有的论者征引这些文字,用以说明李鸿章“不仅著意经史,而且喜好艺文”,实系选择史料不慎所致。
(二)关于在北京期间的函件
致兄弟函件中有4通述及在京期间准备会试的情况, 从下列问题可以看出作伪的痕迹。
1.荐馆于何仲高家是完全虚构的
第23函《寄弟》中说:“日前寄母亲大人一禀中言及文墨能定人生夭寿……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此曾夫子时时论及……兄远客京师,晨昏定省,不得不有劳两弟。”第26函《寄弟》中说:“兄蒙曾夫子垂爱,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公子亦少年好学。”第27函《寄瀚章》也述及:“弟抵京之始,寓狮子胡同马文虎家。北闱中式,蒙曾涤笙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前已考辨,李鸿章初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父母寓所,无需给母亲写信,所谓:“日前寄母亲大人一禀”以及“晨昏定省,不得不有劳两弟”,显然是杜撰。另外,李鸿章中举是1844年,师从曾国藩是1845年。这里说中举后蒙曾荐馆也有悖事实。清代翰林必须是进士出身,但笔者查阅有关史料,不仅道光初年,甚至从嘉庆后期到道光中期,都没有名叫何仲高字居停的进士〔48〕。因此,何仲高其人和马文虎一样,也是虚构的。
2.李瀚章到广东做官是1862年后的事
前引第27函《寄瀚章》开头写道:“天南地北,想念之忱,无刻或忘……兹以两粤总戎进表使者返垣之便,托伊奉上一书。”第30函《致季弟》在说到北京近日“适逢大雪”后写道:“大哥于前月十六日抵粤后,曾有信来,一路安静。现照常视事。”这两函都是冬天执笔的口气,意指李瀚章刚去广东做官。事实是,李鸿章在北京参加考试期间,李瀚章在家乡尚未取得任何功名,更谈不上做官。1849年他得了拔贡,才到湖南做知县〔49〕。他因曾国藩檄调去广东做官是在1862年夏天〔50〕。这些信说还没有功名的李瀚章已经到广东做官,时间提前了18年,又把李瀚章夏天去广东写成冬天,显然是出于编造。
(三)关于在军期间的函件
致兄弟函件中有14通是谈述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事,从下列方面可以看出作伪的痕迹。
1.李昭庆熟知湘军战况,无需函告
第38和第40两函《寄昭庆弟》谈述1862年间湘军战事。前函谈及多隆阿陷庐州和陈玉成败死。后函叙述曾国荃陷雨花台,围逼天京,李秀成自苏常率大军与之对垒,“相持四十六日”。这些是5、6月和10至12月间的事。据记载,李昭庆“初从曾国藩军,淮军既立,国藩留五营,令昭庆领之,驻防无为、庐江。”〔51〕1862年12月15日(十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对王洪春元部进攻无为,“淮军同知李昭庆、张树声会合自金陵派来之湘军臬司刘运捷、水师曾泗美却之”〔52〕。可见,李昭庆于1862年间正在配合湘军作战,对湘军战况自然熟悉,无需李鸿章函告。
2.李昭庆在李鸿章麾下,不在家乡
在给李昭庆的函件中有几通谈述江南淮军战况。第43函《致昭庆弟》述及令刘铭传率部会同戈登洋枪队“克昆山太仓而解常熟之围”,并写道:“文儿、玉侄,家居攻读,端赖吾弟百方指导,纳于正轨。”第47和第48两函《致昭庆弟》,则分别谈述“自克苏州即分兵进攻嘉兴、常州”的情况。所谈都是1863年3月至1864年5月间的事。其时,李昭庆已率部由安徽回到其兄李鸿章麾下。据记载,他参与了淮军攻克嘉兴、常州的战事〔53〕。史称他“解常熟围,克嘉兴、常州,皆在事有功。”〔54〕李鸿章也奏称,李昭庆参加1864年3月攻占嘉兴和同年3、4 月在常熟、江阴等“沿江腹地”的战事〔55〕。可见,其时李昭庆正在李鸿章麾下参战,并不在家乡。这些函件告诉他自己亲历的战事,又要他“指导”“家居攻读”的子侄辈,显然是杜撰。
3.李瀚章有“两广经历”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
致兄弟函件中有4通谈述对捻军战事,也显露出许多编造的破绽。 如第75函《致瀚章》述及1867年11月任化邦败死于“江苏临榆县境”,我国没有临榆县建置,只有临渝关或渝关,即山海关,而任的战死地应是“江苏赣榆县境”。李鸿章谈述自己部下的战绩,绝不会发生将“赣榆”写成“临榆”的错误。另外,第58函《致瀚章》历述了1867年间在山东与东捻军作战情况,末尾写道:“兄以两广之经历,治湖广之大事,遥维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事实是,李瀚章于1862年被檄调至广东会同“办理分卡,抽收厘金”〔56〕。后历任广东督粮道、按察使和布政使〔57〕,1865年3月因授湘抚离粤。1867年2月15日,他因李鸿章新授湖广总督后对捻军作战不能赴任而奉命署理湖广总督。此前,他只是曾在广东做过两年多的地方属官,说不上是有“两广之经历”。而李瀚章后来代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开始有“两广之经历”,那是22年以后的事。此函称“以两广之经历,治湖广之大事”,显然是作伪者把事情和时间颠倒了。
4.李鹤章在乡,未与李瀚章在一起
第78函《致瀚章》谈述1868年2月西捻军抵达天津附近事, 信末写道:“鹤章于上月二十六日上道旋里,遥想已安抵家园矣。”第79函《致瀚章鹤章》谈述1868年8月张宗禹部西捻军的最后失败, 信末写道:“鹤章弟何期来营,望早日写信与兄,以定行止”。实际情况是,李鹤章于1864年11月奉调与刘铭传等“引淮军渡江而北,上援皖鄂”,对捻作战,后又被在山东督师的曾国藩檄调“办理行营营务处”〔58〕,但“未久,迄病归,遂不出”〔59〕。当1868年西捻军打到天津附近时,他早已不在军中,函中说“鹤章弟于上月二十六日上道旋里”,纯属编造。另外,1868年8月李鸿章平定捻军后,为免冒“中外之不韪”, 着手筹划裁撤淮军事宜,连在军淮将都“纷纷乞退”〔60〕,他岂会函问病归已几年的弟弟“何期来营”。再者,其时李瀚章在浙抚任上,李鹤章在原籍家中,李鸿章又怎么会写《致瀚章鹤章》的信。
(四)关于在上海办洋务的函件
致兄弟函件有6通谈及在沪办洋务,全部是赝品。
1.信中出现现代语汇
第67函《致瀚章》写道:“本朝自开海禁以来……国际间交涉,亦因之渐多……弟因是之故,特设外国言语馆于上海。选聘各国旅沪侨民为之教授……吾兄……可命玉侄来申学习,将来为国效力。此亦我李氏所欣幸也。”前文已辨正,李瀚章没有一个名“玉”的儿子,所谓“玉侄”,完全是虚构的。另外,此信中使用了非当时人的语汇和语气,破绽百出。如李鸿章在奏请设立外国语言馆的原折〔61〕中,使用了“中国与洋人交接”、“中外大臣会商之事”、“交涉事宜”等行文,而没有此信中所用的“国际间交涉”的字样;原折中用了“彼酋之习吾语言文字者不少”、“聘请西人教习”等行文,也没有出现“选聘各国旅沪侨民为之教授”等一派现代气息的表述。实际上,就“国际”、“教授”这些语汇而言,它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从日本语汇中吸取来的〔62〕。这些到20世纪初才使用的语汇竟在19世纪60年代的函件中出现,只能说明这些函件是伪作。
2.上海广方言馆初设于城内
第68函《致四弟》写道:“我弟兄四人,惟吾弟年幼,尚在乡攻读……老母年近古稀,精神日退。兄服务在外,不能时时回来。吾弟年逾弱冠……晨昏侍奉,尤须必恭必敬。”紧接着的第70函《致鹤章弟》写道:“兄前致书与四弟,谓母亲年老,倦于家务,劝四弟攻读之外,扶助一切,吾弟想亦表同情也。兄今在歇浦高畔,设立外国语言馆……如愿来学习,望弟告我。”首先应该指出,“兄服务在外”中的“服务”一词,也是从日本语汇中吸取来的现代汉语语汇〔63〕。当时的李鸿章不可能使用这个语汇。另外,李鸿章于1863年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其馆址在上海城内敬业书院西侧〔64〕,1867年江南制造局扩充时,由虹口原址迁至黄浦江边高昌庙。1870年3月初(正月底), 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总局内新址,与其翻译馆合并〔65〕。“歇浦”是黄浦江的别称。这里信中所说的“歇浦高畔”,当意指黄浦江边高昌庙。 但这是1870年初以后的新址,它不应在1863年的信中出现。《家书》杜撰者显然不知这个掌故,所以闹了笑话。再有,李鸿章母亲1800年生,1863年时虽年逾六十,但还不能说“年近古稀”。而李鸿章的四弟蕴章1829年生,此时已三十四岁,既非“年幼”,亦非“弱冠之年”。而且,他“年十三,以目病废举子业”。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怀钧儿》诗中也有“尔目缺于天”的咏述〔66〕。这里,竟将年已三十四岁而且少年时一只眼睛就病残了的四弟意指为少年士子,还劝他“攻读”,作伪的破绽暴露无疑。再说,1863年李鸿章奏设上海广方言馆时,其弟鹤章正在他部下,帮他督率淮军“会克太仓,规苏州”,“会克江阴”,“进攻无锡”〔67〕,且李鸿章又多次亲临昆山、太仓、江阴、苏州、无锡等地前线巡视和督战〔68〕,与鹤章时常见面,没有必要写这样的信件。
(五)关于在直督任上的函件
给兄弟的函件中有8通是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函件, 其中《致鹤章弟》6通,《致昭庆弟》2通,伪造的手法更加离奇和拙劣。
1.说曾国藩死在南昌
第85函《致鹤章弟》写道:“曾涤笙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遽以病入膏肓……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据记载,曾国藩由直督回任两江,于1870年12月12日抵南京,其后除1871年9月27日至11月27 日外出查阅江北江南营务外,直至1872年3月12 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死于两江督署,未再出过南京〔69〕。此函关于曾国藩病死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等,都是任意编造的。另外,第83函《致鹤章弟》末尾说:“吾弟在家,上得奉侍母氏,下得训育子侄。”实际上,李鸿章于1869年2月赴湖广总督任时已迎养母亲至督所。1870年8月他调任直督,长兄李瀚章由原来署理湖广总督改为实授,所以母亲仍住在督署。这里意指李母与鹤章同在家乡,显然是一种编造。再有,第84函《致鹤章弟》述及:“攻破积金堡之后,刘松山死于兵。”这里把“金积堡”错写成“积金堡”,刘松山原是在破金积堡之前被回民打死〔70〕,时间是1870年2月15日,而金积堡被攻破是在1871年1月6日〔71〕。 此函把刘死的时间几乎提前了一年,李鸿章是不会发生这样的讹误的。
2.三封信竟是写给亡弟的
第73函《致鹤章弟》谈述奏请添加直隶所属张家口、独石口和多伦诺尔三厅学额事,并抄录了近千字的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1882 年2月8日)《三厅请添学额折》全文,而李鹤章已于1880年死去。第72 函和第74函都是致昭庆的。前信述及“议照光绪九年奏案”,直隶可以免停“烧锅”(酿酒)〔72〕。后者谈述“铁路尤为交通之根本”,抄录了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与奕譞会奏的长达1200字的奏折全文〔73〕。这里,且不说在家信中整篇抄引奏文不合常理,更重要的是它们说的是光绪九年和十三年即公元1882年和1886年的事,而受信者昭庆早于1873年就死去了。
三、关于给子侄的家书
《家书》中有10通是给子侄的,其中《谕文儿》5通,《谕侄》2通,《谕玉侄》3通,全部是伪造。
(一)关于《谕文儿》和《谕玉侄》的函件
前已考辨,“文儿”、“玉侄”都是虚构的,给他们的信是赝品自不待言。不仅如此,即使从其行文和语气来看,它们也不是出自当时人之手。如在这些应为19世纪60年代初的信函中,用了很多现代汉语中才通用的语汇和表述。如中国有系统的汉语语法和语词分类是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后的事。但第19函《谕文儿》中谈及“名代动静状介连助叹九类之文法”,而行文中所用的“文学”、“思想”、“国人”、“普及教育”等也是现代汉语语汇。另外,第20函《谕玉侄》用500 字的篇幅谈论“古今之五伦不同”,使用了“家族封建时代”、“种族之竞争”、“世界”、“社会”、“民法”、“储蓄”、“教育”、“义务”、“民族”、“适者生存”等现代语汇。研究表明,上述语汇和表述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日本语中吸取来的〔74〕。这些信是伪作当无庸置疑。
(二)关于《谕侄》的函件
《家书》第3函和第12函为《谕侄》,具体对象和时况不明。 前信说:“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后信以“四弟来信云”开头,强调“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这里所谈的“经验”与前述借虚构人物“徐明经”所说的“读经之法”如出一辙。另外,前文已可证明《家书》中的“四弟”并不是指李蕴章,而是错误地指为六弟李昭庆。因此,这两通《谕侄》也全是伪造的。
综上考辨,《李鸿章家书》叙事讹错,谬误百出,可以断言,这90通家书全是伪造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史学研究中的史料选择和辨伪工作。
注释:
〔1〕李鸿章:《原任安徽按察使张君墓表》, 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二册,《李文忠公遗集》第四卷,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二七页。
〔2〕〔3〕〔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 第254、102、10页。
〔5〕《曾文正公家书》第七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6页。
〔6〕《庐州府志》(续修),光绪十一年刻本,第三一卷, 第一○页。
〔7〕〔8〕〔9〕《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1册,《李光禄公遗集》第五卷,第四、五页;第八卷,第二七页;第五卷,第一六页。
〔10〕《李文忠公遗集》第六卷,第一页。
〔11〕〔12〕《李文忠公遗集》第六卷,第一页。
〔13〕曾国藩号滌生,《家书》一再误为滌笙。李鸿章显然不会这样误写。
〔14〕李宗侗等编:《李鸿藻先生年谱》,台湾1969年版,第19页。
〔15〕《李鸿藻先生年谱》,第19页。
〔16〕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5页。
〔17〕《李光禄公遗集》第五卷,第七页。
〔18〕《李文忠公遗集》第六卷,第四页。
〔19〕见李鸿章《诰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李文忠公遗集》第四卷,第三一页。
〔20〕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第2805页。
〔21〕《清宣宗实录》1937年影印本,第四四二卷,第七页。
〔22〕《清文宗实录》1937年影印本,第八卷,第一六页。
〔23〕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652、653页。
〔24〕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 卷,第91页。
〔25〕关于清廷命李鸿章署江苏巡抚,许多论著据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第188页,说是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实误。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初到上海覆陈防剿事宜折》明白记载:“三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臣于十五日接受抚篆”,(《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第一、三页。)是则李鸿章抵沪后第七天,即4月15日(三月十七日)使奉命署苏抚,5月13日(四月十五日)接篆就任。
〔26〕李鸿章:《覆奏近日军情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1908年刻本,第40页。
〔2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一四九页。
〔28〕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一五三页。
〔2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第三十页。
〔30〕见《曾文正公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页;《庐州府志》(续修)卷四十八,第一一页。
〔3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三○页。
〔32〕参见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页。
〔33〕《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册,第11899页。
〔34〕《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六,第40册,第11985页。
〔3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19页。
〔36〕王定安:《曾国藩事略》,第96页。
〔3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21页;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第98、99页。
〔3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六,第五○页。
〔39〕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46—248页。
〔4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九,第二页。
〔41〕《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第41册,第12494页。
〔4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第二九页。
〔43〕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列传二百二十和列传二百三十四。
〔44〕《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出版,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45〕《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46〕《李光禄公遗集》第八卷,第二七页。
〔47〕《李光禄公遗集》第一卷,第四页。
〔48〕参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第2772至2803页。
〔49〕《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第41册,第12494页。
〔50〕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52页。
〔51〕《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第40册,第12338页。
〔5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香港猛进书局1962年版,第2228页。
〔53〕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第2181页;王定安:《曾国藩事略》,第67页。
〔54〕《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第40册,第12338页。
〔5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第六、九、一五、一六、三○等页。
〔5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52页。
〔57〕《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第41册,第12494页。
〔58〕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320页。
〔59〕《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第40册,第12338页。
〔60〕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九,第一六页。
〔61〕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一一至一三页。
〔62〕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第372页。
〔63〕见谭汝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30页。
〔64〕《广方言馆全案》,光绪中铅印本,第六九页;《万国公报》,上海林华书院刊,三六一卷,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日。
〔65〕《广方言馆全案》第一九页,《上海县续志》卷十一,第一页。
〔66〕《李光禄公遗集》第五卷,第十七页。
〔67〕《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第40册,第12337页。
〔68〕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第2133、2139、2141、2166页。
〔69〕参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48—252页。
〔70〕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59页。
〔7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37页。
〔72〕参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二,第五十二页。
〔73〕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232—2234页。
〔74〕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第327—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