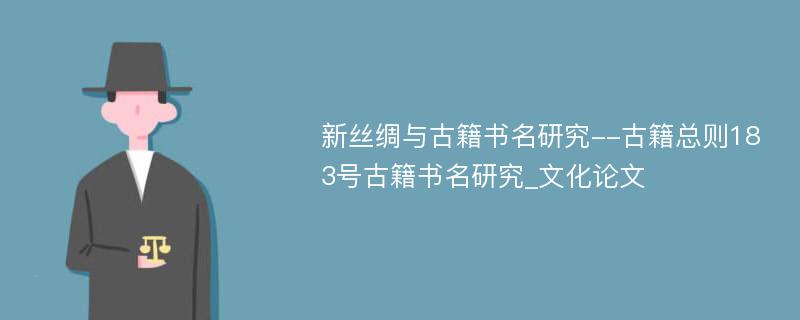
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古书通例#183;古书书名之研究》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书论文,书名论文,通例论文,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一书,详论古书形成的问题,以及刘向歆父子校书的细节,潜研深思,疏通古今。读此书,可以立见唐宋以来疑伪书风潮尤其是近现代疑古运动中许多争辩,不过庸人自扰。此书为余先生于“三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有讲课临时印本……一九四○年排印本”①。然而其时疑古运动中的疑伪书思潮方炽,余先生之说竟几至堙没无闻。
张心澂先生所编著之《伪书通考》,学者多关注其资料作用,此书《总论》中“辨伪方法”部分所录胡应麟、胡适、梁启超、高本汉等学者总结所谓辨伪方法也较受学界重视;惟《总论》中“辨伪事之发生”部分所录若“古人不自著书”,“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书名非著者之名”,则少有学者关注并知道其源于余嘉锡先生;更不知张心澂已经自乱其例,预示着《伪书通考》中所考定的伪书,有不少将来要翻案。
近几十年来,大批简帛古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尉缭子》,《六韬》,宋玉赋,帛书《周易》经传,帛书、楚简《老子》,《庄子》残篇残简,《离骚》、《涉江》残简,楚简《缁衣》等出土,直接推翻古来学者所得辨伪书的结论;不少出土材料也直接证实了余先生《古书通例》中所提出的观点。《古书通例》一书的价值才逐渐为人称道,李学勤、李零先生等在余先生之说的基础上,依据出土古书,重论古书之产生、流传及整理②,影响较大。
可惜余先生的《古书通例》一书没有最后完成,相关文字散见于《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汉书艺文志索隐》③等书之中。余嘉锡先生生前未得见大批简帛古书之出土,其说也有先后不同乃至当弃前说者,笔者在以新出土简帛材料研读余先生的大作过程中,偶有小疑虑;又有余先生之说极简或意在批评随意断古书为伪书,今日之学者未能措意者,似有必要阐发之。今不揣谫陋,选其可说者数节,就教于大方之家。
《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共分四大部分,下面依新出简帛材料,讨论其中和出土文献最相关的第三部分“古书书名之研究”。此一部分,余嘉锡先生先区分官书与私作,指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继而论官书命名之义例。
一、官书命名之义例
余嘉锡先生本章学诚之说,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又引《汉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谓“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
余先生春秋以前无私人著作说,虽然较之罗根泽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稍显合理,然皆为运用“默证”所得结论,未可尽信。罗根泽之文,悍然将相关书籍年代拉晚或归为伪作,今日已不需一一条辨。余先生之说,在今日则只能略述其理以为辨驳。古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就是民间文学,是最古的私人著作。这时的著作,包括口传的文本,不必一定是书于竹帛的文献,当然,有一些文本也有可能曾经书于竹帛,而我们今天尚看不到。先王有采风之官,收集这些作品并润饰之,成为官书,这是民间文学上升为官方政典,而由民间所来之私学,自然远不止此。后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则是王官之学下衍而为私学。这种互动,乃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奈何学者们只论王官之学的流变而不溯其源。官学与私学乃相对概念,官方政典与私人著作也是相对的概念。就如同周相对于大邑商的政治、经济、文化而言,不过偏远小邦,其时的王官之学本来在商。文王招徕贤人,史墙之祖先等影从,周的私学才渐渐兴盛。周灭商后,分殷之遗民,其礼制因殷礼而有所损益,然而虽然有武王访箕子得《洪范》等事,也并未全部吸收商之文化。这时商的文化相对于周的王官之学,却一变而为私学。私学私下流传,或后世才书于竹帛。宋继承商的文化最多,孔子得以涵养周、宋的官、私文化,又周游列国,学无常师,故卓然为一代儒宗。
二、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
余先生指出“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余先生此说,当结合其《目录学发微》所论以观之,“其有古人手著之书,为记一事或明一义自为起讫者,则以事与义题篇,如《书》之《尧典》、《舜典》,《春秋》之十二公,《尔雅》之《释诂》、《释言》等是也。其有杂记言行,积章为篇,出于后人编次,首尾初无一定者,则摘其首简之数字以题篇,《论语》之《学而》、《为政》,《孟子》之《梁惠王》、《公孙丑》是也”。“《诗》三百篇,《国风》皆摘字名篇,大、小《雅》及《周颂》乃有别为篇目者,如《雨无正》、《常武》、《酌》、《桓》、《赉》、《般》之类是也”。
余先生又谓“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其后续引叶梦得之言谓“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余先生以今本《列子》为伪书,故仅注曰:“按《庄子》内篇诸篇目,虽皆有意义,而外篇《骈拇》、《马蹄》之类,仍是摘字名篇。”则余先生已基本认同庄子内篇可能是庄子自撰书名。余先生于《目录学发微》中也说:“古书名篇,有有意义者,《书》、《春秋》、《尔雅》之类是也;有无意义者,《论》、《孟》之类是也。《诗》三百篇则兼用之。盖其始本以为简篇之题识,其后遂利用之以表示本篇之意旨。若《庄子》之《逍遥游》、《齐物论》,则由简质而趋于华藻矣。自是以后,摘字名篇者乃渐少。”然则庄子之时,已有自撰有意义之篇名的现象。
考望山二号墓楚简遣策“……周之岁,八月,辛□[之日]车与器之典”,已经可以看作是书者自定标题;上博简中,有《曹沫之陈》、《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内礼》之类较有意义之篇名,其墓葬年代与庄子中年接近,竹简的写定年代当更早。此等虽或是为官书、他人著作题名,但可以推测自撰子书并题篇名之事,在当时应该已经有可能,其时代甚至可能在庄子稍前。今传本及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中,多数篇名并非摘字,而史籍并银雀山汉简《见吴王》多提及孙武自作十三篇之事,则孙武自题篇名,或未尝不可。《渚宫旧事》载墨子曾献书楚惠王,而墨子所献很可能即是兼爱、非攻、明鬼等基本思想,则此等篇名或出自墨子所定④。上博简《内礼》篇名并非摘字,此篇与《大戴礼记》中《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诸篇颇有渊源,《内礼》或可能是后儒所定篇名,但是其为撰者所定,也不无可能。
余先生所谓“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乃是讲古书单篇别行之例,举《仓颉》、《凡将》为例,可从。他举《王孙子》一篇时说:“愚谓《汉志》诸子,除不知作者外,皆只以人名书。其只一篇者,盖别无篇题。独《王孙子》又别题其篇曰《巧心》,故注为‘一曰’也。”《汉志》“兵形势”有《王孙》十六篇,与王孙子不知是否相关,无论如何,内容当不同。今考《王孙子》佚文⑤,皆为臣谏君之事,疑“巧心”即“考心”,为人君诫书,篇名《巧心》即其本名,或乃王孙子所自题。此篇当曾单篇别行,而《王孙子》之名,殆传其学者所题或校书者改题,以尽量符合“诸子”类“以人名书”之例,而不论其是否只有一篇。余先生于此未言《巧心》之名是否为王孙子自题,殆因王孙子于《汉志》位列宁越与公孙固之间。钱穆先生以为宁越年岁与李克、吴起相伯仲⑥,而据《汉志》原注,齐闵王失国尝问公孙固。齐闵王失国依西元纪年为公元前284年,在钱穆先生所推庄子(公元前365-公元前290)卒后。则王孙子年岁或小于庄子,至少不会早庄子多年。而前文已推测庄子之前已经有可能自撰篇名,因此王孙子确有可能自撰书篇名为《巧心》。
三、古书多无大题
余嘉锡先生说:“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此多就有名姓之人物及有学派传承可考之著作而言。其后余先生举韩非、董仲舒等之例以说明“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谓篇名)。并无大题也(谓书名)”。这主要是就自著作品而言。
余先生“后世乃以人名其书”之说,所论为《别录》、《七略》之事,并非先秦之实。睡虎地秦简有大题《日书》,马王堆帛书有所谓大题《经法》、《经》⑦。今之论者或以《经法》诸篇为《黄帝四经》、《黄帝书》,此与刘向、歆父子编次群书时所用之法或较接近,即是根据内容及篇名等,以类相从,合本相校。马王堆帛书所见标题虽然无关黄帝,然而《经》内有与黄帝相关者,如果别本有相关内容而其题名(未必是大题)关涉黄帝,则《经》颇易归入黄帝书。这仅是据理而推,实际上马王堆帛书《经》等究属何学派,至今尚有争论。由汉代出土书籍的情况,不难推想编次之事,并非皆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
小题、大题之名,似乎不足以尽古书标题。余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曾指出,“《书》有虞、夏、商、周,《诗》有风、雅、颂,而《史》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为全书之纲领。作序之时,举当篇之小题纳之于总称之下,而属之以大名,然后诵读有伦,取携甚便。此大名、总称、小题者,犹之后世之部次也”,进而研究目录之“类例”。则余先生以风、雅、颂等为“总称”。然“国风”之下还有十五邦之名,再其下才是篇名;又古书篇名之下仍有标题,如《荀子·赋篇》下录《礼》、《知》、《云》、《蚕》、《箴》等五篇有标题之赋,及无标题之《遗春申君赋》一篇,《佹诗》一首。因此,顾炎武曾提出“分题”之说⑧。
卢文弨与钱大昕皆以为《诗经》卷首“周南诂训传第一”为小题,“毛诗”为大题,并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谓郑玄注三礼等为证⑨。然而“周南”之下的“关雎”等方为标题,又“毛诗”下尚有“国风”二字⑩,即余嘉锡先生所谓“总称”者,而三礼并无书名、篇名间之标题。钱大昕谓“唐刻石经皆大题在下,如《诗经》卷首,‘周南诂训传第一’列于上,‘毛诗’两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谓大题在下也”。然而唐石经于“毛诗”下亦有“国风”二字,且石经《尚书》在下者乃“虞书”之类(其前有隶书题“尚书序”、“尚书卷第二”等)(11)。案《经典释文》于“毛诗”云“故大题在下”(12),颇疑陆德明所见故本“毛诗”二字尚在“国风”之下。若然,则古人撰著、疏注之篇题书名等,当是依标题外延之小大,依次排列。因此,以小题、大题为篇名、书名之称,恐尚不足以尽古书之篇题。如马王堆帛书《经法》、《经》之名,它是今天所谓的“大题”吗?《尚书注疏》中,仅有“虞书”之类名称,则它没有“大题”吗?有学者以书题、篇题、章题以作区分,然而恐怕也非反本穷源之论。
若以大题专指书名而言,则余先生所说“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并无大题也”甚是。古书多单篇别行,银雀山汉简等有专抄篇题之木牍,马王堆帛书中拟名为《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者,也有专抄篇题的部分,当来自于木牍或竹觚,其时并无大题,而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已有大题“日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也是书名,马王堆帛书《经法》、《经》等或可谓兼有小题、大题。然则此时子书之大题尚处于初创期,或有或无,尚无定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经》诸篇年代,尚难断定,而且作成的年代也未必是题写“经法”、“经”的年代。然而据此以及睡虎地秦简《日书》推测,不难推想大题之起源,当在战国时期。李零先生曾谓书籍普遍书写大题或为隋唐以来之习惯,如汉《熹平石经》尚无大题,唐《开成石经》始有之(13)。然而据《汉志》来看,普遍题大题或是官方行为,与民间传抄书籍习惯容有不同。至若《熹平石经》,今已残,其以一家之经为主,或所录本无大题,因为传者守一经,不需大题以为分别或不必处处列大题,也可能有如唐石经《尚书》之以“尚书”题卷而今已不可见。古书普遍题书名,疑为六朝时事,晋葛洪自名其书为《抱朴子》,梁萧绎自题所作曰《金楼子》,或可为例证。
四、《汉志》为书命名
余先生云:“《汉志》于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古之诸子,皆以人名书。然《汉志》中,亦有别题书名者,则大率不知谁何之书也。”余先生所举之例,有儒家之《内业》、《谰言》、《功议》、《儒家言》,阴阳家之《杂阴阳》,法家之《燕十事》、《法家言》,道家之《道家言》,阴阳家之《卫侯官》,杂家之《杂家言》,并谓“此皆《数术略·序》所谓虽有其书,而亡其人也”。
《内业》、《谰言》、《功议》、《燕十事》、《卫侯官》等,余先生谓:“盖皆后人之所题,或即用其首篇之名以名书。”自注:“《管子》有《内业篇》。”此殆据《管子·内业》而反推。但是,此《内业》是否与《管子·内业》相同尚不能确定。《管子·内业》讲积精得道之术,恐非儒者之言,此不比《管子·弟子职》与孝经类之《弟子职》有可能为同一篇。余先生后文言经书、子书编次之法不同,子书校除重复。倘儒家《内业》即《管子·内业》,或可据以相较而不得单立于儒家。马国翰以《谰言》为孔穿所造,自《孔丛子》中录出相关者以为佚文,然而学者多不信。古书分合无定,后人整理时亦无定法。如银雀山汉简《奇正》,整理者尝归入《孙膑兵法》,后又分开单立。今天所见的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单篇别行,论者据古书记载归其入《子思子》或《公孙尼子》,彼此争议不休。李零先生谓《缁衣》乃记孔子之言,子思、公孙尼都是传述者(14),这个说法比较圆融。然而《缁衣》为何人何派编辑,有无深意,仍然待考。则《汉志》之《内业》等或是别本单行者,久而失其宗。
《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等,余先生以为“刘向校雠之时,因其既无书名,姓氏又无可考,姑以其所学者题之耳,皆非其本名也”。然则余先生之预设,大致仅此等篇章,原本无书名,其他民间藏书则送至秘府之前,多已经有了书名。实则由汉简帛书等可知,汉代古书虽多有篇名,少数亦无或只有总冒下文(15)之语,并非皆有书名。颇疑《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及《六艺略》《易》类中之《古杂》、《杂灾异》,《诗》类中之《齐杂记》,《春秋》类中之《公羊杂记》,《孝经》类中之《杂传》等,为校书之余,或数十篇,或一二篇,缀为一书。考刘向校书未毕即卒,则此等残杂之书,很可能是刘歆等所编定,将散篇零简以类相从,分于各家之下。知者,纵横家中本当有若干杂篇,可名为《纵横家言》,刘向置之于《战国策》;小说家中本亦当有杂篇,而刘向于《说苑叙录》中云别集以为《百家》。大概刘向于杂篇皆造新书,而刘歆等则杂凑为一编,颇为简便,是故其校书,《别录》未完(刘歆犹校《山海经》等),而《七略》有成(16)。《汉志》道家“《杂黄帝》五十八篇”,《汉志》注为“六国时贤者所作”,也可能是杂集有一定水准之“黄帝”言,非一人一派之作,与“小说家”中“迂诞依托”之《黄帝说》性质不同,然而分门别类之法相近。考“兵技巧”有《杂家兵法》,不知张良、韩信或杨仆校兵书之时,是否已兴此法,则刘歆等或可能不过是因袭成法(数术略、方技略中称杂、杂子者尚多,待考;诗赋略中之杂赋类及《秦时杂赋》、《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杂各有主名歌诗》、《杂歌诗》,其分类则或另有类例,待考)。今所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便因篇章结构颇不一致,故取《战国纵横家书》之名,而放弃了初称名“帛书《战国策》”。河北定州八角廊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整理者皆采用了《儒家者言》之名,用来称呼所出的儒学文献,颇为简便。若然,则此一类书虽是不知作者,但“别为之名”有一定之规可循。此节余嘉锡先生有注云:“此条当与《古书不著撰人篇》第十三条参看。”《古书通例》有《古书不题撰人》节,在此条之前。余先生所言,当指“《汉志·数术略》中所著录之书,无姓氏者十之八九”云云。
五、古书自撰书名
余嘉锡先生论“自撰书名之所自始”,先论书名之始,以为“古书自六经官书外,书名之最早而可据者,莫如《论语》”。又以为“自著书而自命之名”,乃《吕氏春秋》,“萌芽于《吕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论语》之名,始见于《礼记·坊记》,据说《坊记》又见于《子思子》。张舜徽先生曾根据汉代载籍怀疑此说(17),恐怕不可据。因为与《坊记》有关的《缁衣》篇已见于郭店简及上博简,与今本大同小异,而且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已见有孔子之语称《尚书》之名,旧传之说当据改(18)。《尚书》虽为六经之一,但古代只称《书》。称之为《尚书》,或出自孔子编次之后,则此书名已不同于一般之“六经官书”。
古书题写书名,当源自于官书、文书,即余先生所谓“六经官书”,大概是为了便于档案管理。从出土文献来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即是所谓书名,下辖众多法律条文。古书自撰书名,因为古人著书不自收拾,多单篇别行,故难考其源。《史记》虽有所述,而余先生惟信《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本有《八览》、《六论》、《十二纪》之名,其号曰《吕氏春秋》,恐怕与余先生所说《虞氏春秋》相近,乃是传之者、时人的称呼——《孔丛子》曾记《虞氏春秋》,以为虞卿自名,然而《孔丛子》此事恐不可信(19)——未必是吕不韦号之。余先生分别二者,大概是因为《史记·虞卿列传》明言“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而《吕氏春秋》则是“吕不韦乃使其客……号曰《吕氏春秋》”。然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申子“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余先生何不以为是自号呢(20)?退一步讲,即便《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自号,它也不是私人自作,应当视为集体著作而吕不韦为之题名,仿佛孔子编次《书》经之后题名为《尚书》一样。与此相同的是《淮南子》之名为《鸿烈》,余先生也以为是自号,大概也因此而宜信“吕氏春秋”是自号。
余先生于“古书多无大题”节,已经多次引《史记》所载为他人之书题名或称雅号者,则私家著作的自撰书名,应当距此不远。现今根据出土古文献来看,南郡守腾所发布之文被题名为《语书》,整理者以为“语书”之意为教戒之文告(21),这就有可能是南郡守腾所自撰的书名。然而这或许属于文书,子书的自撰书名,犹待考。余先生曾于“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节中谓“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然而在那里余先生讳言《巧心》之名是否为王孙子自撰。我们认为余先生既然怀疑《庄子》内篇的篇题为自撰,则不能排除《巧心》即是王孙子自撰的篇名,因为书只一篇,于是就成为书名。
余先生《古书通例》一书,并未对何者为“书”下一个定义。他所讲的“古书”之通例,有“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古书多无大题”,古书多“单篇别行”,这些都是针对的单篇,然而依本节“古书自撰书名”来看,则又是针对的多篇集合之书,用的是现代意义的“书”概念,这里单篇是不能称为“书”的。李零先生曾分别三种不同含义之“书”:作为文字之“书”包括铭刻与书籍,作为档案之“书”文书,作为典籍之“书”古书(22),并曾谓古书篇题即书题(23),有不少好意见。我们认为回溯中国古代典籍时,现代所谓书、篇有别的观念应当被抛弃,每一篇即是当时之书,而每一书或仅后世之一篇。后人所集书多,兴起大题之说,故仅视有小题者为篇,以为一书当含多篇。实际上《说文》云:“篇,书也。”古代称“书”者,不必像《尚书》一样皆含多篇。包山楚简《集书》、睡虎地秦简《语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脉书》等,都是书,其内部虽可分章节,然而并没有篇名以别之。“书”之本意为动词义之书写,写定之后,即为名词义之“书”,《墨子》中常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说文解字·叙》谓“著于竹帛谓之书”,则金人铭、刻石铭文等都是“书”,奏议公文档案也是书,像《尚书》、《集书》、《语书》、《奏谳书》之类。后世专用书指典籍,则仅《尚书》,秦简《日书》,张家山汉简《脉书》、《算数书》等可以视为书,而称书者未必内中有篇可分。
至于竹简的“篇”、“卷”,章学诚虽然曾经三言两语道出古人本意“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然而又说“篇从竹简,卷从缣素”,以及“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等,可谓多滋误会(24)。陈坦、叶德辉、钱存训等皆沿袭其说;劳榦、陈槃、陈梦家、刘洪、奚椿年则根据新出简帛指出帛书未必卷,或有折叠者,简册则成卷存放(25)。李若晖先生总结前人时贤的研究之后,指出:篇谓首尾完整之文章,卷谓由简帛等书籍书写材料之存放方式而形成之书籍计量单位。我们认为此说仍然是根据后世的制度而言,并非穷源反本之论。李零先生曾指出:联简成编则称篇(篇与编通),称卷(以其可以舒卷(26),说是。《史记·留侯世家》说:“出一编书。”《集解》云:“徐广曰:‘编一作篇。’”“篇”以简策编之以丝绳言,“卷”以简策编联成卷言,原义当本接近。如汲冢所出竹书,后人整理,《晋书·束皙传》记有“七十五篇”,而王隐《晋书》称“七十五卷”,是一篇即一卷。由郭店简、上博简等可知,出土简册多有未用之空白简。因此可以推想古人虽然多使用先书后编之法,编订整齐,没有赘余的简,篇、卷即为起讫;然而也当有编好之后待书的空白卷策,若今日之稿纸,或有一些可能在抄写了书籍后尚有部分空白简未使用,以至于出土简册中有空白简。是故篇、卷可书者,多少不定,因而一篇一卷中可以包含多种内容,如《礼记·乐记》疏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上博简《子羔》,由抄手文字看,当包含所谓《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子羔》三文成一卷,而仅题“子羔”(27),以致有此为篇题抑或卷题之争论;至若张家山汉简《脉书》,自称为“书”,它仅后半论脉的部分,大体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书相同,可以说包举多书,而其内容乃《黄帝内经·灵柩》中《经脉篇》之一部分,在后世仅得视之为“篇”。
余先生曾经误信章学诚等之说,以卷为缣帛之特称。不过余先生也曾于《目录学发微》中指出古人虽“多以一篇为一卷”,然篇、卷之分合无定:“古人手著之文,其始不能规定字数,故有篇幅甚短者,则合数篇而为卷。盖过短则不能自为一轴,过长则不便卷舒,故亦有分一篇为数卷者,但大抵起于汉以后耳。”因此,篇、卷之称,本出于竹简之编联,后世则多有篇小卷大之制。《汉志》所载中书,篇、卷之数往往不同,余先生曾疑称卷者为帛书,遂据《风俗通》佚文“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以为刘向校书“皆先书之竹简,取其易于改治。逮校雠既竟,已无讹字,乃登之油素”。但是所引《风俗通》佚文,乃是根据严可均辑本,前人多误读之,并误归为《别录》佚文。余先生后作《书册制度补考·杀青缮写》,已放弃此说(28)。因为中秘之书未必皆登之油素,《别录》佚文有:“《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而前引《风俗通》其下亦云:“今东观书,竹、素也。”
竹简多卷放,然古人有漆盒、竹笥,疑竹简亦可平铺层累如折页。是故包山简《受期》、《疋狱》、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不题书名于简首或简尾数简之背面,《受期》共61枝简,乃至题名于第15简之背面。
余嘉锡先生论《太史公书》时,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所谓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之说,谓司马迁于《自序》中已言及“为太史公书序”,又引古人说东方朔于“每卷篇目之下,别题太史公三字,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非谓《自序》中之书名也”,想说明后人所加之大题乃“太史公”而非“太史公书”。然而张舜徽先生认为王国维说是,因为“为太史公书序”当连下读为“为太史公书序略”,而此七字“乃汉以后学者据《汉书》所妄增”(29)。据王国维所引汉人称《史记》之名不一,《史记》当为《太史公记》之省称来看(30),《自序》中之七字恐怕当如张舜徽先生之说。然则汉世司马迁之时,自撰书名仍少见,多为他人代撰名号。由此来看《吕氏春秋》、《鸿烈》,恐怕确实并非自号。惟有王孙子的《巧心》本为篇名,或出自撰,偶成书名。
古人常言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今验以简帛,则仅帛书或有此现象。今姑依篇名、书名之说以考“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何以可能。竹简抄写的战国古书,多将篇名题于简背。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是少数例外,篇名单独成一简,位置在下半简,当是末简(31);此篇简1背部所题之“竞建内之”并非书名(32)。郭店简《五行》开篇有“五行”二字,恐不能视为篇名,而是总冒下文之词,类似者为银雀山汉简《将败》,《荀子·修身》中“治气养心之术”等标题。今天所见的出土战国古书多单篇别行,未见书名。睡虎地秦墓《日书》乙种,书名另为一简,书于空白简背的上端,整理者定之为最末简,类似者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篇名书于每篇头三简某一之上端,不另为一简,下抄正文;睡虎地秦墓《封诊式》书名书于末简背面,而篇名书于每篇首,空格,然后抄写正文。这些是有书名的,无书名的《秦律十八种》,篇名(律名)书于正文后,二者间留有空格,篇多分段而且每段皆书律名(时有省称);《秦律杂抄》或有篇(律)名,书于正文后,以圆点格开,各篇连写接抄。由此似可见秦时书名尚无定格,而律名似有书于正文后之习惯,包含《为吏之道》所抄之“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因此可知,古人之说,多本汉世以后纸、帛抄书而来,大概先抄正文、篇名,再翻转寻找竹简的书名誊录,因此成为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之式。然而何以篇名多在正文后?并非如此者也很多见,除前举睡虎地秦墓《日书》与《封诊式》外,像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有篇题在行首上端,当是摘自竹简,较晚的有武威汉简《仪礼》丙本《丧服》,“丧服”二字书于首简上端。这一类篇题,便于阅读,故很多见。然而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六韬》(33)等将篇名书于篇末,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定州八角廊汉简《六韬》的篇题中尚有“右方”云云,明确是将篇题放在篇末,类似后世书法的题署;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与银雀山汉简《八阵》、《延气》、《将义》(34)则既书于首简背,亦书于末简尾(35)(唐开成石经也多见卷首、卷尾同题)。概而观之,竹简抄书,篇名不出在正文前与后两种情况(36)(简背可视为在正文后,简背简尾皆有篇名者,亦可视为在正文后),而书名则多在简背。因秦律多将篇(律)名书于正文后(睡虎地秦简《效律》是将篇名“效”书于首简背,同于在正文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法律、法令条文名称也是于正文之后另简书写律令名,书名抄于首简背面——此或是政府公文格式,更具通行性。因此,在国家权威的推动下,小题在正文后之格式逐渐为通行(悬泉置月令诏条书于墙壁,类似帛书,标题书于正文末)。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之格式在后来雕版印书中仍然大量存在,然亦逐渐为人所改,而民间抄书,若敦煌卷子,当然有不按政府格式行文的情况。
注释:
①周祖谟:《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161页。下引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及《目录学发微》之说,皆出此书,不再另外出注,然标点不全依该版本。
②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1页。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7页。
③《汉书艺文志索隐》一书,旧疑已佚。今知幸存,参见《〈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中国经学》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④参见秦彦士:《墨子考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70页。
⑤参见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51-56页。
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5页。
⑦参见李学勤:《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4-282页;李学勤:《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296页。
⑧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27页。
⑨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669-670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上,《十驾斋养新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
(11)参见严可均:《唐石经校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84册,第262、255页。
(12)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13)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5)“总冒下文”之说见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86页。并参见林清源:《简牍帛书疑似标题研究》,《中国文字》新廿九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33-176页。“总冒下文”与标题当有联系,如郭店简《五行》开篇有“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云云,论者以“五行”为总冒下文之词,非标题,而孔家坡汉简《五胜》与之类似,便以“五胜”作为篇名。
(16)《七略》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要在是年四月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之前。参见李解民:《别录成书年代新探》,《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311页。
(17)张舜徽:《广校雠略》卷 ,《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8)参见廖名春:《帛书〈要〉与〈尚书〉始称问题》,《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第155-160页。
(1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65页。
(20)《史记》言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余先生以为是“史公率尔言之”。《汉书·蒯通传》云蒯通“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余先生也以为是“时人号之”者,大概因为《史记·田儋列传》没有“自序其说”及“号曰隽永”之文。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页。吴福助则以为“语书”为“文章类名”,非篇题,参见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22)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9-53页。
(23)李零:《出士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篇卷》,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5页。
(25)赵坦:《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阮元订:《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7-338页。叶德辉以下之说,参见李若晖:《古书流传柬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8-14页。
(26)李零:《简帛的形制与使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6页。
(27)参见李锐:《试论上博简〈子羔〉诸篇的分合》,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85-96页;《论上博简子羔诸章的分合》,《简帛释证与学术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45-155页。按:拙文篇名或称“篇”或称“章”,因当时于书、篇、章之认识尚浅。
(28)钱穆先生所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已先指出前人之误,参见李解民(闻思):《〈风俗通义〉佚文甄别》,《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7-289页。
(29)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
(30)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69年,第510-512页。
(31)参见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简帛网’”2006年2月19日。陈剑指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与原所谓《竞建内之》当合为一篇。从篇题简文字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部分相近而与《竞建内之》不同,以及篇题简在篇题之下所加饰笔与简8在抄完全篇之后所加饰笔相近来看,似更应在篇末。尹湾汉简《神乌赋》篇题独立占一简,书于该简上端,整理者以为是末简。
(32)笔者已指出“竞建内之”可与包山楚简比较,乃景建交纳此一卷书(或还包括未发表的篇章)。参见李锐:《上博五札记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则此篇篇题将使用过之竹简刮去题写篇名,恐属于特殊情况。
(33)李零先生指出《六韬》之定名可能有不妥,称之为《太公》或许更好(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0-372页),当从。下定州八角廊汉简《六韬》同。今为便于说明,姑用此名。
(34)末简尾之“将义”在首简背作“义将”,整理者认为当作“将义”。
(35)银雀山汉简整理者指出:“竹书可以是一篇一卷,也可以是数篇一卷。如果一卷不止一篇,大概只有第一篇才会在首简的背面写篇题。银雀山竹书中有些短篇的篇题同时写在第一简简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又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前者当是一卷的首篇,后者很可能是首篇之外的某篇。例如《孙膑兵法》的《八阵》和《地葆》两篇,书体和行款都很相似,《八阵》篇第一简简背和篇尾都有篇题,当是一卷的第一篇,《地葆》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大概是编在《八阵》之后的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简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整理者之意见值得重视,然张家山汉简《脉书》之书名题于首简背,而书名所对应内容仅为简文后半。
(36)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实虚”篇文末有“·”下题“神要”二字,待考。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在“天下至道谈”上加一点,单独为一简。鄙意此并非标题,当连下读为“天下至道,谈(淡)如水,沫淫如春秋气。”至若何故“谈”下空白,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