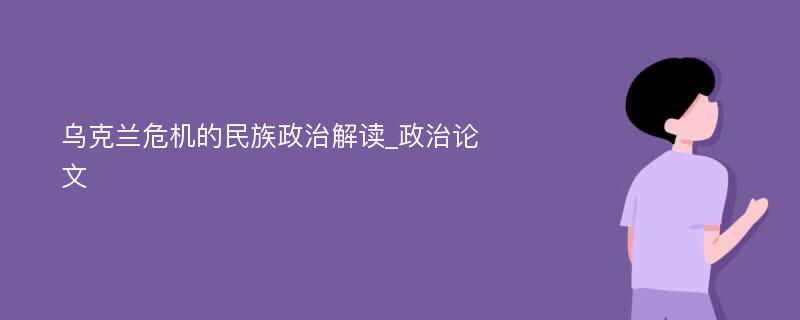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克兰论文,危机论文,民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4-0027-12 一、问题的提出:乌克兰危机中的民族政治视角 2013年11月21日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其重大国际影响力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该事件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导致后冷战格局终结(也即美国单极霸权的终结),倘若如此,那将是1991年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了,政学各界须审慎对待与深入研究之。这一仍在发酵的重大事件,是民主政治(广场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这里的民族政治因素既有其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又常常与民主政治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混搭在一起,因此从民族政治角度审视这一危机的演进及其政策内涵是不可或缺的。 回顾半年来危机演化进程,中间至少有三个拐点性事件使得冲突与危机向纵深挺进。第一,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此举引发乌克兰国内亲欧民众不满,于是爆发了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本已十分脆弱的乌克兰政治生态中,乌克兰广场政治在旧动力驱动下找到了新“广场”,也使本已经极化的乌克兰政治生态进一步彰显与表面化:亲西方的西部乌克兰与亲俄罗斯的东部乌克兰;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①第二,2014年2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出发,朝议会大楼方向前进,举行号称“和平进军”的活动,要求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随后示威者在议会大楼附近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数百人伤亡。惨重的人员伤亡标志着危机升级,而新危机与新挑战势必接踵而至:社会舆情更加愤怒并走向决裂,对立的精英政治家开始摊牌,国际干预日益升级。第三,在俄罗斯因素驱动下,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进行“入俄公投”,95.5%的投票者赞成加入俄罗斯。克里米亚“入俄公投”及俄罗斯的赞同与接受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②下展开的,它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由国内事件转化为国际事件,意味着国际干预的深化以及大国地缘政治摊牌在即,意味着乌克兰危机愈来愈超出乌克兰所能掌控的范围,乌克兰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前述三个拐点性事件中,前两个事件不是显性民族类事件,但其中包含了民族因素,而最后一个事件是一个显性民族事件,因为克里米亚公投的主要法理基础来自俄罗斯族的民族自决。那么,乌克兰危机演化进程中,民族因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在其政治生活中产生作用,这是本文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具体分析思路是,探索乌克兰民族冲突的历史溯源与历史记忆、乌克兰国家建构中的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的冲突与张力,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合流与冲突,克里米亚民族自决权的边界与滥用。 二、历史溯源与历史记忆:民族积怨与民族主义的循环对抗 当前的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ethno-national)构成中乌克兰族排名第一,约占总人口的78%(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中部与西部),俄罗斯族排名第二,约占总人口的17%(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东部),其余为犹太人、鞑靼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渊源颇深,历史上两者既合作也不乏冲突,但在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双方的历史积怨与民族主义循环对抗更容易被两个群体所记忆与提及,这是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 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在文化与族属上是近亲,它们均为东斯拉夫人,历史上都属于古罗斯民族,9世纪时建立了罗斯国家。13世纪蒙古西征改变了古罗斯国家的走向,罗斯大部为金帐汗国所统治,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在波兰等势力支持下得以保持独立,而乌克兰一词由此产生(古俄语中“边地”的意思),这一意涵也暗示了乌克兰的命运(强权挤压下独立困难,生存压力重重)。在蒙古人统治期间,罗斯分化为东北罗斯、西北罗斯与西南罗斯三部分,乌克兰的内涵逐渐由加利西亚—沃伦公国这一“边地”演化为整个西南罗斯。在接下来的乌克兰历史变迁中,乌克兰民族性的建构具有反波兰和反俄罗斯的特性,③因为乌克兰夹在更为强大的波兰与俄罗斯之间,往往处于安全“赤字”与独立困难之状态。1569年乌克兰与波兰合并,1667年乌克兰被波兰与莫斯科公国瓜分(分成西乌克兰与东乌克兰),18世纪末波兰被欧洲列强瓜分之际,乌克兰被归并入俄罗斯。在波兰与俄罗斯统治时期,乌克兰族均遭遇民族同化政策,并曾引发过乌克兰族规模不一、类型不一的各种对抗,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1648年哥萨克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乌克兰一度独立但旋即被波兰占领,1921年列宁与波兰签约承认西乌克兰归属波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苏德签约瓜分波兰,西乌克兰归属苏联。苏联时期,乌俄两族矛盾又有新的积累,苏联领导人工作重点旨在预防与打击乌克兰地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不乏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与举措,这被认为是为乌克兰独立与乌克兰东西对立埋下了新的祸根。⑤ 上述溯源中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决定乌克兰当前危机的本质与形式,但理解这一背景颇为重要,因为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各方政治势力都在动用与挖掘历史资源(特别是独立的民族史叙述),民族历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史,为不同人群因不同原因而“记忆着”与“再造着”。尤其是在国家显现危机(包括族际冲突)时,“历史记忆”既成为凝聚与动员族群的必要资源,又是族群(及其变体)寻求并保障其现代权利与诉求的主要证据(历史正义性)。因此,从历史层面探究乌克兰危机的民族因素,最为关键的是,把握当代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历史是如何被编撰和使用的,其现实指向是什么,特别是政治体系如何理解、阐释与建构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二十余年的历史来看,乌克兰族历史成为了主流叙事,这意味着要对原来的苏联叙事和俄罗斯叙事进行区分乃至清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乌克兰族成为新国家第一大民族。然而,这一新的历史叙述并非天然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与积极社会效果,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后果,需要乌克兰政府审慎权衡其局限性。从现代国家实践一般情况看,缺乏包容并整合民族差异的“向前看”规划指引,工具性地使用“向后看”历史策略,往往导致族群偏见固化,或撕裂社会政治团结,因为那只不过是民族主义循环对抗的续集而已。从乌克兰近年来的实践看,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的大清洗、大饥荒、⑥民族语言政策、移民政策成为当前乌克兰政治争议的重要话题,也是乌克兰民族记忆中新的对立乃至伤痛。因此,乌克兰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地区对立被接续下来,导致其东西部区域国家认同差异与冲突不断积累,重新发酵。 三、国家建设的张力:国族政治主导还是主体民族主导 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政治上面临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nation building)这一重大且全新的现代任务。就发展政治学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路径,前者的主体是政府,后者的主体是公民。从政府角度说,现代国家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威覆盖到整个领土上以及国家在地区、民族等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形成标准化的共同文化。⑦ 关于什么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共同文化,政学两界在思想与实践上不乏分歧,大致存在着最小共同文化与最大共同文化两种不同策略。最小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国家不太关注社会文化的差异与分殊,只强调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这一底线共识及其标准化,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存在,但一定程度上要限制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依托与源自主流社会文化);最大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尽量让非主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被同化,形成文化齐一化。这两种策略均为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遵循,然而从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看,最小共同文化策略占据了上风,但最小共同文化的具体构成内容在各国是不同的、也是存在竞争的。 在乌克兰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通过多方努力,国家权威整体上覆盖到了所有领土范围,到1997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乌克兰周边各国纷纷承认乌克兰边界的合法性。⑧然而,新国家的共同政治文化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则显得问题重重。⑨按照现代政治的一般原则,从民族角度说,新国家应形成超越主体民族的国族建构(国族包含国内所有民族,尊重它们的权利与自主性,也明确其义务与权利边界),形成并巩固超越地区与民族差异的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在这一方面,乌克兰存在着政治实践的思路与努力,譬如1996年乌克兰宪法规定乌克兰民族由全体乌克兰人民组成,不分种族,并赋予少数民族以保留本族文化传统等权利。这里的乌克兰民族是国族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推进宪政⑩民主与政党政治建设,它们能够为现代国家提供超越地区、民族、宗教差异的同质性与秩序架构,它是现代的。但是在实践中,乌克兰政治精英们对乌宪法基础一直缺乏共识。(11)更为麻烦的是,乌克兰政治领袖在建构现代国家(国族)时,颇为自信地采用了“主体民族国家化”的方略(12)——以宪法确定乌克兰族的主体民族地位,极力推广乌克兰语,(13)大力挖掘与利用乌克兰族文化资源。 虽然乌克兰国家建设中的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国家化道路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张力,但一些观察家们一度对乌克兰国家建设颇为自信,即乌克兰不仅不会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而且其精英们的共识正在增加,其分离分裂因素日益可控。(14)实际上,乌克兰新国家建设中的主体民族主导与国族主导的对立是挥之不去的,因为“主体民族国家化”具有传统文化取向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民族排他性,它还面临部分已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族人对此不感兴趣的局面,因而实质上难以也无法为其现代国家提供文化同质性。 四、民主政治的不成熟: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的合流与冲突 在矛盾的现代国家(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建设设计下,乌克兰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它既是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又是2013年以来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 自1991年来,乌克兰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形成了若干特点,(15)它们都与民族政治存在直接与间接的关联。第一,乌克兰实施多党制,但缺乏领导性的、能够稳定全国政局的全国性政党,其政党体系属于小党体系。乌克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多党制,2002年约有120个政党,到2011年该国合法登记的政党约有190余个,形成了多党林立的局面。在议会选举中,上述政党中领先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得票率均不高(往往最大两党得票率之和不及46%),说明其政党制度属于小型政党体系。(16) 乌克兰小政党体系与乌克兰转型时期多元意识形态竞争共生存在着亲和性。从政治文化角度说,其根源是乌克兰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主流现代政治文化。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发展一度以自由主义思潮为主导,但这一自由主义主导只具有表层特点,实际上该国是多种思潮竞争共生的局面,稳定的现代国家认同一直未能形成。1991-1996年,乌克兰一直存在制宪危机,1996年乌克兰宪法出台,但其宪法共识非常薄弱。根据1996年宪法规定,议会代表就职前需要向乌克兰国家进行忠诚宣誓,但一些议员对此表示拒绝,拒绝宣誓的代表主要来自顿巴斯地区(占拒绝宣誓人数的44%),其次来自克里米亚(占拒绝宣誓人数的35%)。(17)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产甚为强大(特别是东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共产党一度是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1998年排名第一,2002年排名第二),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作用则日益上升。目前看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为流行且影响力最大的政治文化,而乌克兰境内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缠绕在一起,这导致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一定程度上合体了,但两者的合体对于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建构并不见得是好事。2014年2-3月基辅广场政治角逐中,几大主要反政府力量(反对亚努科维奇)——打击党、自由党、祖国党、右区(far-right)、乌克兰麦丹——具有程度不一的民族主义特点,其中自由党与右区的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厚,而自由党在最近四年乌克兰政坛中的崛起态势最为明显。 第二,在小政党体系背景下,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中生成了亲总统的党派联盟与反总统党派联盟的极化格局。在转型时期,乌克兰国内政治规范属性偏弱,权力政治高扬,国家的核心权力争夺围绕总统、总理与议会而展开。从2002年开始,乌克兰形成了亲总统党派与反总统党派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一政治极化是在小党体系下形成的,各方既有左派政党也不乏右派政党,(18)因此乌克兰围绕总统而形成的政治结盟与制衡是一种混合型结盟,是权衡性的现实主义利益博弈的体现,说明双方内部缺乏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共识,说明乌克兰国内政治(特别是国族建设)的规范性基础薄弱,它是乌克兰民主政治薄弱的体现,也是其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2004年“橙色革命”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政府与议会的斗争故事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其中乌克兰族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19)与俄罗斯族的亚努科维奇是主角,他们围绕国家权力划分和国家发展道路发生多次纠纷与争夺,在双方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支持者(往往各以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为核心)时常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于此,乌克兰大众广场政治与精英政治共生共振,不断催生出一幕幕街头政治高潮,却未能解决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多元民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协商出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底线政治共识,但它反映的是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同质性与基础共识的缺乏,或者说,乌克兰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往往具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特征。 下面从两个小案例来进一步展示上述特征。在尤先科执政的2006年5月,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允许参加北约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两周后美军只得撤离克里米亚,军演被迫取消。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达成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亦引发强烈反应。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而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则集会抗议。不成熟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刺激乃至煽动了乌克兰民族冲突,也为国家分裂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二,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选举习惯炒作与争论民族类议题,强化了乌克兰内部诸民族(ethno-national)的政治与文化边界,而未能有效塑造出整体性、包容性的国族意义上的乌克兰民族理念。观察家们发现,乌克兰2004年以来的总统选举进程中,不同候选人在民主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纲领与主张大同小异,各方争论、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编纂和语言权利等议题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单”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选民的偏好,即选民的选择更多地被迫聚焦于历史、文化等传统认同,聚焦于对候选人是否是“内群体”自己人的民族性认定。这意味着乌克兰民主政治的民族化,意味着乌克兰民主的含金量颇低,结果恰恰损害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譬如,2010年1月22日,卸任前的尤先科总统授予曾与纳粹合作因而颇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右翼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乌克兰英雄”称号,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发政治风波。俄罗斯族往往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族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大会、全乌“自由”联盟和季莫申科联盟给以积极评价,但乌克兰地区党、共产党则强烈批评之。俄罗斯与波兰也对此表示抗议,对班杰拉评议的国际争议一直延续到2014年3月的联合国会议上。(20) 不成熟的国家建构同时诱发了乌克兰合法性危机与认同焦灼。(21)美国皮尤论坛调研数据显示,乌克兰受调查者赞同转向民主的比例由1991年的72%下降到2009的30%,赞同乌克兰转向资本主义的比例由1991年的56%下降到2009的36%,赞同选择民主领袖的比例由1991年的57%下降到2009的20%。2009年,69%的受访者支持强势领导人,55%的人不赞成民主。(22)乌克兰不成熟的国家建构也导致了乌克兰知识精英在身份与认同方面存在着各种张力乃至危机。2011年夏季,在访谈58位乌克兰知识分子后,卡琳娜·克罗斯特丽娜(Karina Korostelina)区分出了他们的六种身份叙述:双重身份、亲苏联(pro-Soviet)、乌克兰人(Ukrainian)身份的争斗、承认乌克兰人身份、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叙述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身份叙述。这六种身份叙述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每一叙述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和证据支撑;其二是每一叙述关联着具体的群体权力与德性认知;其三是每一身份叙述意味着对其他身份叙述的排斥与拒绝。克罗斯特丽娜认为,这六种身份叙述中的五种是建立在原初性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这些身份与认同的对抗性特征明显,缺乏超越(超越地区、宗教、民族与语言)性政治认同是其共同弱点。(23) 五、民族自决权的边界与滥用:乌克兰危机迈向国家间危机 苏联解体时,以1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为基础形成了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基于民族自决权学说及其实践。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民族自决权存在着列宁与威尔逊两个解释传统,存在着国际法、国内法(及政策)、意识形态三种解释路径。从国家间关系上看,民族自决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基础,应更多地限制在《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规范之下。然而,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来看,不恰当运用民族自决权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环节。2014年3月6日,克里米亚推出“公投入俄”意向。3月7日,俄罗斯联邦会议正式通过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请求。3月11日下午,克里米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并计划于3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其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为:第一,您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之权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第二,您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24)公投结果显示,82%的克里米亚选民参与公决,约96%的选民表示支持入俄。克里米亚公投引发了重大的国际后果,联合国以及各国纷纷发表立场与观点,其中当事方俄罗斯的观点最为重要。2014年3月18日,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演讲分为历史、现实、国际法、强权、恳求、同胞、宣言等几个部分,其中前几个部分对于理解克里米亚公投的合法性尤为重要。 在历史部分,普京旨在阐明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在现实部分,普京抨击了乌克兰此次“政变”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恐俄者和反犹分子;指出乌克兰新“政权”上台提出声名狼藉的法令修改语言政策直接钳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认为乌克兰现在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而抵制政变的人很快受到镇压和惩罚的威胁,克里米亚首当其冲地面对这一挑战。在国际法部分,普京认为,克里米亚议会宣布独立,安排全民公决的举动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民族自决的章程。它既与乌克兰脱离苏联的逻辑与程序一样,也有西方制造的科索沃这一先例可循,也就是说它不违反国际法。在强权部分,普京抨击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主义及其在乌克兰危机中不负责任的玩火。(25) 从法理意义上看,国际法部分最为关键,因为它是公投的法理基础。普京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民族自决权”的威力,但它实际上无法给予公投以充分合法性,而且其间的民族自决权之滥用与过分使用将给国际安全与秩序带来巨大威胁与挑战。第一,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是第一原则,而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集体政治权利——在国际法层面而言是一个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附属性原则(即存在着殖民主义对民族的殖民)。虽然一些学者将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视为后殖民国家,其矛头指向历史上一些国家对乌克兰进行了殖民,但现在并无充分证据说明20年来乌克兰政府对东部地区的克里米亚进行了殖民(普京的演讲中也没有讲这一点),因此这一“入俄公投”的民族自决权基础并不牢固,且挑战了乌克兰的主权权利。第二,民族自决权也可以从国内政治角度找到其合法性。譬如苏联政治生活中承认民族自决权,包括当前的俄罗斯联邦也在国内政治中承认并实施民族自决权。但这一集体权利有着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的差异,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它往往包含着权力博弈(苏联与俄罗斯只给予了部分所谓有名分的民族以一定的政治自决权(26))的色彩,这意味着国内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权并不是普适性的权利。第三,民族自决权还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阐释。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具体主张,它并不具有国际法与国内法(国内政策)的规范性。与其说它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主张。倘若将这种主张作为一种普适性规范推广,那将彻底重构当前的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于法于理上都难以令人接受。毫无疑问,这一主张在政治动员上极具效率与鼓动性,因而常常为政治人物所倡导,但它实质上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因此,虽然普京从国际法上论述克里米亚公投属于民族自决,但国际社会多不承认之。但普京的演讲确实揭示出,大国往往利用它来达到各种目标,也就是说,各大国经常以双重标准的态度来对待民族自决,即以国际法掩盖其权力政治、民族主义政治的本质。而民族自决权的滥用与多维内涵也意味着乌克兰危机将日益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博弈中,乌克兰危机的国际性将进一步发酵。 六、走向失败的乌克兰:民族政治及其未来 一般而言,成熟的现代国家应是法理国家,就国内政治而言,它意味着权利政治高扬,而权力政治受到法理与权利的规约。从国内政治中的民族政治实践来看,它也包含着权利与法理意义上的实践以及权力政治意义上的实践,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前者更应该被倡导,后者更应受到限制。乌克兰近二十余年的政治实践旨在建立现代法理国家,它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它依托主体民族的国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实践,这是一个悖论。与这一悖论相关的是,乌克兰现代国家建构中出现的一系列特征(小党体系、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的对立、民主实践与传统民族政治合流)也包含了浓厚的权力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政治。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单显示,在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恰当的民族化趋向,它是乌克兰最小共同文化建设失败的表现,也促使乌克兰社会文化的民族分界意识日益浓厚。权力政治意义的民族政治在一国上下共振,很容易撕裂这个国家与社会,乃至使得其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极化、动荡甚至分裂。 乌克兰危机显示,该国已由原来经济转轨失败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失败,乌克兰已成为一个脆弱的国家,面临着主权与领土完整不保的重大威胁。从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在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中,以民族冲突为核心的民族问题往往会在失败国家的失败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并引发巨大的负面社会后果,乌克兰危机只不过是新增加的案例罢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失败国家与民族问题、民族冲突的复合因果关系:第一,失败国家可能导致民族冲突。第二,失败国家由于其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必然导致该国原来潜在的民族冲突更加彰显。第三,民族冲突等因素导致并进一步加剧国家走向失败。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进程看,这三类因果关系都是存在的,其中第二种与第三种关系更加凸显。从这一意义说,乌克兰危机的本质在于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该从国家建设层面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14-03-31] [修回日期:2014-05-15] 注释: ①关于两个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极化的早期论述,参见Tatiana Zhurzhenko,"The Myth of Two Ukraines," Eurozine,2002,http://www.eurozine.com/pdf/2002-09-17-zhurzhenko-en.pdf。 ②1954年赫鲁晓夫相对随意地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克里米亚便掀起“回归俄罗斯运动”,1994年俄罗斯族的克里米亚总统梅什科夫曾强行推进克里米亚独立然后加入俄罗斯,而俄罗斯政府表态不赞成方使危机化解。 ③参见金雁:《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载《浙江学科》,2005年第5期,第64-70页。 ④沈允:《乌克兰民族问题》,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4期,第93-95页。 ⑤杨玲:《乌克兰大选中的民族因素》,载《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5期,第28-29页。 ⑥乌克兰族的尤先科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进对苏联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历史清算。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再一次唤起人们对那一事件的痛苦记忆。关于大饥荒的记忆与政治化解读与争议,参见Mykola Riabchuk,"Holodomor:The Politics of Memory and Political Infighting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Harriman Review,Vol.16,No.2,2008,pp.3-9; David R.Marples,"Debate Ethnic Issues in the Famine of 1932-1933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Vol.61,No.3(May 2009),pp.505-518。 ⑦参见[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⑧2014年3月18日,普京总统在关于克里米亚公投的演讲中对于乌克兰边界有不同的认知。 ⑨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曾在演讲时说,乌克兰上层人士大多不知道如何驾驭乌克兰。乌克兰学者也曾质疑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不懂得如何引领乌克兰。参见Nicole Gallina,"Ukraine:Nation-Building Revisited-The Ukrainian President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Politics," Political Sphere,No.15,2011,pp.1-12,http://nicolegallina.com/docstexts/13_text_ukraine_identity_2011_ng.pdf。 ⑩1991-1996年,乌克兰面临着制定宪法的危机。 (11)Nicole Gallina,"Ukraine:Nation-Building Revisited-The Ukrainian President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Politics," Political Sphere,No.15,2011,pp.1-12. (12)参见谢立忱:《乌克兰国家的民族建构问题:根源、成就与挑战》,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第119页。 (13)这意味着乌克兰在国家建构和民族意识重建过程中施行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文化政策,即试图把俄语从乌克兰教育、政府与媒体系统中排挤出去,乃至彻底根除,这触发了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的文化与政治冲突。2012年,乌克兰出台了《关于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根据该法案,俄语在乌克兰因至少10%居民以俄语为母语的地区获得地区官方语言地位。2014年2月,该法案被乌克兰议会取消。 (14)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评论家预测乌克兰会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参见[美]但罗曼·斯波尔鲁克:《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反映》,载《今日东欧中亚》,陈钜山摘译,2000年第1期,第38页。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人比较乐观地认为,乌克兰精英层面对乌克兰国家建构共识在不断增加。参见Taras Kuzio,Ukraine:State and Nation-building,London:Routledge,1998。 (15)关于乌克兰政党制度的详细阐述,参见强晓云:《乌克兰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第25-28页。 (16)一般说来,凡得票率低于15%的政党,都属小党范畴。政治学专家梅勒认为,如果议会选举中有两个政党得到超过八成支持的话,则该政党体系属于大党体系,若有两个政党达到65%,则该政党体系属于中党体系,如得票最多两党只有42%及以下,则属于小党体系了。参见强晓云:《乌克兰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第27页。 (17)谢立忱:《乌克兰国家的民族建构问题:根源、成就与挑战》,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第121页。 (18)Geir Flikke,"Pacts,Parties and Elite Struggle:Ukraine's Troubled Post-Orange Transition," Europe-Asia Studies,Vol.60,No.3(May 2008),pp.375-396. (19)尤先科与季莫申科两者是“橙色革命”中的盟友,但后来两者政见,特别是乌克兰发展道路选择上也出现分歧。前者坚持乌克兰走建立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欧洲发展道路,而后者实质上主张以“家长作风”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独特发展道路。季莫申科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最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通话中。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与前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副局长涅斯托尔·舒弗里奇的电话录音被曝光,通话时间是2014年3月18日23时17分,在录音中季莫申科提出,“是时候拿起武器杀死该死的俄罗斯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了”,说到在乌克兰的800万俄族人,她说“应该直接用核武器弄死”。参见《季莫申科致歉此前称用核武弄死800万俄族人》,载《环球时报》,2014年3月26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930520.html。 (20)2014年3月3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尤里·舍格耶夫在联合国会议上声称,二战时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说,“由苏联代表在纽伦堡审判中提出的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指控是被操纵的”。俄方指出,“乌克兰代表类似的言论侮辱了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牺牲的英雄,以及俄罗斯人民、乌克兰人民、犹太人民、波兰人民以及其他受纳粹暴行支持者伤害的人民”。参见翟潞曼:《乌克兰在联合国为纳粹分子翻案激怒俄罗斯》,2014年3月5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880938.html?qq-pf-to=pcqq.c2c。 (21)有学者从转型国家角度探讨了乌克兰的国家认同状况,参见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第1-9页。 (22)Karina Korostelina,"Facilitating Nation Building in Ukraine," Newsletter Issue,Vol.5,2011,http://scar.gmu.edu/newsletter-subject/facilitating-nation-building-ukraine.更为系统的论述,参见Karina Korostelina,"Ukraine after 20 Years of Independence:Models of Development,Narra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and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Power," 2011,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ukraine/08561.pdf。 (23)Karina Korostelina,"Facilitating Nation Building in Ukraine," Newsletter Issue,Vol.5,2011,http://scar.gmu.edu/newsletter-subject/facilitating-nation-building—ukraine. (24)1992年,克里米亚议会先后通过《克里米亚国家独立法》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此后,由于乌克兰政府的反对,该宪法被取缔。 (25)《普京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演讲》(观察网独家全文翻译),2014年3月18日,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4_03_19_214922.shtml。 (26)在苏联的政治实践中,有名分的民族(tutilar nation)指拥有政治地位的民族,它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建立了不同级别的自治政府。标签:政治论文; 克里米亚论文; 乌克兰危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俄罗斯总统论文; 波兰总统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乌克兰冲突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乌克兰东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