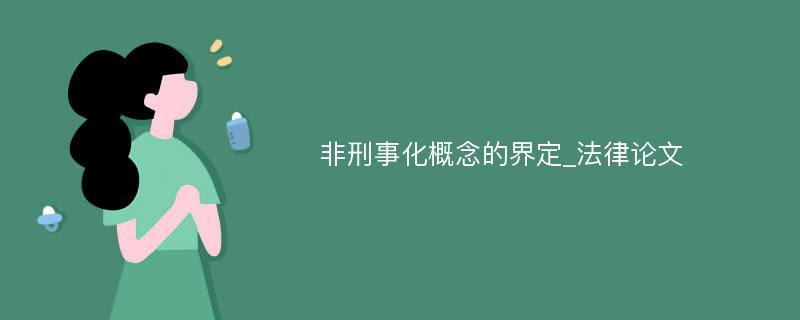
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1-0093-0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端于欧美的非犯罪化运动促成了各国关于非犯罪化的广泛实践,作为这一运动的成果,欧美国家对非犯罪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反观建国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非犯罪化历来不受重视,非犯罪化作为犯罪化的反方向张力对刑法健康发展的重要价值受到严重的忽视。关于非犯罪化不多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个罪的非犯罪化问题,而对非犯罪化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却付之阙如。因为对非犯罪化的概念缺乏明确的认识,非犯罪化有时被与合法化等同使用,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等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也缺乏清晰的厘定。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犯罪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分析,立足于我国大陆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界定非犯罪化的概念。
一、关于非犯罪化概念观点的述评
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三个:
1.欧洲委员会的《非犯罪化报告》认为: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对特定行为的刑罚制裁范围收缩的立法过程。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使被非犯罪化的行为完全合法和获得社会的认可;二是非犯罪化的行为虽然没有获得法律或者社会的认可,但国家对这些行为已持宽容或者态度中立的立场,如卖淫的非犯罪化;三是国家不以刑罚手段干预被非犯罪化的行为,而是选择对这种行为不作反应,留待当事人自己选择处置的方式,或者以刑罚之外的其他手段对这些被非犯罪化的行为作出反应。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对特定行为的正式反应(表现为刑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行为减少了其反应的现象。事实上非犯罪化的主要途径主要有将轻微犯罪行为交由警察机构之外的机关处理、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起诉、法院科处最低限度或者象征性刑罚等。[1]166
2.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非犯罪化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停止对其处罚,因此,它包括变更从来都是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现状,而代之以罚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处罚的情况。非犯罪化可分为取缔上的非犯罪化、审判上的非犯罪化和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取缔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罚法规虽然存在,但因调查以及取缔机关不适用该刑罚法规,事实上几乎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又称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审判上的非犯罪化是指通过刑事审判而进行的非犯罪化,也称“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它以通过变更判例,变更刑罚法规的解释和适用,将从来均被处罚的行为今后不再处罚为内容;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通过变更或废止法律而使过去被作为犯罪的情况不再是犯罪。[2]88
3.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刑事立法政策上的去犯罪化,有五种方法。其一是除罪化。除罪化是指透过刑事立法手段,对于刑事实体法明定的犯罪行为,自刑法规范中加以删除。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纯的除罪化,即不另设替代性的制裁,单纯将某特定犯罪行为加以除罪化,删除其在刑事实体法中的制裁规定,使其从刑事制裁法体系中消失;二是改成民事不法的除罪化,即以民事制裁替代原先的刑事制裁,亦即对于罪责轻微的微罪,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替代刑罚的法律效果,将刑事不法行为改成民事不法行为,而予除罪化;三是改成行政不法的除罪化,即以行政制裁替代原先的刑事制裁,而将某特定犯罪行为加以除罪化,亦即删除制裁特定犯罪行为的刑法条款,并将该行为的制裁规定改行规定于秩序违反法之中,赋予秩序罚的法律效果,将该犯罪行为除罪化,而由刑事不法行为改成行政不法行为。其二是除刑化。除刑化是指透过刑事立法手段,对于刑事实体法明定的犯罪行为若具有法定要件者,则规定得舍弃刑罚,使违犯该犯罪的行为人虽仍成立犯罪,并宣示其罪责,但却免受刑罚的制裁。其三是缓刑。其中包括暂缓刑罚的宣告和暂缓宣告刑的执行。其四是增设追诉要件。增设追诉要件而予去犯罪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针对本属非告诉乃论的特定犯罪,因其行为的轻微情状而明定必须告诉乃论。其五是不予追诉。不予追诉是刑事程序法上的去犯罪化方法,具体包括舍弃追诉或停止程序和暂时舍弃追诉与暂停程序。[3]133
比较以上三个概念,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欧洲委员会所讲的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其实相当于大谷实教授所说的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林山田教授所说的除罪化。只是欧洲委员会和林山田教授对这一非犯罪化的定义着重于非犯罪化的结果,将经过立法非犯罪化后的结果分为三种情况,而大谷实教授着重于非犯罪化的过程描述。第二,欧洲委员会所说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相当于大谷实教授所认为的取缔上的非犯罪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既包括了侦查和起诉阶段的一些非犯罪化制度,如不起诉等,也包括了审判阶段法官通过对刑法作出新的的解释以及运用一些刑法制度如缓刑等而实现的非犯罪化;相当于林山田教授所说的暂缓刑罚的宣告、告诉乃论和不予追诉。第三,欧洲委员会和大谷实教授的分类是从非犯罪化发生的领域,即立法和司法领域这个角度对非犯罪化进行的分类,而林山田教授是从各种具有非犯罪化效果的刑事法制度的角度,即非犯罪化的制度内容的角度对非犯罪化进行分类。事实上,林山田教授所说的去犯罪化的制度,除了除刑化和暂缓宣告刑的执行之外,大致分别可归入欧洲委员会所说的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大谷实教授所说的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取缔上的非犯罪化。第四,林山田教授认为除刑化和暂缓宣告刑的执行属于去犯罪化的内容,而欧洲委员会和大谷实教授并不认为这两个制度属于非犯罪化的内容。总之,欧洲委员会的《非犯罪化报告》和大谷实教授对非犯罪化的界定大致相同,但与林山田教授所讲的去犯罪化有较大差别。
比较和分析上述三种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表述还引申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除刑化和缓刑是否属于非犯罪化的内容;其二,非犯罪化和去犯罪化有何区别。笔者认为:除刑化通过立法手段只除刑不除罪,因此不应属于非犯罪化的内容;缓刑包括暂缓刑罚的宣告和暂缓刑罚的执行,暂缓刑罚的宣告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应属于非犯罪化的内容,①而暂缓刑罚执行因为已经作了有罪宣告,只是没有执行刑罚,因此不应属于非犯罪化的范畴。至于非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后文将有交代。
此外,学界还有其他一些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论述:
1.日本学者森下忠教授认为:所谓非犯罪化,目前国家间尚未达成统一见解,大致有广狭二义:(1)狭义见解,认为非犯罪化不只放弃刑罚且亦不以行政罚处之,而成为适法行为;(2)广义见解,乃对于原为科处刑罚之犯罪行为,放弃刑罚而不再视为犯罪之意,而改以行政罚处之。[4]189
按照一般的理解,概念的狭义的见解应该是广义见解所能包含的内容。但是,单纯从字面含义而言,上述广义见解和狭义见解之间似乎并非包容的关系。如果这正是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则颇让人费解。笔者在此的评述只能是基于以下认识进行:狭义的非犯罪化是指将原本的犯罪行为改为适法行为,广义的非犯罪化不仅如此,还包括将原本的犯罪行为改为行政违法行为。这一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将非犯罪化界定为两种情况,既犯罪的合法化和行政违法化,只是没有指明这样的非犯罪化是发生在立法领域还是亦可发生在司法领域。如果这一活动既可发生在立法领域,也可发生在司法领域,则该概念不仅指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而且包括刑事司法领域的非犯罪化,就基本与欧洲委员会《非犯罪化报告》和大谷实教授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相同。如果仅限于立法领域的话,则这一界定失之于片面。
2.我国台湾学者许福生教授认为:台湾学者一般将广义的非犯罪化与广义的非刑罚化统称为除罪化。至于除罪化的形态,则包括:(1)立法上不除罪而只除刑之除刑化;(2)立法上既除罪又除刑之除罪化;(3)司法上之除罪化,亦称裁判上之除罪化,乃指透过司法实务判例的变更,将其原来为刑法处罚的行为,解释为以后不受刑罚处罚的行为。(4)事实上之除罪化,亦称取缔上之除罪化,乃指刑罚法规尚属有效而继续处罚,只是执法机关基于某些理由,事实上很少适用此法规加以处罚。[4]190
笔者认为,将非犯罪化称为除罪化似无不可,但将非刑罚化称为除罪化却让人费解。因为资料所限,笔者并不确定许福生教授在此所指的广义的非犯罪化和广义的非刑罚化的具体内容为何。但从其所述除罪化的内容来看,这里的除罪化基本相当于林山田教授所说的去犯罪化。至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除罪化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下文将有详论。
3.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认为:非犯罪化的概念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仅包含了刑法制度的消失,而且意味着所有替代性反应的不复存在。换言之,是从任何一种刑事政策模式过渡到零点。非犯罪化既可能源于某种官方的选择即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也可能源于某种一般的实践即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也在酝酿者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不论非犯罪化的起因是官方的选择还是不干预主义的一般实践,非犯罪化总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战略。如果非犯罪化是社会真正企盼的,就是容忍的政策;如果非犯罪化是一种需要加以承受的失败,表明干预的无能为力,那么就是放弃的政策。[5]254
这个概括立足于欧洲委员会的《非犯罪化报告》,是关于非犯罪化的一般原则性概述,从中很难看出非犯罪化的具体内容,不过其中隐含的一些观点仍对我们界定非犯罪化的概念具有启发意义,那就是对非犯罪化的概念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体现非犯罪化思想和精神的刑事法制度都应属于非犯罪化的内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认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官方的选择,而源于某种一般实践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就不是官方的选择。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尽管不像立法上的非犯罪化那样彻底(这些制度只是提供了司法实践进行非犯罪化的可能),但也是有制度依据的,未必就不是官方的选择。
4.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李希慧教授认为:非犯罪化是指立法者将原本由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从法律中剔除,使其正当化或者行政违法化。[6]36
这个观点来源于作者对中国刑法典完善的思考,因此,该观点不可能是关于非犯罪化的准确概念,其发表的语境决定了其不完整性。如前所述,非犯罪化不仅有法律上的非犯罪化,还有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因此,仅将非犯罪化限制在刑事立法领域是不全面的。
5.我国学者王勇认为: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将一些对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事惩罚但又被现时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不再作为犯罪或通过司法不予认定犯罪,从而对它们不再适用刑罚。[7]323
该观点对非犯罪化的界定涵扩了立法和司法领域,是可取之处。但将非犯罪化的对象仅仅限定于轻微犯罪,是非常片面的。不论是非犯罪化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刑法规定,都说明非犯罪化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微罪领域。②
6.我国学者游伟、谢锡美认为:非犯罪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非犯罪化又称本来的非犯罪化,仅指不科处包括行政处罚在内的所有国家制裁的情形,换言之,就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原来规定的已失去了继续存在必要的犯罪,直接将该行为从法律规定中予以撤销,使其合法化。广义的非犯罪化是指对一直以来被科处刑罚的行为不再用刑罚予以处罚。广义的非犯罪化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对原来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予以合法化;二是对原来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予以行政违法化,即对这类行为不再以刑法调整,而改用行政法规去调整;三是对具体的危害行为(也包括少数的某类行为)通过司法的程序不把它当作犯罪处理。[8]347
该观点将非犯罪化分为广狭两义,狭义的非犯罪化就是指合法化,广义的非犯罪化是指合法化、行政违法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关于广义的非犯罪化的界定概括了非犯罪化的主要内容,前两者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后一者包括了事实上非犯罪化中的告诉乃论制度、不起诉制度等。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只是这种对非犯罪化的分类还值得商榷。
二、非犯罪化与相关概念之厘定
起源于英国的非犯罪化运动,在英语中称作decriminalization,非犯罪化是我国大陆地区的通常译法。从上文评述可见,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并没有使用非犯罪化这一词语,相近的称谓有去犯罪化、除罪化、非罪化;还有一些与非犯罪化相关的概念:除刑化、合法化、非刑事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等。该如何统一非犯罪化概念的使用以及界定非犯罪化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问题。在学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刑罚化与非犯罪化是内容有交叉的并列的两个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关于非犯罪化,狭义的见解是指对特定行为不只放弃刑罚且亦不以行政法处之,而改为适法行为;广义的见解是指对原科处刑罚的犯罪行为,不再认为是犯罪行为,而改为行政违法行为。关于非刑罚化,狭义的见解是指对于犯罪行为,以刑罚之外制裁手段代替刑罚;广义的见解是指对于一些轻微犯罪,放弃刑罚处罚,改以行政法处之,即将其改为行政违法行为;最广义的见解认为还包括将观护制度作为独立处分的保护观察以替代刑罚处罚,或以缓刑回避实体刑罚之执行。[9]40另一种观点认为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非刑罚化是非犯罪化的内容之一。如前文所述林山田教授和许福生教授的观点。
如果从“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的立场上看,非刑罚化就意味着非犯罪化,但事实上,刑罚只是犯罪的一种主要的法律效果而已,犯罪还可能有刑罚之外的其他法律效果,因此,非刑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非犯罪化。如果从非犯罪化后当然也就没有了刑罚的后果的角度看,非犯罪化也就意味着非刑罚化,那么非刑罚化这一概念似乎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从最广义的角度看,被非刑罚化的行为既可以仍是犯罪行为,也可能被非犯罪化了,此时非刑罚化包括了非犯罪化的内容,那么非犯罪化就是非刑罚化的内容之一,非犯罪化这一概念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这两个概念无疑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上述三种假设都存在弊端。笔者认为,宜从狭义的立场理解非刑罚化这一概念,即非刑罚化是指对原本被赋予刑罚效果的犯罪行为,以非刑罚的方法代替刑罚。也就是说,被非刑罚化后的行为仍是犯罪行为,只不过对这些行为采用了非刑罚的处罚措施。这样界定符合一般关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理解习惯。
其次是关于非犯罪化与非刑事化的关系问题。非刑事化一词可以包含多种含义,例如,用一个国家性的网络(如行政的、民事或调解网络)来代替刑事网。欧洲委员会的《非犯罪化报告》揭示了非刑事化概念的多重含义,其中区分了刑法体系退缩的好几种情况,非刑事化即是其中的一种。冯德克肖夫(Van de Kerchove,1987)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他根据学者们的用法,归纳了非刑事化与非犯罪化两个词汇的八点不同。[5]219在我国,学者对这两个词汇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非刑事化与非犯罪化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非刑事化这一概念的外延比非犯罪化要广,非刑事化包括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两个方面。[8]347另有学者认为:非犯罪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既包括除罪又包括除刑的情况,但用非犯罪化容易给人不包括除刑不除罪的情况的错觉,因此,应该用非刑事化一词取代非犯罪化一词的使用。[10]笔者认为,如果将非刑事化理解为刑法体系的逐步退却而由行政的、民事的或者调解的变量取而代之的话,则非刑事化即是非犯罪化。但是,从广义上讲,非刑事化应该还包括了除刑不除罪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实质上也是收缩刑事法网的一种方式,只是与除罪的情况程度不同而已。因此,笔者赞同前述第一种观点,即非刑事化包括了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第三,关于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关系。我国有学者提出轻刑化的概念,认为轻刑化包括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将一些对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事惩罚的但又被现时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不再作为犯罪或通过司法不予认定为犯罪,从而对它们不再适用刑罚。轻刑化是指通过立法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从而达到整个刑事制裁体系的缓和化。[7]323笔者认为,应该从轻刑化的本来含义去理解,即轻刑化是指降低犯罪的刑罚幅度,使整个刑事制裁体系走向缓和,被轻刑化后的行为仍是犯罪。因为轻刑化只是降低了刑罚幅度,犯罪行为的刑罚效果仍然存在,因此,轻刑化既不与非犯罪化发生交叉,也不与非刑罚化发生交叉。不过轻刑化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都体现了相同的刑事政策理念,是“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中“轻轻”一极的体现。
最后是非犯罪化与合法化的关系。非犯罪化是将原本是犯罪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对待和处理,至于该行为在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后如何处理,则要根据该行为的具体性质而定,具体而言,有四种选择,即: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对该行为不予评价(即态度中立)。可见,合法化只是非犯罪化的一个结果或内容,而不是非犯罪化的全部。
此外,在笔者看来,除刑化相当于非刑罚化,而去犯罪化、除罪化、非罪化都是和非犯罪化相同的概念。
三、非犯罪化的概念之我见
从前文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评述可见,学界对非犯罪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笔者认为:要给非犯罪化下一个科学、全面的定义,必须遵循以下三个指导思想:第一,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谦抑和法益保护的刑事政策精神,因此,非犯罪化的概念应该涵扩体现这一刑事政策精神的一切刑事法制度;第二,非犯罪化是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一项刑事政策,因此对非犯罪化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刑事立法领域;第三,各国的刑事法制度毕竟有所不同,因此非犯罪化的具体制度或者内容可能会存在差异,非犯罪化的概念应立足于本国的刑事法制度。
在我国的刑事法实践中,不仅存在通过立法活动将原本是犯罪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的情况,如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的非犯罪化、投机倒把罪的部分非犯罪化等,也存在通过司法活动将某些犯罪非犯罪化的情况,如刑事诉讼中的不予立案制度、不起诉制度和自诉制度以及通过审判活动实现对特定犯罪的非犯罪化。当然,国外的暂缓刑罚宣告制度和缓予起诉制度,以及如前文所述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认为的除刑化,并不属于我国(大陆)非犯罪化的内容。欧洲委员会《非犯罪化报告》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界定是欧洲非犯罪化理论和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大谷实教授关于非犯罪化概念的界定是立足于日本的刑事法制度和实践,这两个概念尽管有差别,但为非犯罪化构建了正确的制度框架。借鉴这两个非犯罪化的概念,立足于我国的刑事法制度,笔者认为: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规定或者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一定的犯罪不再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虽然刑法上关于一定行为的罪刑规范没有发生变化,但事实上该行为却没有被司法机关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通过立法活动实现的,因此亦可称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从其结果上看,可分为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态度中立四种情况。合法化是指对刑法原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手段将其改变为法律认可的行为;行政违法化是指对刑法原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活动将其改变为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民事违法化是指对刑法原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活动将其改变为违反民法的行为;国家态度中立是指对刑法原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通过立法活动将其排除出刑法干预的范围,该行为虽然没有获得国家的认可,但国家也不对其进行违法评价,而是持宽容的立场,即态度中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分为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追诉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关于一定行为的罪刑规范没有发生变化,但追诉机关通过不予立案和不起诉等制度而不将该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审判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关于一定行为的罪刑规范没有发生变化,但审判机关通过变更罪刑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将从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该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在我国的刑事法制度和实践中,对犯罪的追诉和审判都属于司法活动的范畴,因此,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合称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
[收稿日期]2006-12-14
注释:
①暂缓刑罚宣告又称为宣告犹豫制度,是指审判机关经过审判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暂时不宣告其有罪,而在一定期限内交有关机关对行为人进行监督考验的制度。如果行为人在此考验期限内遵守所规定的条件,便不再作有罪宣告;如果没有遵守所规定的条件,则作有罪宣告。我国的刑事法制度中没有暂缓刑罚宣告这一制度,因此,我国的非犯罪化制度并不涉及这一内容。
②非犯罪化作为一种刑事政策选择,起源于对道德犯罪的非犯罪化。笔者认为,对我国的刑法典来说,不仅存在轻微犯罪的非犯罪化问题,也存在道德犯罪的非犯罪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