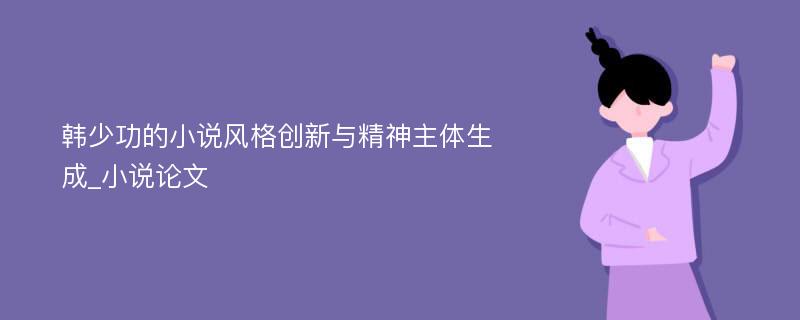
韩少功的小说文体革新与精神主体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主体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韩少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少功小说文体破坏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远离小说的过程。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显然是文体“越界”行为最多的人,他不喜欢重复自己,“自我重复不是一件能让人打起精神的事情”①,他甚至公开宣称“我喜欢冒险的写作状态”②,希望能实现“文体破坏”与“文体置换”目标。③文体上的频频“出轨”吸引了论者关注,但对文体过多关注也遮蔽了诸多关键问题。对韩少功而言,文体不仅仅是落实到形式层面的因素,而是内心一种精神牵引,文体之“变”和精神追问之“常”构成了作为整体的韩少功,显示了他写作行为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 以1985年为界,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尽管在“写什么”上,有着固定的观照对象(“知青经历”始终缠绕其笔下),但在“怎么写”上,却体现了明显的文体意识。直到《马桥词典》出现,他对小说文体的拆解才真正开始,此后的《暗示》走得更远。在不断越过小说边界进行文体破坏后,韩少功似乎很难专注于严格意义的小说写作。 如果说《马桥词典》的出现,表达了韩少功针对传统小说本质化因果关系叙事理念的不满,那么,我们可以将他写作的动因归结到对“怎么写”这一技术问题的思考,及写作方式的调整。到写作《马桥词典》,韩少功明确表达不满,他说:“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④对韩少功而言,“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就是即他“文革”和伤痕反思时期的小说。“一个好的情节永远不可能是秩序井然、完整统一和绝对单纯的,原来的混乱、杂多和繁复的某些成分必须保留,否则,情节就会缺乏生活的气息。”⑤作家通过叙事理念的掌控,凌驾于生活和作品之上的姿态,激起了韩少功的不满,以致在《马桥词典》正文中,他总是控制不住地表达创作动机,以表明对传统小说因果铁律的坚定怀疑,和对传统小说粗暴处理生活的反感。 《暗示》显然走得更远,也许,其极端的文体破坏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因。他文体的打破显然不仅仅停留于对小说文体的不满,更何况,他承认,“人物与情节一直是小说的要件,今后恐怕还将是小说的要件”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承认,形式意味着和我们身边历史的对话能力,那么,自80年代开始的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实验,正意味着这种对话能力的逐渐增强和拓展,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复杂性的深刻把握”⑦。确实,对韩少功而言,尽管他珍惜小说家的名号,但他更为看重的却是和“身边历史”的对话,解构传统小说文体,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韩少功作为小说家的面貌,其身份的改变成为他在和身边历史对话过程中,寻求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之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小说家”向“小说家和散文家”并置的转移。 韩少功对自己作品的文体归属,显然有过认真思考,他借助《暗示》,曾坦率表达:“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⑧韩少功通过《暗示》所进行的“文体破坏”,其用意是要打破小说类似公园的形式桎梏,在给读者提供更为开放空间的同时,也给自己开拓更为开阔的表达领地。只要稍稍留意到《暗示》所关注的主题、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探讨的问题,就可发现,传统的小说形式,根本不可能给他提供如此自由而开阔的空间,而他之所以在同一文本中,要涉及如此多的内容,恰恰意味着韩少功想通过完整的形式,来表达对世界的整体思考,但文本所呈现的最后结果,却让他无奈发现自己已无法把握世界重心,无法对斑驳世界作出整体解释。《马桥词典》固然以词条形式打破了小说边界,但时空的完整、小说要素的保留,使得它依然是一座充满文学氛围的诗意公园,而《暗示》随笔、杂感、笔记小说共存的混合文体特征,则明晰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打破小说文体,丧失通过小说方式建构世界可能后,韩少功终于通过《暗示》的文体实践,找到了通过随笔体来建构另外世界的可能,“现代社会里传媒发达,人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一个文学写作者描述这些事可能是不重要的,而描述这些事如何被感受和如何被思考可能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有时会放弃传统叙事模式的原因。我想尝试一下将笔墨聚焦于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前人的笔记体或者片断体”⑨。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自《马桥词典》开始到《暗示》成熟的“文体破坏”的创作实践,更深刻的原因是韩少功已经无力从对世界的观照中,获得一种本质化理解的精神困境。《暗示》“笔记体”或者“片断体”的写作方式,既是他主动思考写作方式的结果,更是他陷入精神困境后的无奈选择。当韩少功始终站在思想前沿,力图通过思考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时,无法解读的现实和无从表达的生活,成为他遇到的现实难题,并在这一难题逼迫下,彻底放弃了对小说边界的坚守,选择了《暗示》般驳杂的表达方式。对韩少功而言,小说文体不仅是写作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写作行为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意味着坚守小说纯粹之途的步步退却,和精神追问的步步逼近。韩少功文体之“变”的背后是他精神追问的持久和恒定,而他对小说文体的最终放弃,终于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困境。 对韩少功写作行为和生存实践之间深层联系的思考,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整体上考察韩少功的思想资源。他丰富的文学实践、文学行为和文学写作互为话语的状态无不提醒我们,韩少功驳杂背后,存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精神内核,包含着可以开启他文学世界的精神密码。从当代思想流变的层面而言,韩少功的创作凸显了当代作家必然面临的三重思想资源:西方理论资源烛照下的“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悖论表达;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其中,“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表现在韩少功创作中对地域文化和民间智慧的重视,以及人格特质中担当情怀的承续,而并未从表现对象的恒定和理论视野上对韩少功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论述另外两重思想资源。 1985年前的韩少功,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和狂热之后的清醒,开始转入到热烈的现代化追寻中,从否定狂热的革命到为现代化变革欢呼,显示了他根植于时代共识之中的对现代性追寻的热情。尽管1985年的《爸爸爸》呈现出了全新的艺术面貌,但依旧未脱离此前他小说观中对生活本质化理解的窠臼。90年代始,韩少功明朗的精神姿态犹疑起来,并和他文体实践获得了内在同构:一方面,他大量的随笔创作,体现了“对现代化、启蒙、文化寻根,对权力、资本、媒介,对科技、人文以及西方的一些重要思想家等”⑩的重要思考,较早反思了80年代现代性想象实现以后的弊端;另一方面,他通过文体破坏,以《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具体文本实现了对本质化创作的扬弃,从作家本位呈现了现代性反思。如果说,韩少功1985年以前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生活本质化的理解,显示了根植于时代共识之中的对现代性的追寻热情,那么,《马桥词典》《暗示》对情节的放逐,则旗帜鲜明地昭示了韩少功对此前本质主义的怀疑,以及对现代性蕴含的确定性、整体性的反思。当他通过小说文体破坏宣告现代性破产的同时,也就注定他不可能通过小说的形式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而找到其他表达方式,几乎成为他此后作为作家的必然选择。既然“想得清楚写散文,想不清楚写小说”,那么,散文和小说对韩少功而言,不过是他“和身边历史对话”的不同方式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在韩少功思想资源版图中,“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也是重要一翼,这一点从韩少功创作谱系性中创作对象的恒定性,即对知青(“文革”)经验的珍惜和挖掘,可以获得印证。韩少功始终将此置于“精神事件”的层面,并总是力图从中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使得短短六年的知青生活,足够构建作家坚固的经验堡垒,并使得韩少功的表现对象呈现出同一性特征。如果说,西方理论资源开启了韩少功思想的窗户,那么,中国独特的革命实践经验,则成为其思想立足的基点。两者的相辅相成,使得韩少功没有止步于展示经验的故事讲述者,而是成长为立足大地的真正思考者。韩少功尽管表现的对象从未离开知青经历,但却永远无法简单归为知青作家。可以发现“知青(‘文革’)经验”始终是其表现的重点,近两年来的《日夜书》和《革命后记》的完成,展现了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思考所达到的高度。结合韩少功隶属“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并且深入骨髓的“知青经历”的生命体验,可以发现,他多年来思考的基本视域始终没有脱离凝聚了现代性目标的“革命”和统领了反思现代性冲动的“发展”两大命题。如果要用更为简洁和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当下对两者的思考,则是韩少功提到的“脑坏了,心坏了”(11)。 “脑坏了”意味着知识生产出了问题,意味着气势汹汹、自信满满的承载于知识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传承遇到了根本困境;“心坏了”则意味着文明困境的十字路口,人心在一片荒芜文明前景下,内心信念的坍塌,意味着现实困境中价值重建遇到了麻烦。90年代以来,韩少功全部创作,无论是小说、随笔,几乎都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回应。韩少功对知识生产的危机有着很高的警惕,“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12)。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自然更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小说也是创造知识,只是这种知识与我们平时理解的知识不大一样。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要叛离或超越这些所谓科学的规范”(13)。既然“小说也是创造知识”,那么对小说文体的破坏就是对既定知识规范的破坏,“克服危机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14)。由此看来,韩少功文体破坏的行为,其实正是他意识到“脑坏了”之后,作为一个小说家,力所能及的补救和介入,对知识危机的担忧和化解危机的强烈愿望,构成了韩少功文体探索背后的精神动因。 在“革命”乌托邦破碎、精神大厦倒塌后,如何修复千疮百孔的人心,如何平复深受伤害的心灵,如何避免极易被二元对立思维控制,以至于流于义愤从而在寻找价值重建的道路上再次迷失的情况出现,韩少功的态度尤其谨慎,“80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15)作为亲历革命大厦倒塌的一代人,在目睹革命的狂热、极端和对革命声讨的同样狂热、极端后,他的精神立场显示出了迷失背后难得的审慎和理智,显示了知识分子难得的充满智慧的反思姿态。这让韩少功的面目在思想界“左”“右”对立的语境中变得模糊,并且极易招致简单而愤激的指责,“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故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囿于自言自语”(16)。他仿佛戴着X光的眼镜,总是能看到表象背后的真相,看到灿烂背后阴暗的一面。“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17)韩少功从80年代的自信明朗向90年代的犹疑审慎的转变,意味着他对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思想资源有限性的怀疑,意味着他在打量价值重建的路上对知识分子精神姿态的思考和调整,也意味着他在价值重建的困境中企图找到新的思想资源努力。事实上,作为一名有着强烈实践品格的作家,韩少功在对个体思想资源反思、清理过程中,也一直以生命实践形式,身体力行地通过一些小说家之外的社会实践,给新的思想资源的生长找到一线空间。 随着90年代知识界分化加剧,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犹疑和审慎变得独特起来,在热闹非凡有着共识的80年代的思想剪影中,他作为个体的孤独越来越显影出边缘和逆行的姿态。除了对怀疑的确定,对理论实践品格的强调几乎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最为重要的特点。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18),“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19)。 他立足知识分子立场,曾雄心勃勃地企图给中国思想界搭建交流平台,事实上,无论是非常成功但很快折戟的《海南纪实》,还是曾经引起中国思想界震惊的《天涯》,都包含了韩少功青壮年时期,企图以入世的热情来重建价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的结果除了产生思想界的热闹喧嚣外,并未给韩少功价值重建的大厦添砖加瓦,他在《我与〈天涯〉》中说:“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20)这段文字是我看到的韩少功关于诸多生命实践意义表述最为悲观、黯然的文字,其中所渗透的落寞、无奈和他性格的热情、阳刚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内心弥漫的迷茫和无力之感,让他知道凭借以往的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根本无力在整体上对眼前的世界进行解释,更不用提对世界的改变。 回到汨罗乡下,意味着韩少功对自我知识分子身份生命实践有效性的怀疑,也意味着他放低姿态,忘记身份,企图通过接通地气以打通精神通道的努力。如果说,对小说文体的破坏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意识到现代性危机后,力所能及所做的补救和努力,那么,在承担丧失通过小说通道,搭建一个完整世界可能后果后,在以随笔的锋芒呈现了整体世界颠覆后的精神世相,却发现依旧于事无补后,对韩少功而言,他既然选择担当,那就意味着他必须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耗尽以后,如何重建新的思想资源? 韩少功显然有自己的回答。回到汨罗由此具有超越性意义,这意味着他从精神层面向生命实践更为彻底地推进。如果说,知青经历在此以前更多只是韩少功的观照对象,那么,从2000年重回汨罗开始,知青身份对他而言则有了另外的一重意义:他带着时代烙印意识到现代性危机日渐深重后,重回尘埃满面的下放地,以个体的生存体验为依托,带着对知识生产局限强加于个体思想桎梏的警惕,以此沟通和现实的联系。这种和现实对话的姿态,显示了他内心的精神路数和隐秘,包含了韩少功对知识分子精神主体成长路径的思考和剖析,只不过相对学术界更多依赖概念推导的学者而言,他天然更为尊重和信赖个体感性经验。当“文革”结束,伴随政治势能所累积的精神能量释放完毕后,韩少功数次从个体清晰的思想轨道中越出,对种种简单但贻害无穷的思想风暴进行了清理,并愿意以个体的生命实践,去寻找介入精神病相的路径,《山南水北》正是韩少功此次生命实践的成果。 韩少功的行为由此接通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主体的生成。韩少功和鲁迅一样,写作既没有沉入纯粹的书斋,也没有陷入个人迷思,甚至始终没有进入私人领地,但其文本世界却弥漫着大的悲悯和关怀。从横向坐标看,和同时代作家相比,他几乎难以心安理得地只营构一个小说的世界,现实的精神遭遇总将他从纯粹的小说世界中拖离出来,为了更方便和身边历史对话,他甘于一步步放弃小说的领地,乐于寻找小说以外的多种路径表达自己的思考。 韩少功对小说文体的破坏,显然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小说文体的危机,也显示了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及其自我挣扎。随着碎片化的生活逐渐成为现实,随着发展的逻辑理直气壮地替换革命的逻辑,随着反思现代性对宏大整体世界的解构,知识分子在摆脱启蒙和救亡等沉重的历史重托后,精神主体的生成仿佛失去了具体的依傍和载体,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无我之阵,如何在无我之阵中发展成熟的个体精神生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失去共识后面临的现实处境。韩少功在彻底告别依附于宏大叙事,依附于主流意识声音之上的精神成长历程后,越来越呈现出精神主体的强大和独立,越来越显露了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体现了作为作家的复杂和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坚韧。随着时光推移,他作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的观照者、表述者,必将越来越显示其可贵价值。 ①⑥⑧韩少功、王尧:《文学: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之三)》,《当代》2004年第2期。 ②⑨雪峰、韩少功:《韩少功:我喜欢冒险的写作状态》,《南方日报》2002年12月13日。 ③(12)(14)韩少功:《暗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④韩少功:《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⑤[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⑦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⑩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版,第223页。 (11)(17)韩少功:《我的困惑与自信》,《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 (13)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15)(20)韩少功:《我与〈天涯〉》,见韩少功著《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16)余杰:《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韩少功研究资料》,廖述务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3页。 (18)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19)韩少功:《暗示·附录二: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