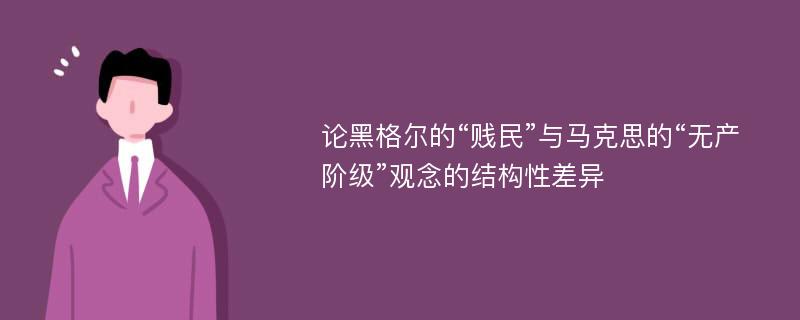
摘 要:激进左翼的思想家试图探寻黑格尔的“贱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贱民与贫困问题一起构成了市民社会阶段无法消除的外在的偶然性。它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存在着质的差异。后者作为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带有思辨属性,它在德国现实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域当中成为内在于体系的颠覆性力量;而作为从现实经验中发现的贱民则只能有待国家理念对它的重新整合。只有坚持内在于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构成对这一原则内在瓦解的哲学规定,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关键词:贱民;无产阶级;黑格尔;市民社会;特殊的普遍性
贱民思想,这个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当中占据很小篇幅的一个理论形态却成为激进左翼思潮关涉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唯一切入点。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人在其激进左翼思想的架构当中,虽热衷于讨论黑格尔,但却大多将研究的视野放置在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及《逻辑学》的研究当中,很少关注《法哲学原理》。其中的原因也并不难理解:法哲学,作为一部试图以自由意志为基础从而建构理性规范的著作,其主旨倾向非在于批判,而在于探询一种合乎理性的建构。因此,热衷于秩序之断裂,并以此为契机去探寻革命之可能性的激进左翼思想,对于这一文本的漠视自然在情理之中。时至今日,只有激进左翼思潮的后继学者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所著的《黑格尔的贱民: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考察》(Hegel’ s Rabb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 s Philosophy of Right)比较系统地关注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研究。在其中,鲁达展现了从贱民到无产阶级过渡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历史性的或者逻辑性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得两者成为同一话语模式之下可以相互转换的两个概念。齐泽克在为鲁达所做的导言部分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渡的可能性。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过渡”的判定,我们或许应保持谨慎的审视态度。
一、贱民在马克思与黑格尔著作中的源发语境
基于马克思的基础性文本来研究无产阶级概念的诞生,我们发现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这一概念是在1843年10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首次提出的。然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虽然是为其写作于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之文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但它与其所“导”之文本之间却似乎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分析语境。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我们读到的是基于费尔巴哈的问题式,纠结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论体系所展开的“唯物主义式”的批判。贯穿其间的批判也仅仅是囿于一种主词与谓词的颠倒,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这种颠倒的唯物主义与观念论间的差别并没有它所表现出的那么巨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颠倒当中,马克思较之于黑格尔更少地触及当时德国的“现实”:即急需要国家的形成以促进社会有效改良,甚至革命的基本诉求。然而当马克思转战巴黎,与卢格筹备《德法年鉴》后,他却完成了一部密切关注德国现实发展情境的《导言》,并在其中提出了一个不仅能够认识自身历史地位,并能敞开德国解放之可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却从未出现。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文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意味着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其生发语境与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由于部分手稿的遗失,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当中第261~313节的一种批判性考察。而这一部分仅仅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伦理法”当中的“国家章”的一部分。它处于黑格尔整个法哲学体系当中的完成阶段,即作为抽象法与道德法的统一所构筑的伦理法的“现实性”一维,已经成为伦理的精神,它“作为启示出来的、自身明白的、实体的意志,这种意志思考自身并知道自身,而它所知道的,要在他所知的限度内在履行”[1]382。换言之,此时的马克思将更多的关注视角放到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思辨性的维度”——理性国家的建立,即在法哲学体系当中理性体系的完成。当时囿于费尔巴哈思想视域之下的马克思,虽然认识到市民社会较之于国家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但却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本身中所提到的诸多细节的分析给出太多观照,特别是贱民思想,更是仅仅出现在对其相关文献的参考与描述中。例如,对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第301节的引用——即“假设政府以恶的或不太善良的意志为出发点,这是属于出自贱民的见解和否定的观点”①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对这一概念并无过多的关注。这并非出于他的疏漏,而是因为在马克思此时所关注的黑格尔的理论视域中,贱民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语境——市民社会,因而它已经变成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成为一个毫无特质的名词,马克思对它的漠视,是其囿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分析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国家章拓展至整个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来,我们会发现贱民问题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当中所埋下的问题却并非与其所占篇幅一般,可以一笔带过。
贱民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伦理法”的第二个环节,即“市民社会”中。从国家中分离出市民社会,在其现实性上,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其理论意义上,又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中最为闪光的一个区分。在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目的的具体的个人成为基本构成要素,并且“特殊的个人本质上是同其他这样的特殊性相关联的,所以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只有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使自身有效并得到满足”[1]329。在这个凸显特殊性利益的阶段中,贱民出现在其第一阶段“需求体系”(主观性)与第二阶段“司法”(客观性)相统一的警察与同业公会的讨论当中。对于这一阶段所发挥的作用,黑格尔这样说:“通过警察与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个体系(即需求体系与司法——笔者注)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操心。”[1]335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中,如何避免基于前两个系列中可能出现的偶然性,并在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中保持对普遍利益的追求成为这个阶段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因此,市民社会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展开以后,正在变成为带有“普遍家庭这种性质”[1]372的存在样态,市民社会要开始依赖于兴办教育,并对那些挥霍无度的人给予监管,但就在此刻,市民社会中仍有新的偶然性出现,这一偶然性就是贱民。在第240节的补充当中,黑格尔指出,雅典曾经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必须陈报他的生活来源,尽管现在在市民社会中,这种陈报似乎并不必要,因为市民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因为市民社会对个人的给养负有责任,它就有权督促他自谋生活”。于是“问题不仅仅在于防止饥荒,而更宽广的观点在于看到,要防止贱民的产生”[1]372。
在此,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贱民的产生是一个有待理性的法的秩序予以预防甚至排除的偶然性。可以说,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着重讨论的正是这个让他担忧的偶然性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可能性途径。
二、黑格尔对贱民的界定及消除贱民的不可能性
无产阶级的源发语境,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恰恰没有发生在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而是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标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力,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力,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15
对律所和律师个体来说,参与法院纠纷处理,主要是为了拓展业务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等,至于是律师调解亦或是其他形式并不重要,甚至牺牲一些时间和精力免费为法院干活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当中的贱民并不是一群在经济上有所诉求的穷人,而总是充满“否定的理智”的一群人,他们“把仅仅否定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把恶的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猜疑提到首位,然而根据这个前提狡猾地建筑一些堤坝,从效用上说,只是为了对抗一些相反的堤坝,所以需要这些堤坝”[1]412。因此,与其说贱民是一群经济上贫困的穷人,不如说他们是一种负面的情绪的化身。可以说,过度的贫困与贱民的过度产生是市民社会中存在的相互依赖着的两类偶然性。
2.3 不同年龄的三维CT结果 低年龄组藏族患儿脱位高度显著高于汉族患儿(P<0.05)。高年龄组患儿髋臼指数及脱位高度两民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藏族组,年龄≥36个月的患儿髋臼指数、脱位高度、颈干角与<36个月患儿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汉族组,年龄≥36个月患儿的颈干角、脱位高度与<36个月患儿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欢迎骨科、小儿外科、神经外科、康复科、生物医学工程相关专业医生报名学习,会务组可协助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有清醒研究的黑格尔,他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只是对于黑格尔而言,贫困所带来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富有经济色彩的)是市民社会内部无法消解的。于是黑格尔转而讨论殖民地的扩张,这是其向内诉求无法实现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尝试——“市民社会被驱使建立殖民地”[1]377,其背后驱使的力量正是贫困与贱民。但这种外部诉求显然只是权宜之计,转移矛盾却并非真正解决矛盾。他们的实现都依赖于作为外部秩序与机制的警察。而黑格尔所诉求的是内在的伦理层面上的矛盾的消解,在这一语境之下,同业公会成为黑格尔防止贱民产生的救命稻草。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无产阶级概念的产生语境却是极为特殊而现实的话题,即德国的解放之路。两种话语语境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绝非毫无关联,相反,社会历史的特殊语境恰恰是马克思推出其无产阶级之思辨哲学式规定的前提。正因如此,马克思让这个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无产阶级概念同时具有了现实的颠覆性力量,因为其来源并非出自一个思辨体系的推演,而是来源于当时德国的现实历史情境。
仿真设计步骤如下:仿真时长为0.05 s,在0.015 s时,串联一个20 Ω电阻扰动;到0.025 s时,串联一个1 V电源扰动;在0.035 s时,并联一个50 Ω电阻扰动。用Scope模块观察输出电压的变化,对比加补偿网络的输出电压波形和未加补偿网络的电压波形,来验证电路的合理性。仿真结果如图7和图8所示。
在此,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强调。无产阶级是内生于市民社会,其基本原则却与市民社会相左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这一阶级之所以成为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是因为它的诉求不是市民社会所特有的特殊的私利,而是普遍的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马克思将这种普遍的诉求视为“社会的原则”,笔者将其等同于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最高原则的设定,“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3]15-16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中的“非”意味的是一种内在于市民社会的自否定,而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贱民,后者是整个外在于市民社会之外的。而在此刻马克思的语境当中,这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界定方式却让其成为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个中介。无产阶级在这一意义上,如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的否定性中介,因此它自身的否定与消亡也就是它所附带的肯定性要素的实现。在无产阶级的理论语境中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带来这个理性体系的消亡,同时还将带来阶级自身的消亡:“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16在这一意义上,它也绝非是齐泽克、朗西埃试图谈论的不能被容纳体系之内的一种特异性(singularity),相反,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带有着思辨辩证法的典型特质。
但在这里,问题是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同业公会之所以可以给人以尊严,所依赖的是对财富甚至财富分配之合理性的保障,因此它的解决路径是非经济性的,而更类似于政治性的安排。黑格尔在此实际上进行了一种逻辑的跳跃,即将经济上无法解决的矛盾直接转化为一种政治的解决。由此,不仅让贫困这一偶然性变成其法哲学逻辑环节中的晦暗不明的一环,同时还使得贱民的产生及其属性的界定也因此变得极为模糊。贱民虽源于经济上的贫困,却是需要在政治上加以规范的一种主观情绪。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贱民没有获得一个清晰的定位,他成为黑格尔理性体系当中无法归类的一种存在样态。齐泽克对此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作为症候性的贱民之所以能够成立,因为他描述了一种现代理性国家的必要的非理性的剩余,它在整个有组织的现代国家内部没有地位,尽管在形式上他属于这一有组织的整体——由此它成为一个特异性的普遍性的概念(这一特异性将自身直接赋予了普遍性,而绕过了以特殊性的中介来加以过渡)。”[2]xiv齐泽克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没有能够指出贱民,作为社会整体的破坏性的剩余,究竟是如何成为这个整体的‘反向决定’,成为其普遍性的直接表现,一个在社会整体的伪装之下的特殊要素在其自身的要素中与其自身相遭遇,但正是如此,构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关键要素。”[2]xiii这种理解显然有过度阐释之嫌,齐泽克将原本在黑格尔当中暧昧不明的概念清晰化,同时也让黑格尔的贱民概念成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的前身,黑格尔似乎只是缺乏一双慧眼帮助其看出贱民的破坏性。但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显而易见的是,贱民在黑格尔那里从来都是在市民社会“之外”的一个非劳动的阶层,因此它作为理性国家的剩余并不能对理性化的市民社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仅仅是一种否定性主观的情绪,而并不能充当一个代表普遍性的特殊利益,它不是富有统一性的“精神”,只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齐泽克以及其激进左翼的后继者们赋予了贱民过多的内涵,不仅误解了黑格尔,也从根本上无法理解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时对于黑格尔思想所实现的革命性的超越。
三、无产阶级诞生的现实语境及其思辨属性
阮孚用手掂了掂布袋,笑答:“只装了一文钱,我是怕这布袋因为没有装任何钱财而感到难为情,所以就用这一文钱来安慰安慰它。”
对于黑格尔而言,贱民的产生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并非依赖于贫困来加以定义。换言之,一方面,贫困,同样作为一种市民社会中的偶然性,基于其某人的自然体质抑或其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它是产生贱民的前提条件,即“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某种生存水平——作为自发调整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水平——之下”的时候[1]374;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活水平的下滑本身也仅仅是产生贱民的前提,贱民的产生却绝非仅仅是因为贫困所造成的。对于黑格尔来说,“贫困本身并不使人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取决于跟贫困相联系的情绪,即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在愤怒”[1]374。当人因为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丧失了通过自食其力的劳动所获得的这种正当、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1]374。换言之,贱民是那些脱离了劳动范围之外,并因而失去正当、正直和自尊的一类人。他们并非仅仅是穷人,还同时是一些不能自食其力,却期待着伸手乞求来过生活的一群人。
在这段引述中,无产阶级在两个矛盾的语境,即思辨哲学的语境与现实历史语境的相互交织之间获得规定。首先,就其带有思辨哲学色彩的规定而言,无产阶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普遍性。一般说来,苦难,总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情感将被特定的阶级所体验到,然而,无产阶级所遭受到的苦难竟然具有“普遍性质”,并由此使得其所享有的权利、其所遭受的不公都不再表现为特殊的、历史的,而成为普遍的、属人的。因此,其所佩戴着的枷锁就是一个“彻底的”枷锁,其所实现的解放也是普遍的解放。这种普遍性不是一种共相性的普遍,即并非是从多个事物不同形态之中所抽象出的共性,而是以一个特殊的存在直接彰显出一种普遍性,这是只能存在于思辨辩证法当中的一种普遍性的规定,它彰显了无产阶级所天生具有的原则高度。它与其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在一种人的复归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成。因此,它们也仅仅是一种富有原则高度的哲学规定。
三年来,全省“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一批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和谐、活动有序、教风端正、管理规范、安全整洁、服务社会的“和谐寺观教堂”涌现出来。
问题在于,当我们阅读黑格尔有关的论述,我们会发现这种偶然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市民社会所内生的,另一方面却又似乎是市民社会无法消除的。因为对于黑格尔而言,市民社会之影响力的扩张,同时包含人口的增多和工业的进步,人们依赖于需求体系而建立的相互关系被普遍化,同时提供满足之手段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与限制,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附性和贫困化也愈益增长”[1]374。这种分析触角近乎触及了现代劳动对于人的异化的维度,指认了劳动的否定性的一维。贫困正是由于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而属于市民社会展开自身的内在矛盾。对于黑格尔来说,所有的内在矛盾都有可能在辩证展开的过程中实现消解与统一。但在黑格尔有关于各类防止过度贫困、从而防止贱民的过度产生的各种手段的描述中,我们却总是能感到黑格尔对这种种手段所持有的否定性态度。例如,由富人阶级承担责任或者动用公共财产所给出的捐赠,将贫困群众维持在正常的生活水平之上,这种非劳动式的资助与市民社会的独立自尊的基本方式相左,因此违背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让穷人参与劳动,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又可能因为导致相对于消费力的产能过剩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黑格尔因此也否定了这种劳动式资助的方式。
在此,黑格尔实际上正在通过一个辩证的逻辑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消解在与伦理法不同层面的理性安排当中。但此处的问题在于,黑格尔对于这两种偶然性的消解只做了一种含混化的处理。在笔者看来,按照黑格尔的解读,贫困与贱民分别属于两种不同属性的偶然性,如果说贫困是一种带有经济属性的客观的偶然性,那么贱民则更多的是富有情绪化的主观的偶然性。两者虽然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却绝非相互衍生。因此,消除一种偶然性并不必然会连带消除另一种偶然性。正如黑格尔在此处所做出的相关论证一样:其所提出的非劳动式的抑或劳动式的资助,甚至向外的殖民地的建立都是以经济补偿为基调的一种解决路径,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贫困,但却并不一定会消除贱民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后者更多地是指那些在主观上持有好逸恶劳的否定性情绪的一群人。经济的发展,从未能真正地彻底消除这种情绪,于是黑格尔的同业公会的设想所针对的更多地是赋予人以等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的保障实际上所依赖的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成为对共同体的复归。因此,当同业公会成为化解贱民的有效手段时,市民社会也的确走到自身的尽头,国家的理念就要出现。
从贱民到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上的结构性断裂,换言之,无产阶级绝非是被马克思重新改装了的贱民概念,它们是基于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下产生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生态、低碳、环保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档案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馆建筑群体及设备设施应遵循绿色环保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档案的保护方式以前是追求快速建造,现如今在逐渐向高效建造发展,更注重生态保护、低毒、无残留,从实质上迎合国家开展的绿色环保政策,从而保证档案馆的合理化建设。
黑格尔所强调的同业公会实际上是在释放个人独特利益与个性尊严的基础上重新强调公共权力的监管,这如同是以市民社会为中介而在更高层面上重建了一种新形式的家庭(“第二家庭”[1]378),它将已经获得独立人格的个体重新纳入一个整体当中,建立一种等级以及与等级对应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不仅财富得到有效保障,而且人在等级中得到有效安置。穷人的救济不再是偶然的,并且不带有任何羞辱的成分,种种可能导致贱民的情绪也在这种合理的安置中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引发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问题域在于:“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3]15对于撰写《导言》时期的马克思而言,当时的德国处于一种现实落后于其思想,现代政治体制与旧有的一切野蛮缺陷相结合的阶段。这种德国的现实以书报检查制度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国九月法令勾连起来的现实事件直接呈现在马克思的面前,这种荒谬的呈现方式让马克思产生了改造德国现实的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德国现实的可改造性以及如何改造的具体操作成为马克思思想中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
首先,德国现实的可改造性在于德国自身作为一种特殊领域正在彰显一种当代政治的普遍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3]12因此,对于德国现实的改造,就不仅仅是改变德国已过的政治特性,同时也是对现代政治的改造。其次,针对德国的现实与改造、现实的革命与解放需要有其特定的呈现方式:“对于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的梦想。”[3]12换言之,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所擅长的或许是一种整体的、普遍的革命,但如果试图直观到德国现实的、可操作性的革命与解放,这种整体性与彻底性恰恰需要首先被悬置起来。相反,德国现实向马克思所呈现的是一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3]13
随后马克思竟然不惜笔墨去描述这一阶级如何实现解放整个社会的具体途径。例如,要在自身和群众中激发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让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成为其总代表。一个市民社会中特殊阶级的解放与人民革命相一致,从而使得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一切缺陷都集中在另一个等级,一个阶级成为普遍的解放者,另一个阶级成为普遍的奴役者,等等[3]13。这是马克思所能设想的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因而也是现实可行之革命的基本方式。在这里,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作为普遍利益代表者的无产阶级,以及日益清晰可见的两大对立阶级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呈现,正是在马克思的德国解放的问题域之下所呈现出的一些还未被合理概括的现象。
在呈现了一种真正现实的革命方式之后,马克思通过对比德法两国的政治文化特质来说明“德国的解放究竟需要什么”这一更为深入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词的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3]13“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一个特殊阶级,而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3]14
通过这样一个对比,马克思发现尽管同样立足于市民社会,现实的革命却由于德国缺乏一种能够担当普遍性的特殊阶级,而在德国变得不可能。而在推崇理想主义的法国,似乎这个阶级天生地、自然而然地、无须特别发现地普遍存在于所有法国阶层当中。因此在法国,革命可以由不同阶级来担任,并最终完成于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阶级[3]14-15。马克思正是在对这一不同民族性格的分析之下,进一步展开了最终指向无产阶级的话语语境:“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我们上文所引用的那样一段关于无产阶级的相关论述。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生发于特殊的德国现实解放之视域下的一个特殊阶级,它的出现原本是马克思试图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特殊的药方,但由于马克思当时所特有的思辨哲学的思考方式,却将这一特殊阶级提升为一个特殊的普遍性。当然这种特殊的普遍性自身同时还是法国革命阶级所特有的一种存在样态:一个人即希望成为一切的革命精神。这种激进的革命意识成为诠释无产阶级作为特殊之普遍性的另一个维度。
四、结语:无产阶级与贱民的结构性差异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产生语境再一次彰显了无产阶级与贱民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首先,无产阶级是发端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构想,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设定,而非基于经验观察所得出的多个个体的共相;而贱民,在黑格尔哲学中反而是一种与贫困有着依附关系的一个经验的、真实的群体。其次,无产阶级的思辨属性,即作为市民社会的内在的自否定性环节使其获得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的否定性是体系自身生产出来的,因而它所否定的,以及它否定的结果将带来体系(市民社会)自身的改造;而贱民,则是完全在法的理性规范之外,在“不法”的语境下产生的,那么法的理性规范在防止贱民产生之中就显得无计可施。换言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范围之内,并不能真正地解决贫困以及贱民问题,承认它的存在,但无法消融它。因此,贱民,对于黑格尔体系来说,是一群无法推动体系展开的外在的偶然性;而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内在的外在性,它虽然有其现实的群体指向,那些“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4],但其自身具有的思辨哲学的规定性却赋予它真正的颠覆力量。基于这一比较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贱民与无产阶级存在着无法过渡的鸿沟。马克思并不是从黑格尔的贱民思想当中得出无产阶级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在与法国大革命的行动原则的参照当中所获得的一种富有颠覆性的理论构造。虽然这种构造仍然带有些许思辨的色彩,但其内在颠覆性的原则的设定是恰当的。虽然随后马克思在其思想的演进中更多谈论的是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工人”而非“无产阶级”,但这一颠覆性原则的探寻方向却从未改变:作为能够承担其社会发展之主体的阶级不应囿于现实的经验性,甚至经济性的规定,如贱民,而应诉诸一种富有哲学高度的规定,即内在于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构成对于这一基本原则的内在瓦解。只有坚持这一哲学原则的规定,革命的无产阶级才不会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彻底消失,而社会发展也才具有永恒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2]Slavoj, Zizek,The Politics of Negativity, Frank Ruda,Hegel’s Rabble: An introduc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roup,20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3-0015-07
作者简介:夏莹,1975年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