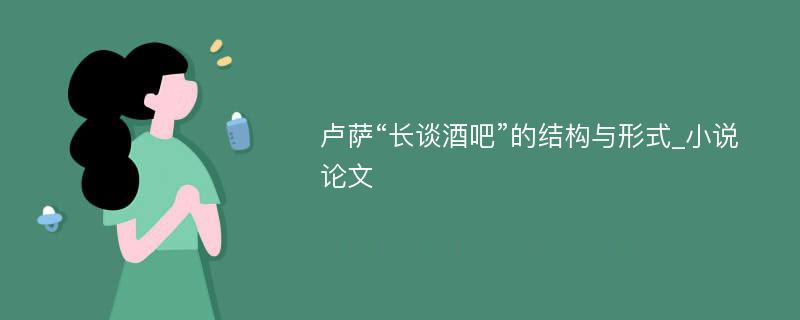
略萨《酒吧长谈》的结构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酒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认为,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结构最大胆、也最成功的“革命”,是来自当代拉丁美洲的结构现实主义。
本世纪4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为变革传统小说的结构作了富有想象力的探索,掀起了所谓“结构革命”。“结构革命”在当代拉丁美洲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和作品中都有反映;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36— )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小说。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个对自己的祖国怀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作家,他的作品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秘鲁的社会现实,同时,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广大读者。从1963年发表《城市与狗》算起,他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绿房子》(1966)、《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莉娅姨妈和作家》(1977)、《世界末日的战争》(1981)等;可以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不同于他过去作品的新探索。略萨的创新是多方面的,而又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夫人帕特丽西亚·略萨曾说,从文学角度上讲,《酒吧长谈》是略萨生平最喜爱、最得意的作品。因此分析一下《酒吧长谈》的结构形态将有助于理解结构现实主义及“结构革命”。
一
《酒吧长谈》反映的是1948—1956年间军事寡头奥德利亚统治时期的秘鲁社会生活。阿莫勒蒂奇·奥德里亚曾任秘鲁总参谋长、内政部长、警察总长,1948年把持军事委员会,废黜在任总统,出任临时总统,解散立法机关,宣布由军人直接统治国家。1950年6月1日他辞职参加总统“竞选”,就任总统后继续强化独裁统治,压制反对派。小说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描绘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出现在作品中的70多个人物,涉及从部长、将军,到流氓、妓女的各个阶层。其中主要人物有五个:(1)圣地亚哥·萨瓦拉。他出生于大资产阶级家庭, 最初生活放荡,但当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了较平民化的国立大学以后,受到进步势力的影响,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曾被政府当局逮捕,然而他虽不满现实,有正义感,却没有明确坚定的信仰,结果一事无成;(2) 卡约·贝尔穆德斯。他本是个商人,奥德利亚上台后,他靠着各种机缘青云直上,最后当上内政部长,是一个生活腐化、残暴无情的刽子手;(3) 费尔民·萨瓦拉。他是圣地亚哥的父亲,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艺术 典型,狡猾、阴险、野心勃勃。奥德利亚上台时,他是狂热的支持者,但后来又参与发动了最终导致奥德利亚下台的骚乱;(4)安布罗修。他出生贫寒,先是投靠贝尔穆德斯,后又效忠费尔民,是个谁给钱就为谁卖力的帮凶和可怜虫,后来在利马的狗场以捕狗打狗为生。从结构上说,他是小说中勾联各条线索的一个关键性人物;(5)阿玛莉娅。 她原是费尔民家的女仆,一度是安布罗修的情人。她被主人辞退后备受折磨,后来到贝尔穆德斯蓄养的高级妓女“缪斯”的宅邸中当佣人,并和安布罗修重归于好。她是贝尔穆德斯丑恶生活的见证人,后者被撤去部长职务以后,抛弃“缪斯”离国出走,处于困境的“缪斯”对费尔民进行要挟,于是安布罗斯杀死“缪斯”,带上阿玛莉亚逃离利马。她后来因难产死去。
应该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的背景、人物、故事算不上特别复杂;但是,翻开小说,读者却会觉得好似走进了一座迷宫:小说的时间、空间一片混乱,摆在面前的是一大堆似乎胡乱排列出来的生活碎片。此时和彼时,甲地和乙地,这个人和那个人,现实和内心活动,这组对话和另一组对话,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时而平行,时而交叉重叠。即使关于同一事件,也不按开始、发展、结尾的自然顺序来展开,可以先见其次,后见其始,有关的叙述又可能突然而来,蓦然而去,使人难知究竟。总之,小说的结构似乎毫无规律可寻。但是,读者之所以可能产生如此感觉,并非因为小说的结构果真如此,而是因为还不了解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而一旦能在创造性的阅读中逐步掌握了解读这部小说的“语法”,就会发现,小说在极其紊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独特、精巧的结构,令人叫绝。
结构现实主义小说又被称为立体小说,可见它的主要特点是立体性。客观现实本来是“立体”的,但小说的传统写法是把复杂的、“立体”的生活纳入一个稳定的叙事平面,井然有序地铺展情节,这正如托多罗夫在《叙事作为话语》一文中谈到小说时间时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这种写法的好处是清晰,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读者容易把握,但做到这一点是以牺牲生活本身的立体性为代价的。结构现实主义则不同。它首先对现实——准确点说,不是对现实本身,而是对传统写法中那个稳定的叙事平面——加以分解,在这基础上,把分解后得到的一个个小块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关系。其结构看似紊乱,其实,各种安排决非是随意的,它是为了在多种层次上、从各个角度立体地反映现实,展示现实的多面性。《酒吧长谈》充分体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个重要特点。
从整体上说,《酒吧长谈》的叙述可以分为两个序列(或层次),一个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酒吧中的“长谈”,另一个是小说叙述人的直接叙述。
小说开始时,正在利马《纪事报》当记者的圣地亚哥因为寻找失去的狗来到狗场,偶然与安布罗修相遇,两人来到一家叫“大教室”的酒吧,一面饮酒一面追忆往事。整个小说就是以他俩长达四小时的长谈为主轴而铺展开来。这种安排在传统小说中也可能遇到,但是这部小说的情况却与传统小说很不一样。照传统小说的写法,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的相遇可能只是小说的序幕或引子,用以引出后面的叙述。但在《酒吧长谈》中,在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话别以后,紧接着的第二节却既非圣地亚哥,也非安布罗修的视角,而是第三人称局外人的叙述。叙述的是圣地亚哥的朋友、参议员埃米诺的儿子波佩耶·阿雷瓦洛和父母的谈话,他正热恋着圣地亚哥的妹妹蒂蒂。三人的谈话中突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在西班牙文原文中作陈述式现在时,中文无法表达,译者孙家孟先生决定用异体字排印,加以区别):
“光劝不行,揍一顿他就听话了。”索伊拉太太(按:阿雷瓦洛的母亲)说道,“你就是不会教育他。”
“蒂蒂和那个总到我们家来的小伙子结婚了。”圣地亚哥说道,“他叫波佩耶·阿雷瓦洛,就是那个雀斑脸阿雷瓦洛。”
“瘦子(按:指圣地亚哥)跟他老头子的关系不太好,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波佩耶说道。
用异体字叙述的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现在”正在进行的谈话。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小说的字里行间一直断断续续出现这种用陈述式现在时写成的“圣——安谈话”的只言片语,好像我们站在高处看到在群山中蜿蜒流去的河流时隐时现一样。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圣——安谈话”和小说叙述人的直接叙述细心加以比较,还可以发现,原来它们涉及的是同一内容。不过,二者并不同步,前者有时走在后者的前头,有时又落在后面。然而小说结束的时候写到安布罗修回了一趟家乡钦恰,在钦恰——
……他坐在临街的桌子旁吃了洋葱烤肉。一边吃一边望着大街,想认出某些熟人的面孔来,但一个也没有认出。他想起了去利马的前一天夜里,特里福尔修同他在黑暗中走着的时候对他说的话:我人在钦恰,又好像不在钦恰;我认出了一切,又好像什么也认不出来了。现在安布罗修才理解他这些话的含义。他又在另外几个区游荡了一会儿,看到了何赛·帕尔多中学、圣何赛医院、市立剧院。市场现代化了些。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小了;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矮了。只有人不一样了。我很后悔去这一趟,少爷,我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利马,发誓再也不去了。我在利马倒了霉,可在钦恰,除了感到倒霉,我还感到自己衰老了,少爷。等狂犬病过去了,你在狗场的工作是不是也就完了,安布罗修?是的,少爷。那你怎么办?后来狗场管理员命潘克拉斯又把我找了去,对我说:好吧,你可以帮我们干几天,没有证件也行。狂犬病过去了,在这之前干什么,我还去干什么呗,我可以到处找工作。也许不久之后再发生一次狂犬病,狗场还会把我找去。以后再到处流浪,到处找工作。对,再以后,就去见上帝,您说对吧,少爷?
通过一连串自由直接引语,小说对安布罗修这段生活的叙述由第三人称(小说叙述人向读者叙述)变成了第一人称(安布罗修向圣地亚哥叙述),再变成了“圣——安谈话”,使两个叙事序列在最后流畅地、巧妙地、不露痕迹地合而为一。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两个叙事序列并非各不相干,它们是以两种“声调”,两种形式出现的“酒吧长谈”。作者隐去了绝大部分“谈话”,只保留下它的零星片断。而“圣——安谈话”的实际内容、涉及的众多往事,则改由小说的叙述人以局外人的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保留下来的两人交谈的片断则时时提醒读者:第三人称的叙述人的叙述其实也正是“圣——安谈话”;当然,是变了形的“圣——安谈话”,或者说,是让“圣——安谈话”中提及的各种人物、事件,以其本来的面目直接呈现出来,而不间接地被转述。这种复杂而精巧的形式、结构,在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
以上谈的是统摄全局的小说中两大叙事序列的关系,下面再进一步分析其中第二个叙事序列的结构形态。
二
先请看下面一段:
(一)“你早该来看我了,安布罗修。”鲁多维柯说道,“人倒了霉,连朋友都不照面了。”
“你怪我没早来看你?”安布罗修说道,“可我也是今天早晨在街上遇到伊波利托才知道的,鲁多维柯。”
“是那个婊子养的告诉你的?”鲁多维柯说道,“可他是不会把全部情况告诉你的。”
(二)“鲁多维柯怎么样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安布罗修说道,“他去阿列基帕有一个月了,可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他住警察医院了,从头到脚都缠着绑带。”伊波利托说道,“阿列基帕人把他揍了个一塌糊涂。”
(三)天刚蒙蒙亮,指挥者就把帐篷的门一脚踢开,大喊:该动身了。……
(按:编号为笔者所加)
这些对答、叙述看似毫无关联,互不搭界,其实不然。可以设想,如果把安布罗修和鲁多维柯的谈话作为基准,那么传统的写法很可能是:或者由安布罗修向鲁多维柯转述伊波利托对他谈到的情况,或者由小说叙述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补叙、交待,不管怎样,实际上都是把一系列事件投射到“现在”这个叙事平面上。但在这里,写法就很不相同了,出现了三个叙事层面。(一)是安布罗修和他的好朋友、贝尔穆德斯豢养的打手鲁多维柯之间的对话。按理,紧接其后的应该是安布罗修的回答,谈他当天早上在街上见到依波利托时依波利托(也是贝尔穆德斯的打手)对他讲述的情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而是出现了叙事层面(二),时间、空间都变了,是直接写当天早上安布罗修和依波利托在街头的交谈。那实际上正好是对(一)中鲁多维柯的问话的回答,只是不是由安布罗修来转述,而是让读者“直接”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两个叙事层面、两组对话又制造了一个悬念:为什么鲁多维柯大骂伊波利托、断定他不会把全部真相告诉安布罗修?鲁多维柯为什么全身负伤、被揍了个够?他遇到了什么意料不到的情况?读者一定急于知道,然而作者好像并不理会读者的期待,而是“镜头”一转,地点变了,时间也被“推”回去了,出现了第三个叙事层面,叙述的是鲁多维柯一伙奉贝尔穆德斯手下人的命令到阿列基帕去破坏反对党组织的集会,在去阿列基帕途中、抵达目的地前一天早上的情况。鲁多维柯就是在后面要写的冲突中负伤的。所以叙事层面(三)实际上是回答了前两个叙事层面产生的悬念——它仍然不是由某一个人来转述,而是让读者“直接”去看事情的原委。这三个叙事层面组成的叙事段落不遵循客观事件原来的时间顺序,而是“倒过来”,剪断了传统的叙事链而重新组合,作者又不加以交待、提示,其效果更富戏剧性、直接性、立体性。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
“现在我起码能睡了,”鲁多维柯说道,“头几天我连指甲都疼。”
“可你着实捞到了好处,你要这么想。”安布罗修说道,“你这次是工伤,应该奖赏你。”
时间又从过去被拉回到“现在”,但马上“镜头”又掉转了,不过,这一次不是简单地推到过去的情景,而是“现在”和过去交错:
“联合党(按:在阿列基帕组织集会的反对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特耶斯(按:鲁多维柯的另一同伙)说道。(过去)
“是工伤又不是工伤。”鲁多维柯说道,“是有人派我们去的,也可以说根本没人派我们去。这一切简直闹不清,你都想象不出来,安布罗修。”(“现在”)
“你只知道他们都是些臭狗屎就行了。”指挥者笑了,“这次我们要把他们的示威集会冲垮。”(过去)
“其实我也是没话找话,活跃活跃旅途气氛,”特耶斯说道,“气氛太沉闷了。”
(过去)
一面是“现在”安布罗修和鲁多维柯正在进行的谈话,一面是过去鲁多维柯等一群打手在去阿列基帕途中、在面包车里的闲聊。在这里,作者又用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手法,把有关阿列基帕事件前后的一些“现实生活”的材料打碎,再加以重新组合,完全改变了人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线性的、平面的写法,对现实作了立体的反映。
前面提到,鲁多维柯和安布罗修的谈话制造了一个悬念,对这个悬念的解除要等到小说对阿列基帕事件做描述时才能进行。
小说描述阿列基帕事件的写法十分精彩。一群过去支持“现政府”、“现在”又出来捣乱拆台的政客,要在阿列基帕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得悉这一情况的贝尔穆德斯决定派出一批打手去破坏集会并组织反示威,但他没料到他的计划被下面暗中反对他的人破坏了。在他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只派去了鲁多维柯等几个人,他们势单力薄,不但不能破坏集合,反而被打死打伤数人。事态扩大后当地警察部门无法控制局面,只得向驻军求援。贝尔穆德斯也在电话中焦急地催促军队行动,而军官们却另有打算,按兵不动,坐观事态的变化。反对党的政客们积极活动,拉拢军官,并一起策划暂时由总统出面组织军人内阁,将贝尔穆德斯排除。这时,小说中出现了互相交叉的若干组对话:贝尔穆德斯的“团体”阿列基帕据点的负责人慌张地在电话中向贝尔穆德斯报告形势紧张;当地警察局长要求军队立即出面干预;陆军部长耶雷纳将军通过电话回答帕德列斯司令关于阿列基帕局势的询问,他大骂贝尔穆德斯把事情搞糟了却要军队收拾局面,使军队进退维谷;当地驻军司令阿尔瓦腊多将军告诉帕德列斯司令:他要是出动军队就会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帕德列斯说,贝尔穆德斯保证不会流血,事件只是一小撮人煽动起来的;阿尔瓦腊多告诉耶雷纳,人民已控制了城市,是否出动部队请他做出决定,耶雷纳则要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穆德斯和耶雷纳通话,要他赶快下命令,不可浪费时间;阿尔瓦腊多坦率地回答耶雷纳,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贝尔穆德斯而让自己的对手沾满鲜血,并说联合党的先生们(即组织闹事的那伙政客)找过他,保证只要贝尔穆德斯辞职就可以平息局势;参议员阿雷瓦洛等向耶雷纳将军说明他们的目的,表示很尊重军队和耶雷纳本人,他们只是要求贝尔穆德斯辞职;阿尔瓦腊多告诉耶雷纳,局势十分严重,完全不是贝尔穆德斯估计的那样,但他已从联合党领袖们那里得到保证:只要贝尔穆德斯离开政府,事情就会和平解决;贝尔穆德斯和帕德列斯通话,抱怨军队方面给他设下陷阱,要他赶快敦促耶雷纳;耶雷纳同意阿尔瓦腊多按兵不动,后者则告诉他联合党负责人又来找过他,建议成立军人内阁;参议员兰达对费尔民说,阿尔瓦腊多表现相当不错……本来,各派政治力量各怀鬼胎,忙着进行紧张的政治赌博,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险恶的阴谋、肮脏的交易,出人意料的转折!形势瞬息万变!但作者没有按照小说创作的“常规”去尽情铺展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场面,而是把“镜头”对准一组组电话上的对话。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记录”下各组对话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从中“抽取”出最关键的一些片断,组成这样一个系列。对转换、省略等等又不作任何提示,跳跃性极大。但是,在这样的新结构中,每一个片断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互相对照、衬托,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面目和它们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所谓结构紊乱只是表面的现象。小说的描述常常突然从一个点、线、面,跳向另一个似乎没有联系的点、线、面,这些都决不是任意的。不难理解,有一条隐而不显的主线贯穿在貌似杂乱的结构之中,只要我们能发现、抓住这条主线,原来好似杂乱的结构就一点不显杂乱了。
有时,作者从一个片断跃向另一个片断时很注意两个片断之间的切合点,这就是略萨常用的“通管法”。
下面的引文出自《酒吧长谈》第一部第二节,涉及的“事件”是:当初圣地亚哥从哥哥奇斯帕斯那里得到一种能使女人动情的迷醉药,他和波佩耶一起决定在女佣人阿玛莉娅身上试试药物的效力。他趁着父母和妹妹外出,把阿玛莉娅叫到自己卧室中,让她喝下放了迷醉药的可口可乐,药力果然发作。圣地亚哥和波佩耶趁机挑逗她,和她胡闹,被突然返家的父亲发现。无辜的阿玛莉娅因此被解雇。事后圣地亚哥深为内疚,一次,他凑了些钱去送给阿玛莉娅。
阿玛莉娅笑弯了腰,她摆动着双臂,但是圣地亚哥和波佩耶仍然抓住不放。有什么呀,少爷,我没有未婚夫。阿玛莉娅一边说,一边用肘推搡着,想把两人推开。圣地亚哥抱住了她的腰,波佩耶把手放到了她的膝上。阿玛莉娅使劲用手推开:这可不行,少爷,别碰我。波佩耶又扑了过来:坏妞儿,坏妞儿。没准你会跳舞,你骗我们说不会,你坦白。好吧,少爷,我收下了,为了表示不是装腔作势,她拿起了钞票,用手卷了起来,放进了毛衣的口袋:我要您的钱,心里真是过意不去,您现在星期六看电影的钱都没有了。
“你别担心,”波佩耶说道,“他没钱,我们一伙人可以凑钱请他看电影。”
“朋友嘛,理应如此。”阿玛莉娅睁大了眼睛,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噢,快请进,哪怕只坐一会儿呢。请原谅,家里太穷了。”
没等两人拒绝,她就跑进了屋里,两人只得随她走了进去。屋里到处是油渍、烟垢,有几把椅子,几张圣像和两张破床。我们不能坐很久,阿玛莉娅,我们还有约会。她点点头,用裙子擦了擦房间当中的桌子:就坐一会儿。她眼睛里闪现了一丝狡黠的光芒:你们先谈着,我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圣地亚哥和波佩耶互相看了一眼,感到既惊奇又高兴。她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瘦子,她疯了。阿玛莉娅格格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着。满面汗水,满眼泪水,扭捏作态,弄得床发出吱吱的响声。……
(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圣地亚哥等的恶作剧直接导致阿玛莉娅被解雇和一系列悲惨遭遇,把事件“打碎”,把恶作剧中的一些场面、片断,与后来圣地亚哥等出于自责去看望后者的一些场面、片断交叉组接在一起,较之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其思想艺术效果会如何不同,是不必多说的。问题在于,这种交叉、组接,十分自然酣畅,有如天成,这就要归功于“通管法”了。上面的引文由三个“切块”组成,“连通管”之一是“好吧”,连着上文看,那是答应波佩耶,愿意跳舞,是在圣地亚哥卧室中的场景;如果连接下文看,又是她被辞退后,圣地亚哥等去看望她,在圣地亚哥的坚持下,她答应收下送给她的钱。另一个“连通管”是“圣地亚哥和波佩耶互相看了一眼”,连着上文看是圣地亚哥、波佩耶对阿玛莉娅所说的“你们先谈着,我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的反应,连着下文则又是他们见到药物在阿玛莉娅身上发生了效力时的表情。
由于作者的独特写法,要把“故事”本来的头绪线索清理出来并不容易,不过,这却不是不可能。略萨在这部小说中为读者精心设计了一个时间参照系。只要我们有耐心,我们完全可以以它为参照,去恢复“故事”的原貌。这个参照系就是阿玛莉娅。在小说的众多人物中,只有她的经历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由于她和费尔民、贝尔穆德斯、安布罗修、圣地亚哥以及“缪斯”的关系,这些人物的活动、遭遇,也就可以参照她的时间整理出一个时间表。
现代小说,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对读者的阅读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富有创造性。结构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重新组合,要理解这一点,我们的阅读不妨包括两个步骤:一、先将小说的结构拆散,寻求故事情节的本来线索,并按照这些线索去恢复(对小说而言则又是重构)故事本来的结构;二、再把这两种结构加以比较,从比较中发掘小说结构的美学意义。阅读变得不易,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获得的是更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限于篇幅,许多问题未能涉及,本文的分析只能是十分粗略的。
注释:
〔1〕《叙事作为话语》,见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