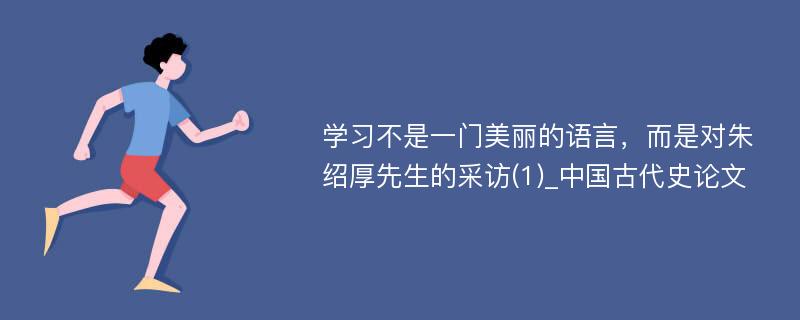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知论文,不为论文,后人论文,访谈录论文,媚时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天,开封古城东北隅,一座静谧的庭院。推开虚掩的木扉,满目绿色令人心旷神怡。芳草绕径,青苔印屐,奇花点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间一棵虬枝老树生机勃发,苍翠浑然。谁又能说,这不是寓所主人的传神写照呢?
老树春深更著花。
半个世纪来,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以其充沛的精力和坚韧不拔的作风,耕耘在学术园地,著作等身,新说迭出,享誉于海内外史学界。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我们决定对八十高龄的朱先生进行一次学术访谈。以下是采访笔录的整理稿。
问:朱先生,您是历史学界尊敬的知名前辈。半个世纪过去了,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请问您在学生时代,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学来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
答:1926年我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不久全家迁居沈阳,我在这里读的小学和中学。要说我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有两个主要因素,都植根于我的学生时代。一是在中学时就爱读历史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这样就引起了我对中国古代人和事的浓厚兴趣。二是我在读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时,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史的是进步教授滕宗汉(又名滕敬东,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他讲课幽默生动,条理清楚,并且旁征博引大量史实来宣传爱国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我最喜欢听的反而是历史课。兴趣是一个年轻人最好的向导。这样,在我1949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时,因为它没有教育系,我就决定转入历史系学习,先读本科,又读研究生班。
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治学经历,从而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学术风格。请朱先生您结合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读研究生时,主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8月毕业后,从东北来到中原,任教于河南大学,主讲课程是中国古代史上段(从上古至南北朝)。我在工作后的前三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等在课堂上站住脚后,然后才开始搞科研。我的体会是,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容易发现问题,科研会无的放矢;不搞科研会使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就浮在表层,人云亦云。教学没有坚实的学识基础,不可能把课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效果不可能好。
我刚开始搞科研时,主要是跟着史学界的热门课题跑,自己还提不出问题来,这就说明自己对科研还没有真正入门。上世纪50年代,史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又被称为“五朵金花”,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其中除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外,其他方面我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对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的课题写文章较多。所以我的老乡、陕西师大的赵文润教授开玩笑,说我也是靠农民战争起家的人。
跟着热门课题跑了一段以后,我认为这样不行。如此随大流,人家顶多认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成员,而你很难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成果。于是我就思考出几个“冷门”课题,如军功爵制研究、户籍制度研究、治安制度研究等。我认为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但当时还没有人深入进行专门研究,我如果进行拓荒,即使成绩不大,也会有创新意义。
在这几个课题中,我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坚持得比较好,先后出版了《军功爵制试探》和《军功爵制研究》两本书,而且我如今正在对后者做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根据近一二十年新发现的秦汉简牍中有关军功爵制的资料,可以把过去人的错误认识订正过来,把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增补进去,算是给我40年的军功爵制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于户籍制度的研究,我只是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两本书中,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阶级阶层的地位变化等涉及宏观历史演变的一些根本性东西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古代治安制度我自己除了写过两篇文章外,没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但是我曾经组织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共同撰成一本65万字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对中国古代历朝的治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在课题研究中,喜欢写成组的系列文章,我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把自己对某一课题研究的时间拉长,方便个人全面思考进而能渐次深入,以便最终解决某一问题。二是便于全面详尽地搜集资料,并使资料在写系列文章时从不同角度得到充分的利用。三是有计划地写成系列文章,每一篇文章就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排列起来显得很有逻辑和层次。四是把系列文章组合成一本著作,这样的书可以保证内容充实,观点和材料结合紧密,学术成果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如果是先定书名,再执笔写书,容易使人走东拼西凑的捷径。我写的《军功爵制研究》和关于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几本书,都是由先期发表的系列文章组成的,书中的每个课题都是我长期深入研究的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
问:朱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研究的领域牵涉诸多方面,除了十几部专著和教材外,您还撰写了150余篇论文,可谓硕果累累。请问您的代表作是什么?并请展开谈一下该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
答: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我认为比较有特色的还是《军功爵制研究》。这是我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过程中发现并加以研究的问题。在读史书时,经常会遇到赐爵的问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中都记有二十级爵制的名称,特别是在涉及秦的历史事例时,好像爵位比官职还重要,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下决心搞清这种爵制的来龙去脉和它的产生背景、演变缘由及其作用价值。秦汉简牍的不断出土,给我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长期研究得知,这种爵制的名称叫“军爵制”,通俗地被称为“军功爵制”,是秦汉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军政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反对西周带有世袭性质的五等爵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
这种爵制对立有军功和事功的人员既赐给爵位,又赐给田宅,与名田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斗争中,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军功爵制曾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秦代,爵位重于官位;在汉初,大小官吏也都拥有爵位,因此通过赐爵培养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是从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衰落而趋向轻滥,从而也不再被人重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对这种制度就记载甚少,使之几乎湮没无闻。我对此加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搞清军功爵制曾经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我根据秦汉简牍提供的新资料,进一步解决了军功爵制研究中的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如刘邦在入关前和楚汉战争中施行过楚国爵制的问题,军功爵制中有侯爵级、卿爵级、大夫爵级和小爵级共四个等级的划分问题,汉初以爵赐田宅的具体实施问题,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以及爵级与官级的对照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军功爵制在秦汉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把握秦汉社会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问:在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者准备构建一个学术体系?而这种成体系的学术课题的确立,又主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答:搞学术研究,不可以没有计划,也不可以没有长远的规划。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即兴涉猎浅尝辄止的做法,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具有相当分量的和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著作成果。我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军功爵制,都是长期计划下的产品。前者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后者我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研究。我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目的,是想搞清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演变情况、中国古代剥削关系的演变情况以及土地制度对剥削关系演变的作用,并由此最终通过这些研究,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及其演变,我在读大学时就知道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就正式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大学任教后又知道了史学界存在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的学术争论。我还知道土地制度史上有个普遍规律,即先有公有制,后有私有制,在二者之间有个土地长期占有制。但在中国以往的土地制度研究史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过渡环节。于是,我在研究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名田制(或称受田制、辕田制)时,认识到名田制就是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按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其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有三点改变:一是废除井田制下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土地定期轮换制,改为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二是亩制计量改小亩为大亩。周的亩制是百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仍百亩给一夫。三是土地占有与军功爵制挂钩。商鞅宣布“明尊卑爵秩等级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按每人军功爵位的高低不同,赐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允许立有军功者在原基础上再加赐田宅,斩一敌首“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这样,不论是庶民受田还是军功赐田,都是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国家并没有明令放弃土地所有权,对授出去的土地,国家有权干预甚至是没收。但是,土地制度的演变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即土地一经被长期占有,早晚会转化为私有。所以到秦朝末年,土地就出现可以买卖的私有现象,甚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使人口大量死亡,无主荒地增多,所以西汉初又恢复了秦的受田和军功赐田制。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相关条文看,庶民受田仍是一家百亩,而军功赐田则数量惊人——关内侯最多可赐田95顷,赐宅95宅;卿级爵可赐90顷、90宅,大夫级最高的还可赐25顷、25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功赐田与庶民受田制度的回光返照。经过汉初70年的发展,到西汉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又几次出现新的高潮,于是官方就推出了“限田限奴”、“王田私属”等应对措施,其理论根据正是古代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时转世移,效果微乎其微。到了东汉,政府再没有实行过庶民受田、军功赐田的政策,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已成大势所趋,不会再遇到干预,田庄经济遂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中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三国时土地国有制一度抬头,西晋占田制实际也是土地长期占有制。北魏至唐早期的均田制,对大田是有授有还;但在具体执行时,又不是土地重新分配,而是在原来私有、私人占有的土地上作一些调整,出现了公不公、私不私的状态。至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至宋“田制不立”,土地私有制才在不受任何约束的形势下发展下去。以上就是我对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史上的一个概括性认识。
关于剥削关系,我研究的重点是考察秦汉魏晋南北朝租税制度的演变。在秦汉时期租与税的含义与后世恰恰相反,当时的“田租”就是后世的土地税,当时的“地税”反而是后世的地租。土地税(田租)是各种形态社会所共有的,只有轻重程度之分,没有性质的区别。而地租(田税)却具有封建属性。从秦汉的历史来分析,地租首先是从私有土地上产生的,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然后国家利用“假田制”而收“假税”,即在国有土地上也收地租,对假田农民实行封建性的剥削。曹魏屯田制就把国有土地的地租正规化,西晋的占田制、租调制同样也是在国有土地上征收地租,而荫客制就是把汉代地主对农民不合法的剥削进一步合法化,国家把一部分农民转让给豪门地主,农民与地主之间建立了封建租佃关系。均田制是国家以地主的身份,剥削均田农民,均田农民沦为国家的佃农。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租税制度的演变趋势来观察,是封建剥削关系的逐渐强化和正规化。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
关于各种土地制度的历史作用问题,说名田制、假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在一定时期内都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家并无太大歧义。但对于我认为在私有土地制度驱动下,西汉中期以后广泛兴起的田庄经济这种劳动组合形式也有进步性,在当时却遭到学术界的普遍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田庄的所有者是豪强地主和门阀士族,他们生活腐朽,剥削残酷,实在体现不出来历史的进步性。我理解反对者的理由,但我认为田庄是一种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经济体制,比起汉初的小农或地主单一经营机制有很大优越性。特别是在战乱时期,田庄和坞璧(适应战乱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田庄组织)对保护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具有积极作用。这种观点以前常常被作为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我在大学本科时学的是“西周封建说”。当时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盛行一时,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主张此说,故当时我想当然地服膺此说,就不知道此外还有其他观点。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陈连庆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说”,同时我所敬仰的唐长孺、何兹全、尚钺、赵俪生诸先生也都很坚定地持此观点,于是我也就转向对“魏晋说”坚信不疑。在大学任教以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占了优势,成为主流。随着《中国史稿》的正式出版,我在教学和编写《中国古代史》讲义时,又采用了通行的“战国说”。对以上三种分期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魏晋封建说”,但我基本上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的专门研究。直到我开始研究军功爵制之后,发现在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中,有“乞庶子”一条。庶子对于有爵位的人,在平时“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也就是说非战时庶子应该给有爵位的大夫一月服六天劳役。到了战时,庶子则跟随主人从军服役。我认为庶子与其主人之间是典型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军功爵制中的“食邑制”,实际上也是封建主向其领地之民收取封建租赋。由此我就确认,中国封建社会应该从战国时开始。这种认识不管正确与否,它是我自己独立研究的结果,与以前那种人云亦云的“观点”应有所不同。
关于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一开始我是对二者分别进行研究的,也曾认为它们各不相属。等到这种研究越来越深入之后,我才发现军功爵制与名田制是同时兴起、同步发展,而且是同步衰亡的。于是我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说井田制是西周世卿世禄制和五等世袭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战国之后的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所谈的互相关联的诸多学术课题,也可以看作是我有计划铺陈设置的一个学术体系。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促进,都使我能够更好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规律和品性特点。
问:朱先生,以上所谈,确实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您为自己所构建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您确实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了您学力的宽广的一面。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一些“计划外”的研究项目的?
答:我说过,搞学术研究不能没有计划,也不能没有长远规划。但学术界有时需要互相协作,搞一些非单个人所能承担的跨界大工程,比如编写带有“通”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另外,这些年各地兴起寻根热,海外和大陆各界寻姓氏之根和文化之根,我也难免被邀参加一些研讨论证会,写些临时性的题目。
我先后主编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历代宰相传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叶姓溯源》、《后汉书精言妙语》、《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今注宋书》等九部书。其中除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叶姓溯源》等属于论文集,不需要我花费太大精力外,其他都是先由我拟定提纲,物色作者,然后由多人进行合作撰写的。在修改书稿时,主编又要统一文风,统一观点,统一体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不亚于自己写一本书。我曾说:“编书不易写书难。”大概没有狠下功夫编过书的人,很难体会个中甘苦。就拿主编《中国古代史》来说,这是教育部组织山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十院校合作编写的本科教材,最初有两位教授宁愿退出也不愿担任主编。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个学校的人合作编教材,意见都很难统一,现在十个学校的人在一起编教材,这协调工作怎么做?等我接受了主编任务后,才真知道了其中的难处。
首先讨论“中国古代史编写大纲”。小组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每个人的理由都很充分,意见很难统一。但一部教材不能容纳五花八门的不同意见,自相矛盾。我一看没有办法,就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解围。当初在《中国史稿》的编写研讨会上,也是各种意见互不相让,范老站出来说,在延安我编《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大家意见不能统一的问题,我就说我是主编,应该按我的意见办;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要按郭老的学术观点、思想体系和具体意见来编写。大家听我一说,也就不再争论,《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大纲就按我的意见确定了下来。
然后就分配编写任务,用半年的时间由各院校执笔人分头撰写,中间在开封还有一次小规模的样稿审定会。但后来等到书稿集中,我一看感到麻烦了。不仅每个人的文风体例很不一致,而且原规定的字数也大大超出。原来规定要用精练的语体文,分期采用“战国封建说”,每章都有字数限制,全书不超过90万字。但在交上的稿子中,有的接近文言文,有的是白话文,而西周那一章则写成了“西周封建说”,字数有的章竟超出一倍之多。我对实在不合要求的退回修改,多数稿子留下来由我来“统”,文言的改“白”一点,白话的改“文”一点,都向精练的语体文靠拢,字数也被压缩下来。西周一章由执笔人改了两次,还是不合要求,最后只得由我完善。令人欣慰的是,“十院校”同志间的关系非常好,包括几位老先生都欣然接受我的修改意见,这就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但是,等到在桂林开全书定稿会时,与会者还是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我肯定田庄经济、门阀士族也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的表述不同意。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先生,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两人的意见经常是一致的,但对这一问题他绝不让步,他说主要是怕犯原则性、阶级性的立场错误。我对他说,“文革”后学术界开放许多,肯定统治阶级及其制度也有一定的历史积极性,这种观点是会被接受的。他说,不,门阀士族的反动性腐朽性太明显了,田庄是豪强、门阀的经济基础,剥削太残酷,不能肯定。我说,东晋的王导、谢安都是高级门阀的代表人物,他们不都是很有作为的宰相吗?田庄和坞壁在战乱时对社会生产不也很有保护作用吗?海鹏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我的意见,没办法我也只好把门阀和田庄的积极作用改得模糊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