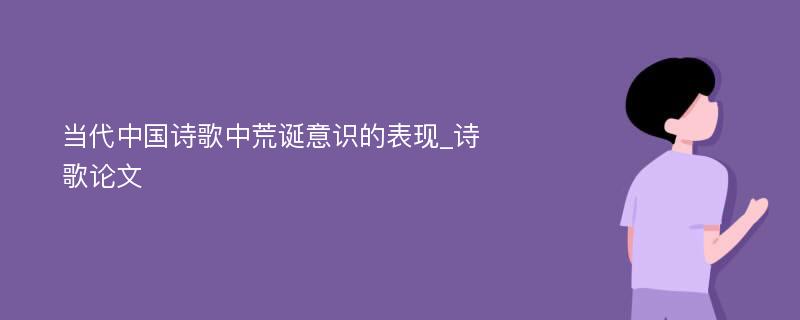
中国当代诗歌荒诞意识的表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论文,表现形式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诗歌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荒诞意识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借鉴,荒诞意识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荒诞意识。首先是以文革后期产生的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对荒诞现实的揭示与否定;其次是诗人对自我生存的荒诞性的表现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对诗歌的缺席;最后是由于当代诗歌对历来诗歌语言传统的否定与重建所导致的诗歌文本的荒诞。
荒诞,从逻辑上来看,是对传统规范的背离与重组;从艺术上来看,是由审美转向审丑;从价值体系上来看,是对“上帝死了,而人还活着”(尼采),或对“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福柯)观念的认同。当人发现了现实与人生的支离破碎和毫无意义时,荒诞感便油然而生。荒诞有时是不可理喻的,但绝不是无意义的。“它们背叛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叛了内在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内在的可能性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魅力。”①桑塔耶那这句概括怪诞的话,借来表述荒诞也恰如其分。怪诞与荒诞原本就有血缘关系,都是对现实的重建与再造;不同之处无非是怪诞更多涉及形象的陌生化,荒诞则侧重事态上的有悖常理,诗化的荒诞其意义首先在于对无意义之现实的揭发与反动。而真正的诗人必须在意识到现实与自己的荒诞的同时又超越荒诞,在对死亡的无限趋近中展现生存的意义,在远离现实的荒诞中复苏人们对“家”的回忆;在这种南辕北辙的回归中,让人们尽一路风景。
目前,有人持严肃的荒诞写作态度,有人转向对小农经济与市民生活的温情吟唱,有人放弃所有的责任开始梦呓,有人则纵身欲入死亡的深谷。(如:海子、骆一禾、顾城,无论海子是否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但他无疑是最值得一提的,他短短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麦地诗。最终穿越他在虚无中开垦的麦地走向死亡。)中国诗坛并不存在荒诞派。正因为如此,荒诞意识并非为某派特有,而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诗歌的各个层面。是整个诗坛的特征之一。
一、对荒诞现实的否定与揭露
荒诞作为一种审美范畴,首先是基于审美主体的人对现实的怀疑与否定,是作为个体的审美主体对社会群体的拒绝与疏离,诗的荒诞源于被意识到的现实的荒诞。荒诞意识在诗中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对现实的否定。现实对于科学是剖析的对象;对于哲学是思考的对象,而对于诗则是必须超越与重建的对象。自从意识把人从自然中凸现出来,把个体的人从群体中分拣出来,个体与身处其中的现实一直存在着矛盾。诗与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发现并且介入现实的荒诞,从置身于荒诞现实与人生中而不知觉到认识与否定现实与人生的荒诞是一种进步。
中国与西方传统中,以不同的方式否定了人的存在。中国儒家哲学把人固定在“礼”与“仁”的经纬上,以道德实体代替了人的终极价值。而道家则力劝人们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和光同尘,以枯木与死灰为理想的人定位。儒与道分别设立了社会与自然这两个实体作为人的归宿。而西方则为人设立了“天堂”,把人归结为原罪的,神与无国成为人必然的终结与归宿。
中国哲学历来缺少对个体的关怀。所以诗不得不站出来,代替哲学给人命名。中国第一位浪漫诗人屈原在发现现实的荒诞性的同时,表现出极度的自恋与自虐,最终导致自杀。屈原的死亡不是一个遭贬的爱国者的死亡,而是一个被现实拒绝的人的死亡,而导致他死亡的最终原因则是以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不断追问中觉醒的荒诞意识,屈原是当代一部分中国诗人的原型。
中国是奉儒家为正统的特定区域,在几千年的造神运动中,多少圣贤在这块土地上羽化登仙。人,一直是“礼”即秩序中的一环。如已故诗人顾城所说:“我在什么面前是一粒沙子,一颗铺路石子,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总之,不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②而“大跃进”等一系列国家浪漫主义运动台日中天又被全盘否定后,诗人们从小沉浸其中的理想、信念、道德标准崩然倒塌,从集体迷狂中苏醒的人们又深刻地感到现实的虚妄与荒诞,如北岛所写:
我弓起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
北岛《履历》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从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猛烈地撞击着茫然而贫穷的国民。带来“神”的死讯。在政治的高压下扭曲的传统也悄然伫立于人们面前,被重新审视。勿庸回避,当代中国人对现实荒诞性有如此深刻的体验除了现实原因外,其思想基础是近年来在国内盛行一时的尼采、柏格森和存在主义哲学。使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从哲学的高度,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到了世界的荒诞。
随着神的倒塌,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人们以悲剧英雄的形象从理想的废墟中站起来,努力驱赶着荒诞的梦。朦胧诗人的歌唱是迷惘的。但他们在执着地寻找着。这首先源于人对终极价值的需要,同时也源于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每个诗人的历史使命和诗人对爱与美的本能的追求。出现了包括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北岛的《睡吧,山谷》以及流传极广的顾城的《一代人》在内的一大批诗作,都体现了寻找的主题,不仅仅为诗人自己,而且为一代人立言: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这些诗充满了对荒诞现实的后浪漫主义的超越与批判。以及“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忧患意识,他们承接了《离骚》的一线血脉,也铭刻着醒者的痛苦与迷惘。虽然诗人们不承认自己是英雄。如北岛所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宣告》)。但既然上帝已死,北岛们还是不自觉地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与“寻找”同步发展的是“愤怒”主题。这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的佯廖与佯狂,而是受西方某些哲学流派及诗歌作品影响的个人心灵的渲泄。诗人芒克在《街》中用类似口语的句子罗列了一系列现实的荒诞图景,结尾处诗喊出了他的愤怒:
现在真想发疯似地喊叫让满街都响起我的叫声
芒克《街》
早期朦胧诗人食指在诗中多次描写过“愤怒”并最终把“愤怒”推向“疯狂”:
受够无情的戏弄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有生的权利
食指《疯狗》
如同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一样《疯狗》是中国式的“嚎叫”,在礼、法及“哀而不伤”等诗歌传统中,在中国特有的灰色大地与人群中,我们感到食指面对荒诞现实的欲疯不能的压抑与绝望。海德格尔认为疯狂是人类在绝望顶点的自我保护本能。在荒诞的现实中,疯狂也是朦胧诗人所表达的普遍欲望。而在中国生命激情自由渲泻的阀门却被理智锈蚀了。但以《嚎叫》为代表的一系列外国非理性诗歌作品的涌入,毕竟点燃了中国诗人疯狂的欲望,虽然金斯伯格们与食指们面临不同的社会现实,但其本质都是荒诞,这是西方诗歌作品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诗歌的原因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新时代的诗人们面临的是膨胀的城市与商品与由此而引起的人的疯长的欲望。人们一面背井离乡向城市蜂涌,一面咒诅着城市。乡村是宁静的,也是贫穷与孤寂的,城市是繁华的,也是虚妄与荒诞的,因为在繁华中孕含着更深刻的孤寂。在人与人的摩肩接踵中,诗人更深地感到人与社会的荒诞。城市群孕育了以宋琳、张小波等为代表的“城市诗派”,以及一大批未被划入这个诗派的散兵游勇。诗人们目睹了继上帝死亡之后英雄的死亡与痛苦。于是不再相信英雄的诗人们只企图固守自我了。失去疯狂欲望的诗人们转而让人们相信现实的疯狂与不可信。他们挤在楼房越来越窄的夹缝中执拗而任性地叫“不”:
你不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女人
失常的是这场下了很多年的雪
这样地下着 下着 下着
宋琳《雪地情书》
这是世人眼中的一个疯女人,也是诗人眼中的情人与一场雪,原有的判断标准遭到否定,人的正常与否不由医院证明而定,雪也不因冬去春来而停止。诗人通过认同一个精神病人而否定现实即那场雪。虚幻不实但又冷酷地无休止地纠缠因保持独立人格而忍耐的情人。雪是“失常”的因而是荒诞的。诗人喃喃道出现实地荒诞。绝望,忧伤多于愤怒。“情人”无疑可解读成恋人,作者的理想或精神归属。
从诗集《城市人》中,我们可以发现波德莱尔、艾略特、金斯伯格等人的影子,以及所有城市的共同意象,例如“人群”:
我不能看那些脸,那些浮着灰尘的吸盘
鼻子贴在明亮的空气里
失去了愤怒
宋琳《人群》
庞德描写过从地铁车站拥出的人群,艾略特描写过穿越伦敦桥的人群,而波德莱尔的目光则永远落在人群中。人群是城市最根本的最普遍的特征。诗人“不是把人群当成避难所来看,而是作为诗人捕捉不到的爱来表现。”③宋琳在《人群》中描写人群、酒巴、大河、读报者。但我们却读出了深陷人群中的中国诗人对人群的拒绝与陌生感而不是西方诗人在人群中的亢奋与激动。“人群”毕竟与古老中国的理想国——“小国寡民”相悖,诗人把人群中的面孔转换成“浮着灰尘的吸盘”转换成“这样下着下着下着”的雪花。最终要问的一句只是“我之外一切都是距离吗?”(《人群》)这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诗人置身于貌似“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景象中必然的疑问。是诗人与他的愤怒被人群冲散后留下的距离。城市诗人在人流的不断冲刷中涤尽了对荒诞现实的愤怒。
朦胧诗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对个体的认同与坚持,包括一部分城市诗在内的后朦胧诗已经不再坚持与愤怒,而是以冷静的态度呈现现实的荒诞本质,但诗人避免发言。如艾略特所说:“诗人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④个性仅仅体现在诗人对事态的选择中,这是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欲说还休的沉默,感情由事态本身来承担。诗人从诗歌的中心转向边缘,出现了诗人对自我的消解与对诗歌的缺席。如:
人能干什么
我们修房子,然后进进出出
我们造船开路 然后来来回回
我们垒砌石阶 然后上上下下
活一天算一天 折腾一生
唐亚平《主妇》
作者对现实进行了鸟瞰,罗列了一系列的现实图景,并且在每一个诗行的下半句,以一个无意义的动作“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等对上半句人的主体活动“修房子”“造船开路”的意义进行消解,最后一句是对以上诸句的消解。房子由传统意义上的“家”还原为房子。“上上下下”不再是“上下求索”而仅仅是无目的的动作。没有形容词,也看不见赞美、斥责、愤怒等情绪,诗人被现实消解。在不加修饰的叙述态度中,我们看见了现实本身,无目的、机械、刻板。如果这段文字没有被分行排列,并在每句间加上连词,那就成了一段无味的不折不扣的散文。正因为分行排列;因为四周空白的装裱,它才成为诗,诗人对诗的缺席是后朦胧诗中的特有现象。八六年南京诗人韩东等人成立的诗社取名《他们》,便是极好的例证。由此,诗由对现实荒诞揭示滑向了对诗人自我荒诞意识的挖掘。
二、表现诗人自我的荒诞
在几千年人与社会相对稳定的共存中,意识一直未停止发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意识在不断发问的同时唤醒了个体。
在哲学上,存在主义的局外人代替了尼采的悲剧英雄,解构主义使人从世界的中心转到了边缘。“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代替了“上帝死了人还活着。”荒诞人生交织着荒诞的现实出现在诗中。中国人尤其是道家以形而上的追问一层层剥落了人与群体,心灵与肉体的联系。比西方更彻底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荒诞性与虚无:
这蝉声浓浓地遮住了我
一遍遍褪去我身上的颜色
最终透明地印出我来
哦,我已经是一个空蝉壳
微茫《听蝉》
道家和佛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人的价值的相对性和虚妄不实。甚至最不强调生命体验的儒家也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封建社会的解体,把大部分人抛出了世代栖息的村庄,被迫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人们之所以纷纷逃离村庄是因为乡村不再是陶渊明笔下那个可以“戴月荷锄归”的村庄了。城市以各种方式向乡村扩张与渗透,乡村作为现实中的归隐处已成往事。无人合一还原为神话。战争造成人类的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特别是文革摧毁了中国文化传统、信仰、梦幻。作为英雄的朦胧诗人被商品与吵嚷着的芸芸众生淹没。随着各种社会准则越来越精致细密,同时出越来越模糊、空泛,生存沦为技术性的操作,诗人们绝望地意识到人的倒塌与自我的异化;看到人格道德的瓦解,终极价值的消失使自我的存在成为荒诞。生存的荒诞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精神的瓦解与失落。诗对现实的超越与重建荡然无存。
于坚作为当代中国诗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跨越了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到这种流变。
在北大未名湖丛书之一《新诗潮诗集》中他以一个纯朴的山里人自居,发现了城市的荒诞。并以山里人的憨厚原谅了城市:
我翻过你们的家谱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我来告诉你们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于坚《山里人的歌》
母亲与故乡是人们的归宿与寄托,诗人对于现实有着自信,对于“城市人”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是母亲与故乡的使者,带着祖训的家法来到人们中间,而在《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于坚写到:“我们的玩具是整个世界。”“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装得象个人”。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玩世不恭的诗人。作为一个诗人,想玩弄世界的于坚终于被世界玩弄了。在《中国青年诗人十三家》中,原来就有口语化倾向的于坚变得更加口语化了,但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口语,而是唠唠叨叨,充满幸存者的窃喜。于坚终于“装得象个人了”——一个异化了的人!
儿子们拴在两旁 不是谈判者
而是金钮扣 使您闪闪发光
您从那儿抚摸我们目交光充满慈爱
象一只胃温柔而持久
使我一天天学会做人
于坚《感谢父亲》
作为一只胃父亲是温柔而残忍的,他(它)消化一切,吞噬一切,一旦进入没有任何活物能够生还,死亡也就成为诗人必然的命运。诗人异化成一只钮扣,这使我们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但于坚的死更为彻底,由一个人变成饰物。父亲是中国千百年来王权父权的象征,也是当代社会的象征,父亲对于坚的吞噬是儒家的礼、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虚无对人的吞噬,对于此,于坚无可奈何,但仍然充满感激。
如果说于坚在荒诞中感到幸存的窃喜而另一部分诗人则感到了荒诞中的绝望与分裂。“蟋蟀”作为一种象征在吕德安的诗中反复出现。代替了古典和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象征物:鹰、鹄、竹、梅等。这个意象直接来源于西班牙现代诗人洛尔伽的《哑孩子》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把它带走的是蟋蟀之王)
“在一滴水中
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
……
“(被俘在远处的声音
穿上了蟋蟀的衣裳)”
洛尔伽《哑孩子》
吕德安在其中发现了人与声音的分裂及人与蟋蟀的契合,发展了朦胧诗的“寻找”主题对人的本体价值进行了进一步寻找:
在繁星寂寞的夏夜
如果有人用耳朵听出蟋蟀
那就是我睡眠中的名子
如果有人奔跑过一条大河
去收回逝去的岁月
那就是披绿的蟋蟀之王
吕德安《蟋蟀之王》
蟋蟀和夜晚相联,蟋蟀不断被驱使着互相厮咬,蟋蟀离将到的秋天不远。蟋蟀在杂草和乱石的压迫下不断哀鸣。这是“披绿的蟋蟀之王”也难以逃脱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尽管如此,诗人还是向“逝去的岁月”作了最后的逃亡。
《蟋蟀之死》是移居美国后吕德安的新作,在这组诗里吕德安以无边的寂静与虚空为背景从各个角度描绘了一只蟋蟀的各种死亡。吕德安拒绝感谢、拒绝幸存决定了他的诗与于坚的诗有完全不同的氛围与基调:抽象、孤寂、焦灼与绝望:
“再没有比今夜更暖昧的夜
我们听见一声叫喊越过头顶
用一个人的名子喊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消失在哪条街
因为在声音中断的时候
寂静仍是寂静”
吕德安《蟋蟀之死》
这概括了人的一生,包括人生的时空经纬,时间从精确重归混沌。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被从他的各种情感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符号。从虚无归于虚无。符号的消失就意味着人的死亡。吕德安最终识破了社会与自我的双重的荒诞。名子作为符号是每个人最真实存在,人作为符号的存在比作为情感的存在更永恒。现实与人的无意义最终被转化成诗的意义。吕德安在诗中对现实与人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化的思考,放弃了诗歌对一切优美事物的爱好,在最大限度内放弃了诗歌传统。因而导致了:
三、文本的荒诞
诗歌的悖理不仅相对于现实与人生而言,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打存了人们所习惯的诗歌文本的秩序。从本质上来看,诗歌比别的艺术形式更易导致荒诞。如李白的诗中有:“白发三千丈”的句子。在现实或小说中,这都会造成荒诞效果,但由于诗歌特别注重夸张性、非叙述性,所以,其一定程度非现实性已经形成传统,被人们认同。“诗的”便可以理解成“不那么可信的”或“不合逻辑”的。因而本段所论述的诗歌文本的荒诞不是产生于对现实秩序的违背,而是由于当代诗人打破了人们习惯的传统诗歌文本的秩序。诗歌语言历来是不断变化,创新的。但这种变化与创新是在一定度的范围内遵循一定“诗格”与:诗式”的创新。而当代某些诗歌语言的变革打破了原有的度,变得不像诗歌了。某些诗人甚至以放弃诗歌为代价。以诗歌的名义从事哲学的工作,《蟋蟀之死》便是一例,形成了类于哲学的诗化的哲学。但诗向非诗的转化并不能证明黑格尔所预言的艺术将被哲学代替的命运,而是实现了海德格尔的诗与思的相遇。诗必须放弃一些才能向前迈进一步。诗歌的生命体现在不断放弃与获得中。正如禅宗所领悟到的,一个婴儿不是成长六十年以后的那个老人,但二者却又是同一个人,他必须放弃他的童年才能获得青春。诗亦是如此。对诗歌传统的拒不认领是先锋诗人对诗歌所持的特有的荒诞态度,诗由对语言的提炼转向口语,由抒情言志转向描写生活琐事。传统诗歌也描写琐事,但总期望从中提炼出真、美、趣味。其原则是“以小见大”,而当代某些诗歌仅仅限于对琐事的描写,如丁当的某些作品:
混了一天
脚丫气味不佳不必不安
被子八年前就该折洗
……
最悲哀的是这一脸疙瘩
脸蛋象一座青春公墓。”
丁当《临睡前的一点忧思》
作者沉溺于一个平凡人的萎琐的生活琐事中,把诗歌演化成一种恶作剧,在读者的反感中诗人体验到渎神的快乐。诗歌由审美转向“审丑”,瘳亦武的长诗《死城》写尽了人间丑恶,丑得令人悚目惊心,正如以前的婉约派词,美得让人心驰神荡。这些诗使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不解、不屑。越来越多的诗人(包括先锋诗人自己)频频发问:诗是什么?诗从哪里来?诗到哪里去?虽然大家对此都不甚了了。但我们的确看见诗歌从有限走向无限,诗国的疆界正在向异域延伸,真正的诗人褪尽了风花雪月,在断裂的传统与现实中寻找突围的方式。
目前,更具先锋意识的诗人已从对现实、对生命的探索中转向对诗本体的探索,先行者在陈旧的诗歌传统中发现了新大陆。于是诗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发现。
的确,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一再发现。最早是抒情功能的发现。“诗言志,歌咏言”志便是情感,是具有强烈情感的愿望。《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是其教化功能的发现。这是诗歌的第一次异化。不可否认,这也是诗歌功能的第一次深化。新诗从“五四”开始,一直抵缓地发展着,并承载着政治、教育、宣传等过重的负荷。终于,诗拒绝承担任何功能面转向本体,诗终于不再体现任何意义,转而创造意义。自觉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诗不仅是美的,音乐的,也是否定的、建构的。诗人不是神,却是最具怀疑与叛逆精神的种族。他们悬置了一切逻辑与秩序,使神圣归于荒诞,使现象还原为本真,也使功能归于本体。诗人说要有光,于是一个幻象世界如此强烈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与现实分庭抗礼。
夸张、变形、具体事物的抽象化。抽象事物的具体化都可导致荒诞效果:
“渡过去还是那座岛
你可以梦过去
也可以生病过去
“因此吃过一付药你就能回来
但你执意要去
那你就去死”
周亚伟《东渡》
“渡”是由此及彼的过程,诗人把“此”与“彼”具象为三个层次:梦、生病、死亡,生病作为生与死的中介在诗中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病往往是被动的,但此刻却成为一种经选择的主动行为,药也成为回归的手段。被定语“一付”点化,东方气息扑面。
千百年来,诗歌永远不能达到生存中心的事实,使当代诗人产生对现实不信任的同时,产生了对语言的不信任。普通语言学的引进使人远远看到语言的更大的可能性。诗人纷纷进行了从所指向能指的倒戈。这项工作的意义绝不等同于古人的炼字炼句。古人炼字,仅出于对词语的选择,目的在于强化诗所承载的情、理;而当代诗人对语言的重塑目的在于语言本身。周亚伟的作品《梦边的死》描述了先锋诗人的创作过程。全诗如下:
我这就去死
骑着马从大东门出去
在早晨穿过一些美丽的词汇
站在水边 流在事物表面
云从辞海上升起
用雨淋湿岸边的天才
使他骑着马而又想起离开动物
远远地找死
出了大东门
你的才气就穿过纸张
面对如水的天空
使写作毫无意义
马蹄过早地踏响了那些温柔的韵脚
自恋和自恨都无济于事
而人只能为此死一次
我命薄如纸又要守身如玉
沿着这条河
在辞不达意时用手搭过去
可顺着某条线索退回去躺在第一个字上
死个清白
周亚伟《梦边的死》
写诗被归结为一个生命过程,由词汇、辞海、才气、纸张、韵脚构成。诗的完成也即生命的完成,写诗被诗人痛快淋漓地定性为“找死”,即《东渡》中那种“执意要去”的与现实的彻底决裂体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诗人对语言全身心的归依。而这种死是在“第一个字”上的“清白”的死。这种“清白”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无邪,而是扫除遮蔽每一个词的尘埃和迷雾,还它的原初意义,同时赋予它崭新的意义。周亚传宣布了他重塑语言的决心以及将付的代价。诗人历来必须忍受孤独与痛苦,而当代诗人最大的痛苦,便是神的失落,传统的失落,整个价值体系的崩溃与自我的异化,他们除了语言与自由外,一无所有。每个人都体验着绝对的孤独。体验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苍凉。在远离人群时候,诗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困惑与幻境。人有寻找自由秩序的双重本能,荒诞的结果便是体验无休止的灵魂流浪。如卖火柴的女孩从燃烧的火柴中看到自己的梦,诗人在焚烧灵魂居所的火焰中看到世界的美梦与伤口。这便是荒诞的代价。
对语言的革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诗的荒诞与晦涩,诗歌传统的中断必然导致诗歌传统解读方式的中断。文本的荒诞导致了当代诗歌鱼目混珠的现象,对于这种探索本身在分清鱼目与珠之前,应先给予总体肯定。这是一场对语言宿命论的革命。诗人挪开语言的表层,挪开日常传播中磨灭了灵气的部分,小心擦亮每一个词,使特定语境中的每一个词都不致于被淹没。当代诗歌以重建语言重建了自己的时空秩序,他们把语言看成一个自足的世界,脱离了现实与诗歌传统而投奔语言。诗人醉心于能指的编排,以及对每一个能指可能的所指的参悟。语言秩序是唯一的,而无序则可以以多种方式出现。诗人对语言的探索呈无方向性,在语言的极限内拥有了最大的自由。所以,诗人韩东的“诗到能指为止”被传诵一时,目前有人把“诗到语言为止”理解成:诗到能指为止”,认为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能指的重新编排。其实,每一个能止的移动必然带动其所指的移动与变更,带动了能指背后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覆盖与显露,诗的目的始终在于所指,就象人们以为仅仅挥动了旗杆,而实则他们却昭示了旗帜。
注释:
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②《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1985年版,第29页。
③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3页。
④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页。
⑤《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