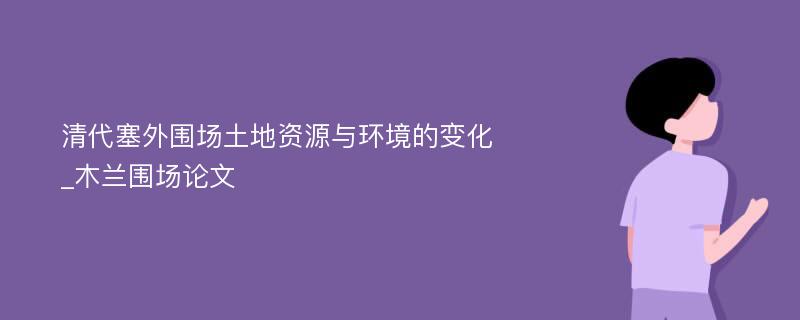
清代塞外围场土地资源环境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围场论文,塞外论文,清代论文,土地资源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的围场,并不是承德木兰围场的特指,除了京郊的南苑围场外,其余都设在塞外,包括木兰、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围场。东北的三个围场,在清初主要作为军事训练基地,外兼皇室珍稀动植物资源的供应。随着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政治统治的加强,文化融合的加快,围场的军事功能逐渐衰减。木兰围场由于地处“蒙古各部落中”[1](P14),自康熙年间设立以来,除了训练皇室子弟习武射箭、继承骑射旧业这一极强的军事功能外,还行使和肩负着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辖与治理等重要政治功能。因此,在大部分时候,“围场”成了木兰围场的代名词,其存在时间之长和受重视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围场。
关于木兰围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已有成果问世①,而东北围场则鲜有论及,有的多是在讨论移民与开垦时兼及环境破坏问题。②本文将塞外围场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从环境史的新角度诠释土地资源利用与社会、环境变化问题。18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认识、需求和利用的增强,土地资源的利用形式和方法随之增多③,规模化地开发森林草原成为人们利用土地资源、增加耕地亩数的另一种主要形式,与其相伴随的是农耕聚居的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于森林草原地带。这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养活众多人口的同时,也产生环境问题于当世,积患于后世。现代环境研究者认为,农业耕作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发展史上影响环境并带有普遍性的一个论题。④
一、官私伐树是围场土地资源利用形式改变的前奏曲
清代塞外围场的自然生态环境以森林草原为主体,伴随着清皇室和百姓对围场资源需求的不断加强,尤其是19世纪中叶后,大量移民自关内涌入塞外,对清廷维持围场原生态资源概貌形成压力,个体或团伙等其他形式的闯入围场偷牲伐树违禁事件不断升级。其一方面促使清廷不得不强化围场管理制度,以显示皇家权力;另一方面,则迫于安置富余人口压力的形势,忍痛改变了最初把围场看成皇家禁苑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的奖励垦荒——定居村落——编入保甲——设官置县的农业制度模式,最终将其纳入国家行政区划管理体系。这一管理模式实施所引发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便是传统的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作为一种环境行为⑤,以新的姿态在森林草原环境中出现,并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环境行为带来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也改变了围场的资源利用形式。
清廷在塞外设建围场,首要目的是为军事性质的行围狩猎,围内常常要圈养一定数量的牲兽保证供给,围内茂密参天的森林植被成为牲兽活动和栖息藏身之处。尽管牲兽和森林同时构成围场地表原生态资源概貌,且环境改变与二者数量、范围变化密切相关,但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资源环境仅限定于牲兽“藏身栖息”的森林资源环境。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官方砍伐、私人偷盗森林树木是围场土地资源利用形式改变的前奏曲,继之,清廷改变管理策略,由禁止私人擅自闯入而为招民开垦。
保护围场牲兽草木,就是保护皇室的利益,是入清以来清廷的一贯政策,颁布有一系列的禁止盗牲伐木条例。即使是皇室利用围场资源,比如要使用木料,对砍伐树木也有严格规定,并特别规定了拣选和固定的围场。乾隆十四年(1749),为保证避暑山庄工程所用木料,限定了允许砍伐的围场,以坚决禁止在留待行围狩猎的围场内砍伐。对于承办者不按规定滥伐了木兰围场中树木者,乾隆帝要求严加追究承办者的责任,同时寻求解决办法,谕令:“其大小净木,并已经伐倒各木,已运未运之数,彻底清厘,不得稍有瞻徇蒙混。所有已办木植,俱令照料运送至京。完竣之后,木兰山场,永行封禁,不许开采。”[2](卷348,P802)但事实上,木兰围场日增的偷牲砍伐之势头已经无法遏制。乾隆后期,人口增多,盗牲伐木日增,开垦也增多。就是在管理相对有力度的乾隆、嘉庆两朝,官方和私人对围场内森林树木的砍伐数量之大也是惊人的。
官方砍伐森林树木,在木兰围场最甚。据手头不完全资料统计,乾隆时期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即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1768-1774)和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1788)。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在永阿柏至他里雅图等22围7处,砍伐堪用回干大小黄红松木 34279件。[3](P190)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在围场北面“莫多图等4围6处”,包括都呼岱围,砍伐回干黄红松木120615件。[3](P116)乾隆三十六年 (1771)十月,报奏砍伐西面英图、巴彦穆敦等围大小木植75 285件。[3](P398,P465)
集中砍伐围场树木的统计数字,相对比较准确。因为伐树进程中,清廷要相应支付一笔砍伐工价和运输费用,故对所伐数量有专人进行严格统计。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查得,三十三年 (1768)所上报的砍伐树木与三十五年(1770)实际拉出围场的树木数量不一致,拉出围场的树木比实际上报的数字120615件多出2576件,也就是说实际砍伐了123191件。[3](P208)据官方统计,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至三十九年(1774)止,所有后围、英图围、莫多图围等3围,原估计共砍伐 346256件,后又续砍了19293件,所以,实际共砍365549件。[4](P406)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继续在黑龙山等3处砍伐103329件。[5](P64)次年七月,在都呼岱、莫多图、哈萨克图、固尔班拜察4处,相连向来不行围、树株稠密处,拣选堪用大小木植共116368件。[5](P71-72)五十三年(1788),在黑龙山、小西沟等处砍伐118116件。[5](P227)三次合计砍伐337813件。
私伐树木也很严重,主要是管理围场兵丁和偷伐者联手共盗。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围场翼长鄂呢济尔噶勒,拿获偷伐树木多人。经查证,共偷伐树3 000余株,且供称是“兵丁伙同民人偷伐”。对此,乾隆帝专门谕令训斥:“围场坐卡人等专司看守,胆敢伙同民人偷伐树木至数千株之多,情殊可恶!复敢恃众夺刀,尤为可恨!若不严审从重治罪,不足以示儆。”[2](卷757,P340)即便如此,依旧做不到令行禁止。
官、私历年砍伐,使围场外缘交通便利处的树木不断减少,可用于建筑等的坚实大木也基本绝迹,至嘉庆年间,危局已不可挽回。嘉庆五年 (1800),为万年吉地工程隆恩殿备用木料时,监办人员就抱怨木料“采觅实属不易”[6](P314),尤其是“大件木植即属难得”。[7](P178)实际需用3 000件木料,采办中只挑选到2000件“坚实黄松”,而真正砍伐所得仅233件。[7](P174)后来在按巴鸠等8围“围边岔沟、不碍围场之处”砍办大小木植59884件。此次采办木料,除了莫多图、哈萨克图、都呼岱、巴彦穆敦等4围,以前曾经砍伐过树木外,按巴鸠、森吉查罕扎布、永安湃、博里沟等4围,则是此前从未砍伐之地。[7](P180-181)更有甚者,要将拣选砍伐的黄松大木运送出围,还需要在围内开挖简易道路。为此,就势必将“所有此路树株自应就势砍伐”,为拉运“黄松大木”开道,进一步加大了对围场森林植被的破坏。
嘉庆七年(1802),为保证官方伐树工作顺利进行,在围场内安设山局,搭设窝棚。是年,在都呼岱、英格川、努呼岱、长林子、固尔班、拜查等5处围场共砍伐118000余件,其中仅努呼岱一地就砍树19100余件。[6](P187)
围场森林大面积减少、破坏后,其阴翳泉源、蓄水造雨等功能也势必随之减弱乃至丧失,导致泉源枯竭,水草不丰,牲兽逃逸他处。人们对围场森林无休止地砍伐,使围场逃脱不了走向衰败的厄运。嘉庆九年(1804),皇帝对“谎报恶化情势”十分生气,因为他在巡幸时发现,有14处留待行围处的森林被砍伐。至十一年(1806),围场内“砍剩木墩余木甚多,兼有焚毁枯枝犹在,往来车迹如同大路,运木多人,各立寮铺”[8](P16),以至于“国家百余年秋弥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9](P550)至咸丰时期,尽管也三令五申饬禁围场地方私伐树株,不得任意开采,不得“偷射牲畜,开垦地亩”,但面对人们对资源的渴求索取情形,终无济于事。不得已,只好改变对策,晓谕众人,一旦“经官方批准”,就可以开采围场树木。[10](卷14,P375)放任的结果,至光绪三十一年 (1705),则完全“设屯垦木植总局以经理之木植”。[11]木植局大肆滥施砍伐,以兜售木材获利。
木兰围场森林地是如此结局,其他围场也不例外,也存在森林被伐、捕杀动物、私垦加大的现象。嘉庆八年(1803)七月,仅盛京、高丽沟地方,就有20000余人从事“砍伐树木售卖之事”。[9](P550)道光六年(1826),盛京、吉林一带冬围,“猎打数围,未获一鹿”。[12](卷114,P915)次年又查得“原为禁止偷打牲兽、砍伐树木而设”的卡伦官兵,为谋柴薪小利,不断做私放百姓砍伐树木、惊散牲兽之事。[13](卷707,P803)更有甚者,官私偷盗者携带鸟枪进入围场,在捕杀动物的准确率和杀伤力加大的同时,枪声也惊吓动物四处逃逸。至同治七年(1868)再查时,吉林围场“南北十七八里,东西八十余里”的广阔之地,“皆无树藏牲”。所以,行围废止的结果是围场之内“游佃偷越”[14](卷3,P7525),进而逐步开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口增加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人口的增加和毁林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却是确定无疑的。
二、为安置人口把农耕环境行为实施于森林草原区
森林砍伐后,表现在自然生态环境上的变化,就是森林地大规模地转换为农耕地,昔日塞外森林草原景观改变为农田村落。不过,这一进程几经曲折,如何安置激增的人口成为清中央和地方官头痛的病根。清廷在强制腾围和弛禁放垦策略之间颇费周折,最终选择了放垦。
改变围场封禁状况,与清廷解决京旗人口生计有直接的关系。被清廷移往木兰和东北围场的旗人,并不热心农耕,这些人将官方划归给自己的土地,又采取私下招民、隐蔽转包的形式出租给移入民耕种。但旗人招垦一来远远消化不了涌入东北寻求生计的移民,二来清廷恐怕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有碍旗人生计,阻止移入,结果陷入两难境地。在安置移入民的过程中,尽管放垦的时间早晚不一,招垦情形也略有不同,但个中显示清廷对围场管理和开发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塞外围场的放垦大致以咸同之际为界,经历了嘉道至咸同时期的严禁到松弛与咸同至光绪年间的招垦到放垦。嘉道时期,清廷并不情愿在围场区域安置人口,还竭力采取设置封堆、部分放垦等措施,阻止和限制人口进入围场,甚至采用腾围的办法驱赶已经进入围场的移民。但至光绪年间,面对自发移入的大量人口,清廷只有放垦之招,没有了封禁之势。
嘉道年间,吉林和木兰围场虽然严禁垦民进入,但边缘地带已经渐次开垦。木兰围场于道光初年(1821)停围后,仅将梨树沟等处闲荒拨给兵丁垦种,依旧采取封禁管理办法,禁止附近围场“招集外来流民,影射占种”。[12](卷31,P556)这种状况基本保持至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间,围场边缘至进深的围荒逐渐展开,垦殖如满弓在弦,一发不可收拾。木兰围场在经历了清廷限垦、腾围、招垦和放垦四个阶段的政策调整后,资源生态系统改变,农业人口急剧增加,步入近代开发历程。
同治元年(1862),顺天府尹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后,允许闲散流民、旗民开垦禁地。次年,施行新的开垦政策,允许招民开垦围场边闲地,酌拟升课押荒章程。招佃开垦热河围场边荒地8 000余顷。[10](卷70,P412)四年(1865),查得已放出边荒地 1492余顷。[10](卷131,P108)此次招垦不仅垦殖了边荒,也侵垦了正围,出现了“招佃展垦乃日久展放,漫无限制,以致侵占正围”的危机态势。对此,清廷谕令禁止在围座伊逊川一带开垦荒地,且河东、河西已佃垦、私垦地亩,一律封禁,并饬令督修卡伦,建立红桩,不得任意展垦,侵入山坡沟岔的私垦户也一律驱逐。[11](卷271,P765)尽管限制开垦,但经同治二年(1863)至八年(1869)的限地开围政策,木兰围场有31处变为农田;继之,开垦不已。
同治九年(1870),经木兰围场官员库克吉泰考察,垦荒已大面积侵占正围,旗佃侵地600余顷,民佃侵地800余顷。对此,清廷谕令“务将正围以内民户,尽数迁出,以清围地”[10](卷297,P1116),实施坚决腾围政策。“令该民佃按照原领系何旗围内之地,即以何旗围外之地如数补给”。[10](卷313,P137)“于东围民佃地内,丈查余地,补还旗佃”。[10](卷325,P298)腾围结果“围场八处,及跸路经过之所,均已一律腾清封禁。其应补民佃之地,亦陆续补足,并于各要路总口立界设卡。以免侵越。”[10](卷313,P137)木兰围场经两三年的腾围,正围基本腾清。但闲置的土地资源,一直吸引着不断增多的为了维持生计的流民。清廷一厢情愿的腾清事件结束不久,“复有民众擅入耕种”,令清廷头痛。“有刁佃于茂等率领二百余人,蜂拥而至,施放枪炮”。“并抢去军械等件”。围场湃布嘎沟门一带修建的卡房,“突被佃民烧毁,并拆倒大墙六十余丈”。[10](卷347,P577)这场资源争夺战虽暂时以佃农的失败而告终,但开发已成趋势,是近代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缩影。
迨光绪初年,移民日众,户口渐繁滋,加之清廷也急需开发围场资源,以收取丈地银,故开发势在必行。光绪六年(1880),热河都统崇绮奏请改变腾围政策,认为围场已垦,即使腾清,也剩空围,“树木一空,牲兽四散”,且“垦种有年,地皆成熟,树木将何日而蕃昌?牲畜更何时而萃止?空空围座,何所用之?”对此,清廷不得不停止腾围,谕令:“所以威逊格尔等处围场著照所请,免其腾移。”至此,围场全面放垦只剩下时间问题了。二十六年 (1900),经查围场伊逊川、布敦川、孟奎川、牌楼川和卜格川有荒地2300余顷,决定先移京旗人口前往垦种。但因京旗子弟一来不愿出京,二来安置经费无着,而罢。此后,清廷意欲放垦五川的意图越来越明朗。二十九年(1903),都统锡良请奏设立垦务局,开垦五川所余35围可垦无碍围座处,得到清廷允诺。此时,围场人口已呈成倍上升趋势:二十八年(1902),各乡共5965户,男女 36399名;三十四年(1908),各乡共12908户,男女75 728名。[11]加上军备需要,经练兵处奏请,开放围荒,设屯垦木植总局以经理木材[12],直至 1916年围场放垦才全面结束。
吉林围场虽自乾隆年间就有垦民进入,但开垦范围尚在地方官的掌控之中。延至嘉庆六年(1801),经查,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打牲乌拉等处流民私开余地76436亩。3年后,又查得吉林、伯都讷两地私开余地51727亩[15](P346),流民移入与开垦呈加速度上升。十六年(1811)时,仅在伯都讷南北两路、拉林河西岸至二道河和黑林子等处,共有流民9548户,其中有地者1594户,垦地15970亩[15](P369),但尚有7952户无地移入民需要安置。移民为了生计需要不断私垦土地,清廷为维护社会安定需要清除不安定因素,此时的土地资源便成为解决矛盾的焦点。自道光末年,安置移入民一直占主流。
道光帝继位后,对东北几个围场的管理十分重视,多次谕令加强整饬,严禁偷盗、私垦。事隔两年,为安置京旗,疏通闲散,先将热河一带的京旗移驻吉林双城堡,后又移往与双城堡右屯毗连的伯都讷新城堡一带,“给与围场荒地垦种”。从大臣松箖的奏报中可以看出,放垦初期,京旗人员尚可自行垦种,但很快就出现雇佣帮工、私垦现象,随之移入民的开垦也不断增多。如双城堡开垦,初有“中屯一千丁,多系旗丁自行耕种。其雇觅民人帮工及分种者二十一户。虽无私行租典之事,唯间有在封堆内携带家眷者”。针对此21户及“携带家眷”垦殖涉及众多人口,清廷的政策还是坚决禁止,谕令“在双城堡、伯都讷围场垦殖,以杜民占旗产”。[12](卷37,P660)两年后,清廷不得已议处将“奉天闲散移驻双城堡”[12](卷167,P588),谕令开垦伯都讷,允许民人代耕。此时,“伯都讷空闲围场,约计二十余万垧,荒芜既久,地甚肥饶。……自应及时筹办,俾旗人生计益裕”。孰料,实际操作中,京旗不愿移住,却被大量不断流入的移民开垦所取代。地方官也查得“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等处,现在纳丁纳粮民户,生齿日繁,均愿认荒开垦”。[12](卷75,P221-222)
道光六年(1826),面对无以数计潜往吉林的流民,皇帝也无可奈何:“现在流民,何致遂有一千余户之多。前此既已容留,则此后严查禁绝,亦祗纸上空言。数年之后,必又渐积至一千余户。”移民“东近猎山,西近围场,断不容令其仍前居住”,只有在令大臣想法解决的同时,于“吉林所属各厅,或盛京所属各厅州县,酌分户口,指出地方,即令迁移,务使分隶散处”[12](卷12,P676-677),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向围场禁地的流动。
事实上,至咸丰年间,垦殖已不仅仅在清廷指定的范围内,已垦入围场封堆。这从十一年 (1861)的一道上谕中可以看出:“吉林围场内外,自有一定地址,既在围场以外垦荒,何以又将封堆向内那(挪——引者)移。其中显有弊混,着景淐即将该处围场内外界址,并现在办理开荒是否在围场以外,详细确查。”[10](卷2,P92)但很快就又开放吉林西北部拉林河上游伊通围地,时尚有围场21处。[16](P22)同治三年(1864),继开放东自伊勒们河、西至伊通河之伊巴丹等5处废围,垦地约28665垧;又开放东自庙岭、西至伊勒们河之孤拉库等2处废围,垦地约8 200垧。[13](P1125-1126)[10](卷10,P224)
同治七年(1868),吉林围场围荒事态扩大,皇帝谕户部:“……设堆置卡,封禁甚严。乃该处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斩伐树木。迨林木牲畜既尽,又复窜而之他”。结果使得“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而且上文所说的咸丰末年尚存的21处围场也已经“全部垦殖”,“皆无树藏牲”。开垦力度之大,令人惊讶。[10](卷241,P340)
自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七年(1868)间,先后开垦吉林地方夹信沟、凉水泉、土门子和省西围场、阿勒楚喀围场等处荒地约30万垧。[14](P7525)其中的阿勒楚喀围场处于吉林拉林河流域,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放垦,以所属蜚克图地方最盛,约可垦荒8万余垧。[17](P1040)这里“河东原系围场禁山,其间边荒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渺无人烟,无须治理”。开放蜚克图河东等处荒地后,远近人民领种谋生,愈聚愈众。至光绪六年 (1880),“生齿日蕃盛”。[18](P7)次年,降旨废除吉林南部禁山围场旧制,移民实边。[19](P1-4)所以吉林将军铭安也奏请设官置县。八年(1882),升伊通围场的分防巡检为伊通州,在苇子沟设宾州厅,五常堡、双城堡二地方设厅,拉林、玛延等处设巡检。[14](P10522)二十年(1894)后,于伊通州所属磨盘山置盘石县[14](P10521-10522),吉林围场不复存在。
黑龙江东荒围场规模开垦虽然晚至光绪后期,但起自咸丰年间,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商议。东荒围场开垦晚的原因:一是地处边境,“恐与屯防有碍”;二是“所属地面均系沙漠山场……原皆封禁,从未招民开垦”。直到咸丰十年(1860),伴随呼兰京旗人口的不断移入开垦而展开,期间因顾忌京旗生计,又未能全面展开。据地方官统计,呼兰旗人私招垦民2500多人,开垦荒地8万余垧。但这些呼兰耕地民大半是由吉林转徙而来,至同治七年(1868)时,仅呼兰迤东蒙古尔山等处已有佃民不下10000余户。[15](P518)迄光绪十三年 (1887),将军恭镗又奏请开放通肯荒地,在阐明开垦利弊的同时,对荒地亩数做了大概估计,“预计通肯地段介居莽鼎、布特哈、墨尔根、呼兰、北团林子之间,纵横合计约有三十余万垧”。[15](P554)但清廷仍以“有碍旗人生计”而搁置。十五年(1889),新任将军再奏,也未奏效。
迨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将军增祺奏准了招民开垦、安设旗屯的折中之策,通肯一段开禁。实际放垦中,旗人认垦寥寥,流民成为承佃主力。二十九年(1903),齐齐哈尔副都统德全会同将军达桂力主改变以往章程,实施“旗、民兼放之策”,于是荒垦加速。[19](卷7,P1252)到三十四年(1908),通肯段所属通肯、柞树岗、巴拜、依克明公、明水泉子等地,共放垦地160余万垧。[19](P1253)伴随放垦,清廷开始设置行政区划,以便于管理集聚人口。二十五年(1899),通肯设副都统;三十年(1904),海伦河北新垦地置海伦厅,4年后升为府,领县2。三十一年(1905),在汤旺河垦地置汤原县,几经周折,三十四年(1908)归兴东道辖。至此,黑龙江东荒围场基本开发为农耕区。
东北围场中,最后放垦的是盛京围场。盛京是关内流民移往口外的第一站,由于移民不断流入,约在乾隆时期人口已经达到饱和点,因此,咸丰、同治、光绪开始了大规模牧场的开放。事实上,自同治以来因吉林荒垦,割断了与盛京围场之间鹿只游走的天然通道,于光绪十三年(1887)废盛京行围。于是,官兵视察松弛,流民垦殖加快,围场荒废在即。次年,仅海龙境的那丹伯、土口子、梅河、大沙河一带,已经阡陌相连,山东移民搭盖窝棚,官方已难以驱逐。不得已,清廷在海龙设围场总办,局部开放围场,前后共拨鲜围20处 102万余亩,予以安置。为保护围场不再被垦殖,清廷采取了添设卡伦,堑挖大壕,设置封堆,杜绝流民潜入他围的办法。修筑面积“西自土口子,东至大沟,东北至色力河,长约三百五六十里,南北宽约百余里至四五十里不等”。[20](P8)但这种办法不能最终解决人口与资源不敷的矛盾,放垦是一种趋势。
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京鲜围20围102万余亩已经“查丈安民”,但“尚有大围八十五围久徒空旷”[15](P972),仍成为移民惦记的开垦对象。当时官方预计,包括东、西流水围的85围招垦后,约可开田500余万亩。[15](P573)结果至三十年(1904)时,西流水围45围垦务事宜一律完竣,除不堪耕种山荒照章留作樵采牧养外,共得正段、山场、城镇基、草甸等项地2985000余亩,与开办之初约计之数相较,属有赢无绌。东流水围于二十五年 (1899)开办招垦,三十年(1904)九月,丈放完竣, 22围共放地1167270亩,城基地2148.4亩,镇基地312.5亩。[15](P602,604)次年,所有地亩一律升科,所有佃农也编户成册,设县管理。光绪四年 (1878)置海龙厅为府,下辖西流水围垦界设西安、西丰2县,东流水围设东平、柳河2县。宣统元年 (1909),在海龙东置辉南厅。[21](P499-500)
三、土地资源利用形式也要适应地理环境
在塞外围场开发过程中,尽管清廷和移入民或其他资源利用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甚至升级为枪械流血事件,尽管其中毁林的行为令人瞠目,但在整个围场管理体系中,官方确实对禁苑原生态资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在对塞外围场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清廷通过设官建制,以实施严密的军事化管理;完善管理制度,以奖惩管理层;刑律与行政处罚相结合,以限制资源利用;设置专门机构具体落实管理办法等来强化围场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只不过这些保护是逆大规模的寻求生路的移民潮而动,与人们对资源使用的需求不断增长相左,是生存与资源的争夺战,清廷本身也卷入了这场资源争夺战之中。尽管清廷不断调试管理办法和政策,最终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改变围场资源利用形式也成为清廷转嫁外债压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光绪年间,是塞外围场森林地大规模转换为农耕地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放垦后大把大把的丈荒银则成了清廷摆脱财政困境的重要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如环境史家孟泽思所言:“人类利用环境,有时是为了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自然资源管理,有时则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而开发自然资源,或者把它们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22](P3)
清代塞外围场生态环境变迁的案例,展示了农业人口不断向原始森林草原地扩展,并将林地转换为耕地的模式,十分典型。这与世界许多民族文明进程中的经历相似,成为人类创造农业文明过程中不能避免的缺憾。这一现象也告诫我们,一定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端正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态度。
提出这一问题,倒不是我们认为“发展和对自然的统治本身可能导致一种文化的毁灭”,一定要遵循如环境史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在著作中对历史学家汤因比某种观点的介绍,认为汤因比在对位于中美洲北部的尤卡塔半岛遗址茂盛的原始森林进行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森林和从树上下来的蟒蛇”一样“吞噬了”玛雅文化。对此,拉德卡还进一步引申说,他还没有想到,这种文明有可能毁于自己一手导致的森林砍伐。[23](P1)虽然这些观点仅仅是环境史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环境变迁问题的点滴思考,属于理论探索的领域;不过,对上述历史史实的考察和重构,让人们又不得不对历久弥新的“环境决定论”重新定位,继续和更深刻地认识环境的系统性、结构性和复杂性等问题,并予以环境史的思维叙述,这就是:人们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活动中,所采用的环境行为也一定要适应相应的地理环境条件。“在做到认识自然伟大的同时,又不能过分地忽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来不断地调节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24](P3)
当一个旧有的生态环境系统改变后,所生成的新系统资源环境概貌,必须有相适应的环境行为。因为新生成的环境系统还将不断地去适应旧系统所固有的纬度、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要素并不一定顺利兼容。由于系统环境景观和社会环境行为的改变,也很可能影响到气候、土壤等相对恒定的主导环境变化的诸种因素,新生成的系统结构也可能会弱化,犹如在原本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中新生成的农耕环境必定不适应纬度、气候等一样,因此,不论是原住民还是移入民,都要不断地调整环境行为方式,以适应结构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环境系统。
森林草原在地理带上一般位于较高纬度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如塞外围场就位居北方干湿带。按照生态学的理论,这一地区属于脆弱生态环境,环境的稳定性差,恢复力弱,对人为不利因素和自然脆弱因素影响的承受能力较低。[24](P22-24)这一地区也属于游牧与农耕的生态过渡带,有着敏感易变的气候条件和多样的环境条件。[25]在农耕环境行为延伸扩展之前,塞外围场植物区系各种植物群落的生长已经有适应的土壤、地势等条件,且更适宜山沟坡地,而新生成系统所培植的农耕作物就不一定能适应原本相同的地理环境。
为此,选择以森林草原地发展农耕的人们,要不断选择和培育作物品种以适应新的环境。这一适应过程是非线性的,极具复杂性,人们要不断接受自然环境的挑战,不断选择适应地理环境的农作物物种,既要承受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化、风沙弥漫等自然营力的考验,又要承受原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后诸多生物物种消逝的生物链中断,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木兰围场,“自放垦设治以来,渐次开垦,不数年,旷土游民兼得其利。然地居万山之中,平地不过十分之五,其他均山地及沙碛不能耕种者,且地高气寒年仅一熟”,“因历年田地之开凿,山上柴草净尽,以致夏季山洪暴发,则田地即遭冲没”。其他如辉南鲜围,“自设治后荒地逐渐开辟,森林即逐渐砍伐。近年人烟日稠,建筑及柴薪消耗日多,原有山林已去十分之四五”。“林木砍伐后即不栽植,日逾一日,且渐有木材缺乏之忧”。[21](P41、447、541)有些地方如前文所述,原本就是沙漠山场,并不适宜农耕。
当然,为了生存的人们,不能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放弃索求自然资源的行动,尤其不能放弃发展社会文明。所以,在进入高新科技时代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在推进文明的过程中,能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协调共生,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新的模式来发展和创造新的文明。
注释:
①参见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291~3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韩光辉、赵英丽:《论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参见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284~292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两者均从人类经济行为对生态恶化的决定性作用角度加以论述。
②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载《史学年报》,1938(5);衣保中:《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载《中国农史》,2003(4)。
③中国古代农业土地资源利用形式有多种,如平原河谷类(是为最基本的传统利用方式)、丘陵山地类和本文所提到的森林草原类等。丘陵山地类为美国学者何炳棣提出,他认为,17~18世纪中国人口激增,结果是到18世纪末,中国的资源已变得极为窘迫,所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区为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而规模化辟为农地。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1、215~2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④2005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把农业称作是“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多样性破坏最大的一种”,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31):118。
⑤关于环境行为,德国学者约阿希姆·拉德卡认为,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环境行为的基本单位是很小的家庭、住家、农场和邻居。参见约阿希姆·拉德卡:《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载《史学月刊》,20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