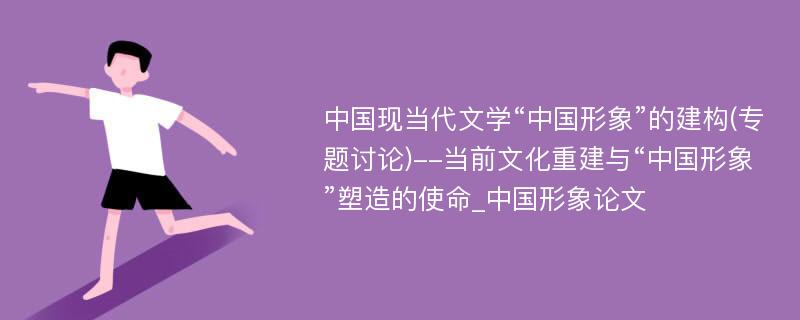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专题讨论)——文化重建与“中国形象”塑造的当下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象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使命论文,现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1-0092-11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塑造,严格地讲是从“五四”开始的,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驱站在启蒙的文化立场,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挚爱之笔书写了阿Q、祥林嫂等一批落后不觉悟的农民、妇女和文人形象,为“中国形象”的塑造筚路蓝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不过,那是文化批判时期“中国形象”的塑造,它主要依据西方异质文化的评价标准,更多看到和发掘的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如今百年过去了,中国在经过沧桑磨难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社会也由文化批判进入了文化重建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及其中国文化在全世界日趋广泛的影响,“中国形象”塑造更是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内涵上,普遍重视民族文化优质资源的开发,包括优质的精神资源,也包括优质的艺术资源的开发;表现在外延上,则充分注意它在跨文化、跨语际语境下的丰富复杂多样的存在,将一个比较本土性的命题延伸和拓展为全球性的话题。这种变化尽管是初步、粗糙的,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但它毕竟反映和折射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当下的精气神,说明我们开始真正找回了那份应有的文化自信,它是我们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表现。而这,在文学文化日趋世俗化、娱乐化的当下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不仅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生成点,而且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点,它蕴涵着文学创新和突破的种种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在讲文化重建之时,我以为不能忘了文化批判,将“中国形象”塑造推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能自吹自擂,搞什么文化自恋。坦率地讲,这种文化自恋在当下是相当程度地存在的,包括全民“国学热”及不少大学搞的孔子学院或国学院,其中也包括央视“百家讲坛”的部分内容。有的甚至虚火上升,有点“走火入魔”了(王蒙语)。学术界也不例外,公开提出21世纪就是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的世纪,认为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的绝不是少数。与此同时,则把“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从而对前者进行全盘的否定,“五四”以及“五四”文化先驱被妖魔化了,似乎成了一个否定性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已影响到现有的中国文学大学科的整体格局,它崇古贬今,客观上对其中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造成贬抑,有意无意地将它边缘化了,其学术价值似乎也大打折扣。
面对这种情形,同行中有人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以应对,即将“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学也当作一种“国学”,纳入传统文化和学统的范畴。这种用无限扩大“国学”内涵的作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倒是使现代文学因模糊或削弱了自我的“现代”个性魅力而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给这个学科的合理合法的存在及其更加健康的发展留下某些隐患。道理很简单,“五四”新文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就当时还是从今天来看,它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深刻的合理性,这是谁也不能否定而且也否定不了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现代的文化启蒙或曰文化自拯运动,为今天的文化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形象”塑造从本质上讲,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因而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阶段,它往往就要借助异质的文化力量对传统旧学采取整体批判的姿态,以此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也可以说是中外文学文化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今天,我们生存的语境与“五四”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民族复兴与文化重建,也为了应对至今犹存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挑战,我们似乎更易也更愿看到寄植在“中国形象”背后的传统文化的优质的一面。时代变了,“中国形象”塑造也是可以变的,而且应该有所变。这一点大概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怎样评价“五四”的文化批判?它是否意味着搞错了而应受到清算和弃置?不能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资源参与到今天的“中国形象”塑造上来呢?显然不是。这里的原因,主要就在于文化重建与文化批判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讲,它们彼此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性。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不能漠视“五四”的文化批判,而且相反,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传统和资源整合到“中国形象”塑造上来。中国文化原本是一个优根与劣质并存的矛盾复合体,在文化批判时期,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并放大其劣质,对其进行酷评;而在文化重建时期,则反之易于看到它的优质,对其进行拔高。我们今天的“中国形象”塑造,对之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们高兴地看到,已有一些当代作家在高涨的文化重建中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陈忠实和唐浩明笔下带有翻案性质的白嘉轩(《白鹿原》)、曾国藩(《曾国藩》)形象,即使侧重于“歌颂”,将其当作正面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两位作者也没有把他们写成一个单面人。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认识,在把握形象基质的基础上赋予以矛盾对立的双重思想性格:一方面,打破习见的阶级论思维模式,放笔描写了他们的仁义道德,温良躬俭、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又殚精竭虑地揭示其身上权谋机诈、虚伪阴损、男尊女卑;并把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官场、党派、宗教、宗族、民间等联系起来,纳入多元立体的文化“场”中进行观照把握,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有些地方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其他如莫言的《檀香刑》、铁凝的《笨花》、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等也都具有类似的意向。在这里,作者文化重建的意图十分显见,他们的文化态度有时还不免有些保守,但反思和批判的成分颇重,而且写得最深刻迪人的往往是后者。不妨说,这是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文化本色,因而也更彰显时代特征的一种文化重建的写作。这大概与21世纪日趋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以及人们更加理性开阔的思维观念不无有关。对传统文化批判是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极为丰厚的积累。文化重建的前提是文化反思,如果没有反思,那是很容易导致文化自恋和自大,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形象”塑造的。我希望在民族文化重建的当下,继续倡扬和继承“五四”传统,对中国文化保持冷静而深刻的反省,显现出它的真实、理性和丰沛的艺术力量。不然,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的塑造就很难避免简单肤浅。
以上所说,主要是就大陆本土的“中国形象”塑造而言,还没有将域外文学包括进来,这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中国形象”塑造从晚清开始以迄于今的百年历程中,一直有域外作家的参与。域外作家的创作不仅构成“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本土作家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域外创作,主要包括西方、华裔和港台三大部分。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形象”在异质他乡的延伸,这些域外创作的确发现或发掘了不少为大陆本土所忽略了的中国文化的潜能,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立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如赛珍珠的《大地》、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雷米的《火烧圆明园》、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等。他们的异域观照,曾经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新奇感和艺术冲击力。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作品在域外毕竟比较少见。可能是与生活隔膜有关,特别是与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有关,大多域外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在整体上是被否定的,成为暴力与黑暗、贫穷与落后乃至恐怖与邪恶的代名词(所谓的“黄祸论”、“红祸论”),它与其说是具象的文学形象,还不如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演绎。相比之下,华裔作家特别是在中国长大的华裔作家,因生活和情感的原因,在这方面相对就比较公允。如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以及严歌苓、张翎、严力、曹桂林、卢新华、陈谦,包括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都有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创作虽然不能进入西方文学的主流,但对传播中国文化还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理所当然进入“中国形象”的视域。“中国形象”是一个没有界限也不应有界限的开放体系。当中国本土作家在进行形象塑造时,不管他有无意识到,客观上他已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世界共同体”的创作机制中,与域外作家形成了既参照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并面临着来自他们背后的西方强势文化的严峻挑战。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跨文化跨语际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重建是复杂的,也相当艰难。也许这样的情形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只有将来国家民族强大了,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改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沉潜下来,苦练内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精神内质。一方面,放出眼光,抛开各种有形无形的歧见,努力向域外作家学习以丰富和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坚守,将思维触角紧紧扎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根须上,在此基础上构建独特的形象体系和文化价值观。生活在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大陆作家,也应该拥有与之相适的开放、宏阔和大气的眼光与襟怀。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所谓的“尊严”或“颜面”而忘了自我反思。有人说得好:“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①这很值得深思。现实告知我们,中国目前的文学生态并不理想,娱乐消遣之风过盛而理性沉思不足。这对具有时代深度和宽度的“中国形象”塑造也许不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悲观,毕竟这不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最终决定文学的还是反映和代表时代本质的那些内在的精神及灵魂的东西。只有返回到这一原点上,中国大陆作家的“中国形象”塑造才有可能超越庸常,在与域外作家共时并存的创造中发挥作为母体文化的更大的作用。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这也是中国作家当下应尽的艺术使命。
注释:
①陈平原:《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载《光明日报》,1988-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