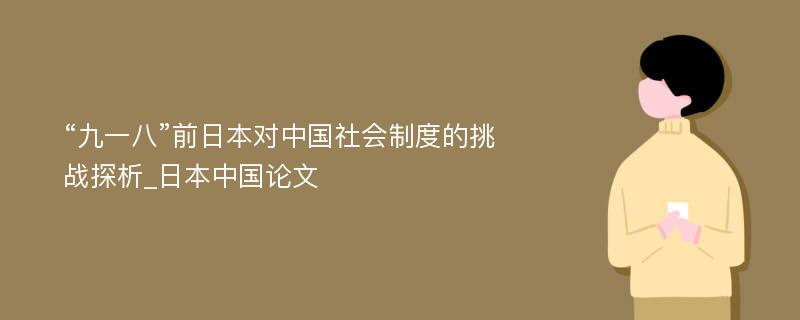
“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会体系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九一八论文,体系论文,济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九一八”之前中日冲突的探究上。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研究视野有所放宽。今年是“九一八”70周年,在回首这场引发了一系列战事,给人类带来浩劫的历史事件时,人们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发问:这场祸变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它能够被避免吗?诚然,历史是不会改变的,但后人对历史的探询并不是无意义的。其实,对这些问题国际学者已进行了数年探讨,这些探讨不再把事变简单视为中日两国在世界一个局部地区的冲突,而是正确地指出事变的性质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勿宁说是对英、美,以及对作为战后远东秩序象征的整个华会体系的挑战(注: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人们又不禁要问,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何以如此嚣张,胆敢不顾一切与诸多华约体系国相抗呢?对这一问题,以往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较多注目于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但笔者认为,对于战争祸源的探讨,仅仅归咎于日本国内的因素是很不够的,历史事变乃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早就深藏于肇事之端,祸变时得到彰显,“九一八”事变也是这样,早在事变之前3年就有预演,这就是发生在1928年5月的“济案”。本文即以此案为切入点,通过对是案来龙去脉的探究,期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对引发“九一八”事变的深层原因作一透视和俯瞰。
一、“济案”与华会体系
所谓“济案”,即指1928年5月3日,驻济南日军蓄意寻衅闹事,枪杀北伐军战士、伤兵和无辜百姓3000余名,并肆意施暴、凌辱、惨杀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外交官的恶性事件。尽管此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和国际都引起巨大震动,但从世界大范围来看,此事件毕竟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性、地区性的外交纠纷,像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某城市的中日冲突事件何以能与华会相连,作这样的联系是否有小题大做之嫌呢?在此有必要把华会体系中主要成员国在中国的复杂关系,以及华会后至“济案”前这段时期中,中国国内局势巨变对华会体系的冲击和影响作一简略介绍和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回到中国,因急于夺回和恢复原来在华攫取的权益,彼此虎视眈眈,关系紧张。而其时正值“五四”过去后不久,中国民众的爱国民族情绪仍在不断高涨中,为了避免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并联合列强力量以对付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在美国首倡下,得英国支持,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召开了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也即华盛顿会议。会议参加者有美、英、法、意、日、中、比、荷、葡9国,会上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远东和太平洋安全问题,最终的成果主要有三项,一是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二是由英、美、日、法、意签订《五国海军协定》,最后是与会9国共签的《九国公约》,涉及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事项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在该公约中与会各国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有三:1.各国将在对华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同意“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2.各国承诺在中国将遵循“门户开放”的原则,并“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3.各国表示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的完整”,“在条件具备时逐步撤废列强在华享有的特权”(注: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8),pp.12151-152.)。对于上述原则以及华会的成果作何评价非本文的任务,但华会显然是美国战后推行其远东政策的一个巨大成功。因为美国通过是会,不仅对战后东亚地区列强的势力均衡和利益关系作了重新构组,而且通过是会最终取得了凌驾于其他列强之上的优势地位。华会上,美国首先通过《四国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又通过《五国海军协定》,联合英国迫使日本接受了美、英、日海军吨位5、5、3的比例,最后通过《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以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与维持现状为基础,统一了各国列强对华政策的步骤。因此,华会体系虽然一直被视作“远东和平和秩序的保障”,但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用来实现战后美国在东亚目标的工具”,这一点是美国人自己也不予否认的(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7.)。
然而,外交历来是以“自利”为原则的,像华会体系这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方案何以会被与会各国所认可并接受呢?当然,美国战后的实力地位以及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性影响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各与会国在加入该体系时也都是有着各自利害考虑的。拿作为华会体系基石之一的“大国一致”原则来说,之所以得英人支持,是因为其时的英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整个远东地区地位已十分衰弱。由于日本在战时在中国的猛烈扩张,重返中国市场的英国不与美国联手就很难抵挡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而日本之加入华会体系则是多方面因素压迫的结果:其一,是因为日本乘欧战已在中国捞到了很多好处,在美、英卷土重来后,不得不稍作收敛;其二,军事上形格势禁,日本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国力,认为“在二十年代这十年中,日本还不可能具备实力同时去与美、英两国在远东抗衡”(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35.);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日本在会上尽管在交还山东问题上被逼迫对美、英作了让步,但作为补偿,美、英对日本所称的中国的满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与经济生存有非常密切的特殊关系”加以了认可,并以条款形式确认了日本在该两地的“特殊利益”(注:麻田贞雄《日本的“特殊利益”与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Sadso Asada,Japan's"Special Interestes"and the WashingtonConference,1921-1922),转引自孔庆文《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而未能实现的。所以,尽管日本加入华会体系极为勉强,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只有中国,在华会上仍被列强视为一块可共同宰割的俎上肉,尽管《九国公约》中冠冕堂皇地列上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的完整”的条款,但确如当时舆论和以后的研究者都指出的,这只是给中国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仅就条款的字面去看,中国被允诺的“独立”也是在确认“现存有效条约”前提下,而条约关系的改变则又完全取决于列强的意志,此正如当时报刊评论所言:华会后中国的状况并未有什么改变,反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列强,“各国在中国所侵略之赃物,在此次会议以前是非法的,在会议以后为合法的”,华会体系不过是“列强结成同盟,共同宰割中国”而已(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等文,《东方杂志》19卷2号,第42-43页;《外交会解释九国公约之危险》,《民国日报》1922年2月22日。)。
尽管如此,华会体系毕竟给战后列强在远东势力平衡提供了一个新支架,这就是美国人自诩的“远东新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各列强国在华利益暂时得到协调,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紧张关系表面上似有缓和,亚洲国际事务受华会体系影响,列强之间的矛盾在一段时间中被掩盖了起来。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华会体系首先遭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并出现了松动。由于华会上中国的利益又一次被出卖,中国民众并没有因华会条款中有一些漂亮词句而得到“抚慰”,反是更激发了对外强的不满,国内反帝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5月因“沪案”而引发的全国范围的五卅运动是一个大瀑发。五卅后不久,因“沙基惨案”而引发的更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更使在华列强感到胆战心惊,特别是在这些运动中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反帝热情以及对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高度关注,对华会体系更是形成了巨大冲击。而这时中国政府受民气激励,也于1925年6月24日照会各国,正式推出“修约”外交,并敦促在华各列强从速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在这一局势下,1925年10月,有中、美、英、日、法、意、比等13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正式开场。
关税特别会议虽说是主要用来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但从各华约参加国心思来讲,显然也有意通过是会对如何应对中国时局协调一下列强彼此的步骤。因为自五卅后,美、英、日三国在对待中国要求已态度已明显有别。美国由于没有租界在中国,五卅风暴时未受大的冲击,故地位超然并有意无意地向中国人示以同情以博好感。英国人则不然,在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人已被中国民众视为“头号帝国主义”。而日本则在激起事端后,看到怒火向英人烧去,于是自谋脱身,公开里支持英国强硬,私下却谋单独解决,这使英人得知后十分愤怒,英领事大骂说,英国人因为日本纺织厂而落得这样惨,而日本却抛下他们单独开工,真是卑鄙到极点。美、英、日三家已有的这些芥蒂会前虽还未十分公开,但已为外界所关注。果然,关税会议一开场,三巨头的“不一致”很快在应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上显露出来。美国从会议开始起,就同意以废除厘金为条件,将税率提高到最高的12.5%。英国见美国已有这样的表示,不便反对,但要求关税附加税的增收要由英国控制的海关执行。日本怕陷于被动,本来是激烈反对提高关税的,却又抢在美、英之先表态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却在会上讨论税则和附加税增收问题时,寸步不让,几使会议破裂。而开会期间,中国南方由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又蓬勃起来,北方则相继发生了郭松龄反奉事件、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在这些事件中,美、英、日三家态度也不相同。这样搞得会内会外矛盾交错,本就同床异梦的列强,荠蒂更深。其实,对于关税会议上与会国之间的意见难以协调,美国在会前是有所料的。五卅后,面对中国国内汹涌的民众反帝怒潮,美国开始意识到,要维护华会时列强在华现状,并要求中国按华会框定的规范“渐进”修改中外条约,已难实现。尽管美国国内仍有相当部分人(包括在华公使马慕瑞在内)认为现在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退让是不明智的(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22,37.),但国务卿凯洛格却认为适时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作些让步,“鼓励中国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这不仅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相符,也有助于远东局势的稳定和美国影响的扩大。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会前就作出了“愿意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考虑修改现存条约”的姿态(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ayer,July 1,1925,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Vol.I,p.767.)。凯洛格并在会议开始时即给参加会议的美国公使马慕瑞以明确训示,要他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如果会议无果而终,各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将单独与中国谈判(注:Kellogg to MacMurray,October 5,1925,FRUS,Vol.I,pp.842-847.)。对此,凯洛格的解释是:“尽管我渴望与其他列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但我感觉到中国的危急形势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消解公众的激烈情绪。”(注:转引自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北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然而,美国对华出现的新面孔,却不受英、日的欢迎。华会后,英国在华政策着重于保住既得利益,但自五卅后,英国人已发现在日人釜底抽薪后,自己正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敌人,本还指望会上能得美国人撑腰,却发现美国正向中国人暗送秋波,这对英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至于美、日关系,本来就矛盾重重,华会后,美国更被日视为日在华扩张的第一假想敌。现美国率先表露出愿就条约向中国人让步的意向,日本自是反对,故币原一再抱怨“国际协调”不见了,要防止被美国出卖,日本须早打主意另辟蹊径。在美、日、英三国歧见显见的情况下,1926年4月19日在会上英方代表提议下,美、英、日三家专门就“会议前景问题”开了个碰头会,会上英方代表首先发言对会议目的作了解释,提出“三巨头(The Big Three)能否有可能在是会上就共同的对华政策以备忘录的方式作个说明”,但英人此议没有得到其他两国的响应(注:FO.371,1926,11652.P.R.O.(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档案,以下略。))。于是,原本脆弱的华会体系在关税会议上不仅未能弥痕,反而更加动摇。而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代已开始,中国局势面临更大的变动,在风暴即将来临之前,列强个个无暇他顾,开始各行其是了。
最先公开自谋出路的是英国。由于北伐在两湖的胜利,使首当其冲的英国自知难以相抗,于是不得不现实地考虑转换其对华方针。原驻华公使麻克瑞被撤换,新命公使蓝普森一上任,就先往汉口访问,成了列强中第一个访问武汉的外交公使(注:British representation in China,15 July,1926,FO371/11690.P.R.O.)。至汉口、九江事件发生,英怕进一步激化矛盾,不仅同意交还中国汉口、九江租界,并准备在治外法权、关税、租界管理等一系列方面作更大让步。英外交部并特别向蓝普森强调,在采取这些步骤时,可“单独行动而无须等待别人”(注:British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1926,FO371/12399.)。英国率先抛出的对华新方针使一心想在这时取得中国人好感上拔头筹的美国人甚为不悦,美国务卿凯洛格认为“这是英国人想在中国人面前充当比美国更好的朋友的角色”(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89.),于是也赶着于1927年1月27日发表了《凯洛格宣言》:“美国以同情的兴趣关注中国民族的觉醒,并欢迎中国人民趋向重组其政府体制的每一个进展。……美国政府以极宽大的精神与中国交涉。它在中国没有租界,也从未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无疑是对英国变相的指责。对此,美公使马慕瑞的评论是:“为争中国人之宠而互相嫉妒。”(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92.)而随着北伐军向西方在华利益集中的上海推进,美、英间扦格更深。当时,英国担心汉口、九江事件在上海重演,建议各国合作以武力保护租界,此议虽得到美公使马慕瑞赞同。国务卿凯洛格却对此作了坚决否定,他在给马慕瑞的回电中说:“如果目前上海的紧张局势需要美国海军出动登陆部队的话,就必须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这支部队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本政府不准备为了保护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动用海军部队。”(注:Kellogg to MacMurray,Dec.23,1926,FRUS,1926,Vol.I,p.663.)至“南京事件”发生,美国虽也出动军舰参加了“护侨”,但在得知蒋介石已准备对共产党下手,并愿意与列强紧密合作后,美国拒绝了英国采取通牒方式进行制裁的建议,在凯洛格给马慕瑞所发的一份经总统修改过的训令中称:“本政府不希望照会确定时限而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持保留意见。”(注:Kellogg to MacMurray,April.2,1927,Vol.II,p.177.)美远东司司长詹森并去电警告主张“强硬”的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不得与列强同事讨论制裁问题,而应以“谅解的心情”,对中国国内斗争的结局持“等着瞧”的态度(注:Kellogg to MacMurray,April.2,1927,Vol.II,p.181-183.)。从而再一次表明,美国在重大利益问题上也放弃了与诸列强的合作。
在美、英不睦加深之际,日本也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更独立的路线。表面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南、北交战中,日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已开始施展分化手段,即利用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在国民党营垒中寻找日本利益的代理人。应该说,日本的谋略是成功的,他很快与在江西南昌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挂上了钩。因此,在美、英还在为是否出兵“护侨”伤尽脑汁时,日本已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细,并已开始“怂蒋反共”,在“四一二”时也大见成效(注:申晓云:《四一二前的蒋介石与列强》,〔北京〕《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然而,币原外交尽管有这些成功,却不能见谅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军部势力(注:日本军部势力,包括日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参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4页。)。在强硬派军人看来,政府在现中国内乱中仍取“不干涉”政策是愚蠢、懦弱的行为,尤其汉口、九江事件后,日本所采取的“撤侨”而不是就地保护的措施,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浪,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不得不单独出兵。”(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7页。)及至南京事件发生,日本军部更认为此事件“使帝国丧失威信”,日政友会于4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币原外交”袖手旁观,因循敷衍,终因发生南京事件而蒙受国耻。”公开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要求“彻底转变我们的中国政策,以保护国家在华的权益。”这些言论在日本国内形成了对币原内阁的巨大压力,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严重衰退也被归咎于“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册,天津大公报社印行,第134-135页。),于是在一片“倒阁”声中,币原下台,取代他的乃抨击“币原外交”不遗余力的日本强硬派军人领袖田中义一。
币原,曾任日驻华盛顿公使,1921年与马慕瑞、蓝普森一样,都作为各自国家的远东事务专家列席了华会,故也是华会“老店”(The Old Firm)成员之一(注:华会“老店”是一些华会时代表各国出席会议,后又代表各自国家负责处理远东事务和中国问题的高级资深外交官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调侃和戏称。老店成员中主要一个角色是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另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再一个就是日本的币原喜重郎,他们在各自国家中都长期负责外交事务,在认同华会体系的共同原则上也基本持相同立场,又几乎在同一时期被派往中国或负责本国的对华事务,在华全体系动摇后,他们的使命也陷入困厄,至“九一八”发生,“老店”成员先后离任调职。)。1924年币原出任日外相,在任内以奉行“不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相标榜,主张以经济扩张达到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与华会诸国关系上,也主张遵守华约规范,以“国际合作”协调列强矛盾,认为这是一条“对日本最为安全的道路”,但也因此他的政策一直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军人的攻击。而币原在1927年4月的下台,也就意味着其政策在日本不再有市场。这无疑是对正在出现剧烈动摇的华会体系的重击。果然,时隔不到一年,“济案”发生了。
二、“济案”——日本为挣脱华会束缚而迈出的试探性步伐
“济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恶性冲突事件,如仅从表面去看,日本制造此事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进而阻挠中国的“统一”。诚然,这确是日本制造此案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全部。因为,国民军的北进不是日本进驻济南就能阻挠得了的,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后,两个月内就入进平、津,宣告“统一”告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日当局不管何等狂妄,也心知肚明。因此,此事件可说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正如上交所述,田中是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声浪甚嚣尘上中上台的,在田中之前币原时期,桀骜不逊的军部势力就在日本国内兴风作浪,并在中国一系列内乱中充当了积极涉入的角色。其中郭松龄反奉时,由日本关东军出兵援张,致使郭的倒戈功败垂成,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些事件中,日军方的行动虽总被说成是军人擅自而为的行径,但实际上也都得到了日内阁的默许或追认,而国际联盟则碍于华会上对日本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的承诺,也未作什么反映,这无疑滋长了日本军阀的骄横,证明了在日本权益受到威胁时,行使武力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因此,当1927年中国形势发生巨变,并可能出现日本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时,币原外交便被抛弃,而军方所坚持的“日本利益只能通过军事行动来保卫”的观点受到重视,并得到不少舆论支持,上升为主导。
那么,什么是日本在中国所最不希望见到的局面呢?这就是中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日本有一种“国论”早就甚为流行,即日本作为一个空间和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有权甚至有义务向其邻国扩张和开发,而近在咫尺、地广物丰的中国却因国内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欺凌,近代以来不仅主权丧尽,而且一直内乱不断,这无疑是日本在华扩张所需要的,也的确滋长了日本的觑觎之心。而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眼见“二次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在即,这对日本长期以来推行的分裂中国政策无疑是个巨大打击。不管蒋介石如何保证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但“统一”本身就是日本所最不愿看到的事实。其二,中国统一以后,作为北伐重要目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将顺理成章地加以贯彻,不管列强如何拖延,归还中国主权也都是早晚的事,这样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的满蒙权益很可能随之失去,而由于英、美两国在资金、技术上对日本的巨大优势,倘中国收回主权,失去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日本是无法在华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这也使日本有了严重的危机感。能阻挠这一切的,在日本头脑发热的军部看来,只有对华用兵一条出路,因此乘中国南、北尚处分割状态之际,以出兵求一逞,也是势所必行。
然而,要在华用兵,日本可以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济案”中日本人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菅,手段之暴虐令人发指就是事实),但却不能不顾及美、英和其他华会成员国的反对。自关税特别会议后,尽管华会各国已开始各行其是,但华会原则对各国仍有约束。特别是美国,在年初就与中国就解决“宁案”(南京事件)签定了协定,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开始后,美国人已明白北京政权是绝对长不了了,因而已放出风来,一旦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政府能稳定下来,并有效行使职权,美国将按华约精神,“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废除在华特权”。而日本一旦出兵强占山东,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华约原则的明目张胆的蔑视,对其他华约成员国在华利益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其后果如何,美、英会有怎样的反映?这是日本在出兵前不能不有所顾虑的。但这时在台上的田中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对华约体系可谓深恶痛绝。而其时日本国内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华会上“日本人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条约体系里,日本的权益一直被漠视”,因而多数日本人不喜欢华约,就像大多数德国人讨厌凡尔赛条约一样,这种情绪无疑给田中这样的军部强人起到了兴奋剂作用,特别当日本自感处于孤立时,军部所声称的“帝国的利益,必须充分利用我方之实力来保卫”之信条也就有了更多的响应者。于是,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开始相信这样的说法,即“同自然资源丰富或富有的西方国家合作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同日本分享空间和财富,而这又是绝无可能的”,既然西方人不会关心日本国的生存,条约又不能保障日本的权益,那么维护它是毫无价值的,打破它才是出路,即使这样做必然会排斥西方利益,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应在所不惜(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28,29.)。
日本国民中滋长的这一情绪和军部的这一信条,在田中上台后不久就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这次会议召开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会议由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参加者有外务、陆军、海军、各省官员,参谋本部二部部长、关东军司令官以及有关的驻华外交官,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内容主要有四点:1.将“中国本土与满蒙”加以区别,坚决将中国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2.估计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之稳健政权”建立适当联系;3.“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之措施”;4.“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之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其来自何方,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之决心。”(注: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1-1945)》下册,第101-102页。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13页。)此4条中的第4点,显然矛头直接指向美、英,日本欲挑战华全体系之决心,于此已昭然矣。
当然,要直接挑战华声体系,其时的日本自忖羽卵尚不丰满,实力上也还有距离,要放胆干去,不能不有所禁忌。于是先以“护侨”为名,在北伐军逼近鲁境时小试牛刀,于1927年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其时美、英两国正以“宁案”一定要获满意解决为辞,要挟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惩凶、赔款、道歉”,故对日之“护侨”无法说三道四。日见列强并无强烈反映,乃进一步放胆,一面暗中策动蒋(介石)张(作霖)妥协,一面积极策划更大的军事步骤,《田中奏折》也于是时出笼。不料半年后,受内部派系排挤被迫离职的蒋介石在重新复出后,打出了“统一中国”的旗号,发起“二次北伐”,一旦成功,日本乘中国内乱和分裂,操纵中国政治,扩张日本权益的整个战略和梦想都将化为乌有,于是日乃不惜铤而走险,以武力作孤注一掷之举,一来强行阻挠中国统一,二来也可藉此观察各国反映,为日本最后挣脱华约束缚,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摊牌作一试探,这就是日制造“济案”的深层目的。
三、“济案”后美、英的反映和选择,以及日本相应的对策
“济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扩大,对日采取了极度屈辱退让的态度,但却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特别是美、英等国的出面调停和干涉。5月10日,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请其采取必要之行动,以停止日军之暴行。12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说明惨案发生情景,请其“出面调停,主持公道”(注:罗加仑主编:《革命文献》,第1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版,第1299页。)。当然,日本在制造事变后,最为关注的也就是美、英的态度和反映。回驻美大使松本在事件发生后,数次往谒美国务卿凯洛格,呈递日官方关于事件的报告。对此,美国和英国作出的反映是什么呢?
美国政府在得知“济案”的消息后,初为避免直接介入中日冲突,反映甚为“持重”。美联社5月11日华盛顿电云:“据国务院宣称,美政府在未得关于济南战事确实消息前,不能决定美国对于中日事件之态度”,但其时美国的报刊文章对日本的批评却甚为强烈。纽约《泰晤士报》8日社评云:“山东之新形势,显然使中国问题陷于纷纠,乃至引起国际的重大结果,试问日本有在济南配置军队之权利耶?中日何方先开始战斗行为,目前无讨论之必要,重大者乃因冲突而将起之结果耳。……田中首相为1915年日计划对华军事的军阀之一,世所共知,然今日欲再恢复其1915年时政策,则日本将如过去受全世界的批难,几至立于四面楚歌之窘境。”(注:《革命文献》第22辑,第71-74页。)美国英文导报并发表佳日社论,略谓:日军当局昨晚行动,殊难为正当,……此即日本拟攫华领地,对华宣战,……福田之残暴行为不容饶恕。”纽约报评也称:“日本占领济南,有害于远东和平。”(注:《济南惨案特刊》,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校刊社1928年5月15日出版,第3页。)舆论趋向激烈。至7月15日,美国正式接受国民政府之请,由众议院通过《调停“济案”争议决议案》,决议指出:“兹因日本与中国以‘济案’近事之故,似有立开战端之险。此种战事因外国在华具有利益之结果,或将牵涉世界许多大国”,故议决由美国务卿与中国驻美公使、日本驻美公使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接洽,提供调停(注:《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较之美国的态度,英国方面的反映则暧昧得多。英外相张伯伦在5月15日,也即“济案”发生一个多星期后,在下议院回答议员询问时,就有关“济案”问题答称“彼尚未接得驻济南英领事之直接报告,所知山东之情形,多系有日方而来”,而后便以一大堆不着边际的空论作了搪塞,却在最后表示,对日方所言“在日人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后,立将日军撤退”认为“满意”,言下也表示了对日本出兵后下一步行动的关切(注:《革命文献》第22辑,第74页、第75页。)。对中国方面要求的“支持”,英政府给蓝普森的指示乃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中国方面示以不带任何评论的同情是可能的,而对中国方面所询及能否予以外交支持的问题是不可能给以答复的。”(注:FO371,1928,7/13172,7/13171,7/13171.P.R.O.)所以,事变后,英国基本采取了沉默、旁观的态度,而其他华约国,甚至非华约国的德国,对是案中中国方面表示了同情,德意志全民报评:“南北两军之交战中,忽有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并济南市,斯诚危险之极且不得不谓为难于承认之事。”德报并称:“英、美两国对于日本之大规模地占领山东其将起而阻止行动鄢?如听此事件之自由进展,势将于列国之对华政策上,发生非常龟裂,乃至引起中国国民强烈之对外反抗心之结果。”(注:《革命文献》第22辑,第76页。)
美国的出面调停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使制造“济案”后的日本不免感到了惶恐,而美、英在事件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差异,又使首鼠两端的日本觉察到了可供利用之隙。恰于其时,美国又与才入平津即宣告“统一”的国民政府就“关税自主”签定了两国新约,美国这种处处“占先”对华约其他成员国形成了压力,尤为英国所反感。于是,日本乃适时加强了对英国的游说。据英外交文件记述:“济案”后,日本即多次通过它在北平的外交官向我们表示,愿意就列强在中国“合作”的问题,特别是日与英两国之风有否可能建立一个较之以往更密切的关系,作“具体”探讨。英公使蓝普森将此向外交部作了汇报,英外交部对此的回复是:“我们的态度是严格的中立,我们不希望卷入任何纯粹的中日纠纷”,至于对日本提出的“合作”,“我们似应约束自己,不要去对日本现正谋求的‘合作’表态,而应去设法探明日本此举的真正动机,即:1.什么是日本现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和目标;2.什么是日与我们接近的真正理由;3.日本对联合行动会有怎样的建议。”(注:FO371,1928,7/13172,7/13171,7/13171.P.R.O.)由于得不到英国方面态度的确切信息,加上“济案”后,国民政府转换外交取向,不仅以接近英、美的王正廷为外长换下了亲日的黄郛,而且正谋“以夷治夷”争取来自美、英的支持,日本担心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会置日本于更不利的地位,于是主动发起新一轮外交,于9月间,派出老道资深外交家、枢密院元老、华会时任日外交部长的内田出使美、英,其使命按日本的说法,是为“取得国际的谅解”,但从他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分别活动来看,对美主要是探口风,对英则着重离间英、美关系。这可以从马慕瑞的“备忘录”和英国外交文档文件记录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内田的出访,先去的是英国。对内田的来访,英国政府预先作了准备,在内田尚未到达前,英外交部向政府呈递了一份详尽的咨询报告,报告中对华会后英、日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了追述,特别提到在以往英与日的交往中,日本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冷漠和自私”,认为日与英“合作”是不可信的,“中国现在给我们的是在贸易上优先这样一个含糊而又不确定的允诺,但日本给了我们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英国现在的对策应是:“在日本解决它与中国的所有问题前,我们必须保证自身有独立行动的自由,而不能受到任何方面的约束。”(注:FO371,1928,7/13172,7/13171,7/13171.P.R.O.)于是在内田抵英后,尽管极力向英方示殷勤,大宴英上层人士,但在谈及“合作”问题时,却遇到了尴尬。以下是内田与当时的英外交代理大臣库欣敦勋爵(Lord Cushendun)会面后交谈的简要过程:先是内田告诉库欣敦,其访英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英国了解日目前对中国的态度,此外就是想就日、英两国政府能否合作的问题具体交换意见,内田说着就拿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文件读了起来。听内田读完后,库欣敦便不客气地说道:“对这一声明,现在我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还没有确切地知道日本政府所倡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声明中所指的特殊问题又是指什么而言?但我确信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只要有可能的话将是乐于与贵国政府合作的。至于如何进行,目前两国政府在北京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应该说是相当方便、有效的方式。”在说完这些后,库欣敦随即将话锋转向对日本的抱怨:“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政府在中国遇到一些麻烦,每次我们都希望能有日方的合作,但却每每失望”,库欣敦并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例,认为日没经任何预先协商,抢先建议在1929年内关税自主权将由中国全部收回,实乃缺乏合作诚意的事例之一。最后,库欣敦用纯粹的外交辞令说道:“英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抱着真诚的希望与日本进行充分的合作,而且不仅是与日本,还要与其他一些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合作。”(注:Memorandum by Lord Cushendun,September 11,1928,FO371,1928,7/13171.P.R.O.)在听完这话中有话的结束语后,内田明白他带到英国的货是推销不出去了,“两个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伦敦所能做的的仅仅是原则上同意就彼此国家的对华政策经常交换意见而已。”(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10.)
内田的第二站是华盛顿,在那里内田受到有甚于英人的冷淡,不仅“货”卖不出去,拿马慕瑞的话来说,他还发现“他实际上把他的货带去了一个最坏的市场”(注:FRUS 1928,Vol.II,pp.425-30.)。内田是9月29日,由日驻美大使的陪同会见凯洛格的。在凯氏与其的会面中,凯除了大谈他对中国目前局势和未来前景的乐观感受外,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东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内田此行的主要目的,也是日本最为关心的事。内田以华约原则相质询,问“美国是否还坚持华约的立场?”意在提请美国注意到日本的利益,而凯洛格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内田在美不仅感到受到“冷淡和不被尊重”,而且还深切感到了“日本利益在美国人那里被完全漠视”,“美国人并不希望,也不打算与日本接近”,华约条款不过是美国人用来束缚他国的空洞说教,而它们自己做的却是“用一大堆讨好中国人的话,鼓励中国人去反对所有国家,除了美国人自己”(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03,112,118.)。
内田的伦敦、华盛顿之行结束了,虽然并不顺利,倒也非一无所获的。因为,内田此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底”,也即摸清美、英在日本制造“济案”后究竟会作什么反映。在英国,尽管内田带去的货没卖得出去,英人不会与日本合作去对付美国人,但也决不会给中国人以援手,在某些有共同利害的场合,却仍有可能成为日本的同盟者(注:比如日本所提“列强合作对付中国”显然对英国产生了诱惑力。在蓝普森给英外交部的一份汇报中明确写道:“日本的政策是继续煽动中国的内战和纷乱,以使得那个国家的任务政权都处在不稳定之中。然而我也相信,这样日本在华与英国利益的对抗将完全消失,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将就可能象以前英日联盟时那样再次变的十分热烈。……假如英国、日本和美国能一致对华的话,那么现在困扰这三个国家的麻烦都将远远离去,我们的发言对中国的任何一派势力都将具有权威性,商业利益将由此得到保障,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蓝普森认为“在‘条约’问题上,我们与日本的‘合作’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在中方要求废约呼声中,日本正在为我们而战,所以也许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FO371,1928,7/13172.P.R.O.)。而美国人,即便会向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公开“支持”中国,但这种“支持”将十分有限,或者说仅仅是“道义”上和“口头”上的,这也使日本深得了美国也不过如此的底牌。
应该说,日本人对英、美在“济案”后的立场估摸是大体准确的。很明显,英国其时对中、日问题的考虑完全是以“实利”为前提的,其政策的要领是“在中日矛盾中,谋求自身的利益”,也即怎样对英国最有利,英国就应怎样去做。尽管如此,由于日本自欧战时起就抱有强烈的在华“独占利益”的野心,英人对此是十分有戒心的。特别是面对“日人正稳定地一步步地向东三省扩大它的影响,直至这块地区终将被并入它的王国”,而“我们的利益却正在被逐步赶出那个地区”的前景,英人当然也不甘坐视。所以在日游说伦敦时,英人对日的警惕远远大于了其时对美国人一些做法的反感,甚至盖过了对中国要求“收回国权”的抵触。所以,英国人可以利用日本人去“维权”但“决不可能不顾中国的抗议而与日本去与日本‘合作’”,英国人会在某些事情上与美国人意见相左,但最终共同的利益需求仍能使他们回到一个战壕中。而美国人,在对英关系上,既希望英和它站在一起抑制日本,又互不信任,对日本,既欲加遏止,又不得不在很多方面与之妥协,这使日本人在挑战华会体系时,越来越无所顾忌。美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对日妥协,姑息养患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马慕瑞在他1935年写成的“备忘录”中,就对日本挑战华会以后,中国态势的发展作了清醒的估计,并对美国可能的选择作了分析。他说: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来,可以肯定,日本在制造事变达成一定目标后,“仍将继续无休止实施它逐步蚕食中国的计划,并将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攫入囊中,并最终谋取在中国的独霸地位”,而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美国在远东就将被迫面对以下三种选择:“1.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占,以积极的态度,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理由去与日本作对,并籍以表明我们的立场;2.承认既成事实,加入进去,这样就需要我们公开的、心甘情愿地尽数撤回以往所有的反对理由,或保留的意见,或有条件的限制等;3.暂时采取一个消极观望的态度,这样做既可无须从我们传统政策所规定的原则作任何后退(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为我们在远东和世界上所奉行),又可至少在时机不利的时候,避免直接的行动。”(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26.)当然,按马慕瑞的意见,对美国来讲,前两种选择都是不合适的,所能做的选择应该是第三种,事实上以后的美国也一直这样去做了,直至太平洋战争的最后爆发。那么,什么是马慕瑞所持的理由呢?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三点:1.避免美国与日本之间最终发生战争。拿马慕瑞的话说,即“避免像这样的一场战争本身就是我们在远东的一个主要目标”;2.在中、日孰重孰轻上,日本重于中国。也即他们所说的,“美国的外交不可能同时去实现两个目标,要想不让日本超出条约体系就须与中国保持某种距离”,而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眼中,正如马慕瑞所云:“必须承认,在远东,中国对我们而言,并不具有根本性影响,甚至已成为一种副面因素。相反,日本对我们来讲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美对中国“统一”后的局势前景并不看好。“二次北伐”后,中国虽然宣告了“统一”,但美国人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内的纠纷仍然十分激烈”,“蒋在维持内部和谐上远非是一个成功者”,“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实质上不过只是内部不同派系暂时妥协下的一种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非常薄弱”。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因‘保护’了中国使之免陷日本之手,并因之而成为中国人眼中的“第一号’,我们也不会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国家,只不过不是最不堪信任的而已。”(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lnstitute Press,1992,p.129.FRUS.1928,Vol,II,pp.425-30.)
正因为出于上述种种现实考虑和利害权衡,美、英对制造了“济案”的日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施以了一定的压力,但根本上采取的都是一个消极、旁观的政策,对日本已形不成任何约束。1928年底,由于东北易帜,加上“济案”后,中国国内反日空气浓厚,田中的中国政策因“不察大局,缺乏慎重,徒遭反感”受到一定攻击,日本强硬派军人不得不暂作收敛之举,币原得以复出,这似乎使一些英、美人士看到“日本重回条约体系”的希望。然而,这一切只是美、英虚幻的一相情愿,在“济案”后,华会体系已因丧失权威性而名存实亡,既然恶行能不咎,违约无制裁,日本国内军部强硬派在尝到挣脱束缚甜头后,只会更加有恃无恐,而币原的复出只是为日本战争狂人更大的军事冒险提供了掩护。30年代始,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列强利益冲突加剧,美、英看到日本势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扩张,终于在对华政策上逐步接近,并开始采取“帮助中国现政权稳定”的政策。由于看到英、美在华政策的这一趋势,乘蒋介石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和与两广实力派对垒,原驻东北的张学良部又在一年前的中原大战中开入关内,日本终于先下手为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目张胆侵吞中国东北,显示出了可以对美国在东亚利益造成威胁的力量。事变发生后,随着中国东三省被日本强占,在日本强力冲击下,摇摇欲坠的华会体系彻底崩塌了,也许这一体系早已名存实亡,但“九一八”后它的“名”也不再存在,正如马慕瑞所说:“华会体系既为中国人蔑视,也被英国人和我们自己忽略,直至它最终在日本人的嘘声中成为笑柄。”(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26.)日本在摧毁华约束缚后,立即用建立满洲国开始了它“重建东亚新秩序”的实际步骤,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开始酝酿,人类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