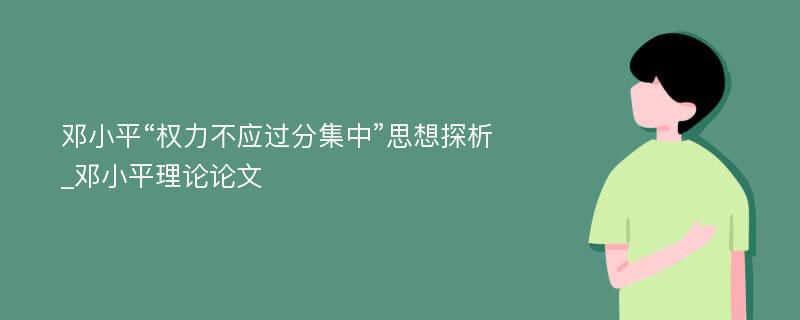
邓小平“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过分论文,权力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权力过分集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表现得尤为突出,致使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抹上了不应有的人治色彩。权力过分集中是由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沿用过去的传统办法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这一论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理论内容,其核心思想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一、权力过分集中的主要表现
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在总结我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对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分析之后,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精辟论断。
究竟什么是“权力过分集中”呢?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以下引文出自该书均只注明卷册及页码)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含义和实质。
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权力过分集中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横向关系上,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二是在纵向关系上,基层和下级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三是在个人与组织关系上,各级各类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而形成了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这三个方面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个方面,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第一层含义。他关于党政分开的一系列论述就是针对这种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这也可以叫做“党委过分集权”。
第二个方面,需要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它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包含着如下不同的内容和情况:(1)党的组织自身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2)政府系统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3)党和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4)党和政府同群众团体的关系。第一种情况属于党组织自身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上级与下级对同一种权力(如党内事务决策权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适当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这与党组织集中了政府及非党组织之权,其性质是不相同的。第二种情况,属于政府系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对同一种权力(国家行政管理权)合理配置的问题,这也与解决党集中了政府之权的问题大不相同。第三种情况,党和政府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本来是一种不同性质和职能的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党政与企事业不分,而使企事业单位政治化、行政化,变成了党政机关的附属物,因此理顺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解决企事业单位的权力集中于上级党政机关的问题,其性质是双层的:既涉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又涉及自身由上而下的“简政放权”,也就是说,横向的过分集权与纵向的过分集权是相互渗透的,相互制约的。第四种情况,与第三种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总的来说,后两种情况大体可以归入权力过分集中的第一个方面,属于“党委过分集权”的范畴;而前两种情况,是中央和地方的集权与分权问题,属于“中央过分集权”的范畴。
第三个方面,“各类各级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这个命题,也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情况:在党组织这种委员会制的领导体制内,各级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主要是书记);在政府系统这种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中,各级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主要是行政首长);在企事业单位里,经营管理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其中最严重问题的是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
二、要害问题是领导者个人过分集权
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的几种表现,虽然都属于过分集权的范畴,但具体来看,其性质(合理与否)是各不相同的,对我国政治体制运行的影响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种表现,对于同一组织(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政府系统)来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组织结构上实行某种“集权制”,这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体制,这在宪法和党章上都作了明确规定。就是说,在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上,实行必要的集权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问题是在于“过分”两字。应该说,适度的集权是绝对必需的,正如适度的分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集权和分权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第一种表现,即党集了政的权或党集了企事业的权,以及第三种表现,领导者个人集了组织的权,就具有与此不同的性质。拿第一种表现来说,由于党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文化组织或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因而党政不分以及政企、政事、政群不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是现实而难免的。
特别是第三种表现,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合理的,不应该存在的,也是危害最严重的。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说过:“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同上,第141-142页)在领导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说到底,其实质就是个人与组织不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从而使党的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这是与我们党的性质、党的领导的本义相背离的。在党内,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是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均实行委员会制,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领导,这本来是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长期被误解和曲解。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同上,第329页)由此可见,权力过分集中的要害问题就是领导者个人过分集权。
三、权力过分集中是历史的产物
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是哪个领导人随心所欲建立的,而是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使然。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体制的影响,这是产生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直接原因。我们党从革命战争时期起,就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1942年9月1日,党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同时推选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三大主席,并规定中央讨论问题时“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与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党实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这种个人集权传统是在俄共(布)党的领导体制的影响下形成的。列宁在建党过程中,鉴于军事封建专制的沙皇俄国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所以党必须实行集中制。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党内的集中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领导体制,必然要把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领袖集团手里,甚至集中于个别领袖人物。列宁在1919年创立共产国际时,特别强调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必须实行集中制,我们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创建时起自然就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
与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邓小平曾经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1980年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同上,第348页)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我们党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封建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而没有能够完成。建国以后,我们时常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而忽视了批判封建主义,以致封建主义的思想政治继续残存下来。
就基本框架来说,则是从前苏联政治体制模式搬来的。1955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省委及市委设立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和文化教育部;地委、县委设立财政贸易部、文化教育部;中央、省委和大城市的市委设立政治政法工作部。依据这些机构,对口领导政府的职能部门。这种做法,大体上是照搬前苏联共产党组织机构的模式和党政关系的模式。而这种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又有很大关系。我们长期排斥商品经济,崇尚计划经济,而这要求行政机关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统一管理社会生产和分配,要求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
四、传统办法难以解决体制的深层问题
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权力过分集中乃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建国以来,我们党也曾经意识到党的组织揽权过多、包办干涉过多,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是由于缺乏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大多是沿用传统的办法,结果几经反复,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未能有效地得以解决。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中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这是对执政党地位的错误理解。但是到了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要求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其他国家机关如人大、政府,都只能按党委的决定去办,无权对任何重大问题单独做决定,这等于给党委包办一切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6年,党的八大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地提出了扩大民主、适当分权的任务。邓小平在作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加强党的领导,不是说可以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应有的界限,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不是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也不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这里面包含着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未能被付诸实践。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误地批判了“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个本来正确的观点。1958年“大跃进”,先是盲目下放管理权,然后又反对分散主义,重新肯定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领导原则,并提出了“书记挂帅”的口号。于是各级党委书记分工把口,采取按工、农、财、文等各条战线分口领导的方法,直接地、具体地领导各行各业的一切工作。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要党委书记说了算,否则不能办,这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日益严重。
从建国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但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从1956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以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个人掌握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巨大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通过简政放权的管理体制改革,基层和地方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下级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组织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使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而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地方和部门的分散主义,一度甚至达到需要再次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地步。在如何解决党组织过分集权的问题时,邓小平多次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群分开,并提出了有关的一系列重要指导原则。特别是对于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更是高度重视,反复论述,同时采取过一些重大举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党中央,邓小平建议废除实行了40年之久的“主席制”,实行“总书记制”;在地方上,取消“第一书记制”,地方党委不再设第一书记。但应当看到,要解决好“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五、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呢?概括邓小平的思想,就是要通过体制改革,从体制上制约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使我们党做到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权力过分集中,是与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客观要求相违背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影响,走上个人专断的道路,以至对党和国家及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第333页)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同上,第348页)一般来说,法制与法治是不同的概念,而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其实并无二致,因为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制内在地包含着民主,以民主为基础的法制就是法治。法治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表现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然而它所倡导的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监督制约的原则则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法治之先河开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法治原则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用。当然,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是有区别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社会主义与法治相结合,是我们党治国安邦的最佳方略。
社会主义法治概括地讲,就是按照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笼统地谈法制还不足以表达法治的实质,法制所关注的焦点是统治秩序,而法治则注重对统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合理使用,强调权力对法律的支持和依从,以确保法律崇尚民主、追求公正的价值取向顺利实现。法治离不开法制,搞法治当然必须运用法制来治理国家,但并不是所有法制国家都是法治国家。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秩序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任何社会都有法制;而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并非对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实行法治。法制的基础可以是民主,也可以是专制,但法治的基础必须是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各种权力都在法律所确定的轨道上行使;由于法制自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上,第146页),因而法治社会一般都具有稳定的秩序。从这种角度来说,邓小平在论述法治与法制时,其精神实质都是相同的。
邓小平之所以特别强调法治,要求全党“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来,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律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同上,第332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旦人治现象严重起来,就意味着允许个别人用个人意志代替人民意志,把个人意志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就意味着个别人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使法律因人而异,随人而变,从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使党和国家的命运之千钩系于一发。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第3卷第311页)
在中国,厉行法治的关键是我们党依法执政,即把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法制的轨道。因为共产党是法定执政党,它的各级领导机关从法理上讲虽然不属于国家机构的组织部分,但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灵魂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第380页)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党能否做到依法执政是决定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体制的关键。为此,应努力加强我们党执政活动的立法工作,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制度化、法律化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顽症”。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