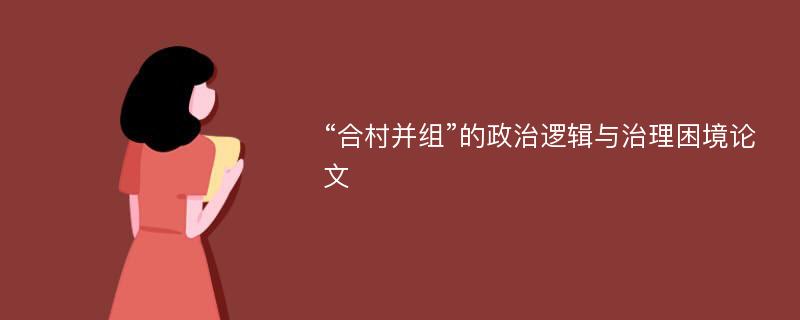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田 孟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
关键词: 村落变迁; 合村并组; 政治逻辑; 治理困境
一、导言:追问大转型中的村落命运
在我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村落将何去何从?对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以1985年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乡政权开始建立,乡以下开始成立建制村的时间开始算起的话,我国村落的总数从当时的 94.1万个变成了2017年的55.4万个,32年内减少了38.7万个。而如果单看1998年,也就是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的时间以来的变化的话,全国累计约有35万个村落是在这一年之后消失的,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1997年,我国行政村的总数有90.6万个,20年内净减少了35.2万个。折算下来,平均每年消失1.76万个,平均每天消失48个,平均每小时消失2个。
由此可知,相对于基于AutoCAD进行二次开发的施工图审核技术的平面视图模式,结合BIM技术的施工图审核技术可以实现“所见即所得”,不仅可以利用三维视图模式显示不满足构件的位置及相关信息,快速定位不满足构件,还可以利用可视化设计的优势直观的显示出二维视图模式中难以呈现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运用三维施工图技术的信息联动修改功能,迅速的完成构件的修改工作,并导出修改后的建筑施工图纸,从而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李培林在他的那本《村落的终结》的著作中曾不无感慨地写到,“仅2001年这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人们似乎忘却或忽略了,在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婴儿之间存在的继替关系,以及后者的血脉和身躯里依旧流淌和生存着的祖辈的血液和基因”[1]1。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感慨还来不及咀嚼和反思,便又有更多的村落消失了。
当然,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或快速转型的大时代里,传统村落的消失并非我国独有,全世界有不少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甚至可以说,连这种因为传统村落的快速消失所造成的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都并非为我国所独有。然而,正如孟德拉斯在他的那本《农民的终结》的著作中提到的“10-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人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之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一样,我国近20年来如此巨量的村落快速消失的现象也向我国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近百万的村落中,是哪些村落消失了?为什么是这些村落消失,而不是其他的一些村落消失?这些村落为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消失?主要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着这些村落的快速消失?这些村落在消失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和姿态?村落的消失给那些原本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归结起来,即是要探究我国的村落何以会如此快速地、大规模地消失的核心动力、运作逻辑和“政治-社会”后果等相关议题。
二、村落消失的核心动力:合村并组
(一)从边界的角度看村落
注 Hh(x)是数学物理中的一种特殊函数,是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一种推广,它的值既可以由数学软件(如Mathematica)迅速求出,也可以用累积正态分布函数递推求出(参见文献[7])。
显然,以上研究启发我们从村庄边界分化的角度探究村落变迁乃至消失的现象和机制。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发现,当地村落边界开放存在着一个从经济边界的开放开始,经历了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的依此开放,最终发生社会边界开放的过程。尽管他很谦虚地指出他不敢说这种“从经济边界到社会边界的开放次序,就一定是普遍的次序”,但是,从目前的主流观点来看,这个次序已经被认为是“‘基本的”次序和‘自然的’次序”[1]40。
教书育人相结合,实现教学相长 和以往的学习方式不同,大学的学习主要是自主学习。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由于没有了教师与家长的陪伴、督促,而变得迷茫,不知所措,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对降低,很容易出现自闭、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有报道指出,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尤为突出。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心理测评不合格人数在逐年攀升,这与在校大学生没有得到教师足够重视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学习中出现问题无人可以倾诉,久而久之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
当然,作者也强调,这个观点是在排除了行政边界和地域边界变动的情况下做出的。众所周知,地域边界的变动来源于自然的不可抗力,而行政边界的变动则来自于被称为大政国基的行政区划,其背后是以国家能力作为后盾的,确实是两个非常特殊的影响因素。但也正是这两个非常特殊的影响因素(变量),构成了与主流所不同的另一种村落变迁的模型。不容忽视的是,在中西部、尤其是某些地质灾害高发或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地域边界的变化并不罕见;继而,因为地域边界的变动所导致的村庄其他类型边界的改变也确实存在。更重要的是,行政边界的变动与村落变迁的关系是后一种村落变迁模型的核心变量。对于村落来说,行政力量其实从来(至少自清代以来[6])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外生变量,村落行政边界以及更高层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是影响村庄其他类型边界的重要因素[7]。
(二)村落变迁的两种模式
但正如杨华和袁松所揭示的那样,在具体实践中,最为关键的并不是行政任务的发包,而是行政任务变成了政治任务,即“政治发包制”[27]。作为执行政策的基层政府而言,上级政府安排下来的并非一般性或常规性的行政任务,而是一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政治任务,因而也构成了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基层政府在开展中心任务时,受限于行政资源的严重不足,往往采取打破常规的方式,打破日常的个人分工和部门分工,打破条块分隔的状态,甚至打破某些通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总之是整合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力量服务于中心工作的贯彻和落实[28]。合村并组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是一项行政任务,然而从本质上看它更是一项政治任务。“行政任务的政治化”是导致合村并组在全国各地迅猛推进的第一推动力,继而也是导致我国近20年来村落急剧减少的第一推动力。
那么,我国的村落变迁主要是体现了诱致性的还是强制性的模式呢?通常的观点认为,我国村落变迁的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翻转。在改革开放以前,也即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比较彻底地渗透进了乡村社会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控型治理”[8],此时的村落变迁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农民缺乏自主权[9]。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行政力量开始从乡村社会中后撤,此时的村落变迁主要是自发的,准确地说,即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村落发生了类似于李培林在羊城村发现的、并被视为新时期主流的村落变迁模式:从经济边界到社会边界依次开放。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村落变迁的模式对村落本身所在的区位具有非常苛刻的要求:村落必须在城市或工业区的周边,或者说在其向外平面扩展的范围内,唯有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受其经济上的辐射、带动和影响,发生经济边界的自然开放,甚至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过程中被纳入其中。
从我国的村落变迁的具体实践过程来看,诱致性的自发模式和行政性的强制模式同时存在。一般而言,村落的消失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其中一种是“农转非”,即由于城市化扩张,位于城市周边的农村被纳入到了城市版图之内,城郊农村地区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迁,既有的行政村(村民小组)建制随之被转为城市居委会(居民小组)建制,村落也随之消失,融入城市之中。另一种是“合村并组”,即将较多的村落在行政组织层面或(和)空间层面合并为较少的村落,从而导致部分村落的消失。值得一提的是,合村并组又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其中一种是仅仅在行政组织上的兼并,不涉及农民搬迁,也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合并;另一种则不仅行政兼并,而且还涉及农民搬迁,也即村庄合并。狭义上的合村并组主要指的是村落行政建制的合并。由于没有触及到农民搬迁等复杂问题,故而在行政合并的过程中,村落的消失主要表现为行政建制数的减少,农民生活的村庄实际上并未消失。而村庄合并则不仅是行政建制数的减少,同时也是村庄的消失,即不再是农村居民点。通常来说,合村并组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而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往往是很复杂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减轻农民负担、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投资效益、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等。
从边界的视角来看,以上两种模式都意味着村落行政边界的破裂。不同之处在于村庄社会边界的破损程度。其中,“农转非”的模式是把原来的农村空间彻底变成了城市空间,因此,这种模式不仅破坏了村落既有的社会边界,而且这种破坏的程度是很彻底的。当然,我们在现实中也发现不少村落“拒绝”彻底融入城市,拒绝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实施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与当地政府就土地非农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它们在留地安置等相关政策的培育下,逐渐形成了零星点缀在城市版图中的城中村。李培林的羊城村正是这样一些城中村。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城中村经济边界的开放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在合村并组的两种模式中,行政建制的合并模式仅仅是在行政组织架构上进行的调整,因而对于村落社会边界的影响最小。这种模式主要影响的是新行政组织的性质,触及到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村民之间的关系则几乎不受影响。而那种由农民搬迁集中居住的模式,则触及到了对村落既有的社会边界的调整,经常表现为大村或大型农村社区等。
(三)合村并组与村落消失
笔者认为,合村并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行为,其背后往往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考量。这项工作从最初的提出到最后的实施,不仅体现了行政逻辑,同时也贯穿着政治逻辑。合村并组是国家因应客观情势的变化(包括农村的变迁和国家的变迁等)做出的有意识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提高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增进政权的合法性。总之,合村并组具有政治正确性,这是我们理解政府在推进合村并组中的各种现象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在新世纪以来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村落急剧消失的主要模式并不是主流认为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所导致的诱致性变迁模式,而是主要由行政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主要由基层政府主导和组织实施的强制性地“合村并组”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一轮又一轮地上演,并且至今仍然在轰轰烈烈地上演过程中。比如,在2007—2010年,山东诸城市将其辖区内的所有建制村(共1249个)全部撤销,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成为全国首个撤销了全部建制村的城市[11]。山东德州市提出将辖区内8319个行政村合并为3339个社区;而该市下辖的平原县提前完成任务,将全县876个行政村合并成了180个农村社区[12]。山东惠民县近期也将全县1118个行政村整建制调整合并为109个农村社区[13]。山东省的模式基本上是采取让农民搬迁、集中居住甚至“上楼”的模式,不仅打破了既有的行政边界,而且也打破了村庄社会边界,甚至是农民私有层面的家庭边界。这种模式的出现肇始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即将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这一政策促使了包括山东、四川、浙江、江苏等建设用地指标名义需求量超出计划用地指标的省份用“迁村”的方式“腾地”(指标)[14]。
由于迁村腾地涉及到对农民的拆迁补偿和集中安置,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进来,这对于财政收入不佳的地方构成了一个硬约束。因此,其他省的主流模式并未如山东等省那么激进,即主要采取了行政建制合并的模式,一般不涉及农民搬迁和集中。但即使如此,其他各省的力度和速度也很惊人。比如,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湖南省共合并17442个行政村,占全省总数的42%[15],短短一年内便有近一半的村落消失了。2017年8月至9月,湖北监利县共合并315个行政村,减幅高达49.4%[16],即不到一个月便消灭了近一半的村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近20年内我国消失的村落到底是哪里的村落?其次,推动这些村落消失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就第二个问题来说,显然,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笔者发现,推动这些村落消失的主要动力并非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所诱致的自发变迁,而是在中央政府倡导或默许、地方政府主导或鼓励、基层政府组织实施的“合村并组”,也即是一种由行政主导的强制性的村落变迁模式。当然,那种自发的诱致性村落变迁的模式也不是不存在,但却并非主要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消失的村落并不是像主流所想象的那样,即位于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村落,而主要是那些较为远离城市的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落。也就是说,从村落边界的角度来看,我国村落变迁的主流次序是由行政边界的开放开始,最终到社会边界的开放。
三、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运作机制
村落的快速消失引起了部分人文学者的高度警觉和密切关注。其中,冯骥才从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角度和高度,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呼吁和实质性的努力[17]。然而,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角度和高度,使得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少数颇具特色的村落上,而对于那些目前仍有农民生活于其中、但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般村落则较少提及。但是,近20年来快速消失的村落并不是那些特色村落,恰恰都是这些非常普通的村落。
由于我国村落的消失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行政力量对于特色村落往往有天然的亲和性,打造特色村落甚至是政府消灭普通村落的经常性理由。故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层面,而在于政治社会层面。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如此不约而同而又不遗余力地推动合村并组以消灭普通村落呢?合村并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合村并组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接下来的两节将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2015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实施《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从煤电、水电、新能源、油气、电网、有色金属、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努力探索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但是规划批复至今,还未见到具体的税收政策扶持文件,老区的企业除了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等国家级的政策优惠,并没有相应的地方政策出台。建议借鉴北部湾经济带的优惠政策制定出台相应老区的税收政策报批,为老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一)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
尽管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所展现出来的惊人速度和良好质量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10],然而,民政部的数据却显示:“农转非”并非我国近20年内村落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以我国城市居委会2017年有10.6万个作为参照,它比1989年的9.4万个仅仅多了1.2万个;而即使与在此期间城市居委会最少的时候,即2003年的7.7万个相比,也仅仅多了2.9万个。而如果与1997年我国城市居委会有11.7万个的数据相比的话,我国城市居委会在行政村急剧减少(约35万个)的近20年内,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增反减”的状态。城市居民小组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城市居民小组从1997年的108.3万个增加到了2017年的137.1万个,20年内增加了近20万个,与村民小组同期约100万个的减少规模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村庄治理规模的扩大。在治理研究领域,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或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话题[30]。从理论上看,治理规模与治理有效性之间具有内在张力。一方面,治理必须要建立在一定规模之上,唯有如此,才能为治理筹集资源,提供运作空间。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治理规模的不断扩大,治理负荷也在快速增加,治理负荷显然会削弱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当治理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以后,治理将会因为日益负重而陷入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看,以上自新世纪初期以来发生的两个巨变似乎并无龃龉之处,甚至反倒呈现出了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18]的特征:一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以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激励下流向了能够使其获得更大收益的部门或领域,从而引发了村庄在经济(经济分化、农业副业化)、社会(社会结构多元化、阶层关系激化)、文化(文化多元化、消费主义文化盛行)、政治(精英流失、干部党员能力弱化)等各个方面的危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视为市场对乡村社会、文化伦理的冲击。另一方,国家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学生村官制度、村医定向培养制度、免费师范生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以一种近乎“逆市场潮流”的姿态,重新将人财物输送回农村,以确保农村能够在市场的剧烈冲击下仍然具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即是对农村社会、文化伦理受市场逻辑冲击之后的一种“反向运动”[19]。
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双向运动在实际的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客观上的约束与限制,尤其是在我国绝大多数村落所具有的高度分散性与国家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相对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更成问题的是,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村落仍然处在、并且必然还将继续处在急剧变动的情况下,这种原本就已经十分棘手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变得更为棘手。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体现的是政治性;但另一方面,提供公共服务需要财政投入,而财政资金又必然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必须要兼顾财政支出暨公共服务的有效性。然而,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大散居、小聚居”的居住传统和居住格局,村落的离散程度很高,这种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对于国家向农村地区转移的必然是相对有限的公共财政资金暨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在于,部分村落很可能正在消失并且最终必然消失——实际上,正如李昌平所言,70%的村落必将消失[20],对于这一类村落,到底应不应该投入财政资金?如何投入财政资金?
已于2018年8月7日重新生效的第1245条要求,总统对“被认定为在明知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向伊朗销售、供应、转移,或从伊朗转移会被应用于能源领域的石墨、金属原料或半成品金属(例如铝、钢、煤,以及集成工业过程中使用的软件)”的人实施至少5项报复性制裁。
在这样的背景下,合村并组成为了有效破解上述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合村并组,对原本零散细碎的村落进行了重新整理或者整合,对处于快速变动的村落进行适当的规划,提供某种确定性,从而使之可以与国家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形成更好的对接。正如龚志所说的:“合村并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21]。因此,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体现在它能够改善国家与农民关系,提高政权合法性。
(二)合村并组的运作机制
合村并组背后所体现的提高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图是中央政府的诉求,主导合村并组的地方政府及基层政府何以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呢?经验显示,如果上下级政府间的意图不一致、甚至难以调和,那么下级政府往往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变通、扭曲、选择性地执行等方式,造成政策目标的迟滞、偏离甚至失败。有趣的是,合村并组的工作在全国各地似乎并未出现过这种政策执行偏差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高度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比如,前已提及,湖南省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把全省近一半的行政村(17442个)都合并了;而监利县更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合并了全县近一半的行政村(315个),并且“没有出现一例恶意阻挠和操作破坏改革的违纪违法行为,没有出现一例在改革中不作为乱作为的事例”[22]。这就涉及到了具体运作机制的问题。
贵州省某磷复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开磷集团和瓮福集团的融合在技术层面是可以实现的,比如磷石膏的处理技术已经成熟,但是是否能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何光亮面前仍有较大阻碍。他说:“两家企业都是国有老牌企业,负债率都比较高,而且企业包袱重,所以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如果资金瓶颈无法解决,后续很多想法是难以落地的。另外是市场的问题,磷石膏绿色建材的发展思路固然很好,但是目前市场不成熟,有待开发。”
从运作机制上来看,合村并组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各地快速迅猛地推进,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基层(尤其是乡镇)在接到合村并组或相关任务时,它已经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比如,在湖南省,撤乡并镇和合并建制村的任务本身就是省委省政府的意志,并直接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层层安排下来。其主要理由有:湖南省土地面积全国排名第10,人口数量全国排名第7,而乡镇数量却位居全国第2,建制村排名全国第5,乡镇平均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均低于广东、湖北、广西、江西等周边省份,乡镇和建制村数量多、规模小、管理效率低、行政成本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23]。为了防止出现政策执行偏差,该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非常明确而又详细的《任务指标分解表》,对各地建制村调整的比例进行了控制性规定。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紧急救助系统建设,主要是借助于手机、监控、智能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机器、紧急求助呼叫器等服务终端和大数据平台,将老年人紧急求助的需求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地传达到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方,养老服务提供方再通过综合分析紧急需求的程度,按实际需求情况,利用系统资源整合功能链接老人身边最近、最优、最合适的紧急救助资源为其提供救助服务,实现由线上线下协同配合提供紧急救助服务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此外,当老年人群体因各种因素所致的危险情况发生时,大数据平台感应系统会在第一时间反馈紧急需求信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是避免老年人因紧急求助无效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再比如,监利县的合村并组就是由省市组织部门提出的一个政治任务引起的,即要求在2018年7月1日前全县各行政村都要建设一栋均价约为120万元的标准化村部大楼。这样一个硬要求对于一个行政村数量众多而县级财政又捉襟见肘的农业大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和负担。数据显示,监利县当时共有638个行政村,这就意味着县级财政将要投入7.6亿元财政资金才能完成任务,而该县当年实现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只有8.42亿元[24],根本满足不了完成上述政治任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即使拿出了这笔巨额财政资金用于每个行政村的标准化村部大楼建设,也必然会出现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问题。因为其中有不少行政村因为人财物的快速流失已经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和迹象,故而根本没有建设标准化村部大楼的必要,建好之后不仅利用率不高,而且很快便有可能面临被废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合村并组,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该县决定借此机会启动全县新一轮的合村并组工作。合村并组的工作完成以后,监利县开始投入巨资(3.2亿元)建设339个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尽管仍属巨资,但相比于合村并组前的需求而言,还是节省了4亿多元的财政。
众所周知,政治任务是不容商量的。上级政府安排的政治任务内容规定得越具体,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具体执行政策以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能够灵活运作的空间也就越小。比如,监利县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建设标准化村部大楼,这是不容商量的。而该县通过“合村并组”这样一个制度创新,完成了上级安排的任务,同时也添加了某些当地政府自身的意志和诉求。而湖南省的合村并组本身就是政治任务,而且省里对于某些重要指标已经规定得特别详细和具体了,这就导致下面市县乡的灵活空间大大降低了。由于合并建制村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执行政策的基层政府往往存在较大的困境和畏难情绪,最终在该省的不少地方往往是按照省里规定的具体调整比例平均分配。比如,H市分到的调整比例是40%,那么,全市范围内所有的县(市区)及其下的所有乡(镇街)都按照40%的比例执行。而到了乡镇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尽管面临不同的具体情况,也不得不坚决完成任务。
对于这种通过将行政任务转变成政治任务,然后在行政系统内层层传递,最终由基层政府贯彻执行的现象,以及该现象形成的原因、条件、效果及其问题,学术界近年来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周黎安、郭亮等人提出的“行政发包制”[25]或“行政包干制”[26]的观点颇具启发。这个观点认为,上级政府将行政任务以发包的形式给下级政府,赋予了下级政府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相应自主权,从而对后者形成了极大地激励,促使其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利益的满足。“发包”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放权让利”的过程,下级政府在完成上级安排下来的任务的同时,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和谋利空间。比如,在完成村庄合并和农民集中居住任务的同时,基层政府也获得了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用于城市周边地区农村的征地拆迁,从而为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准备更多的土地资源。再比如,通过开展合村并组的工作,能够比较有效地减少行政村和村干部的数量,从而减少财政供养的村干部人数和对村级组织支付的行政费用;除此之外,还能以一个更大的组织单元对接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种财政项目资金,避免项目资源过于分散,提高各种涉及农村的财政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最终促进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
综上所述,根据边界开放次序的不同,可以将村庄变迁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类型。在把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作为村落的核心边界的基础之上,主流的诱致性村落变迁模式强调经济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而非主流的强制性村落变迁模式则强调权力因素的主导性作用。
我们喜欢这幅作品的取景构图,主要的引导线由沙袋构成,模特背后的竖直线条也很好地衬托出了她。这是一幅很成功的现场人物肖像,很好地给出了场景的氛围。不过,如果能让模特左手的拳击手套显露出来,或许会进一步丰富画面的亮点。
通过这种将行政任务政治化的“中心工作”模式,合村并组比较有效地实现了预期目标。具体来说:对于执行政策的基层政府来说,首先是完成了上级政府交办下来的这一政治任务,避免了来自上级党委政府的政治上的问责压力。其次是在开展和完成上级工作的过程中,也加入并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比如,监利县以上级政府要求标准化的村部大楼全县覆盖要求为契机,把合村并组这样一个基层政府自己的意图也加入进来,从而既完成了上级建设村部大楼的目标,也实现了自己的减少行政村数量、进而减少县级行政资源支出的目标。而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而言,面对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失而村庄又呈现出高度分散、细碎和流动性大的基本特征,通过合村并组,相对扩大村庄的规模和人口的规模,进而通过行政力量为部分有条件的村庄提供一种稳定性的外力支撑,可以比较好地承接自上而下的资源,落实国家对村落和农民的各种政策和意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国家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良好对接,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等。总之,合村并组有利于密切联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提高农民的国家认同,提高政权的合法性。
四、合村并组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
在湖南省撤并了全省近一半的行政村以后,该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劲夫表示:“农村并村后,建制村人口增多、地域增大,传统的乡村社会从熟人、半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生人社会转变,政府公共服务半径扩大,农村社会治理基础发生变化,农村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面临挑战和机遇”[29]。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逻辑之外,合村并组还有一套治理逻辑。政治逻辑主要关注国家与农民关系,强调农民对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认同;而治理逻辑则主要关注基层干部与农民、农民与农民关系,强调农民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政府的回应等等。
最后,知识产权评议是防范和化解重大投资项目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方法,是维护产业安全和优化产业布局的关键环节。在我国,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往往承载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满足公共需求等政策功能。通过对区域内重大投资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和产业发展规划等进行知识产权评议,可以及时发现其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并提前做好防范和化解工作(包括开展储备性、应对性的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从而起到维护产业安全、优化产业布局的作用。
(一)合村并组的治理逻辑
为合村并组的工作提供政治正确性的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变化。其中一个是村庄本身的变化。在我国近2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庄因人财物大量外流而出现了巨大变化:农民收入多元化和经济分化,农村社会结构复杂化,村庄空心化,农村原子化,村庄价值的多元化,地方性规则的弱化,党员干部老龄化及能力弱化,村庄社会关系理性化,农业生产的老龄化,土地非农化或非粮化甚至被抛荒,村庄公共设施衰败,公益事业建设越来越困难等。另一个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新世纪初,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标志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即国家向农民汲取资源的旧时代结束了,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民(农村)输送资源的新时代开始了。
西方政治哲学对于治理规模的“小”“大”的选择经历了变迁。在工业革命以前,学术界显然更偏爱规模小,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城邦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规模小的优势是可以实行直接民主,通过相互之间的充分讨论和交流,形成共识,实现善治。而在工业革命初期,尽管学术界——比如,卢梭、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仍然更偏爱规模小,但这种主张已经越来越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其对应物了,规模小逐渐成为了一种理论上的最优治理规模。而当作为直接民主的替代性方案——代议制民主被提出来以后,规模大成为了一种面对现实的普遍选择。到了联邦党人在阐述美国的建国方略之时,规模小就是理想的最优治理规模的观念被拉下了神坛,规模大则变成了一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最优的治理规模。然而,各国的治理实践却显示,规模大带来的是民众政治效能感的低下和政治冷漠感的普遍化,这些现象又激励着新时期的政治学家们重新探讨治理规模及负荷与治理有效性的关系[31]。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问,合村并组的工作是否增强了村庄的治理能力?具体来说:首先,合村并组是否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以使之能更好回应农民的诉求,满足农民的需要?其次,合村并组是否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使之能够更好地表达自身的需求偏好、意见或建议?最后,合村并组是否改善了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干群关系),使基层政府与农民能够为着确保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目标达成一致行动?
选择2016年5月—2018年7月在我院就诊的骨折患者783例。这些病例均进行了X线平片检查和CT检查并全部传入了PACS系统。对这些病例利用PACS系统予以回顾性分析,发现X线平片漏误诊77例。这77例患者中,男性患者41例,女性患者36例;年龄2~83岁,平均48.6岁;其中四肢骨折8例,骨盆骨折12例,脊柱骨折10例,肋骨骨折44例,鼻骨骨折3例。
前面关于村落边界的讨论提示我们:村落是一个实体。尽管村落处于整个国家体系中的末梢位置,但村落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社会和文化实体。具体而言:首先,在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以后,我国实行了“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并延续至今。乡政村治指的是在乡一级设置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以下为群众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级村民自治组织,村落是一个政治实体。其次,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集体经济实践(资产、债务)的基础上,村落是一个经济实体。第三,在传统宗法制度和人民公社时期高密度的集体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农民们以村落为单位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自己人”认同,建立了一个包括人情往来在内的互助圈,故而村落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实体。
笔者认为,这些村落既然能够延续至今,保持了基本的秩序和稳定,自然有其内在的道理和机制,从而确保了村落各种力量的均衡,也即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且总体有效的治理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村并组不仅是两个乃至多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体的合并,而且也是两个乃至多个相对独立的治理单元的合并。合并前,各个治理单元具有个自的秩序维系机制和力量平衡状态,合并以后,这些秩序维系机制如何统一?其中的力量平衡在必然被打破以后如何重新建立平衡?总而言之,合并后的新秩序如何达成?
(二)合村并组的现实困境
从全国各地的政策实践来看,合村并组以后,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治理上的困境,不仅没有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甚至还制造出了很多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首先,合村并组并没有起到降低行政成本的作用。合作并组看似减少了村干部的职位数和人数,从而减少了基层政府对村级的财政转移支付,但从客观上说,合村并组并没有减少基层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32]。原因在于:在合村并组以前,村干部的职位数与人数与其所管辖的人口和地域范围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均衡;而在合村并组以后,村干部的职位数和人数减少了,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却扩大了,这就必然导致每个村干部管辖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也会扩大,从而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留任的村干部必然会要求更高的待遇,从而也就稀释了减少村干部职位数和人数所节约出来的行政成本。
明确村落的实质内涵是分析村落消失现象的重要前提。费孝通曾指出:村落“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的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3]。显然,边界构成了村落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基本形式要件。村落的边界具有多元性。贺雪峰基于对中西部农村的调研,将村落的边界分为了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三个内容;并认为,当一个村落同时具有这三种边界时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同体[4]。李培林基于在广东羊城村的调研,在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从而丰富了村落作为一个完整共同体的内涵[1]36。折晓叶指出,在传统时代,村落多元边界的重叠导致了村落边界的多元性处在一种隐蔽的状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村落多元边界的重叠被打破了,村落边界的多元性亦随之呈现出来[5]。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苏蕴山介绍,本次发布的10项标准涵盖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三个方面,包括《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那么,由于留任村干部的待遇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村级组织的行政效率是不是也会随之提高呢?实际上,这构成了合村并组的第二个重要理由和预期目标。我们的调研和分析显示,合村并组在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和村级组织行政效率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其中,对于那些不需要与农民打交道的工作,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行政效率往往是很高的;然而,一旦涉及到需要与农民打交道的事务之时,村干部便往往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治理资源和社会基础而陷入困难之中,从而缺乏积极性。问题在于,政府并不可能包办农村和农民的所有事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接触农民,在接触农民的过程中,了解农民,动员农民。否则也就脱离了其作为“最基层”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村并组并没有激励村干部去接触农民。实际上,早在取消农业税不久,学界便已经发现,基层政权开始“悬浮化”[33],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考虑更多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偏好,而不是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合村并组并没有改变既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因为村落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人口的进一步增多,导致村干部与村庄整体的联系更加疏远了[34]。结果造成村干部与村民互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更遑论接触农民、甚至动员农民。总之,合村并组以后,村干部不仅客观上难以接触农民(原因当然很多,比如合并以后村级事务变多或难度提高了、村域面积太大了、农民变复杂了,不愿意或不信任村干部等),而且主观上也缺乏接触村民的内在积极性,因此,即使政府逼迫其接触农民,其效果也很有限[35]。
第三,合村并组并未改善村级治理,甚至还恶化了村级治理。其中最显著的是由于脱了熟人、半熟人的村庄社会基础,造成了村民自治的制度运行成本高企,村民选举过程中乱象丛生,选举之后的村级治理不仅不能有序开展,甚至陷入了瘫痪[36]。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依然客观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有学者称之为公共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以区别于公共经济资源。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与村外的行政力量的关系十分微妙,如果利用得好,它可以是国家行政体系和村庄治理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和助手;但如果利用不当,它也很有可能是后者的重要掣肘。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不仅会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展示出来,更会在选举等重大事项中展现。村庄精英从来都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村落之中,他往往具有特定的村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村干部配置往往是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性力量长期频繁互动所形成的均衡的一个外在表现。作为一项行政行为,合村并组无疑会打破村落内部既有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均衡和建立在这种均衡基础之上的地方性共识[37]。由此,村庄将陷入到漫长的磨合阶段,以最终重建新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及其均衡和共识。从现有的政策文本来看,合村并组似乎并没有为这一漫长的磨合过程做出过什么准备或努力。
治理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规模小的社会单位,不仅人们交往的交易成本更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熟悉,另一个是基于熟悉基础上的亲密感,是一个很亲密的小圈子、小团体。对于国家建立其合法性即政治层面来说,这种小圈子构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但对于确保区域内的基本秩序即治理层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并且有效的组织单元。在工业革命以前,雅典城邦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具体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其中治理与统治是合一的。工业革命以后,现代国家开始建立,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初期,统治压倒了治理,成为首要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小而具体的社会单元被现代的大而抽象的社会单元所取代,冷冰冰的人与体制的关系取代了温情脉脉的人与人的关系,以手艺为基础的家庭作坊里的小生产被由机器装备起来的工厂里的大生产替代,规模较小的国家被规模较大的国家吞并和消灭。在现代国家的力量广泛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以后,它也替代原来的社会机制,为民众提供保障,从而建立民众对国家及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也即是“民族形成”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这种行政性地保障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甚至还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于是,政治问题(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淡出,治理问题开始凸现,促使人们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做出新思考和新探索,强调社会的多元、活力和自主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规模的大与小并非对立关系,小的治理有效性是增进大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学前专业师范生很多课程能完美契合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如手工、学前儿童玩教具制作、幼儿舞蹈创编、幼儿歌曲创编、儿童剧创编与表演、幼儿园环境创设、化妆艺术、婴幼儿营养配餐等。教师在相关课堂上有计划性地渗透创新创业意识,结合最新、最热、最前沿的市场动态、政策导向、消费者需求、调研结果、成功案例等,让学生在热门的资讯中潜移默化的激发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自信,把高师院校的特色和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此外,还可以结合专业特色开展手工艺品义卖活动、化妆评比、歌舞创造大赛等,在实践中提高学前师范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五、小结与讨论:村落变迁的动力学
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考察了近20年来我国村落变迁的动力学问题。显然,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村落的遭遇和命运,是摆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学术界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因城市快速扩张所引起的村落从经济边界到社会边界依次开放并最终融入城市的“村落终结”分析模式。然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导致我国近20年来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运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我国村落变迁动力机制的探讨,也随即从原来的市场经济与村落社会的关系问题,转变成了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问题。
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行政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是政府等现代性力量有计划地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属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最先提出来的。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了这本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基层”所具有的“乡土性”的精彩论述,却忽略了与之相对的“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38]。其实,后者在费孝通开始讨论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之时已逐渐浮出了水面。按照他的看法,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基本上是被吸收在了社会继替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了“安定”的总体特征。
画画对于我来说很熟悉,小时候就常照着家里窗帘上的卡通图画自娱自乐。从小离不开绘画的我也如愿考上了一所绘画类院校,但是我之后所接触的绘画门类就不再局限于卡通绘画、西方素描色彩这类了。在陶瓷大学的学习中,我慢慢地了解、学习到了另一种独特且有趣的绘画门类——陶瓷绘画。当然了大学中学的不仅仅是陶瓷绘画而已,但是这门课程却是开启了我以后陶瓷绘画的道路。
在乡土社会里,个人的行为动机主要来自其主观的“欲望”,人们对自身及其所在的社会得以生存和维系的条件(客观的“需要”)是不自觉的,但由于个人的欲望的形成过程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因此,在个人主观的欲望与其客观的生存条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从而确保了乡土社会的稳定性。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宏观的传统文化与个体的主观欲望之间的微妙的关联快速被打破了。由此,人们必须要明确知晓其得以生存的客观需要,并依此而计划行事。费孝通认为,当人们行动不再基于客观欲望、而是直接基于客观需要而理性地行动的时候,或者说,当人们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已经开始走出乡土性的社会而进入到现代社会里了。
费孝通认为,计划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普遍现象,而在乡土社会里,则根本没有计划的需要和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计划并不是指狭义的计划经济。计划在这里是人的理性的集中体现。当欲望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人的行为指导之时,需要便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为了满足需要,人类必须利用和发挥其理性能力,做出计划,并依照计划行动。总体上看,社会变动得越快,计划的重要性就会越明显,当然计划变动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更快速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变迁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有计划地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态,也是基本需要。
具体到我国的村落变迁历程来看,在近2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性地介入到村落社会之中开展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导致我国村落变迁的最主要模式。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在近20年内多次掀起合村并组运动的浪潮呢?学术界既有的解释主要是从压力型体制、政绩驱动、土地财政、锦标赛等行政机制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社会变迁的角度之下作更加完整的理解。众所周知,自1840年以后,中国变成了由西方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从过去的中心和先进位置变成了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和落后位置,套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即从一种普遍性知识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39]。面对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现代化是惟一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来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它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比西方早发现代化过程中的守夜人政府更加积极有为。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则是最主要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在农村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表面上是行政逻辑的自主扩张,而实际上却是上述政治逻辑在农村地区的具体体现。因此,合村并组何以能在近20年来如此广泛而又迅猛地在全国各地推进,本文主要从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以及在这种政治逻辑之下所形成的特定行政运作机制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合村并组对村落秩序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在此之前,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村落社会秩序的维系机制自有其内在逻辑;而在此之后,随着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制性介入,村落既有的社会秩序维系机制受到冲击,而新的秩序维系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村落社会治理于是便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村落社会原有的秩序也并不完全单纯地建立在村落社会性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是既有的行政体系与村落社会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简约的秩序维系机制。在这种简约治理机制里,行政组织的边界与村落熟人社会的边界实现了比较好的融合或平衡,也可以说,行政吸纳社会,社会也利用了行政,从而形成了行政与社会的良性结合状态。而在合村并组以后,行政组织的边界急剧扩大,而村落既有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边界则不仅没有变大,甚至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反而变小了,行政组织与村落社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状态。在此背景下,行政无法吸纳社会,从而导致行政成本高企;而社会无法利用行政,从而导致村落社会的进一步原子化。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问题丛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村落治理开始从传统的简约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现代治理是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大量的行政资源作为支撑,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合村并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或者目标就是要降低行政成本,这显然与现代治理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通过将合村并组的逻辑分为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本文可以对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何以会对合村并组具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做出解释。显然,政府部门更多地是从自上而下政治逻辑的角度肯定了合村并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学术界则更多地是从自下而上的治理逻辑的角度揭示了合村并组对于村落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维系机制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的问题[40]。在农村地区人财物大量外流的情况下,通过合村并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规模有所增大,这种状况不仅可以使得合并后的村落能够更好地承接和利用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和财政资源,提高国家对基层行政组织及其干部的支配和激励能力,进而提升农民的国家认同,进一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近20年的合村并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之下迅猛推进。然而,当我们拨开宏观层面政治逻辑的浓雾之后,顺着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政策和财政资源的供给渠道,回到这些制度、政策和财政资源利用的具体执行过程之中以及这些制度、政策和财政资金的供给对于村落社会秩序的维系及其民众生产生活的安排等治理层面的时候,以行政脱嵌于村落既有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合村并组行为显然不利于村庄治理有效性的实现和达成。合村并组之后普遍出现的村落治理危机可以看做是村落社会对于行政力量强制介入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套用斯科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弱者的武器”[41]。
实际上,这种村落传统的社会文化逻辑对于现代性逻辑的应激性反应,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村落也并不罕见。在这里,“村落终结说”遭到了“村落再造说”的挑战。比如,折晓叶发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村落,面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村落经济边界的开放性与社会边界的相对封闭性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矛盾冲突又共生共荣的复杂关系。村落经济边界的开放并没有构成村落社会文化边界开放的动力和原因,反而促使了村庄社会和文化变得更加具有封闭性,甚至后者还反过来影响甚至是主导了村落新经济边界的厘定和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某种“中间”性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即“超级村庄”[42]。
综合本文的观点来说,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这两套逻辑间寻得某种程度的平衡和良性互动。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政治逻辑不尊重治理逻辑,或者说,如果政治逻辑压倒了治理逻辑,从而导致治理陷入困境,那么治理逻辑往往会以治理危机为“武器”,反过来削弱政治逻辑。也就是说,如果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长期脱离其治理逻辑的话,那么尽管国家在账面上向农村地区投入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然而在具体的制度实践和政策执行层面,这些公共资源并未能够有效地转化成治理资源,从而改善农村地区的治理状况,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基本需要,维系农村的基本秩序,甚至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那么,政治逻辑也将因为治理基础的丧失而面临严峻的危机。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2]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
[3]费孝通.江村经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17.
[4]贺雪峰.村庄的生活[J].开放时代,2002(2).
[5]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J].中国社会科学,1996(3).
[6]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8.
[7]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56-66.
[8]吴毅.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项因素的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1997(5).
[9]项继权.中国农村建设:百年探索及路径转换[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2).
[10]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2.
[11]涂重航.山东诸城“一刀切”村庄[N].新京报,2010-11-02(8).
[12]宋延涛.大村制,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探索[N].德州日报,2009-10-29(10).
[13]殷梅英.以组织振兴为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5).
[14]田孟.一石三鸟?——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批判[J].战略与管理,2013(4).
[15]赵强.“村改”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的启示[N].三湘都市报,2016-06-14(A2).
[16]监利县委组织部.推进合村并组强化农村基层治理[J].党员生活,2018(7).
[17]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2013(1).
[18](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2-130.
[19]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5.
[20]李昌平.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J].探索与争鸣,2017(12).
[21]龚志伟.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12(5).
[22]罗序文,程和平,宋从峰.全县六百多个村,一下减掉近半——监利“合村并组”改革纪实[N].湖北日报,2017-11-01(5).
[23]陈勇.破除发展瓶颈,做强做优乡镇——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段林毅[N].湖南日报,2015-09-28(2).
[24]监利县人民政府.2017年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竞进向好[EB/OL].(2018-10-10).http://www.jianli.gov.cn/Item/16201.aspx,2018-03-06/2018-10-10.
[25]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
[26]郭亮.土地征收中的“行政包干制”及其后果[J].政治学研究,2015(1).
[27]杨华,袁松.行政包干制:县域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基于华中某省D县的考察[J].开放时代,2017(5).
[28]杨华,袁松.中心工作模式与县域党政体制的运作逻辑——基于江西省D县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8(1).
[29]李劲夫.强化责任,推进乡村治理良性互动[J].乡镇论坛,2015(12).
[30]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
[31]达尔,塔夫特.规模与民主[M].唐皇凤,刘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2]贺雪峰.合村并组,遗患无穷[J].调研世界,2005(11).
[33]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
[34]吴理财.合村并组对村治的负面影响[J].调研世界,2005(8).
[35]罗义云.村庄规模与村级治理——对村组合并的考察[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6).
[36]邓燕华.村庄合并、村委会选举与农民集体行动[J].管理世界,2012(7).
[37]廖瑀.村庄合并对村级组织的负面影响——以成都市郊赛驰村为例[J].中国乡村发现,2007(4).
[3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9]格尔茨.地方知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0]贺雪峰.评湖北监利县的“合村并组” [EB/OL]. (2018-10-09).http://www.snzg.net/article/2018/0819/article_42055.html,2018-08-19/2018-10-09.
[41]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2]折晓叶.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J].社会学研究,1997(6).
Polit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Dilemma of Merging Villages or Groups
TIAN M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0,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s of village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main force for the end of villages in China is not urbanization, but the merger of villages or group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village society, the merger of villages or groups is not only a top-down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process, but also causes the bottom-up stress response from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has multiple logic of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merger of villages or groups is the first impetus lead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work.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its governance logic has been seriously ignor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political logic is undoubtedly important, the governance logic also needs to be valued and respected. The work of merging villages or groups needs to find some balance and have positive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logic.
Key Words :village changes; merge villages or groups; political logic; governance dilemma
中图分类号: C9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 2019) 03-0107-13
收稿日期: 2018-11-22
DOI: 10.7671/ j.issn.1672-0202.2019.03.0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DJ076)
作者简介: 田 孟(1988—),男,苗族,湖南麻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学。E-mail:tianmeng211@163.com。
标签:村落变迁论文; 合村并组论文; 政治逻辑论文; 治理困境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