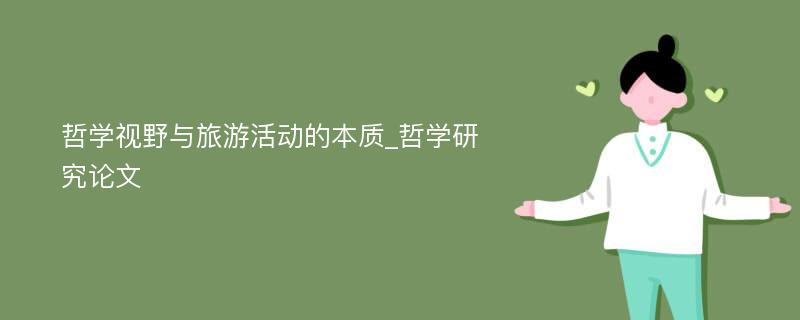
哲学视野与旅游活动之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活动论文,视野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旅游本质”研究方法的反思
“旅游本质”的问题是旅游学基础理论框架的起点,是整个旅游学的核心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正不断深入,但也呈现众说纷纭、难达一致的局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范畴模糊和视野泛化是方法层面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范畴模糊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和“本质”的范畴缺乏清晰的界定。大多数研究是在缺乏对“旅游”、“旅游现象”、“旅游活动”等相关概念必要界定的情况下展开本质探讨的,这是导致“本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也注意到,从“文化”或“经济”本质论到“审美”或“体验”等本质论,实际使用着不同层级的“本质”的概念[1]。我们认为,“旅游”已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如果没有明晰地界定,是不大适合用来作为特定的研究范畴的。“旅游现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旅游者主体自觉到非惯常环境作短暂停留的行为过程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包含旅游者非惯常环境停留过程、旅游吸引现象、旅游经济现象等一系列的现象。为研究方便,我们把旅游者主体自觉地到非惯常环境作短暂停留的行为过程称为“旅游活动”,复杂多样的旅游现象归根结底是由旅游活动引起的。旅游活动是一切旅游现象的原点,是整个旅游现象的核心,“旅游本质”首先应该是“旅游活动”的本质。
随着研究广度的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呈现社会学、美学、生命学、发生学、系统科学等多样化态势,出现一定程度的泛化倾向。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生活世界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宁可说是哲学的普遍问题[2]。我们认为,作为主体自觉到非惯常环境作短暂停留的行为过程,“旅游活动”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现象,自然是一个哲学问题。现象与本质的问题本来就属于哲学范畴,所以应从哲学的视野展开对旅游活动本质的探讨。也有研究者指出,要认清旅游的本质,就必须从哲学的角度阐述[3]。但哲学是人文学科,所以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探究旅游活动的本质。旅游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其本质问题必然关涉人的问题。
二 人类精神矛盾与超越有限时空的精神需求
广义讲,人是能够对自身生存作出理性反思的动物,往往对生命时间和生存空间的生物有限性产生焦虑和恐惧。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人们又往往渴望超越有限时空的永恒存在。生物有限性与精神追求无限性之间的精神矛盾是人类的基本精神矛盾。
叔本华认为,作为有限之物而存在的人类,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相比几乎等于“无”,人类“因为具备理性,必然产生对死亡的恐惧”[4]。弗洛姆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具有“认识理解世界的理性”是“人类一诞生就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新特质”,但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理性,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对生存的种种限制”,意识到“自己的必然归宿——死亡”,因此无法消除“生与死之间”的“两歧”[5]。可见,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的基本精神矛盾。海德格尔则明确地把人类的这种矛盾境地称为“无家可归”,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由于此在(人)对有限的生存领会而处于“畏”的基本现身情态之中,而这种“畏”的情态又“把此在带到其最本己的被抛存在之前,并绽露出日常所熟悉的在世的无家可归性质”、“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6]。
哲学家对人类基本精神矛盾的揭示并不会加剧人们的恐惧,因为理性早已使人类学会用各种途径摆脱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境况。尽管叔本华一直认为人生在本质上是痛苦的,但他也承认出于对生存有限性的认识和反省,人类能够从形而上的见解中获得慰藉,“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是“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7]。弗洛姆也进一步指出:“人的心理的一个特质是,当面对某一矛盾的时候,它不可能依然无动于衷,它会以解决这一矛盾为目标有所行动。人类所有的进步都可归结于此。”[8]为此,“人有着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献身于某种目标、理想或像上帝这样的超人力量”“自然物或祖先”往往是“泛灵论和图腾崇拜”等原始体系所追求献身的目标[9]。海德格尔经过大量的论证,无非就是为了从哲学上证明“存在即永恒”。
无论是叔本华所谓的“解毒剂”,还是弗洛姆所谓的“追求献身和定向的需求”,或是海德格尔论证的“存在即永恒”,实际上都是人类超越自我有限性精神需求的反映。人类总是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超越自身的生物有限性,摆脱有限性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在“永恒的”状态中获得心灵的安宁。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思想的原初起点是建立在宇宙时空知识基础之上的[10],对有限时空的无限超越是人类自我觉醒的开始,形式多样的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或神化传说等,都是人类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精神需求的最初产物,后来逐渐发展的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化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满足人类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精神需求的不同途径。
以宗教活动为例。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在终极境况中“寻求救赎”,而各种宗教就是提供了能够导向个体化行为的某种救赎[11]。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安宁”[12],正是基督徒通过上帝的“救赎”,摆脱因有限性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获得“永恒”的精神享受。“寻求救赎”无非就是人类试图超越自我存在的有限性、满足永恒存在的精神需求。事实上,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构筑着超越人类有限时空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数信众的精神支柱,就是因为它们具备超越有限时空的价值功能,适应了信众渴望时空永恒的精神需求。
其实,对永恒问题探索也始终贯穿整个哲学的历史。从柏拉图主张人类灵魂脱离肉体而回归理念世界,到康德发现人的自由受物理学时间的威胁,从狄尔泰论证时间存在与自由存在的统一,到海德格尔“原始时间”的觉醒,哲学一直面临着人类自身生物有限性与精神追求无限性之间的精神矛盾,一直在试图解决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说,哲学与宗教的救赎“也有类似之处”,哲学是超越了个体化的救赎[13]。
宗教是救赎,哲学是超越了个体化的救赎。哲学视野下的旅游活动,也许就有了超越有限时空的“救赎”意味。
三 旅游活动——自觉的超越
由于理性,人类意识到自身的生物有限性与精神追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超越有限时空的精神需求。各种形式的宗教、哲学、艺术审美等文化活动,都是人类实现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的不同途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着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的精神需求。以宗教活动为参照,就超越有限时空的价值功能而言,旅游活动与宗教信仰活动确有相似之处。
国内有学者在比较分析美国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有关旅游的“神圣旅程”理论和马坎耐有关旅游是一种“现代宗教替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旅游是一种新形式的现代精神文化‘朝圣’”[14]。尽管如此,与宗教活动相比,相对普遍的旅游现象的产生明显较晚,这表明旅游活动应有自己的特殊性。
国内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旅游发展的重要时期。谢彦君认为中国完整意义上的旅游出现于南朝时期[15],曹国新和宋修建认为中国旅游自觉于魏晋南北朝时期[16]。中国古代自觉的旅游活动出现于魏晋南北朝并不偶然,与当时知识阶层的玄学思潮有关。宗白华将这一时期玄学称为“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7]。李泽厚也认为,表面看似颓废、悲观、消极的玄学思潮,实际上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这是一次思想解放思潮,而思潮的主题是“人的觉醒”[18]。魏晋玄学所谓的“人的觉醒”,本质是知识阶层对人的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由的思想恰恰是源于庄学对生命有限的哲学反思和超越时空的精神追求。因此,“晋人”向内发现了自我,也就向外发现了自然。于是,中国早期的山水诗画、自觉的旅游活动随之产生。
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古代自觉的旅游活动发端于魏晋南北朝与欧洲大众旅游现象产生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有相似的思想背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旅游活动的出现,往往与一定范围的思想解放和主体的自我觉醒有关。这表明旅游行为的选择,要凭借主体对自我惯常时空环境的反思和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有自觉性的特征。主体的自我觉醒是旅游行为产生的内在条件,自觉性是旅游活动不同于宗教活动的特殊性(自觉性也是旅游活动不同于商务、会展、探亲等其他异地活动的主要特征)。
主体在对自我惯常时空环境反思的情况下,受到追求超越有限时空精神需求的驱动,自觉地寻求通过空间上的位移,进入新的时空体验之中,借助旅游吸引物的作用以实现对自我惯常有限时空的超越。当人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宗教活动超越时空的价值功能日益减弱的时候,旅游活动的“替代”功能就逐渐浮现,从而日益成为满足人们超越自我时空精神需求的现代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是一种“现代宗教替代”是有道理的,隐含着旅游活动作为一种“解毒剂”的自觉“救赎”意味。
四 “异位空间”、“审美经验”与旅游活动的本质
旅游活动是旅游者主体自觉到非惯常环境作短暂停留的行为过程,包含动机、过程、结果三个要素。从“动机”的角度看,旅游活动不同于宗教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主体对自我惯常环境反思的自觉性,一切旅游活动均出自主体对自我惯常环境的自觉性反思,这是旅游活动的显著特性。从“过程”的角度来看,旅游活动发生的空间必须是非惯常环境,异地性是旅游活动的必要特性。福柯的“异位空间”和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为我们探寻旅游活动的本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之中,“乌托邦”和“异位”是这些空间中“奇特的”两类,它们把一切正常的关系中立化或颠倒了。乌托邦是非现实的空间,是完美或颠倒的社会,异位是现实中存在的、相对于正常生活空间的“异位”。在空间上,异位排斥着现实生活的空间;在时间上,异位与“异时”相关联,积累着时间的永恒性,并与现实时间相断裂,如“狂欢节”、“博物馆”、“度假村”或南美洲的“耶稣会殖民地”。福柯还提出,在异位和乌托邦之间有某种混杂的、居间的经验存在,他称之为“镜式乌托邦”。如镜子是一种乌托邦,使“我”在一个非现实的空间里看到“我”不在其中的我自己,镜子能起到一种异位的功能[19]。
福柯观察到我们生活世界中存在的两类奇特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奇特性就在于它们中立或颠倒了现实生活空间,是非现实的空间。而这些非现实的空间这是相对于旅游者主体的“非惯常环境”。不仅如此,福柯还注意到这些空间具有积累时间永恒的特性,在这样的空间中,“我”已经超越自我的惯常状态。对旅游者而言,非惯常环境就类似于一面镜子,它使主体借助吸引物的异位功能,体味着超越惯常环境的非真实的自我,也体现着异位空间的特质和旅游吸引物的价值特性。
很多学者认为旅游活动的本质是“审美”体验,这是旅游活动本质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审美一般指的就是“审美经验”。按照朱光潜的观点,“美感(审美)经验……就是我们在欣赏大自然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朱光潜先生早期的作品将aesthetic译为“美感”,后来都改为“审美”),“‘美感的经验’就是直觉的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它是从康德以来的美学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原则”[20]。从形式上讲,本质是形而上的范畴,形象直觉不能作为事物的本质形态,我们可以说审美经验是旅游活动过程中重要的心理体悟过程,这一心理过程可能体现着旅游活动的本质,但不能说这种直觉的心理活动本身就是旅游活动的本质。西方美学一直强调审美经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移情作用。利普斯认为移情作用能引起美感,“‘自我’寻常都囚在自己的躯壳里面,在移情作用中它能打破这种限制”“移情作用可以说是由有限到无限,由固定到自由”[21](德国美学的观点,但朱光潜认为,移情作用产生快感而不产生美感)。“由有限到无限,由固定到自由”的审美境界正是审美经验的本质。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马氏认为审美经验是“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直觉根本上说是直观的,而不是理念的”、“永恒满足的死敌是‘时间’,即内在的有限性”,而审美过程是“战胜时间的过程”,具有席勒所谓的“在时间中取消时间”的作用[22]。狄尔泰的艺术“体验”论也为我们展示了同样的结论:生命就是对包含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性的体验,“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命价值超越的问题”[23]。在狄尔泰那里,体验“打破了物我、人我的界限,使物我交融,生命价值升华,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超越有限生命的途径,深刻地触及审美和创作的本质问题”[24]。可见,审美经验或体验都只是过程或途径,而超越有限达至无限的自由境界才是其真正的本质,这一点恰恰就承载着旅游活动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的本质。从内涵上讲,“现象”的本质就是“在一定时间、占据了一定空间的事物”[25],“生活世界是空间时间的事物的世界”,时空性是实在和精神世界的普遍存在形式[26]。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视野,为揭示审美活动乃至旅游活动本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理性促使人能够对自我存在的时空有限性进行反思,产生人类追求永恒存在的精神需求,这实际上是旅游活动的根本动机。而整个旅游活动正是通过非惯常环境异位作用、审美或体验过程中的移情作用体现出其真正的本质:对自我惯常时空环境的超越。
其实,有些学者已经从哲学时空的视野对旅游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讨。陈才提出“应把旅游现象纳入人类社会的永恒时间和立体空间中去分析”,并认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有限性与“人类探索的欲望(人类的好奇心)”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固有的一种矛盾[27]。刘滨谊注意到,旅游目的地除了能带给旅游者“时空精神的异化和强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难以名状的旅游吸引力,姑且称之为人类对于旅游永恒的追求”[28]。孙天胜和曹诗图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旅游行为,主要由于“旅游”能使人处于一种“在而不在”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使人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是对日常社会和寻常意义的超越”[29]。
显然,学界已经注意到旅游活动与主体对自我“日常生活空间”有限性的反思有关,旅游行为的选择具有超越有限时空的动机,旅游行为过程具备超越“日常社会和寻常意义”的价值。这些研究已经跨越具体形态的行为动机,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但是,从上述考察来看,人类社会固有的矛盾不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有限性与“探索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类的生物有限性与精神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精神矛盾,旅游行为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矛盾而展开的。所谓“难以名状的旅游吸引力”,不仅仅是“人类探索的欲望”或“人类对于旅游永恒的追求”,而是人类超越有限时空、追求永恒存在的精神需求。
旅游活动过程中,主体通过空间上的位移,借助旅游吸引物的作用,进入新的时空体验之中,实现旅游活动的实践特性;同时,主体也因此获得超越惯常经验、超越精神束缚、超越有限存在等不同层次的精神享受,使得主体处于“精神上的解脱”的“在而不在”的状态,体现着旅游活动超越自我有限时空的本质和价值特性。从哲学时空的视野考察旅游活动之本质,是符合哲学理路的。不仅能够诠释主体选择旅游活动的行为动机、过程和结果,而且能够体现旅游活动的实践特性和价值特性。
五 旅游活动超越时空的多样层次
由于主体对自我惯常时空的感知和反思的程度不一,他们超越自我惯常时空的需求也会呈现不同的层次。因此,通过旅游活动超越自我惯常有限时空的层次也会有所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层次,即超越惯常经验、超越精神束缚和超越有限存在。对这三个层次的分析和诠释,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活动的本质。
第一,超越惯常经验。由于对惯常生活经验感到疲劳和厌倦,主体总是渴望寻求非惯常环境中新的身体和情感经验,从而满足超越惯常时空的精神需求,这是旅游活动超越惯常时空的最基本层次。孔子所以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是因为曾点所描绘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景与私塾里授课的惯常经验有显著不同。“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是因为只有山水之娱才超越了“醉翁”的惯常生活经验。现代旅游活动中,诸如观光、休闲、游乐、探险、健身等形式都是建立在超越主体惯常经验层次的基础之上。所谓旅游活动的“求异”、“愉悦”、“体验”等说法不一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旅游活动最基本层次的时空超越,即对惯常经验的超越。只有超越主体惯常生活经验的旅游吸引物才具有吸引力,并且与主体惯常生活经验的差异性越大吸引力就越大。
第二,超越精神束缚。由于社会关系、法律、习俗等的束缚,主体会越来越感受到“久在樊笼里”的精神困境。通过旅游活动,借助旅游吸引物的异位和移情作用,主体摆脱惯常的精神束缚,构筑相对自由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层次里,主体所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新的身体和情感体验,而是世俗超脱和精神自由的享受。福柯所谓的“乌托邦”,类似于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其实就是这一层次超越的写照。现代社会精神束缚日益增多,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感。主体通过旅游活动对自我惯常时空的超越,得以摆脱种种社会规则的束缚,获得暂时的心灵宁静,或找到向往已久的“世外桃源”,这是高于身体经验层次的精神享受。所谓旅游活动的“逃逸”、“出离”等“本质”,正是这一层次时空超越价值的体现,“逃逸”或“出离”是形式而不是本质。现代旅游活动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自然生态、原生态文化的青睐,并非完全出于生态、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而主要是出于超越自我惯常精神束缚的内在精神需求。
第三,超越有限存在。如前所述,人类生物有限性与精神追求无限性之间的精神矛盾,使得对有限存在的无限超越成为人类的精神需求。主体通过旅游吸引物的辅助作用,消解自我存在的有限性,将自我放置到旅游吸引物所表达的时空环境之中,满足超越自我有限存在的精神需求,这是旅游活动超越功能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主体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新的身体经验和“世外桃源”的自由境界,而主要是一种消解自我存在有限性的“无我之境”,是超越有限时空的精神享受,这是旅游活动的真正魅力所在。魏源提出“游山”的最高境界是“知山”,即“与山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为一”[30]。也有学者认为,柳宗元所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境界才是真正的旅游[31]。福州鼓山“我无人相”的摩崖石刻,就是游者体悟到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的真实表露,与学者所谓“在而不在”的存在状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现代旅游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体验旅游、养生旅游等的不断推陈出新,在本质上是人们超越自我有限存在精神需求的反映。所谓旅游活动的“审美”本质,就是旅游活动这个层次超越价值的体现。要满足主体这一层次超越的精神需求,对旅游吸引物的基本要求是“原真性”,只有真实的吸引物才能引起主体的时空超越感应。现代旅游开发过程中曾经出现太多的人造景观之所以昙花一现,就是因为它们除了带给主体视觉新鲜感之外,并不能真正满足主体超越时空的精神需求。至于现在仍然大量存在的对自然原貌和历史文脉的破坏性开发,也终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由于具备上述层次不同的时空超越,使得旅游活动能够满足主体不同层次的需求,旅游活动也因此呈现出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此宋人所谓“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32]。合理的旅游开发和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往往同时具备能够满足旅游者上述三个层次时空超越的旅游吸引物。
六 结语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33]。旅游者主体出于对自我惯常时空的反思,自觉地到非惯常环境作短暂停留的过程,本质上是主体自觉地对自我惯常时空的一种超越。从哲学时空视野考察旅游活动的本质,不仅将研究对象和目的限定在“旅游活动”这一“单个体本质”的范畴,而且也涵盖了旅游活动的行为动机、过程和结果,体现着旅游活动的实践特性和价值特性,具有超越具体形态的形而上特征。时空超越的哲学视野,符合现象与本质研究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