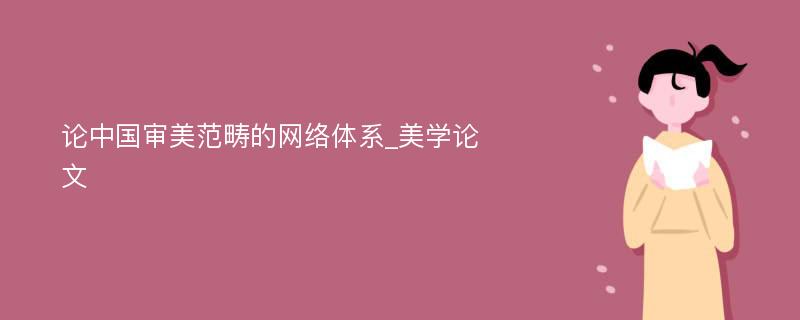
论中国美学范畴网络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范畴论文,体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范畴是中国美学的灵魂。因为汉文字是意象文字,范畴便是意象体,而不是概念符号。意象思维强调生命体验,作为意象体的范畴便有了共通的底蕴,即生命体验。有了共通的底蕴,范畴便相互敞开、相互组合、相互释义,以致范畴之间从形态到义涵都相网相织,形成中国美学独特的网络系统。
中国美学有无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体系?这确实是困扰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难题。有人干脆否认中国美学的系统性。理由是:中国美学自古以来就是点评感悟式的,它散见于各种诗话、语录、家训、序跋之中。即便披沙砾金,也抽绎不出西方美学那样的系统理论。然而,正由于中国古典美学几千年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构建方式,所以必须彻底摒弃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的观念,才能寻找到中国美学自身的体系。
范畴是中国美学的灵魂
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决定着东西方理论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模式。一般来说,西方人习惯于缜密的推理性思维,喜欢追根究源地一层层地剥离事实,从现象到本质地抽绎出一系列的推理模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康德和黑格尔。封闭的理论体系追求的是一种理论的完整结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概念到定义再到推理举证。因此,在西方美学中,范畴(或称概念)只是某种理论的一个标识或一个记读符号,真正的理论价值存在于理论的完整结构中。
东方人着眼于感悟体验,不喜欢剥皮抽筋式的理性思考。故而,中国圣哲往往点到为止,一两句话就把他的整个思想表达完了。比如,老子的“道”论,只简简单单地一段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他的“道”论就算完成了。与他几乎同时代的柏拉图可就了不得,其“理念”说硬是建立了数个等级,一层层地叠架起来。在他看来,最底层的是具体的物质理念,往上是数的几何的理念,再往上是艺术、道德的理念,越往上理念越完美;最顶层的理念是善,是最完美的理念,善又是神的化身,等等。由于中国人是感悟点评式地发表思想,而不是系统完整地表达思想,所以在中国人的思想理论中,范畴(概念)往往是最重要的,理论的全部内涵往往就寄托在范畴之中。范畴也就成了理论的灵魂,而不仅仅是理论的标签。
纵观中国美学史,不难印证这一点。从《易经》的“意象”论,到玄学的“形神”论,王渔洋的“神韵”学说,再到王国维的“意境”学说,整个美学历程中,贯穿着的是一系列的范畴:象、意、形、神、韵、妙、境、意象、神韵、风韵、意境等等。这些范畴没有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定义,每个人对它的解释都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借鉴,读起来似曾相识。而且这些范畴就是理论的支点,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勾连互释,就构成理论的骨架。所谓范畴互释,就是以此范畴解释彼范畴,范畴之间相互释义。如王弼的“夫象者,出意者也”、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就是以“意”释“象”,以“象”释“境”。范畴互释看似在玩一种文字游戏,其实是在建构理论。理论一旦抽离了这些范畴,理论就精髓不存,血脉全无。所以,立范畴对于中国美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巨著专论,还是语录点评,只要范畴一立,精髓便立。
这种以立范畴并以范畴连络成框架的理论模式,得益于中国人历来遵循的意象一体的思维模式。所谓意象思维,就是把无形的抽象的思维内涵与有形的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把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贯穿一体。所以,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中国美学,其范畴本身往往包涵着生机勃勃的内容,表现出意象一体的精神。如“道”、“气”、“理”,本身就包涵着“无”和“有”两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气”,何谓“气”?张载就说:“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在张载看来,“气”既是无形,既是宇宙根本;又是有形, 又是宇宙万物。就“气”本身而言,它本来就是指一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若聚若散的气体现象。借用这种指向聚散隐现的气体变化流行的概念(“气”)来作为他的本根范畴并用以解释他的体用一原的哲学思想,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
意象思维不仅只是决定着范畴“意象”性,而且决定着理论结构的意象性。如中国人运用“太极、阴阳、五行”的模式对宇宙所作的描述。如《黄帝内经》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现实定位。拿“五行”中的“木”作例,《黄帝内经》将它对应:东、春、风、草木、鸡、青、酸、臊、肝、目、筋、呼、怒、等等。所以,整个理论框架意象生动。
由此可见,中国美学范畴之所以成为美学理论的灵魂,是由于范畴本身的意象性。意象性赋予范畴以道、器一体的内涵,使范畴不流于抽象和空洞,而是使范畴血肉精神俱全。
意象中心主义与范畴
提出意象中心主义是缘于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立。
中国人与西方人从思维方式到语言文字再到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都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语言文字是思维方式最直接的产物。在古希腊“逻各斯”既表示思想,又表示说话;在基督教神学中,它又表示上帝说的话,而上帝之语,就是宇宙之道。所以,只有说话、只有活的声音才能传达神的真谛。“神”是什么?是永恒的中心存在,是第一原则和不可颠覆的根据。围绕这永恒的中心,建立起严密的意义等级的思想体系,便是形而上学。在这个等级中,所有与中心原则有关的词,如上帝、本质、存在、本体等等,也都具有了永恒性。而这些永恒性的范畴又被假设与形而下的范畴形成了二元对峙,如灵魂与肉体、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等等。德立达认为,所有的词都不具备永恒性和单义性,因为印欧语言是通过差异对比才显出意义的。所以一个词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或中心的确定意义。词义只能在无穷无尽的语言游戏中,在上下文的不停的流动中,才显出它暂时性的意义来。由于德立达对词义中心论和永恒性的消解,使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本体神学论也随之坍塌。为什么德立达会从语言文字着手,一下子就摧毁了那些至高无上的本体论范畴呢?问题出在:(1 )逻各斯中心主义将本体论与虚幻的不确定的神粘到了一起;(2)本体论范畴失去了形而下的根基, 成为空洞无物的教条;(3 )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下的语音中心论将毫无意义的语音错看成是语言的本质,认为言谈具备在场的直接性,即我在的直接性。言谈因为需要我在,所以它能直接把握住意义的到场和自我意图的表达。德立达认为这种我在的直接性决定言谈优先于书写是不成立的。因为句子的理解,必须要有普遍适用性,即我的“话”,必须具有“无我”时亦能理解的可能性。
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反,意象中心主义首先强调道亦器,器亦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所以,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范畴,都是以一种具体的器物性名词来命名的。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假想中的二元对立。其次强调形象性和象征性。形象性决定汉语言不重语音而重形体,从而确保语言有一个确定的有意义的文字图形。这种有意义的文字图形建立在类比物象现实的基础上。换言之,汉文字作为意象文字,首先关注的是图形文字对所指现实的关联,文字图形必须与所指现实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和一致,从而使文字获取象征价值。
通俗地说,意象中心主义将意义与实在、思想与现实融合在一起,认为意义的传达脱离不了器象的凭借,只有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实在才能表达普遍的抽象的思想。如果说“逻各斯”既表示思想又表示说话的话,那么“意象”既表示意义又表示形象。意象之“象”,则又分别包含文字图形和物象现实。故而,意象中心主义的另一面是文字中心主义,而非语音中心主义。由于意象中心论强调意象一体,也就是强调道器一律,体用一源,所以,在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中,也就不存在纯粹的超验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词,因而也就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语言体系。
文字中心论由于强调意象的明确性和统一性,强调文字要由观物取象到立象尽意再到察象见意,所以,汉文字并不是靠语言游戏的差异对比分延扩散来显现意义的,而是靠文字图形的合理性来显示意义的。所以,意象文字有它的元意义。比如:道、气、理,都有它的元意义。“理”的元意义,是指物之文。韩非子就根据这一“物之文”的元意义,将之提喻为万物自身的规律。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这足以证明,汉文字立象而成的元意义往往是最普通最日常的意义,但是它却支配着对某些终极意义的诠释。无论是“道”、“气”、“理”,还是“精”、“神”、“韵”,莫不如此。这与西方哲学中那些超验的能指和本根的观念相反。后者往往是在终极追问中凭空臆造的,它失去现实的根,却又渴望至高无上。
综上所述,意象中心主义主张由形而下的器象入手来传达思想,因而即便是一些具有终极意义和超验所指的范畴,也都是从最普通最日常的字词中提升转换而来的。而这些日常用语由于它的图形意义构成的元意义,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对终极意义的诠释。所以,在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中,始终没有形成远离现实的解释系统。相反,范畴由于字词的意象一体、道器化一,使范畴本身赢得全整的信息,范畴不是理论的名称,或者说不是一种抽离了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而是意象,是一种元理论。
因此说,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哲学)范畴是一种意象范畴,而不是抽象范畴。所谓意象范畴,是指范畴与个体与主体感受与一切生机勃勃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什么本质的抽取,并舍弃表现本质的具体内容。比如,“神”,作为哲学范畴,生生之谓易,不知其所然,谓之神。就是说,万物变动不居是“易”,万物之所以变动不居是“神”。张岱年说:“神是所以运动变化者,是生生之内在动力。语化之妙,则以神言之。大化奇妙无方,其内在的变动功能,微妙不测,故谓之为神。”〔2〕作为美学范畴,东晋顾恺之首先将“神”用于审美领域, 提出“传神写照”的命题。随后南齐的王僧虔又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何谓“神”,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形神相对来看,“神”当是“形”背后的所以然。比方说:笑,是形;为什么笑,则是神。说到底,无论是哲学还是美学,“神”成为其范畴,其内涵是:“语其不测”。无法说明道白的那些“为什么”便是“神”。
在甲骨文中,“神”即是“申”,“申”就是“电”。追溯起来,“神”的元意义是“电”。闪电在先人的眼里应该是一种骇人的来自上天的可怖现象。而在先人的思维中,这些神秘的现象从来就是不孤立的,而是与神灵、灵魂、生命紧密相关,并将这些自然之谜往往归附为上天的意志。所以,一旦电闪雷鸣,人们便祭祀祈祷。这也就是“神”的字面意义。由此可见,“神”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意象。它描述的是一个兴象感发的场景,同时在其字面形态的构造中亦深深地包涵着一种理解和诠释。或许有人会质疑:“神”是个形声字,“申”乃其声部,表音,无关意。其实,小学史上有“右文说”,即主张汉字的声部不独表音,亦参与表意。安子介考释汉文字90%是会意字。这样一来,所谓形声字,实质上也是一种会意。其形旁声部的合并,也像指事、象形、会意字一样,塑造着一种意象。
再看作为美学范畴的“韵”字。《说文》释:“和也,从音,员声。”音,言也,声也。员,从口从鼎,“口”系鼎之圆口。古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表其意;击石拊石,歌舞足蹈。至三足器(鼎)出,不也会击鼎而歌舞吗?唐代编钟就类似于鼎形,只不过无三足并倒悬罢了。在远古时代,歌舞礼乐是合并在一起的。“鼎”之所以后来成为一种礼器,亦由于它原本既是炊器,又是乐器。现代人一旦兴趣所致不也会时常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吗?故而所谓“韵”,就是指敲击精美器具发出的乐音。喜怒哀乐郁于心,感发而歌,直接宣泄情感,是为歌声;而乐声系敲击器物发出的声音,首先它得八音克谐,同自然之和。嵇康认为,这种“以平和为体”的乐音,无关涉心志情感。但“姣弄之音”毕竟是“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妙。所以“韵”,最初的意象是描述余意无穷的乐音的。北宋的范温便从“韵”之意象入手阐释:“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他认为所谓“韵”,按照原初字面意象阐释当为“有余意之谓韵”,也就是“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3〕。
由此可见,中国美学范畴直接接受意象文字的启迪。其范畴意涵禀承了汉文字的意象性,使范畴本身不是什么本质性的概括,而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意象体。这种意象体“师楷化机,取象形器,而以寓其无言之妙”。换言之,范畴的意象性乃由于汉文字兴象风神、立象尽意的创生方式,将观念、意志、经验、情感与物象现实融为一体,从而确保理解阐释与物性存在与一切被解释的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解释是根据对象的解释,而不是排斥对象的解释。印欧语言就是一种排斥物象现实的解释系统,语言文字完全是一套虚设的符号系统,它与纯粹的数学符号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印欧语言符号中,我们找不到一点现实的影像。汉文字则相反,现实的根深深地扎进文字形态中,并且在文字的现实的根基里又饱含着解释者的观念意志和情感体验。文字在诉说!文字在抒情!比如“大”,大像人形,诉说人就是大,人就是宇宙万物的灵魂!因而“大”字的创生,就标志着人的自觉,同时也是人对自我的赞美!
文字的合理构形不仅只是为了言说,同时也塑造着一种情境,言说是在一种具体可感且极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情景中进行的。比如,人倚木为“休”,人靠床为“病”,跪着的人是“女”,在田中劳作的人是“男”。因此,汉文字构筑的意象,就不只是对物象现实的摹绘,是物象现实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它凝聚了主体的经验认识和心境情绪,它构织的是一幅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图景。因而,意象文字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文字。
意象文字的言说性和情境性,决定了美学范畴本身就是一种元理论,它是理论的根,范畴一立,理论便立。理论不过是对范畴的阐释和延伸。而且这种元理论不是什么本质的抽绎,更不排除主体感受,而是由具体形象、感觉经验、情感体验复合构织的一幅生意盎然的图景。
美学范畴与生命体验
中国美学范畴最难下确切的定义进行解释,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内涵和外延,范畴的意涵随着不同的语境和情境灵活多变。这样就出现以彼范畴解释此范畴的现象,比如,“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以“韵”释“神”,这种循环释义在西方的逻辑思维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西方学术中的概念都是针对某一类物象现实的本质概括,概念彼此间有明确的界域和所指,相互间互不干涉,各司其职。若相互通释,就犯了串错门的逻辑病。中国美学范畴却恰恰热衷于这样的大串门。以神释韵,以气释神,以意释象,比比皆是。甚至将这些不同的范畴融合成一个范畴,比如神韵、气韵、神气、意象等等。究其原因:(1 )中国美学范畴不对立二分。因为中国人是全整立体的观照世界,而不是抽象的二分世界。中国人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含道应物的思维方式,把世界理解成一个相织相网的系统。所以无论是哲学还是美学,其范畴不构成两极对峙的格局,而是相互渗透相互阐释。即如阴阳、形神、有无等这些两一相对的范畴,其实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熹说:“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出去是这脚,行归亦是这脚;譬如口中之气,嘘则为温,吸则为寒耳。”〔4〕(2)中国美学立足于生命体验,西方美学着眼于审美形式的分析。所谓生命体验,就是把宇宙万物看成是活的生的有机体,它有形神血肉情感灵魂。而这些生命因素不是人的生命意识的移入,或者说不是人的生命意识对宇宙万物的强加和虚拟,而是由于人本身的生命意识就是大自然的赐予。生命是共通的,所以以生命体验为内涵的范畴也是共通的。而审美形式是个别的,所以西方美学概念都局限于各自封闭的意义畛域。(3 )中国美学范畴是个意象体。意象没有界定的畛域,它是生动的敞开的形态,是衍射意义之光的发光体。但概念却不同,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内涵是它的中心,外延是它的范围。
中国美学范畴的共通底蕴,就是生命体验。何谓生命?生命是否就是活着?就是存在?换言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系辞传上》:“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生命不止,变动不息。孟子曰:“生之谓性。”“性”又是什么呢?程颢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张载说:“性与天道合一。”总之,在中国哲学中,生命的内涵与宇宙本体是合而化一的。既然“生”是天之所生,也就是“受命于天”。所以,生命最原初的内涵就是:万物化生,禀受天命。王夫之有番话是对“生命”意涵最生动的解释:“一禀受于天地之施生,则又可不谓之命哉?”因此,生命就是天命,“天曰命之,人曰受之;命之自天,受之为性”。因而“性”就是“生之理”,而“生之理”又直接禀承自天之理的,性便也是天之理。王夫之还认为“生”是日日生成,且日生日新,所以生命总是处在一刻不停的新生状态,因而“性”也是日新月异的。由此可见,所谓生命体验,不仅仅是指对活生生的物象实在的认识,实质上更是对天理的昭明灵觉。
由于生命具有本体性征,或者说生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非指个体的“我在”。所以程明道说,“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心、天、性合为一体,便是对生命的体验。所谓“性”,就是“生之理”;所谓“天”,就是“施生”;所谓“心”,就是“受命于天”。与中国美学相比,西方美学着重探讨审美形式和审美的感官经验,所以其美的内涵往往局限于感性材料和感官经验的畛域。而中国美学则把美的意涵定义在对生命的体验中。其生命体验又是天人一体的,是天、性、心的合而化一。换言之“审美观照的实质并不是把握物象的形式美,而是把握事物的本体和生命”〔5〕。因此,中国美学便有气、神、韵、精、 妙等等这样一些与中国哲学本体论范畴紧密相关的范畴。由此可见,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生命体验的美学,而不是感官的美学、形式的美学。
生命体验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即由“天之道”(天,形而上)而至“性之理”(性,形而下);二是自下而上,即由“生之理”(性)而至“天之道”(天)。由上而下,便产生气、神、大、道、境等形而上审美范畴;由下而上便产生精、韵、妙、味、象、意等形而下审美范畴。再由于“天之道”即“生之理”,生命的真谛即在于“天”、“性”一体。于是便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审美范畴的大融合,诸如气韵、神韵、气象、境象、精神、精气等。在中国美学中,形而上与形而下审美范畴之所以能够大融合、大串门,乃由于无论是体验天之道还是生之理,“天”、“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是一样的,因为天、性一体。所以说,中国美学范畴有着共通的底蕴,那就是生命体验。
循环释义与网络系统
中国美学范畴共同的所指是生命体验,且每一范畴都是生意盎然的意象,因而每个范畴都是敞开无蔽的意象体,而不是封闭自足的符号。因此,范畴之间相互敞开融合通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范畴间的大融合。先秦美学范畴主要是以独词为主体的独体范畴,如,“道”、“气”、“妙”、“象”、“美”、“味”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独体范畴开始相互融合,构成复合范畴。如谢赫的“气韵,生动是也”,《世说新语》中的“风韵”、“性韵”、“高韵”。刘勰更是大胆地构合了一系列复合范畴,如“隐秀”、“风骨”、“意象”。范畴的融合不是两个独体范畴简单的相加,而是范畴间的敞开互释。换言之,独体范畴其意域所指相对封闭,复合范畴就标志着独体范畴打破封闭相互敞开融为一体。同时,复合范畴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审美范畴的出现,比如,“风韵”较之“风”和“韵”,应是一个全新的审美范畴。
二是范畴集团和集团范畴的凝聚与消散〔6〕。 范畴融合的方式并非是1+1式的,而是围绕核心范畴凝聚成范畴集团。范畴集团内的所有范畴,我们称之为集团范畴。如以“韵”为核心,构成风韵、神韵、韵味、妙韵、余韵、气韵、体韵等等集团范畴;以“神”为核心,构成神气、神韵、神思、风神、神境等等集团范畴。余下类推,“气”、“意”、“境”等都可以作为核心范畴形成自己的范畴集团,拥有自己的集团范畴。而所有这些范畴集团都不是封闭的互不相关的,而是敞开的相网相织的。所谓敞开的,就是某一范畴既是此集团的范畴,又是彼集团的范畴。如“神韵”,便跨越“韵”、“神”为核心的两大范畴集团。这也就意谓着所谓范畴集团是无形的敞开的相通的,而不是有形的封闭的自足的。所谓相网相织,是因为范畴集团之间的相互敞开,集团范畴之间的相互跨越使所有的范畴集团相互交织相互阐释。这样一来,中国美学范畴就形成以范畴为支点,以范畴集团为骨架,以集团范畴为血肉,以范畴集团之间的相网相织为网络的范畴美学体系。
三是范畴之间的通释互训。循环释义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大景观,如朱熹说“太极只是个一”,“无极而太极”,“太极理也,动静气也”,甚至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性是太极浑然之体”。由此可见,朱熹笔下的“太极”既是“一”、“无”、“理”,也是“人”、“物”、“性”。究其实质,在朱子心目中,由太极而至万物乃是一理,形上与形下乃是一体。故而中国哲学和美学无论是形上范畴还是形下范畴都能串通一气、循环阐释。
中国美学范畴由于有共通的生命体验作底蕴,有“精彩相授、志态横出”的意象作体态,有天人一体的哲学思想作指导,所以范畴之间的组合通释便成为中国美学构筑体系的重要途径和独特方式。独体范畴衍变成复合范畴,实质上是通过两个范畴的形态组合达到相互释义;以命题形式肯定范畴间的互为你我,以此范畴阐释彼范畴,便导致范畴之间循环释义,范畴的义涵因而勾连融通;由形态通释,更构成范畴间的循环组合。通过这样的互相释义、循环释义与循环组合,便构成中国美学独特的范畴网络系统。
注释:
〔1〕《张子正蒙·太和》。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3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钱钟书:《管锥编》第1362~136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朱子语类·九五》。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6〕拙文《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有较详阐述, 见《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