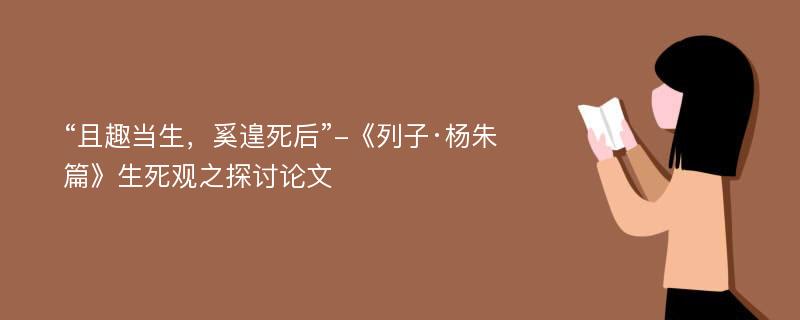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列子·杨朱篇》生死观之探讨
余贵奇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 要: 作为魏晋时期的作品,《列子·杨朱篇》对于生死问题的见解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看法,而拥有独属于魏晋时代的精神特质。通过对生死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该篇作者认为死亡具有必然性、虚无性与随机性等特点,所以人生在世,就应该在遵循“逸身”与“乐生”的前提下,恣情纵欲,放意所为,集中于当下的现实享受追求之上。在关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基础上,该篇作者否定了伪名、虚名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伪名对生命之实的损害,批评那种汲汲于名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 生死观;列子;杨朱
生死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生死观。其中,尤以儒道墨三家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首先,儒家对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乐生安死。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在孔子看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要远大于生命的长度。人类作为生命有限的个体应当竭力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能够做到这,即便人类的生命短暂地如朝夕一般,也可以在死亡来临之时坦然地面对。“孟子继承了孔子这种达观的人文主义死亡观,并将人文精神落实为道德践履,认为‘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2]这种乐生安死的生死态度被以张载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继承:“存,吾顺事;殁,吾宁也。”[3]其次,老庄道家的生死观则具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在老子看来,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与根据,因此,除“道”能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4]以外,万物都有生有灭,而且万物的生灭是相互转化的。“庄子同老子一样立足于宇宙看人生,将人的生命现象看作宇宙自然中的一种物质现象,生命现象中的生死之变也仅仅被视作一种物质之变。”[5]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死之变使庄子合理地得出生命现象的变化由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论,所谓“死生,命也”[6]。最后,墨家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墨子既肯定人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又强调“舍生为义”的献身精神,同时更着重论及了“节葬、明鬼”对生人之利的意义。
本研究显示,天鹅洲长江段浮游植物无论是种类还是出现频次均以硅藻门种类为首,其次是绿藻门和蓝藻门种类,隐藻门也属出现频次较高的门类。而浮游动物中原生动物、轮虫和浮游甲壳三大类群种类数依次为31、27和29。不同季节浮游植物种类与出现频次差异明显。浮游动物虽然种群更替率较高,但DCA排序显示其季节差异并不明显。CoCA分析显示,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之间相互影响显著;拟合权重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硅藻门浮游植物和浮游甲壳动物在冬季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主要关注于浮游生物的种类数与频次,还有待进一步从现存量方面开展研究,以探讨浮游动植物群落之间的联系。
与儒道墨三家对生死问题的论述不同,《列子·杨朱篇》拥有特属于魏晋时代精神的见解。 《列子·杨朱篇》并非先秦时杨朱的作品,学界倾向于该书完成于魏晋时期,如冯友兰先生以为它乃“魏晋时代人之作品”[7]。
日本一位学者两本著作的中译本,近日在图书市场竟然以同一个书名出现,都叫《低欲望社会》。这样的“撞脸”,让图书市场跟风蹭热点的风气又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
一、对死亡本质的洞明
“《列子·杨朱篇》的作者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建置在对现实的经验主义的洞识基础上,体现出一种高度冷静的理性态度。”[8]首先,《列子·杨朱篇》的作者认为死亡具有必然性。依据经验观察,他指出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能够活到一百年者少之又少,“千无一焉”[9]230。寿命的有限标示出人类必然面临死亡的命运。死亡的必然性又具有普遍性:死亡不仅对人类而言是必然的,对于万物也是如此。虽然万物的生命长短有所不同,生时际遇有所不同,虽然有人出生于富贵之家,有人出生于贫贱之门,有人长寿百岁,有人英年早逝,甚至出生时就夭折,有人如尧、舜那般贤明,有人如桀、纣那般残暴,但是不同的人不管人生际遇如何,不同的动植物不管品性如何,最终都面临着死亡的结局。换言之,生前有种种不同的万物在死亡的必然性面前,并没有任何区别,所有的差异都被相同的死亡结局融释了。如果说庄子以“道”齐万物,《列子·杨朱篇》则是以死亡的必然性来看到万物的齐一性。由此可以看出,《列子·杨朱篇》的作者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这也更加佐证了《列子·杨朱篇》不是杨朱本人思想的反映,因为史料记载杨朱生卒年在庄子之前,他不可能受到庄子的影响。
死亡的必然性必定会带来死亡的客观性,“故生非所能生,死非所能死,贤非所能贤,愚非所能愚,贵非所能贵,贱非所能贱”[9]232。死亡与人的出生、贤愚、贵贱一样,是不受主观决定的,并非人力所能改变,是客观必然的。《列子·杨朱篇》通过讲述杨朱的弟子孟孙阳向杨朱请教的事例,强调了这一观点:“孟孙阳问杨朱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9]241“在作者看来,任何人‘蕲不死’或‘蕲久生’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愿望和行为,因为人的生命并不会由于自己主观上的刻意珍重而长生不死,也不会由于对自己身体的爱惜之情而无限延长寿命。”[8]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更是中传统艺术的本体与审美旨归。中国的舞蹈在这种“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思想关照下蓬勃发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舞蹈意象”理论。从《爱莲》到《稻禾》可以看出,在意象类舞蹈作品中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是必需且重要的,但创新也同样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传统古典舞还是现代舞中的意象类舞蹈作品,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必定会朝着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生与死是人生最首要的问题,两者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对死的探讨当然离不开对生的探讨。《列子·杨朱篇》的作者不仅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死亡的本质特征,而且讨论了个体应该如何生存在世上,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以及生存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人生的准则是什么等问题。
然而《列子·杨朱篇》所倡导的追求现实欲望满足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前提与原则的。“杨朱曰:‘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9]233此借杨朱之口指出,感官欲望的满足只是为了获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快乐,否则纵情纵欲不仅不会使人获得逸乐,反而会损伤到享受快乐的载体。因此,杨朱才会批评原宪、子贡,认为钱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及时享乐的需要,而不应该劳心费力经营货财,主张在贫穷与货殖之间遵循一定的原则或者标准,即“乐生”与“逸身”。“乐生”指追求精神上的愉悦,“逸身”则指肉体上的快乐。它们既是原则,又是目的。作者又通过“子贡之世”端木叔的事例强调“乐生”与“逸身”的准则。端木叔虽然尽己之能事追求物欲声色的感官享受,却遵循着“乐生”与“逸身”的原则,所以他“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9]240端木叔作为子贡的后人与子贡完全不同:子贡为货殖而货殖,故被批评为“累身”,被认为这样做“不可”;端木叔则仅仅将财物作为奉养己身的资具,因此能够做到“奉养之余”散之宗族、邑里、一国,所以他才会被段干生赞许为“达人”。在《列子·杨朱篇》看来,能够做到既致力于追求感官欲望满足的快乐生活,又能够做到不因外物而损生、累身,只是把外物作为奉养己身之资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人生真谛的达人。
二、恣情纵欲的人生观
其次,《列子·杨朱篇》的作者指出了死亡的虚无性特点。“也就是说,死是生命的彻底终结。对生命而言,死后一无所有。”[10]死亡彻底地终结了生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命的长短在死亡面前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十年亦死,百年亦死。”[9]232世人皆希冀久生长寿,皆厌恶短寿夭折,但是在作者看来,由于死亡具有虚无性,生命的寿夭其实并无区别,都是毫无意义的。世人都认为长寿比短命好,故而追求长寿,想方设法去养生,以“蕲久生”“蕲不死”,但是《列子·杨朱篇》的作者一反常人的观点,认为活得长其实并不好。因为人们在正常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到“五情好恶、四体安危、世事苦乐、变易治乱”。人们虽以之为乐,但由于久生而不断重复地经历这些乐事则会使人们感到厌倦;人们若是以之为苦,对于如此“切己之患”更不可重复经历。因此“百年尤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9]242活得越长其实越苦,所以世人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久生、长生。由此可见,死亡的虚无性特点不仅使生命的长短失去了意义,也使生命存在时作为生命内容的经历同样失去了意义。作者进一步论述死亡也使个体的天生资质和品德的差异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前为“仁圣”也好,为“凶愚”也罢,都会面临着死亡的结局。那么“仁圣”与“凶愚”有什么区别与意义呢?《列子·杨朱篇》的作者通过尧、舜、桀、纣的例子告诉我们,死亡彻底地终结了生命,生前所拥有的种种都被死亡所终结。除了相同的死亡结局以外,生命一无所有:“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9]232
死亡的必然性标示出生命的有限性,生命的有限性则使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成为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从古至今困扰着无数的人,他们基于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生活经验而从不同的角度对之作出不同的回答。《列子·杨朱篇》作为魏晋时期的作品对此亦有自己的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美厚、声色”,它们的获得与享受能够使人感觉到真正的快乐,也就是说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追求声色情欲的物质性欲望。《列子·杨朱篇》中记载有关于养生的一段问答:“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9]234“在《杨朱篇》的作者看来,人的精神、意识的本质就在于渴望和追求‘音声’‘椒兰’‘是非’‘美厚’等等,也就是说,求得物质享受的最大满足才是人的本性。”[8]
最后,《列子·杨朱篇》的作者认为死亡具有随机性,他借助子产的两个弟弟公孙朝和公孙穆之口明确地指出这一特点:“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9]237生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生命的诞生需要诸多因素的集合才有可能,因此生命是“难遇”的。但死亡却随时可能发生,会很轻易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易及”的。死亡的易及性造就了死亡的随机性。死亡的随机性则使得生命无时无刻不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威胁。所以“在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勾连与对抗当中,死始终伴随着生命,威胁着生命。”[10]
三、对名之价值与意义的否定
《列子·杨朱篇》的作者首先揭示出人生苦短。我们常说人生苦短,然而人生究尽何以苦短则不得而知。从经验事实层面上,作者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与阐释:人生不过只有百年,很是短暂,然而真正能够活到百年的人却又非常罕见;从孩提之时到昏老之年,这是一个人真正能够享受的时光,但是在这段时间中“昼觉夜眠,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占据了一半时光,真正悠然自得“无介焉之虑”的时光是少之又少。人生苦短由此可见一斑。这亦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追问与思考人生之意义何在,人生之真正乐趣是什么?世人对此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名,因为名能够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孟氏问曰:‘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曰:‘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9]237-238人若有名,就能够进一步地拥有富贵、死后的荣耀以及饶益子孙后辈,乃至“泽及宗族,利兼乡党”。由此可见,名能够带来种种利,我们应该“为名”。
《列子·杨朱篇》深入透彻地思考与分析了死与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否定了名的价值与意义。
但此种见解是《列子·杨朱篇》的作者所极力反对的:“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9]248在《列子·杨朱篇》的作者看来,寿命、名声、权位、财货使得人们劳形伤苦,不能恣意所为,以至于损生害身、“不得休息”。这类人也被杨朱称之为“遁民”,他们的命运和前途都掌握在外,不由自己决定。那么这种对“人、鬼、威、刑”的畏惧从何而来,又该以何而解呢?《列子·杨朱篇》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有种种畏惧的原因在于我们有种种羡慕的事物,我们羡慕长寿、美名、权位、财货,只要我们放弃去追逐它们,不去羡慕它们,我们就不再会有种种畏惧,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势、不逆命、不矜贵、不贪富”。
然而名对于世人的诱惑之深是显而易见的,“悠悠者趋名不已”[9]251。当时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9]237这种观点把人之“智虑”视为人与禽兽的关键区分所在,并且认为对名位的追求是人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仅仅从现实的层面指明名的危害,依然不够有说服力,还需要在理论深度上给予其更彻底的批判。因此《列子·杨朱篇》不仅从个体生存层面上去论证“名”对人天性的伤害,主张人们抛却“可杀可活,制命在外”的“遁民”生活,而去追求“天下无对,制命在内”的“顺民”生活,而且从理论逻辑层面上论证“名”与生命之“实”相违,应当“去名存实”。“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9]229作者认为,名乃是伪名,即名实不符、名实乖违。“从价值选择的逻辑上看,名既然是‘伪名’,那就必然要去名;而去名的内在生命依据,是名与生命的本质属性发生了矛盾。”[10]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名”禁锢与妨害了生命的本真天性。生命的本真天性或者说生命之“实”就是对美厚声色的享受与追逐,然而这种享受与追逐却又由于个体对虚名、伪名的追求而受到妨碍甚至是破坏。在《列子·杨朱篇》的作者看来,生命之实受到破坏的个体与“重囚累梏”之人无任何区别。也就是说,名法与刑赏等外在规范对于个体而言,实无异于枷锁、囚笼。个体应当抛弃它们,不使其伤害到自己生命的本真天性。
我们要计算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计算企业的用工成本、计算企业每投入一笔钱的产出回报,要计算每个项目的盈利周期,只有将所有的账都算清楚、算明白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良性发展。
为了彻底地否定名的价值与意义,《列子·杨朱篇》的作者又从死亡的虚无性出发论述名的虚假不实。作者指出,虽然“天下之美归之尧、舜、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9]242,但此对于尧、舜、周、孔、桀、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彼四圣(尧、舜、周、孔)”尽管死后有万世之名,受到世人的称赞与爱戴,但可悲的是“生无一日之欢”[9]244,当他们死亡之后,由于死亡的虚无性,使得“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9]245;对于“彼二凶(桀、纣)”尽管“死被愚暴之名”,但是他们“生有从欲之欢”,顺从自我的天性而生活。当他们死亡之后,死亡的虚无性同样使得“虽毁之不知,虽罚之不知”[9]245。也就是说,由于死亡的虚无性,名对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完全被虚无化了。四圣与二凶所获得的美名与凶名对于他们的生命之“实”无任何影响,而且如果是刻意去获得美名,则反倒会损伤生命之“实”,因为“名者,伪而已矣”,这意味着要获得名就必须“矫性而行之,有为而为之”[9]228,如此自然会损伤生命之“实”。由四圣与二凶完全相反的境况的鲜明对比之下,世人应作如何取舍,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应尽情地追逐生命之实,即“丰屋、美服、厚味、姣色”,且“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9]238,而不应“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9]238,汲汲于虚伪不实的名声。
既然如此,在《列子·杨朱篇》的作者看来,我们就应当效法“太古之人”,因为“太古之人”是一种能够通达生死之道,了达生生之趣的人,故而他们可以“从心而动,从性而游”。也就是说他们真正地认识到名誉具有虚无性和寿命的长短并非生命的真实,而能够不去计较“名誉先后,年命多少”,真所谓“至至者也”[9]231。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70.
[2]张英.儒家生死观的现代解读[J].学术交流,2008(12):29-32.
[3]张载.张载集[M]. 章锡琛,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63.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5:151.
[5]李霞.老庄道家生死观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6-21.
[6]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3.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7.
[8]郑晓江.《列子·杨朱篇》人生哲学探微[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3):14-18.
[9]杨伯峻.列子集释[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贾占新.论《列子·杨朱篇》[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21-126.
Only Living Happily but Not Concerning Dead—View of Life and Death in Liezi ·Yang Zhu
YU Gui-qi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
Abstract: As a work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Lie Zi ·Yang Zhu is a different view of life and death from the main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ssesses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 of life and deat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deat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evitability, emptiness and randomness. Therefore, when we live, we should be lyrical, indulgent, do what we enjoy doing, and focus on the present enjoyable pursuits under the premise of “escape” and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n life and death, the author denies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pseudonyms and illusions, points out the damage of pseudonyms to the reality of life, and criticizes the attitude of life that is notorious.
Key word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Lie Zi; Yang Zhu
中图分类号: B23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10(2019)04-0036-04
DOI: 10.15926/j.cnki.hkdsk.2019.04.006
收稿日期: 2018-11-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后期资助项目(13JHQ016)
作者简介: 余贵奇(1995— ),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标签:生死观论文; 列子论文; 杨朱论文;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