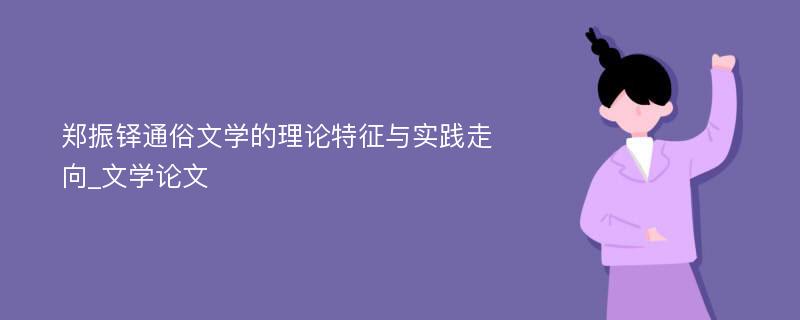
论郑振铎俗文学的理论特征与实践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郑振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郑振铎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俗文学具有“大众的”、“无名集体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是粗鄙的”、“想象力奔放,但有保守性”和“勇于引进新的东西”等六大特质,这种理论特征与现代狭义的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征基本上一致。但郑振铎在对俗文学进行分类、选材和评介等实践环节中,并没有囿于狭义的民间文学范畴,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主要类别及作品未涉及,另一方面却对不属民间文学范畴的通俗作家作品大量评介,体现出在实践中的“通俗文学”倾向。这种理论特征与实践倾向上的差距产生的原因,除时代认识的局限外,还有研究方法和占有材料的局限。尽管如此,郑振铎的俗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发展中国通俗文学事业、扩大民间文学的影响仍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俗文学;理论特征;实践倾向;郑振铎
郑振铎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3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重要奠基作之一,也是郑振铎俗文学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本文将对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体现的俗文学理论特征和实践倾向进行剖析,并对其历史意义和局限进行评述。
一、郑振铎俗文学理论的狭义“民间文学”特征
什么是“俗文学”?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开宗明义写道: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他还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文学》一文中指出:
所谓“大众文学”,乃是“未入流”的平民文学,或“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的别名。②
我们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郑振铎以为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以及平民文学,即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尽管郑振铎把这几个概念作为相同概念并提,但对具体特征作理论阐述时又仅与现代狭义的民间文学特征契合。
郑振铎提出了“俗文学”的概念后,在理论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它的基本特质。他认为,“‘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③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俗文学的“大众性”,是他对“大众文学”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他是从创作的主体、创作目的和动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来界定“俗文学”的。在创作主体和动机方面,它必须是大众的,即为民间的劳苦大众所写和所有的;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反映平民的生活,表现平民的精神;在表现形式上,必须符合民众的口味,为他们所喜好。这里的“平民文学”概念不是指作家所创作的反映平民精神的文学,而是指平民自己创作,并为自己所有的真正的“平民文学”。在对“大众性”这一特质的阐释中,郑振铎十分强调“俗文学”的民间性——“生于民间”,讲述的是“民间的英雄”、“民间的少男少女”、“民间大多数人的心情”。总之,无论是创作者、流传地域,还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无不与“民众”、“大众”、“平民”、“民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注意到郑振铎在对“俗文学”的作者问题上,有时用“平民”,有时用“民众”,有时用“大众”,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在当时文化学术思想的背景上考察。在国际学术界,自1846年汤姆斯提出folklore一词后,相继被许多欧美国家所引用,但对这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总的来看,对lore的理解比较一致,指“知识或智慧”,但对folk一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认为folk应是“人们”,即全民族的国民,后者则认为应指“人民”与“民众”、“庶民”。从folklore的整体意义上讲是指“民俗学”。在俄国,19世纪引入folklore这一外来语,其含义仅限于民俗中的口头文艺民俗部分,并称之为“人民口头创作”。他们对这些作品“民”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大体上有“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人民”等看法;对“民”的范畴的解释,与欧美等国狭义派的观点相近。在我国,“五四”时期,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界限没有严格区别开来,胡适、刘半农以及“歌谣研究会”的同仁们,主张“平民说”,与国际上的狭义观点尤其是俄国的观点相通;而胡愈之、潘麟昌等人则认为“民间文学是流行于民族中的文学”,创作者是“民族的全体”,这与国际上广义的见解近似。到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由于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等人积极主张“民众”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的文学,使这一狭义观点占主导地位。郑振铎对“俗文学”范围的理解,正是受了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另外两个重要特质是“无名的集体创作”和“口传的”。他说:“我们不知道其作家是什么人。他们是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一个地方传到那一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正确的产生的年月的。”“她从这个人口里传到那个人口里,她不曾被写下来,所以,她是流动性的;随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④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俗文学创作主体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创作和传播媒介是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文字。目前,在民间文学领域,尽管在基本理论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但对于民间文学具有集体性和口头性特征的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迄今它们仍是我们区别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外部标志。正因为它是集体创作并流传的产物,才为集体所有而具有匿名性。这里的集体主要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因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也正因为它是以口头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和流传,并将创作、流传过程融为一体,为了适应这种口传心记的流传特点,才在表现上形成了一些极为稳定的表现手法和相对固定的套式,如民歌中的四句头、五句子、比兴、反复咏叹,以及故事开头的套语,情节发展的“三段式”等等。它们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口头艺术实践的结晶,易记易学,为人们喜闻乐见,以至代代相传。这些都是民间文学内部遗传的基因,是构成其传承性的内在机制。
由于民间文学集体性而产生的匿名性,也由于口头语言流播是依赖记忆的不可靠性,因而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将《诗经》中一部分诗意和辞句相同的诗进行比较后说:“显然的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一、因地域的不同,使他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可明了)二、因为应用所在不同,使他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质朴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美文词了。”他还认为“应用之时不同”也是产生变异的主要原因⑤。因地、因人和因时而变,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变异不仅仅表现在辞句上,而且同样可以表现在内容、主题等各个方面。同一类型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可能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主题,因地域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地方色彩,因讲述者的不同会带上不同的个人风格。由于民间文学的这种广泛的适应性,使它具有生机和活力。这种不断变化的形态,一方面使作品日臻完美,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原作品残缺不全,失去光彩。当然,真正的优秀作品只会在流传变异的过程中放射出艺术的光彩,而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基于上述认识,郑振铎又进一步提出了俗文学的下列特质:它们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但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观念,往往是极顽强地粘附于其中,“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此外,俗文学还具有“勇于引进新的东西”的特质,“凡一切外来的歌词,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文人学士们不敢正眼儿窥视之的,民间的作者们却往往是最早采用了,便容纳了它来。”⑥这几个特质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实质上它们是统一的。郑振铎力图运用二元对立的辩证观察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俗文学的二重性。俗文学新鲜与粗鄙的并存、保守与开放的转化,这都是由于俗文学内在规律运动的必然结果。
现代民间文学理论认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创作上最大的不同是即兴创作,它是由现实的社会生活直接激发出的艺术智慧的火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最真实的反映,它在内容上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泥土芳香,在形式上自然、质朴,宛如清水芙蓉,天然浑成。另一方面,由于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表现的形式和运用的语言等作出的是瞬间的选择与判断,不可能反复推敲与琢磨,因而显得有些简单、古朴,甚至是有几分粗俗。当然,民间文学的创作的即兴性也并非完全是自发和无条件的,这“瞬间选择与判断”的过程,只有具备了某些固定的程式、传统的母题、语言和各种表现方式的条件,以及一定的艺术修养之后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即兴的深层结构之中,有着传统的因素起作用。从民间文学的整体情形来考察,即兴性的表层结构中活跃着许许多多可变的因子,这种因子使得民间文学发生变异,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趋势。而在即兴性的深层结构中凝集中许许多多相对稳定的基因,这种遗传因子使得民间文学万变不离其宗,形成一种封闭保守的内核。民间文学就是这种“变异”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尽管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六大特质未作十分详尽的论述,而且有些方面还值得商讨,但从他的基本观点来看,与我们当今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一致的。他所概括的“大众的”、“集体的”和“口传的”特质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和“口头性”的特征相比,不仅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一致,其语辞也相同。从其后的三大特质的阐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所包含的与民间文学特征相似的“变异性”和“传承性”的内容。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对民间文学概念的内涵作了如下概括:“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大特征⑦。郑振铎的俗文学理论与之达到了一种契合。
二、郑振铎俗文学实践的广义“通俗文学”倾向
钟敬文先生在全国解放之际曾这样指出:
“民间文艺”这个名词,用法上颇有广狭的不同,有的人拿它去专指那些产生和流传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的口传文学兼及他们的绘画、舞蹈、扮演等;但也有人把城市中所创作和流传的唱本、通俗小说、小调和戏话等也包括进去。这里所指出的两种文艺,自然多少有相通的地方;可是在性质形态和社会意义上是颇有明显的区别的。⑧
很显然,狭义的民间文学是指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和流传的,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特征的作品。这里广义的“民间文学”是与“雅文学”、“纯文学”、“正统文学”相对立意义的文学,是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的,表现世俗的审美和伦理观念的文学。按现代对文学的范围划分来看,它已不是“民间文学”范畴的文学,而是广义的“通俗文学”范畴了。如前所述,郑振铎俗文学理论实质体现的是狭义的民间文学特征,而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俗文学’进行分类、选材和评介等具体实践过程中,超越了他的理论界定的范畴,体现出钟敬文所认为的广义“民间文学”,即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广义“通俗文学”倾向了。具体表现在:
(一)分类体系的“通俗文学”倾向
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对俗文学从文体上将它分为五大类,并在各类中列举了一定的篇例: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从《诗经》中的一部分民歌,直到清代的《粤风》、《粤讴》、《白雪遗音》等等都包括在内。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即以白话写成的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西游记》、《红楼梦》、《玉娇梨》、《平鬼传》等等。第三类“戏曲”,包括初期戏文(传奇)、杂剧、地方戏等,如《赵贞女蔡二郎》、广东戏、绍兴戏等等。第四类“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如《目连变文》、《西厢记诸宫调》、《香山宝卷》、《榴花梦》、《蝴蝶杯》等等。第五类“游戏文章”,此类属于不重要的“附庸”,如王褒的《僮约》、缪莲仙的《文章游戏》等等⑨。
这里我们且不说它在分类的逻辑体系安排上的合理与否,仅就各类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来看,无疑有许多与其“俗文学”理论特征不一致之处。根据其特质——“大众的”、“无名的集体创作”和“口传的”来衡量,“小说”和“游戏文章”是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戏曲”和“讲唱类”中的“戏文”、“杂剧”、“变文”,“宝卷”等的创作者不是劳苦大众,而是文人、和尚和道士,它们也不为劳苦大众所有。如篇例中的《西游记》、《红楼梦》、《西厢记诸宫调》等,其作者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作家(有的还是著名的),它们是个人创作的产物,是个体意识的反映,完全属于个人所有。其创作和流播媒介是书面文字而不是口头语言,它们大都应列入广义通俗文学之列。上述情形表明,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分类对比其理论阐述来说,无疑存在着扩大化的现象。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又不难发现他把一些构成民间文学主体与精华的神话、传说、童话、生活故事、寓言、笑话、谚语、谜语和歇后语等重要类别忽略了。从其分类体系和所包括的范畴及作品来看,郑振铎是以相当于现代广义的通俗文学的理论来处理俗文学分类及作品的。
(二)选取材料的“非民间文学”倾向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共分14章,选取的材料极其丰富。此书出版后不久,即有读者指出:“这一部著作,起自先秦,下迄清末,从大体上讲,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为平常所不易求的,所以,材料丰富,引证广博。”⑩郑振铎在选用这些材料时,并没有按照他严格意义上的俗文学理论来进行,即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民间文学”范畴,存在着“非民间文学”的倾向,尤其是作为重点评述和介绍的材料,大都是广义的“通俗文学”范畴的。如在“古代歌谣”一章中,他只讲述了《诗经》和《楚辞》中一部分与民歌有关的作品,而对真正属于他俗文学理论范畴的具有更典型意义的作品,如“压弧箕服,实亡周国”(11),“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2)“秦始皇,何强疆,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飨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13)等这样一些表现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作品,却未能提及。又如在评介唐代俗文学时,他并没有很好地去评介劳苦大众所创作的民间诗歌、故事等艺术形式及其作品,而是将评介的重点和取材放在佛曲和变文上,仅“变文”就花了一个章节共90页的篇幅。“变文”是俗讲的本子,就现存的变文来看,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演述佛经故事的,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另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郑振铎在评介时着重讲的是前者,对此推崇之极,赞盛它们“气魄宏伟”“想象丰富”,而对后者介绍甚少。又如在第九章介绍元代散曲时,把《录鬼薄》中所载的作家,以及《阳春白雪》卷首的“古今姓氏”所列入的作家全部划入“俗文学”行列,甚至将宋代苏轼和辛弃疾、元代关汉卿等著名作家写的散曲,也算作俗文学作品之列,更有甚者在介绍汉代俗文学时,竟将刘邦的《大风歌》当作俗文学作品加以介绍。这些显然与他理论中的“大众性”、“集体性”和“口头性”的俗文学特征不尽符合,但与现代广义“通俗文学”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三)评述介绍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一部主要评介劳动人民文学的俗文学史,应当根据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去考察各种文学样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去探讨具体作品所反映了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民间文学发展的轨迹,恰切地反映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在进行史的论述时,只注意考察俗文学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演变的过程,而忽略了促成这种形态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具体作品评述时,只注意到艺术结构、语言风格等表现形式上的批评,而没有深入细致地剖析它深刻的社会意蕴。也就是说郑振铎在评介中国俗文学时,是把文学从社会生活中游离出来加以研究,探讨的只是形式的演变过程和基本特征,而忽略了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如在他讲到中国的讲唱文学时,为我们勾勒了以下发展演变的线索:变文是由印度传入的,“是讲唱文学的祖弥”,“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诸宫调、鼓词、弹词等形式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14)。总之,所有讲唱的形式都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讲唱文学的发展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但不一定事实上都是起源于佛教的。其实,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讲唱文学活动就已萌芽了。《周礼·春官宗伯下》载:“瞽矇掌播鼗、祝、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周初的瞽矇,职掌乐器,这和唱诗有密切关系。《史记·滑稽列传》记有“俳优侏儒”之事,他们以语言滑稽、善为言笑为特征,可见讲唱文学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历史悠久。讲唱文学在唐宋时期的繁荣,除了受佛教文化影响之外,还同当时商业发达,城市生活繁荣,市民阶层产生有密切关系,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生活的制约。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郑振铎实际运用中的俗文学观念与广义的通俗文学概念大体一致。
三、郑振铎“俗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差距的原因及其意义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阐述的关于俗文学特征的理论,实质上是将“俗文学”内缩到了“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实践中对俗文学的处理,又是将“俗文学”外化到“通俗的文学”的领域,同一观念的内缩和外化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产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时代认识的局限。在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人们还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分类。按传统观念,“正统文学”只包括文人诗歌和散文,连小说、戏剧也被排斥在外。作为以反封建贵族的“正统文学”为目的而提出来的“俗文学”观念,它不是由文学体裁划分而提出,而是从文学史的侧面提出的一个包含着多种文学现象的复杂范围的概念。正如郑振铎自己所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范围很广,因为正统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15)将郑振铎的“俗文学”的概念与当时的“白话文学”的概念相比,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胡适说:“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16)“俗文学”是将文学雅俗作比较,针对“正统文学”而提出的,而“白话文学”是从文学的语言形式角度针对“文言文学”提出来的。尽管二者用语不同,所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所含的范围大致相同,其反封建贵族文学的目的完全一致。从这点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郑振铎“俗文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郑振铎无论是在材料还是在观点上都借鉴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其次,研究方法的局限。尽管郑振铎已认识到“俗文学”内容的重要性,但由于受胡适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只注意形式而忽略内容。他在第一章中强调指出:“它们(俗文学)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的许多文人学士的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时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17)但由于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局限,他在对俗文学史和作品的具体研讨时,着重于形式方面的论述。在区别俗文学与非俗文学时,是以形式的大众性、语言的通俗性、流播的广泛性为标准。
其三,占有资料的局限。郑振铎在理论上重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只注意选取和运用书本资料,而忽视了活在劳动人民口头的活资料。郑振铎在1935年9月19日写的《跋山歌》一文中,谈到民间歌谣搜集时说:“当初北大的几位学者们,研究民俗学,搜集各地歌谣的时候,仅知道注重口头上的采集,其后,乃知注意到粤风、白雪遗音、霓裳续谱一类的古歌谣集,现在乃复推广到对于明人歌谣集的注意。这也不能不说是‘进步’”(18)。在其后,他总结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时,也这样说:“将无人注意,野生土长,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长于山野之间的许多大众文艺的著作,特别的指示了出来。给他们以一种新的估测和研究这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时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在做这搜集工作;然而他们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绩,却都烟消云散似的被抛弃了,或被埋藏在破书堆中,竟无人顾问及之。直到了近十余年来,因为民歌搜集的工作发达,方才连类及之,把他们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尘而给以相当的注意和敬意。”(19)“五四”至30年代的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其中一条是着重于对口头活着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另一条则是着重于对古典资料的搜集和研究,郑振铎就是后者的代表之一。尽管郑振铎在1927年就将民歌、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生活故事、笑话等)以及民间剧本等作为中国文学中重点搜集整理的项目(20),但由于古籍中这方面的材料保存得较少而“不易找到”(21),他又不太注意当时所搜集的口头活资料的运用,因此,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生活故事、笑话等重要民间叙事散文作品就成了空白,而那些通俗易懂的通俗书面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书中的主体了。
尽管郑振铎俗文学的理论特征和实践倾向还存在着差距,但在当时文学背景下,作为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这些是难免的。他的“俗文学”口号的提出对整个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俗文学史》打破传统偏见,将一向遭人鄙弃,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各式各样的俗文学作了系统的整理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对于反对封建贵族文学,提高劳动人民文学的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为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其三,他把我国的部分古代民间文学、市民文学和庙堂文学,统称为“俗文学”,并以此代替“民间文学”的概念,从而把变文、宝卷、诸宫调、子弟书、鼓子词、道情、山歌等引入中国民间文学的宝库,扩大了民间文学的范围,恢复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学的地位,对于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由于郑振铎对“俗文学”的积极倡导,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响应者很多,直到如今海内外仍有俗文学学会和有关刊物。因此,郑振铎的“俗文学”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历史的功绩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
注释:
*收稿日期:1994-08-15.
①③④⑥⑨(14)(15)(17)(2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②郑振铎:《大众文学与为大众文学》,《痀偻集》上册,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⑤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⑦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⑧钟敬文:《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集合起来》,转引自《民间文学季刊》1988年第4期。
⑩曾迭:《关于〈中国俗文学史〉之“弹词”部分的讨论》,转引自陈福康《重评〈中国俗文学史〉》,载《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3期。
(11)(12)(13)《周宣王时童谣》;《楚人谣》;《秦始皇时童谣》。
(16)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18)郑振铎:《跋山歌》,载《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9)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同上。
(20)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