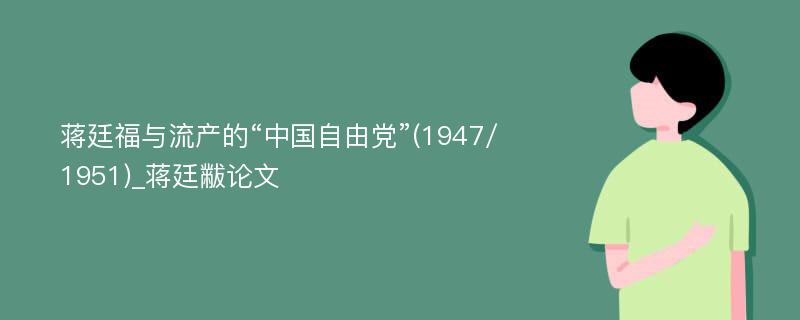
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党论文,中国论文,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3)01-0063-1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云谲波诡,和平建国的曙光转瞬即逝,国共两党随即兵戎相见,力量此消彼长。国家前途变幻莫测之际,各种政治力量与政治人物纵横捭阖,寻求出路。蒋廷黻、胡适等已进入国民党政权体制或与体制保持良好关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既有体制逐渐产生疏离倾向,试图组织新的政党——中国自由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已有学者关注并研究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如张玉龙根据其博士论文拓展成的专著《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有“‘中国自由党’之梦”一节,主要依据顾维钧等人的回忆资料,从蒋廷黻思想发展的脉络出发勾勒出中国自由党的轮廓。闫润鱼的《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主要讨论了胡适与中国自由党的关系。然而,由于中国自由党胎死腹中,知之者不多,资料相当零散,对其研究大多浅尝辄止,尚欠深入[1]。
2000年前后,蒋廷黻后人分批将其资料捐献给哈佛大学,最后全部收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编为“蒋廷黻资料”(Archives of Dr.Tsiang Tingfu),这为研究蒋廷黻及相关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与依据[2]。本文即主要根据这批珍贵资料来研究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的关系,冀能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以贡献于学术界。
一、蒋廷黻的从政经历与理念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最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方面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蒋廷黻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颇为复杂。国民党完成北伐建立统一国民政府后,蒋廷黻起初对其并不完全认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界共同面对的问题。1932年,蒋廷黻参加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开启了与国民党当局合作之门。也是这一年,蒋廷黻在一次北方学人的聚会上,提出办个周刊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5月,《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它凝聚了北方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学人论政的阵地,影响颇大。至1935年底南下从政为止,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支柱作者,先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56篇(包括时论、游记和译著)。他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系统地阐扬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及对时局的看法。张玉龙对蒋的言论有如下归纳:“概言之,即以整个国家的迅速现代化为核心,内政方面,通过新式独裁、革除弊政、武力统一诸途径以建立以南京为中心高效统一的政权,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外交方面,借助国联与国际,以中苏关系为重心的多元外交方略、低调抗日诸项以迂缓日益紧张的中日危机,换取内政建设必需的时间与空间,最终达求制日之目的。”[3]蒋廷黻在那场著名的“民主与独裁”争论中,因主张“新式独裁”而格外引人瞩目。张玉龙评论道:“蒋廷黻的上述构想与主张,既集中地体现出他对民族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思考与关怀,所表现出的强烈工具性政治意向,也彰显出他与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不谋而合的相通之处。”[4]蒋的声名也由此从学术界向社会传播,他自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5]。顾维钧认为,蒋廷黻组织反对党的想法,“早在他参加政府以及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初期就有了”[6]。
1935年底,蒋廷黻应蒋介石之召,以学者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步入政坛。蒋廷黻之入阁,既是他自己寻求“入世”问政的结果,也与蒋介石1932年复出之后有限度地对知识界、工商界开放政权,吸纳人才的策略有关。在1935年改组的行政院各部中,实业部长是精于理财的吴鼎昌,铁道部长是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教育部长是王世杰,行政院的秘书长和政务处长分别是翁文灏和蒋廷黻。在强调“革命伦理”与辈分的国民党政权中,这几位的加入,均是“异类”。蒋廷黻入阁备受瞩目,他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乘机对自己“弃学从政”作公开的解释:“此次投身政治,惟有竭力做事,而不做官,并本科学训练精神处理政务。本人对政治之希望,对内希望一切建设能予人民以实惠,对外希望在保存国家独立主权完整条件下,促进友邦邦交。”[7]
在行政院组织架构中,政务处长实为院长之幕僚,主要负责政策的制订与研讨。蒋廷黻在首度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一年时间,曾试图对中央各部会行政与地方行政进行改革,并建立了“行政效率研究会”,刊行《行政研究》,然而,实际效果远不如其所预期,曾一度萌生去意。1936年底至1938年初,蒋廷黻曾短暂出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5月,蒋廷黻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职,主要负责战时大后方财政预算及地方行政建设等事务。他在此任上有5年时间,因其主要职责是幕僚工作,故很难有显性的业绩。
1943年秋,蒋廷黻奉派到美国,率团出席有关“战后救济”的国际会议。11月,44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不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宣告成立。蒋廷黻当选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常驻华盛顿参与“联总”早期的各种会议与活动,努力争取中国成为“联总”援助预算的最惠国。次年12月,“联总”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建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以协助“联总”在华善后救济工作之展开。蒋廷黻出任“行总”的首任署长,其主要使命是奉国民政府指令办理全国善后救济,同时依据协定,履行中国对“联总”之义务。蒋廷黻等人辛勤工作,致力于中国善后救济计划的制订,并在战后初期全面展开善后救济业务。可惜好景不长,内战全面爆发后,善后救济物资成为国共政争之工具,“行总”工作极不顺利,蒋廷黻也备受质疑,“联总”在华人员指责他,监察院更对其提出弹劾,1946年10月,蒋廷黻被解除了“行总”署长职务。
以上是蒋廷黻1935年至1946年从政的经历,其间,前后两度担任行政院的政务处长近7年,出任驻苏联大使1年,负责善后救济工作2年多。如果要考察其从政的实绩,驻苏大使期间与善后救济署长期间,可说是奉公敬业,恪尽职守,总体上却也乏善可陈,鲜有亮点。政务处长因属幕僚性质,政绩难以显现。如果从这11年间国内局势风云巨变,国民党政权内部人事多次更替,许多权贵上下沉浮,而蒋廷黻能稳坐局中的结果来评判,蒋的从政经历或可谓“稳健”。但如果从其入阁时的抱负,或朋友、时人对其的期望来说,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从更深一层讲,蒋廷黻在入阁后的表现,对于整个政权的性质与结局,未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同为“学者从政”,翁文灏、王世杰等人在国家实际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蒋廷黻更重要些,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些。
二、组党想法的萌生
目前的研究,多指蒋廷黻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想法是在1949年产生的。如张玉龙写道:(1949年6月)“蒋廷黻、胡适与顾维钧诸人又致力于组建‘自由党’的运动”。然而,“蒋廷黻资料”显示,蒋廷黻组党的念头萌生于更早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且与国共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关。
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廷黻参加旁听,其观感并不好:“参加六全大会开幕式,约有600位代表出席,蒋(介石)是唯一的发言者。会场的音响效果很差,布置也太做作不自然。发言者不能唤起与会者的激情,也无法得到积极的回应。在政治操作的民主技巧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8]5月22日,蒋廷黻又写道:
因为六全大会,所有政府部门都暂停办公,虽然留下不少公务要处理,接下来周四要开CEC(“中央经济委员会”——引者)。报纸公布了CEC的新成员,听说蒋(介石)曾提名我,但显然投票时代表们没通过。对“行总”来说,我入选CEC无可无不可,但被提名而投票时遭否决,则挺丢脸。而且,此事也促使我思考自己的政治前程问题。以目前国民党的恶劣情形,其衰落将是灾难。无论是现在,还是从现在往后的十年里,只要国民党当政,我将再不会得到真正重要的职位。扮演友善的批评者角色徒劳无功:民众不可能了解可怕的阴影,政府也将排斥所有的批评。这次党代会我虽未参与,却依然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朋友告诉说是CC系排斥我。我在确定之前,必须先调查清楚[9]。
其对国民党的失望与对个人前途的算计,表露无遗。
几乎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蒋廷黻对延安的动向非常关注,他在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晚,读毛泽东的政纲演讲,从头到尾充满技巧,确实有点佩服,但最后还是有些难以理解。它缺乏对苏联式一党制的反省,对于中国已经在持续一个反苏政策的批评是一种无稽的莫斯科式无根据的回应。毛在演讲中倡导在中国实行混合经济作为过渡,这很引人注目,与我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的演讲不谋而合。
思考创立一个新党,可叫“新自由主义者”(the New Liberals),依靠教授、记者知识阶层、工程师、医师、商人中产阶级等,与新启蒙运动携手并进[10]。
实难想象,蒋廷黻1945年组党念头的萌发,竟与其读毛泽东文章受到刺激有关。蒋日记中所提毛泽东的政纲演讲,应是指《论联合政府》。“蒋廷黻资料”中,保存有一张手稿,写了蒋廷黻对中共“七大”对党章修改的观察。中共“七大”新党章的第一条是“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之党员。”蒋廷黻注意到,此条在未修改前的党章的第二条,原文是:“凡承认共党(应为“产”之笔误——引者)国际及本党之党纲和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重点号为蒋廷黻所加——引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11]这说明,蒋不仅关注中共七大,且对其中一些表述变化背后的政治蕴意也颇费心揣摩。
7月,蒋廷黻因与“联总”接洽业务到美国,他在27日与胡适见面长谈,第一次试探性地询问胡组党的意愿,胡适表示“不愿组建新党,但愿意加入新启蒙运动”[12]。
1946年2月,蒋介石约见蒋廷黻,希望他与社会部合作,并强调说,合作“有益于改善你与党的关系”。蒋介石的意思是,这样一来,CC系会对他“好一些”[13]。然而,蒋廷黻还是在10月被迫辞去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一职。有位朋友告诉蒋廷黻,陈果夫否认与蒋过不去,并请转告蒋不要因去职而灰心,在政界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要蒋“多学些党的原则”[14]。
1947年初,政治上失意的蒋廷黻没有了行政职务,赋闲上海。他在2月著文,提出挽救时局有三剂药方:(一)国民党竭力吸收开明分子,改弦更辙;(二)开明分子团结起来另组社会主义政党;(三)苏联式的共产革命[15]。作为自由主义者又为国民党政权中的一员,“苏联式的共产革命”与蒋的价值理念及政治立场格格不入,也就断难接受。“国民党吸收开明分子”也非他能决定。对他来说,只有开明分子“另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选项有可操作性。于是,组党之事正式被提起。3月,蒋廷黻与胡适等聚会时,胡适表达了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随后他们开始讨论组建新党的问题。蒋记道:
我提出可以称之为新自由党(the New Liberal Party)或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胡适倾向于叫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因为社会主义总是导致极权。张君劢附和。我提出一个党只主张政治民主化,无法因应现在的国家需要,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至于极权主义,我坚持混合经济是可能与必需的。吴国桢(CC Wu)赞同我的看法。最后,我建议中文名字是社会党,既单纯又简洁。胡适重申他是个传统的自由主义分子,傅斯年和我也认为确实如此[16]。
两天后,蒋廷黻为组党事专门给傅斯年写信,内称“胡适将被考虑为(新党)的领袖”[17]。3月19日,蒋廷黻看到报载CC系猛烈抨击宣布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的王世杰,在日记中记道:“在美国,两党会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中国,却是一个党在攻击自己任命的官吏。”[18]对国民党的不满溢于言表。
3月23日,蒋廷黻在报上看到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他的组党设想更进一步:
考虑新党问题。氛围:社会主义渗入民主化的进程。策略:(1)集中于大学和城市,在这些地方首先立足。(2)拒绝加入政府,最多是参与立法团体,在媒体公开讨论。(3)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和国民党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倒行逆施[19]。
如果说,蒋廷黻在1945年5、6月间看到国民党因长期抗战拖累呈现衰败之象而萌生组党念头的话,那1947年初国民党在全面内战尚占上风之时,组党的信念反而更强烈,并付诸行动。据蒋廷黻日记,他有过一连串的行动[20]:
3月24日,蒋尝试着为新社会党(the New Socialist Party)起草一份党纲(party platform),却发现很难精确地将自己所有零碎的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
3月25日,蒋继续写作党纲,“并取得某些进展”。
3月29日,蒋“邀请一群行总的同仁晚餐,谈论新政治党派,总体上是热情高涨”,有人提出,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能使新党“更加吸引人”。
3月31日,蒋完成了党纲草案,并送给胡适“征询意见”。他的兄弟批评党纲草案,说“非常像国民党”。
4月4日,蒋与朋友晚餐时讨论党纲。Chu Chin Lin说他祝福新党,但不会加入,因为他是国民党的终生党员。律师江庸(King Yung)说他会加入,并提议不要加入时下任何的联合政府。Yip说政府运作总是比私人公司更无效率,但却不断提高税率。HC认为关于科学的条款必须重拟,使之更有包容性,Franklin要求我降低超利润率。
4月5日,傅斯年给蒋回信,反对党纲中使用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建议改用“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
4月9日,吴国桢给蒋回复,建议可以先从某种费边社(Fabien Society)开始,而不是建一个政党。蒋廷黻对此建议评论道,这是“胆怯,还是智慧”?事实上,蒋后来也曾有过只做运动不组党的念头。
4月15日,张君劢就党纲问题回复蒋,称“在中国建立某种费边社团将会容易得多”。浦逖生(Dison Poi)的回复亦如是,“他并对党纲提出些了微小的建议”。
4月17日,Elson Wang来谈党纲,对“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充满着激情。他对蒋说,除中共之外,“其他的小党都在背叛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就大打折扣。”
4月27日,罗敦伟(Lo Tung Wei)打电话询问蒋,“能否考虑领导一个新党,江庸与章士钊准备加入,作为实业家,他愿意提供资金”。蒋告诉他,愿意去见他的朋友。
透过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这段时间蒋廷黻有一系列密集的与组党有关的动作:与朋友讨论党名、党纲,考虑党员资格等。他的活动透出了风声,引起了较大的注意,一家晚报披露了蒋廷黻正在组建“中国社会党”(the Chinese Socialist Party)的消息,中央通讯社去电话向蒋求证此事。蒋廷黻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否认这个报道。”[21]显然,他认为公开组党的时机并不成熟。
蒋廷黻对外否认组党,与其个人的处境变化也有关系。4月20日,有朋友访蒋,闲聊中“询及组党的事情”,蒋告诉他说:“我倾向于将事情搁置一段时间”,并谈及自己“可能成为最高经济委员会(Supreme Economic Council)的秘书长”。此前,也有说蒋会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或农业部长的。
虽然暂时搁置组党进程,蒋廷黻内心对组党并不能释怀。5月初,他的乡党、湖南省政府委员萧训打电话,诉说对国民党和政府长久以来的失望,希望听蒋的建议。蒋告诉他,“发展工业将对中国有益,一个新党虽不能满足所有的期望,但能做些事情。”[22]5月30日,有朋友向蒋报告在北平与胡适谈话的情形:胡适等人都很悲观,“不少人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坏”。有人认为当前是“建立政党的机会”,胡适也确信“国家需要一个第三党”,但同时表示,如果新党标榜社会主义,“他不会参加”[23]。
1947年6月,第一届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大会在上海召开,蒋廷黻出任中国代表及大会主席。8月,他与王世杰、顾维钧等被派为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的代表,不久之后,又出任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暂无暇顾及组党之事。
三、组党之事再度被提起[24]
关于蒋廷黻组党活动中止的原因,顾维钧回忆说:他1947年底或1948年初刚到美国,蒋廷黻就向他提起组党事,“一度我们甚至讨论了这个党的纲领和章程,我想他在讨论之后写了草案”。然而,后来国内形势有变,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别处,“这方面的兴趣也就衰退了”[25]。
1948年4月,蒋廷黻曾记与周作民等人的一次关于组党的谈话,内容甚详细:
周作民提起新政党的话题,他建议说,除非大学里的自由主义者全部投入政治,否则形势依然无望。他认为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但蒋不足以创建新政体。我告诉他尽管我已在一年前就请求,但胡适无意担纲一个新政党。周说,如果一切准备好再强迫他黄袍加身,胡适或许同意。我未再继续这个话题,因为不知他究竟对此事有多少诚意,尤其是事涉社会主义。他或许是希望一个扩张资本主义建设的政党。在此方面,我们必须十分细心。我已经为私人资本在贸易与轻工业方面准备了足够的空间,我尚未考虑对私人资本开放运输业、钢铁业、电力与中央银行。他与他的同志会因此而感到满意吗?[26]
以上内容表明,蒋廷黻此时对组党的讨论并不热心,对别人的提议顾左右而言他。
然而,到1948年底,国民党内部分裂,军事连续失利,大势已去。蒋廷黻对国民党更加失望,他在12月中旬与同僚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后,决定“投身到中国自由运动中”,其策略是,“目前先不组建独立政党,既不附属于任何已有的政党,也不公开对共产党之外的任何人提出挑战。要用共产主义在全球的罪恶来教育人民。”[27]其实就是先以较易取得同情的“反共”为号召,先行动起来,再静观变化。蒋廷黻在这年岁末总结的日记中,对国民党表达了绝望:
今年是国民党崩溃悲惨的一年,它沉浮的过程已经有25年。它的兴起缘于民族主义与北洋军阀的腐败,溃败则由于:(1)长期的对日战争;(2)中世纪式的保守主义;(3)在改善人民经济条件方面的失败。后者主要是缺乏远见,长期的内战,这是需要雄心壮志的。蒋(介石)接近成功的统一使日本人与他所有的国内敌人感到恐惧。这个统一并不牢靠,远不像看起来那么真实。这个党在其存在的25年中没有诞生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人了解社会机体的本质。每次都只是将其机械地堆积,而没有尝试从本质上去改变[28]。
对国民党内的主要派系与领导人,蒋廷黻也深不以为然: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CC系都很落伍,他们努力使国家回到孔夫子时代,事实上他们又根本不理解孔子的天才过人之处。CC系取得权力的方法是用共产党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们没有自己的实践与手法。换言之,他们试图建立并垄断性地控制国家的文化生活,结果与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去甚远。
政学系由一群半吊子、老于世故、浅薄和迷恋日本政治生活的人构成,其早期的领导人杨永泰是其中唯一的现实主义者,可惜早逝。
唯一能深刻影响蒋而又受过西方教育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前者的确没有什么能力,而后者是一个在错误时间出生在错误地点的美国大亨[29]。
蒋廷黻对国内已有存在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并不满意。他与青年党领袖曾琦有次长谈,曾琦给他看了一份草稿,上面写了向其美国朋友提出的十个要点,“大部分是批评美国政策的”,蒋认为都是“陈词滥调”[30]。
迈入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国民党败势已不可逆转。4月下旬,解放军渡过长江之时,胡适到达美国,与蒋廷黻见面,两人详商政局与应对之道。胡适对长江防线的溃败很是惊讶,也不认可司徒雷登、孙科等人与联接日本(to hook up with Japan)的企图。蒋廷黻随即旧事重提,力劝胡能在美国积极作为,“并领导个新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胡适则敦促蒋自己来组党[31]。蒋虽认为由他出面独立组党是勉为其难,却也加快了组党的步伐。8月24日,蒋给友人写信,倡议组建自由党(Liberal Party),并对党的一些要件有所描述,如提出自由党的成员来自两方面:无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现有党派中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些人必须抱持如下目标:“(a)国家独立;(b)个人自由,和(c)快速现代化。”新党的目标是“改善(国民的)生活标准”,党的领导机构将由理性的多数来掌权。蒋对胡适说起这些想法,胡均认可说非常好,但他“拒绝当头”[32]。
同一时期,蒋廷黻征询他人的意见,看立法院能否通过自由主义内阁,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蒋介石反对党内的一切改革。蒋廷黻认为:“必须另寻出路。”[33]8月29日,蒋廷黻与胡适讨论组党问题,二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新党发起人名单:
我们开始列出那些可能成为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核心人的名单。我列了胡适、顾孟馀、董冠贤、翁文灏、周诒春、傅斯年、俞大维、陈光甫、郭泰祺、顾少川。胡适加上蒋廷黻、梅贻琦,我们又一起增加了于斌、萧公权、张佛泉[34]。
入选这个名单的,基本上是有相当名望的无党派自由主义分子。
顾维钧9月14日致函蒋廷黻,愿意充当中国自由党的发起人,“赞同草拟的党章”,并提出若干意见[35]。
组党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8月31日,蒋廷黻首次口授起草了中国自由党的党章(the constitution)[36]。之后,他又与胡适等人就党章内容进行详细讨论,广泛接受各种批评建议,蒋廷黻记道:
修改中国自由党的章程,Shushi和Kiang有几处非常重要的建议,一是将民政事务与军事事务区别开来,一是强调教育。与胡适讨论(章程)草案,他最重要的建议是要将自由企业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在这一点上他比我高明。胡适另一个建议是强调教育,特别是自由主义教育,我非常乐意地接受。在组织机构方面,胡建议既可以有个大的执行委员会,也可以是一个大的全国性委员会,再设10-12个人的小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点我接受了。胡适反对雇农给地主缴租式的“封建进贡”,且认为(党章)的词语是言之无物的宣传式。在此点上,我也觉得他是对的[37]。
蒋廷黻在第三次修改稿中,接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之后,陈之迈在翻译自由党党纲时,建议“自由企业”应该成为目标之一。蒋廷黻的解释是,“我们绝对不想把中国自由党变成美国共和党的分支。”并在党章中增加了“工人的福利与安全应是所有公私工厂、矿业、运输业首要的考虑”的内容。陈之迈也反对党员证,认为这是在模仿共产党和国民党。而蒋廷黻则告诉他,党员证是参照了英国工党的实践[38]。
1949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以“中国亟需新自由党”为题,刊出蒋廷黻前一天的谈话,公开了其组党计划。蒋宣称,组建新党是“要在国内国外为中国的独立而奋斗”。新党的目标是:“(1)中国的国家独立;(2)个人自由;(3)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新党将预计由前驻美大使胡适担任首领(logical head)[39]。
蒋廷黻从当年对中央社否认组党事,到在美国公开宣布组党,这是中国自由党筹建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事件。
之后,蒋廷黻着手将该党介绍给国人,请陈之迈将党的组织大纲译成中文。陈之迈用白话翻译了该党纲,不特别讲求言辞,因为他认为如此才更能切合其目的。陈之迈档案中保存了他在译毕后致蒋的英文长信,其中用中文写道:
蒋廷黻在一九四九年秋,鉴于国事之不可救药,有意组织一中国自由党,以期渡此危难的关头。他以一份英文的组织大纲,嘱余译成中文,并询余意见。此一信函即为我的意见,反对社会主义施行于中国。余并以此稿之一份送胡适之先生,盖胡先生公认为此新党当然的领袖也[40]。
1949年12月8日,蒋廷黻刚在联合国内结束了“控苏案”,就听到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的消息,一个时代结束了。当天他满脑子“全是撤退的事”,思考未来,其理想的局面是:自由党在台湾掌权;争取到一年的和平期;赢得岛民支持;美国援助;把台湾建成新的政权中心,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内争与衰落。这时,他考虑的已经比组建政党更进一步,是“自由党在台湾掌权”的问题。他对人说,“中国的关键是一个新的政治领导来提振士气,争取新美援。”[41]蒋廷黻将上述的思考系统化后,写在1950年元旦的日记中:
在黑暗中迎来了1950年。对我们来说,有如下工作:(1)保卫台湾,经济要发展,政治上要赢得当地人的心;(2)在台湾建立一个精悍而有效的政府;(3)等待共产党的衰败与国际形势的变化[42]。
次日,他对来访者谈及未来规划,其中多涉及自由党,他要来者转达给蒋介石。其要点如下:
1、新的自由党将要在新内阁中占主导;2、诸如王世杰、朱家骅及CC系、张群等老党(Older Parties)的领导人仍将留存国民党内;3、自由党必须真正独立,而非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傀儡;4、它的领导人应该是胡适、顾孟馀、童冠贤(Tsung Kuan-hsien)、吴国桢(KC Wu)、俞大维(David Yui)、杭立武(Han Li- Wu)及我本人;5、集中所有力量,促进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只向在大陆的游击队提供少量援助,但要在大陆建立有效的情报网[43]。
1950年元旦,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发行人为胡适)刊出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这等于在台湾公开宣布组党的进程。其介绍词称:“月前蒋廷黻氏在美国招待记者,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这个消息,已引起国人的特别注意。现在,本刊已承在美友人寄到该党党纲草案一份,本想全文刊出,但因篇幅关系,只好刊出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前言》和《宗旨及目标》,以飨读者。”[44]之后,因“各地读者纷纷来信,索取全文”,《自由中国》便在次期中又将全文刊出[45]。雷震致蒋廷黻信中称:“自由中国党章程在本刊发表后,有人询问在台湾的负责机关,以及在美的进展程度,足见社会对此注意。”雷并告诉蒋,《香港时报》也刊出了中国自由党的党纲[46]。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局大变,蒋介石在台湾的地位也渐趋稳定,组建新党的政治空间已经很小。蒋廷黻并未放弃,他于7月中旬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内含“要求新政党的诞生”的请求[47]。直到9月底,他在同台湾来的“财政部长”严家淦(Yen Chia-Kan,minister of finance)长谈时,仍提醒严“注意情势的危险”,说明自己“为何要试着组建一个新党”[48]。
蒋廷黻组党的努力,基本上终止于1951年春他首次返回台湾后。行前,他与胡适午餐,胡适劝他“放弃所有开始一个新党的努力”。胡适说,一个以蒋廷黻为后台的新党,“意味着与蒋和国民党的决裂”。蒋介石已是在阴影中的人物,很容易被打倒,而一旦拉倒蒋,就意味着“将中国交给赤党(Reds)”。胡适并声明,“他和新党的关系已经终结。”他还劝蒋廷黻在台湾多待些时间,可以多了解情况,在台湾时要与蒋经国详谈一次,出言批评时要“谨慎”[49]。
四、组党过程中蒋廷黻与各方的联系
在筹组中国自由党的过程中,蒋廷黻与各方联络,各方的态度影响了组党的进程以至成败。
(一)胡适
蒋廷黻是中国自由党的实际操盘手,但他执意要胡适来做党的领袖。在组党过程中,他始终关注胡适的态度,在所有问题上都征询胡适的意见,并尽量满足。胡适在理念上坚决支持组党,对党章草案多次提出意见[50],但对于自己参与组党实践却常常是退避三舍。故胡与新党的关系,时常是游移与矛盾的。9月8日,蒋廷黻将修订的党章交给胡适,胡表示“愿意做发起者之一”[51]。其后,蒋又专门给胡写备忘录,“讨论中国自由党的角色”。10月15日,胡适同意有条件地出任自由党的全国主席(National Chairman of the Liberal Party)。他的条件有二:(1)当党加入政府之时;(2)当党加入政府时,他出任何职。胡适认为,现在距离此目标尚远,“立即负担起党的责任不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蒋廷黻对胡“能有条件地接受”未来出任党的领袖“非常高兴”[52]。10月22日,蒋把中国自由党党章的最后修订稿交给胡适。
然而,几天后,胡适改变了态度,对蒋廷黻表示,他“对中国自由党很是疑虑”,之前他同意领导党,完全是出于不想让蒋失望的缘故[53]。后来,胡适在电话中对蒋廷黻诉苦说,一份共产党的小报《纽约校园报》(The New York Campus)传播了他的一些流言,使他感觉不佳,几乎令他准备退出自由党。蒋失望地评论道:确信胡又回到了老样子,“这是所有公众人物的通病,他需要更坚定些。”[54]
到1949年12月底,胡适有意疏远中国自由党。他对蒋廷黻说,赞赏蒋的组党目标,但他自己是“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人,终究不适合做领袖。他介入政治,只因自己是个专门的批评家。”他自己“更愿意追求一个教育的运动,而不是政治权力。”希望蒋不要将组党计划与他挂钩,要有他不参与组党运动的计划[55]。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胡适即基本切断了与中国自由党的关系。当天,胡适与蒋廷黻见面长谈,二人对李宗仁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感到担忧,但对未来的设想完全不同,蒋提出应该加快组党步伐,胡适却说,他连领导一个自由协会都不愿意,“更别说是一个自由党了”,无意再介入此类事情[56]。至5月,蒋廷黻认为,台湾人民对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信任,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创造新的希望与信任,需要一个新组织来拯救。当他见到胡适时,胡则大谈自己如何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所关心的是护照与签证的问题,即如何能待在美国。”胡适对他太太得到了美国签证感到高兴。蒋廷黻记道:
我问胡适下列问题:您能重新考虑关于不领导组建自由党的决定吗?他的回答与过去如出一辙:“我是朽木不可雕。”
我很想再问他:“如果其他人来做,您愿意对党提供道义支持吗?”最终没有出口,因为我觉得多问无益[57]。
蒋廷黻十分在乎胡适对组党的态度,长时间将胡适视为未来新党的领袖,寄望甚厚。此时的“多问无益”四字,显示出其内心的无奈与失望。1951年3月,胡适正式向蒋廷黻声明,他与新党的关系已经终结,并劝蒋也停止组党活动。
(二)蒋介石
毫无疑问,正是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失望才燃起了蒋廷黻组党的热情。但蒋廷黻在组党时,没有对国民党与蒋介石隐瞒组党的过程,甚至还“坦荡地”征询过一些国民党内亲蒋人士的意见并寻求支持。
组党期间,蒋廷黻与在美国的宋子文联系密切,两人对时局的看法相近,共同为组建“自由主义内阁”而努力。蒋在与宋子文讨论时局时曾给了他一份自由党的党章,并告诉宋“只有中国出现新的政治领导,才能赢得美国援助”[58]。
1949年10月下旬,蒋廷黻见到了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美龄,向宋美龄通报了组党计划,并希望得到她的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
访问蒋夫人,她认为中国外交犯了两个错误:(1)没有承认佛郎哥;(2)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站在犹太人一边。我告诉她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并对她解释了关于组建自由党的计划,企求她对我们助一臂之力。她没有表态[59]。
尽管在蒋廷黻的意识中,中国自由党并未以推翻国民党为目标,但在一般人看来,一个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的高级官员在其政权行将崩溃之际,大张旗鼓地另组新党,其与蒋介石决裂的意味十分明显。这是个基本的常识,不知为何蒋廷黻似乎从未顾忌到这一点,而当美国记者明确地挑明时,他竟感到“震惊”:
我的朋友、美联社的Frank Carpenter盯着我要进行专访,今天如约进行,专谈中国自由党问题。他的提问让我震惊:这是否意味着与蒋决裂?我还从未以这个角度考虑。我是以宪法为根据——不禁止组织新政党。这给出的答案是新党并不违法,也不可能以此控告我违法[60]。
当然,蒋廷黻也在意国民党对其组党活动的看法,他曾向亲近陈立夫的人士请教如下问题:“CC系会反对自由党的组建吗?”对方称需要时间来征询陈立夫的意见,理由是,“陈立夫肯定不会反对,但对于当下这样一个凋谢的政党,这确是一个问题。”[61]
如前所述,蒋廷黻至少在1950年1月初即明确托人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计划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复职”后的3月6日,蒋廷黻在美国告诉蒋梦麟其组建自由党的计划,说组党是基于两个意图:“(1)蒋介石的光荣引退;(2)较便利地引导(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改变。”他并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将能保留总统职位,但必须遵循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国民党能够作为第二大党参与(执政)联盟”。蒋梦麟答应回台湾后向蒋介石报告[62]。在蒋介石强势“复职”后,蒋廷黻仍坚持组党,明确表示要取代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其设想十分大胆。
1951年4月9日,初次到台湾的蒋廷黻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见面情形记载如下:
王(世杰)和我出发去蒋宅。蒋首先问对日和约问题,称如果没有台湾回归中国的内容,他不会签约。接着他问我对台湾的印象,我高度赞扬了电力行业的工程师们和高雄的工厂,我对军队的称赞很少,要求进一步的改革。最后,我强烈批评了(国民)党和它所称的改造。蒋为改造辩解,并要求我能加入其中。我出门时很气馁,在车上告诉王,我肯定不会就任外交部长。他陪我到宾馆,再三劝我,并说明其难处。我告诉他需要耐心,我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63]。
由此记载可以看出,蒋廷黻虽然对国民党依然不满意,仍不愿与蒋介石有更密切的合作,拒当“外交部长”,但他却未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组织新党的要求,或许是他记起了临行时胡适的劝导,或许是在台湾的实际观察使他确信已经失去了组建新党的时机与空间。
(三)曾琦、李宗仁等人
蒋廷黻在组建中国自由党的过程中与很多人有过联络。除了前文已记述过的胡适、宋子文、宋美龄、蒋梦麟、陈之迈、傅斯年、张君劢、周作民外,他还与曾琦、顾维钧、顾孟余、王世杰、李宗仁等人讨论过组党之事。
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曾琦其时在美国,与蒋廷黻数次见面。1949年10月初,蒋廷黻向曾琦等人详细说明了“关于新自由党的设想”[64]。1950年元旦,两人再次见面,达成如下共识:“国民党已经终结了,蒋(介石)与李(宗仁)也如此。唯一的希望在非政治的力量。”曾琦表示,青年党在四川有可观的实力,“乐意讨论自由党与他的中国青年党之间的合作”[65]。
顾维钧其时任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他对时局的认识及组党理念与蒋廷黻相同,参与了中国自由党的筹组工作,对党章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诸如增加收取党费以作为该党收入以及公布财务和决算报告等。然而,顾不仅为国民党党员,且是中央委员,为此,顾写信给蒋廷黻称,自己愿为拟议中的中国自由党的发起人,且要求蒋把他接受充当该党发起人看作是他放弃国民党党籍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先决条件[66]。
蒋廷黻给王世杰写信,要求他“接受新党”[67]。蒋在给顾孟余的信中,“要求他们承担起在中国组建自由党的责任”[68]。蒋还曾动员“在南美的中国人中发起中国自由党。”[69]
蒋廷黻同李宗仁的关系,可以反映出中国自由党的某些特质。李及桂系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反蒋介石势力,1949年初,桂系势力成功地逼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在蒋廷黻组党过程中,曾有人建议他与李宗仁结盟,蒋断然以“不可能”拒之[70]。12月9日,蒋廷黻与赴美国“治疗”的李宗仁见面,说到中国自由党时,李认为蒋介石恐怕不会认可,表示他能“协助”。蒋廷黻对此“善意”未置可否[71]。之后,在李宗仁与蒋介石激烈的总统职位争斗中,蒋廷黻不屑于李的作为。
(四)美国、英国
美国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的重要因素,蒋廷黻等人筹组中国自由党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甚至可以说,正是受到美国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极其不满的促动,才有蒋廷黻等人的组党行为,参与组党的蒋廷黻、胡适、顾维钧等不仅均在美国,且是与各方关系密切并被美国认可的中国知名人物。在蒋廷黻的日记中,找不到多少涉及美国官方与中国自由党关系的记载,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如蒋廷黻向不少熟悉的美国官员提供了中国自由党党章。蒋曾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普塞讨论过自由党事,并给了他一份党章[72]。据顾维钧所知,蒋廷黻已给杰普塞、司徒雷登和英国的贾德干看过党章草案[73]。胡适等人也与司徒雷登说过组党事。
蒋廷黻在起草中国自由党党章时,对英国工党的宗旨与组织架构均有极大兴趣,也有意模仿。1949年9月中旬,蒋廷黻与其英国朋友谈话后,有如下记载:
见Francis Williams[74],他与Bevin是密友。Francis Williams对新党极有兴趣。我思考知识分子与劳工结盟的问题,故对工党的具体组织结构有极大兴趣。我也告诉他,鉴于英国商人在中国约有十五亿的投资,中国目前危如累卵,在国家的前途不能保证时,商业必然受到危害[75]。
蒋显然是想以商业利益来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但英国人“虽表示同情,却没有任何承诺”[76。
五、尾声
很难断定中国自由党的筹组工作是在哪个精确的时间点结束的,正如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定它开始的时间点一样。如果说大致的时间,则应该是在1951年3月蒋廷黻回台湾前夕,胡适宣布他与新党的关系已经终结,并劝蒋也停止组党努力。这对蒋的影响颇大。此后,蒋的日记中已绝少再有主动组党的记载了。
1951年4月,蒋廷黻记道,《自由中国》编辑在台北见他,谈组建新党的可能性,“他比我兴趣更大”[77]。10月,蒋又记道,有朋友要求他“为结成反对赤党联盟而努力”,组织个新政党[78]。蒋对此均只是记录,而无任何的评论与回应。
筹组“新党”,或是他心中一个挥之不去却难以实现的梦[79]。
在“蒋廷黻资料”中,有两份蒋氏收藏的剪报:一份是4月5日《公论报》,标题是《蒋廷黻斥第三势力,强调中间路线不通,对之尚存幻想乃是错误观念》,另一份是4月5日《中华日报》,标题是《蒋廷黻痛斥“第三势力”,昨在广播电台联谊会演说》。没有年份,但从内容来看,应该是1951年蒋廷黻回台湾时的报纸。两报标题稍异,而内容相同,都是刊登了台湾“中央社”的消息。现摘此剪报一段,作为本文收尾:
“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博士,四日下午三时,在台北各广播电台联谊会招待会上发表演讲,痛斥所谓第三势力。蒋氏认为所谓第三势力,即是又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之中间路线。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般人奢谈中间路线,想以社会主义方式来创造一种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之第三势力,但时至今日,已证明与共产主义者来往无中间道路可走。共产主义对于一切不是共产主义的方法都认为是敌人,都在推翻之列,都要被打倒,根本不容许有中间路线。所谓第三势力者,并不认共产主义苏俄敌为(原文如此,应为“为敌”——引者),但苏俄却视之为敌人。……今日面对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存有幻想,实在是错误的,落伍的观念。蒋氏又谓,渠此次返国后,亲见一般人喜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不胜讶异[80]。
读此段蒋廷黻“痛斥”第三条道路的文字,回顾他那段热情组党的往事,让人不胜感慨:这是蒋廷黻的真实想法,还是他在某种压力下的应景表演?
接下来的事实是:蒋廷黻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体制内,长期担任“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等重要外交职务,直到在美国去世。
(本文承吴翎君教授、张玉法院士提供修改意见,张力教授、刘维开教授、郑会欣教授等提供了部分人名的翻译,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