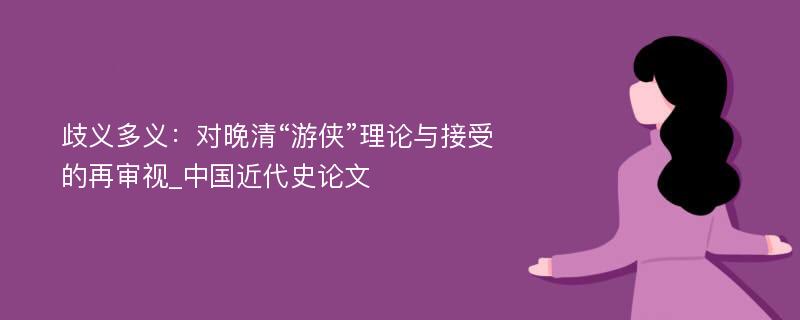
歧义与多义——清末“排满”立论与接受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义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6~0122~13 “排满”是20世纪初中国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因其与辛亥革命联系紧密,又加之“新清史”的推波助澜,研究成果非常多。①相对而言,以往论者多注意“排满”思想的兴起、传播和其对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但至今仍值得再讨论的是,“排满论”一度甚嚣尘上,为何在革命之后消失得如此之快?这当然和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但亦因“排满”是一场理念与事实互相绕缠、真相与幻象彼此交错的“以思想来造社会”的运动。对此不论是赞同“排满”还是否定“排满”之人都有相似的认知。常乃惪即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百日,清朝就终于亡了。这就是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的真力量的表现。”②陈独秀批评排满是“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哪有不失败之理!”③ 辛亥革命是否“失败”自有可讨论之处,但以上所谓文化与思想的“真力量”和感情的“浮动不能固定”说的其实都是排满“似真亦幻”的某一面相,这一特点导致了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中充斥着许多“不可究诘的多义与歧义”,④而这些“不可究诘的歧义与多义”则必须在“夷夏之辨”和“东西洋学理”这两个排满立论的大支柱中做仔细考察。除此之外,本文亦将尝试通过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来讨论排满言论被接受的历史。因此本文将围绕三个主要问题而展开: 第一,作为排满立论发源的“夷夏之辨”,其多重歧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如何产生与嬗变?歧义重重的“夷夏之辨”在清末排满言说的理路中形成了哪些论述上的内在困境? 第二,对于作为排满立论重要资源的“东西洋学理”,时人基于古今、中西、新旧作出的不同解读有哪些?这些解读如何生成了排满立论中的矛盾性与多层次性? 第三,时人阅读反满报刊及明末遗献后,其即时感受和评判的多样性表现在哪里?相较后设的“革命与改良”之争,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该如何描绘? 以下先从排满立论的古老源头“夷夏之辨”谈起。 一 夷夏之辨的歧义 排满立论的两大支柱之一是至少从春秋时代就开始谈的“夷夏之辨”。作为中国传统中极其重要又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夷夏之辨”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产生和嬗变出各种歧义。概要来说夷夏之辨的多重歧义主要有: 第一,从“夷夏之辨”产生的源头看,具有多面混成的特点。谈“夷夏”自然不乏严中国、诸夏与夷狄之防的种族色彩,极端如王夫之会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⑤但另一方面正像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⑥“夷夏之辨”亦以文化为尺度,使得中国、诸夏与夷狄间存在着可转化的开放性,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⑦ “夷夏之辨”多元混成的特点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两宋之时,汉人曾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长时期艰苦地对峙作战,最后不免王朝倾覆、社稷崩塌,不少读书人作为难民和遗民咀嚼着亡国惨痛。在此背景下“夷夏之辨”的文化弹性减弱了许多,很多读书人都非常强调夷夏间的不可沟通与不可转化,蒙文通就指出“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⑧ 不过在“夷夏大防”被强调的同时,宋代的“忠君”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萧启庆认为,“古代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尽忠的义务。两宋时代起,此一相对忠君观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⑨由此当“夷夏之辨”与“绝对忠君观”遭遇时,情形就变得相当复杂,这就出现了“夷夏之辨”的第二个歧义:若王朝为汉人君主,则夷夏与忠君或可得对立统一,王夫之在说“夷夏大防”时,同时在说“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以迁”。⑩若王朝为异族君主,则视乎其实际统治的方式与统治的时间,倘统治日久且不“大失道”则忠君观念一般仍能占据上风。(11)方孝孺就曾很形象地描述过自宋到元“夷夏之辨渐淡”的过程;(12)倾心于民族大义的钱穆亦曾为明初诸臣对于元朝已亡、新朝已兴“茫然不知,漠然无动”,“毋宁以名列元史,归案元儒为得其素怀”的现象困惑过。(13) 相较元朝,清朝既有相似之处——王朝统治者为异族君主,但亦有迥异之别。这种差别形成了“夷夏之辨”的第三个歧义:不同异族王朝造就的夷夏间矛盾之深浅亦不相同,进而会影响此朝与彼朝读书人谈论“夷夏之辨”和普通人接受“夷夏之辨”时史实基础的厚薄。 清朝入关进而统一全国的过程当然血污累累,尸横遍野。但就时间和规模而言,与两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夷夏间结下“经年血仇”的故事尚有区别。而且清廷从立国之初就设立体制令满汉分处,各安其生业。这种满汉分处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或有利于清王朝的整体控制,但对满人个体和家庭而言,因年久生齿日多,饷额却一直固定而弊端丛生,这从清末的满人生计问题就可见一斑;而对汉人而言,因满汉隔离令“上等社会每误于教忠之言,而下等社会则并不知主其国者为何种人”。(14) 更吊诡的是在反满最激烈的时期,满人的整体情况恰是皇室不振、官员式微、民人颓唐。这显然不能与有元一朝“屠杀凶残惨烈,统治昏愚淫暴”,且不能“用夏贵儒”,导致“无地非狄,若将不可复易者”的情形画上等号。(15) 由以上三点出发,清末的排满立论若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推演会在三个层面上遭遇困境: 第一层困境在夷夏之辨的文化性解释上。廖平在光绪二十九年曾针对《新中国》《浙江潮》等诸种持排满立场的刊物,反击说其“丧心狂病,设为迷局,蛊惑少年”,究其根底是“不知《春秋》之义”!按照廖氏的看法,若推及《春秋》,“今之川、湘、江苏皆为夷狄,尧舜以前,中国皆夷狄,今则亚洲皆中国。《春秋》入中国则中国之,将来大统,亦皆为中国”。(16) 梁启超也认为:“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并存,就今日观之,谁能于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别其孰为秦之戎,孰为楚之蛮也?孰为巴之羌,滇之夷也?”(17) 这些认同“夷狄”可转化为“中国”(华夏)的言论均说明“夷夏之辨”的文化尺度在宋以后虽被压抑,却仍是读书人心中认识判别何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尺度。即使是反满人士对清廷欲凭借文化而入“中国”的史实亦无法否认,只不过他们基本是将这些史实矮化乃至丑化为清廷统治的诈术与骗局而已。杨毓麟为论证湖南人的“汉人种性”时就提出: 满洲人知汉种之可以饵也,无端以无足轻重之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粪而壅之,无端以谬为恭敬之孔教,虚加崇奖之朱学藩而垣之,扶而植之,君臣之义,如日中天,而盗据神器,虔刘华夏之穷凶极恶,则遂无人敢目忤而唇反。(18) 第二个困境则在并未完全消逝的“君臣大义”。异族君主入主使得“君臣大义”与“夷夏之辨”间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处于异族羁绊之下,是当主忠君乎?抑当主攘夷乎”?这是一个反满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19)若回诸历史过程,清朝自然是异族入主中国,但从儒家最重要的伦常纲纪而言,其已然君临天下。并且它将疆域拓展至了古之无匹的范围,同时统治时间也足够长久,大大超过元朝,所谓“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20)因此相较于元朝,清代的种族之辨更可能被君臣之义压倒: 自外族迭主中国,而种族之辨遂为君臣之义所消灭。以为君臣之位一定,则无论是何种族,戴之则为顺,逆之则为叛也。雍正间刊《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亦主张是说,故有谓明太祖为元之叛民者。二百年来,释然相忘久矣。(21) 当然“释然相忘”再久,当时代走到了被欧风美雨浸染过的20世纪初,一部分趋新读书人仍是取得了来自泰西的思想资源,以纾解之前一直要面对的“君臣大义”的压力。梁启超等好用的“奴隶根性”一词直接揭示了千余年来君臣间“大经大法”式的自然关系在他们的言论中已渐变为所谓专制统治者与奴隶间的压迫关系。但这套新的思想资源若推其原始,基本与“排满”论和革命党关系不大,而是梁启超等用民权、平等、立宪等来自泰西的学说分离了历来被视为一体的朝廷、皇帝与国家。因此有批驳排满的文章才会说:“所谓排满者,盖游学日本之诸生徒,摭拾康梁唾余!”(22) 不过需要注意,即使如此,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清末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对“君臣大义”有相当的秉持与坚守。1901年《申报》上一篇文章就会理直气壮地说: 我皇上亦满人也,将排满人而并及我皇上乎?则不特食毛践土,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即我祖、我宗亦无一非圣清之赤子,涵濡闿泽历二百数十年。一旦谋叛朝廷,作乱犯上,是蔑祖也,是无君也。(23) 又有像李滋然等作《明夷待访录纠缪》(1909年出版)这类书来批评梁启超和革命党人都特别喜欢引用的黄宗羲“非君”的观点,指出:“目人君为代表,视皇王若雇工逆说也”;臣事君“如人载天,仁暴不易其人”;若“而天下竟无一君,尚复成何世界”。(24)1911年张之洞幕府的重要人物梁鼎芬在家祠中办图书馆,向广州各学堂学生开放,在章程中他仍不忘告诫来看书的生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5)到辛亥革命起,江苏巡抚程德全和其满堂幕僚均借“顺应潮流”之名欲树帜独立时,幕僚成多禄上书痛陈: 公则素以公忠自矢,乃为应道镌级一事,饮恨于心。以一芥之小嫌,失君臣之大体,古之所谓社稷臣者,固宜如是乎?夫人生大节首在君亲,根本既倾,枝叶难附。说者动谓以身救国,保境安民,是何异寡妇改节,而谓藉夫养子者。(26) 这样的劝诫和譬喻已不能仅仅用保守读书人的愚忠与冬烘来解释,它更反映出在一个政治、文化秩序大变动的时代里,对坚持“君臣大义”的读书人而言,或许重点已不在接近消亡的实际君臣关系,而在作为自我期许的人之为人的大节与大义。在清遗民所写的《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自后世种族之说兴,靦颜两姓者得以自遂其趋避之私。学术不昌,四维灭亡,岂知君臣之分,无所逃于天地!”(27)这种借新的价值系统来“自遂其趋避之私”的现象,日后陈寅恪有更深刻的阐发。(28) 第三层困境相较“夷夏之辨”的文化性解释和“君臣大义”的困境更加深刻,由于清代相对缺少夷夏间“经年血仇”和政府残暴统治的历史资源,所以持“排满论”者对清朝历史的构建与不少读书人的历史记忆和实际经历间经常不相凿枘。一般来说排满革命党人可用的历史资源主要可分为五大宗:文字狱和强制汉人辫发胡服两宗基本无太多异议,可是另三宗则因为历史记忆的差异和各种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留下不少可继续讨论的余地。 第一宗是清入关后尤其是平定江南时制造的屠戮惨祸,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都是当时鼓吹“反满”时必然要提到的大惨事,这些历史记忆在道光年间即通过《荆陀逸史》《明季稗史汇编》等丛书的出版而重新被唤起。(29)之后则在清末特殊的救亡图存的时局下震动到一部分趋新的读书人。但那些被震动的新学少年对此实并无太多底气。 首先,这些事件的真伪在他们内部就存在分歧。章士钊即指出,“排满文字,类揭橥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二事,以声讨满洲之罪。邹容尤过甚其词,以张挞伐”,对此(章)太炎曾手录日人永野確所著《读扬州十日记》一文,自为商榷。(30) 其次,反满人士在充分发掘那些明末清初的亡国惨史后,他们发现清朝入关已数百年,遗民也好、志士也罢,往往“姓名湮没,事功废弃,为吾人所不知者,不知其几何人也”。(31)由此新学少年们的“鼓吹革命之言”,经常“多使史迹强附宗旨,偶见为然则然之,见为不然则不然之”,而且“前后不相蒙,还以自攻而不恤”。(32) 第二宗则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时诸多惨杀屠戮的骇人事迹深刻而长久地留在了读书人尤其是江南、湖南等被荼毒甚深地区的读书人的历史记忆之中,从清末到民国的不少材料中都有所提及,而以往研究对此并未加以足够的重视。像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就提到: 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如儿戏,而其掳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其荼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33) 1912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的《中等新论说文范》则说:“洪杨固革命健儿,而恣行屠戮,似相猜忌,实不出盗贼伎俩。爱国英雄,民胞物舆,何必祖述洪杨,反滋吾民疑窦,特揭而出之,足为爱国者作一殷鉴。”(34)到1922年,《奉贤县乡土志》中说洪杨是“清咸丰时候,洪秀全、杨秀清等有兴复汉室的志愿,定都金陵,差遣他们的同党,到奉贤克复县城,守住南桥;但他们的同党都很贪暴,见洪秀全被清兵打败,就到处杀人放火,失了人心,所以不久就衰败了”。(35) 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虽然动用国家力量供奉洪杨为革命先声,顶礼膜拜,但在社会大众的心中,他们的看法好像经常与政府不一致。戏剧史家徐慕云就发现: 盛行全国之《铁公鸡》一剧,原系亡清时代,侮辱革命先进洪秀全、石达开等之武剧。不期于今日革命业经告成时,犹不加以制止或纠正,而一任不学之伶人,肆意唐突先烈。在扮演者固加意描摹清室盛德,向(荣)、张(嘉祥)忠勇,以及铁金翅等之野蛮横暴,行同流寇。即一般低级民众观之,亦无不以捻匪、发匪、长毛诸名称,加于今日革命史上所极端推崇之诸革命先烈之身也。(36) 徐氏的观察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1933年出版的《嘉定乡土志》中仍旧写道:“(太平军)军法不严,兵士没有纪律,沿路焚掠,所以全邑的人民,都纷纷逃到上海去了。”(37) 第三宗则是清朝的实际统治状况。这里形成的一个吊诡情形是,反满人士愈挖掘打捞清廷统治“失道”的诸多事迹,他们可能愈发现清朝皇帝虽为“夷狄”,却并未“大失道”,反而似颇能行“中国”之道。蔡元培在其亲自挑选的学生读本《文变》中不少文章都指向排满,但却仍有“爱新觉罗氏之君临支那已二百余年,虽无深仁厚泽深入民心,然亦不闻绝大之失政焉”这样的文字。(38) 而以“排满”著名的南社中人,革命后惨死于“旧官僚”之手,引来柳亚子为其鸣冤的阮式在其《翰轩丛话》中夸赞康熙说: 当仁皇帝时,入关才几何年,而即孜孜矻矻如此,其勤且精,故其于天地人几无一物不知,所以能牢笼汉族,而奇渥温氏(按忽必烈)决不足以望其项背也,呜呼!其偶然乎!”(39) 这样的言论若与谭嗣同笔下“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的激烈看法相比较,(40)足见有一些排满人士内心深处对清廷统治评断的多歧性。至于尤为人所乐道的“满汉差异”尤其是入仕机会的差异问题,也不乏时人基于其所见之史实而提出的意见,至少可说明满汉差异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巨大。(41) 二 东西洋学理的多义 1906年7月2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先谈自己读蒋氏《东华录》等书后“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又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2)对于太炎谈“东西洋学理”的这段话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43)但笔者仍觉得对于“东西洋学理”之多义的讨论仍似有意犹未尽之处。 一方面对于“东西洋学理”,当时的理解却不只有一个,每个读书人都会因自己所处的中西新旧的位置的不同而有多样、暧昧和游移不定的理解。其突出表现在清末人种新知引入后产生的“如何区分种族”这一问题上。面对“种族”这个硕大无朋、无远弗届的“东西洋学理”,读书人的理解之多义和言说之困难实在非常多。 首先,当时“种族”论的基石性叙述是以白、黄、红、棕、黑等肤色区分人种,进而基于进化之公理以作“种战”。这是清末革命派和非革命派都一致信从的“学理基础”。这里的“多义”在于:黄种究竟包括满人,还是不包括满人?一般来说黄种不包括满人之说笔者尚未见,但如何“包括”满人却形成了三种意见: 一是有些读书人为反击排满,直接以黄种包罩满人,而不言其他。1902年美洲一华侨上书言事就说:“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44)1907年亦有人说“满洲、蒙古、汉人,皆属亚洲黄种”。(45) 二是包括满人,但论述之间表现出要以汉人为中心,建构民族,即梁启超所谓“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46) 三是以往我们较为熟悉的:包括满人,但必须“剖清汉种与满种”。需要注意的是在“剖清汉种与满种”的推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甚吊诡的历史现象:一个现象是做“剖清汉种与满种”工作的不仅仅是持排满论的革命党人,在庚子之前,源远流长的“内中国十八省”意识已隐然将满种与汉种做出了区分,只不过是未用“满种”一词。庚子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清楚地表示过汉种与满种不同。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专门有《人种》一节。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而成,属于“东洋学理”。(47)其中特别指出:“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48) 另一个现象则是究竟谁是“汉种”同类实各说各话,众说纷纭。诸家虽基本都不引“满种”为同道,但不少却能容纳日本等显而易见的“异族”。其包容性之大恐怕都已超出当时日人的想象范围。像桑原骘藏将亚细亚种人判分为两大种:中国人种(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和西伯利亚人种(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古族)。(49)但深受其影响的梁启超对人种的划分却与桑原骘藏大相径庭,《新史学》中表述的黄种三大类中的甲类直接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50) 邹容在《革命军》中将黄种分为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族和土耳其族等,这些大概都是源自桑原骘藏、再转手于梁启超的分类方式。(51)但接下来会发现邹容与桑原骘藏的最大差异在于:日本人、朝鲜人等均被置于中国人种之列。(52) 当然也有不把中日等混为一谈的,像《共进会宣言书》就云:“这世界上的人,种族是不同的,分成黄、白、红、黑各种颜色的种,我们就是黄种。但这黄种中间又分了几样,就是汉种、满种、日本种、朝鲜种等类了。”(53) 其次,有些读书人尽管认同“种族”学理,却跳出了较具有普遍性的“肤色”和“洲界”的分类标准,而另有一套自创的分类标准,刘师培曾说“欧洲人分五洲民族为五种,一为洲界为分,一以肤色为别。此固至确之说”,但他自己又提出另一套分类法即“以世界及肤色区民族可分为五”,但“以性质区民族可分为三”,一是温带民族,二是寒带民族,三是热带民族。汉族为温带民族,“盖世界上最优之民族,文物声明为地球各国冠”。而且“今者寒带、热带之地皆为温带民族所并,其以寒带民族治温带土地者,仅仅满洲治中国,土耳其治东罗马而已”。(54)此外还有以头发为标准来作为分类依据的。(55) 最后,还有一些读书人以无政府主义、汉人西来,苗人原住等另一些“东西洋学理”来衡量品评“种族”这一“东西洋学理”,令“排满”亦或“保满”均在另一套“公理”的考量下失去其意义。刘师培就本着无政府主义学理点评过“排满”的种种不足之处。(56)亦有人在《天义报》上据“汉人西来,苗人原住”的“学理”发文说:“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57) 另一方面,在同一学理的不同表述和理解之外,当时接受的“东西洋学理”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其间孰取孰弃,谁为主要、谁为支流都值得重新考察。前文提到的杨毓麟以反满而著称,但他和刘师培一样也有写给满洲大员端方的密信,其中杨氏对满汉问题的态度极可引起注意。他说:“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终有浑融之一日。”(58)这段话充分揭示了因“东西洋学理”输入,再与中国传统因素相结合后的“排满”论述的复杂性,即他们“是用前人的腔调,穿着古代服装,参加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9) 清末的“排满”自有“满汉分际”(夷夏区隔)甚至“杀尽满人”(灭夷兴夏)的言说理路,其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自不必多言。不过这套论述并非只有种族之一面,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谈满汉分际,常常会与建设新国家、塑造强国民联系在一起,这即是“排满”论述的第二层面——“国家(民)主义”之一面。 1903年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已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60)章士钊则在《读革命军》中提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61)正是在这种“政略之争”的推动和“国民主义”的鼓噪下,四川学生郭沫若会认为“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62)1920年刘文典回忆往事时也说,当时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其实那时候的国势比现在强得多),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63)正是有这些将国家的强大与排满直接关连的想法,所以鲁迅才会说清末的“老新党”们“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64) 再向前推进一步,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心中一分为二,一个对应于国家观念,另一个则对应于“世界”观念,(65)因此所谓“排满”论述的丰富性在种族和国家之外还会有第三个层面——世界主义之一面。 中国传统时代读书人希望能以教化的方式统合天下,而甲午之后尽管屡挫于东西洋列强,但读书人心中却依然不乏统合天下的雄心。1905年有读书人就说:“我不乐闻他国之侵略我,我尤不乐闻他国之保全我。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66)这句话透露的正是“士以天下为己任”心态的延绵不绝。同时读书人亦保持着对世界上其他受东西洋列强欺凌侮辱国家的关注与关切,遂使得排满“尽管带有种族色彩,其最终针对的,主要仍是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67)而中国人引为“同种”的除了菲律宾人、越南人和朝鲜人这样的近邻外,甚至包括了许多遥远的民族,诸如波兰人、南非人、土耳其人、古巴人、印度人和夏威夷人。(68) 不过要应对以“金铁”为凭恃、以“霸蛮”为态度的东西洋列强,要使“天下”仍能成为“自家”,或使天下弱小国家都不再受欺忍辱,在时人看来已基本不可能再通过平和无进攻性的“教化”为方式,而不得不转变为亟亟乎富国强兵来“竞雄称霸”于世界的方式。因此“排满”革命即成富国强兵后“竞雄称霸”世界的步骤之一。同时又基于想象中光明未来所开启的美好愿景,遂使得不少读书人做起了关于日后中国人统合整个世界的“好梦”。 像邹容在《革命军》中就强调中国本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如果没有满洲人的羁缚,“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迸息敛气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而印度、波兰,埃及、土耳其等国,“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69) 刘师培则对“醒后之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做过一番畅想:其版图“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人口接近7亿,“中国人之宗主地球,岂不易哉”!陆军“战必胜,攻必克”,实业“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等等不一而足。(70) 《江苏》杂志中亦有《大阪怀徐福》诗云:“员峤蓬台觅地新,实行政策殖黄民。由来不少哥仑布,兹是神州第一人。”(71) 到辛亥基本功成前后,在报章和时人的日常之作里这类“执牛耳于东亚”,“俯视世界”乃至“称霸全球”式的论述更多。从报章论,南社中人包天笑在给《时报》写评论时虽以“人心思汉,天意灭胡”等“排满”套语开篇,但最后要归结到“看我新民国一跃而为地球第一等国也”。(72)在杭州出版的《汉民日报》发表的“革命祝词”中亦有各类投稿会先说“胡酋强暴诉无门,黑雾满天大地昏。嘉定三屠冤莫白,扬州十日记犹存”等等,不过写到收尾处要么说“举动文明欧美慑,中华民国奠金瓯”,要么是“从此寰球腾美誉,飞扬云起大王风”,足见报章文体已形成从“排满”到“报捷全球”、“声震五洲”论说的模式与套路。(73) 还有时人已不囿于内陆十八省的“走向共和”,而是认为“汉室复兴,方将并蒙古,包新疆,合西藏、青海而建设一共和大国。与美利坚联邦政府相提携于太平洋之上”,因此东三省绝不能让于清廷,因为“白山黑水,衣冠制度,久为我大汉民族之殖民新地”也。(74) 以时人的日常之作论,郭沫若在1912年春节时就写过相当多的联语来歌颂革命,其中一联云:“实行黑铁主义,可保平和;世道尽强权,问欧洲十九世纪之神圣同盟,究有若何成绩在。竟有黄种新书,殊堪快慰;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此联已可说是“豪气干云”。另一联则更为夸张,竟出现“国势未可量也,何难郡县西欧城美澳,统地球员幅,尽入版图”这样的句子。(75)茅盾学堂作文里亦有与郭沫若相似的句子,其洋洋洒洒写到“睡狮既醒,群龙势危,加以土广人众,物美气和,将席卷欧美,雄视全球”,他的阅卷座师则应和批语云“西人闻之,当为破胆”!可谓师生同心,梦想一致,足可见时人心态之一斑。(76) 三 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 在初步梳理了排满立论的歧义与多义之后,笔者将对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实际阅读作一些讨论。这是因为既有研究多注重排满报刊本身,而较为忽视这些报刊和遗献的阅读和接受的情形。王汎森在讨论明末遗献和反满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即使读的是同样的文献,也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77)这一洞见提醒或有必要重新思考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被阅读的复杂性,简单地说以下几点应值得注意: 第一,或许不能从后设的从改良到革命的线性方式来考察排满报刊的阅读和排满言论的接受。在许多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屡屡见到的是:某位读书人先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报刊,然后被革命思潮吸引,向往革命,随即在日常生活中弃读维新报刊,转而改阅《民报》等革命刊物。这些描述不少都应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几乎不存在那么阶段分明、轻易转向的“阅读”。所谓“改良(维新)”与“革命”经常是后设的分野,当时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分界。(78)比较而言,1940年代俞颂华之言或许更接近真实情况,他说:“当时我年幼寡知,思想如同一片白纸,无论革命的理论,维新的主张,脑筋正像吸墨水纸一样,都吸得进去。”(79)这从常熟士人徐兆玮的阅读经历中就可得到印证。 徐兆玮会认为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康党”所为。(80)1905年3月5日他记其读过的报刊,其中既有《时务报》《新新小说》和《国文汇编》,也有《江苏》《浙江潮》与《女子世界》。5月3日则既读《时务报》《绣像小说》,也读《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与《国粹学报》。(81)从他的阅读书目颇可看出所谓“革命”与“维新”报刊阅读的混杂性。(82) 第二,以报刊对阅读者具有的吸引力而论,从各种材料看,清末《新民丛报》等由梁启超所主笔的报刊,其并不少于革命派报刊阅读受众。徐兆玮在1902年说:“梁任公之倡《新民丛报》……我中国之守旧迂谬之儒同声赞美,不胫而走,沪上行销几及万本,村塾僻陋亦置一编。”(83)而据舒新城、李季、吴玉章、周佛海、沈宗瀚等人的回忆,《新民丛报》在湖南、湖北、四川、河南、东北、浙江的小县城和乡间都能读到,且他们阅读的时间点分布非常广泛,从清季末年到民国初年均有。(84)可见徐氏之说近真。 返观革命派报刊,虽有大量研究不断论证其被阅读接受的广泛性,但反例也甚多。以《民报》为个案,在四川小县城里读书的郭沫若即说:“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85)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906年宋教仁曾请日本书商新智社代售《民报》,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内容太激进,甚危险,实不敢代售”。(86) 除了搜集购买的不易,从读后感来看,读者对《民报》文字和思想的接受度不容乐观,同时多样易变。像吴宓就觉得《民报》“沉闷而无趣味”,如《论土地国有》《俱分进化论》等文章,篇幅太长,“读之不解,且厌恶”,只有释卷不读。吴宓以为:“用此报提倡排满、革命,尚不如1904年《中国白话报》上登载的《扬州十日记》和小说《玫瑰花》吸引人。”(87)萨孟武也说:“《新民丛报》文字通俗,影响清末的人的思想甚大。《民报》文字太过古奥,所以影响力不如《新民丛报》。”(88) 钱玄同因为师承章太炎的缘故,他不喜欢初期的《民报》,因为“此为兴中会(孙文所组织者)之机关报,内容不甚佳”,与《江苏》之类在同一水平。但到1906年11月钱氏观感发生了变化,已认为《民报》“较之松江一般词章新党及《江苏》之口头禅,则不可同年而语也”。到1907年3月,他明白说出“《民报》自太炎以来,固大放异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89) 以上不同读者阅读《民报》之感受可稍揭当时读者对革命报刊的感受的多样性。 第三则要注意很多读书人阅读这些报刊和明季遗献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读出了什么?就“为了什么”这个问题而论,“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对搜读明季文献有极大热忱,有些是倒满的支持者,有些则只是跟随时代风潮”。(90)像徐兆玮就是一个“跟随时代风潮”的典型人物。一方面他在其乡以搜集整理明季文献多而闻名,但其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想借此做“书贾”来赚钱的缘故。 1902年12月徐氏就在与友人谈“集股印小说报”的信中说:“《新小说》万难学步,不如取其旧者。明季野史多可喜愕,诚能汇集数十种,杂以新译东西小说及近人所著小说可爱玩者,月出一册,亦足开一新眼界。”又过几日,他继续提出“取明季野史及近人杂记,亦是避熟就生之法,能多觅几种罕见之本,即东瀛文学士亦喜欢也”!到1903年10月徐氏收到合伙友人的信说“图书集成局之《明季稗史》售罄久矣,若即续印,定可广行”。他根据友人提供的市场行情作回函道:“《稗史汇编》极佳,无庸增损。鄙意不如将初编排印,重定续编,取《明季稗史》之佳者编入,亦以十六种为限,定可风行也。”(91) 除了明季遗献外,徐兆玮阅读后世认定的“革命报刊”可能也与其是否认同或参与革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在他看来这些报刊只是应对科举考试的利器。1903年他在读《江苏》时提到:“近时留学生竞出杂志,有《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湖南)、《直说》(直隶)五省。掇其菁华,亦正无几。拟删取要略,嘱儿辈抄阅,以为新学进化捷径。盖繁文不杀,阅之亦颇费日力也。”(92) 以“读出什么”这个问题而论,有学者已发现:咸、同年间的读书人在日记或书信中谈禁书和文字狱时“口气中似乎全无种族情感的激动”。(93)而在庚子后,情况虽和咸、同年间已大不相同,但在部分读书人那里依然有乏匮“种族情感”的延续性。 徐兆玮在知道《革命军》案后曾逆向评论说:“革命军风潮甚巨,但压于外权,章、邹依然逍遥法外。国势积弱,何苦以空言为网罗,徒令竖子成名?邹容仅弱冠,且不必通同,此之刊《革命军》全是小儿脾气;章则怪僻性成,书生造反究竟不成,断不如枭匪之可畏也。”(94) 在温州的张阅读倾向革命的《神州日报》等报纸,知道浙江发生徐锡麟、秋瑾党狱案,虽然他受这些报纸影响,亦认为秋瑾是弱女子,而被清廷枉杀。但他对清廷压制学生造风潮却无太多意见,反而出作文题表示其心中倾向云:“近今仿行西法,废科举,崇学校盖取士之典……然而各省学校屡起风潮,士习远不及古人、外人者,其何故欤?”(95)同时张氏也定期阅读《国粹学报》,但似并未受到明季遗献的激发,读出种族革命的宏愿,反而说:“章氏《诸子学说略》中多抨击孔圣之语,其强悍博辩,咄咄逼人,宜其为革命党魁不见容于祖国也。此君逋逃海外,尚无忌惮,若此设得志于中原,天下大局宁堪设想乎?有心人所以深世道之忧也。”(96) 清末十余年的排满似真亦幻,从其立论依据看总不乏“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之处。章士钊的回忆中就提到过《苏报》向壁虚造“严拿留学生密谕”一事。章太炎为与严复商榷《社会通诠》,则在巨笔文字中听任蒙古、回部分离而不顾,其理据是“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97)而刘师培因要论证日本大和民族与其他蛮族不同,特据《说文》引申云“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同时解释“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时也无惧挑战以往各名家的经典注疏。(98) 以上均是排满立论中“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的一些例证。这种现象一直到民国仍有余绪。邓之诚读《太炎文录续编》时就指出:“太炎自居光复有功,每于清初及洪杨事,多信传闻无稽之辞,如谓曾文正刻《船山遗书》为提倡革命,梅伯言为太平三老无更,皆决无是事,决无是理,其他类此者甚多,不免通人之蔽。”(99) 而从阅读接受看,当时确有相信“今天下教习均不可恃,十分之三为康党,十分之七为孙党”的读书人。(100)但在不少时人眼中此等人不过是“妄人”而已。真正受到遗献及种族思想波动之影响的,或许只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当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接触到大量禁毁文献仍然非常忠于满清。”(101) 不过呈现排满的“似真亦幻”并不是讨论的终点,而可能是一个起点。前文说的是反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幻象”,这里则要对其“似真”的一面做一个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话间的检讨。 1936年钱穆评说章太炎的学术,指出“近年来之学者只知民族主义之可贵,不知其可爱”。(102)这一洞见提醒“排满”就其即时的历史过程看“似真亦幻”,但其折射的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进程异常复杂的情形,其表现在: 一方面“排满”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其“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革命一方借“排满”以立种族,同时亦希望以“排满”来建国,甚至他们将“排满”看作中国屹立世界乃至称霸世界的一个步序。而所谓改良或立宪一方其实与革命一方分享着相当多的共同观念,章士钊就指出“立宪党人之持论,与革命党人仍有其不可畔越之共同点”。(103)在这些共同观念里虽不乏中西交冲,创巨痛深后催逼出的狂想与妄想,但也有现代革命与古老大同理想相结合的希望与希冀,所谓“大革命即大同主义之先声也。夫为一姓而革命,功不及于一国,为一国而革命,功不及于全球,而吾华之革命则异是,有世界之观念者其可忽视此时机也?”(104) 而且从日后的历史进程也可证明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对现代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抗战前夕。胡适在《政治统一的意义》(1934年)一文中就分析道:“在那割裂之中,还能多少保持一个中国大轮廓,这不完全仰仗那些历史的大维系,其中也还有一些新兴的统一势力。”在这些势力中有一点就是通过“报纸与学校里传播出去的一点点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爱国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薄弱的可怜,也居然能使一个地方发生的对外事件震撼全国,使穷乡僻壤的小学生认为国耻、国难”。(105) 不过这种对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强调往往会压抑对民族主义“可爱”之一面的认知。可以发现,在这一个初始以“排满”为名称的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个以“中华民族”命名的集体认同,但1895年后中国人破碎的自我形象和民族自信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反而似有愈滑愈落的趋势,因此另一方面或许要拨开由种族、国家(国民)、世界等问题为“排满”缠上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在“排满”过程中或能发现民族主义之“可爱”的那些因子。而民族主义“可爱”的因子有哪些呢?据钱穆说在于一个国家的语言、风俗和历史,这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以相似的文化来整合民族,以共同的历史来凝聚民族的过程。 但无论是章太炎或是钱穆,他们读中国书的深厚基础虽帮助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可爱”一面的同等重要性,却仍在其根底未扎实的青年时期难挡“东西洋学理”中强分种族思想对其内心的侵蚀。如章太炎在《正仇满论》里就用文字、风俗等因素来强行论证日本与中国亲近,而满洲与中国疏离。这种今日看来至牵强的说法看似在谈历史、析语言、讲风俗,但实则相当无视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语言与风俗。到1930年代,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派凌纯声、商承祖等前往东北调查通古斯族之赫哲。在报告中凌氏等指出“满人男子虽与汉人无异,常人不易分别,然学过人类学的一见即知其为通古斯民族”。(106)凌氏等人的报告当然有其置于现代民族学学术体制内的意义,但报告中的一句“学过人类学的一见即知”恰反证出满与汉之差异对于普通人(未学过人类学)的不易辨别和有限区分。因此如何在今日各个民族(甚至于不是民族的“民族”)已然“大分”,语言、风俗、历史建构似乎不再同一的境况下,重塑庞大中国的文化性认同或是今日一直要去思考的重要问题。抗战期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就已一反早年激烈的排满立场,强调说:“昔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民族!”(107)而厘清“排满”的似真亦幻也许能提供一些能“见中华之大”,然后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基础。 注释: ①择其要者有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24页;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Zhao Gang,“Reinventing China: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odern China,2006,.Vol.32,no.1,pp.1~28. ②常乃惪:《中国文化小史》,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75页。 ③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向导汇刊》第2集,第703页。 ④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26页。 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2页。 ⑥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⑦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2册,第432页。 ⑧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⑨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62~363页。 ⑩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第586页。 (11)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84页。 (12)方孝孺:《后正统论》,《逊志斋集》卷2,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3)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85页。 (14)黄天:《答邓秋枚书》,《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15)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第85、91页。 (16)廖平:《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第八》“襄公二十八年”,六译馆丛书本,第64A、65A、65B页。 (17)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影印本(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页。 (18)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6页。 (19)志攘:《忠君主义及攘夷主义》,《复报》第1号,1906年4月,第53页。 (2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0页 (21)陈垣:《种族之界说》,《陈垣全集》第1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22)《排满党驳议》,《申报》1901年12月28日,第1版。这种将康、梁,尤其是梁启超视为“革命”中人实为时人一较普遍的认知。而《申报》这样说大概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有些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梁氏既像在为革命即将发生而忧心忡忡,同时却又似在为如何起“排满”革命指明道路,非常暧昧。见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影印本(一),第11页。 (23)《排满党驳议》,《申报》1901年12月28日,第1版。 (24)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缪》,孙卫华注解《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0页。 (25)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杨静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香港自印本,1962年,第93页。 (26)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27)张其淦:《元八百遗民诗咏》,周俊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71种,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1页。 (28)陈寅恪:《艳诗及悼亡诗》,《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29)参见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611~612页。 (30)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31)阮式:《翰轩丛话》,周实:《无尽庵遗集》(外一种),朱德慈校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32)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224页。 (33)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6页。 (34)蔡郕编《中等新论说文范》第一册,上海会文堂粹记1912年版,第12b页。 (35)朱醒华、胡家骥编《奉贤县乡土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奉贤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725页。 (36)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37)匡尔济编《嘉定乡土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9页。 (38)深山虎太郎:《培根论》,蔡元培编《文变》,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代印,卷上,第3a页。 (39)阮式:《翰轩丛话》,周实:《无尽庵遗集》(外一种),第277页。 (40)加润国选注《仁学——谭嗣同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41)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221页。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18页。 (4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269页。 (43)可参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李泽厚:《章太炎剖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8~428页;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4)叶恩:《上振贝子书》,《新民丛报》第15号,光绪二十八年8月1日,119页。 (45)《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1页。 (46)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38、39号合期,光绪二十九年8月14日,第33页。 (47)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61页。 (4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夏晓虹、陆胤校《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3页。 (49)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桑原骘藏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页。 (50)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新史学》,第100页。 (51)参见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518页。 (52)邹容:《革命军》,张梅编注《邹容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53)《共进会宣言书》,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54)刘师培:《光汉室丛谈——五州民族之性质》,《历史文献》第1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55)余謇辑:《地理略说》,江西法政学堂讲义,宣统年间铅印本,第11~12页,转引自孙江:《肤色的等级——近代中日教科书里的人种叙述》,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56)《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新世纪》录《天义报》,第22号,1907年11月16日,第4页。 (57)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报》第3期,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16页。 (58)杨仁安(毓麟)致端方,《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郑匡民:《英伦蹈海烈士之真史——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王晓秋主编《辛亥革命与世界: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 (59)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19页。 (60)蔡元培:《释仇满》,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78页。 (61)章士钊:《读革命军》,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84页。 (62)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63)刘文典:《我的思想变迁史》,原载《新中国》1920年第2卷第5号,《东方西方——刘文典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64)鲁迅:《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65)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6)《世界将来大势论》,《南浔通俗报》十六、十七期合册(乙巳年五月望日)。 (67)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68)柯瑞佳(Rebecca E.Karl):《创造亚洲:20世纪初世界中的中国》,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116页。 (69)邹容:《革命军》,张梅编注《邹容集》,第29页。 (70)刘师培:《醒后之中国》,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56、57页。康有为曾作《爱国歌》:“我速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纵横绝五洲兮,看黄龙旗之飞舞!”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刘师培与康有为无论在学术意见和政治立场上都极其对立,但在清末狂想中国如何“竞雄天下”上竟如此相似! (71)佩忍:《大阪怀徐福》,《江苏》第一、二期合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1983年影印本,第350页。 (72)笑:《时评二》,《时报》影印本第46册,1912年2月13日,第307页。 (73)祝词八,《汉民日报》第3号,第1版;祝词十一,《汉民日报》第4号,第1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8页。 (74)云鹏:《论满洲三省不宜让诸清廷》,《汉民日报》第10号,第1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6册,第76页。 (75)郭沫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5页。 (76)《西人有黄祸之说试问其然否》,《茅盾少年时代作文》,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77)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631页。 (78)像《江苏》杂志会刊登《新民丛报》的目录,或许就是一个好例证。见《江苏》第一、二期合册,第405页。 (79)俞颂华:《论梁启超——谈谈我对于他的认识》,《人物杂志》1948年第1卷第1期。 (80)《徐兆玮日记》第1册,1900年12月18日条,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39页。 (81)《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471、483~484页。 (82)章清已注意到此点,他指出“《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交锋看似剑拔弩张,水火难容,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未必如此……更富意味的是,这两份刊物于读者产生的影响,似乎也没有在政治立场上多加区分……思想上激烈对决的双方,在读者那里却全然没有这样的分野。”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8页。 (83)《徐兆玮日记》第一册,1902年9月16日条,第388页。 (84)李季:《我的生平》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74页;舒新城:《我与教育》上册,龙文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5页;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吴恩培编《松石斋日记摘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卫挺生:《读书时代的奋斗》,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沈宗瀚:《克难苦学记》,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8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120~121页。 (86)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4页。 (87)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1页。 (88)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89)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1905年12月18日条,1906年11月24日条,1907年3月10日条,第10、70、89页。 (90)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638页。 (91)《徐兆玮日记》第1册,1902年12月18日、23日,1903年10月10日条,第402、403、445页。 (92)《徐兆玮日记》第1册,1903年7月10日条,第430页。 (93)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611页。 (94)《徐兆玮日记》第一册,1903年8月18日条,第437页。 (95)《张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条,未刊打印稿,温州图书馆藏。 (96)《张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条。 (97)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58页。 (98)刘师培:《攘书》,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1、18页。 (99)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1942年9月27日条,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100)《徐兆玮日记》第1册,1906年7月6日条,第667页。 (101)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640页。 (102)钱穆:《对于章太炎学术的一个看法》,《史学消息》1936年第1卷第3期。 (103)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226~227页。 (104)《中国光复后之世界观》(续),《汉民日报》第64号,第1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6册,第430页。 (105)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106)转见《徐兆玮日记》第5册,1930年6月24日条,第3283页。 (107)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