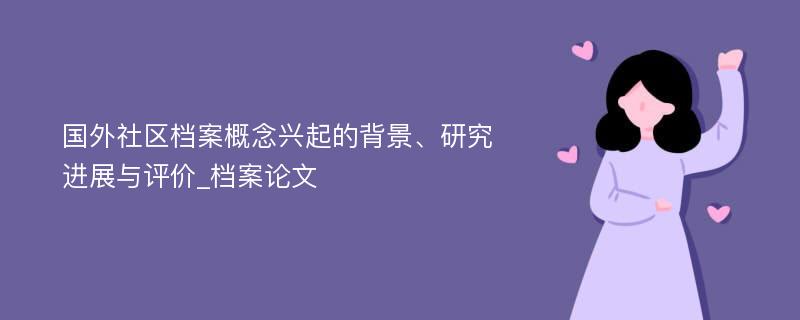
国外社群档案概念的兴起背景、研究进展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社群论文,概念论文,背景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9 2011年库克在中国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档案学科经历的四个范式:证据(evidence)、记忆(memory)、身份(identity)、社群(community),并梳理了不同范式下档案理论和档案实践发生的一些新转变。更多中国学者开始将新范式下衍生的一些术语“档案权力”、“社会参与”、“集体记忆”等应用到档案问题的论述中,但对“社群”这个概念避而不谈。事实上,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并非新兴事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新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出现、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的高速发展以及欧美国家去工业化和移民等因素造成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变化,西方国家呈现出这样一种潮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主流机构叙述的缺失和偏见,渴望拥有自己的历史保管权和发声权,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群档案活动。到了80年代,西方档案学者和文化遗产工作者开始广泛关注和研究社群档案概念及其带来的影响,将社群知识吸纳进档案学研究范畴中,抵制档案专业忽视土著居民视野、边缘化群体的趋势。在社群档案研究中,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从档案角度去概念化“社群”。社会、文化、政治背景是新理论、新概念滋生的温床,也是造成不同国家对概念理解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从西方社群档案概念兴起的背景出发,解读社群档案概念,为今后我国档案研究和专业实践提供思想源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并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档案的属概念,即不能被看做档案的一种,因为它指社群产生的或相关的材料集合,也指西方近年来开展的保护社群档案的项目和实践举措,甚至可以看做一种思想范式。 1 西方社群档案兴起的背景 1.1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权利意识觉醒 1.1.1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博弈 “社群主义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兴起的”[1],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颂扬使得个人主义极度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并在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上达成共识,才形成了社群主义这一新的政治哲学思潮。爱茨尼对社群(community,也译为“共同体”)界定了两种特征:(1)一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群个体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网络;(2)共同体需要有对一套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意义及对一种共享的历史和认同——简言之,即一种共享的文化——的承诺[2]。社群主义者强调社群历史和文化对于共同体身份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只有在社群历史传统或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一个人。社群主义学者提出的积极权利观“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认为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其义务。这些思想观点对后来社群档案理论中关于社群身份和记忆的构建以及社会参与模式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20世纪90年代,社群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不仅局限于政治哲学理论探讨的范畴,更对各个实践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改革实践的参照点。 1.1.2 政治权利运动与边缘性群体诉求 20世纪50到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和解、自由、平等、性开放等成为这个时期思想的潮流,反抗和权利运动成为各种各样的社群争取权益的有效途径,也成为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历史悠久的社群——欧洲国家早期的殖民历史和移民浪潮中形成的原住居民社群或少数族群,从未停止抗争和诉求,土著或族群诉求成为后殖民时代重要的社会议题。一些新型社群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亟须通过权利运动得到社会承认,其中最著名的是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反传统运动等。这些政治权利运动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需要予以保存的历史记录,另一方面使得社群成员和各专业学者意识到社群文化遗产对构建社群身份、争取社群权益的重要意义,因此推动了一系列社群档案馆和文化遗产项目的建立,像建立于1981年的黑人文化档案馆(Black Cultural Archive)致力于“收集、记录和传播居住在英国的非洲和加勒比血统居民的历史和文化”,从而抵制英国主流社会所带来的疏离感和挫败感。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也称“女权运动”)也促进了女权档案馆(The Feminist Archive)的建立。同时,随着同性恋社群的发展以及公众对同性恋身份的认知,1984年成立的the Lesbian Archive and Information Centre和1989年成立的Brighton Our Story,都聚焦同性恋生活和活动的记录。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奇卡诺人档案馆(Chicano Studies Archives)是1960到1970年间的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运动中学生和学者诉求的直接结果,收集奇卡诺社群成员自己认为重要的记录和叙述[3]。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是推进一系列社群档案馆成立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赋予了社群档案“政治性”新的时代意义,使社群档案在当时和未来成为边缘化群体、少数群体形塑历史和争取权益的工具。 1.2 地方历史和历史工作室盛行 20世纪中叶,不管学院派还是外界,他们对历史的关注点都倾向于反映更广泛的历史,如,所谓的地方历史、底层历史和社群历史。这些新问题引发历史工作室运动和各种身份历史运动,要求更多地关注新的材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社群档案直接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社群历史的推进和地方历史项目的开展,这里主要以英国为例加以阐释。二战结束后,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工人教育协会和成人教育课堂的鼓励,地方历史很快在学术领域和非专业草根阶层变得流行和受推崇[4]。而到60、70年代,学者不再局限于以地理位置为身份特征的社群,开始关注工人阶级和劳工社群的历史。1960年,英国劳工历史研究协会成立,致力于支持劳工档案的保存,工人或劳工历史吸引了更多学院派、政治派甚至非专业人士的兴趣,他们收集大量的关于劳工运动和劳工历史的材料,收藏在当地文件机构或者高校档案馆中。 20世纪70到80年代,历史工作室运动(the 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在西方国家繁荣发展,主要目标是推动底层历史、社会历史、日常生活历史或普通公民历史的发展,正如Bill Schwarz所说,“它与主流历史专业的保守主义做抗争,发展根植于英国社会底层社群中的历史知识”[5]。该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地方口述历史项目和历史工作室小组一直致力于记录社群生活,包括即将消失的行业人群、家庭、妇女等一些经常被主流历史所忽略的群体。具体的历史项目例如the Waltham Forest Oral History Workshop,这是伦敦成立时间最久的口述历史项目,鉴定和保存大量的口述历史录音带、照片和文件[6]。受历史工作室运动、口述历史和公民历史发展的影响,加上学院派的热心研究,社群历史发展成熟,档案学家也开始加入历史学家和一些志愿者的行列,去关注那些仍然被排除在历史实践之外的人,不再强调讲述人的身份而是重视讲述内容,并重新思考如何使档案工作实践满足历史学家构建社群历史的需要,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历史研究潮流带来的挑战。 1.3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虚拟社群的形成,它意味着社群不再需要一个实际的会面地点,借助在线的虚拟环境就可按共享的地理位置或身份特征组成虚拟社群,推动社群成员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和数字化项目的开展。另外,随着一系列软件包的开发,像Comma,Community Sites,UK Villages Community Heritage Stores用不同的方式使得社群能够自己建立网站,数字化档案,上载和存储他们的图像,或通过网络、光盘分享他们的档案,大量的地方性历史研究小组或社群档案项目借助这些软件实现了对社群档案材料的线上保管和分享[7]。 1.4 档案教育机会和项目资助机会不断增多 来自于英国一个黑人社群档案馆The George Padmore Institute and Archive的Sarah White表示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思考创建他们自己的档案馆,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相关的档案教育课程,档案世界给人的印象是“几乎封闭的”[8]。社群档案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社群成员或草根阶层发起、组织、操控,很多时候并没有专业档案工作者管理,因此,“被边缘化的社群在保管历史上遇到的重大的障碍时档案专业知识十分匮乏,需要找出档案教育的合适方式,根据当地和土著社群的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专业知识。”[9]许多档案教育论坛和社群档案协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为了弥补主流机构向社会提供档案技能方面的缺失,提供了各种相关的培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和一些在线学习资源。不断增加的资助机会也是社群档案项目大规模兴起的推进因素,充足的资金保障决定了其稳定性和活动的正常开展,The Heritage Lottery Fund是目前英国在社群档案领域最大的资助机构,国家历史出版物和文件委员会、美国人文基金会也在支持美国社群档案活动的开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2 西方对社群档案概念的研究进展 2.1 定义社群档案的困难 在西方,长久以来社群档案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对其下定义是困难的。首先,“社群”与“档案”这两个术语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专业学科对其定义、内涵尚存在一定的争议。这里的“社群”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基于地理位置的社区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而且包括所有基于血缘、背景、文化、情感、兴趣甚至是某种身份的共同体。如,有相同信仰的群体,特殊病患的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移民、流浪汉),共同特殊经历的群体(“9·11”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而这里的档案似乎超越了传统的文件形式,更加包容和颂扬口述、歌唱、舞蹈、手工艺品等传统文化遗产。其次,在不同国家,社群档案举措或社群档案项目虽然都立足于“社群”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两个基本方面,但是其开展形式、所有权、组织构架、合作模式等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难以要求不同国家的不同社群在档案收集上达到某种特征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最后,西方的“Community Archives”起源于多种多样的社群历史举措或社群遗产项目,这些举措或项目可能依附于地方性历史协会或地方博物馆、图书馆,也可能是由对社群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或志愿者发起,导致对其命名的术语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像社群图书馆、地方历史小组、社群遗产中心、口述历史项目、社群记忆项目等。随着“社群档案”概念在文化遗产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越来越多的档案专业人士受到鼓励才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股潮流中[10]。尽管各个国家的社群档案活动存在许多差异,反映着不同的社群文化、目标、动机,尽管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名字,但是这些举措在回应正式文化遗产机构在历史叙述上对社群的排外和边缘化上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大多数社群都被讲述自身历史的渴望所驱动,致力于保存、分享、推动公众了解他们的历史从而寻找身份认同,获得自身权利。随着“community archives”被广泛地用来概括、讨论这些对社群文化遗产进行收集、保护和提供利用的现象,社群档案的概念和定义才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讨论。 2.2 西方学者对社群档案概念的认识 由于翻译问题,不同的学者用来描述社群档案的术语也稍有差异:community archives、community-based archives、community of records、community digital collections、ethnic archive。内涵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然而,对这些概念直接下定义的论述并不多。2007年,从围绕社群档案展开的活动去理解,英国社群档案研究者Andrew Flinn对“community archives”的定义是“记录、记载、探索社群文化遗产的草根活动,且社群对这些项目的参与、控制和所有是必需的”[11],在随后Flinn和其研究团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2009年、2010年),又对“Community Archives”做了一个新的诠释,指“主要由某个特定社群中的成员收集起来的材料集合,从而实现社群成员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们或者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遗产机构,或者接受来自这些机构某种形式的支持”[12]。并认为其本质特征应该是社群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张积极参与到其历史的构建中。该定义一方面将社群档案与地方性的权威机构或政府机构馆藏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社群档案的保管方式或社群档案馆的独立性没有严格的限定,而使其能够包容更广泛的社群档案活动组织形式。虽然前后定义稍有差异,但是都强调了社群成员对自己材料的控制,即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意愿持续参与记录、分享社群历史来实现一定的文件保管权利和历史发声权利。而Jeannette A.Bastian对community of records的定义为社群中的成员或组织在多层次的合作、互动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文件的集合[13]。该定义使得社群档案的概念更接近我们对其最直接的理解。而“ethnic archives”则被理解为记录移民或种族(族群)历史的收藏。显然此概念聚焦的是基于民族、种族、移民等具有明显政治性的社群。英国的The Community Archives and Heritage Group(CAHG)在支持和推动英国社群档案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CAHG采取了“Community Archives”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定义,只要某个组织或项目认为将其馆藏描述为社群档案是合适的,CAHG就会考虑将他们纳入其名单,但是前提是它必须拥有原始档案材料[14]。 2.3 社群档案的具体来源 Flinn在其早期论述中认为社群档案都是“社群中形成、收集或持有的材料”。而根据澳大利亚的土著社群档案项目“Trust and technology:Building archival systems for Indigenous oral memory”总结社群档案的具体来源如下:(1)以故事、民族语言、表演、舞蹈、艺术和歌曲的形式流传的口述记忆;(2)土著居民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材料(文件、家谱、社群活动的记录或人工制品、艺术品等);(3)从正式文化遗产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返还给土著社群的文件的电子版;(4)研究机构或高校保管的土著研究数据;(5)非土著机构或个人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关于土著居民的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关于土著事务管理、医疗、教育、领土方面的文件)、教堂文件、私人文件等。这里的社群知识和档案并没有特指由土著组织或个人形成的文件,也专注非土著机构包括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形成的关于土著社群或个人的文件以及其他土著知识来源。 3 西方“社群档案”概念评析 虽然西方学者对“社群档案”尚未给出一个明确的、一致的定义,我们也不能因为缺乏一个普适性的核心概念而忽视这种新现象。因为一种新范式的产生会改变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会改变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同时也会导致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15]。我们不一定去追随这种范式,而是在对其充分的理解上使其在我国档案理论环境和理论体系中确立起自己的作用方向。长期以来,由于学术规范和学科要求,我们习惯对事物或现象给出定义、设定范畴,造成了凡是不符合这些范畴和定义的事物,均受到排斥和否定。然而定义是为了起一个解释的作用,而不是为了限制和排斥。“社群档案”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概念,绝不能按照中文字面来拆分理解,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并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档案的一种,它包括社群产生的或相关的材料集合,也指西方近年来开展的保护社群文化遗产的项目和实践举措,甚至可以看做一种思想范式。将社群档案看作档案的属概念,或者是等同为体制外档案(家庭档案、健康档案等),甚至与我国传统的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档案概念混淆在一起将会形成文化转译壁垒,使社群档案概念或理论的理解和引入面临障碍。笔者赞成更广泛、更包容地去理解社群档案的内涵,不必太拘泥于定义,而使其呈现的内容更生动、丰富。另一方面,西方理论或概念的引入“必须在其源文化中对其背景和含义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之后,才能确定其在源文化和对象文化中的等价性,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对该理论的概念进行操作化。”[16]如何译释一个外来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融入其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对其充分理解,才能更好地移植和推广到其他文化体系中。社群档案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社群档案现象或社群档案活动,将之运用于对中国档案现实的分析需要考虑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一概念更有效地发挥理解档案现象的功能,并寻找到对档案学科和档案事业的作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