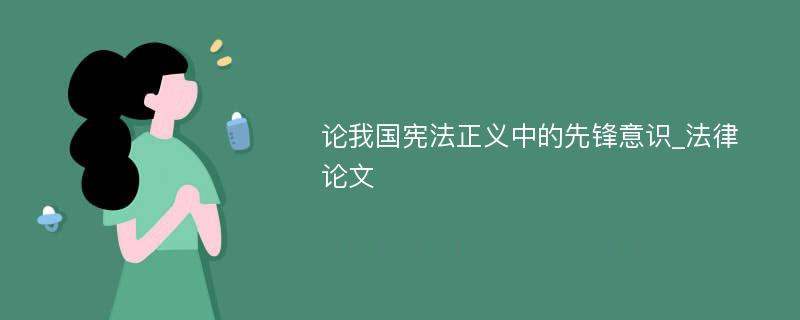
论我国宪法司法中的前卫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宪法论文,司法论文,意识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99(2002)05-0589-05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法律法规全库·司法解释库》及媒 体报道的资料看,10余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人民法院以宪法为依据处理具体案 件的现象,如:杜融诉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工伤赔偿案; 王发英诉刘真及《女子文学》等刊物侵害名誉案[1](第48页);王玉伦、李尔娴诉村民 委员会非法扣留土地转让费案[2](第42页);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 公司和罗友敏工伤赔偿案[3](第172页)。学界聚焦于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宪法规范 在审判中直接适用”[4](第36页);有人称之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5](第78 页);有人称之为“法院判决引用宪法条款”[6](第21页);有人称之为“直接适用宪法 的条文裁判案件”[7](第56页)。学界如此注目于这一现象,是因为其背后蕴含着巨大 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着力结束宪法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 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各种法律法规的‘ 母法’;其次,它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再次,它 标志中国当代的宪政主义从学院主义开始迈入实践主义。笔者认为,从历史的教训、现 实的要求和长远的目标看,宪法的司法适用是维持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发展、推动依法 治国的良好路径。然而,审视这些案例,笔者又为其中表现出的前卫意识深感担忧。
这种宪法司法中的前卫意识,是相对于世界宪政实践和我国当前宪制而言的,或豪迈 地超越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或大胆地偏离我国宪制的原则和规范基础,表现在下述四 个方面。
一、启动机制的前卫:公民个人提起
让我们从这些案例中权利争议的主体来开始分析。争议的一方——诉讼提起人,如: 杜融、张连起、张国莉、王发英、王玉伦、李尔娴、刘明、钱某、齐某,全部是公民个 人,这就是说,我国的宪法诉讼,全部是由普通的公民个人来启动的。
纵览当前世界各国宪法司法的启动机制,能提起宪法诉讼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如 国家元首、中央政府、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一定数量的成员、总检察长、宪法法院、普 通法院以及声称法律侵犯了宪法所赋予其权限的地方国家机构。由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 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可以由普通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来予以保护, 因此,大多数国家排除了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可能性。直到二战以后,少数国家建 立了宪法诉愿制度,才从理论上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但无不对此进行了极其严 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其他司法救济手段必须穷尽,如《西班牙 宪法法院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三项、《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第九十三条 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在诉诸于所有的司法救济途径后,仍 然不能得以解决时,才能够向宪法法院提起。其二是可以提起宪法诉讼的诉由非常狭窄 ,只有两种:一种是公民个人认为法律侵犯了他们所享有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如《西班牙宪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六十二条 第一款第二项,《奥地利宪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九十三条 第一款,匈牙利1989年《关于宪法法院的法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款;另一种是 个人的权利由于法律致使行政机构或司法机构的行为产生侵权,只有西班牙、葡萄牙、 奥地利、瑞士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的公民才享有提起这种宪法诉讼的权利。由于公民个 人提起宪法诉愿往往会导致滥诉,造成受案法院负担过重,因而实行此制的国家对之慎 而又慎。
再回头来看我国的宪法诉讼,公民个人不但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而且既不受穷尽其他 司法救济手段原则的限制,又不受起诉事由方面的限制,可以说,我国公民个人在提起 宪法诉讼方面,享有了比世界上所有国家公民都多的特权;我国宪法诉讼的启动机制, 已走到了世界的最前之列,这在我们下车伊始、经验浅薄之际,后果堪忧。特别地,当 将这些宪法诉讼提起人,与诉讼另一方联系起来分析,我们会确信这不是杞人忧天。
二、受案范围的前卫:聚焦私人领域
争议的另一方都是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者,如侵犯了人格尊严权、受教育权、劳动者 获得劳动保护的权利、妇女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等,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如纯 私法意义上的公民张学珍、罗友敏、刘真、陈某及其父亲,半私法意义上的(刑事自诉 案件中的被告人)公民沈崖夫、牟春霖;一类是私法意义上的法人,如铁道部第二十工 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屈臣氏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女子文学》等刊物、齐某中学 母校;一类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中的组织,如村民委员会。这三类侵犯公民基本权 利者,除王玉伦、李尔娴案中的村民委员会外,其余全部是私法上的公民和法人。因此 ,我们可以结论:中国已出现的宪法诉讼,竟有85%以上发生在纯粹的私人与私人之间 。这实在是宪法司法史上的崭新景观。
从宪法产生的缘起和立宪最初的目的考察,“权利的保障书”。但是,宪法保障的权 利,其实是一种公民在与国家权力关系上的自由权利,因此,宪法权利规范的效力,主 要限于个人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权力内部之间的关系,而不及于私人之间的关 系领域。对此,K·罗文斯坦总结道:“基本法不得不对个人自律的领域、即个人的诸 权利与基本自由作出明示的确认,同时也不得不针对某个特定的权力持有者和整体的权 力持有者可能施行的侵犯而对此领域作出保护性的规定。这一原理曾在立宪主义展开过 程的初期就已得到认识,乃因其表达出了立宪主义所蕴含的那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目的。 与权力的分割和限制的原则相对应,一般的政治权力所不能侵入的这个领域,正是实质 宪法的核心。”[8](第164页)这种西方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亦可从宪法作为公法的性 质中得到力证:罗文斯坦流所言的这种“个人自律的领域”和“一般的政治权力所不能 侵入的领域”,实际上也就是留待私法自行去调整的空间,国家权力不能涉足,也无能 涉足,由此形成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并立与平衡,这种观念的结果,即产生了宪法权 利规范对纯私人之间领域的无效力说。
正因为如此,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坚持宪法权利乃系针对国家权力这一命题,将 那些基于纯粹私人行为所构成的宪法权利侵害排除在宪法诉讼的范围之外,惟一有些特 殊的是美国。根据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美国法院出现了一种 “国家类似说”理论,主张将侵害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特定的私人行为,视同侵犯人权的 政府行为,从而适用宪法的规定,这些特定的私人行为主要有两类:一是在接受了州和 联邦政府租借公共设施等国有财产、财政、免税措施等方面的援助,或从州和联邦政府 中取得某种特权的情形下所实施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二是实施了该私人行为的主体是高 度的行使公共职能,即纯粹地或排他性地行使某种统治行为的团体[9](第314页)。可见 ,美国的这种“国家类似说”,仍然是建立在宪法权利规范对私人之间领域的无效力性 这一前提之上的。
的确,宪法对权利的保障,在规范的延伸意义上内在的蕴含了同时排除私人之间侵权 行为的规范内涵,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主要是为普通法律在私人之间关系上保障宪法权 利提供了依据和要求,宪法本身的重点应落脚于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之上。从 逻辑上推论,私人之间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一般是特定的、个别的,影响范围窄,社会 危害性小,而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些微侵犯,却可能一般化、普遍化,影响范围广 ,社会危害性大。如果像中国现有的“宪法司法”那样,无视“宪法权利规范对私人之 间领域的无效力”这一命题,将宪法权利规范所调整的范围无限泛化,欲彻底解决公民 基本权利保障中的所有问题,那么,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把握立宪的精义,在实践上必然 要走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局。
三、适用方式的前卫:普通法律式适用
中国的这些宪法判例,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甚至刑事诉讼这些普通司法程序中 作出的。一种形式是直接引用宪法条款来裁判案件。如在杜融诉沈崖夫、牟春霖案中, 针对沈、牟二位上诉人要求保护新闻记者合法权益的诉求,二审法院引用宪法第三十八 条和第五十一条,界定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和权利的含义来反驳诉求,判定上诉人构成诽 谤;在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案、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及罗 友敏案中,涉案法院引用宪法第四十二条,支持原告的工伤损害赔偿要求。另一种是采 用引用宪法原则、规范的形式,如在王玉伦、李尔娴诉村民委员会案中,四川新津县人 民法院认为:蔬菜村的村规民约,要求妇女结婚后必须迁走户口,是对妇女的歧视性对 待,有违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因此无效;在齐某诉陈某等侵权案中,涉案法院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2001年8月13日《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 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陈某等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王发英诉《女子文学》等四家刊物案、 钱某诉屈臣氏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案中,涉案法院认为被告行为违背了宪法的有关规定 。这两种引用形式的共同点是:涉案人民法院像适用普通法律那样,将宪法作为了判决 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案件的直接依据。
目前,学界很多人认为,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 须的。他们从宪法的法律性出发,强烈要求宪法“亲政”;从宪法具有自身的实体内容 出发,强调宪法的“可诉性”;从一般法律存在着空白和缺漏出发,冀望宪法“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的大能。这种观点目前声浪甚大,对司法实践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 笔者看来,他们大都没有将在民事、行政、刑事这些普通程序中适用宪法,与在违宪审 查程序中适用宪法区别开来,而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违宪审查程序中直接适用宪法的 理论和通例,来论证宪法应作为法院在普通程序中判案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混为一 谈”的表现。笔者不是想加入宪法能否作为法院判案依据的学理讨论,笔者想强调的是 ,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着两条途径,一条是学界大力推崇、并已成为司法实践的“普通 法律式适用”,一条是“违宪审查式的适用”,这两条途径都能导致宪法作为法院判案 的直接依据,从而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结果是有巨大差别的。笔者要讨论的仅是这种 结果的差别。
宪法在普通司法程序中引用,第一,极容易导致宪法的降格;第二,极容易导致“法 院造法”,因为中国宪法较为抽象、原则,特别是中国宪法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章程化 、纲领化、政策化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司法程序中引用宪法审查案件,具有巨大 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质上是以法院的司法功能取代了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因为这两个 极易导致的结果,当我们使用宪法司法化的这种途径时,必须小心翼翼。
其实,在世界宪法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国家是在违宪审查程序中适用宪法,到1993 年,世界上建立了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制度的104个国家中,像适用普通 法律那样适用宪法的国家极少。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宪法可由法院直接适用,但大多限于 宪法权利条款。如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 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1979年《孟加拉国宪法》第 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法院可直接适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1982年《葡萄牙宪法》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1993年《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在俄罗斯全境具有最高法律 效力,直接作用并适用。”考虑到这些国家大多建立了宪法法院,这种直接适用宪法的 法院可能并非全是普通法院。而且,他们还尽量避免直接适用,一是严格区分宪法诉讼 与非宪法诉讼,防止司宪权的滥用;二是坚守“穷尽其他救济办法”[10](第205页)的 原则,即使当部门法缺乏具体规定时,亦要尽量通过解释部门法的一般条款和具有概括 性的规定,或法言法语,将宪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避免使用宪法诉 讼这一救济手段。德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宪法的典型。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在1958年的“吕特事件案”判决中指出:基本权利的内容可以私法规定为媒介“切入 ”,像《民法》第826条有关善良风俗这种一般条款,即是很好的“切入口。”日本大 阪地方法院在1969年的“日中旅行社案”中判决:《民法》第90条的公序良俗条款体现 了宪法中的平等权规范的精神,被告日中旅行社以政治观点取舍雇员,其对原告人所作 出的解雇决定违反了《民法》第90条,因而无效。
对照这种司法中消极地适用宪法的“国际通例”,我国像适用普通法律那样来大胆适 用宪法,大有赶超德、日,甩掉英、美,将所有宪法适用的老牌国家抛在身后之势。这 种前卫气概确实该收敛收敛。
四、适用效力的前卫:最终决定效力
在已有的宪法判例中,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最终决定力:一如民事、刑事、行政案的 判决,两审终审,立刻生效。这远远超越了我国现行宪制。
这些人民法院宪法判例实际上是在“于法无据”的“非法状态”中作出的。由于我国 宪法已将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之权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在第126条中规 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此处的“法律”因是狭义的,不包括 宪法;在规定由人民法院的任务时,采用列举式:“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特定的 行政案件”不包括宪法案件。从宪法规定来看,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不适用宪法,是 确凿无疑的。
这种行为必将导致了与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直接冲突:我国宪法实质上是基于人民拥 有绝对立法主权的理论,而不是用根本法限制人民立法主权的理论;我国宪法目前的司 法适用,其趋势是走向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而违宪审查制度的理论前提,认为人民 的立法主权不是绝对的,而应该受约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11](第32页)。
宪法的司法适用的确重要,但以与现行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巨大冲突为代价,来引入这 一制度,恐怕又是一种“良性违宪”。宪法是否该进行“温柔地抵抗”呢?
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法治之路后出现的,特别是在“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后才少成气候,个中缘由是: 宪法是法治的载体、法治的保障,是法治制度设计的体现,法治首先表现为宪治,依法 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因此“宪法至上”成为“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然而,“宪法 至上”需要宪法的司法适用,“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 折扣”,“没有宪法适用,宪法的规范性便无从谈起,甚至宪法的存在价值也有必要从 法律的范畴划入道德的领域。”[12](第29页)因此故,宪法司法适用现象才得以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只有以保障宪法的至上性为己任,并以此服务于 依法治国的长远目标,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后劲。以违宪的方式来适用宪法,无 视世界各国已有的宝贵经验,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不但不能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不能 助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且潜藏着断送宪法司法前景的危险。
收稿日期:2002-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