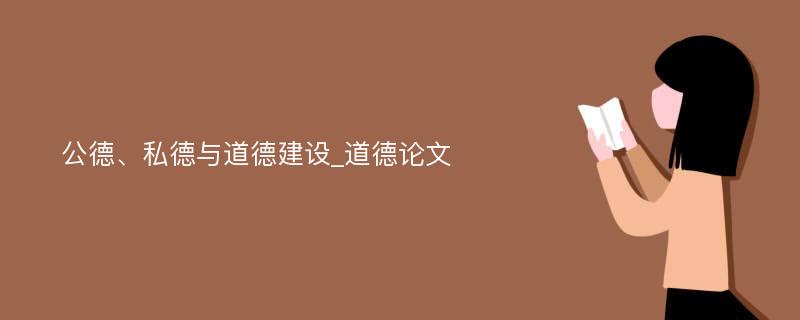
公德、私德与道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德论文,公德论文,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于社会公德给予充分的重视,其中谈到:“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公德是相对于私德而言的,要搞好社会公德的建设,首先有必要弄清公德与私德这两个范畴的界定及其关系。
一、公德与私德之区分
公德(public morality)和私德(private morality)这两个术语以及类似的术语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文献中时有出现,不过其用法尚有一定的歧义性。(注:比较集中讨论公德与私德问题的论著当推英国道德哲学家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主编的论文集: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笔者对汉普希尔的有关理论的评论见拙作《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在我国首先凸显这两个术语并借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设两节专门讨论公德与私德。(注:梁启超《新民说》的《论公德》一节写于1902年,《论私德》一节写于1903年,均载于《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这两文写作时间相隔一年,所述观点有所差异。具体分析这些差异以及对公德与私德作出更为恰当的界定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涉及梁启超在《论公德》中所表述的观点。)从一种意义上讲,公德与私德的关系类似于法律中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注:《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2页。)我们知道,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始于古罗马法学家,这种划分在西方法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不过划分公法和私法的依据却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公法,如宪法、刑法等;凡是以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私法,如民法、商法等。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法学和伦理学的长足发展,公德与私德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在西方首先明确地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19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密尔紧随其后。(注:参见J.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ed.J.H.Burns and H.L.A.Hart,London,1970,Ⅹ Ⅶ,3-4.在此,边沁用了“Private ethics”(“私人伦理”)这个词,定义为“the art of self-government”;与之对立的是“the art of government”,他在其他地方称之为“public ethics”(“公共伦理”)。密尔提到“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并强调二者之区分。(参见《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2页))梁启超正是从边沁和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发现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并加以引申和发挥。他这样定义这两个概念: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注:《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2页。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关于公德与私德的定义是比较粗糙的。拙作《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对公德与私德的定义给予进一步的讨论。)梁启超将中国旧伦理与当时的西方伦理即“泰西新伦理”作了如下的比较:
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团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注:《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2-13页。)
在这里,梁启超指出中西方伦理学之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中国伦理是重私德而轻公德,亦即重家庭伦理而轻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而西方伦理则比较完整,相比之下,更看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亦即公德重于私德。为此,梁启超向国人大声呼唤善群利国的新道德,而把惟善家庭的理即由是生焉。(注:《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第15-16页。)笔者以为,梁启超对中国旧伦理的批评基本上是打中要害的。
中国旧伦理还常常谈及“事父”与“事君”的关系。尽管事君在中国旧伦理中已被私人化,但比起事父来毕竟更接近国家伦理。因此,从中国旧伦理对事父和事君之关系的处理上,也可看出其重私德而轻公德的特征。如,《论语·子路》云: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子。”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楚国叶县长官,向孔子夸耀他的乡党有个人,因其父偷羊而出面作证,是为人正直的模范。隐瞒其父偷羊以孝长辈,是事父的问题;证明其父偷羊以利国法,是事君的问题;这件事包含着事父与事君的矛盾。孔子驳斥叶公说,在偷羊的事情上,父子相互隐瞒才是正直。由此可见,在公德与私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是以私德为重的。
在事父与事君的关系上,孟子与孔子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孟子·尽心上》云: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瞍瞽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的弟子桃应向他提出一个假设的难题即:如果舜的父亲瞍瞽杀了人该怎么办?孟子一方面认为舜应当让法官皋陶把他父亲抓起来,另一方面又主张舜应当帮他父亲越狱潜逃,逃到海边安享天伦之乐,为此他可以将国家像破鞋一样丢掉。我们看到,在重私德而轻公德上,孟子比起孔子来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要包庇的已不是父亲偷羊的小罪,而是性命关天的大罪。(注:关于类似的问题,涂又光先生在其《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和批判。)
孔子和孟子关于事父和事君的讨论虽说不能完全反映当今中国人的看法,但他们所表现出的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态度,对于当今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仍然潜在地甚至直接地发生着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婚外情事件为例,看一下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一般伦理态度有何不同。(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1页。)
我们看到,美国人是把家庭伦理置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之下的;具体地说,对于克林顿在家庭伦理上的不良表现和在国家伦理上的良好表现,美国人赋予后者以更大的权重,以致最终对克林顿给予原谅。对于美国人的这种伦理态度,若从中国旧伦理来看便会感到大惑不解。人们会想:万恶淫为首,像克林顿这样一个淫荡的人怎么能当好总统呢?为什么不赶他下台呢?进而认为:美国人尽是些浅薄之辈,只重经济,不重德性;只看钱,不看人。按照中国旧伦理,人之所以为人者就在于人有忠孝之良知;如果一个人缺乏忠孝之良知,那么,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做总统的资格?这话听起来似有道理,但需要进一步推敲。
中国旧伦理的一个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人是有可能成为道德上的完人的。中国旧伦理的全部目的就是教人做完人做圣人,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由于欲求圣人为王,所以主张社会以人治、德治、礼治,而排斥法治。与此不同,西方近代法学和与之相应的伦理学是以自利的个人为出发点的。以梁启超颇为欣赏的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为例,它从自利的个人出发,却得出人应当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否则自利的个人之间将发生冲突,结果是俱败俱伤。法律就是体现这一伦理原则的社会契约。遵守社会契约以维护公众利益,同时坚持个人之独立自由以维护私人利益,这两种看似相反的伦理倾向却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近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主要内容。由于西方的法学和伦理学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个人,所以它一方面确立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它对任何人都不抱有过高的期望,都使之处于法律和舆论的监督之下。既然国家元首也是一个自利的个人,而不是圣人或完人,那么他犯一些错误并且受到舆论批评或法律审判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甚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愈高,其受民意监督的程度就愈高,因而他的隐私权就愈小。
与此不同,由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事情常常是相反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愈高,其受民意监督的程度就愈低,因而他的隐私权就愈大。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以德治国的必然结果。因为:要使老百姓都具备完美的道德,就不必让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既然认定作为社会精英的上层官员具有更好的道德,那就不必对他们进行监督。然而,人性中毕竟有自私的一面,在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难免恶性膨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官僚腐败风气屡禁不止的制度性原因,对它的医治主要地不应强调德治,而应强调法治。
诚然,道德建设对于法制建设具有辅助的作用,但是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辅助作用是如何发生的;这就需要对公德和私德加以区分,因为公德是介于私德与法律之间的,它在法规他律和道德自律之间提供了一种过渡。
二、道德准则的排序
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并非只有一条,而是有许多条,如“不要说谎”和“要减少他人痛苦”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不同的道德准则是并行不悖和相辅相成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之间会发生冲突。例如,当你面对一个患有绝症的病人,是否把真实病情告诉他就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道德问题。若按照“不要说谎”的准则,你应当告诉他真实的病情;但若按照“要减少他人痛苦”的准则,你不应告诉他真实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作出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就必须对不同的道德准则进行排序,即按照公德性程度的强弱进行排序。
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契约。一般而言,一个道德准则与社会契约的关系愈近,其公德性程度愈高(私德性程度愈低),反之,一个道德准则与社会契约的关系愈远,其公德性程度愈低(私德性程度愈高)。这使得,道德准则的公德性或私德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同一个道德准则有时被看作公德性的,而有时被看作私德性的,这取决于它所相对的其他道德准则是什么。例如,“要信守诺言”相对于“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是私德性的准则,因为前者与后者相比,离社会契约较远,既然后者本身是社会契约即法律的一部分。然而,“要信守诺言”相对于“要谦虚谨慎”则属于公德性的准则,因为前者相对后者离社会契约较近,既然前者关系到社会契约能否得到正常履行的问题,而后者则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这一区分公德性准则和私德性准则的方法叫做“契约论方法”。由契约论方法可以派生出另一个标准,即:公德性准则具有较强的义务性,而私德性准则具有较弱的义务性,或者说是超义务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德产生于社会契约之后。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大致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先理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1页。)休谟在这里所说的正义和非义、权利和义务都属于公德的范围。
既然公德产生于社会契约之后,那么,制定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公德体系所必须满足的基本道德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们看作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或者说是对康德绝对命令的一种新的解释。即:(a)每一个缔约者都是自由平等的;用康德的话说,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就是康德的“人权原则”。(b)每一个缔约者都必须期望社会契约得到普遍遵守;用康德的话说,一个人必须按照他同时期望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就是康德的“普遍律原则”。(c)每一个缔约者都必须自觉地用社会契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致使社会契约成为自己的意志;这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意志自律原则”。当然,这种“绝对命令”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而是相对的绝对,即相对于社会契约来说是绝对的,是契约社会的最基本的公德准则。相对于它们,其他道德准则的公德性要弱一些。
当一个人面临道德冲突的时候,他首先应当把所涉及到的彼此冲突的道德准则列举出来,比较它们的公德性程度,然后按照公德性较强的那个道德准则去行动。例如,你的朋友在走私活动中遇到困难,请求你给予帮助。按照“要帮助朋友”的道德准则,你应当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按照“不要走私”的道德准则,你不应当满足他的要求。面对这一道德冲突,你就要对“要帮助朋友”和“不要走私”这两个道德准则的公德性程度进行比较。显然,“不要走私”的公德性更强,因为它本身属于基本社会契约即法律的内容。于是,正确的道德选择就是拒绝你的那位朋友的请求。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道德体系应当以公德为主而以私德为辅。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私德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因为,一个签约者对自己的利益或幸福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背景知识和私德;这就是说,按照民主原则确立的社会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私德是怎样的。这样,公德和私德就成为相互依赖的了,这就是道德哲学的复杂性之所在。公德是以社会契约为轴心的,遵守社会契约是道德的底线,对它的违反将从根本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他更高层次的道德标准无从谈起。因此,当公德与私德发生冲突时应以公德为准。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发生冲突的两个道德准则在其公德性上并无明显的差别,这种道德冲突不能通过契约论方法加以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公德无解”。公德无解的道德冲突便转化为一个私德问题,相应地,公德有解的道德冲突则是一个公德问题。这里要注意区别道德准则的公德—私德性和道德问题的公德—私德性。我们通过为道德准则排序来确定其公德性或私德性的程度,进而为解决道德问题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私德问题的评价和选择,有时并无一个公认的标准,取决于行为者个人的倾向或偏好。例如,前面提到的对绝症病人隐瞒病情还是告诉实情的问题就属于此类。不过,另一些私德问题则有一个多数人倾向的评价或选择,如婚外情问题。需要提出,既然是私德问题,就不能强求一致;对待私德问题的态度应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更好,但不按多数人的意见做也无可厚非。
对于公德和私德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一点在密尔那里已经得到比较清楚的表达。对于所谓的“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密尔有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注: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2页。这两条格言通常被称为密尔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界限,实际上也是密尔关于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界限,即把个人道德限定在不涉及他人利益的行为范围,而把社会道德限定在涉及他人特别是有损于他人利益的行为范围。这与笔者用社会契约来界定私德与公德的做法大致相当,但也有重要的差别。在笔者看来,不涉及他人利益的行为太少了,这使得私德或个人自由的范围太小,也不符合密尔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评价。社会契约方法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简言之,对于私德问题只应采取软性的劝导方法,对公德问题则应该采取硬性的强制或准强制方法。
我们说婚外情问题属于私德问题,因为它是公德无解的:一方面,婚外情行为违反了要忠实于配偶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在进行正式结婚程序(如领取结婚证)时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契约的性质;另一方面,婚外情行为却维护了个人追求爱情的权利,爱情本身是无辜的,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追求爱情。后者属于人权范围,其公德性并不低于前者的公德性。因此,从公德角度看,婚外情作为道德问题是无解的;于是,我们只能转到私德的角度对它进行评价。从私德角度讲,一个人搞婚外情是不应当的。不过,既然是私德问题,对于搞婚外情的人只应给以善意的建议或劝导,而不宜公开地批评或指责,更不应该诉之于法律的惩罚。
联想到我国最近出台的新《婚姻法》,其中增加了追究包括婚外情在内的“破坏一夫一妻制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条款。对此,本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它不仅把一个私德问题变成一个公德问题,而且把一个道德问题变成一个法律问题,这是对公德和私德、法律和道德的混淆,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由此也可看出,在当今道德建设和法律建设的过程中,区分公德和私德、法律和道德,并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重蹈传统儒家的老路,不适当地强调私德,甚至颠倒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欲速不达,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笔者并不轻视传统儒家的私德伦理,而是主张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即放在公德的基础之上。我反对把私德作为道德基础,但主张把私德作为更高层次的个人修养。缺乏私德修养的人在人格上是有缺陷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这样的例子。然而,缺乏公德自律的人则失去做人的起码条件,我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就是如此。离开公德是提倡私德,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助长伪善,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伪君子们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以公德为主就是突出道德底线,即自觉遵守和维护公共法则或社会契约。如果一个人连这点都做不到,还奢谈什么更高层次的私德修养。既然如此,我们的道德建设首先应在完善公共法则和社会契约上下功夫。可以说,我国现在面临的道德危机首先是公德性的危机,屡禁不止的官员腐败首先来自制度层面的缺陷。我们期望一个能把公德和私德、法律和道德完满结合起来的政治伦理体系,也许,这有待于西方伦理与东方伦理的某种融合。
标签:道德论文; 饮冰室合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法律论文; 梁启超论文; 社会契约论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