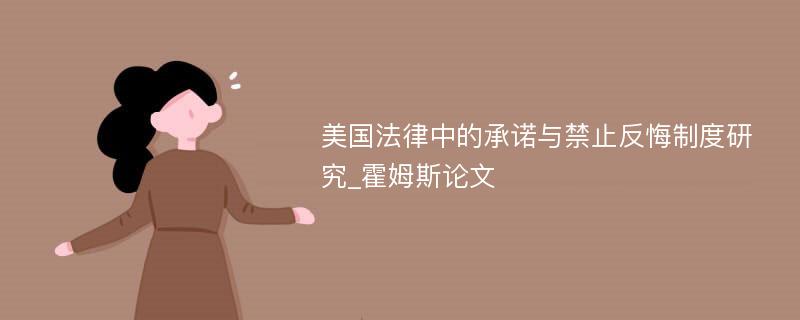
美国法上的允诺禁反悔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法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允诺禁反悔是英文" promissory estoppel" 的意译。英文" estoppel" 一词首次出现在爱德华·科克公爵于1628年出版的《英国法概要》中。据科克所言," estoppel" 来自于法语词" estoupe" 和英语词" stopped" ,它之所以被称为" estoppel" ,是因为一方当事人自己的行为或承诺使其难以再开口主张或辩解事实的真实性。①
禁反悔是一种类型繁多、构成复杂的法律制度,允诺禁反悔只是其重要组成之一。我国一些学者虽然也时常以“允诺禁反言”或“不得自食其言”为名提及此制度,但对其复杂性明显认识不足。概括地讲,尽管现代允诺禁反悔制度表现出保护合理信赖的普遍特征,但英美法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允诺禁反悔制度,仅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上的允诺禁反悔而言,它们在产生原由、确立时间、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等方面皆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探讨英美法上的允诺禁反悔制度时,绝不可将其脱离于特定的时空维度。
美国法上的允诺禁反悔制度集中体现于其《合同法重述》(以下简称《重述》)第90条第1项规定,其具体内容为:允诺者应合理期待其允诺会引诱承诺者或第三人的行为或不行为,并且,其允诺确实引诱了这种行为或不行为;如只有强制执行该允诺,不公平才得以避免,该允诺具有约束力。因违反允诺而准许的救济可限制在维护正义的需要内。② 美国学者与法官一般将上述规定简称为“允诺禁反悔”,认为“对允诺的信赖是一个创设权利和义务的独特的基础。它既不依赖于建立任何协议,也不依赖于建立任何相互交易的对价”。③ 对至今仍对意思自治理论推崇备至的大陆法系而言,上述规定给人一种怪异、独特之感。其实,就是对同属于一个法系的英国或澳大利亚的合同法学者而言,《重述》第90条的规定也令他们感到新奇和迷惑。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一条规定?它与作为美国合同法之核心的对价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它在美国合同法中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方向?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一 允诺禁反悔之由来
在英国法上,允诺禁反悔制度的兴起来源于对古典合同理论局限性的克服;在美国法上,允诺禁反悔的产生,表面上在于科宾对霍姆斯的交易性对价理论的挑战,实质上牵涉到以科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美国形式主义法律思维的强烈批判。
(一)霍姆斯的交易性对价理论
对价,全称为“允诺的对价”,来自于罗马法上的“原因”概念,意为允诺的原因或动机,即允诺者做出一项允诺时他正考虑或思考着的东西,或促使他允诺的东西。在对价的早期含义中,允诺者已经对承诺者负有某种债务之事实,如承诺者已经出借给允诺者一笔金钱,或已经为允诺者做了某事,将确定地满足对价的要求。④ 在19世纪以前,对价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并未形成独特、稳定的含义。在18世纪晚期,曼斯菲尔德法官建议,在英国法中,就如在大陆法中那样,所有严肃做出的允诺都应被看作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建议在曼斯菲尔德死后的半个世纪里不仅未被采纳,并且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拒绝了曼斯菲尔德法官的意见后,英国法院开始试图解释对价的内涵。在1842年的托马斯诉托马斯案中,法官帕特森对何为对价做出了如下权威性总结:“动机和对价并不相同,对价意味着在法律上具有某些价值的事物,其来自于原告;它可以是对被告的某种利益,或者是对原告的某种损害;但无论如何它必须来自于原告。”⑤ 这种对价理论一被提出即流行开来,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价必须来自于承诺方,二是利益和损害同样可作为允诺方之允诺的对价。美国著名学者吉尔摩由此总结说,在早期适用这种“利益—损害”对价理论的绝大多数情况中,实际上,不具有强制履行效力的允诺仅仅是未被发生信赖的赠与允诺。⑥
19世纪末,“利益—损害”的对价理论在美国遭到霍姆斯法官的强烈批判。霍姆斯认为:“事实上,给予或接受对价之目的仅仅在于使允诺具有约束力。而根据协议的内容,对价作为允诺的动机或诱因被给予或被接受,这才是对价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允诺必须作为约定的动机或提供对价的诱因被做出和接受。在对价和允诺之间,全部问题的根本是互利约定引诱之关系,每一个之存在旨在为了另一个。”⑦ 换言之,“无论实际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允诺和对价在整体上或者至少在部分上必须声称一个是为了得到另一个的动机”。⑧ 这就是被一些人称为革命性学说的交易性对价理论。因为,在霍姆斯看来,在当事人之间明显存在利益与利益、损害与损害关系,而不是利益与损害的关系。无论承诺人可能遭受了多大的损害,他并未因此必然地提供一个对价,互利约定引诱之关系才是合同的根本。
与“利益—损害”的对价理论相比,交易性对价理论具有两个显著效果:⑨
第一,通过向对价强加一个新的“交易”要素,使一些原本可执行的允诺不再可以执行。从实际情况看,当交易是当事人的交互行为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构成因素时,交易要件对发生在市场中的交互行为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发生的交互行为则完全可能缺乏交易要件。例如,家庭内的交换时常不是根据讨价还价达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允诺根据交易理论就时常是不可执行的。
第二,通过消除传统对价理论中的利益或损害要素,使一些原本不可执行的允诺可以执行。这就使法官不再注意当事人交易的实质,而只需调查,当事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交换的过程,即它是不是讨价还价的行为就行了。
霍姆斯的交易性对价理论充分反映了他所主张的合同观念:“合同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正式性和外在性”。依据“交易理论”,当事人之间只要具有形式性的允诺交换,即可满足强制执行允诺的基本标准。这种理论相当应合19世纪美国人的基本情绪:信任自由企业,尊崇个人的尊严和创造;信奉亚当·斯密的“通过自由竞争的交易,社会能更好地利用人类的自爱”的宣告。因此,交易性对价理论在19世纪末一被提出即很快被许多人视为真理并随即取代先前的“获益—受损”对价理论成为主导性学说,并对1931年的第一次《重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信赖——科宾反驳交易性对价之唯一性的利器
《重述》(第一次)是由塞缪尔·威利斯顿主持完成的,亚瑟·科宾以威利斯顿主要助手的身份参与了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当大家谈到如何规定“对价”时,深受霍姆斯影响的威利斯顿提出了后来成为《重述》第75条基本内容的建议,⑩ 而深受本杰明·卡多佐影响的科宾,则向重述者们提出了卡多佐式的对价定义(11):一种宽泛、模糊的对价理论。
在两种对价理论的交锋中,威利斯顿·霍姆斯派明显比科宾·卡多佐派更受欢迎,但科宾并不甘拜下风。据吉尔摩的大概回忆,在重述小组的一次会议上,他向重述小组的成员们说:先生们,你们正致力于普通合同法的重述,你们最近已采纳了一种对价定义,我现在向你们提交一份案例清单,在这些案件中,根据你们的对价定义,不存在对价,也因此不存在责任;然而,法院都根据具体情形强加了合同上的责任。先生们,你们打算怎样对待这些案例?(12)
既然有翔实的判例事实,合同法的重述者们感到难以反驳科宾的论点;但为了避免再次陷入对对价定义的不休争论中,他们选择了一条折中路线,即,坚持威利斯顿的意见,以霍姆斯的对价理论为基础订立第75条;与此同时,根据科宾的建议内容以“禁反悔”思想为原则规定了第90条。客观地讲,《重述》(第一次)第90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75条在决定允诺是否具有执行力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但是,第90条在怎样的范围内具有这一效力并未被阐释清楚。《重述》不是法典编纂,其采纳的是条款—评论—例证的编制格式,条款具有明显的分析性、松散性,评论比较冗长,例证则大多是从一些真实的判例中抽象出的。而在《重述》(第一次)的所有规定中,第90条几乎是其中唯一毫无评论的部分,仅仅提出了四个完全假设的案例作为例证。(13) 但对这四个例证的集中研究只会导致分析者得出失望的结论,第90条文本本身深奥难懂的特性当然也加强了这一认识,因而无人知道第90条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思想。第90条的规定因此也就成为《重述》(第一次)中最受关注、最具争议性的条款。(14)
由上可知,《重述》(第一次)第90条表面看来是为调和威利斯顿和科宾之间的意见冲突,实质上反映了理论和实践在合同强制执行力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在霍姆斯的交易性对价理论提出之前,美国并无统一的对价理论指导或约束法院的审判活动。但实际上,具有很强哲学思辨能力的霍姆斯所提出的交易性对价理论之所以很快就被当作了真理,并被规定到《重述》(第一次)之中,并非因为它在理论上具有多大的建树,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对价是一种限制合同责任范围的工具”观点迎合了19世纪末依然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民众的情绪。但是,历史地看,将霍姆斯的对价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法院行为的基本原则,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交易性对价理论并不符合判例法的传统,因此,即使其在实践上被普遍接受,却始终未充分地被其他人在思想上接受。(15) 在处理丰富多样的案例事实和扑朔迷离的对价含义之间的关系上,霍姆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削足(事实)适履(理论)的弊病。第二,统一的对价理论其实暗示着,法院应按照严格的演绎推理审判案件,这显然严重背离了美国法的司法推理习惯。始终对案例事实而不是理论感兴趣的科宾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科宾认为,“法院的功能不是创设定义和规则,然后再机械、教条地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程序适用定义和规则;相反,它的功能是决定执行允诺的合理、充分的理由是否存在。当法院发现这样的理由时,它可热情地称它有充分的对价。对法院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允诺应当被执行,而不是什么是一个充分的对价”。(16) 因此,将对价严格限制为一种交易互换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当然也就很难引诱法院去遵守它。《重述》(第一次)如果接受这样的对价定义,那么它必须与此同时伴随另一原则,即,许多非正式的允诺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执行的,即使根本不存在任何对价。这将有助于将司法思维从狭隘的演绎逻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将注意力集中到根据社会风俗和流行习惯决定合理的司法政策。以此来看,第90条确立的规则并不是一项法学上的新开发,而实际上是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司法判决的一种名副其实的重述。(17)
二 《重述》(第二次)对第90条的修正
20世纪50年代,为使合同法能与不断增加、变动的法院判例保持一致,美国法律协会在他人捐赠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合同法的第二次重述工作。到60年代后期时,各编陆续有新版面世,《重述》(第二次)则于1981年最终完成。
《重述》(第二次)将第90条名称修改为“合理地引诱行为或不行为的允诺”,并对其内容做了重大修正,新的规定如下:(1)允诺者应合理期待其允诺会引诱承诺者或第三人的行为或不行为,并且,其允诺确实引诱了这种行为或不行为;如只有强制执行该允诺,不公平才得以避免,该允诺具有约束力。因违反允诺而准许的救济可限制在维护正义的需要内。(2)根据第1款,无需证明允诺引诱了行为或不行为,一项慈善捐赠或结婚财产赠与是有约束力的。
与第一次《重述》相比,第二次《重述》主要有四个突出变化:第一,删除了确定承诺者的信赖程度的“确定、实质的”要求;第二,增加了根据个案灵活给予救济的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规定;第三,适用对象不再仅限于承诺者,而可及于关系第三人;第四,增加规定了慈善性捐赠与结婚财产赠与的允诺无需证明引诱行为或不行为。
上述修正反映了允诺禁反悔规则在20世纪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回应了理论界对信赖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合同法而言,在《重述》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没有哪一部学术作品对合同法产生了如同朗·富勒发表于1936-1937年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那样的影响力。阿狄亚认为,富勒的关于信赖利益的伟大著作是许多现代信赖理论的起点,它拉开了讨论对价原则与合同上各种类型的可判给的赔偿之间的关系的大幕。自17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人深刻地主张,合同上的债务可被认为主要建立在承诺者的实际的或可能的信赖之上。(18)
富勒著书立说的年代正是形式主义法学日薄西山、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深受德国法学家鲁道夫·耶林的“目的法学”影响的富勒,(19) 显然厌倦了形式主义法学的“概念游戏”,于是,他首先分析法官判给合同损害赔偿或执行合同所追求的目的;然后追问,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情形下这些目的在判决和学理论述中得到了表述;最后,简单分析普遍承认信赖利益的结果。
富勒认为,法院在授予原告损害赔偿上,主要基于三种目的: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返还利益是指,在对D的允诺的信赖中,P已经转移于D的某种价值;授予返还利益的目的在于阻止不当得利的发生。信赖利益是指,因对D的允诺产生了信赖并实施了一定行为,P已经改变了他的地位;信赖损害赔偿要使P处于在允诺被做出之前他所处于的地位。期待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基于合同之效力所产生的期待价值,授予期待利益之目的,在于使合同当事人一方获得对合同的期待价值。
富勒将合同上的利益进行区分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合同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以期待利益赔偿为目的的观点是虚幻的,真实情况应当是,在理论上一直被忽视的信赖利益赔偿在现实的判例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信赖利益赔偿这种救济措施,在承认期待利益赔偿或完全否定赔偿责任的二者必择其一的传统合同法理论中,正发挥着开拓中间的救济之路的功能。(20) 换言之,信赖利益赔偿可以作为一种比较合理、便捷的赔偿方式,既化解期待利益赔偿在计算上的困难,又弥补有合同与无合同之极端思维所造成的不当。比如,在对合同履行受到外部情况干扰(履行不能或目的落空)的判例进行分析后,富勒认为,“当我们检查在‘恢复原状’案例之主题下所列举的判例时,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怀疑,在其中的一些判例里,信赖利益在化名之下得到了保护”。(21) 基于此发现,他主张,当法院在维护合同之神圣性与强加合同责任之间彷徨不定时,也许在授予一方返还利益之同时再判给一种信赖利益的赔偿比较恰当。
富勒论文所含的洞察显然并不仅限于上述总结,日本学者内田贵先生非常明白这一点,认为富勒的重要洞察有二:第一,如果说合同责任不但以保护期待利益而且以保护信赖利益为目的,这将意味着合同法上存在着这样的规则:“违背合理信赖的行为产生补偿由此招致的损害的责任。”该规则之存在将打破正统的以合同与侵权作为损害赔偿基础的二元化责任机制。第二,富勒在阐述信赖利益在合同法上的重要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在合同法上为何应保护期待利益的疑问;并从经济、秩序与法律的角度上论证了保护信赖利益作为授予期待利益赔偿的正当性依据。
但毫不客气地说,内田贵先生其实夸大了富勒的理论贡献。就所谓的第一个“洞察”而言,受损信赖可作为一种独立的赔偿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富勒的原创或首次发现,先于富勒的文章三年,学者科恩(Cohen)在1933年的《合同的基础》一文中就已提出,虽然它尚未被充分地阐述,受损的信赖看起来是当时合同法上一种最受欢迎的理论,是合同上责任的一种重要基础。(22) 读过科恩文章的富勒按说应当在科恩观点的基础上,就受损信赖为何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基础在理论深度上“更上一层楼”,(23) 或者对作为合同上损害赔偿基础的受损信赖理论与意思自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分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富勒只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向我们暗示了受损信赖可作为一种独立责任基础的诸多可能性。
相对而言,内田贵先生所说的富勒的第二个洞察也许更有意义,富勒在此方面的探讨冲破了长久以来由“意志理论”形成的理论羁绊,在法律现实主义的风起云涌中,如一道刺目的闪电,给许多志于法律变革的人们开启了一条崭新的智慧通道,从此,法学院与法院之间的距离被逐步拉近,法学家逐渐将迷惑的目光投向丰腴的现实世界。
富勒的利益分析方法对《重述》(第二次)关于合同救济的规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被授予不超过期待利益的救济”的思想可在《重述》的很多条款中被发现。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信赖利益赔偿要么作为期待利益赔偿的替代,要么作为无期待利益赔偿时的有限救济。《重述》(第二次)对某些缺乏对价的允诺(第86条、第87条、第89条以及第90条)、被《欺诈法》禁止的口头允诺(第139条)、尽管有精神缺陷的抗辩但仍被认为可执行的允诺(第15条)规定了这样的救济。对一些依据错误、目的落空或不能实行之学说被免责的允诺(第158条与第272条),《重述》(第二次)也规定了不超过期待利益的救济。另外,它还规定:当期待利益的价值不能被证明时(第349条),法院可授予当事人一种信赖利益赔偿金;当赔偿全部期待利益被认为有些过度时(第351条第3款),法院可做出一定的限制。除上述具体规则外,《重述》(第二次)的“救济”一章还以一节明确规定了三种利益,并对其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第344条)。
三 允诺禁反悔的适用条件
根据第90条的立法精神、《重述》的具体规定以及学者们的见解,允诺禁反悔在适用上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允诺者明确地做出了允诺。根据《重述》第2条第1款的规定,“允诺是旨在以具体方式行为或不行为的表示,如此为或不为,以至于能证明承诺者认为一项义务承诺已经形成”。允诺不同于要约,根据《重述》第24条的规定,要约是愿意参与交易的表示,它是如此被做出,以至于当事人另一方有理由相信,他被引诱同意该交易,并且他的同意会导致交易的达成。允诺与要约均是一种意愿表示,要约几乎都是允诺,但允诺不是要约。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意愿表示的程度不同,要约必须具备确定性,即包含了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具有较强的受约束的意旨:受要约者一旦承诺即受约束的意图。然而,作为一项意思表示,允诺只是向承诺者表明允诺者愿意对自己的言辞负责;至于允诺者对自己的允诺应承担怎样的义务或责任,仅从允诺本身难以做出判断,因此,与要约相比,允诺具有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受约束意旨的软弱性。一般而言,要约在做出之后,尚不能对要约人产生确定的约束力;与之相比,允诺在做出之后,所谓的“愿意对自己的言辞负责”则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重述》报告人说:“允诺的萌芽是一种信用。”(24) 在人际往来中,信守诺言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事件中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秩序,一方向另一方做出一项确定的允诺,不但意味着允诺者应以自己的言辞行事,而且更暗含着,允诺的受领者在允诺做出之后也会对允诺者的未来行为产生某种程度的期待,对允诺的期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不同于交易理论中的要约,通常情况下,允诺禁反悔规则中的允诺,并不被要求具备像要约那样的确定性;而是强调允诺者须是明确、肯定、直截了当地向对方做出了允诺,即允诺在形式上必须具备确定性。因为只有这样,对方当事人才可能对允诺产生合理的信赖;任何含混不清、犹豫不决的允诺都不足以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决定,因而也不足以引发信赖。而对允诺之实质与形式的确定性的不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允诺禁反悔的适用范围。譬如,美国某些州曾要求允诺须具备像要约那样的确定性,这样就将大量的只具备形式确定性的允诺排除在允诺禁反悔制度之外。
第二,承诺者实际上信赖了允诺。该要件历经了一定的变迁,《重述》(第一次)对此的规定是“承诺者的信赖须具有确定和确实的性质”。(25)《重述》(第二次)删除了这一点,认为承诺者只要实际上信赖了允诺就足够了。所谓信赖,指意思表示的相对人相信了他方的意思表示,并以此实施了一定行为,付出了一定代价。如甲向乙许诺说,他将肯定与乙达成协议,乙相信了甲的许诺,放弃了与丙的谈判,并开始发布广告招募工人,扩大生产。如甲背弃其许诺,乙因甲的许诺所放弃的缔约机会、广告费、生产费等费用均属于信赖。
根据新的规定,直到承诺者实际上信赖于允诺,允诺才可被执行并不可被允诺者撤销。该要件强调承诺者的行为或容忍应当是被允诺引诱之结果,以此推理,即使无允诺者的允诺的引诱,承诺者通常情况下本也会做出的一定的行为或容忍就不属于信赖的范围。
但是,该要件也存在一个例外,即根据《重述》第90条第2款的规定,无须证明信赖的存在即可强制执行结婚赠与或慈善捐款的允诺;简言之,该两类允诺一旦被做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规定是对美国支持慈善捐款的传统政策的承袭。
第三,允诺者本应有理由期待信赖会发生。即使承诺者信赖了允诺,如果允诺者根本无理由期待任何信赖,或有理由期待信赖但发生的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信赖,允诺者也不具有责任。最简单的案件是附条件的无报酬的允诺案件,在这样的案件中,对允诺者而言,期待承诺者根据允诺所规定的条件采取行为是清楚合理的。
该要件是从允诺者的角度加以规定的,检验“合理期待”的标准是客观的,即理性人的标准,凡一理性人置身于与允诺者相同的情形,可“合理期待”承诺者将因该允诺而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即可满足该要件。(26) 根据上述标准,如果允诺者有理由期待信赖会发生,其将受到其允诺的约束,即使允诺者事实上并没有期待信赖会发生。
这个要件也可从承诺者的立场给予界定。如从此方面来思考,一般要求承诺者需合理地信赖了对方的允诺,或者可以说,承诺者的信赖需为“合理”。所谓“合理”,指承诺者对他人允诺之信赖需出于真诚、善意。在判断是否“合理”时,仍需采用客观标准。
第四,需强制执行允诺才能避免不公平。判断是否有不公平之发生,通说认为应根据承诺者是否遭受损害来决定,承诺者如果没有受到损害,很难认定有任何不公平。
如具备上述要件,允诺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承诺者可以向允诺者请求赔偿。
四 允诺禁反悔的赔偿范围与赔偿根据
受威利斯顿观点的影响,第90条在确立之初即倾向于对期待利益的赔偿。与初始想法明显不同的是,《重述》(第二次)对第90条的保护范围采取了一般性规定的立法策略,即规定“救济可被限制在正义的范围内”。如此处理的意旨是,依据每一个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正义观念的指引之下,法院可自由决定,是给予承诺者期待利益的赔偿,还是信赖利益的赔偿。重述者之所以对第90条的规定做这样的修改,表面的缘由在于,应与《重述》(第二次)删除“信赖须具有确定和确实的性质”的规定相协调;实质的理由则是,吸收富勒文章的精华,使允诺禁反悔制度在适用上不至于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然而,这种规定仍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重述》还是《重述》的正式评论都未指出决定正义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承诺者何时应获得期待利益的赔偿,在什么情况下正义要求赔偿请求应当被限制为信赖利益的价值?对此,范斯沃斯认为,下列情况一般比较容易判断:第一,在允诺者缺乏诚信时,法院将更大方地采用期待利益的赔偿,而不是更受限制的信赖利益的赔偿;第二,在巨大价值的期待利益和微小价值的信赖利益之间存在差异时,法院将倾向于赞同信赖利益的赔偿;第三,根据一个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额比较困难时,将鼓励法院使用另一个赔偿标准。如此之下,如允诺的不确定性使期待利益赔偿额在计算上变得非常复杂时,赔偿可能被限制在信赖利益的范围内;相反,如信赖利益赔偿的计算被估算损害时的困难弄得复杂时,期待利益的赔偿将可能被适用。(27) 由此看来,《重述》第90条所保护的不仅包括承诺者的期待利益,而且有时也可为信赖利益;到底采取哪种赔偿标准,需在实现正义的要求内个案地加以判断。而这种难以理性化统一标准的司法判决方式其实意味着授予了法官一种自由裁量权。
承诺者获得赔偿的依据何在?赔偿范围的二元性使得对该问题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一种理解是,赔偿是限制在信赖利益的范围内的,在此情况下,因允诺者只赔偿承诺者在对允诺的信赖中所遭受的损害,因此,允诺者和承诺者之间显然不存在合同关系。通说认为,当当事人一方通过做出一种允诺、然后再以破坏自己允诺的方式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时,允诺者因此而承担的赔偿责任按照侵权责任的原则来思维比较合理。后来的一些判例也逐渐显示,根据第90条或者说依据允诺禁反悔学说所建立的赔偿责任是有别于合同责任的。吉尔摩因此认为,由于基于欺诈法、合同时效法以及口头证据规则的抗辩被公认为是以合同为基础的,第90条规定的赔偿责任因此对其也就不再可以适用。这种思想如果传播开来,在损害赔偿规则的发展中可能会产生一个有趣的分支。(28) 1983年,梅茨格与菲利普斯教授认为,允诺禁反悔开始成为一种不同于合同责任的“独立的赔偿理论”。(29) 他们指出,允诺禁反悔反映了20世纪相互依赖的观念,同时也反映了流行于19世纪末期的合同理论中的个人主义的退位。他们认为,允诺禁反悔是一种类似侵权的救济,其旨在赔偿承诺者的合理的、可预见的对允诺的受损的信赖。该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另一种理解是,赔偿是局限在期待利益的范围内,在此情况下,学者与法官一般均认为,允诺者和承诺者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与一般合同关系迥异的是,这种合同关系不是立足于传统的对价原则而是建立在保护合理信赖的观念之上。
五 允诺禁反悔的适用范围与发展趋势
允诺禁反悔的适用一直颇受美国学界关注,它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允诺禁反悔的规范对象(适用领域),二是允诺禁反悔与对价之间的关系。前者关乎允诺禁反悔的存在意义,后者涉及允诺禁反悔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从逻辑关系上看,后者决定于前者的存在价值及影响。
(一)允诺禁反悔的规范对象
在对允诺禁反悔的早期法律适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中,存在一个基本假定,无论它如何被表达,第90条即使不是全部也是主要地适用于“非商业环境”。汉德法官曾建议,第90条如果说有任何适用空间的话(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其都仅应被限制于捐献的或赠与的允诺。吉尔摩将汉德法官的意见形象地描述为:专业选手应当根据专业规则进行比赛,在商业环境中,A向B发出一个要约,那么A对B的责任应当取决于要约、承诺和对价的正式规则,而不是依赖于其他规则。(30) 在20世纪早期,关于《重述》第90条的适用范围,这种观点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一些司法管辖区根据传统习惯将允诺禁反悔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下列方面:家庭内的交易;向教育的、慈善的、宗教的机构做出的慈善捐款;以及免费寄托中受托人做出的无报酬的允诺(主要涉及寄托物的保险问题)等。这些司法管辖区不愿意将以信赖为基础的可执行的允诺拓展到其他社会关系中,尤其不愿意将它扩展到商业关系中。
进入60年代后,允诺禁反悔制度不适用于商业环境的观念与做法开始受到商业现实的严峻挑战。1965年的霍夫曼诉红猫头鹰商店(Hoffman v.Red Owl Food Stores)案是允诺禁反悔制度挺进商业领域的典型案件。在该案中,罗科维茨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向原告表示并与原告达成协议(意向书,非正式合同),被告将在希尔顿修建一家商店,为使原告得以经营,该商店备有商品;作为回报,原告应当提供投资18,000美元。基于对以上协议和表示的信赖,原告卖掉了他们的面包店和杂货店的设施和营业,并购买了在希尔顿的经营场所,在希尔顿为他以及他的家庭租了住房。这样,原告信赖协议和表示的行为就破坏了他们原有的私人和经营生活,原告因而失去了大量的收入和花费了大量的其他开支。后被告违背自己做出的表示和协议,原告请求赔偿损失。法院依据《重述》第90条的规定支持了原告的主张。(31)
根据近三十年的司法判决,《重述》的起草者对《重述》(第一次)第90条做了一定修改。这次修改的主要变化体现在起草者精心写成的评论中。评论之一明确指出,该条时常以“允诺禁反悔”被提出,允诺禁反悔是禁反悔学说的一个扩张。根据禁反悔学说,在承诺者信赖允诺者对事实的陈述之后,允诺者不得提出与其曾经做出的陈述相反的事实。该评论进一步认为,“信赖肯定是强制执行已完成了一半的交易的一个主要基础,信赖之可能性对尚待履行的交易的强制执行提供了支持……这样,时常致使无须去调查强制执行交易的确切范围”。由此可以看到,信赖原则可能已历史性地成为“损害赔偿之诉中非正式契约强制执行”的基础。第90条提出的新例证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非商业性环境,而且在商业性环境中也有一定的用武之地。具体而言,允诺禁反悔可适用于下列商业性案件:(32)
1)对默示交易的信赖,这是单独根据允诺禁反悔而强加责任的最大的一类案件;
2)肯定的要约,即不可撤销的要约;
3)合同的变更;
4)可能被看作全部交易的一部分的担保,该情况的典型案例是,在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人是否应受关于保险单条款的虚假陈述的约束;
5)在退休或接近退休时允诺的退休金,这主要适用于雇佣合同中。
另外,允诺禁反悔规则在欺诈法之适用上、对违背不确定协议的救济上、虚幻允诺的执行上,以及允诺性虚假陈述的规范上均有不同的适用余地。
(二)允诺禁反悔与对价之间的关系
由前文可知,允诺禁反悔规则之所以能在美国法中赢得一席之地,根本缘由在于,交易性对价理论存在明显的规范漏洞,仅仅以此为核心来重述美国合同法会造成立法与司法之间的严重分野。当其只能适用于非商业环境的情况下,允诺禁反悔在规范地位上还仅仅是交易性对价的一个有效的替代品。但是,当其逐渐渗透进商业领域之后,允诺禁反悔与对价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美国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一些学者对允诺禁反悔之适用范围的实证分析来看,(33) 允诺禁反悔向商业领域的扩张是十分有限的,对于绝大多数合同而言,对价仍是一个核心概念;因此,可以说,允诺禁反悔适用范围的拓展并未改变对价在美国合同法上的支配地位,如美国学者费恩曼所言,“甚至在今天,尽管司法和学界广泛地接受了允诺禁反悔,但带有修饰色彩的对价的统治仍然将允诺禁反悔推到一个从属的地位”。(34) 1994年,一位学者在《允诺禁反悔的式微》一文中指出,(35) 允诺禁反悔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独立的债务理论,而仍然是一个从属的学说。因为只有在承诺者穷尽了其他所有的诉讼之后,允诺禁反悔才被加以适用,法院以很大疑心看待这样的要求。无论合同死亡说的学者如何主张,允诺禁反悔的式微证明了传统的交易理论的持久的活力。由此可以说,我国一位学者的下列观点存在严重谬误,“信赖是美国合同法上的产物,自产生之日起便一改美国传统契约理论中对价中心的局面,而成为整个合同制度运转的轴心”。(36)
总之,《重述》第90条以概括性规定的特质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赢得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给予追求正义的法律人士解决棘手社会问题的几多灵感和欣慰。但是,在法律面前,激情和想像总是受到无情的限制,灵活性虽然能够赋予法律更多的柔韧性,并使法律实现实质的社会正义;然而,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法官对正义之理解难以取得一致的客观事实面前,第90条也隐藏着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子。对于商业发达、崇尚交易安全的美国而言,第90条所潜藏的隐忧总是时隐时现、挥之不去的。这大大限制了它的适用空间。
注释:
①Black' s Law Dictionary,Bryan A.Garner,editor in chief,7[th] ed.,West Group,1999,p.570.
②§90,美国《合同法重述》。
③[美]克劳德·D.柔沃、乔登·D.沙博:《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④19世纪后期,当交易性对价理论建立后,这种“过去的对价”不再被当作充分的对价。
⑤Peter Benson," The Unity of Contract Law" ,in The Theory of Contract Law,edited by Peter Ben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54.
⑥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0-21.
⑦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Common Law,quoting from a second source,Amy Hilsman Kastely,Deborah Waire Post,Sharon Kang Hom,Contracting Law,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96,p.277.
⑧Peter Benson," The Unity of Contract Law" ,in The Theory of Contract Law,edited by Peter Ben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56.
⑨See E.Allan Farnsworth,Farnsworth on Contract,Volume Ⅰ,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0,pp.63-64.
⑩《重述》(第一次)第75条的规定:(1)允诺的对价是:A.行为而非允诺;B.容忍;C.一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D.对待允诺,也就是用以交换另一个允诺的交易或所付出的代价。(2)对价应由承诺人或其他人向要约人或其他人做出。
(11)即使在霍姆斯的交易对价理论几乎被普遍接受后,在卡多佐任法官期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仍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在他担任法官的长时期里,卡多佐零散地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契约观点,尤其是广义的对价观点。卡多佐的对价观点对科宾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8-69。
(12)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70。
(13)吉尔摩认为,它们没有一个是以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71。
(14)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71-72。
(15)吉尔摩认为,霍姆斯在对传统的“获益—受损”对价规则进行批判时,明显着意于提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学说,而对普通法原状的陈述或者重述一点也不感兴趣。像说英语的任何法律人一样,霍姆斯通晓法律史——包括合同法的历史,但他在撰写讲稿以弥补普通法的不足时,对“对价”真实意义的分析几乎没有援引任何权威或者先例,而只是对那些普通的“说法”和“思想”作了即兴的论述。霍姆斯的想法始终未充分地被其他人在思想上接受。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2-23。
(16)Corbin," Recent Development in Contracts" ,50 Harvard Law Rewiew 449( 1937) .
(17)Corbin," Recent Development in Contracts" ,50 Harvard Law Rewiew 449( 1937) .
(18)参见P.S.Atiyah,Essays on Contract,Clarendon Press,1986,pp.79-80。
(19)内田贵在“契约的再生”中明确指出,“对德国法学造诣深厚的富勒以肯定的态度引用了耶林的研究成果”。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8页。在研究耶林对富勒的影响时,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容忽视,由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富勒生前所有或使用的图书中,赫然陈列着耶林的《法律的目的》第一卷(1884)和第二卷(1886),富勒生前曾对这两本书做过很多旁注和插注。参见http://oasis.harvard.edu/html/law00074.html。
(20)参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7页。
(21)[美]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7页。
(22)See Cohen," The Basis of Contract" ,46 Harvard Law Review p.553,pp.571-589( 1933) .
(23)富勒在其论文中明确引用了科恩的文章,参见[美]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注释16,第429页。
(24)E.Allan Farnsworth,Farnsworth on Contract,Volume Ⅰ,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0,p.9.
(25)确定性和确实性的理解,并非易事。威利斯顿为此而举的例证,也许能给出答案。A允诺赠与B1000元,以使B买车,如B确实买下车,那么,A应受其允诺的约束,因为这样的允诺具有“确定性”,可强制A履行其允诺。假使A允诺赠与B1000元,但未说明赠与物的用途,即使B信赖其赠与允诺而前往买车,A也不应受其允诺的约束,因为该允诺并未达到“确定性”。从此例证可看出,信赖必须具有合理和可预见的特性。参见杨桢:《英美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26)Dial v.Deskins,221 Va.701,273 S.E.2d 546( 1981) .
(27)参见E.Allan Farnsworth,Farnsworth on Contract,Volume Ⅰ,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0.pp.145-146。
(28)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73。
(29)Metzger & Hillips,The Emergence of Promissory Estoppel as an Independent Theory of Recovery,35 Rutgers L.Rev.472,509-511(1983) .
(30)参见Grant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73。
(31)http://www.waukesha.tec.wi.us/busocc/law/hoffman.html
(32)参见Randy E.Barnett,Mary E.Becker," Beyond Reliance,Promissory Estoppel,Contract Formalities,and Misrepresentations" ,15 Hofstra Law Review 443,457( 1987) .
(33)参见Randy E.Barnett,Mary E.Becker," Beyond Reliance,Promissory Estoppel,Contract Formalities,and Misrepresentations" ,15 Hofstra Law Review 443,457( 1987) .
(34)Jay M.Feinman," Promissory Estoppel and Judicial Method" ,97 Harvard Law Review 678,680( 1984) .
(35)参见Phuong N.Pham," The Waning of Promissory Estoppel" ,79 Cornell Law Review 1263,1290( 1994) .
(36)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
标签:霍姆斯论文; 信赖利益论文; 法律论文; 契约法论文; 合同目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要约承诺论文; 赔偿协议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