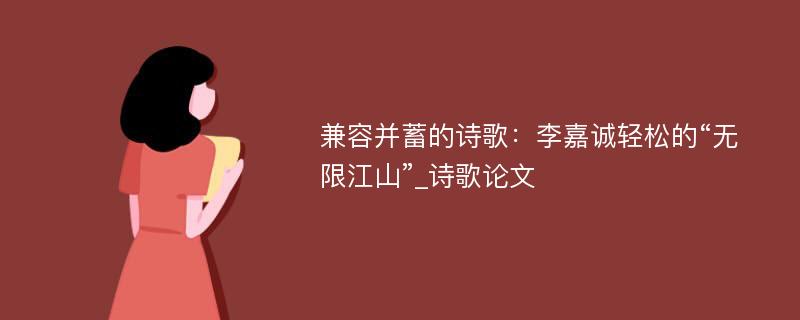
包容的诗意——李轻松的“无限河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山论文,诗意论文,轻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被无限的河山打动
你左边的青郁,右边的荒凉
都是我书写的浓重部分
我的根须伸向你,那无尽的关系
盘根错节的一场戏①
——《致无限河山——》
这一段近似于向“无限河山”深情告白的诗章,在作为读者的我看来,是李轻松在用一种诗人特有的书写方式,为我们提供一条进入她的诗歌世界的通道。作为诗人,到了“而立之年”的李轻松呈现出了一种分外包容的创作姿态②。这种姿态,在她近年来的写作中,首先表现为一种漫游的存在方式。
对诗人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抒情写意的负载,它同时也承担了诗人实现自我陈述的“任务”。相对来说,对于诗歌的阅读者而言,读诗,也不仅仅是感受诗意的过程,它同时实现了对诗歌中的“诗人”形象的勾勒与充实。《无限河山》的阅读者们,想必能够看到一个以漫游者形象出现的“诗人”。这位“诗人”在医巫闾山之南长大,“石头的七间房,我避过少年时代的那场疾雨/在大小豁牙口,我受的伤一直未愈”(《北望医巫闾山》),或许是由着这因为历史、自然与世情、成长交融而成的名山大镇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诱发的意趣,成就了“诗人”漫游的自我。那些“四下漫游”的经历,是许多诗章书写的对象,同时也是这些诗章本身。
夜宿黑龙江边,“午夜的收音机轻轻唱着一首歌/喝酒的赫哲人操着汉语/跟我谈起流行音乐,现代派,风情园/我却想着那个打鱼的老人/有什么从我们身边溜走,我抓不住一条鱼”(《在黑龙江边听〈伊玛堪〉》),一路南下,蓦然惊觉,“这是哪里?雨刚刚下过,那些植物/突然抬起头来。我未被润色/眼睛被什么轻轻地擦了一下/由此我看清了一些幽暗的事物”(《清新印象》),来到五月的江上,“在江上我任风吹着,时间不想说话/我的前后都失去了参照”,“在江上,我是个在梦中睡眠的人/不愿醒来。一个独自的漫游者/不愿显露”(《在江上》),迢迢千里,触摸到“这飘忽不定的天气带着南方的气质/我闷在里面,要说的话被卡在胸口”(《醉生醉死》),触摸到数十年前那位新月诗人留在江南的气质,以致“我无力再怀疑爱情。二○○五年我在海宁/左手燃着你的诗篇/右手握着灰烬。我一步步走下你的楼梯时/你的风久久不散/我像风一样终生颓废”(《蔷薇之远》)。
独行向西,在诗章中化作“无力重述的事物”,“在山西,我吃到了面,一直吃到依依不舍/从此我对山西有了具体的想念/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无法拒绝与后退”(《亲爱的“面”》),“云岗,你这云中之云,光中之光/在我的心力到达的时候,我的脚步却徘徊在外”(《云岗在上》),“我愿是你树下的须子,抱紧的泥土,被水卷走的叶子”(《在大槐树前认祖》),还有那龙门的黄河,普救的西厢。
或者是漫游到“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以精神聆听千秋绵延的“高山流水”,“一声断裂。仿佛那余音真的/带着故国的神韵/突然降临。仿佛是高山在上/有人看见了你的巍巍之志/他比高山还高。仿佛是流水在下/有人领会了你的汤汤之意/他比流水还低”(《用琴声寻觅》),“那浩渺长江正好做了分别的背景/从此无心览胜/对岸的黄鹤楼也心怀惆怅”(《两地音》),鹦鹉洲、汉阳城、楚波亭,种种种种,成为漫游者的乌有之乡、精神属国。
我愿意冒着惹人厌烦的风险援引与缀连这些足迹,是因为我相信,通过“还原”这些足迹,领会这种四下漫游的存在方式,乃至在我们的阅读世界里具象出这位“诗人”的漫游者形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作为现实中的诗人的写作姿态。在《我的诗歌现场》,李轻松这样表述自己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我从自我中脱胎而出,我的目光投向更加辽阔的世界,并开始带有时代的内省”③这样的变化,如果可以描述,我想,至少在某种层面上有这样的意义:这位诗人不再只是自我的抒情者,她同时也将成为自我之外、那包容了自我的辽阔世界的叙事者,并从叙事中,寻找诗意与省察。在此,漫游是诗人赖以重建对世界的诗意叙事的依托,更是激发自我的“云上光芒”。
我曾去过那世上受光最多的地方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
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但丁《神曲》
这段被李轻松借用作《无限河山》题记的诗句,在此,或许显示了李轻松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诗歌写作的困境——在精神的漫游与文字的表达之间存在的巨大困境。这种困境亘古存在,但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它又是具体而细微到每一次试图将自己的精神游历化为文字表述的过程中的。李轻松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对这个困难过程的回应中化形而出的。
漫游的诗人,重新面对着凡俗的世界,山川河流,城市街道。我所说的包容性的写作姿态,在此恰恰表现为,对于这凡俗世界诸般事物的诗意表达。我不得不说,这世上的诸多事物,所拥有的诗性多寡并不均匀——如果能用多寡来形容的话。这或许是天赋其形,也或许是往日的人文历史抹上的一道道油彩。琴棋书画当然和古典诗意有关,荒草杂粮、烟火饮食就很难归结到“天然”带有诗意的那类别里去了。在李轻松的“无限河山”里,让阅读者惊异的,恰恰是她对后者的传达:
这条街的尽头在哪里?落日已尽
我的身上沾满了灰。那小贩的吆喝声
那疲惫的脚步,那在风中打瓦的少年
都被夜幕收走。一个剪影扶着窗子
在笛声里掉魂儿,在河水里招魂儿
又一场没头没尾的戏,是没人喝彩的——④
——《在傍晚的街头愣住》
一个行走了一天的漫游者,在黄昏时到达这个城市,这条街道,天已昏暗,身上落满旅途的灰尘,疲惫地低声发问:这条街的尽头在哪里?在背包客的眼里,这个时候,往往只剩下找到一个旅馆、一张床和足够的热水,洗尽尘埃好好睡一觉的渴望。但在作为诗人的漫游者眼里,这样落满旅途疲惫的尘埃的风景里,同样有不可遏止的诗意生发:小贩的吆喝声、疲惫的脚步、风中打瓦的少年的声影,都在夜色中渐渐隐去;河岸边的窗子亮起了灯,一个剪影出现,相伴而来的,仿佛是魂兮悠悠的笛声与轻淌的流水声。这样的凡俗风景,在诗人眼里,是一出人生的戏,它自成天地,没有前生,没有后世,也没有观众,更不需要喝彩,它就那么存在,稳稳当当,无论高声低步,都有它自己的线条和命途。诗人在这里,并没有介入风景的打算,她只是偶然停在那条街的起头,看着这出“没头没尾的戏”,察觉出了其中的诗意,并试图用文字为它化形脱胎。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李轻松长久注视过的:
葵花都是向阳的。这就像真理一样
当乌云漫过医巫闾山的山顶
一头獾子站在河边,向葵花地眺望
我比葵花的头更低,满怀羞愧
她前世的籽粒一直怀到今生
还未饱满。那些田垄延伸到无边
叶子在勾引中交换了花粉
一种私通的气息。在躯干中直起腰⑤
——《葵花地》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诗歌呢?那些我们惯常所见的,比如一株向阳的葵花,枝干笔直,花盘微垂。只不过它可能在医巫闾山下,可能是那么一阵风中,那么一片乌云底下,一只灵动的獾,人立而忘。但最触动我们的,却是其后属于李轻松的那些近乎灵异的感觉,它们不为我们惯常所见,或者说,它们只属于一个敏感的灵魂构筑的世界。如果可以表达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与凡俗世界对应,或者说,它由凡俗世界的诗意相互凝结、对凡俗世界诗性表达的探索凝结而来。看看李轻松是如何发现葵那极端甚至妖异的诗性的:“在躯干中直起腰/在头颅转动时审视天空/疯狂与抑郁是她的两种版本/被人过分地传说过。她有着病态的黄昏/通过一只蜂鸟的复眼看我/仿佛我也具有了花的特征”。这是通过诗人的灵魂探索才呈现出来的异样世界,葵仿佛是一个有着精神内爆力却又由强大外壳包裹稳固的人,她不安定,头颅转动,审视天空,或而渗出些那从强大外壳缝隙间流露出来的疯狂和抑郁。那满花盘的花籽,仿佛成了复眼,漆黑尖锐,刺透观者的内心。
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包容的敏锐。在更近的《棉花田》里,李轻松透过诗行将现实世界与灵魂世界悄悄对接起来:“从坚硬里抽出的丝绒/一直到抽尽。我都不说疼/而棉花如何去抵挡刀和流水?/这暴力的始作俑者,这无声的催眠术”。甚至烟火缭绕的厨房里都有象征的意味:“我靠近了厨房,虚无就退后了一步。/我站在火苗前,与温暖就面对了面/这象征性的姿势,像不像在热恋?/其实这与写诗和种花也没什么区别”。谁又能说,凡俗世界不是诗意依托的所在呢?只是大部分人如我,无从去察觉、把握,还有述说,或者是因为见闻知识的拘泥,或者是因为灵魂无法包容尘埃。
这是我的寻找。总是与山水有关
江山大多是黯淡的,风也传情
从桃林传出的剑声酷似仙乐
我懂得那韵律,像熟知我自己的经典⑥
——《琴·山水》
江湖,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山川河流这样的存在与风景,还有一重,则更多地出于耳濡目染的人物故事,各种小说、电影、传奇之说,各种侠客、杀手、恩怨情仇、昔日情节。在前面所引的短短几行诗句中,我们发现,这两重含义那么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了一起。由“山水”到“江山”,一个由物到人的转换已经悄然完成;“桃林”与“剑声”,又接着构筑起另一个世界中的江湖;“韵律”与“经典”,终于连接起“我”与“他”的精神河流。于是,在这首诗里,听琴的“我”与抚琴的“他”,同时勾连了江湖的两种意境。而遍阅李轻松的《无限河山》,我们还能发现,这种勾连,时时隐现。李轻松的“无限河山”,在纳入了风景的同时,也令人惊异地纳入了我们习惯于从小说、影像中去触摸感受的“江湖”风情。
“顺着风声和鸟声而来的高手/总是隐于桃林。一个怀抱水罐的女子/和空穴里的风,瞬间红过/有如英雄的寂寞,剑里的一截秋水/要拿你爱人的血练剑,每天一滴/直到她流尽。直到桃花成泥。”(《剑·孤独》)我们能感受到这首诗所传达出来的李轻松式的风格。它或者外表艳丽惊厥,或者声响拔地而起,有着戏剧一样的起承转合,甚至可能还有高潮冲突,但骨子里,却显示出一种克制的力量,一种将核心容纳在怀、试图变得圆融温淳的企图。这种纳于一体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那些特殊的语言资源:风声、鸟声、隐、桃林、英雄、寂寞、剑、秋水、血、桃花……这些语言资源本身就蕴含了可以被层层剥落的想象。
在现实的语境里,我们都是文化的接受者,我们有着可以共通的想象,在很多时候,也有着相似的理性克制。我们可以共享一个关于江湖的充满力量、色彩的想象,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个想象之间的距离。正是这种可以共通的想象和认识,为我们领会李轻松类似诗歌的风格与力量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我们可以侧耳听取戏台上生杀起伏的“锣鼓点”:“他脸上的杀气隐住鼓点/手里提着刀像提着灯笼/不过走个过场。他是侧翻还是空翻/都由不得自己。他的刀被绿林识破/他的灯笼被红颜所伤”。(《锣鼓点》)而在另一场戏里,我们看到的是“跟一个暗处的人幽会/难免要骑马,要趁着幽野星空/跑到山河破碎,马蹄冰凉—”,“此刻镜子反光、房间紧闭、暗器横飞/我脸部干净、夸张,有点犹疑”(《下一场戏》)。我想,阅读的惯性会让读者很自然地从诗句中把那些特殊的语汇攫取出来:杀气、鼓点、刀、灯笼、绿林、红颜、山河破碎、马蹄冰凉、暗器横飞。在这些语汇纵横交错的诗歌空间里,一种江湖的气息已经被融入完整的诗意中。
还有对这种语言资源周纳得更丰富的,比如《大苇荡》:“被蒙面的黑衣人追杀到此/顿时苇海无边,武功尽废/其实我没有根底,空有一腔乡愁/更不善于飞刀传情”,以及“我的无间道,就从这荡漾开始/从这险恶中,提出我的轻功我的剑术”。或许是浸润于戏剧的功底给了李轻松这样落笔收笔就勾勒出极富于画面感与情节感的“故事”的能力,成就了属于她个人的诗歌风格。或许诗歌本身就是一场语言与灵魂的较量,至于诗歌的成功,也往往来自于诗人语言的厚度强度、灵魂的感受力突破力,以及它们之间对应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纳入更为丰富的拥有广阔生机的语言资源,不失为诗歌成熟的表征之一。
到这里,再来听李轻松对于自我诗歌创作历程的总结与对未来的自我表达:“我的诗歌里有了起承转合,每首诗都随着那锣鼓点、那兰花的手势、那迷人的眼风有了自己独特的命运”,“现在我要把锐利的锋芒藏于平静中,那将更有力量。但我永远不会失去我的体温、我的浓度、我的血性,我在不断地寻求变化,不想重复自己,哪怕是失败,我都义无反顾” ⑦。我想,我们无疑可以对此抱有更大的期待。
注释:
①李轻松:《致无限河山——》,《无限河山》,第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②李轻松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到今年,恰好30个年头,也可以说是创作上的“而立之年”。
③李轻松:《自序:我的诗歌现场》,《无限河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④李轻松:《在傍晚的街头愣住》,《无限河山》,第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⑤李轻松:《葵花地》,《无限河山》,第2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⑥李轻松:《琴·山水》,《无限河山》,第3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⑦李轻松:《自序:我的诗歌现场》,《无限河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