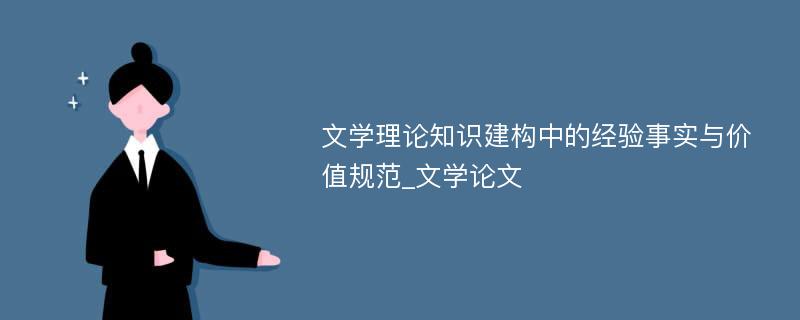
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知识论文,事实论文,价值论文,经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4月17~1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学术讨论会。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在其精彩发言中①,就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提出自己富有洞见的设想。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文学特征论”与“文学本质论”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前者是事实性提问,不涉及价值问题,它回答“实然”问题;后者则是一种价值确认,回答“应然”问题,是规范性叙事,它必然涉及价值(“善”)。“什么样的文学具有天然正当性?”这是文学本质论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余虹进而认为,以往的文学理论均为事实性提问,都是在把各种文学的所谓“特征”(比如押韵、分行排列、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等等)加以搜集、汇聚,没有涉及价值问题;而真正的文学理论知识应该是“特征论”与“价值论”的统一,事实与规范的统一,而且后者是更加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就是为文学立法”。
第三,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余虹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私我”(包括阶级、族群、性别等)利益的表达,比如阶级中心的、国家中心的、人类中心的等等。但是仍然有些文学现象是超越意识形态(私我)的,这种文学才体现了文学的“本质”。
余虹教授治文学知识学用功甚勤,建树卓著,其发言给人颇多启发,给我们留下了继续探讨的巨大空间。以下是我的一些非常粗浅的、没有经过整理和加工的感想,提出来向余虹教授及学界同仁请教。
首先,在关于文学本质的知识建构中,怎么处理实然和应然、事实和价值、经验与规范的关系?余虹教授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文学本质理论首先应该区分文学特征论与文学价值论,前者是事实性经验性的言说,后者则以价值为核心,不可能不涉及价值问题;它必须回答什么样的文学具有“天然正当性”或“自然正当性”的问题。但同时又认为,文学本质论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事实性依据;二是该事实必须具有价值正当性。也就是说,它必须同时满足事实性和价值性的要求。这就必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1.为什么文学本质论必须要有“事实性依据”呢?既然它涉及的是价值问题,需要满足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的要求,那么,没有经验性的事实依据又如何呢?应然判断为什么要建立在实然判断的基础上?为什么需要实然判断的支持?比如,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一种完全没有“事实性依据”的“好文学”?正如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一种完全没有事实性依据的“好生活”?既然余虹教授说体现本质的文学(他举的例子是反日常惯例化的语言)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不是已经在逻辑上排除了经验(事实)证明的必要性了吗?
2.即使我们承认文学本质理论应该同时满足价值正当性和经验实存性的要求,那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从“事实性”(实然)推导出“价值性”(应然)呢,还是从先验的价值出发来建构文学的事实?
我觉得,任何人文科学的核心都是价值问题,并且,它从根本上说就是价值/规范判断。换言之,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哪个群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而建构“文学事实”、“文学特征”。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涉及价值规范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事实”本身,就是因为文学规范陈述在现代性语境中面临的科学化压力而建构的(这种科学化压力来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建立的知识霸权)。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无论是“阶级斗争的文学”、“工具论的文学”、“审美的、自律的文学”,无不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自己)。所以,这里面必然会产生循环论证的问题:从特定的文学规范立场(如“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或意识形态”)出发建构事实(历史上那些所谓体现了“审美本质”或“意识形态”的作品),然后,这个被选择出来的所谓“事实”又反过来被用以证明这个规范判断的正当性。这样,历史上各种文学理论知识之间的较量从来都是价值立场的较量而不是事实的较量。任何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建构的“事实”都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它只能是部分的事实。正如余虹所说,“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却不是全部事实。如果说它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事实的不周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周全的事实来证明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不但“文学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是如此,“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不那么审美或反审美的文学事实不是随处可见吗?我们根本不能因此认定“文学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或“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论述是不合法的。如果说一个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全部文学事实的支持上,那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对“文学”以及“文学事实”下一个独断的认定,凡是不符合这个认定的就不是文学或文学事实。这不仅有专制主义的嫌疑,而且也陷入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3.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从规范出发来建构文学理论此路不通。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我们只能从关于文学规范判断(文学应该是什么)出发来建构文学理论本质论。我的立场其实更加彻底:我们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地和经验论调情,给自己的文学神学披上文学“科学”的外衣,从而陷入规范和事实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
在说明了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规范主义”立场(规范先于且优于事实)以后,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规范”理解为程序规范而不是实质规范。这是我和余虹教授的一个根本性分歧。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当我们从实质规范而不是程序规范出发,来判定某种文学和文学观念体现了文学的“本质”或具有“自然正当性”的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无法寻找到全部事实的支持(无论是“文学是意识形态”,或“文学是反常规的语言组织”,或“文学是审美”等等判断,都可以找到相反的事实),而是实质性的规范陈述逻辑上已经包含文学理论的独断论、一元论、绝对论。这样说有两个理由:首先,在一个价值多元化、文学多元化的时代,就一种具有实质性价值内涵的文学本质论达成共识已经极其困难;其次,如果是在一个平等、民主、理性的对话交往机制还没有确立的语境中,赋予某种具有实质性价值内涵的本质理论以“自然正当”或“天然正当”,那么,显然将非常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我们曾经见到过很多文学理论的霸权话语就是打着“天然正当”的旗号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强调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不是忽视了价值问题,或局限于事实性提问和经验性描述。其实它一直在确立规范,一直在做“立法”的工作(不管是为“工具论”立法,还是为“审美论”立法)。问题不在于它的文学观念的具体内容是否合法,而在于它的“立法程序”是否合法。余虹教授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的理解,都是属于实质合法性而不是程序合法性,是实质规范性而不是程序规范性;而我理解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合法性是一种程序合法性,它不询问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的具体内容是否合法,而只涉及关于文学本质的知识生产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具有就文学本质或文学价值做出规范性陈述的权利,只要这种陈述是合乎程序正义原则的。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不是某个文学现象或文学观念的具体内容或具体价值取向,而是平等、民主、理性和公开的建构文学知识、谈论文学本质和价值的程序。
把文学的知识建构建立在这种程序规范或程序正当性基础上,不但是基于理论的考虑,而且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觉得确立一种具有实质内容的文学本质理论的绝对正当性或天然正当性是行不通的,如果强行推行,就必然陷入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专制主义。但是,就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程序达成一种共识是可能的。就像我们今天很难就何为“好生活”的实质性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所能够做的或许是就“好生活”的讨论方式讨论程序达成一致意见。比如,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强权来强行推行一种关于“好生活”的价值,但是,经过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大多数人应该能够达成一种交往理性。同样道理,经过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都不能借助于理性言说之外的权力(不管是政治的或金钱的)来强行推行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由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界仍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骚扰和干涉,由于我们的某些组织依然在权力的支持下凭借着不合法的程序,正在建构或试图建构和推广一种钦定的文学本质观、文学价值观,我觉得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正当的程序正义是否必然能够得出正当的实质正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仍然只能诉诸一个规范判断:我相信,只要我们凭着理性、平等、民主的原则,就文学的本质进行商讨,达成一致或大体一致的实质性文学规范理论是可能的。这正如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凭着理性、平等、民主的原则,就“好生活”问题进行商讨,达成一致或大体一致的关于“好生活”的共识是可能的,但却不见得是必然的。但是,不管如何,在合法正当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程序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匆忙地建构关于文学的实质性规范知识,其后果将比先建立正当的程序、先悬置实质性的文学规范知识要严重得多。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私我”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什么是“私我”?我理解的“私我”实际上就是文学的言说主体的社会规定性,即广义的利益归属。的确,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这样的一种“私我”利益的表达。但问题是,这样的“私我”是否可能超越?应该怎样超越?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超越“私我”的主体(公我)应该如何确立,而不是是否可能设想一个超越“私我”的主体。从规范意义上说,超越私我的普遍主体(公我)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个普遍的主体(公我)仍然必须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下才能确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各个利益群体在共同遵循正当程序的前提下,自由地就何为普遍利益、何为普遍主体(公我)进行平等、民主的商讨,然后达成一致的共识,而不是越过这个程序。
作者附识:本文是2006年4月17~18日在浙江湖州师范学院召开的“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其主要的灵感和动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的挚友余虹在同一个会议上的发言。余虹教授的发言当时尚未正式发表,所以,本文对于他的观点的概括,主要是依据笔者在会议期间作的笔记,特此说明。
注释:
①余虹教授的文字稿请参阅本期杂志《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