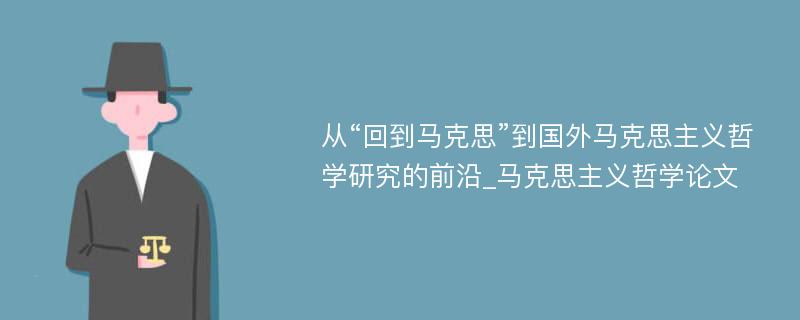
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云(以下简称“蔡”):1999年,您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一书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目前还在不断引起国内学人的许多争论。
张一兵(以下简称“张”):《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这本书,实 际上概括了我之前许多年的不懈追求。从1989年前后开始,我花了很长时间踏踏实实地 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力图在与马克思的直接面对中,实现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马 克思真实哲学视界的历史地回归,我认为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蔡: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您在该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回到马克思”是20世纪90年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您认为这种回归是摆脱前苏联和东欧式马克 思解读模式的理论无根性的真正开端,这种种提法对学界来讲可以说是相当耳目一新的 。但是甚至在这本书引起的争论和反响还未平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自己的研究方向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的研究重点似乎已经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转移到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去了。该书在您的整个研究思路中仿佛具有一个分界线的意味,因为 从该书出版以后,您似乎就已经不再以“回到马克思”为研究的重心了。
张:首先应该说明一下,“回到马克思”这一努力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完成。最近,作 为这一方向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我与蒙木桂合作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 的当代阐释》一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更广大的青 年读者。另外,我所主持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在MEGA2第四部分的马 克思早期经济学笔记研究方面,以及新编马克思哲学史稿方面都将形成新的重要学术成 果。当然,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一世纪末,我们已经将主要研究方向调整到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来了。
蔡:因为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您突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异常活跃,发 表了不少论文。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在研究方向,或者说是研究重点上的这种改变的原 因和意义何在?能不能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您近年来的研究思路做一个梳理?
张:确实如此,在1998年之后,我的确把主要精力从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转移到对国 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来了,不过实际上我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方向并没有变,你所观察 到的这种所谓的分界,其实还是在同一个总体研究方向上不懈前进的两个理论准备阶段 而已。
事实上,我并非是在今天才开始“突然”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初次遭遇西 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一世纪80年代初),其时正逢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领域的一次具有重大意 义的延展,简单来说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一举得到改变,理论研究的 学术含量大大提高,也为后来的学人们开拓出理论创新的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不过,那 时的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当时我仅是直觉到一种深深的 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在这种震惊的驱动下,我才开始了最初的文本阅 读。可是,早期的阅读总是囿于传统哲学解释构架的惰性制约,真有些像《哲学笔记》 开端时的列宁,我总是努力地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地方错了。
蔡:真有意思,早在二十年前,您就开始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处!而近年来您却一 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具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
张:是的。当时这种否定性批判思考的正负坐标系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教条主义构架。 毫无疑问,这个阶段的阅读既不系统精深,也失之盲目与不够成熟,不过阅读中倒也约 略感觉到一些力不从心,对我今后的思路有些启迪,可以说我后来所质疑的正是我当年 也怀有的那种阅读和评判态度。
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静下心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一个专题的研读,从时 间上看应该是在1985年到1989年间,这可以算是我正式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 个阶段。那个时期的研读成果是一篇近七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先是收在孙伯癸先生主 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卷中,有一编的篇幅,后来我又把这个提纲 扩写成了一本十七万字的小册子,即《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一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觉研究本身还是踏实的,积累下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资料, 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不过,也正是在这本小册子完成不久,我开始反 省自己的研究思路,并且决定暂时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程搁置下来(那 大概是在1989年前后)。原因很简单,还是我多次提到过的那几个字——力不从心、窘 迫不堪。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从前就曾经感觉到的理论基础上的力不从心,因为 自己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正在被我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这是一场不同层次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本称不上对话,说严重点,当时的我以及 所有进行类似“批判”的人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某种自说自话的自欺。如果真实一点地直 面现实的话,这种理论水平上不平等的“批判”是无法再进行下去的。这是我十多年前 自觉中断这一研究进程的真实原因。
我后来曾多次追问:“我们是否具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在许多前辈看 来,我的追问是大不敬的。其实,这个后来招来不少批评的追问倒真不是一种狂妄简单 的他性指责,因为我最初质疑的对象正是我自己。应该说,我的这次反省是相当深刻和 诚挚的,对此我曾不留情面地对自己做过剖析——“我俨然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 上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面貌,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但是,在内心里我却已深深 地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 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 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又真是建立在对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我曾经指认过:‘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 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 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 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 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 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 文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所以,我已经内省到 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进而认为,关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这需要我们完成‘回到 马克思’的历史任务”。
蔡:这么看来,应该就是这次深刻的反省,直接促动你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花 费十余年时间研读马克思的文本,致力于“回到马克思”的。
张:并不仅于此。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已经说明过“回到马克思”的复杂原因) 。不过,这次深刻的质疑和反省使我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难度之大,已远 远超出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西方哲学研究,它要求一种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 方哲学领域的双向深度内居,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不能真正深入当 代西方哲学,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将永远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这次反 省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最终促成我强压急于批判、急于写作的不成熟的 冲动,而下决心真正沉静下来,排除一切诱惑,包括创作的诱惑来做两件事。
其一,就是大家熟知的“回到马克思”。正如刚才我所讲的,如果我们自己根本就不 曾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那么我们凭什么去 判定他们的对错?简单地将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它显 然将带来理论上的无根性,这也是我在研究中深感窘迫的根源。“回到马克思”花费了 我接近十年的时间。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的文本,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读过的书, 主要是与古典经济学相关涉的领域。之所以选择从经济学的视域重读马克思,一方面是 孙伯癸先生的学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优秀的思想家大多具 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背景,我认为只有先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才能居有批评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仔细研读了当代不少大师的论著, 甚至包括后现代的大量文本。那是一段很苦的时日,坐“冷板凳”真是十分艰难,不过 我想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所幸我扎实地走了出来,阶段性成果不仅凝聚在《马 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里,更重 要的是,当我再一次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自己觉得有底气多了。《回到马克思 》的序言里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形容这种隐性的成果:“从我自己的理论研究来说,在呈 现了过去自80年代以来就一直让我不安的马克思哲学的初始理论地平线之后,我终于可 以重返实际上自己更关心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了’”以该 书的出版为标志,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主体部分基本告一段落。
此时就出现了你所提到的我的研究重点的转移。在十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之后,我重 新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研究反省后下决心做的第 二件事情。我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据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 如青年卢卡奇在成为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 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这时候我们就遭遇另 一个窘境——如果我们自己根本不能透视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那么又何以实现 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十多年前写作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时 ,这个窘境也曾带给我切肤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楚: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 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仅不能算是科学 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滑稽的。所以,在完成第一个十年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之后, 我将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重新投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就是1998年到现在我 一直在做的工作,根据我的计划,还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日子。
蔡: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回到了过去曾经中断了的研究思路上来了。可是,这还是同 一个思路吗?
张: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我原来的研究思路是越来越明晰了,当然也有认识上的改变。我认定,只有加强自己的内功,我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研究视域才能达致新的深度和广度。我想,在经历前十多年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化一步的时候了。在这里,我还是要 重申我多次强调过的观点,这种深化需要我们怀着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诚挚 的态度,甘于首先伏案完成认真踏实的文献学工作,建构起一种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当 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深度研究模式。
蔡:这个思路听起来十分令人向往,不过我想会是十分艰难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的新 型深度模式。我注意到,您总在提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新型深度模式应该又是您提出 的一个新概念。
张:不错。深度解读模式确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新模式,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主要 还是基于我对国内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总体估计。这恐怕还是得从徐崇温先 生的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进”谈起。1982年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中国学界已经进行了20年,应该是时候冷静地返观这些研究的成果了。
具体来说,20年来,国内学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成果主要还是在翻 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从翻译方面看,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截止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但主要涉及的还是哲学、文 化、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本,而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 科学的学科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当然,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逐渐在弥补这个缺陷)。可见,在研究的广度上说,余地很大 ,我们面前展延着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对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也未 能生成必要的理论定位。逐一回首自《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起点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典研究,我们是十分汗颜的,因为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仅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 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能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多是在众多 二手资料的客观描述之上冠以“主义”的大帽子,而缺乏一种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 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刚才详细谈到过的我们在马克思文本解读和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两个领域上的理论准备不足,我才提出了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模式。我想, 对于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对我们一度 以为完成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以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 候”所在。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重新面对必须以一种深度解读的模式来进行。这很重要 。
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关于当前的研究,除了深度解读模式之外,您还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研究范式的问题。用你自己的话说,是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平台,是吗?
张:是的。2000年,我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 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全新的概念,以重新定位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 展的最新动向,这种定位是我们深入研究必不可少的新的理论平台。
我在《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走向》一文 中已经指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前置是关于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新 左派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出现了很大的分化,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如本真马克思和资本 主义政治批判两大主题)的内涵与外延已不再能统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倘若再不 进行研究范式上的重新界划,我们无疑将陷入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之中。基于这种认知, 我提出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只有指认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建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并存新 格局,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蔡: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线索。你能谈得具体一些吗?
张:可以。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要明确指认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这 种理论思潮的发展脉络作一追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在反叛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释中无意识建构起来的,比如卢卡 奇以总体性,葛兰西以实践一元哲学,柯尔施以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反对分裂的理 论逻辑和资本主义现实,他们拒绝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官方座架,尤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神化的非科学解释方式,而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理 解,区分出异质于恩格斯及斯大林体系的某种非正统的“新马克思主义”。有意思的是 ,马克思的这波“新生”往往又都寄居于某一现当代西方文化和哲学流派,这些左派理 论仍然坚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现实还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明确反对资本 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3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突现为一种人本学的马克思主 义,包含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活动,同时也指涉布洛赫、萨特和列菲伏尔等人的人 学建构;到了60年代,恰在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迎来理论建构和泛化的颠峰状态之时,以 阿尔都塞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举起科学主义方法的大旗猛烈冲击人本主义主 流,他们以科学结构和对客观规律的关注,拒绝了非历史的人与主体性,以此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内部,重演了一部学术无意识中的现代西方理性分裂的悲喜剧。此时正是60年 代末——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中后期,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 的出版为开端,特别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等论著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逻辑意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变的关节点。这种逻辑意向内在地拒绝全部工业文明,作为 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 然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或者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 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被批判性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 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我认为,阿多诺的这种理论倾向已经 溢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终结在理论层面上 以阿多诺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为质性标志,在历史实践层面上则是由60年代末西方 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画上句号的。
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您的这个界划体系中,似乎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不错,老实说,关于阿多诺的研究给我了很大的惊喜,我甚至在原有的计划之外 写作完成了《无调式的辨证想象——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一书(2001年 我已经将其先期出版)。阿多诺哲学既标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也开启了一种走 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其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这就是我 所定位的后马克思倾向。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 但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在一般理论文本的写作上 ,他不再像依从根据式地援引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倒是更轻松、更自由地批评或赞 成马克思。这种后马克思倾向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众多西方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 左”派思想家的理论形象。正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理 论转向,全新的后人学成为基本点。例如,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家弗罗 姆,在其最后一本著作《占有还是生存》(1976)中,也已放弃了抽象的主体中心论,区 分了“占有性”的人道主义主体生存与后人学语境中的非占有的、非中心的“生存性” 的主体论。他明确反对传统人本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利己和占有欲”,反对“奴役 自然”和人对自然界抱有的“仇视态度”。至此,虽然弗罗姆也试图将这一理论意向与 自己原有的人学理论统一起来,可无论如何他先前那种强调人类主体主导性和超越性的 历史逻辑已经大打折扣。后来的波洛克和哈贝马斯的思想也都是建立在这一新的理论转 折之上的。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真正解读哈贝马斯超越劳动经济学后的非同一性交 往理论。因此,正是阿多诺开创了后(现代)马克思思潮之先河。
阿多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阵线一边,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 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出现了。其中的主导方面是藉后现代思潮重新构建的后现代 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这些理论家还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异质的是,他 们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 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因为这种人类主体强制性奴役自然的非生态态 度,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再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批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的观点同样是父权制的,原因是马克思在关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时,只是指认了在交换市场之中实现的劳动,而无视妇女家务劳动在劳动力生存条件中 的地位,这同样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以上的种种观点已不再从属于传统西方马 克思主义力图确证的“本真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意向。
在“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 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思潮。他们明确表示不赞成马 克思主义,但却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如德鲁兹、鲍德里亚和晚期德 里达。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他们本身就是巴特、拉康和福科所开创的后现代思 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右派的政治立场(如利奥塔、罗蒂和哈桑等人)。他们从 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还可以 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这就是我所谓的“后马克思 思潮(Post-Marxian Trend)”。
作一个明确的指认,这种思潮本身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急剧向右转的 一个理论变种。
蔡:这里我想打断一下,您的学生胡大平博士最近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 似乎是在您所提出的几个范式之外的问题,您能否解释一下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与后马克 思主义的关系。
张:好的。后马克思主义一语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西方学界出现了, 比如波兰尼在1958年就已经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味上使用过此词。而我自己,当初 在重新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域的时候,也已经注意到国外学者对后马克思 主义(Post-Marxism)一词的广泛使用。可是,必须指出,这一指称在目前西方学术界的 能指是完全漂浮的。一是时段性的指认,它可以泛指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论”之 后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指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解之后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并且 这种指称只是在一种消极的贬谪语境中使用的。二是质性指认。从目前比较集中的理论 认可来看,主要是指拉克劳、墨菲等人于1985年出版的《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 书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革命策略。因为她们直接而明确打出了“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旗号,自称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书 中,她们承接并结合后阿尔都塞与新葛兰西的观点,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 质主义逻辑的反统治权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当然, 这种建立在异质的逻辑上的、以完全的他者为支点的“真正”批判,在以将政治理论化 的方式远离现实而完成了“革命的逻辑”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无奈的 认可。在此书出版之后,围绕这一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激进社会主 义讨论域。
在我新构筑的理论平台中,原来考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哲学逻辑构架,因 此,专门排除了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线索,现在看来,这一领域在整个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是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有保留地支持胡大平 的观点。但关键的问题是,一定要在学术研究中有精确的逻辑界划,否则,由此必定造 成一种理论研究中的视线混乱。
不过,在整个后现代思潮成为西方激进力量的主体逻辑之后,还存在着一种可以说是 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与以上两种流派相比,这种思潮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最 为接近,在内在的理论逻辑上可以说是一种延续关系。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 基本的原则和根本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是后工业社会无法超越的。面对 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们拒绝承认其质的改变,只是策略地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 义”(Latecapitalism,曼德尔语)或全球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不同于后马克思思潮 的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现在仍处于西方学术界前沿的有杰姆逊、伊格尔顿 和德里克。其中,最富创建的是德里克的“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之论见。晚期马 克思主义超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处在于,尽管他们坚持其前辈在对待问题方面的构 架与原则,但毕竟已是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条件下面对种种新生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全 新言说,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印证。
关于上述全新的研究范式,学界还有异议。不过,我自己坚持认为,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这种重新界划,即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 终结之后,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同样是从西方马克 思主义中分离出来的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新的研究范式来重组这一领域的具体讨论。从 根本上看,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平台的重新构筑:通过新的定性分析,以区分目前仍然在 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同一性旗号下所混杂的当代各种异质性的左派哲学学术思潮,是一 项极为重要的学术理论域的预设性建设。
蔡:说到这里,我对您现在正在做的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程 非常感兴趣,最后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您的研究计划安排。
张:从大块的时间上看,我是从1998年之后开始专题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不过,在80年代专题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个不成熟的阶段里,我已经扎扎实实地积 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1993年以后,我开始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中开设“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课程,1994年起,又为全校文科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西方社会思潮”课程开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1996年,我开始招收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1998年之后,在专业博士生课堂上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这些,都 是重要的积累。而自从《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完成以后,我的大 部分精力就集中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来了。除去与胡大平博士合作完成一本供研究 生使用的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以外,这一次的 研究我主要采用了已经非常上手的文本学解读方法(这一方法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 书中创立的),这也是我近期的研究重心。
我计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进行一 次系统的解读,研究的进展总体上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开始陆续形成一批学术成果。 1999年,我开始撰写《文本的深度耕犁》一书,原计划出三卷:第一卷:《西方马克思 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第三卷:《西 方后马克思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其中,阿多诺和阿尔都塞都写爆了, 关于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研究专著《无调式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辩 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关于阿尔都塞的文本学研究专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 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都已经陆续出版。《文本的深度耕犁》的第一 卷已经完成,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这次系统解读原先计划用五年时间来 完成,目前看来,时间将拖得更长久一些,这个过程与马克思文本研究将同样艰难,但 是正因为我坚持认为,在进行专题式或概括性的全景描述之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最重要的经典文本进行一次认真的解读十分必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所以我一定会脚踏实地、恭恭敬敬地读下去。令我特别高兴的是,孙伯癸先生和我共同 培养的一批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正在以更高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这一理论工程 中来了,同时开始以全新的理论个性登上中国的学术舞台。(注:唐正东:《从斯密到 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和历史性诠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大平:《后革 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2年版;张亮:《阿多诺:“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版。)
还是那句话——我在寻找一个新的起点,实现一个与研究对象同等的高度,回归一个 真实的视界!我坚信,自己的努力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是相当有意义的,但是,这些努力 都只是一种“在路上”的台阶式努力,我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是梦想仍旧是自己的真正 的哲学创造,用马克思的方法,广纳世界文化之精华,以真正实现属于民族精神的东西 。
为了问津这个光亮的梦想,我将坚持自己脚踏实地“在途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努力!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阿多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