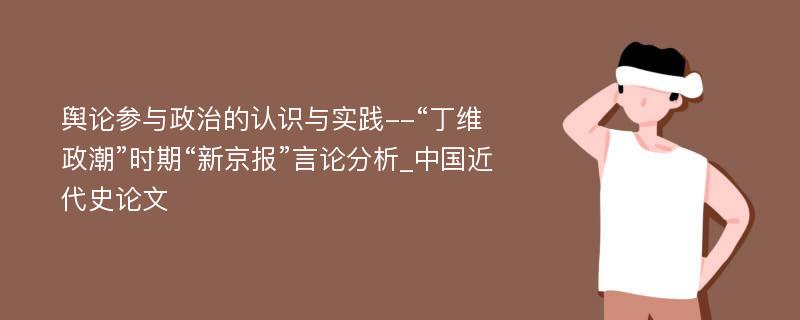
舆论参政的理解与践行:解析“丁未政潮”期间的《京报》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报论文,舆论论文,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7年8月25日,清末报人汪康年创办于北京的《京报》随“丁未政潮”的完结而遭到封禁,结束了自3月28日创刊以来历时五个月的短暂历程。“丁未政潮”是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围绕官制改革而展开的政治事件,其结果对清末政治走向造成影响。值得瞩目的是,这场“政潮”由《京报》报道所引发,几乎涵盖了报纸的整个生存期,在此期间,这份报纸以“专以纠政府之过失”为参政手段,以舆论压力极力推动政治变革。在清末乱局下,其对舆论参政的理解与运用较之当时改良派、革命派及其他民间报刊都有所不同,虽然以报刊舆论为参政途径并不鲜见,但这一点仍为相关考察提供了新的观察点。
一、《京报》与“丁未政潮”
有关“丁未政潮”的报道与言论是《京报》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也是其“舆论参政”典型体现。这一事件的导火索由《京报》报道引燃,也使报纸遭到封禁厄运,几乎贯穿了报纸整个生存期。
“丁未政潮”的背景是清末宪政改革。1906年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第二天即下令官制改革,以此为预备立宪之首要,开启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体制革新。官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核心,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两大政治集团的政争即由此展开。
负责编纂官制改革方案的袁世凯提出组建责任内阁作为行政总机关,裁撤军机处,意以奕劻为总理,自任副总理。时任军机大臣的朝中“清流”瞿鸿禨对“浊流”奕、袁种种“招权纳贿”之举素来反感,袁多次拉拢瞿不成,遂行排挤,双方交恶已久,此时借官制改革之事,瞿鸿禨向慈禧进言称成立责任内阁之后,一切用人行政大权皆由总理大臣与各部大臣会商后请旨颁行,这引起慈禧对大权旁落的担忧,成立责任内阁的方案被推翻(沈云龙,1966:61-62)。不久公布的新官制中,袁世凯被迫交出北洋四镇军权,辞去八项兼差,与其关系密切的徐世昌、荣庆退出了军机处,而瞿鸿禨仍留军机,并兼外务部尚书,奕、袁集团在中央的势力受到了很大影响(周育民,1988:92)。但在地方势力的争夺中,“浊流”却占据了上风。先是岑春煊由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其接任者正是袁世凯亲家周馥,后是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徐世昌与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皆为袁世凯亲信,其中段芝贵由直隶道员直升黑龙江巡抚,实属“史无先例”,岑电请入觐,参劾奕、袁及其他大僚20余人,被授邮传部尚书,朝中“清流”势力更强(戴逸,李育民,1997:151-152)。
正在两派势力交锋之际,《京报》开始向“奕、袁”集团发难。先是抨击奕劻借七十寿辰之机广收贿赂,继而揭出东三省督抚任命中的隐情。《京报》称,奕劻寿庆暗备账册,现金一万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入禄字册,现金一千以上及礼物三千金入寿字册,现金一百以上及礼物数百金入喜字册,整个寿庆共计收受礼金五十万之巨,礼品折银亦不下百万,《京报》讽其为“老庆记公司”。而早在1906年,奕劻之子载振与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考察官制,路经天津时,载振为歌妓杨翠喜所迷,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不失时机地将杨赎身献与载振,又借银十万两为奕劻寿庆贺礼,后段芝贵果列奕劻与袁世凯所提议的东三省巡抚人选(许指严,2007:148;陈墨公,1994:43)。
《京报》对“奕、袁”集团的抨击从一开始就非常尖锐。1907年4月5日刊载的《庆亲王七十生辰特别赐寿记》中痛斥奕劻“问之当世,实无可纪之功,笔诸史编,更无可书之绩”,值国家危亡之时大办寿庆而不觉“不自安”,但“固己位则易,箝人口则难”,这一举动应受舆论指责。
《京报》的报道与评论当即引起舆论大哗,御史赵启霖公开弹劾,清廷迫于压力命载沣与孙家鼐彻查真相。这给奕、袁集团带来了极大麻烦,他们先一步将杨翠喜送回天津,并安排参与纳妓的当事者出具证词否认,借银十万两给段芝贵行贿的王竹林也矢口否认这笔借贷,使调查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告终。赵启霖因“污蔑亲贵重臣”之罪被革职,同时清廷也撤销了段芝贵黑龙江巡抚一职,并准载振辞官(郭卫东,1989:81-82)。
对于清廷为平息事件“各打五十”的做法,《京报》分别作评。首先肯定罢免段芝贵之举,5月8日《读连日罢斥朱宝奎段芝贵谕旨谨书》一文称贿官买爵世人皆知,辇毂之下“几成为运动剧烈之场”,“登进之故,多无可言,一言以蔽之,则非其私昵,即在纳贿之多寡耳。”如果都像罢段一样,让这些贿官者“求荣反辱”,就有望使“用人者必求其有以相副”、“求官者必思所以自效”。而对于赵启霖遭革职一事,《京报》在5月19日连发《读初五日谕旨谨注》与《读初六日谕旨谨注》两篇评论,指近年来政府屡经弹劾,然而竟“悉置不问”,只见言官数次遭谴,难道被劾者竟“无瑕可指”吗?质问“近五年来,国事之进步如何,民生之休戚如何?”任由一二大臣搅乱朝局,其利害波及全国,政府竟不能加以制止,难怪招致天下责谴。后赵启霖在御史江春霖、赵炳麟、陆宝忠等保荐下得以复官,《京报》7月17日言论《读开复赵启霖革职处分上谕谨注》给予清廷适度肯定,“虽不能不尊隆亲贵,而尤以能容直臣为尚”、“虽用独断之体载,而仍视舆论为从违”、“于一时奸慝,照察至深,不能任其把持”,若以此促成“以时艰共济为首图,以竞进贪婪为至戒”的风气,则国家将免于危险。
《京报》舆论对奕、袁大不利,加剧了两大集团的对立紧张,奕、袁认为瞿、岑二人“非去之不能自全”。他们先借广东革命党起事之由奏请调岑春煊为两广总督,接着以1.8万两白银买通御史恽毓鼎参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致瞿遭开缺革职。之后,广东人蔡乃煌为讨好袁世凯,将康有为与岑春煊照片合为一张,做成两人聚首密商的样子,由奕劻进呈慈禧,再由恽毓鼎参劾岑密结康梁意欲“推翻朝局”,触动慈禧大忌(沈云龙,1966:152)。8月10日,岑遭开缺,次年蔡即补上海道台之缺。至此,以瞿鸿禨为首的“清流”集团在这次政争中失败,袁世凯取代瞿鸿禨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此番经过使清廷对袁也怀有警惕,安排张之洞同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场“丁未政潮”宣告结束。
而《京报》也很快就遭到厄运。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刊登消息,说奕劻病弱,慈禧已有替换之意。据传此事慈禧只向瞿鸿禨一人提及,因瞿在家中泄露消息,瞿夫人又告知汪康年夫人,汪康年又将此事透露给《泰晤士报》访员曾广铨而致消息公开(陈旭麓,1979:58)。此事也是袁世凯、奕劻指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的缘由,1907年5月17日,瞿鸿禨回籍,8月25日,《京报》亦遭封禁。
汪诒年将《京报》遭禁的原因归为其“伉直敢言”触动了当朝权贵(汪诒年,2007:1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记载,《京报》“至宣统元年,以论杨翠喜案被封”(戈公振,1985:171),盛宣怀《齐东野语》中记“七月以前政界各事,均列新出《京报》中,该报发人阴私,固属遭忌,实则泄露秘密,为众报所无,为当道最忌。特于七月十七夜,由民部传谕该报停止出报。”(陈旭麓,1979:63)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中记杨翠喜案“首由《京报》将其秘密披露,一纸风行。京津各报纸以全力搜索此项事实”,《京报》“举真无遗”,披露杨翠喜位于北京西城撒子胡同的住所,在“官场丑行不容于清议”之时,《京报》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后瞿鸿禨去职,《京报》“遂连带而被查封矣”(管翼贤,1943:300)。可见《京报》因牵连“丁未政潮”而停办为人所共识。“丁未政潮”起于1907年4月,终于8月,几乎与《京报》同始终,《京报》舆论引发事件并影响其走向,而这一政治事件的结局也左右了报纸的命运,在新闻史与近代史中,两者互为存在,密不可分。
“丁未政潮”期间,《京报》除“对于奕劻搏击最力”外(汪诒年,2007:134),“于中外骫法营利诸人,亦列举其非,抨击不少宽”(汪诒年,2007:139),如《论粤督限制报馆》、《论札派黄开文为东三省森林总干事》、《敬问东三省借外债四千万之理由》等文,直论朝中“巨公”。时人评价汪康年对此报“用力至劬”(汪诒年,2007:141),《京报》也成为舆论参政的一个典型。
二、“专以纠政府之过失”的舆论参政
清末政治变革背景下兴起的国人自办报刊,其动力在于国运危局中知识阶层通过“议政”进而“参政”的意愿,然而,由于中国政治系统的自封闭性,舆论议政若不能介入政治运作的实际过程,也就难以实现它的现实政治功能(许纪霖,1999:112)。因此,报刊大多依托会党,会党亦热衷办报,据此当时国人办报高潮又被称作“实质是政党的斗争高潮”(吴廷俊,2008:124),政党的嚆矢“强学会”、成熟的政党“保皇会”与“同盟会”都积极办报进行政治宣传,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政论报刊发展主流。既有“党”又有“报”,即如所称“既以舆论参政,又以组党参政”(丁三青,2009:70)的传统从此开启。
作为机关报的政论报刊通过传播政治观点,勾勒政治蓝图,以获舆论支持之力。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以《变法通议》引起广泛关注,为维新变法创造了舆论基础,至清廷尝试立宪改制时期,这种方式并未大变。有研究者对此总结出一个“立宪报刊的传播模式”,即“先提出一个目标,形成一致的舆论,继而鼓吹一致的步骤与行动,且相信其所提出的步骤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张朋园,1969:77)。
不过,《京报》并未沿用这一模式。《京报》持明确的立宪立场,不属任何会党,形式上不能算是“政党报刊”或“机关报”,却是一份深度参政的报纸,并将焦点集中于“纠政府之过失”。从内容看,针对政府之谬的批评是《京报》的言论中心。报纸原件目前暂未见存,但由汪康年胞弟汪诒年所辑《汪穰卿先生遗着》中收录了汪康年在这份报纸上所发的全部言论,共计44篇,平均每月近9篇。总的来看,44篇出自主笔汪康年的言论除《读谕旨定十五年立宪喜而书此》与《读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演绎词义敬告国民》主要内容为阐释立宪主张外,其余皆为批判时政之谬与国策之误,以此来看,这份报纸的言论重心在于批判国是,以形成舆论压力来促成政治改革,可见,是“批评”而非“鼓吹”构成了《京报》的舆论焦点和参政力量。
《京报》的这一特色,与创办者汪康年办报活动的动机与经历密切相关。从办报动机来看,作为维新时期出现的重要报人,汪康年“舆论参政”的意愿一直是明确的,其报刊活动首因于筹办“中国公会”促进维新,《时务报》即是为办学会做思想铺垫这一思路的产物,以此为开端,其报刊活动历经了不断的舆论参政重心的尝试与调整。在《时务报》、《昌言报》与《时务日报》、《中外日报》时期,他曾以“广译各报,指陈利病”与“内之情形暴于外,外之情形告之内”等加强信息传播的办法来促动政治改革(汪诒年,2007:77),终觉作用有限,仍想进一步扩展报刊的政治影响力,遂意进京办报,希图能触及政府,发挥更直接的政治效用。早在1901年,他便有了进京办报的想法,曾接受英敛之《大公报》主笔之请,但因提出“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对报纸加以设计”,未能被接受(侯杰,2006:44-45);1903年,这一意图更广为人知,广东籍报人朱淇同他商议合办《北京报》,表示“能与君同处,为君执鞭,则所欣愿也”(汪康年,1986:237),他又没有应允。几经曲折,1904年,在“绝意仕进”十年之后,汪康年赴京补应朝考,谋得“内阁中书”一职,为《京报》的创办做准备(汪诒年,2007:109)。《京报》存在期虽不长,却是汪氏办报生涯中蓄势最久的报纸。
从充分的蓄势可以看出,汪康年对《京报》政治影响力有更高设定,《京报》首期《发刊献言》中也议及当下“报章虽多,然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人国,如是难也”,“处今之时局,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他”,“然则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抑亦无恶于天下欤”等等,这些字句明确表达出其舆论参政的急迫与坚决。“丁未政潮”中的表现证明,《京报》不止于清议,更进一步立场鲜明地打击“浊流”,介入政治角争,直接充任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表现的动因与性质值得探讨。
由于时人多知汪康年为清末重臣瞿鸿禨的“门生”①,又因言论以贬袁为主,有利于以瞿为首的朝中“清流”,所以《京报》为瞿“机关报”之说颇为盛行,如:
盖《京报》主笔某公为九公门下士,数年来出入九公之门,专为侦探起见,今年即舍《中外日报》,而特开《京报》,于杨事极力而登之。《北京日报》始系独立,继因斧资缺乏,贝公济之,所以于贝公必极力护持,于杨事必力辩其诬。在杨、段之事交哄之时②,众人即云:“《京报》为九公之机关报,《北京日报》为贝公之保护报。”虽至妇孺,皆如此称谓也(陈旭麓,1979:59)。
如何看待汪瞿之间的关系,是判断《京报》“舆论参政”动因与性质的关键。师生名分加上瞿身处军机要位确使汪视瞿为倚傍。但需明晰的一点是,倚傍并非依附,确切地说,《京报》舆论的最终目的,是助“立宪”,而非助“清流”,《京报》虽极力贬袁,却非专为维护清流,其表现虽相似于政党报刊,但本质并不相同。这一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促动立宪是汪办《京报》的首要动机,却并非清流的首要主张,在这一点上汪与瞿并不是完全合拍的;第二,汪与瞿的交往,并非出于被动的依附,而在于主动的借力,《京报》并不是为瞿所用的舆论工具。
就第一点来说,纵观汪康年的政治活动历程,其重心虽然历经倡导维新、主张地方自治、推行立宪等等不断调整,但渐进改革的主张基本不变,是贯穿其政治及社会活动的主脉络,有研究将汪的“不变的核心思想”总结为“以实现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渐进、有序的改革”(汪林茂,2011:9),从这一点来看,清政府“预备立宪”是与其心目中所设定的渐进改革理想步骤相符合的,所以首先在支持与维护立宪的立场上,《京报》是坚决的,这是其舆论参政的动机与目标。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是否主张立宪却并非瞿袁之间,或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根本分歧。袁世凯曾被认为是立宪改制的一大障碍,清室立宪主张者镇国公载泽曾断言改制一事“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但是,袁后来并未反对立宪,相反极力推动改革,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争”(李细珠,2009:117)。由组建责任内阁之举可看出,袁世凯态度转变的原因是欲限制君权,执掌内阁,所谓支持立宪实际是为了揽权,这一点可谓“路人皆知”。相对应的,瞿鸿禨阻止袁世凯组建内阁,客观上虽制约了袁世凯大权独揽,但其最大动机在于打击政敌,对立宪制本身他却没有公开的支持或反对,有时论议其“暗中决断,变化百出”,表面中立,实则是反对立宪的“魁首”(时报,1906)。瞿与袁,或清流与浊流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政治利益的争夺,而非改革观点的不一,《京报》贬袁之举虽在行为上与清流一致,在结果上助瞿贬袁,在动机与目的上却并不一致,这方面它与政党报刊或机关报是有所不同的。
对袁世凯的意图,汪康年自然很清楚,但同时,他对瞿鸿禨的看法也并不简单。以权力地位而言,瞿当然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人物,汪康年最初对其寄予厚望,认为此人可托,若厉行改革,时局尚有可望,因而要极力“匡扶”。汪康年与其任职外务部的堂兄汪大燮都将与瞿的交往当作游说朝中重臣支持立宪的好时机(汪康年,1986:837、865),抱有这一想法对作为立宪改制的积极推动者而又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汪氏兄弟来说,是自然的,可以说其“匡扶”瞿鸿禨的目的,不在依附,重在借力,如相关研究所论,汪对瞿的“匡扶”,实际上就是向瞿鸿禨灌输自己的政见,潜移默化,使瞿鸿禨成为其“政治代言人”(廖梅,2001:321)。1905年,汪康年打算组建政党“台党”,以对政府形成监督与批评的压力来促动改革,并欲推瞿鸿禨为政党领袖(廖梅,2001:324-326),但是此事不但未成,日久天长相处之下,汪康年觉得瞿并非胸怀改革大志之士,而是“专门弄小巧机”之人,“迈幅极狭小,倚以办实事不能”(汪康年,1986:836、928、903),原本的信任与期望也随之打了折扣。原本就欲“借力”的汪康年,当“借力”初衷归于失望,更不会简单地以办报为瞿所用,所以,从第二点来看,也可看出《京报》贬袁的根本动因,应非维护瞿鸿禨,谋取政治利益,《京报》为瞿之机关报或充当政党报刊的说法并不确切。
若《京报》本意并非充当政党报刊或机关报,那么应可推断其打击“浊流”的表现乃至“专以纠政府之过失”的舆论参政是基于汪氏政治立场的主动选择,是对报刊舆论效力的一种运用,体现出汪康年在其“害马不去,良政不立”观点之下(汪诒年,2007:836、928、903),欲以舆论形成压力扫除政治改革障碍,影响政治格局的急迫意愿。
这一特征使《京报》与当时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革命派报刊之间出现了区隔。虽然报刊的“监督”职能已为同时期两派报人所认识与重视,但专以监督政府为参政途径的办报情形在当时则可属鲜见。被誉为“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知水平”的梁启超(陈力丹,2004:237),最为肯定报馆的“监督”功能,他的传播思想是:
以1899年为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报纸的传播功能,认为报纸是国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是开通维新变法风气的有力工具,主张办各种类型的报纸,后一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报纸的舆论机关作用和维新报纸的党报作用,肯定报纸的监督职能和向导职能。(方汉奇,2009:176)
在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7号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他将报馆“天职”归纳为“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方汉奇,2009:46),并认为报纸是舆论的代表,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一种舆论的监督(方汉奇,2009:176)。但在实践层面,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并不侧重于实现这种“监督”,其舆论参政重在“建言”。如其《时务报》言论重在提供维新变法构想,《新民丛报》的宗旨为“养吾人国家思想”,特别指出“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新民丛报,1902)。1907年创办的“政闻社”机关报《改论》,是本月刊,有演讲、论著、记载、社说等栏目,宗旨为“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以《国会论》、《政党论》、《国权论》等对立宪政治解释与设想的政论为主,并宣言“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罗福惠,2001:344)。同时期的革命派报刊在关于报纸性质和作用的论述中也涉及报纸的监督与向导作用,不过“在实践中,革命派更重视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夺取政权之前,对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并不寄予过高的期望”(方汉奇,2009:179)。20世纪初,“监督”作用也为另一些民间报刊所重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尤为突出,在立宪改制期间的言论亦随事指摘,不稍回避(吴廷俊,范龙,2002),发挥了“干政”影响,但它并不以介入“政治运作”为动机与目的,与《京报》主动的“舆论参政”仍有不同。
三、舆论参政何以实现
《京报》在“丁未政潮”中的“舆论参政”虽不免导致自身遭封禁的命运,但在特殊政治情境下,也取得了现实影响。作为一份希望以舆论之力“纠政府之过失”,从而实现参政目标的报纸来说,其“舆论参政”集中于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借报刊的监督之力介入政治运作,取得现实政治效应,对“报章监督”效力的充分运用是其最为突出的特色。
早在国人自办报刊第一次高潮初起之时,报刊的“监督”职能即多见于表述,如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创刊号上刊载《开设报馆议》一文,其中说,办报有“六利”,即:“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其中的“除舞弊”即舆论监督之效,这被认为是中国报刊史上首次提倡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方汉奇,李矗,2005:132),再如康有为“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康有为,2007:330),梁启超的报刊职能“监督与向导”说等等,不过,对于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实现监督效用的条件与方式,却少有详述,而《京报》言论恰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探究,这也形成了对舆论参政实现条件的认知。
第一,民主政治是监督的前提。1907年3月30日,在报纸发行的第三天,《京报》刊出题为《说机关报》的言论,申明报刊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指出所谓“机关报”非依附于政府、政党,“漫然为人指使”的报刊,而应是与政府、政党“志意相同”的独立报刊,其作用应是助政府沟通民意,其存在的前提在于民主,文中质疑“吾国今日,有此政府乎,有此政党乎”,若没有民主的政府与政党,则所谓“机关报”必为人所指使,“使吾为鹰,吾将捕雀,使吾为犬,吾将逐兔。”因此报刊监督应在民主政治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争取办报自由、言论自由是监督的保障。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其中规定,地方官吏有权封闭印刷所,由巡警部制定的《报章应守规则》又补充规定,新开报馆必须经过巡警所同意(徐培汀,裘正义,1994:209),时任两广总督的周馥认为广东地区民立报馆颇多,“辩言乱政”,又额外提出“限禁报馆”,规定报纸“禁毁谤国家”、“官绅军民贤否得失准其议论,但须叙明事迹,不可空言胜谤”、“凡激变生乱之语、鄙野秽亵之词,及涉诉讼未经判定之案妄加是非毁誉者,皆在所必禁;若涉叛逆不道有碍治安之事,即由官讯明拘究封闭”(广东省档案馆,1996:699)。对这一限制舆论的举动,《京报》4月19日刊载《论粤督限制报馆》提出质疑:(一)新开报馆允准与否,标准何在;(二)藩学臬三司,是否有限制报馆的权力,是否有甄别报馆的辩识力,为何掌控允准与否的权力;(三)既然不欲准许添设报馆,又何必以种种限制来作矫饰;(四)假如报馆欲获允准而讨好官场,那么这种报馆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清政府以言论封禁报刊的事件越来越多,其中1906年创刊于天津,1907年4月24日由天津迁奉天发刊的《通报》,出版未及三个月即因“有权者压制”遭封禁,奉天《通报》以“监督某国在东之横暴举动以警告我国民”为宗旨,其馆主孙颀感叹:“敝报对外之胆量虽有余,对内之势力则甚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4:203)。《京报》7月28日以《通报停闭感言》评论此事,将通报停闭原因归为“语言不慎,激怒官场所致”。评论讽刺“近来重臣之行事,足以慰吾民者绝鲜,而惟于封报馆一事,则勇为之”,假如官场动辄封报的原因在于对革命报刊活跃于海外的忌惮,那么封禁国内报刊并不是解决方式。文中提出,报刊舆论是“全国人之指南”,准许报纸各发言论,采其可用,宽其过失,则国之士气才有望养成。
第三,建立新闻法制才能促进监督。《京报》认为舆论监督是报刊应尽的责任,在国家处于乱局之时尤其应该勇于承担这一责任,但法制的缺失使报刊普遍回避风险,削弱了监督的力量。5月10日言论《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认为,当国家处于“累卵不足喻其危,沸釜不足比其惨”的情势之时,需要舆论刺激以使其“速警醒、速改革,扫尽旧态,力建新基”,但现实是报纸连“偶发一直言,讦一秽蹟,抨一宵人,乃一极细微不足指数之事”都不敢大胆作为,究其原因则在于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愤于时局”的言论犹如“当车之螳臂”、“撼树之蚍蜉”,不仅具有风险,且于现实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四,于京城之地多办报刊有利于加强监督效果。6月22日《论朝廷宜激厉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一文指出京师为“风动全国”之所,“正言至,则邪言日远,邪言至,则正言亦日远”,所以政府应“使四方之有怀欲陈者,悉趋而麕聚于京师,而上之于朝廷,使全国人心,皆以京遇为依归,而朝廷亦得听采之益”。不过,现实却是国人“未有敢以都城为事者也”,因为“偶有一二人焉,不顾一切,而欲以所愤懑,发为论议,贡之朝廷,语之切直,未及海内外各报十之一也。其揭发奸弊,未及实际千百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诬谤繁兴”。当天下“睽离怨疾”之时,政府仍以言论为罪,使言者惊惧骇怖,令来者望而却步,这样下去国家的命运实不可测。所以,“纵言论,释群疑”,鼓励京城报刊活动才是政府所应该做的。
第五,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应该受到监督。《京报》对“段、杨之事”的报道与评论,使奕等人“切齿腐心”,因此嗾使某些报刊指责《京报》“揭人阴私”,缺乏报德、报识,声言政界人士“馈仪物、赠婢妾”,不过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未产生社会影响,报纸不可对此过多报道、议论,否则即是侵害个人自由。
这涉及到报刊舆论行使监督作用的范围问题。6月15日《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中对这些“质疑”一一辩驳。言论首先明确,所谓政界人士“馈仪物、赠婢妾”之事,并非“个人私事”,而与社会大有关系。因为这些人握有权力,馈赠者目的无非是升官发财,这就使“国家之禄位,成为报施之具物”,“社会公共之政府,成为个人交际之私界”。假如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则求官者“惟有亏蚀国家之帑项,敲吸小民之脂膏”,甚至“举及外债”,而外债之取偿,“必许以特别之权利,是直卖国耳”。当权者接受了“馈赠”,则对任职者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甚至“终也明知其放弃职守,甚至贪赃罔法,亦必设法包庇以留彼我馀地”,所以说,普通人有“私德之失”,报章可以不加干涉,但政界人士则只能有“守法的自由”,如果报纸对此绝口不提,那又何谈“监督政府”、“谋求社会公益”。
第六,报刊舆论同样应受到约束。《京报》并不认为报刊监督作用的发挥是无限制、无约束的,如果滥用这项权力,同样会造成恶果。6月21日《论报章之监督》在肯定“清议于必宣之报”的同时,指出报刊在发挥监督作用时,也需要接受政府与社会的监督,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凡奸慝佥壬,皆得借以济其所欲”,“借社会之力,以成己之所志,而去己之所忌”的现象,导致报纸沦为私器,“指鹿为马,反黑为白”,结果大乱听闻。
《京报》遭到封禁的消息传出,“海内志士成为悼叹”,身在湖北的汪康年密友梁鼎芬甚至发出“发指皆裂,心伤涕零”的哀叹(汪诒年,2007:139),其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可见一斑。《京报》对“舆论参政”的理解与运用,呈现出近代知识阶层报人参政救国的迫切愿望,以及在这一迫切愿望下所做出的特殊选择。
注释:
①据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一章所记:1883年汪康年进京求助四伯父时,曾拜访过时任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尚书的王文韶,王与汪为同乡,与汪父为乡试同年,且汪康年时为王文韶外甥的家庭教师,故汪与王结交,而瞿鸿禨为王文韶的学生,汪与瞿很可能在王文韶座中就已结识。瞿对汪一直特别赏识,在汪考中举人时“喜溢颜色”,汪则终身称其为老师。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②指“丁未政潮”中“杨翠喜”与“段芝贵”两大事件。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京报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时务报论文; 奕劻论文; 瞿鸿秙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