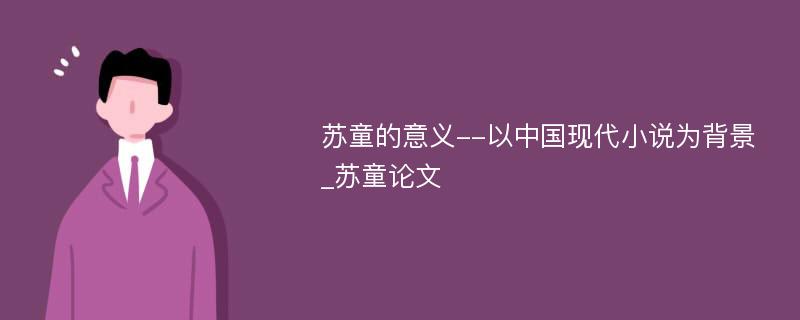
苏童的意义——以中国现代小说为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意义论文,背景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与苏童文学年龄差不多的作家中,像苏童这样一直保持着对短篇小说的热情的人实在罕见。写作短篇是苏童维系创作的缆绳,以至成为他的日常生活。苏童说:“我写短篇小说能够最充分地享受写作,与写作中长篇作品相比较,短篇给予我精神上的享受最多。”①从一九八三年发表《第八个是铜像》,或者从一九八四年发表他自认为“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②《桑园留念》算起,苏童迄今已发表了一百五六十篇短篇,这是相当惊人的。本文拟就苏童短篇小说谈一谈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发展上的一些问题,进而借以揭示苏童短篇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被认为是有短篇创作传统的国家,至少到魏晋南北朝已经有了志人志怪的短篇形制。其后从语体上讲,短篇一直以白话和文言这两个载体平行演进,各自产生了话本小说和《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这两个传统到近代开始发生变化,可以梁启超等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加上西方小说的翻译,报纸刊物这样的新兴媒体的出现,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大变革的发生,短篇小说从目的、功能、文体特征都不得不发生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它不再是消闲,不再是时代背景不明的一味的“从前”与“前朝”的传奇故事,而是贴紧时代与社会,在故事情节之外开始注意到情境的营造,叙事节奏、视角与时空结构也较过去有了变化。以前人们对晚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意义似乎不怎么看重,其实夸张一点说,它给其后中国二十世纪短篇小说的发展培育了成长的基因。对短篇小说,胡适与鲁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胡适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③所谓“横断面”是他的说法。鲁迅则认为短篇小说“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有存在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炫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④。这些都是奠基性的观点。中国现代短篇在二十世纪初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外观上也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并且大规模地发展而成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样式。
那么,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什么?首先是它与时代的共生关系,它将目光聚焦当下眼前,并且时时努力以小说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当中去。中国现代短篇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沈从文、艾芜、张天翼等人的创作都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即使像废名,也有如《莫须有先生传》这种正面接触现实的作品,而张爱玲以及新感觉派小说家对都市的描绘,对变化着时代风气与心理的把握,可以说与现实贴得很紧的。这种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一点更是得到了功利主义的强调。茅盾在《试谈短篇小说》中就说:“今天我们正需要各种各样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来及时地迅速地反映我国的大跃进的步伐,在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的方针下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⑤“十七年”文学期间,赵树理、康濯、周立波、李准、王汶石、茹志鹃等人的创作无不努力在追踪变化着的“新”的现实。即使到了“文革”结束,从表面上看,这时的短篇小说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有了大的变化,但在本质上依然保持着与现实同步甚至企图引领时代的姿态,从所谓“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命名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文学的取向,当时的短篇小说名篇《伤痕》、《班主任》、《顶凌下种》、《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等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指向。其次,就是短篇小说的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短篇小说开始更新换代,与创作一同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对短篇小说的接受、审美上的新的认同与理论话语的转换。茅盾在《小说研究ABC凡例》中认为,“小说的要素比较普通的说法,单以结构,人物,环境,三者为止”⑥。从何穆森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当时许多国外小说包括卡夫卡、沃尔芙已经被翻译或进入了中国文学界的视野,但人们对短篇小说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人物的性格之发展”、如何“借着形态的限制获取最大的效果,并把捉短篇的特质,用以表现人生”。所以,都德、爱伦·坡、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成为短篇的审美典范,而“惊异”,类似中国“戏曲”的倾向,“某种性格在某个瞬间的心理状态,以及某个行动发生前后的情状,或是写出静止的所谓一瞬间的心理状态”等“话术”渐渐成为短篇可以把握的通常性的手段⑦。胡怀琛将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从八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其中有“结构却不可不缜密,绝对不可松懈”,“注意于人物描写的逼真和环境与人物配置的适宜”⑧等等。总之,在有限的篇幅表现“无限”的社会人生这个过程与目标中,短篇小说的一些要素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明晰。老舍在指导如何写小说时说“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短篇小说的要素已经越来越清晰明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茅盾就短篇的创作进行过大量的论述,特别是他对当时许多短篇小说作品优劣的分析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但给创作树立了具体的目标,而且给读者评判树立了具体的标准,给读者评判鉴赏短篇小说提供了范例。概括起来说,除了所谓在内容上要贴近时代、反映重大问题以外,茅盾对短篇小说的要求有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要短,他对“一些太长的起码万言的短篇小说”常常提出批评,认为“为了多快好省的省,我以为作品也应当可以短则短”⑩。第二是要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认为五十年代末短篇小说的收获就是塑造了许多新人形象:“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女子,在我们这个灿烂沸腾的跃进时代所起的巨大作用,文学方面有了怎样值得赞美的反映。如果把这些新人的形象和两年前的人物形象作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两年来我们的进展是显著的。”(11)第三是故事与情节结构。他在称赞沙汀的《你追我赶》时说它“从容挥洒,全篇故事的发展层次分明,前后呼应,波澜迭起;写人写事写景都有鸟瞰式的全景,也有特写镜头——一句话,就是通篇结构既严整而又灵活。”(12)第四是环境。“短篇小说中的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描写必须为主题服务”,比如小说里的风景“不是为风景而写风景,即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渲染或衬托故事发生时的气氛,或者为了加强故事发生时人物的情绪”(13)。第五是细节描写。创作目的要“创造性地从合情合理的细节描写达到”。在许多地方,情节、人物、环境都是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的,他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地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14)可以看得出,茅盾对短篇小说的这些理解是建立在欧洲写实主义短篇小说传统之上的,给青年作家讲短篇,他喜欢举的例子也是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而在理论表述上显然受到了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当时的主流,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是如此。如同时期影响很大的由著名作家与评论家靳以群主编的大学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就认为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细致而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性格;生动而完整地叙述故事情节;充分、多方面地展现人物活动的环境”。这就是后来几乎成为定律的“小说三要素”,短篇小说自然必须具备,只不过是因为“容量小,篇幅短”,“人物不宜多,情节、场景要求集中紧凑,线索不能太复杂”而已,但“仍然可以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或主要人物某一阶段的经历、遭遇,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典型来,形象地提出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某一重大的问题”(15)。这就是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主流表述,也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概括,同时还可以理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鉴赏的短篇趣味与审美标准。“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史固然如此,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短篇史虽然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占主导地位的也是它们,这可以从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短篇小说奖与九十年代开始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见出一个侧面。其入选作品大都是依据的上述理念,即以最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的评选结果看,除了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外,其余作品在现实的指向、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传奇性展开上都暗合了这一强大的传统。
这就是苏童从开始创作一直到如今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种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足以使每一个写作者感到压力,甚至干脆放弃抵抗。为什么评论界对苏童经常有回归写实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苏童创作中对这种传统或现实的妥协。以新世纪以来苏童的短篇为例,就有《白雪猪头》、《人民的鱼》这样的作品。《白雪猪头》虽然没有明确地交待故事的时代背景,但是从后来视点的转换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这个童年的故事发生在物质极度贫困的七十年代。母亲至少生了四男一女五个孩子,但常常因为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食欲、不能让孩子吃上一顿肉而苦恼,她最大的愿望是能让孩子吃上一顿猪头肉。故事就是从母亲凌晨到肉铺排队买猪头开始的,母亲没买到,便怀疑是店员张云兰私藏了猪头,与她赌了气。但为了孩子能吃上肉,母亲又不得不央求邻居帮忙从中调解,不惜起早贪黑以自己缝纫这一技之长为张云兰赶了五条裤子,希望能感动张云兰为自己买到猪头。然而当五条裤子做好后,张云兰却从肉铺调到了卤菜店!正当一家人已经绝了望死了心过一个清汤寡水年的时候,张云兰却在雪后的清晨提着两只大猪头送到了“我”家,还顺带给孩子们送来了奢侈的“尼龙袜”。小说首先要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它的故事性,以意象见长的苏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起于日常生活的简单而复杂的故事,总能使情节在柳暗处闪现出明亮的花朵,充满了戏剧性。故事一开始就让母亲与张云兰吵上了,吵得不知如何收拾时却由见喜的母亲出面让母亲罢场而去,好像不再指望这对冤家还能沟通时又由邻居从中撮合;而当因张云兰调动工作因而对猪头彻底绝望时,张云兰又被安排踏雪提着猪头上了门,可谓一波三折。这当中,母亲的形象与性格刻画是最为鲜明的,善良、狡黠、勤劳,处处透着城市普通市民盘算日子的精细与无奈,而这种性格无疑具有特定时代与阶层的特性。以母亲为中心,小说编织了一个女性社会网形成作品的小环境,特别是母亲与张云兰吵架时众人的“拉偏架”,明显地透出市侩的风气。再如《人民的鱼》,讲述的也是邻居间的故事。干部居林生每到过年过节就有人给他家送鱼,其妻柳月芳为处理这些鱼而伤透了脑筋,热心的邻居张慧琴过来帮忙,柳月芳便将自己家不爱吃的鱼头送给张慧琴。后来,不时兴送鱼了,居林生一家也失意了,两家也渐渐少了往来。后来张慧琴的儿子做起了个体,开了鱼头馆,生意越做越红火。日子好起来的张慧琴一定要邀请柳月芳一家来吃鱼头宴,而且竟真的让柳家破了例,并且喜欢上了鱼头。小说由柳、张两条线交错向前,有分有合,起伏跌宕,充满了喜剧色彩。由“鱼头被鄙视到被器重的变化,写出两家人命运的变化,一家当初穷得只能吃鱼头,如今开了鱼头连锁店,一家原是趾高气扬的食品公司的小科员,如今落寞得不得不接受当初他施舍人家鱼头的店主的施舍……世道人情,社会变迁,尽在不言之中”(16)。这样的一些作品是完全可以与传统的小说经典媲美的。
但是,这样的作品在苏童的短篇中并不占主导的位置。苏童说《桑园留念》是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小说,其实放在苏童大量的短篇中,这个四千多字的短章并不起眼,但是它标志着苏童对短篇看法的形成,意味着苏童经过阅读、思考、蜕变、化蛹成蝶后可以开始属于他的一种“新”的短篇创作了。小说采取童年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将人们带入历史的现场,几个男孩与女孩,经历着青春与前青春期的冲动、渴望与冒险。故事被有限的视角遮蔽与掐断了,焦距变虚了,使得写实转成朦胧的意象,“形象”意义上的人物,“情节”意义上的故事,“环境”意义上的社会背景都淡化了,人的欲望、人的成长与死亡这些抽象的探究以及淡淡的忧伤,这种诗意的氛围取代了明确的主题。现在看来,不管是否幼稚,它确实在苏童创作中具有标志性,为苏童至今的二十几年的短篇写作定下了调子。这篇小说写于有意味的一九八四年,中国文学正从伤痕、反思、改革进入轰轰烈烈的先锋时期。对苏童写作发生学,我曾这样作过概括:“苏童是中国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学习,那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肇始期,中国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而思想界与文学界更是得风气之先。从文学渊源上知识谱系上看,苏童以及他的同龄人大体上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较少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新中国‘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的束缚,他们有着宽阔的胸襟,民主的意识,认同人类普达的价值观,因此更能便捷地与他民族进行文明的对话。”(17)同样在新时期开始文学写作,苏童与复出的作家、知青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当苏童开始系统进行文学阅读与创作准备时,正值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它成了苏童第一的文学课堂。二十年后,苏童编选《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18),其入选作家除了契诃夫与莫泊桑外,大部分作家都是我们传统文学教育中陌生的,这份名单非常值得研究,它多少说明了苏童短篇的一些师承与渊源。与这样的文学阅读与准备同时发生的是外部文学环境与文学观念的变化。继八十年代初文学工具论的讨论之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文学的属性与功能的讨论,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许多观点与思想注定要对中国文学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如对文学就是人学的重新审视,文学的“向内转”以及对“文学性”的认识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苏童短篇创作的阐释背景。正是在这些文学观念的作用下,文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文学与现实的距离也发生了变化,夸张地说,文以载道,从梁启超开始的赋予新小说的“新一国之民”、“改良群治”(19)的使命被相当一部分作家卸下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的现实主义文学定律也受到了质疑。所以,我们看到了与前面茅盾的表述不同的另一种文学观念。苏童认为将小说与外部社会现实相联系是一种误会,“小说因为用语言说话,它必须记载社会事件、人际关系等,这就引起了歧义”,而“那种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对它的拯救灵魂、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夸大,淹没和扭曲了小说的美学功能”(20)。他十分警惕作品中人物的社会身份将写作引向歧途的可能,比如当有人说他喜欢写“小人物”,写“底层”时,他几乎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我小说中的人物鲜有阶层标志,也就是说我从未刻意写某一个阶层的生活,至于生活在香椿树街的人们他们肯定是小人物,所谓人小物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关心柴米油盐胜过政治、艺术和新闻,他们不考虑生活的意义而只关心怎么活下去。”(21)在此,苏童从主题学的层面上将他的短篇与人们眼中习惯了的经典做了区别,他反复说明他关心的是人,但这里的“人”显然与传统文学中粘连于现实环境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因此,他们所面临与需要解决的也就不可能是一般社会学意义的事件,而是他们意识到或未曾意识到的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限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可以随机举出几篇来感受一下苏童人物的孤独,比如《樱桃》、《西窗》、《水鬼》、《骑兵》、《手》、《哭泣的耳朵》、《白杨与白杨》、《点心》、《五月回家》、《桥上的疯妈妈》等等。苏童自述,《樱桃》是从一个朋友处听来的鬼故事,只不过将原故事中的两个男的变成了一男一女,从而使叙事多了一层引而不发的意味,也因为苏童擅于女性的书写,使叙述更为凄艳。小说叙述邮递员尹树在他邮路上的一个医院的废置的门口遇到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天天等信,可天天无信,直到有一天她对尹树说其实并不是等信,等的是他,是与他的交谈。尹树给了她一块手帕并答应去病房看她,而当尹树如约而至时,才知道这个病区早已改成太平间,叫白樱桃的女病人是一具长时间无人认领的尸体。当我们在小说的前面读到白樱桃苦等亲朋的来信而无果时,感受到的是人物的孤独、凄楚与绝望,而联系到叙事人对尹树的描写,到了小说的后面,我们体会到的是尹树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以及由这种孤独而生的幻想与谵妄。小说看上去将注意点放在樱桃身上,其实尹树才是作者真正关注的存在,甚至这场意外的遭遇可能就是尹树的幻象与白日梦。再看《骑兵》,小男孩左林是个罗圈腿,因此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他也无法融入到群体的生活中,“左林不喜欢体育课,不喜欢团体操,不喜欢军训,可我们的学生时代几乎就忙着做那些事了”。这样的境遇使左林心生狂想,他竟然如人们嘲笑的罗圈腿该去当骑兵一样真的要当一名骑兵了,这种妄想不但使他白日梦一样看到了狂奔的“白色的长鬃骏马”,更使他发狂地要在别人身上体验骑兵的快感,而最后的结局却使他由骑手变成别人胯下的坐骑。小说通过情境的设置将人物的孤独与对孤独的反抗推向了极致。还有《桥上的疯妈妈》,“疯妈妈穿着白丝绒旗袍,手执一把檀香扇,仪态万方地站在桥头”,可谁会理会一个疯子呢?她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臆想中,生活在不为人知的但却通过旗袍、胸针、檀香扇可以猜想的过去的时光里。我们可以将作品中疯妈妈胸针与旗袍上纽扣的丢失理解成对她的伤害,但她却无法抗拒,抗拒的结局只能是将她送到疯人院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感受到苏童对一些看似日常却是非常情境的设计,看到他建立在隐喻与象征上对人的伤痛、残缺与病态的描写。他们可能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沟通而心生妄想(《水鬼》),可能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交流(《白杨与白杨》),可能心有许多的善意却终究无人能解(《点心》),受了伤害却无处诉说,诉说只能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西窗》),也可能因为某种身份而遭到永远的排斥(《手》),更可能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五月回家》),或为亲人与朋友所排拒而只能永远在路上(《一个朋友在路上》)……苏童有一篇小说《门》,主人公是毛头女人,因为丈夫毛头经常在外,独居的毛头女人对楼上的住户老史有了情感上的期待,于是每晚她都虚掩门扉,但老史却一直没有过来。终于有一天,门被推开了,但进来的却是小偷。毛头女人本来等待的是美好,结果等来的却是丑恶,她只能将自己吊死在门上,她以这种方式关闭了通向世界的门。小说到此有一交待,老史竟然是一性无能者,这是毛头女人到死都没有想到的。这个世界不仅缺少爱,从根本上就没有爱的能力,这才是一切孤独者最根本的绝望。不仅是孤独,在苏童的作品中,人们经常感受到的还有隔膜、误解、绝望、欺骗、伤害或死亡。苏童非常钦佩卡弗,阅读苏童的作品,确实时时让我想到卡弗这位美国短篇大师的一些话:“我们能确切地记起失望和绝望的构造,我能尝到它的滋味儿并且感觉到它的存在。”“我的作品中世界对许多人来讲是个很具威胁的地方。我所选择写作的人物对象的确感到威胁存在;我认为许多人感到这世界是个很具威胁的地方……假如你改变生活道路的话,威胁就存在,而且看得见,摸得着。”(22)
这么说并不是说苏童的短篇永远是一种冷色,其实,当世界存在孤独、伤害、威胁和死亡时,它的另一极就已经存在,而这恰好也是苏童小说的构成,只不过这两极呈现着严重的不平衡罢了。但我们毕竟在《樱花》中感到了美丽与片刻的欢娱,在《骑兵》中有沉浸于白日梦的辉煌,在《点心》中有着一厢情愿的幸福,当然,更典型的是《二重唱》、《小偷》这样的作品。《二重唱》只写了都市出租车载客的短暂旅程,作品中有两个人物,出租车司机与醉汉,一个清醒,一个糊涂,一个心存美好的念头,一心想能载到酒店漂亮的女服务生,一个则是背运的,被抛弃的倒霉蛋,小说以看上去啰嗦的语调,反复叙述两个人物纠缠不清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但是这南辕北辙的两个人渐渐合拍了,以两个声部演奏起了共同的旋律。小说的最后,醉汉安静了,司机也从失望、赌气、恶作剧中走了出来,他们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对方,在新年将到的深夜,他们拿起了钟槌,一起将各自的愿望融进了钟声。这无疑是一个让人安静,给人温暖与希望的作品。《小偷》写小镇上的两个孩子,郁勇和谭峰。谭峰经常偷盗别人家的东西,他偷到的最心爱的东西是一辆精美的小火车,谭峰谁也不说,只与郁勇玩并告诉了郁勇藏匿的地点,而郁勇竟鬼使神差地将此事告诉了失主,当铁匠的父亲竟然用烧红的烙铁惩罚了当了“小偷”的谭峰。后来这辆谭峰宁死也不肯交出的小火车竟然被郁勇找到并隐匿了起来,这当然让谭峰愤怒与伤心不已,以致两个小朋友反目成仇。然而当郁勇随父母调动要去往异地时,谭峰却将小火车发条的钥匙悄悄交给了郁勇。这个故事自然也涉及到阴谋与伤害,但正如苏童自己所说,这把钥匙所含的“那份情感,包括我在内都非常感动,洋溢在其中的关于少年人与成年人世界的对抗,和这么一个小镇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的空间感,它带来的两个孩子之间心灵的互相依赖、互相依靠,我觉得都是非常感人的”(23)。不管是哪一极,苏童的短篇从语义学的角度讲就是他的超越性,因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想方设法使作品能挣脱题材的有限空间进入精神的无限,从对具体的人事上达到对生存的感悟。当苏童面对历史时,他的工作是使历史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成为一种符号,他关注的是人,人性。为什么苏童喜欢过去的生活场景,习惯使用童年视角与回忆的叙述方式,就在于可以拉开距离,使作品成为一种过去的静物,既脱离了彼时的羁绊又不可能进入当下的情境,从而更为方便地将其中的意味呈现出来,也更容易展开想象。相比较而言,现实题材就较为困难一些,苏童自己就深有体会,“当下题材的危险性在于具有真实感,人人都会可能有体验。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满足读者的认知程度,那就是失败的,作家应该远远超出别人对此的认知”(24)。苏童早期的短篇多写少年时期的生活,如“少年血”系列,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又多实验之作,如《仪式的完成》、《祭奠红马》等,在超越性上确实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多了现实的甚至当下的题材,这既显示出苏童艺术上的自信,但也确实在超越性上多少显得不太平衡了。
相对而言,辨析苏童短篇小说主题学与语义学上与传统小说旨趣的异质性可能方便一些,而要从小说的技术层面、审美范畴、艺术标准上进行指认则要困难得多。历史上经典的短篇小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积淀与品化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和被公认的审美标准,并且在阅读上也具备了强大的审美惯性。依照如茅盾阐述的那些标准,小说的优劣好坏是很容易判别的,只要细读茅盾那些年所作的短篇评论,可以发现他判断的迅速、肯定与自信,但是,现代短篇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概念运用上的困难,为了说明苏童小说的作为后来者的异质性,我们不得不使用“传统”、“经典”、“现代”这些词汇,其实,即使在传统中,也有与“传统”不一样的另一些短篇风格,正如在目前的短篇创作中,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已经是现代小说的一统天下。这种状况同样存在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中。自从十八世纪短篇小说从早期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与民间传说中脱胎出来经过安德森、爱伦·坡、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等改造后就相对定型了。十九世纪现代小说兴起并形成新的传统后,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在两种传统中发展的。只不过在中国,情形更为复杂而已。现代短篇小说的新传统始终得不到广泛的全面的认同,这一半有时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与遮蔽了。关于这个问题,陈思和以鲁迅为例作过论述,他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就呈现为两种形态,两个传统,“既有对西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的借鉴和继承,如《夜》、《风波》、《祝福》等;也有对前者的解构”,他称这一类根植于现代文化与个人性的作品为“诗性小说”或“精神小说”,如《白光》、《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但是,“短篇小说的新审美形态自鲁迅就开始创立了,但长久以来被小说文论研究者们所忽视,没有从《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等作品中提升出反故事的叙事特征。这些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品所呈现的审美形态与通常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使命感要求的并不一样,可以说是拥有了一种在西方文学里只有长篇小说里才可能有的神性与诗性”(25)。如果说这条线从鲁迅始,间或在沈从文、废名身上有过停留,那么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有规模地被中国作家所实践。而苏童是从那时起至今未曾中断、满腔热忱、孜孜以求且成就卓然者,这也是本文选择从文学史角度,从中国现代短篇发展史的层面论述苏童短篇意义的原因。
批评家们对苏童的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大体将它定在南方的风格与唯美精致的叙述上,并从人称、意象、语言等方面进行过许多详细的描述,这些都有道理;但是这些是不是他短篇本质性的地方,甚至与短篇这种文体的关系都不大能说得清楚。我们以为苏童的短篇形态除了前面详细论述过的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摆脱社会功利话语的束缚,从现代性意义上探究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精神困境这一重要方面以外,还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的实验性与叛逆性。不少评论家将苏童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苏童对此是有保留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也好,先锋也好,都是有规定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文学,而苏童的短篇则是一种否定性的文学行为,与其说它是什么,不如说它不是什么,这使它与传统、与当代短篇小说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短篇小说很难用一种形态去描述,一直在变化之中,从外在叙事形式上讲,它们之间并不是在相互认同,而可能是相互对比,相互否定,比如既有神话形式的《拾婴记》,也有写实性相当强的《私宴》、《堂兄弟》,还有抽象的、后现代式的《祭奠红马》。其次是对传统戏剧性叙事方式的解构与颠覆,苏童的小说叙事大都是连贯的,甚至是完整的,但是却并不追求传奇与戏剧化,苏童明确地说他不喜欢欧·亨利,也不喜欢《项链》这样的作品,原因就是太戏剧化了。戏剧化是建立在世俗性的基础上的,它将注意力牢牢地锁定在“事件”上,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非现代性的。第三就是氛围的营造。苏童的短篇既不去刻画什么展开人物,也不依靠戏剧化的情节,那么它的精神追求靠什么去完成呢?靠氛围,苏童不去讲故事,但他是一个善于叙述的作家,有相当的自信,会通过看似平淡的故事,似断非断的场景,出入自由的叙事人的评价和散文与诗化的渲染慢慢地向目标接近,最终完成于一种情绪、色彩、调子与感觉之中。读者也许会有一种人物不过如此,事件不过如此的感觉,但却会在不自觉中跟着叙事人走,进入他的思路,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是有冷暖、轻重、强弱、明暗、粗细、厚薄、新旧之别的,而这正是进入小说内部进行深度思考的动力。第四就是简单性。这与苏童的反戏剧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戏剧化,小说必须繁复、叠加、层层推进或转折,做的是加法,而苏童做的是减法。苏童的减法是多方面的,他削减了对社会背景的交待,对人物性格成长的介绍,对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设置,对故事的各个环节更是自由取舍。与人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苏童对实验小说推崇备至的叙事形式采取的也是减法,苏童的小说大都是简洁的顺时叙事,很少人为去设计“叙事的迷宫”,由回忆产生的时间的变化,由讲叙人与故事本体的转述与呈现产生的人称上的变化在苏童这里已经是相当突出的叙事形式特征了。除此,似乎很难指认出苏童还有哪些属于他的具体的风格化的技法。事实上,正如陈思和指出的:“诗性不是技巧,精神性也不是技巧,小说批评过多地探讨小说的修辞、技巧、结构等要素时恰恰疏忽了:精神性的因素是无法用定量与技术来达到的。”(26)在苏童那里,小说家应该能让人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常常忘记牵引我们的是一种个人的创造力,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曙色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就这样,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这就是虚构的魅力,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27)。我们确实在理论上还不能给苏童的短篇小说从审美形态上予以概括,但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建立在现代短篇传统上的“新”小说。这就是苏童短篇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的现代小说还在发展,虽有苏童这样的作家,但要从根本上完成转型尚需时日,这么说并不是说传统就是旧的是应该舍弃的,相反,从文学多样化的角度讲,任何类型的文学都应该存在,哪怕是再古老的艺术。然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文化环境而言,现代小说实在面临太多的困难,一方面,主流话语以强大的权力使得传统小说依然站在主导的位置,另一方面市场又在催生类似于通俗故事的作品,短篇小说如何参与到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建中去,又怎么能担当此重任是相当严峻的问题。
最后,引用一段苏童的话,不管它是否与本文有关:“我想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和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却只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28)
二○○八年,中秋,龙凤花园
注释:
①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②苏童:《纸上的美女》,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③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④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⑤茅盾:《试谈短篇小说》,《文学青年》1958年8月号。
⑥⑩茅盾:《小说研究ABC》,《文学青年》1958年8月号。
⑦何穆森:《短篇小说的特质》,《新中华》1933年12月10日。
⑧胡怀琛:《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正中书局,1934。
⑨老舍:《怎样写小说》,《文史杂志》1941年8月15日。
(11)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1959年2月号。
(12)茅盾:《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年第5期。
(13)茅盾:《试谈短篇小说》,《文学青年》1958年8月号。
(14)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
(15)靳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下),第398、39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6)王干:《三十年短篇小说艺术创作轨迹回顾》,《文艺报》2008年7月24日。
(17)何平、汪政编:《苏童研究资料·后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8)苏童编:《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入选的小说家为马里奥·贝内德蒂、君特·格拉斯、艾丽丝·门罗、伊弗林·沃、维克多·普里切特、迪诺·布扎蒂、诺尔·夏特莱、弗兰茨·卡夫卡、约翰·契弗、胡安·鲁尔弗、卡森·麦卡勒斯、纳撒尼尔·霜桑、安东·契诃夫、居伊·德·莫泊桑、艾萨克·辛格、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豪尔斯·博尔赫斯、杜鲁门·卡波特、雷蒙德·卡弗。
(1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20)林舟、苏童:《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0期。
(21)苏童、王雪瑛:《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22)雷蒙·卡弗:《雷蒙·卡弗访谈录》,《外国文艺》1997年第3期。
(23)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24)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25)陈思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小说评论》2000年第1期。
(26)陈思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小说评论》2000年第1期。
(27)(28)苏童:《虚构的热情》,《虚构的热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