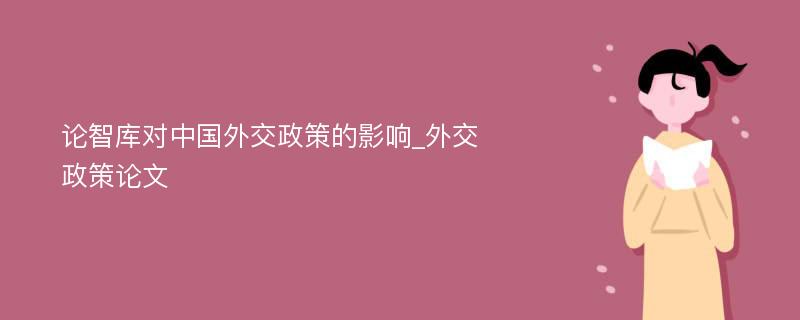
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常常被忽视;而关于思想库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问题,也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的外交决策基本是一种“黑箱”运作,外界很难窥其真相。故本文并不试图考证某些思想库或其成员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案例,也不打算对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影响力作定量分析;而是从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入手,先对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进行解析,看思想库在其中的静态位置;再从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周期角度,将其放入外交决策的进程中去动态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思想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种种具体方式,以期对其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和功能有较为客观的认识。①
一、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看思想库在其中的静态位置
要分析思想库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认识中国外交的决策体制;而要研究中国的外交决策体制,则需要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权力结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以中央为核心的“6+1+2”体系。“6”是指通常所说的“六大领导班子”,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含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是指国家主席;“2”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中枢的“党”、“政”、“军”、“法”四大方面,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就是这四大方面的展开及其相互关系。②同时,为了对整个国家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把这四个系统的不同部门按功能分为六个“口”,即军事口、外事口、财经口、政法口、人事口、宣传口等,以便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其进行归口管理。③
具体到“外事口”,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对中国的整个外交工作进行领导。实际上,如果把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比作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概可以把这个金字塔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最高层是中央领导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以及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中央外办;中间一层是主要的政府外事机构,包括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国防科工委、台办、港澳办、侨办、新华社、中联部、总参等与外事相关的重要部委,其下通常会附属一些起咨询和调研作用的政策研究机构,这就是所谓的外交思想库,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金字塔的底层是地方外事机构,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级的外事办公室。④
从各自的分工来看,处于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是外交决策权力的核心,在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上占有决定性地位(这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央负责处理外交的主要办事机构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通常,重大议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决策,而中央军委则在涉及军事安全的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多数跨党政军系统的重要政策议题则会在外事领导小组中先行讨论,形成初步政策选项,再供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中间一级的决策单位,主要负责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些重要的部委如外交部、商务部等承担了分工各异的工作。具体来说,外交部负责总体外交政策的解释、协调和把握;商务部主要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等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国防部与国安部则在与外交密切相关的军事安全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最重要机构;总参负责驻外武官的筛选、监督和对外军事方面的交往;新华社是中央领导信息的重要来源,起着决策者眼睛和耳朵的作用。⑤
需要指出的是,在提供外交决策参考的机构方面,各系统几乎都有各自外事方面的思想库。如党的系统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等;国务院系统下属的思想库最多:有直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直属国务院的中国社科院(国际片)、新华社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育部下属各高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等;属于军方的思想库则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等。
从以上整个外交机构的职能和角色可以看出,各有关部委单位既独立承担各自的任务,又互相协调合作,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外交思想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周期看思想库的动态作用
一般来说,公众所感知的中国外交政策,通常只会看到政府(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外事职能机构)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直接性作用,这也是传统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的特点:较多关注政策的结果和内容,而较少关注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方式。实际上,按照美国著名外交政策研究学者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F.Hermann)的理论,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周期应当包括:(1)设定议题或任务(problem/task recognition);(2)政策选项的制定(problem and option definition);(3)政策的选择(advocacy of options);(4)政策的执行(implementation);(5)政策的评估(evaluation)等五个阶段。⑥在这个长期的政策制定周期中,政府是外交政策的“直接决策者”,而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还有其他各种政治力量,如议会、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共舆论和思想库等。因此,如果我们以此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将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延伸得更远一些,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周期来看,则可能对中国外交思想库的作用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1.设定议题或任务
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始于决定什么事情需要做出决策。确定或者界定要决策的问题,即设定议事日程,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第一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内外问题非常多,轻重缓急各不相同:有的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非根本性的;有的是整体性的,有的则是局部性的;有的是短期的,有的则是长期的。而不断变化着的国内外环境,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使某些问题变得突出,取代其他问题或改变各种问题的优先次序。如此千头万绪,把哪些问题提上决策议程,便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又要考虑到公共舆论的支持。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对于国际事务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讨论、酝酿初步反应、界定国家利益和区分外交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其决策的程序比较难以观察,但我们仍可以通过某些公开的信息来反向分析这一过程。这里仅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该项目可谓是中国社科研究领域层次最高、权威性最强的科研活动,每年所出版的“课题指南”往往可以看做是政府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的“风向标”。200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出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课题建议共有34项,其中除8项基础研究之外,其余的全是应用对策方面的研究,包括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及我国对策研究、我国能源安全与石油战略储备问题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相关问题研究和朝鲜、伊朗核危机与核不扩散条约机制面临的挑战及我国对策研究等一系列与中国当前外交事务密切相关的国际问题。⑦这些课题都是各大思想库尤其是高校系统外交思想库竞相争夺的目标。⑧
此外,在本阶段,各国传统上只有政府首脑和相关的外事职能部门会参与确定政策议题的制定。但近年来的趋势表明,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思想库、媒体、利益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政策讨论阶段。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政策讨论的参与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一般说来,较多方面参与政策讨论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决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⑨现在,中国的外交思想库也经常会做一些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协助决策者发现问题,确定政策目标,这样就会在第一阶段介入决策进程。
2.政策选项的制定
上层的所思所想被传达到各政策研究机构和思想库之后,政策制定的过程便拉开了序幕。这一阶段也是各思想库“大展拳脚”、发挥作用和功能的主要阶段。在中国,有关外交事务方面的思想库有不少,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这些思想库和政策研究组织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根据政府所确定的问题,收集有关的情报信息,作出定量或定性的分析,设计出多种政策方案,供决策者进行参考。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面临着一些过去很少碰到的新问题,比如国际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环境保护、金融安全等等,这些领域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是任何个人的知识、智慧和经验都无法包容的,因而必须借助于外部的智力,通过各相关领域的专门人员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来弥补决策者智力的不足,从而使政府作出更为客观和正确的决策。
过去,中国思想库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并不大,但改革开放以后它们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并且正逐步形成某种“机制化”。2004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文件,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一位中国著名思想库的领导人也指出:“中央政府现在非常重视智库建设和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建立起多条官方与智库的咨询对话机制,重大决策之前基本上都会反复听取不同智库、学者的意见。决策‘拍脑袋’的时代已经过去,广泛的决策机制正在建立。剧变的中国面临许多复杂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智库发挥作用。”⑩
3.政策的选择
在本阶段,政府将对各种政策方案进行权衡,作出最佳选择。过去,有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只考虑直接目标而作出单一的决策,但这已日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决策前强调提供客观、全面和多样的政策选项,陈述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有的国家由外交部门提供备选政策,有的国家则由跨部门机构提供,后者的优点在于备选政策相对平衡和全面。一般说来,备选政策要经过好几个层次的筛选,最后才能送至最高决策者。外交政策因其重要性而由不同的决策者作出最后决断。(11)
这种趋势仍可从2007年度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立项的结果上看出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蔡春林的“国际贸易摩擦新问题及我国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王厚双的“国际贸易摩擦的产生机理、影响与对策研究”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刘海云的“国际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等三个类似课题最终被批准立项。这一方面可见政府对于当前中国所面临贸易摩擦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决策的多元化选择。
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作出最终的选择之后,政策的制定流程就进入到执行阶段。在本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机构如外交部、商务部等负责将具体的政策贯彻实施,这也是媒体和舆论最为关注的一个阶段。最后,作为政策制定周期的最后一步,政策评估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评估和反馈可以确定新的问题,并在下次过程中进行修补。由于本文主要探讨思想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故对政策制定周期的后两个阶段不作详细阐述。
三、思想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方式
由以上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周期分析可以看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尤其是第二个阶段的“政策选项的制定”过程中。(12)由于思想库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媒体和公众的视线之外做的,所以它比其他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所引起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它对中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具体来说,思想库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思想库的专家充当直接的咨询人员
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现在常会就广泛的政策问题咨询思想库专家的意见。这种咨询有多种方式,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例如,一些思想库的专家有机会见到高层领导人、随同领导人去国外进行短期访问或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等,这时他们会提交一些个人的意见或建议。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机制,也就是说它因人而变动,并不以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固定存在。尽管如此,它仍是思想库专家介入外交决策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李慎之、前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宦乡,他们由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而能够经常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13)
此外,一些著名外交思想库的领导人或学者经常会被邀请参加政府外事部门举行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有时也会对决策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咨询方式相对要正式一些。实际上,近些年来,专家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正呈现出日益固定和制度化的趋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02年12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该活动平均大约每一个半月举行一次,迄今已举办52次。(14)通常每次活动由两位著名专家主讲,主题涉及经济全球化、国家发展战略、依法治国等国内外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社科院余永定、江小涓讲授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外交学院秦亚青、社科院张宇燕讲授的国际格局变化。这些专家主要来自社科院、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重要思想库和高校。通过这种直接交流的方式,思想库的专家有可能对最高层决策者的思想施加一定的影响。
2.思想库的人员直接在政府中任职
当今世界各国思想库除了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担当政府的人才储备库,这一点尤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与多数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不同,美国的政府部长并非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很少来自公务员,而是多来自各大思想库;而且,政府中的官员在任期结束或退休之后,也常常会选择思想库为他们的落脚点。这种人才互动的模式,就是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旋转门”效应。
在中国,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外交思想库的发展还不成熟,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在人才的流动上也已初步具备了一些“旋转门”的雏形。比如按中国的官场惯例,高层领导人退休后发挥余热通常是去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但近几年来,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选择思想库作为发挥余热的舞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他退下来后担任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退休后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而老将军肖克和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则联合创建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这些原政府高级官员退居思想库,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相关政策研究机构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提高了这些思想库的知名度。
不过,作为“旋转门”的反向功能——思想库的专家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在当代中国还远未形成潮流。目前在中国外交思想库中“旋转门”效应最为突出的应该算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大约有1/3的研究人员是轮换的外交官,(15)但这种“盛况”显然与国研所本身直属外交部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对其他思想库或在更高级职位上,思想库官员进入政界的例子似乎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与中国思想库本身的发展还不完善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更多地依靠官僚体制内部进行人才的输送和培养,而体制外的各种机构几乎没有参与的渠道。
3.撰写政策研究报告
思想库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就相关国际问题撰写政策研究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或者渠道,通过提交政策报告给政府高层领导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思想库及其专家们的观点和建议就有可能进入到外交决策进程中去,从而对政策的最终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外交事务的特点,国际问题研究报告要求紧跟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抓住其重大动向、事件和问题,冷静观察、深入分析,正确评估其对世界和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人员的政策意见和建议,供中央和有关外事部门参考。(16)从形式上看,思想库的政策报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发表的;一类则是属于内部报告,并不公开。这些报告是中国政策研究机构的主要产品之一,也是思想库专家传达信息给高层领导人和外交决策者的最通常途径。
以中国重要的思想库——中国社科院为例。社科院“国际片”各研究所的内部报告,大多刊载于各所的内部刊物上,每年少则出15—20期,多则出70—80期;除此之外,各研究所还要应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完成并直接提交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大量的研究报告,且这种任务的数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这些内部报告,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新发展,各国国内政局变动、对外关系动向、突出的地区问题、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舆论等等,都是各研究所注视、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报告,多是很及时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又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观察和全面的估量,向中央和各部门献计献策。有许多内部报告,对外交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7)
4.出版国际问题方面的专著和文章
针对当前或未来的重大国际问题出版专著和文章,也是中国外交思想库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皮书”系列,由一系列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组成,由于作者的权威性(均为社科院等著名思想库的专家)和发行的及时性(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18)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基本上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形势认识的最高水平,往往会对政府部门决策人员、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等产生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中国的主要外交思想库一般都会定期出版专业的学术期刊,因其学术水平较高,往往都是该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双月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现代国际关系》(月刊)、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外交学院的《外交评论》等等。各思想库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或邀请中国政界、外交界重要人物发表看法,或对重大问题展开辩论等方式,为政府内外的国际问题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
除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中国外交思想库的专家还时常在一些普及型的国际问题杂志(如《世界知识》)或报纸(如《环球时报》)上撰写文章和评论。通过这些文章和评论,思想库的专家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对于复杂国际问题的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在引导公共舆论,最终有可能对政府的决策造成间接的影响。而且,通过普及国际问题方面的知识,使民众更多地了解政策背后的隐情,也可以帮助说明政府的立场,从而有助于政府外交政策的顺利出台和实施。
5.在电视、网络视频等媒体上露面
由于国际问题的特点,与在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上撰写文章相比,在电视媒体中发表评论无疑是思想库专家影响公共舆论最及时有效的方式。当然,电视媒体对嘉宾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他们不仅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所评论的问题作出简洁明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概括,还要用普通民众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述出来。那些被邀请的专家学者大多来自中国著名的思想库,他们在电视媒体中露面,一方面提高了自身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可使其所代表的研究机构的知名度得到提高。
有关此类节目较为出名的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每晚9:30播出的“今日关注”和英语频道每晚7:30播出的英文访谈节目“Dialogue”,这两个栏目经常邀请中国著名外交思想库的专家学者深度分析国际大事,在观众中影响很大。如“今日关注”曾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等众多中国著名外交思想库的专家就当前的国际问题发表评论和看法。(19)实际上,该节目仅2008年上半年邀请的中国各大思想库的专家便达到了一百多位,他们在电视上频繁亮相、发表评论,借助于电视媒体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公共舆论施加了重要的影响。
6.思想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外交思想库开始逐步加强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由于思想库介于政府官方机构和完全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独特身份,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时可产生“官方外交”所无法起到的效果。通过中外双方思想库之间的对话(即所谓的“学术外交”),不仅可以使国外的研究机构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也会进一步加深国内思想库对别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理解。最终这种非官方的交流信息传达给官方机构,就有可能会对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995年开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长期合作进行的有关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试图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找出对现实的启示;1997年,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起了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边对话的“第二轨道”圆桌会议项目,中国内地几个著名思想库的学者也积极参加,对于促进台海两岸的相互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20)2001年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中美之间“危机管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合作;2004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开始举办年度的中欧思想库圆桌会议,由中方与欧方轮流主办,旨在为中欧学术界就深入发展中欧关系等问题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多届。
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最初发起并参与组建的、由东亚13国参加的“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NEAT)。该组织成立于2003年,是“10+3”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第二轨道”外交的一个活动平台。其宗旨是整合东亚地区的学术力量,加强思想和研究的交流,为推动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撑。(21)“东亚思想库网络”协调单位现为外交学院,学院下属的“东亚研究中心”负责网络的实际工作和日常事务。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对外交流与合作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而崛起中的中国也会碰到许多复杂的国际难题,这些都为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政府现在越来越重视思想库的作用,思想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同国外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相比,中国外交思想库无论是机构规模、研究领域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这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存在着管理规划、发展思路等方面的种种不足。具体说来,中国外交思想库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作如下一些提高和改进:
1.加强思想库的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
目前中国的外交思想库总体数量已不算少,涉外直属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军队和党校系统等各类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思想库加起来足有上百家。但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不同部门,在研究方向、科研成果质量、资源及效率等方面差别很大,相互之间也缺乏沟通和联系,重复劳动的现象经常存在。
实际上,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筹各大思想库的联合机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简称NIRA)的设立就很值得中国借鉴。该机构成立于1974年3月,当时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日本政府认识到,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个企业或一个研究部门是无法做到的,需要汇集有关各个领域的智慧,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此背景下,NIRA应运而生。该机构是根据国会通过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而设立的半官半民组织,号称是日本脑库的“总管”。其基本职能包括对全国的思想库进行调查,并提出未来的发展规划;拟定适当的研究议题,鼓励其成员进行研究等。(22)它的成立,对于日本思想库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相比之下,今日处于剧变中的中国,同样面临许多复杂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也需要思想库发挥积极的作用。成立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中国思想库联合组织,无疑有助于国内思想库的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或者至少在目前阶段,可以通过加强国内思想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个松散的全国性思想库网络。通过调查摸清中国思想库的总体情况、制订中国思想库的总体发展规划、发布年度性的中国思想库发展报告、建立“中国思想库研究中心”(可以看做是中国思想库的“思想库”)等具体措施,一定会促进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发展。
2.拓宽研究领域,突破以往“政策研究”,加强“战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国际政治格局向着多极化演进。如何深入理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如何界定中国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如何客观判断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与作用?如何识别中国发展的各类机遇与挑战?这些宏观的、重大的问题都需要深层次和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在这一点上,中国外交思想库的作用显然还有待加强。
这方面也有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如中国著名思想库“改革开放论坛”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23)但总的来说,中国外交思想库在提出原创性的战略思想方面成就不大。这一问题已经逐步引起国内思想库的重视。正如一位著名思想库领导人在接受访谈时指出:“过去,国际问题的思想库比较重视政策研究,或者说策略研究、对策研究,在今天这个时代看来是不够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外交必须同时应对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没有综合、长期、前瞻的国际战略研究,没有国际战略理论的支撑,显然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24)
3.提高研究人员素质,优化研究人员的结构
现代国际问题总体呈现出一种交叉性、跨学科的特点。中国在崛起的发展道路上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不仅有传统的大国关系、地区安全等问题,也有国际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环境保护、金融安全等非传统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需要相当的专门知识,而中国现有外交思想库的研究人员,专业结构较为单一,基本都是以文科人才为主,缺乏理工科和管理类的人才。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对比国外的著名思想库,差距尤其明显。试以美国的兰德公司为例。该机构研究人员专业背景极其广泛,涵盖的范围从政治学、经济学到工程力学和医学等领域。据统计,目前兰德公司700多名全职研究人员所属专业学科及人数占全体研究人员的比例大致如下:政治与国际关系,12%;经济学,12%;行为科学,11%;法律和商学,11%;工程学,10%;数学运算及统计,9%;社会科学,8%;政策分析,8%;生命科学,7%;艺术和文学,5%;物理学,3%;计算机科学,3%;无学位者,1%。(25)在兰德公司,几乎所有的重大研究项目,都是由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采用集体研究的方法完成的。当然,中国思想库短期内达到此类世界著名思想库的水平也不太现实,但这应当成为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4.加强思想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
思想库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教育公众和引导舆论,而中国思想库在此方面的作用尚待加强。目前在各大网站的论坛、BBS和博客评论中,所谓“愤青”的言论异常火爆,其中不时出现反美反日、抵制日货、武力攻打台湾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与中国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反差目前还有扩大的趋势。从长远来看,这种反差有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造成消极的影响。
对此,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认为:“政府和公众两方面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是那样的政策;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加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26)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对于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思想库来说,无疑都能够胜任:一方面由于思想库的半官方性质,在解释和说明政府外交政策时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对公众普及国际问题知识,思想库的专家们既有能力做到,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重视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应用
最近几年来,互联网在中国高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7)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中国公众了解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众多国际问题相关的网站中,中国国关在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网等专业性网站吸引了众多的国关、国政等专业的学生,而人民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的国际论坛都是人气很旺的地方。
然而,与这些网站上的热烈气氛相比,中国各大外交思想库的网站人气似乎并不高。虽然大多数思想库也顺应时代潮流开设了各自的网站,但内容过于单调,更新也不及时,明显缺乏互动;对于新发生的国际大事也鲜有及时的分析和评论。相比之下,美国的各大外交思想库,都十分注重对网络的利用。他们不仅设立网站较早,而且非常重视对网站的管理和更新,同时也有论坛等与读者互动的内容;在其主页上,经常可见其对某个国际事件的立场和主张。
鉴于网络的重要性和中国外交思想库网站建设相对落后的现状,思想库的管理者们应当尽快重视和加强对网络的应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发展和利用网络,使其成为传播思想、扩大影响和引导舆论的工具;同时,通过网站中论坛和博客的互动,了解来自各方的观点,使之成为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同行的思想交流平台。
6.增加与企业界的互动
中国外交思想库尤其是大型的思想库应当加强与中国大公司的联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日益活跃,掀起了一股“走出去”的潮流。这其中有海尔公司在美国投资设厂、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华为和中石化等在非洲大量投资等等……中国企业近年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表现令世人关注。然而激情退去后,苦涩的事实让人们趋于冷静。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28)
在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不顺利的原因时,有关专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海外投资环境不够熟悉、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不够准确。(29)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一定要具有战略眼光,而战略研究和海外安全形势评估则是外交思想库的研究强项。事实上,国外一些著名的思想库早已有了这样的先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公司会员制度”吸引了250多家美国和非美国的大公司参加,涵盖了制造业、金融业、咨询业、法律和媒体等几乎所有的商业部门。具有会员身份的大公司领导人,可以通过参加思想库定期举行的高层人士会议、同思想库内的专家进行交流等方式,获得全球化背景下有关国际形势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深入认识,而思想库也能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等业务为自己的知识和资源找到更广泛的应用领域。(30)
因此,中国公司与思想库进行联合,通过学界和商界的互动具有直接的益处:不仅有助于思想库获得新的资金渠道,也可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提供必要的战略咨询,双方的合作可以达到一种“共赢”。
五、结语:思想库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之,虽然存在着以上种种不足和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越来越开放,思想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强。通过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和引导公共舆论等方式,思想库正在对中国外交决策的进程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发展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是体制的制约,依托于政府的结构性矛盾,意味着思想库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仍然有待提高;其次,由于思想库提供产品的思想性特点,人们很难对其作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给出精确的评估。
毫无疑问,思想库能够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宝贵贡献,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学术界所要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思想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它们如何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追问和探索,将会不断加深人们对思想库这一中国重要社会现象的认识。
注释:
①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未讨论中国思想库的概念、分类等基本问题,相关研究可参见陈广猛:《中国外交思想库:定义、分类和发展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57—69页。
②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③杨光斌:《中国政府和政治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8—52页。
④Lu Ning,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2nd edition,Boulder,Colorado:West view press,2000,p.34.
⑤Ibid.,pp.7—16.
⑥Charles F.Hermann,"The Knowledge Gap: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the Foreign Policy Communi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Chicago,Illinois,September 7—11,1971.转引自Stephen J.Andriole,"Decision Process Models and the Needs of Policy-Makers:Though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interface",Policy Sciences,Vol.11,No.1,1979,pp.19—37.
⑦详细项目情况可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
⑧实际上,各思想库尤其是较大型的思想库每年所承接的课题远不止国家社科基金这一类项目。以中国社科院“国际片”的研究机构为例,每年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1)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问题;(2)中央有关部门交办的任务;(3)“十五”、“十一五”等国家重点项目;(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院重点项目;(6)各所的重点课题;(7)研究人员自己选定的课题。见李琮:《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世界经济》,1997年第8期,第9—10页。
⑨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⑩《中国智库:使命与挑战——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解放日报》,2007年6月29日。
(11)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第26页。
(12)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以上模式只是一般的外交决策模式,并未涵盖所有的外交决策类型。从外交决策的种类来看,主要有一般决策、创议决策和危机决策三种。三种决策的特点不同,参与者的作用也不同。总的来说,危机具有突发、紧急和对国家利益构成极其严重危害的特性,因此要求决策果断迅捷,参与者多为国家领导人及其选定的核心,思想库和各种研究机构既不能也无法影响这种决策;日常决策基本上由行政部门作出;创议决策则由领导人和有关行政部门共同做出。后两种决策在政府的整个决策中占绝大多数,思想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多是发生在后两种决策过程中。参见席来旺:《美国的决策及其中国政策透析》,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13)杨光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14)数据截止至2008年9月28日:其中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8次,具体学习内容可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0/content_6856447.htm。
(15)He Li,"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49,No.2,March/April 2002,p.38.
(16)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10页。
(17)李琮:《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第12页。
(18)详细情况可见中国皮书网,http://www.pishu.cn。
(19)具体节目情况可见央视网站,http://www.cctv.com/program/jrgz/03/index.shtml。
(20)详细情况可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FP)的网站,http://www.ncfp.org。1997年,由于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该活动实际已经中断,但NCFP仍继续派出人员来往于海峡两岸进行交流活动。
(21)有关东亚思想库网络的详细情况介绍和活动安排,可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neat.org.cn/chinese/index.php。
(22)徐之光、刘挹林编著:《日本的脑库》(修订本),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2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外交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自信心越来越足,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抱着越来越大的疑虑,一时之间“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面对此种情势,“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及其团队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后经中国领导人“和平发展”等思想的逐步调整和演变,最终形成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一重要外交战略构想,该思想现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
(24)《中国智库:使命与挑战——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
(25)资料来源:《兰德公司2006年度报告》,见兰德公司网址,http://www.rand.org。中国著名思想库中国社科院虽然从学科分布上来说也较全面,但基本上都是以各自的研究所为单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并不多见。
(26)《传媒评论中国公众舆论为什么不支持政府的外交决策?》,《环球时报》,2004年1月26日。
(27)资料来源:2007年7月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详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址,http://www.cnnic.org.cn。
(28)《前外交官解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65%亏损率》,《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8月10日。
(29)同上。
(30)有关“公司会员制度”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网站,http://www.cfr.org/about/corpo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