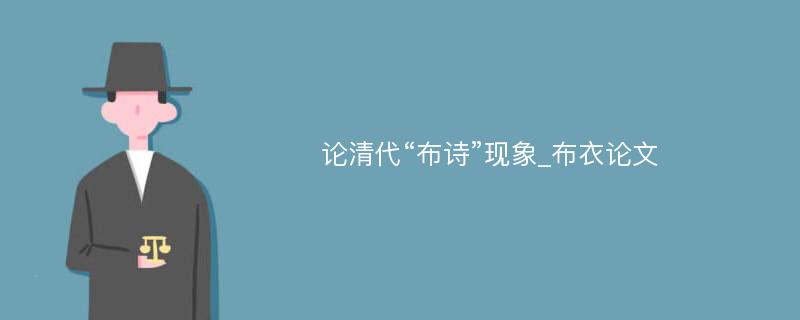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衣论文,清代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41-04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拙文《论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推动》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清代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繁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文在此基础上,就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进行探讨。 一、清代“诗在布衣”现象概述 清代有着数量十分庞大的布衣文人群体。笔者根据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做了统计,此书收录的19700名文人中,布衣文人有10761位,占总数的一半有余。众所周知,古人能文者皆能诗,更重要的是,布衣的创作风格各异,成果丰硕。王豫在《盟鸥溆笔谈》中对布衣诗有过这样的评价:“本朝布衣诗如彭爰琴之秀拔,吴野人之直朴,蒋前民之真挚,邢孟贞之淡永,潘南村之清折,冷秋江之悲壮,周青土之闲逸,徐东痴之幽奥,沈方舟之警炼,李客山之高老,盛青屿之坚栗,张永夫之澄洁,於亦川之雄骏,鲍步江之超秀,吴淡川之新隽,朱二亭之淡逸,潘兰如之清雄,石远梅之高浑,张竹轩之淳古,能各具唐人之一体,洵韦布之雄也。”[1](p.137)清代布衣诗人可谓群星璀璨,“布衣诗”自成系列,充实了清代诗坛。兹略举数人。吴嘉纪:“一生不出东陶路,自有才名十五州。”王士祯评价邢昉曰:“余最许石湖邢孟贞五言诗,以为韦、柳门庭中人”,陈田也尤其推崇他的五言诗:“孟贞五言,取径唐人,而时涉柴桑藩篱,以幽秀淡宕为宗,得储、韦之自然,兼韩、孟之刻厉。明季布衣诗,邢昉第一,洵为确论。”[2](pp.3012-3013)厉鹗堪称“浙词巨匠”,吴锡麟认为:“吾杭言词者,莫不以樊谢为大宗”,谢章铤也指出:“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谢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3](p.343)事实上,清人早已注意到布衣在清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屈大均就曾指出:“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4](p.201)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大抵好诗在林壑,可怜名土满江湖”[5](p.3450),“评诗推许称同辈,落落关东老布衣”[6](p.232),“循吏而今有子孙,江天吟啸布衣尊”[7](p.6631)等等。 二、清代“诗在布衣”现象的成因 文学史上,仕宦文学与布衣文学的分野由来已久。刘再复先生曾经指出:“诗词要写得好,一定要在‘发达’之前,不可在发达之后。诗词要写得好,诗人必定要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必定要有各种情感上的波动与折磨。发达之前和发达之后,诗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人文环境极不相同,精神、心境、性情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不‘发达’,诗人就容易与人间的苦痛相通,人生的体验就会真切而丰富,作为诗人的真性情也会得到充分表现。诗‘穷而后工’,我赞成这种说法。诗人一旦发达,进入宦门、权门、宫廷之门,自然就与广阔的人间隔起一堵高墙。‘一入侯门深似海’,能不被各种桂冠所诱惑而继续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并与人间的痛苦相通的人极少。”[8](p.287)清代,布衣文人在创作目的、创作态度、创作轨迹及创作过程等诸多方面均迥异于同一时期的仕宦文人。 (一)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 布衣文人布衣终老,人生充满了不得志,在“事功”已很渺茫的现实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立言”:“身前之遇,不自我;而操身后之名,可自我。”[9]生前的境遇不由自己决定,而死后的名声则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故而,创作是布衣文人全部的寄托,也是他们实现人生抱负的重要手段,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石卓槐《芥园诗钞》托名沈德潜写序一事。“至于山林隐逸之士,一生无他嗜好,惟孳孳矻矻于五字七字之中,既无名位足传,复不得一人表而章之,数十年后,其人与诗皆归于无何有之乡”[10](p.513)。石卓槐担心逝后别集散佚,希望能得到达官贵人的揄扬而闻名于时。沈德潜深得乾隆器重,大权在握,石卓槐这样一个无名之辈,不可能与之攀上关系。为了抬高身价,他索性假托沈德潜之名,自己操刀写序,这种做法当然不可取,但这一个案反映出布衣文人欲以诗文闻名当世、扬名后世的迫切意愿。急于“立言”的布衣远不止石卓槐一个。江干“一编诗草当儿孙”[11](p.794),真是乐在其中;章敬修“迨穷愁之交迫,始发愤而著书,孳孳矻矻,罔顾揶揄,动而得谤,名与之俱。老冉冉其已至,行难补于桑榆。而乃垂空文以自见,欲争一得于区区”[12](p.157)。可见,布衣文人“立言”心情之恳切,创作是布衣文人生命中的重要构成,是他们留名后世的重要手段,他们反复学习、揣摩、习作,并终生倾力于此,其成就自然不可小觑。 仕宦文人则完全相反。清朝历代帝皇对诗文普遍有着特殊的偏好,他们不仅自己创作诗文,而且还经常与臣僚们诗词唱和,尤其在大规模的宴会中,赋诗纪事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上行下效,仕宦文人自然也热衷此道,在一个推崇风雅的国度里,仕宦文人如果不会吟诗作赋,官场上的应酬往来将颇为被动,因此,要写得出一手文章。但总体而言,仕宦文人与布衣文人的创作目的是不一样的。就仕宦文人而言,“三不朽”中立功、立德都已经唾手可得,“立言”并不是那么必不可少,于是他们多借创作展示才华,或借创作消遣应酬。袁枚曾经记载了一则轶事:“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傔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赋七律一首,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公喜,从此又与枚叠和不休。”[14](pp.4-5)一和再和,志在压倒对方,创作成了逞才斗胜的手段,而且案牍劳形、迎来送往,让仕宦文人难以勤力于此。对他们来说,创作已经不是生活的主业。综观仕宦文人的创作,其高峰往往在出仕之前或致仕之后。 (二)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 在对待创作的态度上,布衣文人与仕宦文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创作是布衣文人终生的寄托,他们心无旁骛,“诗堪托死生”,对创作寄予了全部的热情。布衣张隽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抄书、著书中度过的,在人生陷入困境时,著述成为他唯一的安慰,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月末,遭萑苻,青毡不存。继而家难洊起,顾影自畏,平生之所尊闻,至此茫无用处,亦且惭其儿子。因忆古人都从忧患疢疾中讨活路,支离委顿间,辄复取古今简编而究图之。”[14](p.14)贫病交加之时,尚能笔耕不辍,他从创作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清初遗民布衣更是如此。白孕彩“鼎革后,弃举人业,居测鱼村,行吟泽畔,时为诗以自娱,悲歌慷慨,藉以见其怀抱”[15](p.59)。吕留良“比向当年一半遗,书成涕泪欲何为。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16](p.323)。对这些遗民布衣来说,支撑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便是保存文脉。张笃庆曾就此赋诗:“胜国拒儒谁遁迹,躬耕述作惟遗民。遗民不只徒避世,著书万卷无其伦。”[17]布衣看重文字的巨大力量,认为著述也是救世的一种有效途径。当清王朝的统治日渐稳固,柔弱的书生无力在武力上与之相抗衡时,他们便自觉承担起传承精神的历史使命,视创作为与现实相抗争的武器,从而以诗存史。韩畾“好学能诗,尤善琴,然不轻为人鼓。请者必肃衣冠,卑颜色,伺至夜分,或闻一奏。有左右顾及笑语者,即拂衣囊琴去。游江南,遍历台宕诸胜,所携惟一琴,并负二筐,贮其平生所为诗文,如性命,顷刻不以离也”[15](p.195)。甚至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时,布衣也依然不放下手中的笔。据钮琇《觚剩》记载,吴愧庵、潘柽章被卷入《明史》案后,关押入狱,时常被提审,即便如此,他们继续笔耕,吴愧庵有《营中送春》、《怀古》四首,潘柽章有《漫成四首》《与美生对酌绝句》等数首诗。遭受无妄之灾,生命面临着终结,创作仍给了他们极大的勇气,伴随他们度过人生最后的短暂时光。创作在布衣文人生命中的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与之相左的是,仕宦文人的创作多数是一时的兴之所至,态度称不上“端正”。如一代名宦于成龙,顺治十八年(1661年),授广西罗城知县;康熙六年(1667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八年(1669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八年,迁湖广黄州府同知。十三年(1674年),擢武昌知府[18](p.541)。后做过福建按察使、直隶巡抚、江南江西总督,“江宁知府缺,二十三年三月,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升任湖广总督,成龙兼署两巡抚事。四月,卒于官”[19](p.58)。逝后被康熙誉为“操守端严,始终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18](p.548)。于成龙可谓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被誉为“一代廉吏之冠,德业粲然”,但“不以诗重”[15](p.177)。再如谭吉瑄,康熙己酉(1669年)举人,历官礼科给事中。其作品“仅存疏稿。竹垞赠持有云:‘雕虫何足尚,辛苦羡名山。’殆其志不欲以诗名也”[15](p.214)。仕宦文人的注意力不在创作,他们并不指望以创作成名,因此创作成了他们公事之后的余事,多为一时兴之所至的消遣。袁枚曾言:“余春圃、香亭两弟,诗皆绝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画,皆未尽其才。”[13](p.101)仕途对文学创作是有干扰的。 (三)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 清代文人进入仕途,最普遍的方式便是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清代科举沿袭明制,以八股取士。八股取士,束缚了文人的思想,酿成了严重的流弊,直接影响了创作。董说感叹道:“今世试士经义,所谓先圣之术,策士时宜;所谓当世之务,一循汉制,而有司束缚绳墨,甲短乙长,论者以为豪杰满野,实由制科驱除。”[19](p.131)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20](p.85)廖燕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取土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本质上是一样的,“故吾以为明太祖制义取士,与秦焚书无异。特明巧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21](pp.12-13)为了确保入仕,文人通常是先一门心思研习八股文,获得功名之后才去学习诗歌创作。陈维崧记载徐唐山一段话:“昔予之为诗也,里中父老辄譙让之,其见仇者则大喜曰:夫诗者,固能贫人贱人者也。若人而诗,吾知其长贫且贱矣。及遇亲厚者,则又痛惜之。以故吾之为诗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妇知。旦日,妇从门屏窥见余之侧弁而哦,若有类于为诗也,则诟厉随焉,甚且至于涕泣。盖举平生之偃蹇不第、幽忧愁苦而不免于饥寒,皆归咎于诗之为也。”[22](p.489)诗歌的创作与功名富贵完全背道而驰,因此,通常来说,文人首先沉潜于八股文的创作,获取功名之后才开始学习诗歌写作,这样的轨迹对仕宦文人创作成就的取得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布衣的表现与此不同,很多布衣文人都有与科举考试决裂的经历。屈复,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博学鸿词科中被推荐出山,但他借口年老体衰推辞不就。其后,贤清王先后三次以千金重礼敦聘他,他终不为所动,赋诗《贞女吟》:“女萝虽小草,不愿附松柏。平原赠千金,仲连笑一掷”,可见其志向。奚冈也是如此,“终身不与试,征孝廉方正,辞不就。”[23](p.81)还有布衣尽管参加过科举考试,而一旦认识到其欺世盗名之实,就改弦易辙了。黎简,“入乡闱时,以搜检太严,慨然曰:‘未试以文,而先以不肖之心待之,吾不愿也!’遂掷笔篮而去,从此不复应试。”[24](p.496)无独有偶,于祉也是如此,“入场时搜检至祉,忿然而返曰:‘上不以士礼待士子,而视如狗盗,何考为!’自是隐居不出。”[11](p.1224)吴颖芳应试时,“为隶所诃曰:‘是求荣而先辱也。’自是不复应试,壹志于读书”。[25](p.303)他们立志不走科名之路,“视一切骑羊、斗鸭、世俗荣名若槐安中之蚁国也。”[26](p.1115)幼年即沉潜于诗歌世界当中,全力以赴,不俗的创作成就的取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冯舒“早谢举子业,枕经藉史,肆志千古。其为学,尤专于诗,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编削伪谬”[27](p.596),最终开创了虞山诗派。 (四)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 文学创作需要个性,但仕宦文人的创作,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束缚。清代文坛文字狱盛行,此外,皇帝通过扶持文坛领袖来干预创作,这就使得仕宦文人的创作不可能生发由心,高压造成了仕宦文人的谨言慎行、明哲保身,朱克敬指出为官之道是:“仕途钻剌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论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28](p.119)这样的行事方式,自然会体现在创作上,那就是四平八稳的“盛世元音”充斥文坛。张英,“久直禁廷,不忘丘壑,尝以乐天、放翁自拟。《四库提要》称其:‘鼓吹升平,黼黻廊庙,无不典雅和平。至于言情赋景之作,又多清微淡远,抒写性灵。台阁、山林二体,古难兼擅,乃兼而有之。’……《拟古田家诗》有云:‘面无忧喜色,胸无宠辱情。始知於陵子,灌园逃公卿。’何等胸次。”[15](p.211)喜怒完全可以不形于色,其情感的压抑到了如此地步。所以,不难理解,越是位高权重者,其创作也就越四平八稳,充满了八股文的气息。如范文程“诗无专集,流传仅见《永平府志》载《清风台宴集》二律,清越高华,犹见名臣襟度”[15](p.107)。徐乾学“集中高文典册,多关掌故。诗虽余事,要皆雍容宽博,自然名贵,此台阁之异于山林也。”[15](p.217)所以,朱彝尊批评说:“后世君臣宴游,辄命赋诗记事,于心本无欲言,但迫于制诏为之,故其辞多近于强勉。若学土大夫用之赠酬饯送,则以代仪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土,限之以韵。其所言者,初未尝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知所好,以是而称之曰诗,未见其可矣。”[29](p.321)张英、范文程、徐乾学等都是深受帝皇器重的高官,与帝皇的酬唱不绝。这样的权势,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创作过程,使他们的创作势必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所克制。这就与诗歌创作讲究真情真性背道而驰。 与仕宦文人相左,布衣文人听凭心声,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远离仕途,远离权力中心,保持着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加之本身大多个性张扬,“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4](p.201),故能任真情真性自由宣泄,“尝见山人(石卓槐)读书,有所当意,每抉摘向余谈说不休,谓不信今人非古人也。其自许如此……至议论古今,及有关当世之务,则意气慷慨,时大声狂叫,目上视,气勃勃,若使气者。座客为之避,即老成宿儒亦莫不呷舌焉。”[10](p.515)周容“初则奔走于患难,继则奔走于饥寒,间偶有述,皆激楚忿懑之余,且护爱而逞恃,慕亢而讳因,以故气满于词,意尽于腕,其忸怩愧悔,更甚于足下所云。”[30](p.164)方文说:“野老生来不媚人,况逢世变亦嶙峋”,“试中愤感妻常戒,酒后颠狂客每慎。”[31](pp.379)吴嘉纪《后七歌》道:“朝来得与显者遇,宾客笑我言词拙。男儿各自有须眉,何用低头取人悦。”[32](pp.446)他们率意耿直,而仕宦唯唯诺诺,二者对比如是鲜明!有这样的个性特征,发为诗文,自然也任性驱使,少有随从附和了。布衣虽“穷”,却获得了创作的自由,正如焦循所言:“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启发,则百世之文也。”[33](pp.266)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重视与否,决定了仕宦与布衣在创作上精力投入的差别。仕宦的案牍劳形导致他们对文学创作无法专一执着,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就认识不足。布衣疏离朝廷,摆脱了皇权施加于文学的影响,保留了真性情;能够直面现实人生,执着于内心的咏歌,坦露各自的个性。他们潜心艺术,坚持己见,不再“怨而不怒”,多了横眉怒目,多了匕首投枪,多了讽刺针砭,创作出足以流芳后世的“百世之文”。布衣文人苦心经营,清代文坛得以充实丰富,清代文学得到了光辉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