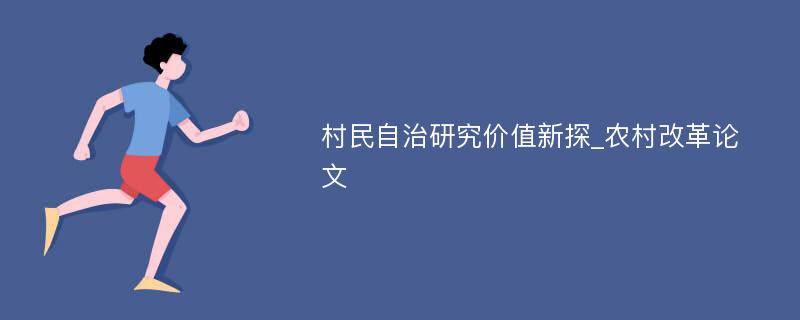
村民自治研究价值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民自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村民自治是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基础工程。近年来,村民自治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视角涉及村民自治的各个方面,但对村民自治研究本身的价值及其作用、意义,探讨不多。特别是关于村民自治研究的知识定位和学理意义还不曾有人涉及,本文拟在此作一尝试。
村民自治研究的定位
要探讨村民自治研究的价值,应将其置于一定的脉胳背景中,才好进行知识定位。论证村民自治研究价值的基础和依据,则是村民自治所要分析和强调的社会现实。因此,改革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村民自治研究是改革理论与实践脉搏共振的产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就全局而言,是国家通过调整路线、方针、政策起步的。它带有现代化后发展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即改革政策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理论界常用“放权让利”四字来概括这一进程。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特点在改革初期更富有典型性。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亦谈到,发展中国家现代改革的实施,没有中央政府的强有力行政指导很难收到成效。因为在高度集权体制的条件下,没有权力上层的首肯和推进,任何来自下层的创新活动都会被压制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或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但是一当改革冲破传统的樊篱,它便会有自身的逻辑轨迹,不以人们的主观预设为转移。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性运动是人们根本无法阻遏的。村民自治就遵从了上述路径,它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而导致的政治体制上的一种超越:由行政——自治。[①]
同时,改革越是深入,要扭转它的方向,恢复旧时的秩序,便越不可能。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革的不可逆特点由于自下而上的冲力不断加大而日渐显示。因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二种不同力量之间复杂、丰富、多样性的交互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后改革发展的方向将取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力量。
今天看来,“放权”比“让利”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根本性的利益格局调整,引发了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巨大变动。概括地说,国家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放权型改革牵动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政府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二是国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前者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目前引起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村民自治研究所针对的只是后一大问题,村民自治研究所要寻找的答案是乡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关系。如果说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数次调整的试验,那么如何通过自治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颇为生疏的问题,几乎谈不上什么经验。“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自治的传统,没有大量的资源可供开发和利用。几千年来,农村社区主要实行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式的封闭自治,它既缺乏民主性,也缺乏开放性,这种历史传统,是我们的一大包袱。[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农村完成了社会结构的重组过程。以行政手段垄断和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成为农村组织的基本形式,在这种组织体制中,国家权力从上到下、层层渗透。缘此,乡村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乡村社会附属于国家为特征,社会本应有的独立空间和自主性没有存在的余地。
这种格局被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逐渐改变。国家有意识地主动放权,意味着让渡了相应的活动空间和领域,让一部分权力保留在农民手中,放弃了那些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情,或许叫“抓大放小”更简明。一个总的趋势是:这种让渡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衍化中的矛盾和困境要求我们对演进中的乡村发展作深入的考察与反思。政府让渡出的活动空间在实际生活中是谁占据了并在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农村新出现的组织是否可以自由存在和发展?如何正确地把复活的宗教团体、宗法关系当作一种历史遗留的组织资源纳入到人民民主专政体系下加以利用?其自主性程度和活动范围要不要明确划定?如何划定?政府的间接管理如何跟上去?如何尽可能地减少由暂时的“真空”或规则转换导致的所谓“瘫痪”、“半瘫痪”软弱涣散状况?最突出问题是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又如何制订其操作性规定?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事情。
村民自治的研究正渊源于此。它是向这一特定角度来应答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这一挑战。从本质上讲,是主权在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观在农村研究问题上的体现。村民自治研究一个重要关注领域便是研究与国家相对应的乡村社会生活领域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问题。如果说国家提出“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那么正好相反,村民自治研究则可看作是“自下而上”的另一种努力。相反相成,“真理”也许就在这两者关系的互补之中,这就是村民自治研究的基本定位。无独有偶,这恰恰是现代政治发展理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基层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要求。[③]
村民自治研究的学理意义
村民自治研究的学理意义很少为人们所注意,然而又是村民自治研究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笔者试图在此作一发掘,不一定成熟,其意在抛砖引玉,促进研究的深化。从学理层次上讲,村民自治研究标志着农村问题研究视角的转向,研究方法的转变。村民自治研究的发育、成长是学人以“眼光向下”的务实精神探索我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表明学人不再拘泥于单纯的“上层政治”,而诉诸对“社会力量”的关注。
“村民自治”一词,愈来愈被学人所关注和重视,并非偶然现象,我们可以依据知识界在80年代后期所凸现的两方面动向来分析。第一,以往知识界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上,往往偏向于只从政治学角度入手,把整个社会问题约化为民主问题,过分意识形态化,而少从社会学角度入手,作实证分析,因而往往显得浮躁、急进,缺乏真正的学理探讨,或因追求新异而流于空泛,或因止于“策论”而显得肤浅,村民自治研究集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长,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入手研究农村社会,可以说这是对以前学风的一种反思;第二,是学人对我国的未来发展给予更成熟的学理关注,力图依据改革深化所提供的新的经验材料对农村现代化问题作出富有创意的探索,在研究取向上直接切入最现实的基层实践问题,直接面对急迫的现实需求,在寻求解决答案时,注重操作层面,抓住要害,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种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转变应该说是有深远意义的。
综上所述,村民自治研究是对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一种理论回应,它的根基在于农村改革经历了巨变的农村社会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它的价值将进一步显示。
注释:
[①]参见杨光秋、熊吕茂《邓小平的村民自治思想浅探》,载《学习导报》(湘)1996年第6期。
[②]王振耀:《全国村民自治发展趋势及进步政策选择》,载《实践与思考》,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③]参见周忠德、严炬新编译《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