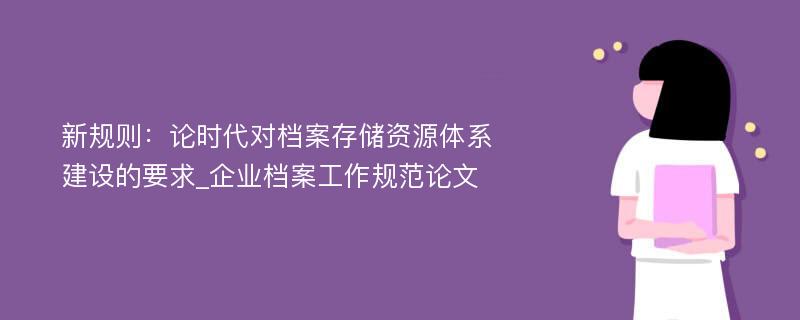
新规则:论档案记忆资源体系构筑的时代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规则论文,体系论文,记忆论文,档案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罗·康纳顿将仪式行为视为传送和保持社会记忆的手段,同时也特别强调了仪式操演的规则,认为“仪式只有通过它们的显著的规则性,才成其为表达性艺术。它们是形式化艺术,倾向于程式化、陈规化和重复。因为它们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它们不会自发出现变化,或至多仅在有限范围内可能变化。它们不是因为一时内心冲动被操演,而是被认真遵守。以表示感情。”[1]从康纳顿关于仪式操演规则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延伸出同样的问题,即档案工作在构筑社会记忆活动中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说:“整个历史就是一种选择”,“历史甚至是偶然性的选择,偶然在这里将历史遗迹毁灭,而在那里又将其保留了下来。”对此,法国国家档案馆总保管员C.诺加雷从一个档案工作者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既然肩负着收集历史材料的使命,就要尽力做到人要超越偶然。”[2]要做到“超越偶然”,我们就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规则,合理规划和引导未来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整体性构筑。 一、体制内档案记忆资源与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并重 在近年的档案学研究中,如何构筑社会记忆已开始进入部分学者的视野。从现有的研究主题看,人们似乎还是更多地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档案馆档案记忆资源的收藏上,探讨如何扩大档案馆收集范围,改变档案馆馆藏结构,从而丰富社会记忆的问题。档案馆是社会记忆的“殿堂”,丰富档案馆藏、调整档案馆馆藏结构也确实是社会记忆构筑的重要内容,但就社会记忆/档案记忆的整体性构筑而言,它仍是局限于体制内档案记忆资源的建设上,对于如何合理规划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建设关注度还不够。 “体制内”和“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是档案资源的新提法、新概念。虽然其概念和范围大体相当于我们以前的国家——民间档案资源,或国家——社会档案资源,但是这一新概念的使用却更能准确地表达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或社会记忆构筑中的资源结构与资源内涵,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思考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 一般而言,体制内档案资源是指在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框架下,受我国档案管理体制规范和约束的、在国家控制下的档案综合体,它包括国家管理体制下的党政群团及直属机构形成的档案和垂直管理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等形成的档案,也包括各级各类档案馆内保存的档案;而体制外档案资源是指与体制内档案资源相对应的,在国家档案管理体制之外,处于社会分散管理状态的档案资源,包括所有非国家性质的机关、团体、组织、企业以及家庭(家族)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或通过合法途径所获得的,没有进入国家档案保管部门收管的、有价值的档案综合体。体制内档案资源与体制外档案资源的划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首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与功能。多年来,人们对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档案馆馆藏结构不合理,保存的多为党政机关的“官文书”,而普通民众的档案保存甚少。这种批评是否超越了档案馆的制度性职责?人们在重新思考档案馆应该保存什么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考虑档案馆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作为体制内档案资源管理的机构,它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档案馆要不要包揽一切?其次,在国家行政体制转型过程中,促使我们思考体制外档案资源社会化管理问题。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将由非政府机构与组织办理,作为国家事业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也需要思考如何逐步向社会拓宽,动员社会力量,完善各种体制外档案资源的管理。 对体制内档案资源,我们经过60多年的建设,现已积聚了丰富有效的管理经验,而对于体制外档案资源,我们仍处于探索和实践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档案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类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管理问题:如“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档案管理,村民自治条件下的农业农村档案管理,城市社区自治条件下的社区档案管理,社会管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档案管理,以及日益活跃的家庭和个人档案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质都涉及传统档案管理体制外档案资源的管理,档案界在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立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管理模式(如家庭档案管理的沈阳模式、济南模式、徐汇模式;社区档案管理的上海模式、青岛模式、沈阳模式和南京鼓楼模式等),也颁布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管理办法和意见(如《关于加强上海市社区档案工作的意见》《辽宁省城市社区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等),为相关档案资源的管理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但总体而言,与体制内档案资源管理相比,还未形成有利于工作持续开展的长效、协同和整体的运行机制。 体制内和体制外档案资源作为社会记忆,特别是作为国家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现在的学者在论述体制外档案资源(如社区档案、家庭档案、私营企业档案等)的社会功能时,都会从社会记忆的角度阐释其社会价值和意义。如冯惠玲教授曾提出“共建社会记忆——让方方面面的人关注档案,参与档案资源建设”[3]。因此,在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整体性构筑上,我们要坚持体制内和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并重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深入思考体制内和体制外档案资源管理的各自特点和状况,在强调体制外档案资源转化为体制内档案资源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和探讨体制外档案资源的社会化管理。当体制外档案资源管理得到广泛和有效保护的时候,对档案馆的苛求和批评或许就会消除。 二、传统记忆资源与电子记忆资源并举 沃尔夫·坎斯特纳说:“电子媒介已不可摆脱地被卷入集体记忆建构和演变之中,注意到这些是至关重要的。”[4]电子记忆作为一种“新记忆”的出现,促使人们审慎思考它对人类记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社会记忆的当代形态是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社会记忆类型,它根源于当代社会的剧烈转型,同时又反过来进一步保证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当代转型”[5]。 尽管在电子记忆的主导下,“口承记忆和文字符号的社会记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造”,但是,人类在记忆形式上始终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正如文字符号社会记忆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神话传说和口承记忆的消失一样,信息化大众电子传媒的诞生和全面扩散也不是对人类过去诸种社会记忆类型的完全否定”[6]。 在档案界,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发现自己正两脚分开困难地叉立于现在,一只脚踩在过去,以确保我们的共同记忆得到保护;另一只脚踩在未来,以确保我们的知识和技能继续地为社会所需要”[7]。其实,斯威夫特的这句话似乎还可以再延伸一点,即踩在未来的那只脚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共同记忆得到保护。因此,在电子记忆不断生成的年代,新的电子记忆我们需要保护,传统的记忆资源也需要我们继承和延续,传统记忆资源与电子记忆资源各有特点,都是历史的记录,是以文本方式记载下来的社会的共同记忆,在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构筑中,需要我们秉持两者并举的思想。 传统记忆资源(即传统载体档案,如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和录音录像档案等)和电子记忆资源(即电子文件或数字化档案)的保存保护,是档案工作构筑社会记忆的两条基本途径,两者各有侧重,同时又存在交融:一方面,传统记忆资源的保存保护侧重点在于对濒危历史文献的抢救性保护、对散存民间的文书档案的集中保管,以及对流失海外的历史档案的追索;而电子记忆保存保护的侧重点在于对电子文件积累归档方式和措施的逐步完善,对电子文件长期、安全保管保护的规范、标准和规划的制订,以及对电子文件中心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等。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强大功能,传统记忆资源也正在逐步被数字化,成为电子记忆的组成部分。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传统记忆资源和电子记忆资源保存保护作为构筑档案记忆资源体系两条基本途径的特征也非常明显。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国家档案理事会积极参与,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以促进对濒危珍贵历史文献的保护和无歧视地提供利用,大力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认识[8]。与此同时,在1992年的国际档案大会上,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了专门的电子文件委员会,引领国际电子文件管理向大众化、规范化和科学性发展。国际档案理事会曾呼吁说:“我们现在在各种电子媒介上创造的信息构成了将来的档案,面向未来,信息社会需要记忆,不管它是记录在石头上、纸上还是电子媒介上,因此要做出努力,采取紧急和必要的措施来保存信息社会的记忆”[9]。 与国际社会相呼应,我国对传统记忆资源和电子记忆资源的保存保护工作也在各个层面展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将“强化‘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专项经费’落实力度,确保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加快数字档案馆及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建设,完成国家数字档案馆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对电子档案进行安全有效的管理”[10],作为“十二五”期间档案事业发展的两大主要目标,也体现出传统记忆资源与电子记忆资源保存保护并举的思想。 三、中心记忆资源与边缘记忆资源兼顾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记忆都有中心,有边缘。在我们个人的人生旅程中,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记忆中心。有学者说,如果我们制作一个家庭相框(册),那么,小时候,父母的照片可能摆放在中间;青年时期,恋人的照片可能摆放在中间;而到年老时,孩子的照片可能摆放在中间。照片在相框(册)中摆放的位置,体现出人的关注对象或焦点。对一个民族来说,“作为文化意义生产中心的文化主体,其内部的结构和成分是极为复杂的。每个民族文化内部既有官方和民间的分层,主流和支流的交叉,也有边缘和中心的区别。它是长期以来特定民族内部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能量之间相互激荡、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11] 中心记忆与边缘记忆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框架中相对应。①如果我们把官方记忆视为中心,则民间记忆即为边缘。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编纂的中国地方珍稀文献《石仓契约》(共8辑),就被媒体称为“记忆边缘的历史”[12]。②如果我们把统治群体(阶级)记忆视为中心记忆,则被统治的少数民族(阶级)记忆即为边缘记忆。③如果将中心记忆视为被记住的记忆,或扬·阿斯曼意义上的现实状态的记忆,则边缘记忆即为那些将被遗忘的记忆或处于沉潜状态的记忆,这是哈布瓦赫“现在中心观”的体现。④如果将中心记忆视为主流记忆,则边缘记忆即为支流记忆。因此,对中心记忆与边缘记忆概念的使用要看清其具体语境。 中心记忆和边缘记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以及价值、情感、利益的取舍等,它们呈现出三种关系:即一致性关系、互补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就是通过分析华夏边缘族群拥有的祖源记忆的改变,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周边族群借由创造“共同的祖源记忆”,逐步汇入到“华夏”之中。“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13]。华夏族群与其周边族群的抗争、统合的关系,是中心记忆与边缘记忆不同关系的具体体现。当中心记忆与边缘记忆出现对抗性关系时,就产生了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反记忆”。 中心记忆和边缘记忆在档案工作中有着明显、多样的表现,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当我们突出档案工作政治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就突出了政治、政权档案的中心地位;当我们在确定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时,我们也就肯定了机关职能活动档案的中心地位;当我们在开展档案价值鉴定,确定档案的保管期限时,我们实际上也就肯定了重要机关、重要活动、重要人物的中心地位;当我们举办档案展览时,我们可以看到重要活动、重要人物形成的手稿、照片排在展板的中心位置;甚至当我们说档案馆是记忆保存“中心”的时候,我们也就肯定了体制内档案的中心地位,而将体制外档案置于边缘地位。在强调档案保存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对保存的档案记忆资源必然有着现实的和历史的考量,重点留存哪些机构、哪些人物、哪些活动,以及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哪些档案,也是档案工作者“现在中心观”的体现和选择。 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理论的批判,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边缘记忆,希望对于民间的、支流的、边缘的社会记忆给予更多的关怀。因此,我们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树立中心记忆和边缘记忆兼顾的思想,在维护官方的、主流的、中心的档案记忆资源完整的同时,顾及到各种边缘记忆的呼声和利益诉求,丰富和完善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构筑。在档案工作中,有四类边缘记忆值得关注:第一类是边缘群体形成的档案记忆,包括基层组织、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失败者和普通民众记忆(这是我们后文还需分析的);第二类是机构非职能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记忆,这些档案往往从另一方面在无意识地记录和反映社会记忆;第三类是在一项社会活动中,那些非主题的、反映活动边缘内容的档案;第四类是一项社会活动中,除了主要组织者、参加者,那些非主要组织者、参与者,甚至旁观者的档案。 中心和边缘是相对而言的。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一些传统上的边缘记忆正在转化、吸纳为中心记忆。缩小记忆边缘或记忆范围,有意识让某些记忆资源“被边缘化”,是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 四、精英记忆资源与民众记忆资源互补 “精英记忆——民众记忆”(或称为“草根记忆”)同“中心记忆——边缘记忆”有一定的关联,但也不完全相同。中心记忆与边缘记忆是在平面位置上来观察思考社会记忆所处的位置,而精英记忆与民众记忆则是在立体层次上来观察思考社会记忆的阶序关系。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将社会记忆分为三个层次,即:由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主控记忆;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记忆;由来自草根社会地方的主体记忆。“这三个阶层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所赋予的社会身份差别,这样的差别会导致他们在记忆历史时采取不同的资源组合方法来进行分层性的历史建构”[14]。当然,三种记忆样态在现实层面上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力量也各有消长。清华大学景军教授也讨论过文化精英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认为在研究村落社会记忆时有必要注意它们与农村“文化精英”的关联。“文化精英”包括家谱的编写者、历书的阐释者、对联的撰写者、祭祀的组织者、处理亲属矛盾的仲裁者、口碑历史的守护者、培养儿童的优秀教师。这些人经常凭借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文化知识,处于阐释地方历史和风俗的主导地位[15]。 一般而言,精英记忆包括“政治精英”(掌权者)、“经济精英”(富有者)和“社会精英”(有社会声望者)掌控的社会记忆,其依据国家机器、行政手段和知识信仰体系,利用所掌控的立法、文字、宗教和传媒的权利,进行“强制性记忆”的推行和“主导性话语”的贯彻;而民众记忆是草根社会、草根力量通过自己的记忆系统,如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口头传承、民间风俗仪式、文字记载等来突显自身价值[16]。从社会影响力看,精英记忆显然具有其控制性优势,但民众记忆也有其策略性的选择与应对。 对于精英记忆,人们有不同的态度,或强调其在民族国家认同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性,或批判其在民族国家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主宰性。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和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精英记忆受到了更为猛烈的抨击。有学者指出:精英记忆是经过精英阶层精心修饰的、上升为有意识的、理性的部分,符合的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特定利益集团的愿望和要求,投射出的只是一个非现实的、理想的、虚幻的民族文化自我镜像;而民众记忆则是历经千年之久积淀的民族文化记忆,尚未经过精英化、理性化,保持着比较纯洁的地方性文化身份标志。“尽管这是一种不成系统的、感伤的、怀旧的、零星的文化记忆,但它们却来自民族记忆的深层,积淀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还残留着些许原始的‘灵氛’。”[17] 著名学者易中天在论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时曾指出:是“精英”主宰“大众”,还是“大众”引领“精英”,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并不冲突,甚至是密切相关的。在实际生活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正是在同化与异化中共同进步与提高的,谁也离不开谁,它们之间维系着一条永远也割不断的“血缘”纽带。他还套用了苏轼的一句诗,引申出“欲把文化比西子”,“大众”“精英”总相宜[18]。 因此,精英记忆和民众记忆是一种互渗互补的关系。没有民众记忆,精英记忆“曲高和寡”,社会记忆难以渗透到基层,难以形成社会动员的力量;没有精英记忆,大众记忆处于分散、零散状态,难以形成民众的整体历史意识,不利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和民族力量的凝聚。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档案领域近年来不断有学者质疑“档案馆保存的是谁的记忆”,批评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了顽固的偏见,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地位。这既可以看作是对精英记忆资源保存的质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民众记忆资源保护的呼吁。 在构筑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过程中,档案工作者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和多元的目光,在重视保存精英记忆资源的同时,也要关注民众的生活史、生产史,重视民众记忆资源的收存。对民众记忆资源的收藏,不能完全归于档案馆的责任,需要动员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共同参与民众记忆资源的保存和保护。2007年,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档发[2007]12号),首次提出要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对民众档案记忆资源建设具有某种划时代意义。 社会日新月异,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预言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19]。这种自觉中是否也包含着社会记忆构筑的自觉?构筑全面的档案记忆资源体系是一个艰巨的,也许是永无止境的任务,但档案工作者应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标签: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档案与民生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工作记忆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档案管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