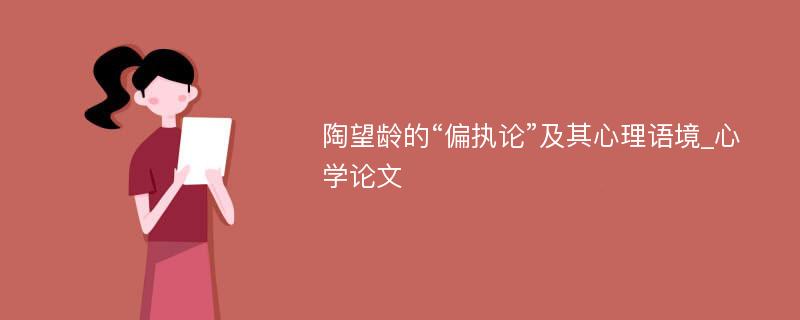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心学论文,陶望龄论文,偏嗜必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偏嗜必奇”说的提出
万历十七年,陶望龄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①与同官焦竑、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②此时袁宏道尚未登上文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周望于诗,好其乡人徐渭。作洞庭山游记,规摹柳州,近效蔡羽。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周望为眉目云。”③明万历中,以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后七子”流传下来的复古模拟风气颇盛,以至于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对于新奇有创见的作品,往往横加诋毁,视为野路。在这样的风气中,陶望龄敢于率先汰除王、李习气,并提出了一些反对复古,主张新变的文论主张。如《徐文长三集序》:“文也者,至变者也。”④《方布衣集序》:“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第242页)《门人稿序》:“予生平喜人读古书,而憎袭其语,每诮之曰‘女食生物不化耶’。”(第249页)《答求墓铭友人》:“今为传志文者,奇浮蔓延,务为备密,如画生者嘴距毛毳,件件描摹,总视反失真神。”(第427页)这些观点明确反对剽古因袭,显然是针对“七子”复古派的。他提倡写作应以一己之真“与焉”,实开公安“性灵说”派之先声。更为独特的是,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了“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之正,一时振聋发聩,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见于《马曹稿序》:
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氐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蒲,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第237页)
刘邵《人物志》有“偏至之材”的说法,《九征》篇曰“偏至之材,以材自名”,《英雄》篇称赞张良、韩信为“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⑤陶望龄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刘邵《人物志》中人物品评“偏至”之论,引入文论中,提出了“偏嗜必奇”说。陶望龄《人物志新刻引》:“刘邵《人物志》,其言九征十二流,备矣。然括其大凡,略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间杂,四曰依似。昔夫子叹中庸之为德,自昔难之,而间杂、依似,邵以为风人末流,不足具论。其于偏至之论,独详焉。盖材本人性,随性所近,谁独无至哉。虽矇瞍、侏儒、颛愚、狡贼亦有之。”(第619页)陶望龄认为刘邵《人物志》中九征十二流,已经论述很详备了,概括起来有四种:中庸、偏至、间杂、依似。刘邵在四者中最看重“偏至”。陶望龄《马曹稿序》认为屈宋以降至于唐宋的文人都是“偏至之器”。自古以来,“偏”因为不全不正,而饱受诟病。比如李翱《答朱载言书》:“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⑥李翱批评文章尚异、好理、溺时、病时、爱难、爱易者均是情有所偏,而陶望龄则反是,他并不认为“偏”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要提倡的正是“偏”。《马曹稿序》认为“偏”能尽性、达道、独造、传世。首先,“偏”能尽性。偏至之人“缘性而抒文”,所谓“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即顺性情之势而张扬之,扬长避短,将其所擅长的偏才发挥到极致。如果偏至之器,都各尽其长,则“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所以陶望龄提出“惟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其次,“偏”能达道。正如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所言:“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⑦只要能尽心尽性,则与天通。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认为正因为“偏”,“故其势充,其量蒲,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再次,“偏”能独造,“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陶望龄认为唐代诗人风格各自独造,正因为他们的性情偏至不一。最后,“偏”能传世,“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缘性抒文的结果是风格各自独造,诗文才得以流传后世。
陶望龄还提出“善魇”说,为偏嗜提供了合法依据。《书王世韬卷》认为处于觉醒之前的“善魇者”最苦,但“魇者,醒之机也。古之人盖有善魇者矣,孔曰‘愤’,颜曰‘苦’,商曰‘战’,竺乾古先生曰‘闻思修’,祖庭曰‘参’,曰‘疑’,曰‘吞金刚圈,餐粟棘蓬’,皆魇也……然则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魇;不患不乐,而但患其不愤不苦不战。苟愤矣,苦矣,战矣,安有不能转而乐者。至是方为真乐、常乐、永绝苦因之乐,而非睡梦之乐也。”(第371页)这里“愤”、“苦”、“战”均是偏至之情,但又会转化为真乐、常乐、永绝苦困之乐。这既将偏嗜与觉醒之乐相联系,又为“诗穷而后工”这一诗学命题,提供了心学上的依据。明代申时行《织里草引》:“尝闻之诗必穷而后工,尚矣,顾其牢怪沉郁,佗傺不平之怀,蓄而时发,不入于怨诽,则出于愤激,虽有偏至,终乏大雅。”⑧申时行认为诗穷而后工虽有偏至,但乏大雅,在认识上不及陶望龄深刻。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认为黄庭坚“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⑨胡仔初步认识到“偏”有独造之妙,然他并未明言“偏”字。可以说,首次系统地从诗学上为偏奇张目者,正是陶望龄。
二、偏奇与圆美之关系
南齐谢朓评诗时提出“圆美”的标准。《南史·王筠传》:“谢眺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⑩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引《王直方诗话》:“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及《送欧阳弼》云‘中有清员句,铜丸飞柘弹’。盖谓诗贵圆熟也。余以谓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不失于二者之间,可与古之作者并驱。”(11)王直方是北宋江西诗派中人,他认识到圆熟多失之平易,而老硬多失之干枯,介于圆熟、老硬之间,就可以与古人争锋。对于奇与平、偏与圆的认识,陶望龄则往前推进了一步。从尽性出发,陶望龄提出“偏嗜必奇”,亦从尽性出发,他一反“奇平”之分,大倡内外之别,提出了“不平不足为奇”的观点。《登第后寄君奭弟书》:
今人不晓作文,动言有奇平二辙,言奇言平,诖误后生,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内外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中陶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涛,奇者以江河风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双目两耳,人曰此奇丽也,岂有二哉?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老杜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陆平原云:“谢朝华于既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难哉。”自古不新不足为文,不平不足为奇。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第431页)
陶望龄反对将“平”和“奇”截然分开,他认为辨别文章好坏的标准是“内”与“外”。只要是“自胸膈陶中写出者”,不论是奇是平都是美好的;相反,“从外剽贼沿袭者”,不论是奇是平都是伪劣的。陶望龄指出人们将江河波涛汹涌和风恬波息都称为奇景,西施与常人一样都是双目两耳,人们称其奇丽。因此,奇和平“岂有二哉”,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在陶望龄看来“不平不足为奇”。《甲午入京寄君奭弟书》:“文之平淡者乃奇丽之极,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厌平淡不为,政是不能耳。来书云,心厌时弊,思力洗之,甚善。但不可失之枯寂,恐难动人目,此是打门瓦子,亦不可大认真。切忌舍奇丽而求平淡,奇丽不极则平淡不来也。”(第432页)陶望龄认为文之平淡是奇丽之极,求平淡不可失之枯寂,否则不能动人;奇丽又是打门的瓦子,舍奇丽而求平淡,则平淡不来;只有奇丽至极,才会有平淡。
在对奇平的认识基础上,陶望龄对偏奇与圆美的关系有进一步论述。《序马远之秦淮草》:“法书家之妙,在运腕状之如漏痕沙画;歌之妙,在转喉状之如串珠,皆言其圆也。昔人称好诗如弹丸,又言廿字诗如二十贤人,夫句栉而字比之,靡不圆美者,而后摹难状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旨于词外。诗而不圆,如书偏锋,歌曲而直嗓者耳。余尝引以论诗,古文若时义其佳处类然。”(第252页)他提倡偏至之奇,又认为偏奇要与圆美相结合,“偏而不圆”则亦为一病。《汤君制义引》:“文有意到,有语到,古之人盖亦有意至而语未至者矣,夫了然于心胸之间,而词不能宣,故繁而不约,偏而不圆,繁似博,偏似奇,凡博与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第250—251页)他称赞汤君:“宛陵汤君之于举业,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划磨,无粉泽脂膏之态,约而能圆,其意与语,可谓近之矣。观者将以为浅易,与以为艰深,与世有苏子当自能辨。”(第251页)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陶望龄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所谓偏而圆,就是要奇得自然。《登第后寄君奭弟书》所谓“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第431页)即是此意。陶望龄所谓的“自然”带有较强的心学色彩,强调的是“自胸膈中陶写出”。王阳明认为“心”是最高的本体,《答顾东桥书》:“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2)《答季明德》:“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3)陶望龄深受王学影响,亦以心为本体,他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来谈论“自然”的。钱振锽《谪星说诗》“良知之浅语则曰‘自然’”,“奇须从良知上出,从格物上出,方是真奇”。(14)这种观点若用来注解陶望龄“偏嗜必奇”的心学语境,甚为恰当。
三、“偏嗜必奇”说的心学语境
陶望龄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涉猎,其中儒家心学思想对他影响最大。《明史》说他“笃嗜王守仁说,所宗者周汝登”。(15)对于王阳明,陶望龄给予了最高评价,《海门文集序》:“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第223页)他对王阳明、王畿推崇备至,认为他们道术大明,且文学也妙乎一世,是明兴二百年来唯一可与前代相抗衡的代表。《旴江要语序》描述了王阳明后学的情况:“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第223—224页)心学由王阳明(新建)传与王艮(心斋)、王畿(龙溪),王艮、王畿并称为二王;王艮传罗汝芳(近溪),王畿、罗汝芳又并称为二溪。周汝登受业于王畿,而陶望龄则受业于周汝登。《海门文集序》:“望龄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受教最久。”(第223页)周汝登对陶望龄的心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周海门先生》:“望龄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动逾数年,而见处未彻,信力未充,日夜忧念,未有安歇。重荷垂闵蒙蔽,意将拯而引之,自惟钝昏,无以为地,每念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征诘,盖将令之刳肠剖脏,发露病源,投以神药,敢自匿瑕恶,仰孤盛心。”(第402页)可见陶望龄对于周汝登授他心学的感激之情。
在心学思想影响下,陶望龄认为道即是心。《尧舜以来相传之意》:“为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第444页)《圣学宗传序》认为儒家对道有不同的描述,但都归于心,“万途宗于一心”,“道州状之以太极,河南标之以一体,在子静乃立其大,在敬仲则号精神,在姚江为不学不虑之良,在安丰为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异名也”(第219页)。周敦颐所谓的“太极”,程颢所谓的“一体”,陆九渊所谓“大”,杨简所谓“精神”,王阳明所谓“良”,王艮所谓“物”,都是“心”的别名。《重修勋贤祠碑记》:“是道也,尧谓之中,孔谓之仁,至阳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徽称乎。诏之以中,而不识何谓中,诏之以仁而不识何谓仁,故先生不得已,标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图绘也。犹不识火而曰炎也,不识水而曰湿也。”(第321页)儒家之道的命名,尧称之为“中”,孔子称之为“仁”,王阳明称之为“良知”,陶望龄认为,所谓“中”、“仁”、“良知”均是心的徽称和图绘。
禅宗之道,在他看来也是“心”。《永明道迹序》:“禅宗指决,唯心无他。”(第229页)《净业要编序》:“记有言,人者天地之心。则今所谓世界者,岂非吾心为之耶?曰:然。曰:心土一也。心净,土净;心秽,土秽。”(第228页)《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认为,王阳明辟佛“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王阳明是“真有功于佛者”(第436—437页)。禅宗强调悟,利用禅宗的悟,有助于体悟诱导良知,所以不少儒生为了体悟良知而学禅。《与我明弟》:“人但生处熟些子,熟处生些子,自然合辙,大慧老人断不欺我,吾辈心火熠熠,思量分别,殆无间歇。”(第420页)陶望龄运用宗杲禅师所谓“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的思维方式来明心见性。《圣学宗传序》:“譬诸天王正派,非崔、卢、王、谢之可伦,济渎孤流,虽袱地经川而难混,远寻脉络,若渗枯漉血,祖祢必通,妙协枢机,如握节挟繻,远近斯契,此岂有异术哉?以心传心而已。”(第219页)对于儒家道统的传承,陶望龄用禅宗“以心传心”来解释。
道家之道,在陶望龄看来依然是“心”。在《解老》、《解庄》中,他用“心”来阐释老庄思想。《解老》:“今所谓天下者何始乎?知其所始,则得其母矣。得其母,然后知万事万形,皆心所生,而无非心也。安有知子而不复守其母者乎!”(16)陶望龄对《老子》五十二章“天下有始”的解释,正是从“心”入之,他认为“心”是万物之始,是老子所谓的“道”。《解庄》释《齐物论》:“受成形则物我立,师成心则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识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真心曰真宰,妄心曰妄宰。迷真心而后认成形,受成形而后有成心。此是非之窠窟,众论之根苗也。”(17)释《人间世》:“虚一者,师心而强为者也。”(18)释《大宗师》:“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师未成乎心者也。不特生死去来是其影像,仁义礼乐是其名件。”(19)这些都是陶望龄用心学思想对《庄子》的解读。
基于儒释道三家之道的内涵都是“心”的认识,陶望龄强调纵心,《圣学宗传序》:“纵心,皆活泼泼之地;举目,即斯昭昭之天。”(第220页)正是在“纵心”的心学语境中,他反对文章模拟,强调偏至之奇。《方布衣集序》:“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第242页)《阳辛会稿序》:“文如画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犹可匠心。率意而为,逮心蒲意,极而至矣。惟画而貌人,文而经义,则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于人之面与书之题,不蒲不极,则弗能善。”(第248页)率意为文,力求逮心满意,力求极而至,这就是陶望龄所谓“偏至”的意思。
四、“偏嗜必奇”说与晚明尚奇文论
针对复古模拟之弊,晚明文坛出现了一批崇尚新奇的文论。李贽《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高呼“天生我辈必有奇”,《读律肤说》又曰“古怪者自然奇绝”。《杂说》认为真正奇文是真性情积蓄爆发,是“心中之不平”的发泄,所谓“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20)这描述的是奇文产生的心理状态。袁宏道《答李元善》:“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21)袁宏道反对复古,他的“新奇”观,内则提倡“独抒性灵”,外则提倡自然趣韵,这实际就是唐代张璪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意思。(22)汤显祖《合奇序》指出奇文出于自然灵气:“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23)他批评“拘儒老生”步趋形似,一味模拟复古,毫无个性。上述尚奇文论均受到心学的影响,李贽受学于王襞,又从罗汝芳问学;袁宏道受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的影响较大;汤显祖则师从于罗汝芳。他们的尚奇文论与陶望龄“偏嗜必奇”说有着共同的心学语境。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强调抒写性灵,追求新奇独创,在晚明掀起了一股文学尚奇之风。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在前代未之有,在明代文论中也独树一帜。晋代葛洪《尚博》:“偏嗜酸咸者,莫能识其味。”(24)葛洪认为偏嗜者不能识味而加以否定。陶望龄对偏嗜有新解,他以心学中的纵心、尽心思想为依据,对“偏”与“全”有更为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在晚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晚明士人对“偏”有了全新的认识。李培《闽游草叙》照抄陶望龄此说,曰:“诗文随世运升降,窍人性灵,抒于才情。无诗文则无性灵,无才情矣。然才情有全至,有偏至。学者患不偏至耳。偏师必捷,偏嗜必奇。三百篇得其全而称经,唐人得其偏而后世莫及。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沈舒促,称淡悲愉,固已判若苍素,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浅而惧入,郊、岛唯恐其不入;韦、沈冲而惧尽,藉、建唯恐其不尽;温、许冶而惧稚,卢、刘唯恐其不稚;韩、柳亢之以诘崛,长吉探之以幽险。而其浅也,冲也,冶也,与夫入焉,尽焉,稚焉,诘崛而幽险焉,各成偏至云。尔不知偏亦全也,世运才情不得不尔也。”(25)从上述表述来看,李培基本上是复制了陶望龄的“偏嗜必奇”说。李培《修上虞县志节略》对偏至之词复有称赞:“夫风水为文,云汉为章,自昔尚之。而贵不言而躬行者,往往訾为空谭,不知无文不远,言亦胡可少也。无论载道者,即偏至之词,犹足宣泄精英,而辉映宇宙,千载之下并称不朽,傥谓文无用也者。”(26)李培认为偏至之词宣泄精英,可称不朽。缪昌期《评新唐书与两汉文章何如》:“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郁积于中,而后奋之于笔,故身可杀,名可污,而笔不可夺。虽其独出手眼,不无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27)缪昌期也将“偏至”与“不朽”相联系。张大复《城南唱和诗序》认为“性偏至则奇”,(28)陈仁锡《侍御顾公暨配黄孺人合葬传》认为偏至“能动天地,开金石”。(29)方以智《东西均·全偏》:“合并诸偏,偏亦不偏矣。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世遂以公全不如偏精,井蛙耳”,(30)亦为“偏”正名。
综上,陶望龄“偏嗜必奇”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陶望龄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突破了儒家中和之美的局囿,推动了晚明文学尚奇之风的形成。
注释:
①参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12—5713页。
②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22页。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23页。
④陶望龄:《歇庵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⑤刘邵:《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1页。
⑥《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1页。
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⑧申时行:《赐闲堂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13页。
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8页。
⑩《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页。
(11)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12)(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5、214页。
(14)钱振锽:《谪星说诗》,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05页。
(15)《明史》,第5713页。
(16)陶望龄:《解老》卷下,明陶履中刊老庄合解本。
(17)(18)(19)陶望龄:《解庄》卷一、卷二、卷三,明天启元年茅兆河刊朱墨套印本。
(20)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0、370、272页。
(2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6页。
(2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3)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78页。
(24)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杨明照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6页。
(25)(26)李培:《水西全集》,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88、160页。
(27)缪昌期:《从野堂存稿》,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82—183页。
(28)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29)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30)方以智:《东西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