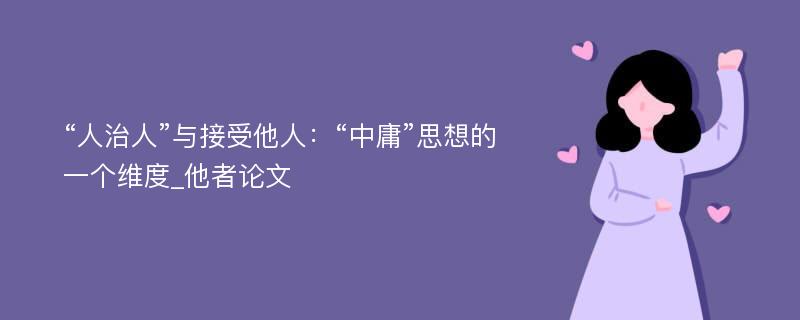
“以人治人”与他者的接纳——《中庸》思想的一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与他论文,中庸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2-0056-06
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成为论题的总是自我,自从莱维纳斯以后,他者的问题就成为现代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接纳他者的问题萦绕在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思想家们(如德里达、哈贝马斯等等)的心灵深处。中国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能否提供一种资源,从而改变以自我为中心而忽略他者的人文景观?在这个背景下,打开《中庸》,似乎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
一、从”道不远人”到“以人治人”:他者问题的呈现
在《中庸》中,承担中庸之道的主体是君子,在某种意义上,中庸之道首先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展开为世界的当下接纳,而世界在具体的个人那里,首先打开的往往是那个人与人之间的维度。正是在这个维度中,我们经验到作为个体的自我以及同样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他者。当《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①时,这里的“人”就同时包含着自我与他者。
“道不远人”,道即于人而见也。天下之人,人也;己,亦人也,即此而道在焉。②
日常生活中的当下活动,往往同时也是自我与他人遭遇、交接的活动。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人类的事务,乃是将自我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活动。但正因如此,我们当下的事务,既可能是接纳他人的方式,也可能是拒绝他人的方式。如果当下的事务成了拒绝他人的方式,那么,也就同时拒绝了世界。因为,对于此一当下事务而言,世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通达中开启自身的。所以,在当下活动中,接纳他人其实也是世界的当下接纳的具体方式。
但我们如何才能在当下接纳他人,从而接纳整体性的世界境域本身呢?在第十三章中,《中庸》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砍伐木材作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砍伐者手头使用的这把斧头之中,二者具有相同的原理;但即使这样,手头的斧柄与即将作成的斧柄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斧柄。即将要制作的斧柄的大小、长短、粗细以及斧柄插入斧孔的方式等等,都不能由手头已经在使用的这一斧柄来决定,而是由所要砍伐的木材自身的质料实际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斧孔的大小、深浅等等才能得以确定。因而,即将要制作的斧柄的实际法则就存在于它自身之中。与此相应,在当下事务中得以聚集的自我与他人,固然都可以展现人性的可能性,但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展现方式。他人存在的法则,就在于他人自身,并不能由我或其他存在者的法则加以替代。从我的角度创立的法度搬运到他人那里,就会发生与他人不相应的情形。
因而,在当下与他人交接之时,“以人治人”才是接纳他人的唯一的方式。而所谓“以人治人”,也就是朱熹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③
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在我的当下活动中,他人能够以他人自己的的法则来治理他自身。换言之,在当下接纳他人,意味着在我与他人交接的当下,自我后退一步,空出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人可以他本人的方式治理自身。
因而,作为君子,当他以自己的方式打开中庸之道时,他没有理由要求他人都以他的那个方式,也即以君子的方式打开中庸之道。士人不能要求民众以士人的方式打开中庸之道,上根之人不能要求中根之人以上根之人的方式来生活。因为,一旦那样,要求本身就超越了他人的知行范围之外,不能真正落实,而只能以难以企及的理念、话语等方式虚悬地存在。
君子有鉴于伐柯以为远也,而以推之于治人之道,就人之所可知者使知之,其不可知而不知也,然后施之以法;就人之所能行者使行之,其能行而不行者,然后督之以威。故但纳之于饮、射、读法之中,申之以悬法、恂铎之令,导之以孝弟力田之为,能革其习俗之非,以尽其愚贱之所可为,则君子之教止于此矣。仁期于必世,而礼乐待于百年,未尝以君子自尽之学修,取愚氓而强教之也。由此观之,则夫人之可知可能者,即治人之道,是天下之人皆道之所著也,而岂远乎哉。④
不是以自我去要求他人,而即是在他人之所与知与能的当下,去引导他人获得那个立足于他人自己的生活法则。而自我呢,在与他人交接的过程中,同样也努力保持那个立足于自己的那个法则,而不是让他者替代自我。在自我的当下所为中,自我与他人的差异性必须被保证。
这是自我与他人的法则同时在场的过程,在我当下的活动中,由自我所确立的法则治理自我自身,这一法则同时保证了他人自己的法则的同时在场,由此,在我当下的活动中,自我抵达了自我,而他人也获得了抵达他人的可能性。可见,“以人治人”包含着他人与自我的同时接纳的可能性,这里既不存在为了他人而奉献自我的宗教性教义,也不存在为了自我而牺牲他人的极端利己主张。既然道不远人,道体不仅流行在自我的当下,也见端于他人的当下,所以,修道的君子就要在当下同时保证自我与他人的同时接纳,而接纳他者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他人作为他人自身的可能性之中。
二、接纳他人同时也是向着他人世界开放自身
接纳他人,并不仅仅意味着在自己的世界中给他人一个位置。如果世界的显现在每个人那里都是不同的,甚至对同一个人而言,在不同的时刻也是有差异的,那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人那里,也有着不同的世界。这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世界里,而不同的世界在其相互指引中构成了层层展开的褶皱式境域总体。接纳他人,其实也就意味着接纳他人的世界,向着不同的世界开放自身。尽管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论了一整天,也许这些谈论并没有使他们进入一个共同的世界,以至于他们依然处在各自的世界里;也许一个当下的注目,或一个会心的微笑,就当下地沟通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打开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关于世界,德里达有一段话耐人寻味:
任何人都无法证明两个人居住的是同一个世界,无法证明人们通常所指的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世界可能有许多个世界,谁能向我们保证只有一个世界?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世界,还没有,或许永远不会有。当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刻,我们对某一个人充满怒气,而有时是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轻率地、单纯地、温柔地、粗暴地称作自己人,或者亲人的人,在我们之间,在与我们分享一切的人之间,哪怕是与我们分享爱的人之间,我们生活在其间的那些世界也是多么不同,彼此难以辨认、难以置信,彼此毫无相似或相象之处,彼此不可同化、不可转让、不可比较、不可共享的情形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而我们知道,不可否认地、固执地知道,那是不可分享的深渊,我的意思是,我们彼此像被大海深渊分隔开的岛屿,深渊以外无边无岸,我们不能指望从那无边无岸的深渊以外得到什么,横在这些无法沟通的岛屿之间的深渊让我们头晕目眩,以至于我们只能听到孤独的声音。我说的不是在同一个世界可以与别人分担的那种孤独,而是没有一个共同和相同的世界的孤独,换句话说,是那种不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孤独感、孤立感、岛国状态。然而,我们应当承认,这个不可逾越的距离,至少在一个“仿佛”的时空中,却可以被语言和对话轻轻跨越。⑤
世界或共同世界的退隐,是作为在世者的人们随时都面临着的一种可能性,在今日,相对于世界的当下开启而言,共同世界的退隐的可能性更具有可能性。没有一个共同世界甚至是无世界性的孤独感,与公共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构筑了晚期现代性的主导的存在景观。⑥
但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人们仅仅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而没有各自的世界,那将是同样的可怕。无世界的孤独感与没有自己的世界的存在状态,同样都可以成为极权主义统治的策略。因为,一个从各个方面都被结构、被决定的世界,恰恰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原型,而那些将人们分割在不同世界中以至于不相往来,也正是极权主义所建构的那个“共同世界”正当化的基础,也是它到来的准备,而极权主义的到来恰恰伴随着每个人各自的世界的剥落。因而对于具体生命而言,立足于自身的世界,向他人的世界开放,并在不同世界的相互指引中抵达作为境域总体的共同世界(天下),由此而得以在这个最终意义上是共同的世界中筹划自己的个人世界,实际上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为坚实的个人基础。
通过“以人治人”的原则,《中庸》赋予了每个人自己的世界的正当性。个人的世界具有他人所无法穿透、抵达的幽暗性质,它意味着一片永远无法澄明的黑暗地带,它自身将自身带入隐藏着的遮蔽状态之中。就在个人的世界向他人的世界的开放之中,这种自行的隐藏也同时发生。或许,正是这种自行的隐藏使得向他人世界的开放成为可能?即使与他人的世界相交,即使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相遇,即使作为境域总体的共同世界得以打开,个人的世界也还是得以保持着。一旦这种保持不再可能,那么,共同的世界的打开、向着他人世界的开放,都将不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向着他人的世界开放自己,或者站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打开他人的世界,都必须尊重那个在各人那里同样自行隐蔽的世界,而那种在透明的、光亮的、没有黑暗的理想中相互抵达彼此的世界,总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梦想,它既不能抵达自己的世界,也难以抵达他人的世界。对一个能够理解自我、毫无隔阂地进入自我的世界的他人的期待,总是一个奢望,相比之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⑦则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加以把握的要求。即使相互之理解的发生,总是姗姗来迟,总是稍纵即逝,但对他人及其世界的接纳,在自我这里,也是可以实实在在加以把握的。
我如何在当下之活动中同时打开接纳自我与接纳他人及其世界的可能性?《中庸》向我们显示,不是其他,而是忠与恕,为之提供了真正的基础: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⑧
分而言之,忠是尽己的维度,恕则为他人在我的当下所为中作为他人自身而被我接纳打开了可能性。
所谓尽己,也就是充分地实现自我,因而“忠”要求我们走向自我与自我的通达,因为我们的当下所为未必能敞开自我,也许恰恰是封闭自我的方式。例如,当我们绝对地依附于他人,例如君主时,我们就失去了忠的可能性。忠于君主,不是绝对地服从、顺从君主,而恰恰是在面对君主时,同时打开自我,与君主交接的活动,同时成了打开自我的活动时,才是尽其在己之忠。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地忠实于自己,充分地尊重并实现自己,这就是尽忠的首要的含义。所以,王夫之认为,忠意味着“躬行心得之实”,“以尽其心之所安”。⑨这意味着,在君主面前,臣之忠就在于直接面对着来自内在良知的裁判,以这种裁判作为准则处理与君主的关系。由此,能够根据自己的真正所见、所想、所思对于君主的行为提出批评,也即能否直谏,在古代往往被视为忠臣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如下的表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⑩事实上,“忠”在字形上“从心,中声”,这意味着它是内在心性的直接的、自然的流露,故而,贾谊《新书·道术》云:“爱利出中谓之忠。”当爱利从内心流淌出来而达于四肢百体的时候,这意味着内外之间相互通达、没有隔膜阻遏,心尽于身,身达于心,身与心在当下的活动(如与他者交接的时候)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正是这种和谐与平衡保持了生命对自身的那种由衷的礼敬之情。许慎在《说文》中以“敬”释“忠”,的确有所见地。
而所谓“恕”则意味着“如人之心”,也就是以人观人,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设想他人,用《中庸》自己的语言来说,“恕”意味着“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这就是所谓的“推己及人”,从自己出发,接纳他人,而所谓接纳他人,在这里表现为给他人也预留一个“忠”(尽己)的可能位置。这样,在“恕”中所发生的就不是自我之“忠”,同样,还带出了他人之“忠”的可能性。因而,“忠恕在用心上是两件工夫,到事上却共此一事。”(11)但通过“恕”而获得的他人是否只是自我的移位?或者自我经验的变相的建构?而不是真正的他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他人的接纳难道不是自我的接纳的扩展或补充形式而已?因而也就是变相的拒绝他人的方式而已?《中庸》并没有要求自我通过认知的方式而抵达他人或绝对陌异性的他者。与人类所置身其间的世界总体一样,他人的生命中也包含着自我所不可测知的维度,一个永远无法澄明的幽暗地带。当我们说我们已经完全地理解了世界与他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拒绝世界与他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生活在自我的自负之中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接纳他人,接纳世界,在消极的意义上,其实只是意味着自我来到自身的边界,止于而不去跨越这个边界。然而,抵达这个边界,却不是通过自我本身的视野来实现的,而恰恰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那个“之间”的地带。事实上,“恕”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之间地带。在《说文解字》中,我们看到,“恕,仁也。”马叙伦云:“古书多借仁为恕。恕实仁义之仁本字。故此训仁也。”(12)而“仁”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恻隐之心”的同情感的仁,打开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维度,这个维度固然显现、作用于此一个人与彼一个人之间,但同样也是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个人生命之中的维度。自我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到人与人之间的地带,意味着他在展开每一个作为之前从这个之间的维度去构想,如果这个作为由他者作出,而达到自我这里,那我将会怎么样?由这个到来的所为而带给我的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自己不能接受这个所为,那么我就也应该收回这个所为,不让它施展到他人那里。这是基于同情(共通感)的考量,而不是剥离了情感的认知,正是这种共通感的促动,才引发了那个“之间”的维度,以及为他人预留位置的可能性。这样,就不难理解张载所说的话:“忠恕者与仁俱生。”(13)
三、在日用伦常中接纳他人及其世界
对他人的接纳展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维度,这个维度为彼此的各尽其己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维度不是抽象的,而是展开在人伦或伦常生活中。每一个个人在某一个时刻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而由这个位置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自我如此,他人亦如此。自我所经常与之相遇的他者,总是各种伦常关系中的他人,因而,接纳他人,不能脱离伦常关系形式来进行。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14)
在这里,被道及的是四个最基本的伦常关系维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进入这些维度的他人分别是父亲、君主、兄长、朋友。而修道的君子以何种方式接纳他们呢?作为儿子,在他的当下之所为中,父亲是否得以可能作为父亲而进入其之所为,或者更准确地说,修道的君子是否在其当下的所为中,将自己真正保持在“子”的位置上,从而也为父亲在此当下以父亲的方式而存在预留了位置?换言之,父父子子,并不能完全由儿子一人来承担,而是由父子二人共同抵达的事情。但就作为儿子的自我本身而言,“父父”或“父不父”并不是他的考虑、作为所能抵达的结果,但是保证自己的“子子”,却在他力所能及的畛域之内,而且也是不可推卸的。儿子以儿子的方式面对父亲,他也就同时在他当下所为中接纳了作为父亲的他人。对于儿子而言,作为父亲的他人是否来到自己的生活中,需要自己打开一个“空—间”,一个空去的“位置”,一个可以让他人作为父亲抵达这里的处所。同样,我是否真正打开了“位置”,从而可以让君主、兄长、朋友等等都在当下抵达我的生活世界,从而我个人本身也得以成为真正进入伦常中的个人?
显然,对于《中庸》而言,那些在不同伦常位置上与自我当下交接的他人,也只有在伦常中才得以真正作为他人而进入自我的生活世界,伦常不仅是对自我的自我性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人的他者性的肯定。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伦常行动中,自我抵达了一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将自我保持在某种不可能的界限之中,这个界限为生命以及这个世界中隐藏着的某种东西的存在提供了不言自明性。因为,一个基于伦常的回答其实是对追问的限制,追问与怀疑在伦常中都不再有意义,父父子子不存在何以必须如此的正当性的理由,何以如此的正当性追问只是在伦常生活退隐以后才面临的课题。在伦常的真正展开的过程中,没有哪一个自我被单向度地突出。相反,在平平淡淡中,伦常确立了相互作用的两极,通过在两极之间的“礼尚往来”,作为“此在”的自我发现了相异的“彼在”。
如以朋友一伦为例,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伦常的意义。
《礼记》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的双方只有在平平淡淡的交往中,才保持了持久性的友谊;往而不来与来而不往都可能导致友谊的中断,而往来之间也必须保持着那种给出“彼在”的平淡,才能抵达朋友之谊。此中平淡,正如于连所说:“诸物的平淡呼唤内部的解脱:在我们之中导致可感的极限,在可感物消失和解除的地方,平淡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彼在’。”(15)只有在发现了“彼在”的时候,也就是将被我们称之为朋友的那个人作为“彼在”来看待、来尊重的时候,朋友才得以在“此在”这里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伦的朋友意味着一种来自作为朋友的“彼在”但又不是由“彼在”个人发布的要求,(16)而“此在”在对此一要求的回应中接纳朋友。也许一个人不懈地回应这种要求,但身边与之交接的“彼在”却不能回应这种回应,因而他身边也就还是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的孤独,没有相互通达的世界的孤独,也许在当世都无法克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也许是“百年孤独”者,甚至是“千年孤独”者,他不得不在百年或千年之前的时代寻找自己的朋友,例如“尚论古之人”的孟子就是一个百年孤独者,他在一百多年前的孔子那里才发现自己真正的朋友。当然,也许一个孤独的人,他的孤独甚至无法以年份来计算,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不在过去,但也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出现,“他还没有面世,我就因他而退下,先他一千载,我已经虔恭于他的精神。”(17)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不是容纳现有之“此在”,不是任意、任性的“此在”的一个接收者,而是将“此在”纳入到朋友的伦常要求中,因而,在严格意义上,朋友无论是对于“此在”,还是对于“彼在”来说,都是在“此地”抵达远方的一个收获过程。因而,朋友,真正的朋友,总是在到来之中,不管他是来自遥远的过去,还是不可测度的未来,还是面对面的当下,“此在”必须为其到来而准备,相对于朋友的到来而展开的先行准备,这是作为伦常的朋友之道的要求,当然也是在到来的朋友之间抵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论语·学而》第一章与我们的论题之间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生得一知音、知己足矣,读书学习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上失散的朋友,它是为远方朋友的到来而作的一种准备;尽管君臣、夫妇、父子、兄弟等等日用伦常赋予了我们种种不同的身份,但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们把这种身份都看作是在特定场景中所佩带的面具,那么,这些伦常的身份并不能阻碍或掩盖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便是在不同伦常关系下的两个个人在尽其伦常关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朋友——好兄弟总是朋友;好夫妇相敬如宾,如同朋友;好的君臣也是朋友;正如好父子也可以保持朋友的维度一样。朋友之所以成为伦常,之所以位于日用生活的最表层与最深处,正在于人与人的分离而带来的孤独,正是这种孤独可以使面对面而坐的人们生活在彼此各自的世界,以至于共同的世界根本无法打开,而朋友却是冲破自己的个人世界的一个端口,它将人们引向一个共同的世界。
而礼乐,也就是那些日用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无疑是彼此往来的媒介。日用伦常生活是在这些礼仪、仪式所开启的礼乐生活境域中到来并展开自身的,通过后者它获得了自己的“实体”形式,变成了可以实实在在加以触摸、加以感觉、具有“文—化”意味的氤氲着、弥漫着的精神氛围,换言之,成为可以通过向人们的感触能力开放而兴起、提升人性的“文—化”境域。生活在伦常世界中的个人,如何能够绕开这一伦常的世界,绕过那些礼乐,而去展开接纳他者的事业?
显然,在日用伦常生活中,虽然伦常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基的,但伦常的要求首先总是自我对自我的自向性要求,而不是对他者的要求,而这种指向自己的要求本身却表达了对伦常中的他人的尊重。“于是以其所以责彼者,自责于庸言庸行之间,盖不待求之于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则,具于此矣。”(18)
接纳他者,对于修道的君子而言,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持续展开的“反身而求”的自向性活动。这种活动将修道的君子保持在那种勤勉、笃实、一贯的生活形式中: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造造尔。(19)
子、臣、弟、友,乃是日用之伦常,即使是最普通的生命也有所与知、有所与能的“庸德”与“庸言”。修道的君子在这最日常的庸德与庸言中自尽其己,致其身于父、君、兄、友之前,以子、臣、弟、友之道责任其身。这就把日用伦常的活动转变成了个人的道德要求,也就是一种不断地自我更新的收获过程,这一过程在言语与行动的相互照看中打开自身。
注释:
①《中庸》第十三章。
②王夫之《四书笺解》卷二《中庸》,《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35页。
③《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④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三《中庸》二,《船山全书》第七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36页。
⑤引自陈力川《德里达的最后一课》,《跨文化对话》第17辑,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⑥阿伦特曾经谈及,在今日的大众社会,人们之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如同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们不再彼此分离,但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⑦《论语·学而》。
⑧《中庸》第十三章。
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230页。
⑩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92页。
(1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中庸》,《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498页。
(12)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八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71页。
(13)《张子全书》卷十二《语录》。
(14)《中庸》第十三章。
(15)这是弗朗索瓦·于连《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1991)所表达的思想,参看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6)因为“彼在”存在着还没有进升到作为朋友的“彼在”的可能性,也许甚至这种可能性是永久的。
(17)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这一句话,很可能显示出,在他的意识中,符合他所界定的自己的朋友,在一千年内可能都还不会出现。当海德格尔以他的这句话作为自己维塞尔访谈的回答时,他可能是在期待,他的朋友,能够肩负起他所说的准备着的思的朋友,也许要到千载之后才能来临。与此相类,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有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
(18)《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4页。
(19)《中庸》第十三章。
标签:他者论文;
